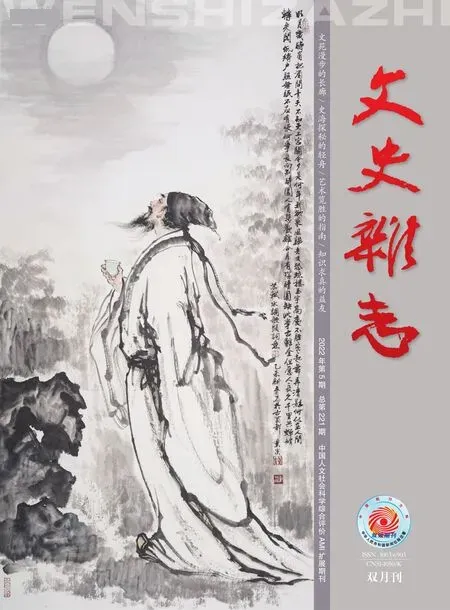方孝孺的谱牒思想与乡村自治设计(下)
江苏 赵映林
三、方孝孺提出的宗族制度乃为乡民自治
(一)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体系
明代从立国之初,就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政权。
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家如何对这片广袤的土地实施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如何使中央政府的政令畅达于四面八方?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制,即史家和政治学者所说的封土建国或封邦建国,通过封土建国解决控制与管理。中国呢,是否例外?根据历史记载,也没有脱出这一制度。《左传·桓公》中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这就是中国西周时期封建制的形态,通过封建制控制天下。通俗地说就是分封诸侯,建立国家。
天子所统治的地区就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活动范围,称之为“天下”。至于这“天下”究竟有多大,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对“天下”的统治就是通过封土建国实行的。把“天下”分成若干地域,不就好统治了吗?
通俗地讲,就是周天子把自己居住的以王城为中心的地区划为“王畿”,王畿之外是层层叠叠的各级地域,即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兄弟亲友功臣作为诸侯建立国家,使之各自统治一块地域,这就是“国”,俗称诸侯国。如齐、鲁、宋、晋、郑、吴、越……天子之位是世袭的,由直系血缘的嫡长子继承,诸侯国的王位也是世袭的,也是由直系血缘的嫡长子继承。诸侯又把自己居住的国都以外的土地分封给卿大夫立家(这些土地称为“采邑”),卿大夫又把采邑中自己居住使用的那部分土地之外的土地再分封给士。如此这般的分封,形成“天下—国—家”三个基本的地域层次,这就有了四书中的《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分封制所形成的地理背景;相应地在政治上就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民”这样的等级制。
所以,封建制的主要特征是将土地的授予和人连在一起,这就奠定了封建等级制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以此观之,中国的西周是典型的封建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后,行政上确立了郡县制的管理体制,封建制就退出历史舞台,全国行郡县制。汉、西晋、明的分封制虽有原因,也只是历史的部分回光返照;再说明代还不是全盘照搬。
但是,郡县制只是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县级)的制度框架,县以下怎么治理?中国古代广大的农村,从封建制退出后,已完全形成了私有制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朝廷的治理触角很难伸到基层;即使能伸到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可以支撑对广大乡村的治理。同时,广大乡村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力量,这就是家族所拥有的族权,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族社会。一家一族长期居住一地,几无迁徙,早已形成一套自我管理体系。这套管理体系,约定俗成,很难打破。
但专制主义的一大特点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封建制逐渐瓦解的过程中,最早在秦国献公时就开始了对乡村的治理体制的改造,将全国人口编为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单位,称之为“户籍相伍”。经商鞅变法再到秦统一全国后,乡村基层治理体制基本成型,形成了乡—亭—里三级制的治理模式。这套模式渐为历代所继承。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名称叫法偶有不同而已。
(二)明初的乡村治理体系
明朝建立后,完全沿袭了历代乡村的三级治理模式,即乡、里、甲三级模式。方孝孺居住的“缑城里”的“里”就是明初的乡村基层组织,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虽然在广大乡村实行了三级治理体制,有了保甲制(有的称什伍制、里甲制、乡绅制),但在基层治理中最起作用的主要是里长和乡绅。按照规定,方孝孺也轮值做过一年的缑城里里长。
明初乡以下组织的形式是里甲制,以110户为一里,每里设里长10人,由丁粮多的10户轮流担任,以一年为期;其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每甲每年轮甲首一人管理一甲的事务。由于里甲制后来逐渐变为专管赋税徭役的基层组织,乡里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管理就成为保甲组织的专项职能。
每里设“老人”,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任的,得由年高(50岁以上)有威望者担任,“导民善,平乡里争讼”。刘邦入关中,“召诸县父老豪杰”。这“父老”就是秦王朝时期乡里的“民官”,又叫“三老”。所谓民官就是有位无禄,与明王朝规定的“老人”是同一性质的,掌乡里之事,各朝各代均有。名称虽异,职责相同。这“三老”“老人”虽不是政府的正式官职,却在乡村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他们攻进陈县后,不敢自立为王,只敢称将军。过了几天,陈胜召集三老、豪杰来开会,商议事情。三老、豪杰异口同声地说:“将军身披战袍盔甲,讨伐无道君王,诛暴秦,应该以楚国为社稷,功宜为王”。有了三老、豪杰们的这番话,陈胜才敢称王,号为“张楚”。
乡里“老人”在农村之所以享有很高威望,正由于他们是皇权专制政体在基层统治的社会基础,同时又因为他们可能是族长、族中长辈,且有文化,更可能的是属于乡绅。他们是乡村社会阶层中最高的一个层级了。所以,乡里政权与族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时候在一些地区这二者可能就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乡里政权一旦离开族权,只怕会寸步难行。
乡村中这种里甲基层组织是我国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拥有按照户口督催赋税、摊派力役、宣布教化、维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职能,被称之为“治民之基”,受到历代专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方孝孺(1357—1402)画像(选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
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乡村太熟悉不过了。所以,他做了皇帝后,对乡村治理除了上述行政组织外,还重视引导。他规定地方凡有品学兼优为地方推重者,死后可由地方要员提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以此促进乡村教化。
朱元璋还规定,在乡里建申明亭和旌善亭。申明亭专记本乡本里犯罪者姓名,凡在地方有恶迹又不够法律制裁者,皆书其名及恶迹于上。触犯法律的本乡官员也记于申明亭。这种精神上的惩戒,搞得这样的人臭名远扬,在本地抬不起头来,甚至影响到他一家人的婚丧嫁娶,也使乡邻与后世子孙有所警戒。旌善亭则记本地常有善举与为官善政者姓名,以此劝善惩恶,使乡民知道儆戒。申明亭由里老主持,里长襄助,还需负责宣讲法律诏令。
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时规定,农村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向老百姓灌输圣谕,宣讲律令。时间一年两次。正月十五与十月初一,举行乡饮酒礼时,县令主持,县里所有官员,包括教官如教谕、训导,还有胥吏、退休居乡的官员,一起到县学的申明亭,召集耆老民众,当众宣谕。谕旨是朱元璋钦定,千篇一律:“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仪式完毕,开始饮宴。
朱元璋搞的这一套,还是有点用的:凡乡里70岁以上者,都被请至台上就坐,县里官员向他们行礼以示尊重,既沟通了官民之间(主要是官府与乡绅、宗族领袖与年耆者)的关系,也或多或少起到教化的作用。因为宣读完谕旨后,县官会把养老、恤孤贫、表善良等事当众宣布,颇有点作工作总结的味道;还会宣读禁赌、禁侈、禁乱伦、禁流民、禁私自阉割等事。据永乐时出生的叶盛说,每逢“乡饮酒礼”之时,“观者如堵墙”,全城洋溢着欢乐喜庆气氛,让人感到这就是太平盛世。不过,几十年后,逐渐流于形式,也就不能起到沟通官民关系的作用了。明末时王夫之就说:“无暇顾及乡饮酒礼,以致世风日下,恶习远播”。从王夫之所说来看,乡饮酒礼在初时还是有点作用的,只不过到了后来,徒具形式而走样;所以王夫之予以了肯定。
朱元璋下令,各乡里应从里甲中推选3—10名年龄在50岁以上,有德行、有见识并为众人所敬服的老人,负责本地教化。朱元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6条被称为“六谕”。要求“父母有过,必恳告至于再三,毋限父母于危辱”,“恭敬长上”,要求“尊敬其师”等等。朱元璋搞的这一套是以乡民治乡民,含有一定程度的乡村自治性质;费用则全由乡里祠堂支出,官府可以不花一文。
(三)乡绅是乡村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所谓乡绅,就是居乡里的有功名仕宦者。它是科举制度造就的一支社会队伍,细分一下,可有两部分:乡绅上层为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退休的;乡绅下层为有“功名”而尚未取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读书人(士),如秀才、举人、国子监生。这些秀才、国子监生、举人只要不犯法,其功名是终身的,不会被革去。他们虽然不是官,但他们是官员的候补者,是“准官员”,犹如后世的二、三梯队。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官,却高于普通民众,在民之上,成为官民之间一个重要的阶层。可以说在整个国家社会结构中,乡绅是介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个阶层。缺了他们,乡村还真可能不是国家能治理得好的,至少会大大增加朝廷的治理成本。如要用今日阶层理论去套,乡绅有点类似于今天说的中产阶级。
乡绅下层中绝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官做,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传统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社会地位优越,由此获得各种权力,尤其是舆论的操控,让他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朝建立后,如前所述,由于朱元璋的重视,很快就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学校与科举制度。这套制度的直接目标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和选拔人才,但它却带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副产品,这就是使大量拥有“功名”的人士“沉淀”在地方社会。他们有文化有能力,掌握着基层社会的话语权,成为基层社会结构中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而且是一个在基层具有一定权威的阶层。

方孝孺墨迹(刘宗周题跋)
乡绅构成了地方基层社会的精英力量。只不过,在明初由于朱元璋对士人的打击,而科举制度的推行直到洪武十八年才步入定制。因而,最初他们还在里甲制度控制的秩序之内。但是乡村中的里甲长又往往是乡绅。
但总起来看,地方官对乡绅往往会礼让三分,上任之初会拜访有头脸的上层乡绅,以及乡绅下层中能力出众又有威望的士子,给足他们面子,取得他们的支持。地方遇有重大事情,很少有不听听乡绅意见而一意孤行的;因为国家政策的实施好坏与乡绅关系极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并感慨道:“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乡里基层治理得好,则能成就国家“世盛”;反之,则成“世衰”。所以州县官员无有不重视与乡绅拉关系的。这里的乡绅,主要是顾炎武说的“小官”,就是有位无禄的“老人”“里长”“甲首”一类乡村“民官”。
而乡村中这类有位无禄的“老人”“里长”“保长”“甲首”往往又是家族的族长、长辈,或族绅,这二者是合而一,一而二的。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基层行政是与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古代村落基本都是聚族而居,这是我国古代基层行政制度的一大特色。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发挥治理作用的还是家族制度。族长的权力之大,超出常人的想象力。不妨以近代的袁世凯为例,袁世凯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父亲的妾。袁世凯是小儿子,在家族中处于边缘地位。袁世凯生母去世时,袁世凯已是封疆大吏——直隶总督,还兼着北洋大臣。袁氏家族此时的族长是袁世凯的胞兄袁世敦。袁世凯想把母亲的灵柩运回河南老家项城,跟父亲安葬在一起,可袁世敦就是不同意——妾怎么能与老爷安葬在一起。袁世凯无法,只好放弃这一想法,气得发誓永不回项城。袁世凯后来削官回籍住在河南彰德,死了也葬在彰德。多本关于袁世凯的传记都讲到这个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宗族力量强大到能与政治力量抗衡。一个家族的族长能与封疆大吏对抗,而后者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中国古代在农村基层虽然有朝廷的里甲制度,但里甲长往往是由族中长者或家族中有声望者担任。朝廷的管治力量不通过宗族是毫无办法的。
当然,也有一些非本姓家族的外姓人居住在同一村落。农村中的“大姓”“小姓”的说法,反映的正是这种“杂族”而居的情况。其所带来的问题是大姓压迫小姓,此类事也是层出不穷。小姓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忍气吞声,很少敢于对着干。
(四)方孝孺设计的乡族(村社)自治制度
方孝孺的乡族制度设计除了他在谱牒学中所论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方孝孺提出乡族(村社)制度,是基于对儒家学说修治理论的认同,而重视对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家庭的认识。他重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在《宗仪》九篇的序文中,他开宗明义,指出:“君子之道,本于身,行诸家,而推于天下则。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
尧的儿子丹朱是个不肖子。当年尧之所以把帝位禅让于舜,原因即是把“家政”与“国政”结合起来看。治理国家的政务从个人修养这一点出发,由修身到齐家,进而治国,到平天下,这是儒家“礼治”的基本方法。舜以孝顺且善于理家而著称。舜父是瞽叟,因喜小儿子而屡屡加害舜;而舜不以为意,孝顺如常,关爱兄弟。四岳因此把舜推荐给尧,理由是只有能把家治理好的,才能够治理好国。这就是天下之本,系于家齐。
正是儒家的这种思想,所以方孝孺作《宗仪》九篇,以为“正家之道”。无家齐,岂有国治?这就是孝孺所强调、所重视的。一宗于儒家之说。故而方孝孺尤其重视家庭教育。对子女进行文化教育之外,在家教中也重视教育子女忠君。他教子说:“国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孙是也。忠信礼让根于性,化于习,欲其子孙善,而不知教,自弃其家也。”忠君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教育子女遵守国家法律,完纳国家赋税,遵守族规族训,并非一般理解的只是忠于皇上。有的族规族训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赋税宜依期输纳,差徭合依理承认……
其次,方孝孺重视人的后天的学习与努力。他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知本”:“人之异于物者,以其知本也”;“所以知本者”,是因为仁、义、礼、智、信五性是“天”赋予人的。“礼义之性根于天,备于心”。这也是他在谱牒理论中强调“化天下之俗”的根据所在。
再次,中国古代农村聚族而居的特点决定了方孝孺乡族(村社)制度的设计模版是自治性质。他设计的乡族制度,除集中体现在前面所述他的谱牒学理论之外,还在《谢氏族谱序》中讲到三项内容:“先王之地,以井地养民,以比闾、族党之法联民,以学校三物之典教民。”
这三项内容,一是家家有田种。方孝孺说的有田种,其实是希望通过井田制来解决。二是有“比闾、族党之法”以维系乡里秩序。他所讲的“比闾、族党之法”,是指通过修家谱办祠堂与国家律令的结合来维护村民族众的团结。三是有学校(族学、义学、社学)让孩子读书,建立以“三物之典教民”的教化制度,使那些居住在同一村落,不论贫富,虽然相互之间不一定都有血缘关系的居民、村民,也能互相帮助:“凡群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亲,宗族之序”,能够实现“贫能相牧,患能相恤,丧相助而死相葬,喜相庆而戚相忧,……其情如骨肉之亲之厚且自笃也”。这是他要通过修族谱祠堂以“化天下之俗”后的理想的乡里社会。明朝廷对此也持支持态度。
四是方孝孺还进一步提出,乡族(村社)组织的大小,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强求形式上的一致、规模的一致。这样的乡族(村社)组织,人口不宜过多,“小而五家之比,大而方二千五百家之乡”,都是可行的。在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五家为一乡。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一乡之人可达六七万口。
方孝孺乡里制度设计的第五方面的内容是定期举行“燕乐之会”以联络感情。孝孺说,一个大家族上百甚至数百上千人居住一起,因求学、经商、外出做工等种种原因,未必常能见面;且又由于血缘远近,一年半载见不上面是很正常的事。倘若如此,可能会“亲而若疏”,导致“疏而不相恤也”。这就不合家族之礼制目的。故尔孝孺提出解决的方法:“祭酺之法,合之以燕乐饮食,以洽其欢忻慈爱之情”。
此即予以欢聚饮乐,增进感情。具体做法是“宗族岁为燕乐之会四”,每年举行4次“燕乐之会”,时间放在二、五、八、十一月。燕乐之会时,杀猪宰羊,准备酒醴羞果,让族人欢聚一堂,但不得有违尊卑长幼之序,不能醉酒;还要让两名会歌者引吭高歌。总之,让族人通过燕乐之会增进感情,增进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方孝孺的谱牒学说完全是按照中国先秦以来的礼治学说这根轴来阐述的。是乃由治家而臻治国,这是一种血缘政治。家族血缘中的父子兄弟关系,是国家政治中君臣上下关系之本。这就是《礼记》所说的:
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伦也。
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系,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
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
根据血缘关系的自然秩序,由修谱尊祖收族的家礼遂上升为国礼,从而使家族治理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基层地方的自治,直至国家治理。
四、乡里建设中宗族组织发挥的是自治作用
(一)发挥宗族组织的五项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方孝孺设想宗族组织在乡里建设中可以发挥五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概括如下:
1.立宗祠,定祀祖之规。通过每年举行的祠祀祭祖活动,教化族人,“敬父兄,慈子弟,和邻里,时祭祀,力树艺,无胥欺也,无胥讼也,无犯国法也,无虐细民也,无博弈也,无斗争也,无学歌舞以荡俗也,无相攘窃奸侵以贼身也,无鬻子也,无大故不黜妻也,勿为奴隶以辱先也”。如有犯禁上述任何一项,死后不得入祠堂。
2.修族谱,目的是“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孝孺提出,族谱要常修,族谱不仅要记载族人生平,更重要的是“举族人之臧否”,患难相恤,劝恶从善,养亲事长……总之,有值得教育族人、后人的事迹皆应在族谱中得到反映,而“死则为之立传于谱”,即在世系之外,专门书写条目立传记使后世子孙记住他们的业绩。所以他进一步又提出“重谱”的观点,力图通过重视修族谱,以固宗族、维系族人团结与互助,由此来保障宗族组织的有关功能的持续存在。
3.置义田,以恤贫济困。举凡贫穷族人,死了无钱购棺木入殓者,有病无力医治者,等等,皆可以从义田收入中给予救济。义田的一切收入应由“族之长与族之廉者掌之”。
4.设族学,为本族子弟提供免费教育,族学开支从义田收入中支出。保证族人不论贫贱,抑或富贵,皆能受到教育,使诗书礼义在族中世代相续。
5.行聚会,即居住在一起的虽非亲族,在大族亲友聚会时,非该族之邻里也应受到邀请参与聚会。通过经常性的聚会,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联络感情;有怨仇的则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沟通,化仇为谊。通过行聚会使邻里乡亲之间形成融洽祥和氛围,不再发生争讼斗殴。
方孝孺设想,以宗族为核心,推而广之,“试诸乡间,以为政本”。他说:
人之亲疏有恒理,而无恒情。自同祖而推至于无服,又至于同姓。爱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于天而不可易,然有亲而若疏者,有疏而若亲者,常情变于所习也。阅岁时而不相见,则同姓如路人。比庐舍,同劳逸,酒食之会不绝,则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岂人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也。圣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于离,恐其以不接而疏,疏而不相恤也。故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乐饮食,以洽其欢忻。慈爱之情,恐其徇于利而不知道也;肃之以乡射读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于怠肆。祭而酺,所以为乐也;读法,所以为礼也。约民于礼乐,而亲者愈亲,疏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为盛也哉!举而行天下,今未见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职也,故欲自族而行之乡,为之制。
(二)孝孺的设计符合礼治的乡村治理形式
按方孝孺的判断,居住在一起的虽非血缘之亲,然而皆乡里邻舍,“比庐舍,同劳逸,酒食之会不绝”,彼此交往密切,日出而作,日没而歇。因此,均能守望相助,济难纾困。这正是方孝孺所设计的“自族而行之乡,为之制”的政治理想。按照孝孺的设想,就成了这样一种关系:
家庭——宗族——乡族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族则是以宗族为核心,以地域来划分的。如此,乡族的人口就远较宗族多得多。那么,以宗族为单位设置的义田、族学显然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孝孺进而又提出设想:
1.每一个乡闾设乡廪二处,储积粮麦,用于灾荒之年的赈恤,以及常年的扶危济困。乡廪中的粮食从占田在百亩以上的富户中抽取,原则是每户一年不少于10升,多不超过10斛。如遇灾年,则不抽取。如此,一年可得千斛左右的粮食。
2.设立乡学三所,负责实施文化教育和社会教化。
3.在乡廪左侧附近建立乡祠。入祠的条件有二:一是入粟乡廪多者,二是推恩及人,经常赈济贫困乡邻居。具体说,乡祠的功用也有二:一是“嘉善,书其人之绩”,让乡族之人皆知其贤,通过扬善教育乡人。二是鞭笞丑陋行为,将“丑顽”行为书于乡祠,每到年岁集合乡民,当众宣读。
丑陋行为指那些为人吝啬而自私,缺乏同情心,富有家产却常常拖欠甚至不肯交纳乡廪稻菽,以及“渔其利而不恤民”等行为。
方孝孺设想通过立乡祠,鞭恶扬善,推进邻里之间的互助精神,以利于乡村基层的稳定。
4.举行各种聚会,以联络和增进邻里感情。
为了保证上述四项措施的落实,方孝孺设想在乡族中设置司教二人、司过三人、司礼三人负责上述事务。孝孺的乡里治理基本撇开了乡村基层行政。他设计的这套治理制度完全就是乡民自治。更值得重视的是,方孝孺设计的这套乡村治理模式不仅暗合了朱元璋的乡村基层管治制度,而且具有了符合礼治的一整套乡村治理的实践形式。

方孝孺铜像(在上海浦东方孝孺纪念馆)
[25][26]《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
[27][28]《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29]明·谈迁:《国榷》卷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
[30]《明史》卷五十六《礼十》。
[31]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乡饮酒礼》,中华书局1980年版。
[32]清·王夫之:《噩梦》,《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
[33]《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五。
[34]《全明文》卷二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5]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八《乡亭之职》;岳麓书社1994年版。
[36][38][47]《逊志斋集》卷一《宗仪·尊祖》,卷一《宗仪》序、卷一《宗仪·尊祖》,卷一《宗仪·尊祖》,清道光丙午刻本。
[37]《逊志斋集》卷一《杂诫》第二十二。
[39][40][41]《逊志斋集》卷十三《谢氏族谱序》。
[42][43][52]《逊志斋集》卷一《宗仪·广睦》。
[44]《礼记·礼器》,《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
[45][46]《礼记·文王世子》,《周礼·仪礼·礼记》。
[48]《逊志斋集》卷一《宗仪·重谱》。
[49]《逊志斋集》卷一《宗仪·尊祖》《宗仪·睦族》。
[50]《逊志斋集》卷一《宗仪·睦族》。
[51][53][54][55]《逊志斋集》卷一《宗仪·体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