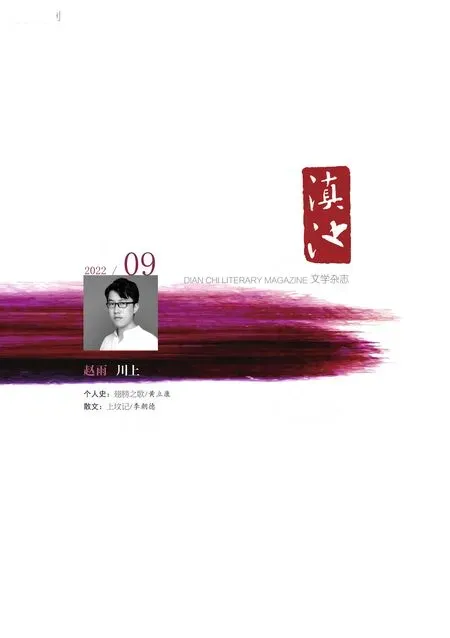上坟记
散文 李朝德
纸货店门面很小,没有店名也没有招牌。
店主是名老年妇人,坐在门口,昏昏欲睡。
春风吹拂,刮起一阵小小的漩涡风,街道上的灰尘垃圾碎屑随风飘扬,纸货店门前各种黄白纸钱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浮尘。
我习惯在村里这家纸货店买些上坟的用品。
这名老年妇女,母亲在世时与她熟识,年龄大概长母亲几岁。父母过世后,只要回老家上坟我都在这里买纸钱。她认出了我,母亲过世三年多了,她见到我还是会叹息母亲的突然离世。
从没想过父母也会成为先人。看着满屋子的上坟用品我不知怎么选。
以前回家上坟,都是父母替我准备好这些祭祀用品,我哪里知道操持这些。父母在世时,我更多去的是纸货店隔壁的红星超市,买些吃喝用品,大包小包拎着提着,欢天喜地热气腾腾沿着街道回家。
如今,站在只够两三个人转身的小店望着各种上坟祭品,心中凄然,纸钱白得耀眼,黄得灿然,香烛冥币塑料花艳丽得如梦境。
人间一过,缈缈万里,到底哪一头的世界是真实?哪一头的世界是幻灭呢?
我不会挑选上坟祭祀用品,每次来都是这名店主帮我搭配好。烛火香纸、黄白纸钱一应俱全,花花绿绿的冥币、白花花的坟标、色彩艳丽的塑料祭祀鲜花,她都低头默默替我选好装好。我也不问价和数量,可每次她都要少收几块,我很固执坚决付足付够,一方面小本生意,她那么大的年龄,淘生活本就不易;另外一方面,父母在世也不曾辜负与亏欠过这人世间一分一毫。她不再推辞,接了后弯腰把这一百多块钱压在筛子里一摞冥币下。我这才注意到,那冥币大小图案色彩设计与真钱高仿,只是面额大得吓人,动辄成万上亿。那么大的面额,钱来得如此容易,倘是真如此,那边应该早已没有穷困潦倒之人!
当地上坟,习惯近亲家族邀约着一起去。一方面是体现整个家族的认祖归宗,回到出发的原点。再者可能是为了好玩,大家平时各忙各的,即便在一个村子里,也很难得相聚。一起上坟,一起聚餐,曾经的生生死死哀哀啼啼化为现实的吃吃喝喝与热热闹闹,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人间烟火终将覆盖生死凉薄。
清明时节,墓碑之前,草木萧瑟,山河肃穆。
冬去春来,正是草木萌动的季节,上一年度的草木已经枯槁,这一年度的草木才刚刚冒出嫩芽,一岁一枯荣,自然也在生死交替接力。
“有人坟头飘坟标,无人坟上长青蒿”,上坟的人带着各自购买的坟标见坟就挂,一会儿的功夫,荆棘杂草丛生的坟地上到处飘荡缀有或红或绿或黄的白色坟标,白色的坟标迎着浩荡的春风飘荡、穿梭的人群在坟地间行走,冷清了一年的坟地迎来了短暂的热闹。
每年看望一次长眠地下的先人,对逝者是尊重,对生者是抚慰。
挂过纸、插过坟标,燃过香、敬过烟酒、敬过盘福斋饭,坟地迎来了本该有的庄重严肃。
草木枯荣,死者安息,生者安然,上坟让一切有了自然的归宿和生死固有的秩序。
李姓在中国是大姓,与我们村里相邻的一个村子就叫李家屯,村里上百户人家全都姓李。但在我们村李姓人数并不占优势,村里以姓氏为地名的有潘家台、张家大地、刘家街、禄家街、肖家沟、王陈坝、殷家野……唯独李姓分散居住没有大的地名标识。我们这支近亲的家族在村里人数不多,至今还经常联系并能在清明节一起邀约上坟的也就一二十户人家。
家族的坟地不大,却很分散,竟然有四处。
家族的历史,没有人能准确说清楚。
在古代,云南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云南的汉族,大多认同的说法是外来迁入或者移民。在元代末年,云南还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之地,明初朱元璋大规模移民之后,这种情况才出现了变化。生活在云南的汉族人,很多人都自称是从南京柳树湾来的。都会言之凿凿地说自己老家在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柳树湾高石坎一个虚无而又神秘的地名,无从考证实际来由,却是很多云南汉族人心底认同的故乡。我们这个家族以前有家谱,但可惜的是一把火烧了,其中缘由令人喟叹,不提也罢。家谱化为灰烬,一代代先人作了古。
先祖什么时候来的,到底怎么来的,最初来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是充军而来,移民军屯还是回不去的戍边士卒就地安家?
没有答案。如今,只留下分散的坟与枯萎的草。
有些坟是有名有辈分的,但更多是无名无辈分的小土堆。除了立过碑,能指认得出的坟茔外,祖坟堂里,更多的只是一个个荒凉和杂草丛生的土堆,里面躺着的人具体是哪辈叫什么名字,年代久远早已无从考证。部分老坟,也曾有立过碑文的,可惜的是在破四旧时被推倒拉去镶水沟铺路桥,光滑平整的碑石或立于桥墩、镶嵌石桥沟底或铺于路面,失落分散年代久远无迹可寻。而更多的坟茔,应该是从来就没有立过碑的,活着寂寂无名,死了一捧红土草草掩埋,终其一生并没有留下一个字,巴掌大的碑石也没有,一个个生命最后变成了一个个圆圆的土堆。
平头百姓,这不奇怪。日子紧掐紧过,大多时候,活着的人为生机愁眉不展,哪里有能力为长眠于地的人镶嵌石碑呢。
四块坟地,在村子的东西南北都有,上坟的顺序是以交通的方便程度来确定的,上完坟刚好转了个圈又回到村里。
上坟祭祖更像是一场规定时间内规定动作的朝拜与寻根。
先上的祖坟位于村西边的九龙山。九龙山坟地是爷爷那辈人从外村人手里买的。严格上说,这块坟地虽然在村子的西面,但九龙山已经属于另外一个叫古城村的地方。
如果不是殡葬制度改革,一代一代人都会在此找到最后的归宿。
九龙山坟地位于半山腰,面朝开阔田野,背靠巍峨青山。极目远眺,村庄原野尽收眼底。就在坟地前方几百米外,有口咕咕流淌的清泉从地下涌出,当地人叫九龙潭。那些年,九龙潭常年冒着冷清的泉水,长年累月,龙潭里涌水的洞比水桶还粗,周围秘密麻麻都是气泡翻动,清冽幽深的泉水不停从洞中涌出,里面冒出的气泡有鸽子蛋大,让人感觉洞中确实有九条龙吐出泉水。小时候我是不敢多看的,我相信这洞中真住着龙。更有村民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地说,他们曾经见过降雨前有龙从这里腾空而起。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龙潭的上方,修着一座龙王庙。附近村寨的风调雨顺,全在这里掌握,干旱或者洪涝,大家都来这祈求跪拜。
当地人相信,山上住着山神,水里藏着龙王。
在看不见的地方,自有神的旨意。
李氏先人乔迁风水宝地,家族欣欣向荣迎来新机。
迁坟的第二年清明,族人在新迁的坟地里杀鸡宰羊庆贺。
一群不速之客来到了这里。附近村里的一老者作为代表发难:“自坟地迁来,龙潭水突然变小,究其原因是坟地位置压了龙脉,龙王翻不了身,出不了水,附近村寨吃水及田地灌溉都受影响。不迁走,龙王生气,周围村寨遭灾。”老者说完,跟随来的一群人跟着附和,怒气冲冲,那架势就要上去扒坟。
双方各执一词,眼看就要发生一场械斗。
那时爷爷虽然年轻,但漂泊在外多年总是见过一些世面。对于怒气冲冲的人笑脸拱手相迎,满口答应:“如果真是压了龙脉,让龙翻不了身,影响到附近乡亲吃水生活,那是大事,一定要迁。不用说等到明年,就是今天挖走也可以!”此话一出,族人不解,其他村民也面面相觑。而后议论纷纷,乱糟糟一团。
“但是!迁祖坟是大事,你们谁说的我们家族的祖坟压了龙脉,就麻烦签个字,留下个书面的见证。如果迁了以后,龙潭水变大了,证明我们家族的确有错,明年还拖羊宰鸡给乡亲们赔礼。但要说明的是:如果迁坟后龙潭水还是没有变大,证明你们是欺负我家祖宗,那对不起!祖宗的尸骨谁签字我们送谁家去!”
穿着藏青色布衫,腰扎黑布宽腰带的爷爷用尖刀挑起一块羊肉,送到嘴中,冷眼扫过喧闹的人群。
“谁签字?”爷爷大声喝问。“李氏也是大姓,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和善乡里,不曾惹事。迁坟我们可以答应,但不给祖宗个说法,就是欺祖。”
众人鸦雀无声,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以后也再无附近村民找事闹事。
这个故事,家族人都知晓。如今,爷爷那辈也躺在这里几十年了。当年起争执的龙潭水流了几百年,但就在近两年也彻底断了流。
但早已没有人在意!村民喝自来水,原先靠龙潭水灌溉成百上千亩的秧田祖辈奉为至宝,但在年轻人眼中,稀泥烂塘,不值一文,被大片大片地撂荒了。
就在前几年,父亲也来到了这块祖坟。
就在父亲来这里的前一年,我与父亲、母亲还一起来到这片坟地祭奠先人,上好坟磕好头后,我们在一棵高大的雪松下坐着吃着东西,在路边上折了柳条,编了个柳帽戴着,那天太阳热辣,山野春风吹拂,百花盛开。
谁想到,一年后的清明节,父亲也就来到了这里,上坟的时候,我们在外头,父亲却进去了里头。
顺着一条乡村柏油路从村西到村北,来到了另外一处坟地。这坟地离高家大山并不远,但先祖却没有选择上山。
这块坟地在一片没有名字的小山坡,是家族中最古老的坟地,没有碑文没有记载,甚至家谱也未提及。用现在话来说,多年以来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几十年来,我们整个家族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块坟地存在着。
近些年,村子周围被各种大小工厂包围着蚕食着。这块最为古老的坟地就在附近大大小小厂矿和堆煤场子之间的一小块高地上无人问津。工厂包围农村,象征现代意义的推土机和挖掘机轰隆隆向前推进,摧枯拉朽、翻天覆地中日新月异。但某次,驾驶室里的人透过高高的举起铁斗缝隙,看见了荒草丛中凸起的一片坟包,触目惊心,现代化的铁爪犹豫中后退了。
在场的人没有人知道这片坟地的历史与归宿,但谁也不敢冒冒失失向一块坟地推进,即便它是无名的,暂时无主的,但每个土堆下面都有一副枯骨,都住着一个魂灵,再莽撞冒失的青年也不敢随意推平和践踏。
追根溯源,这片坟地与我们家族最近。
远古的祖宗,音讯全无,却因现代化的开发一下来到了整个家族面前。
这是片认不出任何一座辈分和年代的坟地。实在太古老太陈旧了,最高的坟堆还没有一米。大多坟堆,只是略微高出地面几十公分,有些基本与地面齐平。以至于在上坟挂纸的时候,只能凭猜测大概哪里住着个先祖。在坟地间行走,相互提醒不要踩在祖坟上。
沧海桑田,如今坟地的前后左右都不再荒凉,被现代化的开发团团围住,前面的一块空地早被其他村民在家族管理坟地前几十年就种上了桑树,地权、坟权纠缠不清,只有各后退一步,承认既定边界与事实,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共享这片土地。左侧是家小工厂,右侧是堆煤的货场,后来者居上,边界被打上围墙,已成既定事实。后面不知何时被挖成山崖,估计是想把后面荒山挖空搬走,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把后面一块荒地变成另外一个货场或工厂。坟地最顶头有块石头,石头下面挂着黄纸,是坟地的后山石。石头下一棵比人稍高的松树遒劲苍老,看得出已经有些年代,这是坟地间唯一的一株松树,孤傲地挺立着。可惜的是,连续两年,都被人用火烧过,一半是青翠一半是炭黑。就这样顽强而坚定地活着抵抗着。
这地方并不顺路,也没有人管理。有一年,上坟忘记带锄头和砍刀,荒草荆棘疯长得高过了坟堆,人钻不进去,难于发现坟包具体位置,我们只有站在高处,把纸钱大把大把往坟包方向撒,大风吹来,白色的纸钱四处飘飞,挂在草窠上,吹到半空中,飞往远方。
那株松树今年又被火烧了,松针全被烧糊,也不知能不能活过来。人间的恶意连坟地间的树都不放过,有几个年长的嫂子气愤不过,对着旁边的工厂骂,但谁在乎,谁听得见呢,里面的机器隆隆作响。
第三块坟地在村子的北边,坟地方圆快一里附近的地方叫罗家坟茔。
李家坟地在这片罗家坟茔的地方。实在想不出到底为何如此。
这坟地自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是块耕地。坟地空隙的地方都被开垦成了庄稼地,耕地的时候,犁耙小心地绕开一个个坟包,如理发一样把空地修理得整整齐齐。春天,犁耙把泥土翻起,红得耀眼,蛰伏了一个冬天的虫虫蚂蚁在上面爬,一股新鲜的泥土味扑面而来。夏天,包谷、豆角、洋芋铺满了土地,万物萌发、生机勃勃,绿色的纱帐把一座座坟茔掩盖了。秋天,圆滚滚的南瓜爬上了坟头,金黄的包谷掰下来,装在口袋里靠在坟包上。冬天,地被清空耙平整,一个个坟包就像大大小小的馒头散落在红色的幕布上。
逝世的先人在地下沉睡百年,忙碌的后辈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
农耕时累了,就坐在坟堆边,喝水吃晌午。大人在地里干活,孩子在旁边玩耍,坟地间支撑起一把伞。玩累了,躲在伞下靠着坟堆休息,一代又一代在大地上繁衍生息。
在坟地旁边一块还有座孤坟,不属于我们这个家族。从记事起,就是座野坟,从没有见过上坟的人,在好多年前清明时还能见到挂在上面的纸钱,想是还是有后人在记挂着想念着。这些年,再没见后人挂过一张纸,听说这家后代搬回贵州去了。倒是我们,上家族坟的时候,会特意走过去几十米,给这座无名无姓的坟插几炷香挂几份纸,让孤坟不至于太过冷清。
家族里的坟地,我们是不会害怕的,即便里面的人死去多年,但总觉得那里睡着的是我们的亲人。
对于其他坟地,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会害怕,莫名的恐惧。
上初中时,一个月明之夜。我们几个小伙伴去偷蚕豆煮吃,却被看蚕豆的人追赶,慌不择路,我没有沿着来时的大路跑,却跑向了另外一条山路。
等我发现四周都静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狂奔出好远。月明星稀、夜莺咕咕,整个田野只有我一个人。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回家的路。折身返回走大路,安全平整,四周开阔,但却多走出一倍多的路程。往前继续前行走小路,夜深人静,要翻越一座山和穿过一片坟茔,但却很近。最终,我鼓起勇气,选择了走小路。整个世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隔着山和森林,看不见村里的灯火,也听不见公路上的汽车响声,静得我只能听见我裤腿走路摩擦的沙沙声响。
在山边一座坟地前,我站住了,再不敢动。
月光下,我分明看见了一座坟地旁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招手。
我才突然想起,不久前村里有家新娶的儿媳妇不知何故上吊死后被埋在那里。
我头皮发麻,手脚冰凉。前进还是后退,又一次摆在我面前。回去,显然不现实,绕得太远了。我鼓起勇气,在路边庄稼地里拔起一根一米多长结实的木桩,拖在地上往前走,我冲着远方的黑影大喊大叫,企图把她吓走。她还是在那里,不退也不走,我甚至能看清,是个女的,她穿着件臃肿的棉袄。
我又在路上捡了几个鸡蛋大的石头装在裤兜里,拖曳着木桩往前走,木桩与地面摩擦,咔咔作响。我发出几声尖锐的长啸,一只山鸟还是野鸡扑棱着翅膀突然飞起。
但她还在那里招手扭着身躯,我头皮发麻,但没有退路。我横下心往前走,如果真有什么东西扑过来,我准备迎头痛打。
那个身影没有扑过来,还是站在原地招手。
在相逢的那一刹那,我大着胆子站住与她对视。夜光下,光秃秃的新坟,纸钱和花圈旁边,一件红色的棉袄被人穿在了新坟边一棵一米多高的松树上。风一吹,两只袖子就像在向人招手。虽然是一场惊吓,但红色坟包、地下散落的白色纸钱、花花绿绿的花圈、裹着绵纸的哭丧棒、纸扎的棺罩、红色的棉袄这些丧葬之物还是让我觉得恐惧。
我鼓起勇气往前走,穿过另外一片坟茔。月亮皎洁,但山上森林里的坟地在树木掩盖下,有的地方亮着,有的地方黑着,总觉得黑暗之处隐藏着什么,让人心里恐慌。
最后上坟的地方是村里的墓地。母亲在2018年来到了位于村里东边的胡叶山脚下的公墓里。2015年离开人世的父亲,成为了最后一个睡在祖坟堂的人。而母亲,由于殡葬制度改革,来到了公墓。她与父亲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中间隔着一座杨梅山和一座叫松林的村子。在这个村,她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而那座山,他与父亲也爬了几十年。
母亲突然离世后,我们也曾想过,暗地里偷偷地把母亲的骨灰与父亲的埋在一起,公墓作衣冠冢,掩埋个空坟,父母活着恩爱、死后同穴,也算是一种修为。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对于心心相印的人,什么样的万水千山能阻隔呢,形式上在不在一起哪有那么重要。父母一生都是光明磊落之人,哪里会在乎这些。如果真有另外一个世界,隔着一段距离,一个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一个在太阳落山的西边,一个在传统的祖坟,一个在现代的墓地,走动起来不是更好嘛!
公墓占地狭窄,墓碑前跪不下那么多人。上坟的时候,直系亲属跪着,其他人站立着。世事难料,六十多岁身体健朗的母亲竟然也成了享用香纸斋饭的先人。
每年,公墓都在生长,一列列一排排在山坡上延伸。每次从这些墓碑的行列里走过,我都感觉到这些村里的人并没死去,他们只是换了另外一个地方居住,一样可以晒太阳聊天,一样可以锅碗瓢盆家长里短。
上坟季节,新坟总有人在哭,纸钱和泪水伴着袅袅的香火。而三年以上的坟,就成了老坟,很少有人在老坟前哭泣,只有零食、水果和艳艳的鲜花。
再大的哀伤和不舍,都抵不过生活的琐碎和磨难,岁月把哀伤稀释摊平得悄无声息。
看见母亲的名字和照片在墓碑上,我还是会轻轻的抚摸,也会告诉她一声:妈,我来看你了。就像她还在世时,我推开门喊她一声那么自然。可惜的是,她再也听不见。
每年,我上坟挂完纸后,都要站在松树下眺望着村子的方向,总会天真地想,如果父母还在,上完坟后可以回家,村里老屋的门一定不会上锁,一推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