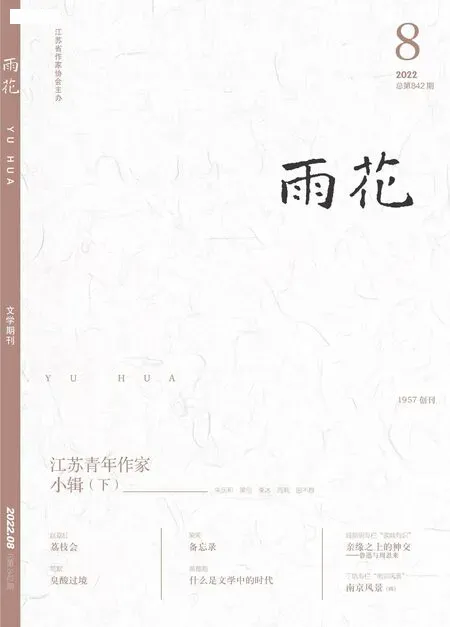什么是文学中的时代
黄德海
一、客观的时代
任何领域中的大词,都容易左右人的基本判断,因为人的每一个具体感受,几乎都可以笼统地装进大词的躯壳,从而在人们丢失具体性的同时,产生客观性的错觉。比如文学讨论中常用的“时代”一词,就仿佛是客观的,它不过是按某些标准制定的时间界限,用来指称某些时期,跟通常依据天文或朝代沿革确定的纪年方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我们指称的大部分当代文学写作,尤其是叙事性作品来说,似乎确实存在一个个客观的时代。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这些时代界划甚至已经客观到了条分缕析的程度,一个阶段连着一个小阶段,一个时期挨着一个小时期,一个巨浪续上一个巨浪……近代以来有识之士面对的复杂局面,那困扰人的、至今尚未结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代文学写作中,几乎变成了固定时代公式的背书。
不可否认,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动太过剧烈,也太戏剧化了,时代本身的巨变仿佛就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情节。只要选好了时代节点,一台好戏差不多已蓄势待发,很难期待一个人能从时代中挣扎出来。漫长的百年光阴,在客观性的时代之下,最终只会剩下几个典型的情景、典型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并且大部分时候,这些典型的指涉都有规范的指向,只要在阅读中看到几个符号,我们就不难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个时期,有什么幸运或灾难正等待着作品中的人。
悖论随之产生,这种对客观时代的典型提取,难免会高度压缩,极度提炼,表现在叙事性作品上,就是社会环境会突出,人物性格会鲜明,情节会集中,调子会高亢。绵延的生活之流即使在极端条件下也自我维持的舒展和从容消失了,时间和情节的节奏会不自觉地进入特定的轨道,删除一切旁逸斜出的部分,剩下的只是意料之中的时代起伏。
更为重要的是,写作者拣选出的所谓时代特征,并非完全出于自觉,甚至可能是经过误导的自觉。
如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所言,文学作品的独创性是一种卓越的努力,“是叠加在自我之上的更高的顶点,这个自我与他同一世代人中中等才能的人的自我原本并无二致;不过,这样的自我,这中等才能,原本就存在在他们身上”。如果一个人身上的创造性受制于中等才能者给出的客观时代,也就不难想象,那个本来就存在于人身上的平庸的自我,将大面积地覆盖写作者的卓越努力。“当我们在每一页书、人物出现的每一种情境,看到作家没有对之加以深化,没有对之进行思考,而是运用现成的表现手段,从别人——而且是一些最差的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作为提示,如果我们没有深潜到那静谧的深处……他就只能满足于粗陋的表象,这种粗陋的表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给遮蔽起来。”
写作者往往借用了教科书式的客观时代划分而不自知,还以此为框架填充进了自己的文学材料。这样的文学填充方式,即便作品在某些方面写得再好,也并不是以个人为基点去进行艺术或文学求索,仍然未曾进入艺术创作的深层,只是一个固有结论的优秀证明,从而会极为明显地影响文学作品的品质。
似乎没有必要把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名篇,拿来验证时代的客观性问题,只举知青小说为例吧。大多数知青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总是苦尽甘来,那些在作品里早逝了的灵魂,无非是不幸没有等到厄运结束的一刻而已。这样的写作,已然忘记了知青们置身的,其实是一个没有确定未来的当下,前途未卜,命运叵测,并不知道他们在此间的生活是否会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又会如何。循此推演,几乎可以发现,当代大多时间跨度较长的小说,都有那么一条后设先至的命运红线,因而人也就无可逃脱地会撞上时代客观性的铜墙铁壁。
要避免碰上这面坚硬的墙壁,文学写作就必须试着打破时代客观性的桎梏,让生活之流淌进蔓延的日常,从而得以体贴人物在时间之中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这些生活带来了何种复杂的滋味。惟其如此,生活才会从被切割的条块状态变成绵延的时间之流,它不仅仅是时代起伏的佐证,而是一种常恒的、流动的、你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人们需要日日面对的,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受的命运。也惟其如此,文学作品中的时代也才不只是社会变迁的写照,而是一段风尘仆仆的光阴,有人世的风光荡漾,即使悲苦,也有属于自己的骄傲自足。
二、必然的时代
除了时代的客观性,文学中的时代,还几乎是必然。这个必然性有两方面的意思,起始的一点,是时代发生的必然,即过往的任何一个时间段落,其间发生的种种,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无可避免。
这差不多是某类哲学教科书的老生常谈了,对如此单一的必然性说辞,以赛亚·柏林在《自由论》中早就作出了反驳——对时代的必然性认知,与对历史的必然性认知一致:“主要源于一种推卸责任的欲望,在我们自己不被评判,特别是不被强迫去评判别人的情况下停止评判的欲望;源于逃到某种巨大的、与道德无关的、非人的、磐石般的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艰难时世’或社会结构的不可抗拒的演进——的欲望。这个整体将把我们纳入并整合进它那无限的、冷漠的、中性的机体中;对于这种整体,我们的评价与批判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不是讨论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争论的地方,我要说的是,很多作家对时代必然性的接受,根本未经反省。在不少作家看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不过是这个民族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甚至连最具灾难性的社会问题,都被看作是盛衰循环的必然。果真如此,那所谓的文学作品,就都不过只是证明时代必然的趁手材料,用不着太过用心;而后来者对过往的思考,包括任何写作,都不免多事——既然都是必然的,那只要等待必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了。
更进一步,有些作家认为,时代是一种必然的回环结构,糟糕的一个时期过后,必有一个相反的时期来补偿。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人类尽管放纵自己的邪恶和贪婪,社会将遭受怎样的破坏,人会受到怎样的屈辱,根本不用担心,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巨大灾难后的历史补偿即可。这样的回环性必然,从根本上取消了反思的必要,当然也就用不着作家来寻找原因,探讨责任,对人物表达必然性的同情。
除了时代发生的必然性,还有一种更为奇特的对必然性的认识,即很多人似乎认为,经历过一个即使苦难的时期之后,这个时期必然累积了足够的能量。然而精神领域的任何问题,大概都不只是数量的堆积。
与此相应,一直有人慨叹,相比于多数人看来苦难、沉重、无奈,或一些人眼中奋进壮阔、激越的百年历史,华语文学还没有写出一部足以与之匹配的作品。作家们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居然没有写出一本配得上那个时代的书,实在遗憾。这样的必然性设想里,隐含了一个怪异的前提,即经历过一个伟大或多难的时代之后,理应有一本与之强度相配的作品,累积的能量肯定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而一些作家将自然地拥有写出一个时代的能力,这样的作品也必然会产生。
在这样的假设里,时代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共同构成了时代的物质性。写作者不过是物质性时代的某种特殊加工机器,只要把伟大的时代原料放进去,自然会生产出伟大的作品。现下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品,不过是因为写作者不够努力,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承担这个必然,故此作家们需要的是督促,良驹奋蹄,时代的洪流将汹涌至作家笔下。
这么说的时候,人们大概忘记了,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即使真的有一个能够划归物质系统的时代,一旦进入写作领域,它也只有被再次创造出来,才能够证实自己从属于精神领域。作为自然时间的时代,在未经精神性转化之前,根本不是真的写作素材,或者什么都不是。不妨记住普鲁斯特的话:“我们书的内容,我们写出的句子的内涵应该是非物质性的,不是取自现实中的任何东西,我们的句子本身,一些情节,都应以我们最美好的时刻的澄明通透的材料构成。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处于现实与现时之外。”
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必然的时代,不是人们经历了一个独特的时代,就必然应该产生独特的作品,而是有了一部好作品之后,那个此前晦暗的时代才被点亮。伟大的作家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改变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陈旧认知,并将作用于将来。说得确切些,时代的独特是在不断地讲述中被发现的,并不天然存在。有志于写作的作家必须一切从头开始,丢掉必然性的幻想,全面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在写出属己的时代之前,一个作家并无任何证据来表明自己的伟大。
三、属人的时代
检讨时代的客观和必然误区,当然并非说时代跟人没有关系。相反,只要时代不再是物质性的,而是作为精神氛围或文化形态,它就恢复了与文学的天然联系,作为写作者,不可能脱离作为精神风气的时代。虽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不必一定为时代风气所限,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像雪莱说的那样,写作者“和哲学家、画家、雕塑家及音乐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创造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时代的产物,最超拔的人也不能逃脱这一从属关系”。即如圣佩韦所言,人们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
这样的时代风气是作品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精神背景,仔细阅读作品,就可能如钱钟书所说,可以“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我们从当代作品中能够辨认出的时代的风气是,作为物质性客观和必然时代里的人物,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会如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说,“都是陷入各种不同陷阱中的困兽,最后手足被绑任人宰割”。高高在我们之上的时代,而不是运行于我们之间的时代,才是那些强调时代的小说的重点所在。
小说中的物质性时代,就像挡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堵堵墙,或者渡河时不停翻卷过来的巨浪,人在这个境况里,差不多只好碰壁或卷入其中。生存在物质性时代里的人物,也只能在给出的框架里挣扎,他们将在辛亥时振奋,抗战胜利时欢欣,新中国成立时欢庆,下乡时无奈……随着一波一波的形势变幻,人物不免一时有被抛上高天的得意,一时又体味沉入地狱的凄惨,一时是过街老鼠似的无奈,一时又显现反抗英雄的悲壮,再忠厚的人也会凶相毕露,再凶狠的角色也会一朝沦为阶下囚……乱云飞渡,进退失据,一不小心,人物就沦为了时代变化的浮标。
这生硬的界划,取消了人物的生存弹性,既抚恤不了已死的冤魂,也给不了幸存者安慰。即使某些囿于物质性时代的作品致力于写人性,人物也并不具有宽敞的自为空间,往往是时代苦难的判词,或是受难者的证据,难免经受随时代符号起伏的命运。在一些借时代因素深挖人性黑暗的作品中,写作者又往往容易把时代因素设置为测量人心的外部情境,没有与作品对人性的探察结为一体,人物不过在时代的起伏里展露深处的善良或罪恶,以此表达作者对人性深处进行发掘的惊喜。
不妨说,在这样的作品里,主角永远是风急浪涌的外在时代,人物并不怎么重要,本该是具体而郑重的人物性格,根本不是这些作品首要关心的。即便作品里涉及私密事件,由客观和必然定性的时代,仍然响亮地奏出固定的节奏。锁闭在时代里的人物,落入的是早已被清晰规定的时间起伏框架。时间段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人将在什么时间受苦遭难,什么时间苦闷无奈,以至什么时间满怀希望,都被后来规划的各个时段界限锁闭在里面——不管是怀念还是反思。如此情形下,人物当然会被挤压得瘦骨伶仃或极度亢奋,鲜明倒是鲜明,却少了些活人的气息。
这样的情形,如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所说的那样,当然是有理由的:“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总会有一些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样的能量慢慢累积起来,“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所有用文学来证实物质性时代的强大,其实都不必要,因为关键的是,文学中的人物,要从刻板的时代套路中站立起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
只有写出独特的人物,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属人的时代,时代也才会从干枯冰冷的符号系统中还原出来,显示出内在的活力和神采。这样的作品,通过人物性格特征的有效持续,会冲破各种时代界划,展现出一个非中断的线性日常。这个线性的日常并不把人生刻意地分为高光时刻和黯淡岁月,也不再是人物跟随时代被动起伏,而是时代始终跟随着人物的步伐,小说里的人诚恳地接受了生活里发生的一切,显现出一种运行于常人之间的命运。对一直被高高在上的命运主宰的人们来说,这种运行于常人之间的命运,虽然也有悲苦,也有无奈,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还有什么比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更值得关心呢?
这样的人物,当然仍置身于强大的社会力量之中,也会受到社会的约束和牵绊,却并不是作者为了证明什么而写。他们只是跟时代生长在一起,互相障碍,也互相适应,反抗也好,适应也罢,都以自己的喜怒哀乐,慢慢地与时代生长在了一起。或者可以说得更坚决一些,只有在展示了自为能力的人物身上,我们才可能意识到,无论言说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时代都必定是由人构成的,并毫无疑问是属人的。
我曾听过一个故事。有位画家教自己的孩子画雨中芭蕉,孩子先仔细画好了芭蕉,然后认真地画雨。画家告诉孩子,不要专门画雨,而是画芭蕉的时候,雨就在里面了。所谓时代,也是如此。没有跟人不相干的时代和生活,在叙事作品里,所有的时代信息,都必须全面地复合在人物身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谓的时代,最终必然是人身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