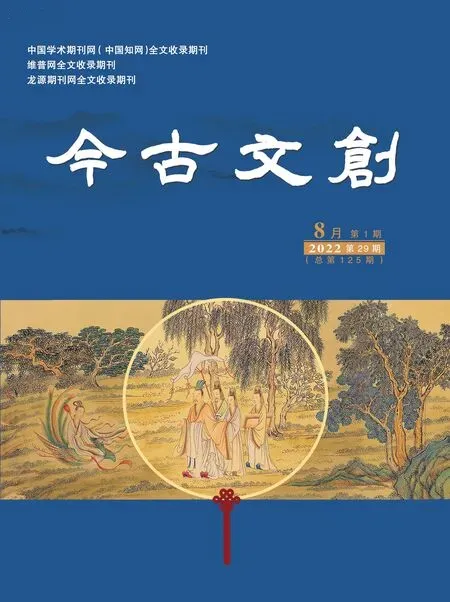孟子“君子之守”意蕴初探
◎曾 卓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之一,“君子”已然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道德载体。“君子”一词在先秦早期典籍中已频繁出现,只是其含义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在孔子之前的“君子”,其含义大多意指以“君王之子”为代表的身居高位之人,着重突出“君子”之位,以此显示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地位差距。然而到了孔子时代,“君子”被赋予了内在的道德内涵,重点凸显的是君子之德,除了保留部分地位差别之意,其意更侧重于突出君子的道德修养以及德性的外显,由此则奠定了“君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基础。此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对君子的塑造,将“仁义”并举,赋予了君子更多的道德性,令“君子”逐渐成为人人可以追求的道德理想人格。“君子”在《孟子》全文中共出现八十二次,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涵盖甚广,但总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君子的内在道德修养;二是君子的外在道德影响,而恰好这两点在孟子“君子之守”的表述中得以集中体现。
一、“君子之守”的始终
孟子言“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以下引用《孟子》原文,只注篇名。)其中“君子之守”是孟子对君子特性的延伸和具体化,意指君子的自我要求及其操守,由此便引出一条贯通君子内在修养与外在道德影响的进路,从修身开始直至天下治平。依此观之,孟子“君子之守”的路径则非常清晰,修其身,君子之守始也;天下平,君子之守终也。
“君子”在孔子时代,已经发生了“位”与“德”的转变,再到孟子所处的时期,“君子”的德性意蕴则更加明显,孟子认为此时的君子应当展现出比以往君子更加强烈的社会担当与道德示范,其强烈的动因则是源自于孟子对“君子”历史演变的细微观察,孟子言及“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公孙丑下》)孟子发现当世君子在自身的持守上不仅没有超越往古之君子,反而还不及往古,孟子深以为忧,古时的君子有错就改,由错到改正这一过程皆被百姓所观察与感知,由此心生敬意,然而今日之君子,不仅依错而错,还会为自己的过错寻找借口与托词。朱子认为顺过而不改,实不可取,因而言之“顺而为之辞,则其过愈深矣。”也正是由此,尽管并没有否认君子在“位”上的一定属性,但孟子的表述则显示出其对君子“过则改之”德性的认可,所以在孟子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对“君子”的德性建构是其人格论述的重点。在孟子看来,“修身”是“君子之守”的力量之源,“君子”是人在道德上自我挺立的结果,是由主体自身努力能够达到的状态,而这一切都指向“修身”这一环节。《大学》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传统儒家的观念之中,“修身”始终是道德发用之本,因而“修身”被放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是后三者得以实现的基础与起点。孟子也秉持类似观念,充分相信人性本身的善性倾向,坚持人的道德修养应始于自身,因而论及“君子之守”时,起始就言及“修其身”。这也恰恰证明,孟子知晓君子的操守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深远影响,但这一切影响的原初起点,则是从君子自身内发的修养开始。
在孟子的观念里,个人的修身只是一个开端,君子的最终指向应当是天下治平,而之所以最终会落脚于“天下平”,这与儒家的社会担当以及孟子个人的理想抱负有着密切联系。《大学》中提出的“修齐治平”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化,是君王行道的具体规范,是儒家培养理想君主的理想途径。但是无论以何种具体的方式来立身行己,在传统儒家的思想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要为了达到“天下平”的愿景。孟子被称为亚圣,志向远大、敢于担当,其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三圣所指禹、周公、孔子,禹治洪水令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给予天下百姓安宁、孔子著《春秋》令乱臣贼子畏惧,孟子则正是要继承并护卫前圣之大道,而如何能让自己达成前圣大道的志向,除了“正人心,息邪说”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平天下”,所以孟子更是豪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由此观之,在孟子的观念里“修身”并不会是君子操守的终点,而是“天下平”。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无论是“安人”还是“安百姓”,其原初的基础都是“修己”,“修己”即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安人”“安百姓”则涉及社会整体的稳定和有序,从孔子的主张中我们不难可以看到,以“修己”为起点在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最终乃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也就是群体的安定。而孟子则将这样广义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放大为“天下平”,将其融入“君子”人格的社会责任之中,以此言及“君子之守”应由“修其身”直至“天下平”。依此观之可以发现,“君子之守”的路径则贯穿了“君子”人格所蕴含的道德自我从自我完善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全过程,而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心不安的战国时期,“天下平”无疑是“修身”价值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同时它也是“君子之守”的最终归宿。
二、“君子之守”的工夫
“君子之守”之起始为“修其身”,其最终所达为“天下平”,而在这一过程中“修身”的工夫是长久存在的,换而言之“天下平”的结果是“修身”影响的最终体现,因此“君子之守”的工夫的核心就在于君子自身的道德修养,而结合孟子的性善主张,修身需要正己,正己则离不开保有善之“心性”。
孟子言“守,孰为大?守身为大。”(《离楼上》)论守护什么最为重要,孟子则认为是守护自身的品质节操。孟子深知“天下平”的原初基础就是“修身”,要使其长久发挥效用就需持久守之,因而身修之后得以自身持守则是其价值影响的关键所在,由此孟子言“守身,守之本也。”(《离楼上》)这也就将守身上升到守护的根本地位,因为守身之后才能正己,己正才能正物,因而焦循所言“身正,物正,天下平矣。”焦循认为“身正至平矣”,这也就将“修身”提升到了“身正”的阶段,对“修身”的宽泛意义进行了具象化,明确只有通过“修身”以至“身正”,才能使“天下平”,所以“身正”则成“君子之守”前期修身阶段的一个具体的要求,而“守身”则是满足这一要求的必要条件,只有“守身”才能“正己”从而达到“身正”。“君子之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君子的自我实现,也就是人之为人对理想之我的一种追求,而在这一过程中,守护自身所认同的操守是自我价值显现的重要体现。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坚守并认同的道德操守,那么他也就无法达到“身正”的状态,因为无本可依“修身”也就无源可循,即便有身修的迹象,那也只能是像昙花的一现,无法有“正己”的可能。因而君子在修身之时,也定当持有“本”之方向,“守身”而后“正己”,以至持久保有“身正”的状态。
在与告子人性论的辩说上,孟子主张人之性善,其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仁义礼智是理想人格的基本规定,在孟子看来这一规定从一开始便萌芽于每一主体,并以此构成了主体自我实现的内在根据与出发点,先天的善端则为君子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道德动力,而向理想境界迈进的过程,就是展开这一先天潜能的过程。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如何能认识到人之本心与原有之性,孟子认为只有极力发展人的善心,而孟子所尽之“心”就是善心,所知之“性”也就是善性。孟子将心性的存养上升到“事天”的层次,使其成为超越人之实然的层面而跨入人之应然,所以其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由此孟子便得出何为立命的最好方法,那还得回归到个人之修身,其言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因而,无论是“尽心知性”还是“存心养性”,其工夫仍旧需要以“修身”为依托,那这也就照应了“君子之守”的起始,君子的操守应当以“修其身”为出发点,而这也就正好印证了孟子的思想主张,从这一层面来看,“修身”的另一个阶段就是“守性”,借“修身”之道明人之善心并守护人之善性。
从这一发展进路,可以发现要到守护“善性”这一阶段,则需要经过“尽心”而后“知性”,到“存心”后再“养性”,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每一阶段皆是由“心”起始,因而“尽心”“存心”得以实现的基础则尤为关键,这也就需要回溯到“养心”的开端,孟子所言“四心”仍是“端也”,还需要扩充与涵养,才可显露出“仁义礼智”的德性之源,由此孟子给出了养心的具体方法“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依此方法人减少自身之欲望,善性即是有所丧失那也是很小的一部分,若欲望不见反增,即便善性有所留存,那也微不足道了。依此观之,“心”有所养则“心”可尽、存,“心”得尽、存则“性”可知、养,有此基础之后,“性”则得守。因此“君子之守”的工夫由此进路则可以明晰。
三、“君子之守”的境界
从起始之处与最终结果的关联来看,毫无疑问“君子之守”由“修其身”起始直至“天下平”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君子,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君子将“仁”与“礼”存于“本心”,辅之以“善”,则到达“存心”的至高状态,由此结合君子“反求诸己”特性,得以造就“自反不患”的“心安”之境界。
孟子言“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由此可以知晓,君子与常人皆属同类,而君子之所以高于常人,只是因为君子善于“存心”,若有了“仁义礼智”之心,并将其保存好,就意味着“君子”的达成,若不能保存将其丢失,体现的也就只是“常人”之平常所性。因而孟子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将“仁”“礼”存心,是对于道德的巩固以及人之为人的内在认可,其影响极为广泛,在儒家的人伦观念里,人人爱其亲,重其情,将“仁”“礼”转化为外在道德行为,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就可以持续而长久,并伴随人伦延续而不断扩大。而四德固有之说, 明确把仁、义、礼、智作为德性, 而不是德行, 这是儒家德论内在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阶段。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在 《孟子》 中仁义礼智都仅仅是德性, 而不再具有德行的意义。因而,从“君子”本身德行外显的层面来看,“天下平”的美好愿景可以通过“君子”德行的广泛影响而实现。所以孟子延伸了“仁”与“礼”的影响,谈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将“仁”“礼”存于心之后,其在人伦之中的道德影响作用并非是短暂的,相反而是可以恒久保持,只要“君子”在,其影响就“恒”在。因而孟子讲“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除了显示“仁”“礼”之本身在人伦道德中的效用外,其更想突出的是君子“存心”的这一独特功能。
就孟子思想体系而言,“君子之守”主要是对“君子”这一理想人格的内圣特质及其现实影响的集中概括,其持守之意蕴仍旧需要从“君子”的具体行为之中进行体会。杨国荣认为“健全的个体固然表现为内在的我与外在的我的统一,但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在道德上得到升华,主要以其‘存心’为依据,而君子高于一般人的地方也正在于其‘存心’。”将道德主体与“仁”“礼”相联系是体现“存心”效用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表现出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孔子言及“克己复礼为仁。”这一主张巧妙地连结了“主体”与“仁”“礼”,意指若要实现“仁”则需要由自身出发去符合“礼”的要求,并由此再提出“为仁由己”不能“由人”,从这一进路观之,尽管也含有内发道德自我的显现,但仍旧更突出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与之不同的是,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之为人的道德本性的建构,以道德伦理为土壤,播下以善为核心的本性种子,并为其预设出实现“仁义礼智”的本性可能,由此对道德性进行建构,使人对道德自我意识的存有更加关注且愈发认同。因此“君子之守”的境界在“自反”意识之中得以充分体现,孟子认为当行事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目的之时,则需要“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离楼上》)孟子通过对“爱人不亲”“治人不治”“礼人不答”三个人情伦常情景的建构,连用三“反”来突出个人内在的道德“自反”意识,并由此引出所有“行有不得”之事,全都需要“反求诸己”,孟子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自反”,才可以使人达到“身正”的状态,进而得到“身正而天下归之”(《离楼上》)的理想结果。
“自反”人人可为,但并不是人人都有“自反”的意识,因为这也是区分常人与君子的标准之一。“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离娄下》)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君子拥有超出常人的“自反意识”,这也是“君子”操守的可贵之处,如遇他人蛮横对己,君子必定反省自己是否足够仁爱有礼,通过自省君子则进一步涵养了“仁”“礼”之心,即便此后他人“横逆由是也”,君子仍旧“自反”自己是否足够忠敬,直至通过多次的“自反”,确认自身言行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君子则可得己“心安”,因而无所多虑。君子通过不断的“自反”,已经持守并巩固了自身内在的道德之性,所以即便最后知道“横逆之人”的行为是源于其本是“妄人”,“君子”也不会心生任何抱怨。因此孟子得出结论“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离娄下》)“君子”没有一时的担心,因为君子的“自反”意识保有终身,遇事则思是否合于“仁”“礼”,凡自觉不合“仁”“礼”之事,皆“自反”求之,有此意识,君子自然“心安无所患”,而“君子之守”的境界则恰好体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