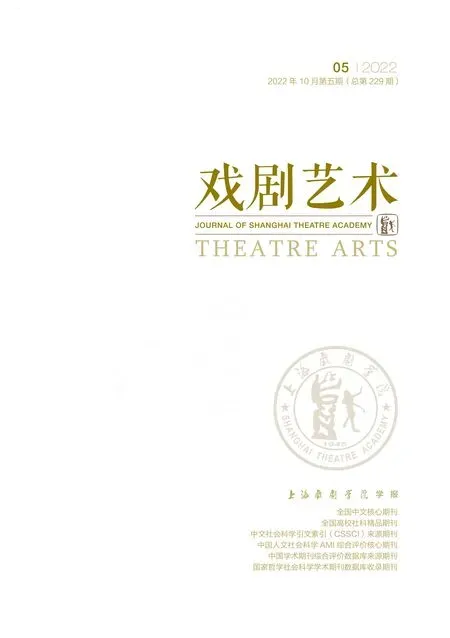后戏剧剧场中的《哈姆雷特》
陈 恬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在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举办的名为“莎士比亚现场”的活动中,有一段风趣的表演,多位曾经扮演过哈姆雷特的著名演员以及查尔斯王子争相上台,教一位新人演员念“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每个人都将重音放在不同的单词上,并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这一场景颇具象征性,因为《哈姆雷特》在戏剧剧场(dramatic theatre)的演出史,大体可以看作莎士比亚文本的朗读与图示。文本不仅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被认为其中隐藏着确定的作者意图,舞台呈现就是关于“莎士比亚到底讲了什么”的文本索隐和解谜,其评判标准是谁更忠实于原作。
如果对20世纪以来戏剧剧场排演莎剧的方法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大致有两种,即普世性的路径和语境化的路径。前者认为莎剧本身包含普世和永恒的意义,至今仍与我们的生活具有深刻关联性,因此更强调“忠于原作”“照写下来的去演”;后者则寻找莎剧与当代语境相结合的新的阐释角度,比如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使莎剧参与当代的政治和美学批评。尽管语境化的排演通常会对莎剧文本进行改编,但是只要保留戏剧剧场的整体框架,以摹仿和再现情节为基础,那么莎士比亚的文本就仍然是意义的主要提供者。
后戏剧剧场根本性地改变了排演莎剧的方法。在1970年代后出现的这类新型剧场中,文本不再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意义提供者,而“只被理解为和姿势、音乐、视觉等要素相平等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在排演莎士比亚、拉辛、莫里哀、易卜生和契诃夫等经典戏剧时,后戏剧剧场所做的文本改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物形象或情节设置的调整和重塑,而是文本的“去戏剧化”(de-dramatization),也就是说,这些经典文本不再呈现为一个由对话、人物、情节构成的封闭的戏剧性世界,以模仿和再现为基础的戏剧性框架被打破,从而为自我反思性的符号使用敞开了空间。考察后戏剧剧场如何排演经典戏剧文本,不仅有助于揭示后戏剧剧场的文本特征和排演方法,而且可以为解读经典戏剧文本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在这方面,《哈姆雷特》可能是最好的例子。
后戏剧剧场对《哈姆雷特》的“去戏剧化”,其可行性基于这个事实: 随着莎翁崇拜传统的确立和《哈姆雷特》的正典化,王子复仇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哈姆雷特》已经逐渐失去通过情节制造张力的条件。尤其是对今天越来越专业化的剧场观众而言,从全剧的第一个问题“谁在那儿”开始,《哈姆雷特》就没有什么戏剧性悬念。因此,将《哈姆雷特》置于戏剧性框架之外运作,寻找模仿和再现情节之外的替代性路径,不仅具有可行性,甚至应该成为当代剧场的优先考量。本文选取的后戏剧剧场案例并不试图再现莎士比亚笔下的戏剧性世界,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与之对话,突出莎士比亚文本中的独白和声音,彰显演出的现场性和作为事件的意义,这些都是在戏剧剧场中曾经被遮蔽的维度。
一、 “去戏剧化”的独白剧场
1995年,《哈姆雷特: 一场独白》(:)首演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艾利剧院,这是美国导演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一次重要的返乡之旅。作为后戏剧剧场的代表性导演,同时也是这部作品的编剧、导演、舞台设计师和唯一的演员,威尔逊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对《哈姆雷特》原作进行了“去戏剧化”,用独白完全取代戏剧性再现。从哈姆雷特临死之前开始,直到说出最后的下场白结束,15个互不连续的闪回场景勾勒出了整个剧情和整个人生,一切仿佛发生在哈姆雷特的头脑中。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最频繁使用独白的作品,其戏剧效果唯有《理查三世》差堪比拟。哈姆雷特比别人更需要这些可以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刻,是因为他在剧中戴上面具,扮演一个角色,还因为在戏剧进程中,他逐渐被孤立,并被周围人误解,除了霍拉旭,他不能对任何人畅所欲言,不得不采用隐晦迂回的说话方式。当哈姆雷特独自在舞台上时,他有摆脱不自然的束缚、说出自己想法的冲动。从哈姆雷特的独白中,我们既能感受他的解脱,又能理解他在人群中需要注意言辞的压抑状态。
今天我们倾向于将独白理解为一种内省的冥想和情感表达的方式,它像思想的气泡一样运作,表达了自我沟通的内在性。黑格尔认为独白的功能在于:“人物在内心里回顾前此已发生的那些事情,反躬内省,衡量自己和其他人物的差异和冲突或是自己的内心斗争,或是深思熟虑地决策,或是立即作出决定,采取下一个步骤。”帕特里斯·帕维斯将独白定义为“人物对着自己说的一段话”,它区别于对白之处在于缺少语言交流的对象。然而詹姆斯·赫什断言:“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在17世纪中叶之前,任何欧洲戏剧中的独白被设计成内部独白,或被观众视为内部独白。因此,在17世纪中叶之前,只有两种独白,即对观众讲话和对自己讲话,两者都代表人物的演讲。直到17世纪末,独白的历史是这两种独白交替进行的历史,是主流的惯例。”这两种独白可以融合成更复杂的形式。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足够聪明,能够同时在多个层面上处理他们从舞台上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一个角色可能在一次演讲中既对观众说话,又对自己说话,被观众听到,但不被其他角色听到。
从戏剧史的角度来说,莎士比亚属于早期的戏剧剧场,莎剧中的独白延续了中世纪剧场以来的惯例,仍然有其合法地位。然而,独白既意味着戏剧时间进程的暂时中止,也意味着舞台和观众席之间交流轴线的存在,对于以摹仿行动、再现世界为目标的戏剧剧场而言,它始终是一种离心力量。因此,17世纪以后戏剧剧场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排斥独白的过程,到了19世纪,对于独白、尤其是长篇独白的批评变得非常严厉。戏剧家们试图完全摒弃这一惯例,或者至少试图真实地激发它,将其作为一个不安的心灵的表达,或者作为人物在半梦半醒之间无意识说出的话。这些话语停留在舞台内部,演员默认观众不在场,而观众相信他们偷听到了“第四堵墙”后面角色未说出口的心声。
《哈姆雷特: 一场独白》显示了独白在当代剧场的强势回归,它的意义不是作为一种溯源实践,试图恢复独白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功能,而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剧场类型,即以独白作为戏剧文本和舞台基本结构,而放弃人物、对话、冲突、行动等戏剧剧场的形式法则,笔者称之为独白剧场。作为后戏剧剧场的一种类型,独白剧场中的独白首先不是角色对自己说话,而是演员对观众说话,即使演员仍然保留某种虚构的戏剧角色身份,他/她的话语也并不停留在舞台内部的戏剧情境中,不是为了表现角色的人际关系异化、交流障碍和孤独感。在此剧纪录片《制造独白: 罗伯特·威尔逊的哈姆雷特》中,威尔逊谈到,莎士比亚的文本是“一块不可破坏的巨石”,而他呈现的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哈姆雷特》为威尔逊提供了一个创作语境,观众不是在看威尔逊扮演的哈姆雷特,而是看哈姆雷特在威尔逊身上引发的情感和判断。以独白剧场演绎《哈姆雷特》,其目的不是塑造一个复杂、丰满而完整的人物,而是传递一种不连贯的、碎片化的印象,以表演的形式探讨表演哈姆雷特的各种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莎士比亚的原作中,独白赋予观众分享哈姆雷特真实想法的特权,但并不意味着它提供了解哈姆雷特所有秘密的钥匙。事实上,每段独白都会引出新的问题,有些独白还包含了对先前话语的反驳。这不仅是哈姆雷特内心冲突的问题,在几段独白中,这种自我对抗变成了自我戏剧化。有时,哈姆雷特似乎要把自己的情绪推向极端而故意夸大其词,他在这种时候的自我评价并不客观可靠。对莎士比亚来说,独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虚假或扭曲的自我形象,表达了自我欺骗的因素,甚至是蓄意欺骗他人的企图,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哈姆雷特》中独白的特殊戏剧性正是建立在不透明效果之上。
大多数戏剧剧场的演绎都试图澄清《哈姆雷特》中独白的意义,使仅仅被暗示的东西变得明确,相比之下,《哈姆雷特: 一场独白》则凸显了哈姆雷特的自我戏剧化和独白的表演性。这一元戏剧的路径在原作中已经被暗示,而在独白剧场中,通过强调表演性和剧场作为媒介的功能,自我指涉优先于情感或叙事功能,从而引起观众对戏剧幻觉和剧场艺术作为虚构或人工制品的关注。威尔逊并不是戏剧化地扮演哈姆雷特,他让哈姆雷特说出葛特鲁德、奥菲利亚和其他角色的台词,让他展示不同的状态。有时他将台词重复三四次,不断改换重音;有时他听自己的录音,并与之对话,使观者看到他如何看待哈姆雷特所处的情境。例如,对王后的态度表露出一种矛盾心理,“母亲,喝下这药水”这一段表露了哈姆雷特想要毁灭母亲的欲望,而“看王后在那儿”那一段独白表露了哈姆雷特想要拯救母亲的愿望,尽管威尔逊模仿女高音时隐含着嘲弄。有时候威尔逊的表演带有一种古怪的幽默,他用巨大的鹅毛笔记录鬼魂说的话,“再会,再会,记住我”,笔尖的刮擦声像是将纸撕裂,当他停下笔时,刮擦声仍在继续,交替出现的是虫鸣声。在这一场景的最后,一只飞舞的苍蝇干扰他记录,而他不断用笔尖去驱赶它,深沉的痛苦和琐碎的烦恼混合在一起。它提醒我们哈姆雷特的经典舞台形象身着黑色的服装表示始终忧郁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19世纪德国批评家的发明。实际上,哈姆雷特不仅是忧郁的王子,同时也是机智的王子。曾经的宫廷小丑郁利克已经埋在地下二十三年,但他的精神并未消亡,哈姆雷特自己扮演着宫廷小丑,在他身上,悲剧性和喜剧性毫不违和地并存。
作为一部后戏剧剧场作品,《哈姆雷特: 一场独白》不是从独白文本中获得全部意义,姿势、音乐、视觉等要素共同作用于主题表达。它以典型威尔逊风格的视觉构图开场,灯光照亮威尔逊的剪影,他斜坐在六英尺高的岩石上,背对观众,右腿伸出,右手抬起,手指张开,这是一个失衡的姿势,使人产生人物陷入困境、惊恐呼救的联想。背景是一片静谧的蓝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舞台布景,人物仿佛被偶然地抛入某个魔幻空间(正如哈姆雷特从威登堡大学回到厄耳锡诺宫廷),孤独地漂浮于背景之上,不再受自由意志的支配。在这个舞台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灯光,人物的言语和姿势都配合着灯光的变化,仿佛被神秘的力量所操纵,雷曼将之与古希腊英雄由预言所决定的神秘命运相类比。如果说莎士比亚是用复杂的修辞暗示哈姆雷特的自我戏剧化和独白的表演性,那么威尔逊则是用视觉构作传达了“全世界就是一个舞台”这一元戏剧的主题,他甚至比莎士比亚走得更远: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傀儡。
二、 声音与听觉的剧场
布鲁斯·约翰逊指出,《哈姆雷特》成为文学正典,意味着它现在最常以印刷文本的形式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重置了它的特性,因为莎士比亚不是为印刷而是为声音写作,而且是为习惯于细微听觉符号的观众而写作。莎士比亚身处早期现代,那还是一个主要通过口语来交流观念,通过听觉隐喻来理解世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由声音所定义的时代。《哈姆雷特》是一出嘈杂的戏,从开场黑暗中不见其人的说话声,到终场时幕后的炮声,莎士比亚进行了复杂的声音构作,它要求观众在视觉之外感知声音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然而,随着戏剧剧场越来越成为一种以视觉为主导的剧场模式,莎士比亚戏剧的听觉维度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视觉成为戏剧剧场的主导,与西方视觉中心主义传统的确立密切相关。在这一传统中,眼睛被认为是最适宜理性认知的器官,视觉成为通达真理的根本途径,甚至演化成理性、真理、本质的代名词。与此相对应的是,剧场艺术逐渐成为一种静观默察的对象,伸出式舞台退居到镜框式台口之后,场景设计致力于创造视力幻觉,观众的注意力通常被概念化为一种由视觉主导的思维活动,排斥听觉、嗅觉、身体接触等具身沉浸的体验。戏剧剧场当然无法脱离声音,但是无论台词还是音效,出现在舞台上的所有声音都被限制为可供观众解读的信号,声音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文本中的语义信息,而不在于唤起感知的丰富性,正如雷曼所说:“近代剧场演出一直可以看成是文学剧本的朗读与图示。即便有音乐、舞蹈等成分掺入,即使这些成分有时甚至还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从可被理解的叙述与思想的完整性来看,文本依然是主导性的。”
后戏剧剧场存在一个普遍的音乐化趋势,它不是在戏剧情境中加入装饰性的音乐,而是探索声音作为本体的表演性,将非语义性的声音作为一种侵入性、情感性的力量,创造特殊的剧场听觉体验,引导观众对声音、记忆、经验、情感和想象力之间动态关系的理解,并使观众对感知方式产生自觉。在排演《哈姆雷特》,尤其在表现其中的死亡和悲悼主题时,声音所具有的沉浸特征可以激发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性体验,波兰山羊之歌剧团(Song of the Goat)的《〈哈姆雷特〉评论》(—)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山羊之歌剧团受到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的影响,他们沿用戏剧人类学的方法,将训练、排练和表演过程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实验,他们对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和礼拜仪式的圣歌尤其感兴趣,总是寻求将动作、声音、歌曲和文本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内在音乐性的表演,并在感官层面与观众产生联系,被评论家称为“声音与灵魂的剧场”。《〈哈姆雷特〉评论》中没有任何对生活表象的模仿和再现,文本被赋予旋律,14位演员通过声音诠释人物、事件和情感,整部作品主要是以无伴奏合唱形式吟咏死亡与悲悼主题,舞台上的声音和音乐不是为了传递语义信息,而是一种引领观众进入精神领域的能量。戏剧构作阿莉恰·布拉尔(Alicja Bral)的填词朴素而富有诗意,例如《哈姆雷特的哀歌》:
你死后,父亲
鸟儿继续歌唱。
太阳没有黯然失色。
时间没有凝固。
也没有人警告过我。
你留下我一个人
你的沉默使所有的话语都变成了谎言。
我没有信仰,我把手指伸进我被刺穿的一侧,寻求
确认。
你不断回到我的梦中
嘲弄我的生活。
不要带我走,父亲。
比文本更重要的是无伴奏合唱这一形式,这种源自教堂的音乐形式给予表演一个身体的、感性的维度,它实现了一种超越语言和文本的交流,合唱强化了声音的沉浸性,观众不是把声音当作对象,而是具身地成为声音世界的一部分。声音的悲怆和痛苦变成一种精神性的逾越,引发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通过声音传达的情欲交流,并最终建构起一个基于声音和听觉的共同体。这是一场远离莎士比亚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的演出,它似乎发生在一个阴暗的、未定义的、潜意识的区域,发生在人物的头脑和我们自己的头脑之间。
丹麦共和剧团(Republique)与英国老虎百合乐队(The Tiger Lillies)合作的《老虎百合演出〈哈姆雷特〉》()与《〈哈姆雷特〉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演出的基本形式类似“音诗画”,老虎百合以朋克卡巴莱的形式评论了《哈姆雷特》的故事。主唱马丁·雅克(Martyn Jacques)作为一个想象中的司仪,在戏剧事件展开时对其进行评论,他对人物和观众吟唱,但基本不参与剧情。奥菲利亚的疯狂和死亡是全剧中最抒情的场景,它将声音激发感性的力量发挥至极致,不仅正面展示了原作仅仅出自格特鲁德叙述的著名场景,而且提供了与米莱斯著名的拉斐尔前派画作《奥菲利亚》完全不同的俯视视角: 奥菲利亚悬挂在钢丝上,背景是汹涌的浪花,她在半空中旋转,渐渐没入水中。此时,雅克用阴郁怪诞的假声吟唱《释放我》,“我不关心你是否正确,不在乎你是错是对,那里的水在向我招手,过早的死亡等着我,甜蜜的自杀释放我”,借用罗兰·巴特关于“声音纹理”说法,这不仅是演唱乐句,而且是“一个领唱者的身体直接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腔体、肌肉、膜和软骨的深处。……声音的纹理就是: 身体的物质性在说它的母语”。
作为一出复仇悲剧,莎士比亚为《哈姆雷特》提供了一个晦暗的结局。在多次殃及无辜之后,哈姆雷特和他的仇人同时死于一个随机而混乱的复仇场景,没有人欢呼迟来的真相,也没有人庆祝哈姆雷特的斗争。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的赢家是入侵者福丁布拉斯。《老虎百合演出〈哈姆雷特〉》最后以一首《苍凉之歌》中表达了一种宿命感:
你知道他们会把你钉上十字架
你知道他们会让你完蛋
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他们已经,已经抓住你
没什么对,也没什么错
只不过是一首苍凉的歌
这种通过感官而非理性所达到的宿命感也表现在《〈哈姆雷特〉评论》的结尾。当众声喧哗岑寂下来,所有人排成一列面对观众,点燃手中薄薄的纸卷,燃烧的纸卷飞向空中,嗤的一声,便化为白色灰烬,缓缓飘落,就像某个不可见的世界在瞬间的显形,就像死亡和永恒本身。
三、 现场性与当下的剧场
彼得·布鲁克曾经批评道:“没有什么比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更能让僵化剧场找到如此安全、舒适、狡猾的藏身之处了。僵化剧场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莎士比亚。”僵化剧场最易假借虔敬之名,用经典的权威掩饰创作的平庸。然而,所谓“忠于原作”是很可疑的,因为《哈姆雷特》是戏剧史上最著名的不稳定的作品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它是否作为一个单一、确定和独立的文本存在。它至少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早期刊印版本: 1603年的第一四开本,1604年的第二四开本,其长度是第一四开本的两倍,也比第三个版本,即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长200行。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版本中没有一个是由莎士比亚本人批准或授权出版的。尽管有大量的工作致力于“还原”一个未受污染的、作者认可和普遍认同的《哈姆雷特》文本,但我们似乎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仅是版本差异的难题,而且是一个关于剧场艺术特性的根本问题,即作为一种被表演的短暂现象,它使所有稳定的参照物受到质疑。
强调剧场艺术的现场性,即剧场艺术首先不是文本的朗读与图示,而是演员和观众在具体空间中共同度过一段真实时间,这是贯穿20世纪剧场革新的一个主要面向。虽然一般地说,剧场艺术都是现场艺术,但是戏剧剧场的目标是在舞台上建构封闭自足的再现性世界,所以其理想的状态是压抑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排除演出过程中的偶然性干扰。正因如此,“英国国家剧院现场”才能将《哈姆雷特》制作成一个可以随时放映的媒介复制品。后戏剧剧场则更强调相对性(关系优先于实体)、情境化(偶然性优先于必然性)和开放性(建构优先于给定),其现场性往往体现在作品的“未完成”状态。后戏剧剧场在演绎《哈姆雷特》时,意义不是隐藏于六百年前的文本,而是在当下演出过程中生成,并且热情地拥抱偶然性;观众不是作为已完成作品的消极接受者,而是未完成事件的共同创作者。爱尔兰盼盼剧团(Pan Pan Theatre Company)的《排练,扮演丹麦人》(,)充分展示了演出的现场性。
正如剧名所示,这部作品分为“排练”和“扮演”两部分,共同构成“戏中戏”的总体结构。在正式演出前,一位学者牵着半人高的大丹犬走到台前,朗读了一篇讨论《哈姆雷特》版本的学术文章,揭示了《哈姆雷特》文本的不稳定性以及人类状况的不可知性。“做人就是易变的。”他总结道。通过将每场演出的选角权交给观众,《排练,扮演丹麦人》拥抱了这种易变性。在该剧前半部分,导演加文·奎因(Gavin Quinn)对三名有望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进行面试。在风格上,三位演员的试演或偏重思想,或偏重形体,有沉稳、狂躁和忧郁的差异。然后导演让现场观众选出他们的王子,投票方式是观众登上舞台,与自己喜欢的演员站在一起,赢得最多观众的演员胜出,在后半部分演出哈姆雷特故事的缩略版本。
在《排练,扮演丹麦人》中,观众的参与行为不是活跃剧场气氛的点缀,而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主题而言,观众选择的演员成为一种集体意识的投射,它暗示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哈姆雷特,并选择以何种风格扮演这个角色。即使在后半部分演出中,观众仍然清楚地意识到,哈姆雷特不是“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被表演”的形象,这一元戏剧的主题与上文所述《哈姆雷特: 一场独白》有相近之处。从创作方法而言,观众在选择演员的过程中,从消极的旁观者转变成了积极的共同创作者,它使这部作品始终保持开放的未完成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演绎的不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而是现场观众的哈姆雷特,每一次演出因此成为完全当下的体验,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通过观众构作凸显现场性,《排练,扮演丹麦人》远离了布鲁克所批评的僵化剧场。
对“忠于原作”的强调可以被视为莎翁崇拜(Bardolatry)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一传统中,莎士比亚不仅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而且是最高的智者、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以及最忠实的人类状况和经验的描绘者。向莎翁致敬的方式不仅要“照写下来的去演”,而且要尽可能地复原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条件,追求所谓“原汁原味”的风格。英国独立剧团强制娱乐(Forced Entertainment)的《全集: 桌上莎士比亚》(:)项目以完全当代的方式实现了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 既是对莎翁崇拜传统的反讽,又是一次面向当下的真正的莎翁崇拜。
强制娱乐剧团多年来致力于探索仅用语言召唤出场景、图像和故事的可能性,《全集: 桌上莎士比亚》呈现出该剧团代表性的低科技特征,它完全没有再现戏剧性场景,而是以桌面为舞台,以日常物品为角色,由一位表演者叙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同时通过在桌面移动物品展现舞台调度,每部剧作持续40分钟左右的时间。整个项目包含全部36部剧作,每晚演出4部的话,完整的演出需要9个晚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传统概念中的剧场作品,而是一个持续性的事件或仪式。参与这一仪式的观众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建构莎剧场景,在贫瘠的语言和物品的基础上开展无边的想象。
剧中的日常生活物品,如酒瓶、熨斗、刨丝器、洋葱、鸡蛋等等,看似随意选择,却又与角色存在某种联系,有时不乏神来之笔,例如,在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出场时,演员讲到:“国王和王后召来他的密探”,说着掏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卫生纸卷芯放在桌上,随意地瞄一眼,“他们的名字是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有时是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这两人是哈姆雷特的旧友,却被克劳狄斯召来监视哈姆雷特,他们的身份立即被识破,他们的死亡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报复性玩笑。《哈姆雷特》的世界似乎是一个荒诞的宇宙,不是由深思熟虑的行动,而是由意外和偶然支配。斯托帕德的剧作《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已死》发展了这一主题,而强制娱乐则用看似稚拙的表演表达对小人物荒诞命运的深刻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强制娱乐的重述故事并没有改写剧情,也未加任何主观判断。他们的叙述内容简单而奇特,荒诞而引人入胜,使用的语言完全是今天的口语,句法简单,词汇量少,在主要的戏剧行动线之外,尽可能地减少华丽的修辞,例如波洛涅斯对雷欧提斯的著名教导,被简化成“这是一段很长的演讲,他说啊说啊”。这种叙述策略可以看作对莎翁崇拜的反讽和祛魅,然而并无损戏剧故事本身的张力,甚至使某些本质的东西得以凸显。有评论家写道:“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高潮展示了针对女性的暴力,而罗宾·亚瑟讲述的《皆大欢喜》是如此无情,人类在爱情中的彻底荒谬变得更加凸显。”这既是对故事力量的庆祝,又是对戏剧本身的持久性的致敬。
阿尔托曾经宣布“与杰作决裂”。他说:“过去的杰作对过去是适用的,但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有权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说被人说过的话,甚至不曾被人说过的话。我们的语言是立即的、直接的、符合现今的感知方式,而且人人都能懂。”《全集: 桌上莎士比亚》用最朴素的语言和形式重述莎士比亚,使莎剧不再是过去的杰作,而是完全当下的生活,正如剧团总监蒂姆·埃切尔斯(Tim Etchells)所说,其目的是使“意义非凡的莎士比亚戏剧与日常生活碰撞”。这是后戏剧剧场对莎翁崇拜的诠释: 通过使用而非通过供奉。
结语
扬·科特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莎士比亚,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书中提出:“《哈姆雷特》就像一块海绵。除非是以程式化或研究古董的方式制作,否则它立即就会吸收我们时代的所有问题。”莎士比亚的文本是戏剧剧场希望抵达的终点,却是后戏剧剧场创作的起点,它是一组原材料,人们可以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自由的塑造。后戏剧剧场排演《哈姆雷特》,并非对经典文本的轻佻亵渎,也并非单向的利用剥削,而是一种双向的馈赠。经典文本为后戏剧剧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而后戏剧剧场的排演方式发掘了经典文本被戏剧剧场遮蔽的维度,创造了阐释经典文本的新视角、新方法,也使经典文本与当代观众产生新的联结。
当我们为后戏剧剧场的激进改写辩护时,最充分的理由也许在于,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哈姆雷特》就是以同样的先锋实验的态度写成的。它将国王和小丑、悲剧和喜剧、疯狂和理智混在一起,它对非正统改编的吸引力,可能主要并不是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的它具有正典地位和思想上的普世性、永恒性,而是因为其内在的政治颠覆性和艺术实验性。在每一代人中,《哈姆雷特》似乎都具有一种对先锋实验产生吸引力的品质,在无休止的改编中刺激新思维,创造新事物。正如被抛掷进宫廷政治的桎梏中的年轻王子发现的,只有疯狂才是批判规范性经验的激进方式,《哈姆雷特》在根本上反对普遍而支持变革。挑战规则与超越边界,正是剧场艺术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