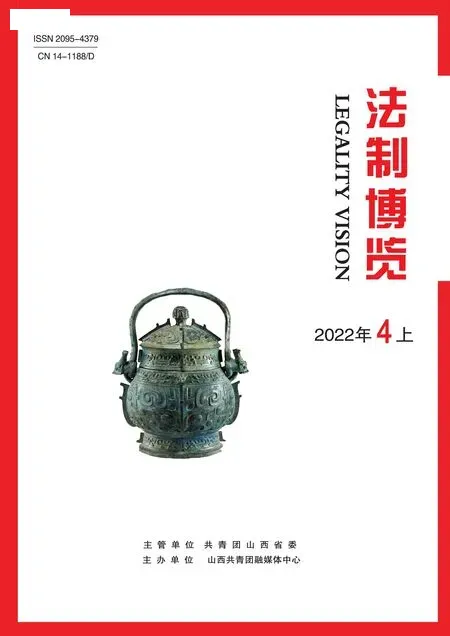“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不足及完善对策探讨
范祥明
甘肃曙明律师事务所,甘肃 临夏 731801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自身权益维护的意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之后,选择通过认罪认罚争取从宽处理的案件逐渐增多[1]。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而言,这种发展现象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最起码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或认罪认罚人员的人权。但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行角度来看,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设层面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极容易在认罪认罚制度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不利于法治社会建设的现象。所以,法律建设者和执法者需要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研究,从根本上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正性,提升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品质。
一、“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内涵
单从有效辩护的角度来看,该理念主要源自1791年《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应当享有……获得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因该法案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明知性和明智性,所以其才能在美国法律建设的过程中被引入和承认[2]。而我国在对有效辩护的研究仍停留在普通程序中维护正当程序的层面,但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价值和意义却是明显的。就目前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研究来看,其意义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其一是有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认罪;其二是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性质和后果;其三是有助于监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争取对被告人最为有利的法律后果;其四是有助于保障被迫诉人自主选择诉讼程序并确定辩护方案。因此,在我国推行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各层级工作人员有必要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工作的研究,争取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二、我国“认罪认罚案件”有效辩护中存在的不足及形成原因分析
(一)辩方权利与控方权利的失衡,影响有效辩护的公正
表现形式:虽然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形式上,法律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有效辩护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影响辩方权利与控方权利的因素很多,如值班律师的职业素养、司法机关的决定权、司法人员的主观情感等。最为明显的是,部分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时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从而导致法院和检察院并不会对值班律师赋予辩护人的身份,令控方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以至于出现值班律师价值不显,量刑辩护工作流于形式等问题。
原因探究:认罪认罚制度的全面展开,从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各类型的诉讼造成了影响,让部分刑事案件也可以像民事案件一样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而人民检察院在量刑的过程中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建议,适当地对定罪项目和量刑的程度上进行调整。但要想让辩方和控方进行平等、有效的协商,显然存在较大的困难。因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方和控方的态势是先天的,本身就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如果被迫诉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帮助,就难以对检察官的公诉权进行制约,从而导致不公正裁判的产生,从而影响整个司法环境。基于被迫诉人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法律帮助的问题,从一定程度取决于司法机关的决策。因为目前只有司法机关才具备启动认罪认罚程序的权力,如果司法机关不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属于认罪认罚的范畴,那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与不认罪的处罚标准则是相同的,除了增加犯罪人员对司法的不认可之外,也会给整个司法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二)惩罚罪犯和保障人权的错位,影响有效辩护的秩序
表现形式:从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现状来看,始终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已经认罪的前提下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有效辩护[3]。基于此,也始终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认罪认罚制度实施的前提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已经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则表示其自愿接受所有的不利于自身的判决,此时的有效辩护则是一种形式上的辩护,仅需要在程序上合法即可。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论案件的形式如何,有效辩护作为司法中的一部分,其应该以更有实质性价值的方式存在,而不能流于形式。虽然从理性分析的角度,第一种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执法者、值班者以及辩护律师是否能够基于有效辩护的价值,重新定位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却难以评定。而且无论法律的规定如何,认罪认罚价值的体现还在于犯罪嫌疑人自身的理解。所以就目前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工作中仍存在着犯罪嫌疑人不配合以及辩护前后量刑标准变化不大等问题,从一点程度上影响了有效辩护的秩序。
原因探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惩罚罪犯和保障人权的制度,其在强调惩罚犯罪的同时,也强调司法者、执法者等应当尊重罪犯的基本人权,从而让整个定罪和量刑的过程更加公正,让定罪和量刑的结果更加的公平。所以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特意设定了值班律师,期待借助值班律师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值班律师做被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见证,防止检察官或其他执法者用威胁、强迫或欺骗的方式,诱导犯罪嫌疑人认罪[4]。在长期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值班律师逐渐模糊了自身的职责,不仅未能及时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更是沦为了诉讼权利行为合法性的“背书者”,打破了认罪认罚制度中惩罚罪犯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从而影响了司法的结果。
(三)司法辩护和辩护质量的悖离,影响有效辩护的效益
表现形式:就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而言,司法辩护是否真实、有效的存在与辩护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从而产生了司法辩护与辩护质量悖离的情况,影响有效辩护的效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两点必须注意的问题;其一是值班律师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司法帮助的第一人,在值班律师的帮助下,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够获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启动的资格。其二是在委派律师、指派律师以及值班律师等的帮助下,犯罪嫌疑人的量刑证据是否能够取得较大的突破。就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在具体司法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以下现象;一是犯罪嫌疑人明明已申请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启动,但司法机关却并未予以通过。二是司法机关已经启动了认罪认罚制度,但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和量刑前后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取决于司法辩护与辩护质量关系。
原因探究:有效辩护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正性的重要保障,但有效辩护是否能够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需要被诉人都能够获得有效的法律援助,这种法律援助应当是基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之上的援助[5]。换言之,就是需要法律援助工作者不仅需要告诉犯罪嫌疑人可以选择的为自身辩护的方式,还需要让辩护具有更为真实的价值。但从目前我国司法层面的建设情况来看,基本已经形成了在律师辩护方面“委托辩护为主,指定辩护与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为辅”的模式,在有效辩护的广度层面具有了较为充足的保障,但值班律师、委托律师或者辩护律师等是否得到了切实的法律帮助,却并未形成较为完善的保障,从而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保障,体现不出有效辩护的效益。
三、我国“认罪认罚案件”有效辩护工作的改进和完善对策
(一)重新定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价值取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基础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系的失衡,从而产生多种不同的司法问题。所以在认罪认罚案件有效辩护工作中,司法者和执法者都需要重新定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价值取向,体现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的价值。如在2018年武某某伤人事件中,二人在酒后因感情纠纷产生争执,随后武某某用床头柜上的尖刀往唐某某的身上捅刺,导致唐某某因失血过多丧生。在该案件中,检察官经过审阅案件材料后认为,案件的证据充分,证据链条完整,可以对其进行定罪和量刑。但在具体审判的过程中,武某某积极地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标准。之后在检察官、值班律师等的帮助下又与被害人家属和解,并出具了和解书。在本案件中,武某某犯有故意杀人的重罪案件,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下,案件采取了量刑建议,从鼓励真诚悔罪和转化教育的角度实现了对武某某的惩罚。不仅对犯罪之人进行了处罚,也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化解。基于此案件的处理结果,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实现有效辩护时,工作人员需要定位清楚有效辩护的价值取向,尽可能地争取对被诉人和社会最有利的结果。
(二)重新调整“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工作范围
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实施,受工作范围的影响,在实际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工作中,不需要过度地探讨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而是需要深度探讨控诉方、辩护方等的权利范围,先实现辩方权利与控方权利的平衡,然后再思考如何诉求司法的公正性。如在2019年5月黑龙江省林业局中丰某某伐树案中,丰某某为了给五味子搭种植架子,用手锯盗伐暴马丁香树121株,其中幼树115株,涉嫌盗伐林木案。在该案件中,为了提升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价值,值班律师提前介入案件,对涉案人员进行了法律讲解,并签署了《认罪认罚承诺书》,对于林业管理部门而言,其根本的诉求除了让违法人员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外,更是需要让违法人员履行“补植复绿”的义务,所以在有效辩护的过程中,值班律师从双方的诉求出发,对控诉方和辩护方进行了引导,让二者在更加平等的条件下提出各自的诉求,从而实现了社会矛盾的化解。所以在实际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时,强调辩方权利与控方权利的平衡是重新调整有效辩护的重要方向。
(三)重新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工作制度
工作制度的建设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实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能够协调好司法辩护和辩护质量之间的关系,各层级工作人员有必要从工作制度的角度进行思考,重新构建更具有操作性和规范性的工作制度[6]。如在2019年武汉吕某某伤人事件中,虽然硚口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充分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向两名犯罪嫌疑人告知可能提出的量刑建议,说明了量刑建议提出的方法,并取得了事件双方的认可,从司法程序上体现出了从快、从简的原则,但理性分析,在这种工作模式下,有值班律师和辩护律师的参与,可以保障司法辩护的广度,但却缺乏合适的衡量标准,如辩护律师及值班律师是否履行职责、在工作中是否存在歧视或侵权行为、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的建议是否规范有效等均未直观地展现出来,难以体现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原则和意义。所以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有效辩护,工作人员需要及时构建相应的工作制度,用以规范、约束和评定值班律师、辩护律师等的行为。
四、总结
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刑事速裁程序的推进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开展,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各层级人员都应当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的研究,找出其中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真正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