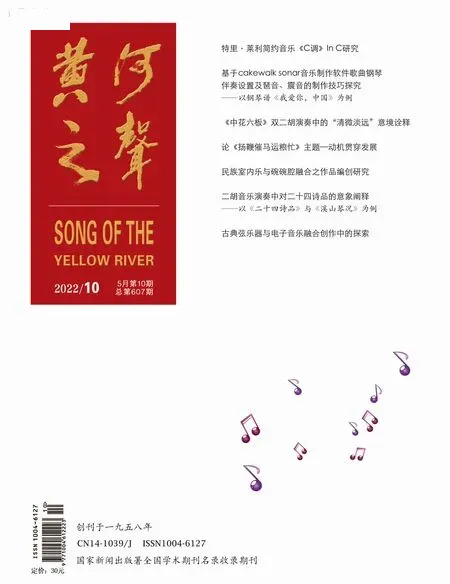论歌唱中的“声”“音”“乐”三分
郜宪福
引 言
歌唱从原始“杭唷、杭唷”的号子发展到今日之歌剧、清唱剧、音乐剧艺术歌曲、诗词歌曲、民歌、戏曲、流行唱法等等,可谓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充分展示了数千年来人类歌唱艺术发展的丰硕成果。特别是在中国,声乐艺术一直备受喜爱,古时候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认为歌唱是超越管弦乐的、更美的音乐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声乐艺术迎来了春天,声乐教育的中外交流频繁多样,国内外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们被“请进来、走出去”,极大拓展了声乐学习者的视野,各类唱法蓬勃发展,声乐乐坛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生机和态势。
关于歌唱有诸多概念和术语,如“腔体、共鸣、气息、声音、音色、音乐、乐感、声线、声腔”等等,大多与歌唱的技术有关。其中“声”、“音”、“乐”是最难分辨的,也是最重要的三个概念。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就有“声”“音”“乐”三分的理念和思想,三者的含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古代有“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声”的表述,老子主张“大音希声”,《乐记》中也有“夫乐者,与音近而不同”的说法,可见“声”“音”“乐”三分代表着从声音到音乐的不同层次。古典文献《酉阳杂俎》中对此的解释颇有启发意义:“乐”为器乐,“音”为音曲,“声”为单声。按照王小盾教授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乐、音、声三分:经部·乐,内容为乐书,《四库全书》评价其为“大乐”;集部·词曲,内容为曲词,《四库全书》评价其为“乐府之余音”;子部·艺术,内容为杂艺,《四库全书》评价其为“讴歌末技、管弦繁声”。这种三分理论不仅是音乐文献、形式的分类,更包含着伦理等级的差别。[1]这种理论多为音乐史学学者关注,对于声乐学习者来说似乎与自己毫无瓜葛,不知又何妨。然而从一个艺术家、歌唱家、声乐教育家的基本素养来看,这一理论有着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声乐学习者在面对一些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声乐困惑,用此视角解读会产生拨云见日的神奇效果。
一、“声”、“音”、“乐”的诠释
在中国音乐史上“声”、“音”、“乐”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声”是一切因振动而产生的声音、音响,“音”是“声”中好听、悦耳的部分,即去除杂音、噪音后留下的部分,“乐”是“音”的有机组合,也就是说把“音”变成“曲”后形成的美好、动听的艺术作品。从科学唱法的角度来看,声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歌唱中所不能用的,因为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对音色有着近乎极致的追求,一般带有杂音、喉音的声音是不完美的,需要经过大量科学的、成体系的发声训练,保证所发出的声音都是“音”。因此,打开、放松、稳定的腔体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而且这些腔体(头腔、口咽腔、胸腔)是可调节的、自由控制的、协调的,要根据歌曲风格、情感情绪的需要改变各个腔体的大小和比例,从而保证以完美的技术来演绎音乐作品。但是并不是歌唱中没有不完美的音,一方面,歌唱者的嗓子、身体是随时变化的,可能因为疾病和疲劳会产生一些声音瑕疵,形成音色缺陷;另一方面,一些特殊的歌曲乐句、歌词因表现的需要,要求演唱者发出一些嘶哑或、带有喉音的声音(如表现痛哭中撕心裂肺的声音等)。在发声训练中,演唱者通常要尽力去除喉音和杂音,努力发出干净、明亮、清澈、饱满的乐音。
由“音”至“乐”是一种高级的艺术意识和理念。通常音乐界所说的乐感,是音乐演奏者、演唱者对于音乐线条的处理感觉和方式。在声乐中就是:演唱者通过发声训练获得了美好的“音”之后,如何变成一个个动听、感人的“乐”的旋律线条,这是一种对“音”的组织和控制能力。其中包含着歌唱时呼吸、腔体的控制和运用,如何保证身体各个器官、肢体的协调性;同时也包含着对节奏、节奏型的理解,也包含着对音乐动机性格和气质的解读。即便演唱者已经拥有了较高超的发声技术、歌唱技巧,在面对具体音乐作品时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简单的发声训练无法表现纷繁复杂的音乐动机的节奏型。一般声乐训练中,呼吸的练习分为快吸快呼、快吸慢呼、慢吸慢呼、慢吸快呼等几种,这种训练只是呼吸方法,距离演唱实践还有一定的距离。歌唱的气口在不同作品中要有专门的设计和规划,往往超出了发声训练的要求和难度,同时节奏的特性也会制约着歌唱者的演唱效果。比如《游击队之歌》,音乐的速度很快,乐句中大量的十六分音符和密集的歌词留给演唱者换气、吸气的时间很短,需要用极其灵活的呼吸来抢气。其次,音乐的节拍变化也是发声训练中不常有的。音乐专业院校使用的发声练习曲没有固定的曲目,即便是《孔空练声曲》也是不为大部分声乐教师所用。声乐老师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教学模式和体系习惯性使用一些常见的练声曲,如五度音阶上下行,大三和弦分解进行等,所谓的变化也无非是连音和跳音、速度的改变而已,在强弱变化上的训练十分稀少,因此与音乐作品中节拍的表现需求相去甚远。比如歌曲《美丽的心情》中6/8拍的强弱变化,在发声训练中就基本不出现,歌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借用的戏曲中的一些节拍1/4(“我为祖国生、我为革命长”这一句)是普通歌曲不常见的,这些都需要针对歌曲片段的具体需要进行专门训练。再次,作品演绎中音乐的连贯性也远远超出了发声的要求。发声训练中歌唱者的主要精力会潜意识地集中在音色、共鸣、呼吸等方面,对音乐的连贯性和表现力的要求自然会降低,而演唱声乐作品时又要求歌者技巧服从于音乐,因此发声与演唱形成了一定的隔阂和障碍。特别是在一些长乐句中,歌者往往力不从心,或是气息不够用,或是音乐的连贯性、表现力不足,无法达到演出的完美水准。比如歌曲《我爱你,中国》开头的引子连续的高音和长音,每一口气都要演唱两个长音,而且两个长音又要连贯成一个乐句,不能形成割裂,就是一般发声练习曲中所没有的难度。最后,大幅度的音域变化和歌词咬字吐字拉大了发声训练与演唱实践之间的距离。平时的发声练习曲中多为简单的母音,偶尔加一点辅音,然而歌曲中的咬字吐字却是变化莫测,尤其是中国作品中的快速部分,大量的母音堆积、辅音变化对唇齿舌的灵活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加之还会有各种大跳、小跳的音高变化,形成了一个个演唱难点,这些也是练声曲远远不能满足和替代的。中国普通话不仅母音比意大利语多了许多倍,而且还有“阴阳上去入”的声调要求,光有娴熟的歌唱技巧也不够,很容易闹出类似费翔的“鬼(归)来吧,鬼(归)来了”等笑话,因此演唱者不仅要唱好乐音,还要掌握中国的腔音(一体多音或音高可变化的乐音)。比如歌曲《我爱你,中国》开头“百灵鸟,从蓝天飞过”,其中的“鸟”字不加腔音就会唱成“尿”、“蓝”字唱成“烂”,这都会形成听觉错误,甚至造成“音乐笑料”。
由此可见,由“声”到“音”是一个技术问题,是解决歌唱的科学性难题;而由“音”到“乐”是一个艺术挑战,是个别组成整体的艺术方案,是化技术为艺术的音乐目标和归宿。歌唱者要从音乐审美和表演美学的角度理解“声”、“音”、“乐”的三分关系。
二、“声”、“音”、“乐”理念的歌唱训练
更新歌唱训练理念,重视音乐性的练习。目前声乐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重技术、轻艺术(乐感),许多歌手整天苦心钻研,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解决打开喉咙、去除喉音、美化音色、获得轻松自如的高音、气息的控制力等方面,在琴房练声时基本上不太关注音乐的流动性、流畅性、活跃性。这一现象不仅在声乐界,在器乐界也十分常见,许多琴童都是技术一流、乐感偏差。几乎所有我们请进来的国外声乐大师都始终给学员们强调语言感觉和音乐感觉,认为中国歌唱演员的发声能力十分突出,高音通透、声音明亮、有爆发力,唯独缺少音乐意识。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声乐作为音乐形式的一种,其本质属性是音乐性,人声只是一种媒介。舞台上表现出的乐感缺失,反映出台下琴房里歌唱技术技巧与音乐处理练习的不均衡,我们过度追求了技术,忘掉了技术服从于艺术的基本原则。当然有些人认为音乐理解、处理本身就是一种技术,这种理解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对于技术技巧的使用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和素养。
用音乐分析知识指导声乐训练。所有的声乐作品都是从动机发展而来的,不同的动机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和气质,歌唱时表现这种特点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比如歌曲《春天的芭蕾》的动机是一种三拍子、快速的舞曲风格,要想唱好此曲就要针对性练习舞曲风格动机的演唱,突出气息的灵活性,明确地唱出强拍,并用呼吸把音乐的舞动性、连贯性表现出来,形成既有明显的强弱节拍、又有流畅、活泼的、炫舞的音乐感觉。歌曲《大地飞歌》是同主音宫羽调式交替转换的双乐段曲式,两个乐段的动机性格完全不一样。第一个乐段(“踏平了山路唱山歌……”)是五声羽调式,本来应该是含蓄内敛,但是徐沛东给配上了鼓乐等打击乐,形成了柔中有刚的舞动性格,显得气势宏大豪迈雄壮。第二个乐段(“唱过春歌唱秋歌……”)变成了同主音的宫调式,本来应该有类似大调式的阳刚,但是作曲家却创作成了抒情、平缓的旋律,配器也是以弦乐为主,显得十分温情。这种刚柔并济的作曲手法是一般歌唱者并不能准确把握的,需要作曲家的细致讲解和耐心指导。这种A、B两个乐段动机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作品,在演唱时需要演唱者体察作曲家的创作初衷和目的,不能盲目地、不加比较的演唱。如果用同样的情绪演唱这两个乐段,就属于典型的有技术、没音乐的瞎唱。
中国作品演唱中腔音意识的训练与形成。我们平常学习的乐理都是西方体系,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知之甚少,在演唱时运用到中国声乐作品上会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调式体系、行腔润腔的差异等等,其中腔音的演唱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惑。在西方乐理中单个乐音都是固定音高的,不能发生改变。而中国乐理中的腔音却是“多音一体”或者是“可变化音高的乐音”。也就是说,腔音超越了单个音的概念范畴,已经有了乐的含义。原因在于汉语声调的重要意义,即同一个声音的字因声调的不同而意义完全不同。这些困惑在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里完全不存在。所以腔音不是装饰音,不能用装饰音的思维来理解。腔音的“音”因为包含了“腔调”而显得与众不同,同样也因此成为中文歌曲演唱的难点和重点。民族声乐中的行腔、润腔、腔调、创腔、腔韵等音乐意识也需要在发声练习中专门训练,可以用民族歌曲中的部分唱段、乐句、字句进行范例性训练,从而演唱出深受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声乐作品。
结 语
由声到音、由音到腔和乐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歌唱艺术之美因此而产生。声乐是歌唱之乐,是音乐家唯一以自身作为乐器而发出的声音艺术。正因为如此,这个乐器的操作成为一种极度抽象甚至不可描述的过程(其他乐器都是有形的,甚至是固定音高的,演奏过程也是具象的),这就造就了歌唱学习的特殊性。歌唱者需要借助镜子才能看见自己的“乐器”,但演唱中也只能看到外表的动作和表情,声带和共鸣箱具体工作的状态和模式仍然无法看清。源于此,可以说歌唱家必须是智商极高、乐感极好、表演能力超强的全能型人才,而且必须有良好的嗓音天赋,可见其有多么稀缺。在歌唱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有全局性思维,坚持艺术性理念,并不断提高其人文修养,不能以“声”代“音”、以“音”代“乐”,要深刻理解声音材料和声乐作品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声乐课堂需要不断改革、进步,汲取其他音乐艺术的营养,同时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理念和思维,努力提升声乐课的教学效率。金铁霖教授曾提出民族声乐的四性(民族性、艺术性、科学性、时代性),其中的时代性不仅仅是歌唱演员的演唱特点,也是声乐教育、教学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如此,民族声乐教学才能永葆青春,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