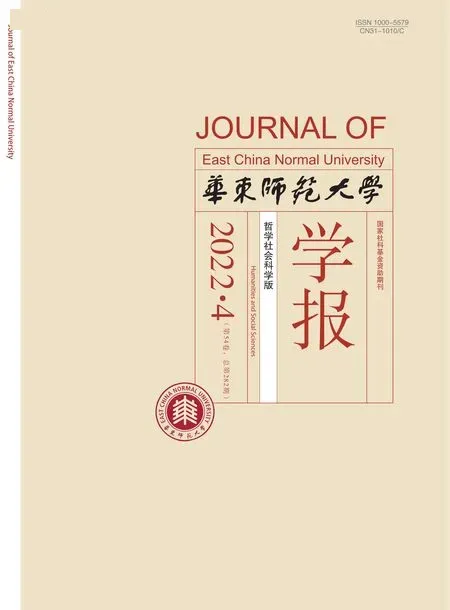塑造纪念的时间:全球思想史视野下的帝国日
朱联璧
苏迪普·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认为,思想史既包括研究观念的出现和传播及其所在语境的历史,也包括与社会史的认识兴趣更为接近的,有关“评价理念或思想过程的因果效应的重要性”的历史。①Sudipta Kaviraj,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Meanings and Methods,”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95; p. 304.克里斯托弗·L.希尔(Christopher L. Hill)对以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抽象概念在更广泛世界中的传播机制的分析便是前者的代表,指出受众和观念之间存在协调(mediation),并被认为是全球思想史的研究探索。②Sudipta Kaviraj,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Meanings and Methods,” 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95; p. 304.若以后一种方式来理解民族主义,则不仅需要考察体现这种观念的文本,还要考察由此引发的实践,例如被认为属于特定民族的民众是否愿意加入该民族的国庆节活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五一节(May Day)的研究和以克里斯蒂安·阿玛尔维(Christian Amalvi)对法国国庆节的研究为代表的成果,表现出了欧洲学术界对纪念日的研究兴趣。前者回顾了国际性纪念日在不同国家的实践,后者追溯了7月14日如何被确立为法国国庆节进而成为该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不同立场的人士又如何利用这一象征来表达自身认同。③[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年的欧洲》,[英]E.霍布斯鲍姆、[英]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63—370页;[法]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七月十四日:从狂暴之日到庆典之日》,收录于[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9—138页。阿玛尔维从实践和广义的文本中探讨民族这种观念的社会影响,可被视为是与社会史有相似旨趣的思想史研究实践。不过,无论是此后对五一节的研究,还是对本文所要讨论的帝国日(Empire Day)这类跨国性纪念日的研究,数量都比以国庆节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纪念日要少。
将阿玛尔维对法国国庆节的研究方法拓展到一国之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人类学家卡罗拉·伦茨(Carola Lentz)等人对非洲多国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一系列研究便是一例。他们解析了民族独立这种观念是如何通过仪式在不同国家的语境中表达的,探究了仪式将民族实体化(embodying)的过程,引入了比较研究的维度。①Marie-Christin Gabriel, Carola Lentz and Konstanze N’Guessan, “Embodying the N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in National-day Parades,” Ethnography 21(4), 2020, pp. 506-536.拙著《加拿大国庆节的诞生与发展(1869—1942)》 在探讨加拿大国庆节的起源和流变的过程中,论及加拿大之外的庆祝活动如何呈现其他民族的成员对加拿大的认识,以及参与海外活动的加拿大人如何定位自身认同,从空间和全球性影响的角度讨论了特定民族国家的纪念日在本国之外如何被理解,作为反观加拿大认同的棱镜。②朱联璧:《加拿大国庆节的诞生与发展(1869—194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而以帝国日和五一节为代表的全球性纪念日,同样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传播、接受、排斥和再生产。因此,研究与帝国日相关的纪念日群组如何被创设、改造与实践,同样是在探求节日背后的全球思想史。本文将在梳理出适用于研究跨国性纪念日的概念工具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帝国日及其变体被发明的过程,指出不同变体折射出了帝国不同身份的成员对帝国和本民族的认知。既有全球史研究大多侧重空间维度的扩展,而本文则尝试深化对时间维度的理解,进而更多地展现纪念日的参与者的能动性和多样性,侧重从行动者而非经典文本和政治家的角度,剖析有关帝国和民族的观念在全球流动的历史及其产生的实在效应。
一 塑造纪念的时间
全球史著作对时间的讨论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关注的是全球各地如何接纳或抗拒时间的标准化,将时间作为研究对象。③[美]瓦妮莎·奥格尔:《时间的全球史》,郭科、章柳怡译,孙伟译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另一种关注的是全球史研究应如何划分出特定的时间范畴来确定研究对象,此举也意味着赋予研究对象某种特点。④[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七章《全球史中的时间》中的讨论,杜宪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世界的演变》 的引言中指出历史学的不同分支都有其特有的时间结构。⑤[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页。选择某一时间段开展研究,也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历史观。不过,对于和时间的关系尤为密切的跨国性纪念日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与纪念日有关的时间可以被细化为事件的时间、休假的时间、参与者的时间和纪念的时间。事件的时间即生成纪念日的“因”,纪念的时间则为“果”。休假的时间展现的是各级政府对纪念日的承认,以立法赋予事件的时间以休假的功能为标志。参与者的时间对应的是不同立场的民众对纪念日背后的观念的理解和态度。他们所在的区域、所抱持的传统,所属的社会阶层、职业和性别都会影响他们对纪念日的理解。
创设国庆节意味着国家要为某一天发生的事情(happening)赋予建国神话的地位、构建相关的合法性叙事,并以宣告或立法的方式将事情发生之日认定为假期,确保参与者可以放下工作、参与活动(教会弥撒或街头庆祝)且不会对他们的收入和生计产生影响。①Gabriella Elgenius, Symbol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elebrating Nationhoo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65-178.一旦目标受众参与了庆祝活动,也就认可了国庆节的合法性及其背后的观念,让事件的时间、休假的时间、参与者的时间和纪念的时间得以重合。不认可国庆节活动的群体,可以利用休假的时间自行组织活动,或是塑造新的纪念日,并为之构建正当性叙事。②朱联璧:《加拿大国庆节的诞生与发展(1869—1942)》,第19页。相比之下,跨国性纪念日的缔造者缺乏将事件的时间与休假的时间结合起来的权力,加之参与者的时间过于多样,削弱了纪念的时间的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同一或同类事件会在不同时空促成不同的纪念的时间,无法实现四种时间的协调。五一节便是一例。
霍布斯鲍姆在研究五一节时明确排除了劳动日(Labour Day),理由是这个看似与五一节有关的节日并没有仪式上的意义。③[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 年的欧洲》,[英]E.霍布斯鲍姆、[英]T.兰格:《传统的发明》,第363—364页。但这两个纪念日都是为纪念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成就而设立,分别发展成了全球性和地方性纪念日。与劳动日有关的事件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82年9月5日(星期一)。在此之前,美加两国各类工人团体都组织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活动,但时间并不固定。④加拿大的情况见 Craig Heron and Steven Penfold, “The Craftmen’s Spectacle: Labour Day Parades in Canada, the Early Years,”Histoire sociale / Social History 29. 58 (November 1996), p. 362。1882年9月5日,美国纽约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两年后,组织这一活动的机构倡议将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确立为劳动日,并得到了其他工人组织的响应。在手工艺人团体和美国工人联盟的共同努力下,美国总统斯蒂芬·格罗夫·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在1894年6月28日签署法案,将劳动日确立为全国假期,用于庆祝工人的成就,展现有组织的工会的实力和团结。参与者将自身定位为爱国的好公民,穿着统一的制服参加活动。⑤Donna T. Haverty-Stacke, America’s Forgotten Holiday: May Day and Nationalism, 1867-1960,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5-70.同年7月23日,在时任加拿大总理兼大法官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John Sparrow David Thompson)的推动下,劳动日成为了该国的公众假期。⑥加拿大王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也支持确立劳动日假期,见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7 May 1894, 7th Parliament,4th Session, vol. 1, column 2410。将假日固定在星期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商业活动的影响,与参与者的时间匹配。换言之,作为纪念的时间的劳动日和国庆节一样,是与休假的时间和参与者的时间协调的,以便民众接纳,相关叙事可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衔接。即便劳动日与事件的时间的关联并未被完全切断,但与之相关的叙事,以及纪念日和社会主义思潮的联系均被淡化。⑦如Historical Labor Day 1898, Souvenir and Official Programme, Toronto: Unknown Publisher, 1898。这份资料中提及劳动者对国家的贡献,将劳动者的纪念日变成了全民的节日。
而在劳动日获得官方认定之前,五一节的传统也发展了起来。在美国多个劳工组织商议应在1886年的哪一天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游行的过程中,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成员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提议维持1882年的安排。负责组织这次活动的商业组织与工会联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的加百利·爱德蒙斯顿(Gabriel Edmonston)却提出应在5月1日举行活动,理由有三:一是这天是建筑行业合同的起始时间,与他所在行业的关系密切。二是为了纪念1867年5月1日在芝加哥举行过的活动。三是因为这天是所谓的“五月搬家日”,很多租房合同会在这天重新开始计算,因此有望吸引搬家的人们参与活动。最终,商业组织与工会联盟的成员投票认可了这一时间安排。①Haverty-Stacke, America’s Forgotten Holiday, pp. 23-27.
1886年的活动开始后引发了5月4日的干草市场惨案(Haymarket Tragedy)。虽然这一惨案的影响力之大使之有潜力成为被纪念的事件,但晚近的研究表明,第二国际在1889年决定将庆祝劳动者成就的节日安排在5月1日的主要理由不是为了纪念此事。第二国际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巴黎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来自法国的参会者建议在次年5月1日(星期四)组织抗议活动,理由是美国工人联盟(American Federal of Labor)已经确定要在这一天举行活动。在该建议得到认可后,第二国际给予各国工人以充分的灵活性来选择次年活动的形式和安排,避免他们必须在工作日参与游行而被认为是“罢工”,激化与雇主之间的矛盾,也没有要求必须组织纪念干草市场惨案的仪式。②例如马克思的女儿爱莲娜·马克思所参加的1886年的五一节活动就是5月4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组织者有意将活动安排在了星期日,见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A Biography, Vol. 2: The Crowded Years (1884—1898), London: Verso, 2018, part III。时人甚至担心,干草市场惨案所具有的暴力性质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会让某些工人团体的成员拒绝在这一天参与活动,不利于吸引和团结不同类型的工人加入。再者,欧洲原本就有五旬节的假日传统。③关于这一认定的讨论,见Herbert Reiter, “The Origins of May Day: History and Memory,” in Abby Peterson and Herbert Reiter eds, The Ritual of May Day in Western Europ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14-30。这也是后来部分国家的工人将五一节称为“工人的复活节”的理由之一。换言之,欧洲的五一节利用了前现代已有的假日,让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庆祝自己的成就,展现自己的理念。④[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激进传统·节日的诞生:五一劳动节》,《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王翔译、柯雄校,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6—188页;第183—186页。
第二国际在1891年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发表了针对五一节的决议,建议国际工人运动每年庆祝劳动节,确认举行活动不是为了悼念干草市场惨案中的受害者,从而引发支持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团体的不满。决议还要求将活动固定在5月1日举行,要求组织者纳入“推行劳工立法”和“反对战争”这两个主题,吸引工人之外的群体加入。⑤[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激进传统·节日的诞生:五一劳动节》,《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王翔译、柯雄校,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6—188页;第183—186页。但由于第二国际没有能力赋予五一节假日的功能,也很难完全主导各国对五一节的叙事和活动安排,因此无论所在国政府是否将五一节认定为假期,民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经验和身份(包含地方节日传统、阶层、区域和社会性别等因素)来选择度过这一天的方式。在实践层面,参与者的时间会持续地产生影响,增加纪念的时间的不确定性。
通过简要展现与五一节和劳动日相关的四个时间之间不同的关系,可以看出获得民族国家认定的纪念日相对容易实现四种时间的协调,更利于传递节日所承载的带有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跨国性纪念日则很难实现四种时间之间的协调,参与者的重要性因而更大,催生大量地方性变体。所以,在研究跨国性纪念日的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多个相关的纪念日的情况,进而全面展现纪念日群组所承载的观念在全球范围内传递的情况。
二 缔 造 帝 国 日
与帝国日有关的纪念日群组可分为原生的帝国日和扩展的帝国日,以及平行变体(parallel variation)、继承变体(successive variation)与替代变体(alternative variation)。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可以使用四种时间来分析其特点,从中挖掘帝国各处的群体对帝国的不同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之后如何影响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识,彰显了参与者如何推动跨国性纪念日的生成和变化。同时考察这些案例并展开比较,有助于解决已有帝国日研究中存在的分歧,突破单纯从帝国或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研究帝国日所存在的局限。
原生的帝国日源自加拿大,主要创设者有两位。一位是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中学女教师克莱芒蒂娜·费森登(Clementina Fessenden)。她是英国移民的后裔,认为有必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向年轻一代强调加拿大和英帝国的联系。①Molly Pulver Ungar, “TRENHOLME, CLEMENTINA,” in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vol. 14, University of Toronto/Université Laval, 2003-, accessed January 25, 2022, http://www.biographi.ca/en/bio/trenholme_clementina_14E.html.另一位是时任安大略省教育部门负责人的乔治·W.罗斯(George W. Ross)。他让帝国日获得了官方背书,也促成了相关活动得以在加拿大推开。
1896年6月6日,费森登参加了汉密尔顿的温特沃斯历史学会(Wentworth Historical Society)举行的活动,并提议通过不同的手段帮助学生铭记帝国的历史,传承英国移民后裔对母国和帝国的忠诚。②“Everyman’s World,” May 1916, in The Founding of Empire Day, Hammilton, Bermuda: The Bermuda Press, Limited, 1926.此后,她积极联络各级学校的董事会,希望学校可以在公民教育中投入资源以达到上述目的,并得到了响应。她还致函省级和联邦的政界要人,希望政府能指定一天,让学校向青少年传授帝国的历史,解释帝国的旗帜的含义,与美国当时盛行的同类活动相抗衡,让年轻一代认识到自己和美国人的差别,进而增进对加拿大的认同。于费森登这类英国殖民者的后裔而言,增进对帝国和对加拿大的归属感是相辅相成的。
次年,英帝国各地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组织了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庆祝活动,出版了大量介绍性和纪念性文献,讲述女王的生平和帝国的成就。亲帝国的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威廉·J. 麦克唐纳(William J. MacDonald)在这年4月向议会上院提出动议,要求将女王生日(5月24日)认定为全国性的维多利亚日(Victoria Day)公众假期,以展现加拿大对帝国的忠诚。③Senator Bill, An Act to Commemorate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by Making Her Birthday a Holiday For Ever, Ottawa: S.E. Dawson, 1897.此举试图通过立法将女王的诞生认定为“事件”,塑造具有休假功能的纪念的时间,但未获成功,这反倒激励了费森登创设一个纪念日来达成同样的目标。④Chris Tait, “The Politics of Holiday Making: Legislating Victoria Day as a Perpetual Holiday in Canada, 1897—1901,” in Matthew Hayday and Raymond Blake eds, Celebrating Canada: Volume 1: Holidays, National Days, and the Crafting of Identitie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p. 89.
1898年5月22日,费森登所在地附近的小镇顿达斯(Dundas)组织了首次庆祝帝国成就的活动。⑤Marcel Martel, Allison Marie Ward, Joel Belliveau, and Brittney Anne Bos, “Promoting a ‘Sound Patriotic Feeling’ in Canada through Empire Day, 1899—1957,” in Hayday and Blake eds, Celebrating Canada, p. 115.8月,乔治·罗斯明确设立帝国日(而非费森登想要的旗帜日)作为推广爱国情怀的节日名称,时间为每年5月24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教学日,确保可以在学校内组织活动,让学生参与并接受教育。⑥朱联璧:《帝国日的产生和跨大洋传播(1899—1958)》,《全球史评论》(第十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95—196页。这一建议很快被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新斯科舍省的学校采纳。罗斯所在的教育部负责筹备安大略省学校的活动。至1900年,帝国日庆祝活动已在加拿大全境出现。⑦Marcel Martel, Allison Marie Ward, Joel Belliveau, and Brittney Anne Bos, “Promoting a ‘Sound Patriotic Feeling’ in Canada through Empire Day, 1899—1957,” in Hayday and Blake eds, Celebrating Canada, p. 115.
原生的帝国日萌芽之初,英帝国正面临着第二次布尔战争和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两件大事,促成了加拿大议会在1901年确认每年的5月24日为维多利亚日公众假期,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创设了一个能协调四种时间的民族国家的纪念日。在议会商议此案的过程中,费森登表示如果联邦议会不创设维多利亚日,那么现有帝国日应被更名为维多利亚帝国日,扩大活动的内涵,同时庆祝女王和帝国的成就。①Tait, “The Politics of Holiday Making,” pp. 99-102; pp. 102-103; p. 99.
需要指出的是,维多利亚日纪念活动的叙事主要围绕女王本人展开,不会刻意凸显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获得多数加拿大民众的认可,尤其是反帝国群体的认可。相较而言,原生的帝国日不具备假日功能,被安排在维多利亚日的前一天,明确将帝国作为纪念的对象的做法,虽然会引发对帝国不满的群体抵制赞颂帝国的活动,却也保证了活动的目标受众(青年学生)能参与。②Tait, “The Politics of Holiday Making,” pp. 99-102; pp. 102-103; p. 99.两种不同的安排都体现了参与者的时间的重要性。
当1899年加拿大各地要举行帝国日活动的消息通过《泰晤士报》 (The Times)传到英国后,慈善家米思伯爵(Earl of Meath, Reginald Brabazon)建议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将这种活动形式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推广。张伯伦接纳了这个建议。③“News in Brief: Canada,” The Times, March 20, 1899, p. 8; Lord Meath, “Empire Day,” The Times, April 25, 1899, p. 3.这便是扩展的帝国日的由来。1902年起,米思伯爵亲自在报纸上发文,在议会内发言,希望能在英帝国的殖民地推广帝国日假日,但未获成功。次年,他将5月24日认定为帝国日,鼓励帝国各地在当天组织“帝国日运动”(Empire Day Movement),讲述帝国的成就,教育帝国的臣民,明确具有宣传帝国主义的功能。④朱联璧:《帝国日的产生和跨大洋传播(1899—1958)》,《全球史评论》(第十集),第198—201页。也是在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出现了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生日的活动,形式和目标受众都与原生的帝国日高度相似。⑤Tait, “The Politics of Holiday Making,” pp. 99-102; pp. 102-103; p. 99.
尽管扩展的帝国日与原生的帝国日并不在同一天,但针对的是同一个事件的时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诞生,纪念日的目标都包含增进对帝国的认可,教育的对象以青年人为主。至此,可以简单总结维多利亚日、原生的帝国日和扩展的帝国日这三个相互关联和影响的纪念的时间与另外三种时间之间的关系。维多利亚日与劳动日相似,是可以与事件、休假和参与者的时间相协调的。原生和扩展的帝国日与五一节一样,都拥有成为跨国性纪念日的潜力。费森登创设纪念日的初衷仅是希望能在加拿大(甚至是安大略省周边)组织教育活动,但乔治·罗斯推动组织的帝国日活动引发了帝国其他地区的模仿。不过,扩展的帝国日依然无法和休假的时间相互协调,因为帝国缺乏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立法确认公众假期的能力。然而这并不妨碍帝国日最重要的目标受众参与活动。殖民地还是会出现帝国日的活动。目标受众会根据自己是否支持帝国来选择参与活动,殖民地政府会基于自己对帝国的态度,选择是否通过立法为纪念日赋予休假的功能。
三 帝国日的分化
英帝国在20世纪经历的变化,让参与者对与帝国日有关的叙事产生新的理解,不同的力量各自塑造了与帝国日有关的变体和活动,让这个跨国性纪念日成为了新的认同生成的土壤。帝国日的变体可分为平行变体、继承变体和替代变体三类,与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认同、英联邦认同和前殖民地的民族认同相互对应,折射出原生和扩展的帝国日在不同空间产生的影响,也能涵盖多数帝国日的变体的情况。
在加拿大,由于维多利亚日、原生和扩展的帝国日共享事件的时间,导致无论是平民还是政治家都无法清楚区分三者。①见如“Hamilton News to Make Victoria Day Celebration A Big Affair,” The Globe, 27 April 1907, p. 5;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5 May 1922, 14th Parliament, 1st Session, vol. 2, pp. 1769-1770。参与者由此也混淆了与纪念日最直接相关的观念,使三者共同成为推广帝国和加拿大认同的手段。不过,无论是帝国日所具有的军国主义色彩,还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影响的不断增加,都让帝国日的影响力在20世纪20年代日益减弱,情况在以说法语人口占据多数的魁北克省表现得尤为显著。②Robert M. Stamp, “Empire Day in the Schools of Ontario: The Training of Young Imperialists,”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vol.8, no. 3, 1973, pp. 39-41;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24 June 1925, 14th Parliament, 4th Session, vol. 5, p. 4849.多拉日(la fetê de dollard)这种关联次民族国家的、有欧洲根基的群体的认同的纪念日的出现便是例证,它也是帝国日的平行变体。
1917年之前,魁北克的新闻报道依然愿意将省内说英语的社群庆祝帝国日的情况记录下来,赞颂帝国的成就,呼吁帝国内部团结。其他省份说法语的加拿大儿童被要求参加学校的帝国日活动,但活动中会穿插法语歌曲,推崇帝国主义的修辞较少,以期获得参与者的认可。法语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呼吁民众效忠帝国,表述和措辞都较为积极和正面。③Joel Belliveau and Marcel Martel, “‘One Flag, One Throne, One Empire’? Espousing and Replacing Empire Day in French Canada, 1899-1952,” in Hayday and Blake eds, Celebrating Canada, pp. 129-132; pp. 132-136; p. 137.1917年募兵危机爆发后,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日益强调自己独特的民族认同,且认为这种反帝国的认同应是加拿大认同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在实践中的表现,是魁北克省说法语的加拿大人选择以被重新发现的民族英雄奥姆的亚当·多拉(Adam Dollard des Ormeaux)作为在每年5月24日举行的活动的纪念对象。即便与多拉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的时间并不在5月24日这一天,但有着魁北克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者选择在这一天组织活动,以便利用维多利亚日公众假期,激励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向多拉这样的年轻英雄学习,守护自己的语言和信仰。与多拉有关的历史叙事和仪式也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起来。④朱联璧:《帝国日的产生和跨大洋传播(1899—1958)》,《全球史评论》(第十集),第202—203页。这些叙事明确将英国文化和新教作为对手,激发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的特有的爱国情绪。多拉作为士兵的身份、活动组织者的立场和庆祝活动中使用的仪式和叙事,都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和原生的帝国日相似。学校也是在原生的帝国日这天,组织学生集中学习关于多拉的英雄事迹。法语报刊上不再出现关于帝国日的活动报道,转而用大量篇幅介绍多拉日的情况,庆祝活动还慢慢扩展到了安大略省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中。⑤Joel Belliveau and Marcel Martel, “‘One Flag, One Throne, One Empire’? Espousing and Replacing Empire Day in French Canada, 1899-1952,” in Hayday and Blake eds, Celebrating Canada, pp. 129-132; pp. 132-136; p. 137.
至1922年,开始有魁北克省的报纸直接称呼多拉日为民族节。⑥Joel Belliveau and Marcel Martel, “‘One Flag, One Throne, One Empire’? Espousing and Replacing Empire Day in French Canada, 1899-1952,” in Hayday and Blake eds, Celebrating Canada, pp. 129-132; pp. 132-136; p. 137.这里所说的民族并不是作为整体的加拿大民族,而是说法语的加拿大人这个群体。对于认可维多利亚日和原生的帝国日的加拿大民众来说,加拿大国民的身份和英帝国臣民的身份是一体的、一致的,但对接受多拉日的民众来说,两种身份是分裂的、冲突的。多拉日既占用了维多利亚日的休假的时间来确保有关活动能在不同的群体中产生影响,又利用了原生的帝国日组织学校活动的时间和形式,达到推进年轻一代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特有的民族认同的目的。因此,多拉日是一种平行变体,虽不能动摇帝国日在加拿大其他省份的地位,但在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的社群中,成功占据了维多利亚日、原生和扩展的帝国日的时间和功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帝国的领导人为平息帝国内的不满情绪,通过召集帝国会议的方式协调内部关系。取代英帝国的英联邦应运而生,至少在名义上为帝国内的部分政治体赋予更多的权力。不过,帝国日的活动依然存续,以强化参与者对帝国的归属感。⑦Jim English, “Empire Day in Britain,” The History Journal, vol. 49, no. 1, 2006, pp. 247-249.而且,即便对英帝国的认同是此时英国人认同的重要组成,英国政府依然没有将帝国日认定为公众假期,也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将这个纪念日作为本国或整个帝国(英联邦)的官方纪念日,使得与扩展的帝国日有关的四个时间依旧不能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拿大联邦议会面临了大量要求更改公众假期名称的动议,其中就包括将维多利亚日和扩展的帝国日更名为英联邦日(Commonwealth Day)的要求。①“A Commonwealth Day,” The Global and Mail, 24 May 1947, p. 6.顾名思义,英联邦日关联的是超民族国家的认同,旨在将泛帝国的认同转化为泛英联邦的认同,正式出现是在1959年。更名之初,英联邦日的时间安排和功能均从扩展的帝国日延续而来,故称之为帝国日的继承变体。而在加拿大,英联邦日是原生的帝国日的继承变体。②“Commonwealth Ousts Empire in the Title of Day,” The Globe and Mail, 25 May 1959, p. 12; “Celebration of Empire Day - May 24th - Change of name to Commonwealth Day - 1958,” 23 May 1959, RG25-G2, v. 4344, file part 1, file no. 11390-40,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The World of Learning: Observing Commonwealth Day,” The Globe and Mail, 14 May 1963, p. 7.魁北克省民众则将对帝国日的抵触情绪延续到了对英联邦日的态度上。③“Montréal Goons Join Separatists, Protest Victoria Day: 85 Arrests,” The Globe and Mail, 19 May 1964, p. 1.
时至20世纪70年代,英联邦成员国对自身作为独立国家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让英联邦日的日期显得不合时宜。为更好地适应参与者的时间,1975年召开的英联邦领导人会议上,以加拿大总理为首的参会者要求将英联邦日的时间调整到每年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因为这一天在所有英联邦成员国都是教学日,便于开展有关英联邦历史的教育活动,以增进英联邦成员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④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2 March 1979, 30th Parliament, 4th Session, vol. 4, p. 4033.继续出任英联邦首脑的英国君主每年还是会发表英联邦日演讲,来强调这个跨国组织的团结和特殊性,延续了此前在帝国日的活动。⑤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1 March 1991, 34th Parliament, 2nd Session, vol. 13, p. 18270 and pp. 18282-18285.不过这一变化让英联邦日失去了与特定事件和观念的联系,使之能产生的影响力难免小于帝国日。
前殖民地出现的替代变体彰显了不同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种有地区差异的反帝国认同。在尼日利亚,这种民族认同受到了扩展性帝国日庆祝活动的影响。该国从1905年开始组织帝国日庆祝活动,将这一天视为儿童的活动日。在校学生参加有组织的巡游,在拉各斯聆听总督演讲,演唱英国国歌《神佑君主》 ,表达对王室的敬意,还参与体育赛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的内容逐渐丰富,政府、企业和地方要人为活动提供经济资助,参与者的规模不断扩大,遍布尼日利亚各地。米字旗在活动场地的上空飘扬,参与活动的年轻一代将自己想象为和帝国各地的同龄人一样平等的成员,默许了帝国的霸权和对各地的统治。有关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内容则不包含在活动的演讲中。⑥Saheed Aderinto, “Empire Day in Africa: Patriotic Colonial Childhood, Imperial Spectacle and Nationalism in Nigeria, 1905-60,”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6, no. 4, 2018, pp. 734-737; p. 740.
而在这一代儿童成长起来后,逐渐认识到帝国日活动的内在矛盾,反思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境遇,进而产生了对帝国的抵抗情绪。⑦Saheed Aderinto, “Empire Day in Africa: Patriotic Colonial Childhood, Imperial Spectacle and Nationalism in Nigeria, 1905-60,”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6, no. 4, 2018, pp. 734-737; p. 74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日在尼日利亚的热度也开始消退,替代变体随之产生。带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开始煽动那些享有共同的帝国日活动经验的年轻人的反殖民情绪。反对帝国日成为了反对帝国的手段。尼日利亚西部的民族主义组织讨论决定,从1952年开始拒绝帝国日的庆祝活动,转为在每年4月28日庆祝“全国青年日”,以纪念当地民族主义机构首次召开大会。但殖民者此时依然在组织帝国日的庆祝活动,显示出了两个纪念日之间的对抗关系。在当地获得自治权后,当局将接近5月24日的5月28日确定为地区性青年假期,继续组织与帝国日的庆祝活动相似的活动,延续了帝国日的形式和功能,将活动的内涵从鼓励对帝国的效忠改为鼓励对国家的忠诚。①Aderinto, “Empire Day in Africa,” pp. 746-750.
印度与尼日利亚的情况类似,差别在于替代帝国日的纪念活动针对的是国旗。有印度学者指出,发明印度国旗针对的就是帝国日活动中介绍和挥舞米字旗的环节。政府选择将7月18日确立为国旗日呼应了帝国日的同类活动,以强调团结和统一的印度民族主义。②Arundhati Virmani, “National Symbols under Colonial Dominati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ian Flag, March - August 1923”, Past and Present, no. 164 (Aug. 1999), pp. 193-197.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情况与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有联系。战役发生前,帝国日活动已面临争议。战役发生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遭受的沉重打击,使得澳新军团日(Anzac Day,每年4月25日)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成为了更多学校学生组织庆祝活动的场合。帝国日并未在当地消失,但原本属于帝国日的功能和活动都被转移到了澳新军团日,后者也得到了更多当地人的认可和参与。③Maurice French, “The Ambiguity of Empire Day in New South Wales, 1901-21: Imperial Consensus or National Divis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24, no. 1, 1978, pp. 68-74.
概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的不断瓦解让扩展的帝国日在帝国各地都面临了冲击。相较于加拿大的政治家选择制造平行变体或继承变体的方案,更多国家选择的是创造替代变体,也就是在沿用帝国日的某些功能的基础上,使同类活动服务于本国的认同,亦呈现了对各种民族主义的解释,表达了对帝国统治的抵触。替代变体作为民族国家的纪念的时间,再度实现了四种时间的协调。原本就无法协调四种时间的帝国日在与替代变体的竞争中无疑处于下风,预示了其继承者英联邦日未来的弱势地位。
四 作为观念和实践复合体的纪念的时间
既有关于纪念日的研究或是侧重特定国家的纪念日,或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研究某个跨区域的纪念日,而很少关注像帝国日这样的不同地区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纪念日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将与帝国日相关的纪念日群组放在一起开展比较研究,以厘清纪念日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不同群体对纪念日的接受或改造上,考察帝国日所代表的观念是怎样被解读、接受和抵制的。
通过将纪念日所塑造的纪念的时间和事件的时间、休假的时间与参与者的时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纪念日(尤其是国庆节)更容易实现四种时间之间的协调,这也为传递纪念日背后的观念提供了基础。对一国之内有特定目标受众的纪念日来说(如原生的帝国日),休假的时间便无法与另外三种时间同步。跨区域的纪念日(如扩展的帝国日和英联邦日)也很难让休假的时间与另外三种时间相协调,原因在于跨国组织缺少认定休假的时间的权力。以多拉日为代表的继承变体试图强化的是民族国家之内的族群认同,利用民族国家已经确认的休假的时间自行组织活动。
前述讨论中也已指出,与纪念的时间关系最密切的并非是事件的时间,而是参与者的时间。跨国性纪念日看似是为了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空间内推进共识而生,但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需要考虑的是与参与者的时间相互协调。参与者的能动性因而可以影响跨国纪念日在当地的效果和未来的变化趋势。加上在不同的情境中,参与者很难被简单归入特定的族裔、性别、阶层和文化群体中。以帝国日的目标受众在校学生为例,是否参与活动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同学校的学生归属不同的族裔和阶层,无法用一个标签来归纳其特点,他们也不处于一个边界明晰的物理空间之中。
从英联邦日的生成过程中还可以看出,参与者的时间固然重要,但也不是影响纪念的时间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事件的时间作为构建纪念日的正当性叙事的基础,被塑造出来的纪念的时间只是空中楼阁,逆果为因,无法与纪念日背后的观念建立联系,也就很难利用纪念日的活动来推广特定的观念。这是因为纪念日原本就是推行观念的工具,而非观念本身。
通过分析与纪念日有关的四种时间是否协调来观察这种传递观念的工具的效用,可以从实践的层面理解观念流动产生的影响。是否接纳帝国日的活动,接纳哪一个帝国日,是否塑造帝国日的变体,体现了不同群体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认识,并且他们的认识会随着时间变化。这些观念的载体,就是描述纪念日的正当性的叙事,包括历史书写、立法过程中的讨论和与之相关的出版物,以及他们自身选择的实践。
因此,相较于其他全球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对纪念日被发明和转化的历史的研究,可以利用更为多样化的承载观念的史料,并将实践纳入考虑。此举有望摆脱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所谓“方法论民族主义”这种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先天缺陷,可以纳入不同空间中的案例,也能更为充分地展现出参与者的能动性,与康拉德所认定的全球史有着相同的认识前提。①康拉德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讨论,见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2—3页。如此也能容纳流动的、活动空间不定的群体在不同时期的观念转变,而不用受制于他们所在的区域,所在的阶级、社会性别和族裔群体。因此,以如何“塑造纪念的时间”为主线来理解受众对特定观念的差异化的回应,可以突破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视角,更多地从行动者而非经典文本的角度剖析某种思想全球流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