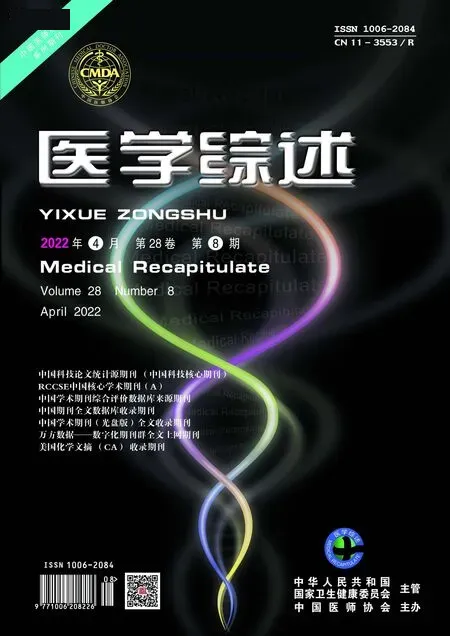外泌体在炎性肠病诊断及治疗中的作用
范春娇,黄贵华,高松林,林星阳,黄木圣,邱华
(1.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南宁 530001; 2.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病科,南宁 530023)
炎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以直肠出血、腹部不适、体重减轻为主要症状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间歇性复发和静止性炎症缓解为特征,其中最常见的是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目前IBD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较为公认的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肠道微生物、免疫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肠道黏膜损伤,损伤肠黏膜处的微环境发生变化,包括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局部组织氧供需失衡以及大量活性氮和氧中间体产生,由此产生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和缺氧应激反应信号等,从而影响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肠道细胞存活及免疫调节[1]。在IBD的肠道微环境中,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之间通过分泌的细胞因子进行动态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细胞因子参与IBD相关炎症级联反应的持续和放大[2]。炎症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和适应性免疫细胞(T细胞和B细胞)被招募以响应活跃炎症部位产生的趋化因子信号,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8、白三烯B4、血小板激活因子、补体因子C5a等[3]。目前,IBD的治疗侧重于抗炎及肠道黏膜修复,药物主要有5-氨基水杨酸、类固醇、抗菌药物、免疫调节剂和单克隆抗体,但这些药物也存在局限性,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部分患者无反应。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有效的、安全的IBD治疗方案。研究发现,外泌体通过免疫调节作用在IBD的发生发展及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4]。现就近年来外泌体蛋白、RNA和脂质对IBD免疫细胞和肠黏膜屏障等的调节作用和外泌体在IBD中作为诊断标志物的潜在价值及不同来源外泌体在IBD发病机制及免疫调节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以为探寻IBD新的诊疗方案提供依据。
1 外泌体的来源及功能
外泌体是由不同类型的细胞以胞吐形式释放的大小为30~150 nm的双层脂质膜囊泡,最初人们认为外泌体是人体内的一种“垃圾”,但近年的研究发现,外泌体通过细胞间传送的方式清除体内垃圾以及维持细胞间内环境稳定[5]。外泌体内包含多种生物学分子(脂质、蛋白质、核酸、信号转录因子、炎症因子、热激蛋白等),且表面携带有特殊功能的蛋白(黏附分子、共刺激分子、配体、受体等),外泌体通过内吞、吞噬、膜融合等机制将以上多种生物学分子从亲本细胞传递到受体细胞,以促进或抑制细胞基因表达,调控信号转导,从而影响细胞功能,发挥免疫抑制或免疫激活的作用[6]。外泌体存在于多种活细胞中,尤其是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淋巴细胞、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另外在血液、尿液、唾液、羊水以及母乳等体液中也可检测和获得外泌体[7]。研究发现,外泌体参与内分泌系统疾病[8]、心血管系统疾病[9]、生殖系统疾病[10]以及肿瘤[11]等的发病,并在疾病诊断以及作为药物载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2]。
2 外泌体在IB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免疫失衡及过度的炎症反应是IBD重要的病理变化,目前研究表明,外泌体能够诱导免疫反应,导致免疫失衡,进而破坏肠黏膜上皮;同时外泌体还能启动炎症反应,致使肠道中炎症因子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加重肠黏膜炎性损伤[13-17]。
2.1参与炎症反应 外泌体中的炎症介质通过触发免疫细胞间的免疫反应加重肠道炎症反应。外泌体可启动炎症反应和细胞间通讯。肠黏膜促炎和抗炎作用失衡是IBD发生的主要原因,外泌体作为炎症介质参与肠黏膜炎症反应。Li等[13]研究发现,肥大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微RNA(microRNA,miRNA/miR)-223通过介导封闭蛋白8的表达,减少miR-223相关蛋白的表达,破坏肠黏膜屏障,导致肠上皮通透性增加,从而参与IBD的发生发展。也有研究发现,肥大细胞分泌的外泌体能够诱导DCs成熟,促进肠道炎症反应[14]。在动物实验中,从葡聚糖硫酸钠盐(dextran sulfate sodium salt,DSS)诱导的IBD大鼠相关的黏附侵袭性大肠埃希菌感染的肠上皮细胞和巨噬细胞中分离出的外泌体,可通过激活核因子κB、胞外信号调节激酶、p38和c-Jun氨基端激酶激活幼稚巨噬细胞,并导致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和IL-6分泌增加[15]。
2.2诱导免疫反应 外泌体具有强大的免疫激活和免疫抑制作用,它们通过调节免疫反应在免疫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16]。巨噬细胞和2型先天性淋巴细胞作为自然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IBD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Lu等[17]尝试从巨噬细胞及2型先天性淋巴细胞的角度阐述IBD的发病机制,在DSS诱导的IBD小鼠中发现,来源于巨噬细胞的外泌体miR-21a-5p的表达增加,且miR-21a-5p的表达与肠细胞中上皮钙黏素的表达呈负相关,同时也证实了2型先天性淋巴细胞的表面抑制受体杀伤细胞凝集素样受体亚家族G成员1通过促进GATA结合蛋白3分泌参与IBD中2型先天性淋巴细胞的过度激活,提示miR-21a-5p可能以上皮钙黏素为靶点破坏肠黏膜上皮,即异常极化的巨噬细胞通过上皮钙黏素导致肠黏膜屏障破坏。外泌体为阐明IBD的发病机制和改善治疗效果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3 外泌体对IBD的诊断作用
目前尚无诊断IBD的金标准,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症状和胃镜检查,同时排除器质性病变。外泌体存在于大部分的体液中,且具有高度稳定性,在病理条件下外泌体含量和外泌体蛋白的表达发生变化,使其可能成为疾病诊断的标志物。Wong等[18]对IBD小鼠的血清外泌体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结果共分析出56种蛋白质,其中大部分为急性期蛋白质和免疫球蛋白。血清外泌体对巨噬细胞具有明显的激活作用,其对于IBD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19]。Zheng等[19]在17例IBD患者的唾液外泌体中检测出2 000多种蛋白质,其蛋白含量已远超过健康人水平,其中8个蛋白质与炎症、蛋白酶体活性和免疫反应有关。基因本体论分析显示,蛋白酶体α7型亚单位在IBD患者中的表达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提示蛋白酶体α7型亚单位有可能成为IBD的生物标志物,为IBD的诊断提供依据[19]。Schönauen等[20]研究发现,IBD患者血清中miR-155和miR-223高表达,而miRNA的表达水平与疾病活动性及粪便钙蛋白、C反应蛋白水平等有关。由此推测,血清和粪便外泌体中miRNA有可能成为IBD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4 不同来源外泌体对IBD的免疫调节作用
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主要通过抑制肠道炎症反应以及调节免疫反应,改善IBD的上皮屏障功能,缓解结肠炎肠道损伤。
4.1炎症细胞来源外泌体 巨噬细胞是抵御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其分泌的外泌体具有抗炎作用。巨噬细胞可分为M1型和M2型,其中M1型巨噬细胞分泌较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IL-1α、IL-1β、IL-6等),M2型巨噬细胞具有抗炎作用,并被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cell,Th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IL-4、IL-13和IL-33)所极化[21]。Yang等[22]从巨噬细胞的培养上清液中分离出M2型巨噬细胞(M2a、M2b和M2c型)外泌体,观察其在IBD中的作用发现,M2型巨噬细胞外泌体可以减轻DSS诱导的结肠炎的严重程度,且M2b型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较M2a和M2c型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更有效,经M2b型巨噬细胞外泌体治疗后,结肠炎小鼠脾脏中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细胞)的数量和IL-4水平均增加。此外,经M2b型巨噬细胞外泌体治疗后,与结肠炎相关的细胞因子(IL-1β、IL-6、IL-17A)的表达受到显著抑制[22]。M2b型巨噬细胞外泌体对DSS诱导的结肠炎有保护作用,其保护作用主要与CC趋化因子受体1/CC趋化因子受体8有关[22]。Cao等[23]通过使用双靶向纳米颗粒将miR-146b运送到肠巨噬细胞中,通过诱导M2型巨噬细胞极化,激活依赖IL-10的信号转导及转录活化因子3通路,从而促进肠道黏膜修复。以上发现为IBD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
4.2免疫细胞来源外泌体 T细胞是免疫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DCs则是启动初级免疫反应的抗原呈递细胞中最有效、最专业的细胞,具有捕获和呈递抗原的功能[24]。DCs来源的外泌体(DCs exosomes,DCs-Exo)具有免疫刺激或抑制作用。经IL-10处理或转染IL-10基因的DCs-Exo可通过刺激CD4+CD25+Treg细胞抑制三硝基苯磺酸诱导的大鼠结肠炎[25]。外泌体可以用作自身免疫性疾病干预治疗的载体。髓源性抑制细胞是调节免疫反应的未成熟髓系细胞的异质性群体,其释放的外泌体通过抑制Th1细胞增殖和促进Treg细胞增殖,降低DSS诱导的结肠炎的严重程度[26]。胱天蛋白酶(caspase)-12是一种促凋亡蛋白,在先天免疫应答过程中被激活,并参与IBD的发病[27]。Liao等[28]研究表明,Treg来源的外泌体(Treg exosomes,Treg-Exo)减轻了DSS诱导的IBD的严重程度,其可能是通过促进肠上皮屏障损伤的修复实现,具体是由miR-195a-3p直接靶向caspase-12,负调控caspase-12的表达;进一步研究发现,Treg-Exo miR-195a-3p通过靶向caspase-12促进体外培养的YAMC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该研究结果提示,Treg-Exo将miR-195a-3p转移到肠上皮细胞中,miR-195a-3p通过靶向caspase-12促进肠上皮屏障损伤的修复过程,减轻IBD的严重程度[28]。Treg-Exo的使用可能为IBD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4.3干细胞来源外泌体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具有诱导再生、维持一般组织动态平衡和定位于靶部位的能力,其分泌的外泌体具有实现自我更新和修复受损组织的作用[29]。MSCs通过分泌免疫调节因子调节先天免疫反应和获得性免疫反应,控制IBD的炎症反应[30]。研究发现,人脐带MSCs释放的外泌体(human umbilical cord MSCs exosomes,HucMSC-Exo)通过抑制巨噬细胞中IL-7的高表达减轻DSS诱导的IBD[31]。粒细胞髓系来源的抑制性细胞的功能性外泌体被称为CD11b+Ly6G+Ly6Clow细胞,其具有粒细胞样形态,是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的主要群体[32]。CD11b+Ly6G+Ly6Clow细胞可通过抑制Th1细胞增殖和促进Treg细胞扩张减轻DSS诱导的结肠炎[33]。在Wang等[34]的研究中,HucMSC-Exo处理可恢复IBD结肠组织结构的完整性,降低促炎细胞因子(IL-1β、IL-6)的水平,而增加抗炎细胞因子(IL-10)的表达。HucMSC-Exo通过修复受损的大肠组织减轻IBD。HucMSC-Exo富含miR-326,在抗炎过程中,miR-326抑制神经前体细胞表达发育下调基因-8与底物蛋白cullin1结合,抑制炎症反应过程中E1、E2、E3酶的表达,进而抑制核因子κB信号通路激活,达到缓解IBD的目的[34]。嗅外-MSCs(olfactory mucosa MSCs,OM-MSCs)可用于自体移植。OE-MSCs较骨髓MSCs具有更高的增殖能力和更强的抑制能力。Rui等[35]研究发现,嗅外-MSCs来源外泌体(OE-MSCs exosomes,OE-MSCs-Exo)通过调节T细胞反应,改善小鼠胶原诱导的关节炎的严重程度,具有较强的免疫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OE-MSCs-Exo通过抑制CD4+T细胞增殖,降低γ干扰素、IL-17的表达,增加转化生长因子-β、IL-10的表达,发挥免疫抑制作用[35]。在实验性结肠炎小鼠中,OE-MSCs-Exos治疗明显减轻了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后Th1/Th17亚群显著减少,Treg细胞明显增加[36]。
4.4肠上皮来源的外泌体 维持肠黏膜完整性和促进损伤肠上皮修复是预防肠道炎症进展的重要方式。有研究表明,来自DCs的外泌体miR-146b通过激活核因子κB改善上皮屏障功能,缓解结肠炎肠道损伤[37]。研究显示,在P物质刺激下结肠上皮细胞中miR-21的表达上调,然后被选择性地分选到外泌体中,进而促进人结肠细胞和小鼠结肠隐窝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从而促进结肠上皮细胞增殖[38]。
4.5寄生虫来源外泌体 胃肠道寄生虫通过免疫调节减轻IBD的炎症,从而起到保护肠黏膜的作用[39]。用钩虫来源的外泌体处理溃疡性结肠炎小鼠发现,参与溃疡性结肠炎发病的炎症因子(IL-6、IL-1β、γ干扰素和IL-17A)的表达受到显著抑制,而抗炎细胞因子(如IL-10)的表达明显升高,从而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起到保护作用[39]。Eichenberger等[40]发现,日本血吸虫和曼氏血吸虫卵来源的外泌体对结肠炎小鼠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此研究还发现,经日本血吸虫可溶性虫卵抗原处理的DCs-Exo治疗后,结肠炎小鼠体重增加,疾病活动指数明显降低,且小鼠结肠长度增加。由此可知,寄生虫对IBD具有一定免疫调节作用。
5 小 结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外泌体与疾病的发病、诊断及治疗等联系紧密:在发病机制方面,外泌体通过炎症反应和诱导免疫反应参与IBD的发生发展;在诊断方面,外泌体作为一种潜在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病情;在免疫调节方面,外泌体以感染的方式成为免疫反应中强大的促炎和抗炎介质。不同来源的外泌体参与维持肠道的内稳态,包括改善上皮屏障功能、发挥Treg细胞抑制作用等。因此,外泌体途径为IBD的治疗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目前关于外泌体的知识主要来自体外实验模型,外泌体通路在特定类型免疫细胞中的功能尚未被研究。此外,未来还需要探索外泌体在给药后的药动学或生物分布情况。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在纳米技术、基因组学等技术的辅助下,外泌体将被更好地应用于IBD的诊断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