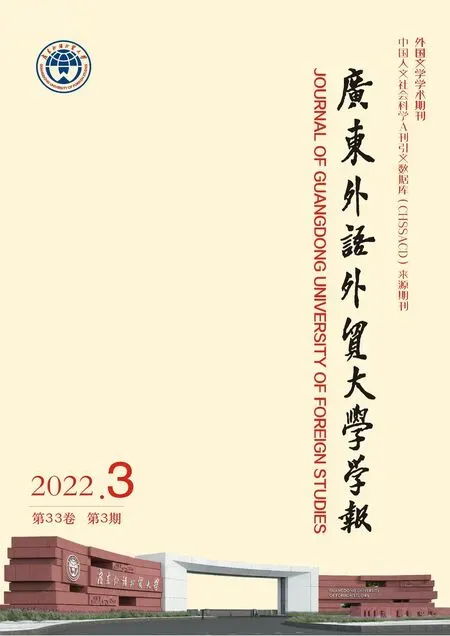倾听荒野:《天空,群星,荒野》中人与自然万物的内在互动
邱小轻
引 言
瑞克·巴斯(Rick Bass, 1958-)的中篇《天空,群星,荒野》(TheSky,theStars,theWilderness, 1997)以安妮的口吻和视角讲述了她与家人以及与两任男友在以德克萨斯州希尔乡野(Texas Hill Country)为原型的上万公顷的普雷德农场(Prade Ranch)跟自然万物日夜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生的点滴。叙述充满自然界各种声响,加上安妮不断回忆起童年时期与弟弟欧马奔跑在树林与河流间以感受埋葬于荒野中心的母亲的存在,整个叙事极具抒情性。
有学者着重研究了安妮的外祖父强调自然万物有各自名字,以及模仿众鸟鸣叫而重获言说能力这两件事,指出这凸显了人与自然的联结(Melzow, 2012: 369)。其实,在对巴斯早期作品的整体研究中有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并认为人物与自然的积极密切互动丰富了人物本身,或者改变了他们;该学者还发现巴斯时常使用“神奇”(magic)一词描写自然散发的能量(Wise, 2008: 156,154)。的确,《天空,群星,荒野》不断讲述安妮一家与自然万物的紧密联系,并展示了自然的神奇。近年学界对巴斯的研究聚焦人与物不期而遇时互不干扰,强调物独立于人类而实体存在(唐伟胜,2017:16;唐伟胜,2018:36)。然而,《天空,群星,荒野》以及以该中篇命名的故事集聚焦的却是人与物的持续密切互动。事实上,收录在巴斯最新短篇小说精选集《过一会儿》(ForALittleWhile, 2016)中的新作《蓝色的树》《鱼的故事》等也有同样的聚焦。遗憾的是,批评界没有关注《天空,群星,荒野》里面的人与自然万物互动时频繁使用的感知方式及其意义,也没能注意到自然万物发出的声响的本质及其意义。
本文运用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兼哲学家爱布拉姆(David Abram)的语言观以及物质女权主义理论家巴拉德(Karen Barad)的内在互动论,结合巴斯在非虚构作品中表达出来的自然观,来解读《天空,群星,荒野》中人与物内在互动的方式与结果,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小说为何一再强调人物通过身心,特别是通过聆听与观察来感知荒野?他们从自然万物发出的各种声响中具体感知到了什么?人物与自然的内在互动对彼此产生了怎样深远影响?
感知与内在互动
物质女权主义理论家巴拉德对玻尔的量子物理论作出后人文主义阐释。她赞许玻尔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她也坚信科学实践是感性的,需要充分调动起实践者的感官功能,即对“环境感知”(陈瑜明、杜志卿,2019:105);她也赞许玻尔对实践的强调以及把认识论、本体论、伦理观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是,她发现玻尔的物理观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元素,对此她持反对意见,认为人类认知不是从外部对自然世界进行干预的过程,而是一项参与到世界之中的活动,并认为科学实践是一个自然的过程(Barad, 2007: 247-248)。为此,她提出了“内在互动”论(intra-action)和“施动性实在主义”(agential realism),指出“内在互动意味着物质在纠缠中互相生成”(Barad, 2007: 33)。她强调“内在互动”不同于“互动”,“互动”强调的是个体的形而上学特性,尤其是个体先于其他物体而独立存在;而“内在互动”突出的是个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即个体不能独立于其他个体而单独存在(Barad, 2007: 128, 140)。巴拉德认为自然与文化不可分,而且人的身体与非人类自然均具有施动力(Barad, 1998: 109; Barad,2007: 332)。在内在互动论基础上,巴拉德提出了“施动性实在主义”,强调人类是不断内在互动的世界的一部分,所有物质均具有施事力;此外,客观性与施动性均与责任、义务相关,因此,人类对自然担负着责任(Barad, 2007: 184, 361, 392)。巴拉德的“内在互动”反对物体先于各种关系而存在,得到物质女权主义理论家艾莱默(Stacy Alaimo)和黑克曼(Susan Hekman)的高度认可,她们指出,既然世界以复杂难解的方式永远内在互动,那么人类就不能大言不惭宣称自己为世界的主宰(Alaimo & Hekman, 2008: 248,250)。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兼哲学家爱布拉姆(David Abram)也坚持人的物质性,他在对人与自然万物密切接触的大量观察与研究中发现,人类与其他物质共享一种由身体直接感知的语言,该语言比人类词语更古老、更深刻(Abram, 2010: 173-74)。
的确,与巴拉德和爱布拉姆一样,巴斯也强调人类与自然打交道时要用身心去感觉、感受、感知万物。他虽以地质学家出道,却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者,笔下人物常常感受多于思考、感知多于言说(Solomon, 1997: 2)。在《雅克之书》(TheBookofYaak, 1996)这部述说蒙大拿州最西北的雅克山谷的纪实性作品里,他记录下在最心爱的一座山头意外发现一只棕熊留在雪地的大大脚印时的各种感受:他对棕熊充满着敬畏,认为自己“可以看见、听到、感受、品尝、闻到棕熊的特别之处,但就是无法知晓或者名状”(Bass, 1996: 51)。他还多次提到感觉的重要性:“我能真真切切感觉到什么时候可以动笔创作虚构作品”(Bass & Johnson, 1998: 144)。在回忆录《我为何来到西部》(WhyICameWest, 2008)一书中,他强调“感知力和激情”是人类获得生物意义上完美的两个首要步骤(Bass, 2008: 7-8)。与《天空,群星,荒野》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另一中篇小说《熊的神话》的男女主人公更是感官动物,常用动物般敏锐的感官去感知自然万物(邱小轻,2020: 4)。
在《天空,群星,荒野》中,巴斯借安妮之口道出感受对于她和弟弟童年时期认识世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当时,所有这些东西都被纯粹感受着,而不是理解”(Bass, 1997: 106)①。事实上,成年后的安妮仍然感性大于理性。她虽然获得博士学位,但发现科学领域存在太多胡言乱语,却不再怀有敬畏之心(181)。这也是完全以书本为知识来源,而对自然万物缺乏直接感知的第二任男友不被她的外祖父待见的根本原因。巴斯对感知和对参与到世界中的强调,跟巴拉德的后人文主义物质观高度契合。
倾听荒野的神奇与逝去母亲的声音
《天空,群星,荒野》强调用身体去直接感知自然,尤其是通过倾听与观察来“获取知识”(189)。有时候安妮“能感觉到地球暂时停止了运转”(167-168),她和家人“能感受到海洋的存在”(139)。她特别强调倾听或观察各种声响,尤其夜晚时分;多次提到当夜幕降临,父亲和弟弟在门廊收听城里举行的体育赛事时,她和外祖父一边仰望星空,一边静听荒野的动静:“萤火虫就在我们身后的树林穿梭,仿佛要求我们跟随其后。巨大且鬼魂般的月形天蚕蛾从树林里飞出来,盘旋在窗户边,像小型的鹰一样扇动着翅膀,试图飞进屋里,飞到欧马和父亲在听棒球比赛的地方”(97)。此外,他们还听到群星“坚实的回音”(97)。人物通过感官来认识自然万物的做法在整部小说俯拾皆是,呼应了巴拉德强调的人类认知是感性的、是一项参与到自然世界活动的观点(Barad, 2007: 248)。
除了人物主动感受自然,自然也用各种方法吸引人物注意,表现出明显的施动力,验证了巴拉德的“施动性实在主义”,即人是不断内在互动的世界的一部分,所有物质均具有施动力。例如,夜晚与河流“召唤着”(calling)安妮和欧马(106);姐弟俩还能感觉到 “河流的牵引力”(pull)以及“橡树与雪松的引诱”(lure)(106)。这也与爱布拉姆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共享一种由身体感知的古老语言的观点相契合(Abram, 2010: 174)。除了施动力,自然万物也展现出强烈的感知力和灵性。比如,安妮的外祖父注意到,她出生那天,有着金色脸颊的刺嘴莺从墨西哥飞了回来;深红色的捕蝇鸟则从白天一直鸣叫至半夜;扁嘴蜂鸟也在安妮即将出生时飞到她家门廊,一动不动地逗留了30分钟 (113-114)。安妮也感叹自然的灵性。她与母亲在门口补红色衣物时,一群红尾蜂鸟出现了,令她感慨不已:这些鸟在500英里的远方,“何以知晓我们那天早上会织补红色衣物呢?”(127)。她还发现,在动物界,当挚爱之物逝去时会发生奇异事件(160)。为外祖父的好友查波奔丧时,她看见一只红尾鹰出现在他们上方半英里处,便“想看清楚它是不是查波”(160);外祖父去世那天,蜂鸟与鸽子则在屋外盘旋、呼叫(188)。
事实上,自然科学界的一系列实验证明,自然万物具有同情心(Massumi, 2015: 11)。由此可见,自然万物能感知人类的情感。当然,这些鸟类的种种奇异行为也是它们与安妮一家长期内在互动的结果。这再次验证了巴拉德的观点,即万物内在互动意味着物质在纠缠中互相生成(Barad, 2007: 33)。此外,巴斯在长期荒野生活中体悟到神秘是一种知识,值得人类去体会(Bass, 1996: 6)。因此,他不断强调安妮一家用身心去倾听和观察自然。
有学者指出,倾听一词源自德语,原意是“关注”(Schneider, 2020: 49)。可见,倾听包含观察等身心体验。该学者继而发现,有些作家把倾听大地与灵性(spirituality)相联系,认为灵性往往使人类得以与非人类自然连接,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承认以非科学路径来接受知识与真理是理解环境能为一切疗伤的关键(Schneider, 2020: 49)。的确,在《天空,群星,荒野》中,倾听与观察是安妮一家,尤其是安妮用以治疗失去挚爱母亲的方式。事实上,该小说的一个主题就是亲人的逝去,特别是年轻母亲的离世。小说不断使用“失去”一词,单单在第99页就出现三次。安妮不断回忆起她小时候如何带着弟弟在荒野全身心感受埋葬在农场中央的母亲的存在。
安妮特别强调已逝母亲的声音。她饱含深情,详细描述已逝母亲使用的语言具有的特征:
我晚上听到她(母亲)跟我说话,在那特别的地方——我看着河流,或者走在洒满月光的钙积层道路上。我不是说我听到她以人类的语言在说话,她也不是用英语在说话,而是说,它更像是我听到的声音的回响,而非声音本身。它就像一个词被说出之后或一扇门被关上之后发出的那种声音。它像你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声音,从而把你从梦中唤醒,同时又融入你的梦中(96)。
如此看来,已逝母亲的说话声随处可听见,它既特别,又平常;既柔和,又坚实。因此,安妮一家坚信母亲仍然活着,只不过换了一种形态罢了。从安妮的母亲亲自在荒野找好一处安葬之地,并要求家人在她死后把她“种植”(plant)在那里这件事(95),可以看出安妮的母亲也相信自己离世后就成为荒野一分子,换成另一种形态活着,这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安妮小时候常带着弟弟不断穿梭在溪流、树林以及母亲的坟墓之间,不断奔跑在林间,直至觉得母亲已经活过来。“某个东西在离我们而去”(104)。因此,他们在荒野中大声叫喊,以将母亲唤醒(107)。换句话说,他们仍然能够与母亲密切互动,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方式。安妮与母亲之间的内在互动在下面这个例子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母亲)虽然离去了,但她的大部分仍存在于荒野,或许她的全部仍在。我至今仍无法完全知道,她的哪一部分是她的,哪一部分又是我的。有时候我看到或者听到某个东西,使我产生一种奇特的共鸣,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东西,一种气味,或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与曾经触碰过她本人的相类似,甚至一模一样。每当这时候,我会停下来,思索这种共鸣的意义。(95)
“共鸣”一词生动体现了巴拉德所说的“物质在纠缠中互相生成”(Barad, 2007: 33)。安妮已逝母亲以自然物质的新姿态继续与她内在互动,两者在不断互动中产生共鸣,以致难于区分彼此。另外,安妮对母亲的感受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母亲的存在形式包括了几乎各种感官样式——视觉(一种景象)、听觉(一种声音)、嗅觉(一种气味)、触觉(一阵微风)。因此,安妮不禁自问:“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而言,是不是总是一个谜?也许我错了,但我认为没有人独立存在”(95)。“谜”(mystery)与“没有人独立存在”恰恰彰显了万事万物内在互动的事实:不管是人类还是自然万物,均非独立存在于世界,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正如巴拉德指出,现象不仅仅标记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认识论上的不可分,现象就是内在互动的施动者之间本体论上的不可分。每个人或物都是一个“被关系者”(relata),即每一个施动者都是在某种关系中得以存在(Barad, 2007: 333-334)。
安妮努力让弟弟去“感受母亲(的存在)”(feel Mother),认为唯一让他感受到母亲存在的方法就是像她那样去“感受她(母亲),倾听她”(99)。她认为,母亲的新生活是“星星的生活,岩石与土壤的生活。唯有拼命、快速穿过地面,才是与母亲说话的方式……这是感官的圣坛”(99)。换句话说,面对拥有新生活样态的母亲,必须采用新的交流方式,这种新方式就是动用各种感官。安妮还认为,她的父亲肯定也是通过倾听和察看来感受她的母亲的新样态(111)。
诚然,安妮的母亲象征着“大地母亲”(Seaman, 1997: 385)。但是,如上面所展示,安妮一家都能强烈感受到她仍然拥有具体的形态。巴斯在回忆录《我为何来到西部》中表示,他相信两个相隔千里的人与物之间存在某种意识,或者令人战栗的潜意识,使他冥冥中受到“召唤”(summons),从南方跨越中西部,来到人烟稀少的西北部(Bass, 2008: 10)。因此,安妮等家人虽然与其母亲阴阳相隔,但仍可以彼此感应,可以感受到她的具体样子。值得注意的是,巴斯原本是地质学家,而他上面这些感性十足的话语再次说明他对人与物所持有的观点与巴拉德的“内在互动”论及“施动性实在主义”惊人一致,即尽管人与物相隔甚远,两者仍然能相互纠缠;人与物均为具有施动力的物质,会对彼此施加影响。
人与物内在互动的结果及启示
除了亲人的逝去或分开,小说还讲述了另一种失去,那就是荒野不断缩小,多个物种从农场消逝。巴斯早在1992年就指出,荒野正以比其他东西更快的速度消失,他甚至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关于失去(Bass, 1992: 76)。
小说开篇就传递了珍贵物种“失去”的主题。开篇选段来自跟巴斯一样生于长于德克萨斯的作家格雷福斯(John Graves)的著作《群鸟自画像》(Self-PortraitwithBirds, 1991),弥漫着浓郁的怀旧气氛——曾经万里迢迢往返于美国大草原和阿根廷高山之间的高山千鸟(upland plover),如今只能在书本看到(89)。荒野不断失去,还可以从“猎食者俱乐部”(Predator’s Club)以及外祖父收到的信件这两件事得到明证。前者打着保护农场牲畜的旗号大肆捕杀动物,特别是珍稀动物。外祖父在长达一世纪的人生长河中目睹多个物种从农场消失,包括狼、熊、狮子(118,141)。安妮也痛心发现刺嘴莺濒危,绿鹃减少,豹、狼、水牛均已不见(126)。一个名叫荷马·杨于1902年写给外祖父和查波的一封信件则讲述了一名职业猎人四处射杀水牛的事件(186);他于1905年写的信件又讲述了他因为和朋友误杀美洲豹而感到愧疚(187-188)。这两件事均让外祖父和安妮感到十分痛心,安妮想到几十年后农场将空无一人,这倒令她感到宽慰(188),因为这意味着不再有人破坏这片荒野。
由此可见,《天空,群星,荒野》充分展示了人与物的内在互动,强调人与物的不可分以及双方对彼此施加的深远影响。这也彰显了巴斯持有跟巴拉德的“施动性实在主义”相类似的观点:正因为人类是不断内在互动的世界的一部分,会对自然产生种种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担负着责任与义务(Barad, 2007: 392)。遗憾的是,人类长期以来把自然视为客体和征服的对象。小说多处提及人对自然万物产生许多负面影响,致使荒野不断缩小;而自然万物也对人施加种种影响,正如安妮所发现的那样,夜里蹚过河流时,觉得自己甚至变成了河流本身,感觉到寒冷的水与火热的肚皮完美结合(105);她“被万物塑造着,挤压着”(108),因而发出感慨:“我们都互相关联着,是一个生物体,并非单独存在”(120)。
由于人与自然万物的持续内在互动,人物深受万物影响,他们使用的语言充满“物性”。小说频繁出现“种植”(plant)一词:安妮一家把母亲“种植”在荒野里(95);安妮把荒野的意识“种植”在弟弟的头脑里(161)。此外,人物时常被比作“物”:在安妮的眼里,父亲像“蜕去皮的蛇” (159),外祖父和查波则像“半人半树”(127)。外祖父越老,身体变得越沉,似乎一辈子吃进身体的各种矿物质都来向他索取他的身体(166)。实际上,他早已跟荒野融为一体(blend in, 164),所以他和查波死后都自然火化,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他认可自然万物的本体地位,坚持记住他们的名字,认为这就像一个人会记住家人的名字一样(98)。他还强调事物有其归属地(98)。诚然,记住万物的名字体现了人与物的平等地位以及人跟自然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物种本来就跟人类存在于同一星球,而且它们比人类的出现要早得多,理应被承认、被记住。
而最能体现自然万物对人物的影响当属安妮的外祖父从众鸟的鸣叫中重新学会说话。万物发出的声音就是它们各自特有的语言。外祖父中风后失去言说能力达7年之久,90岁那年,他模仿各种鸟儿的鸣叫声,尤其是模仿黑白相间的莺、绿鹃、哀鸠、印加鸽的啭鸣、唧啾、责骂声,众鸟则聚集在他的周围,听他唱,并和唱(165)。最终他重获说话能力,尽管安妮说他是在说-唱(said-sang 169)。“说-唱”这个词语生动且贴切地体现了外祖父与众鸟内在互动的结果,也再次印证了爱布拉姆的语言观,即人类与非人类自然拥有一种由身体直接感知的古老语言。外祖父谙熟各种鸟,不仅能叫出它们的名字,而且能发出相似的鸣叫声。记住动植物名字,从而认识它们,这的确体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亲密联结(Melzow, 2012: 363),也证明这是两者沟通的重要且有效途径。事实上,巴斯在近年的作品里也表达了同样看法。如短篇小说《蓝色的树》的主人公威尔逊的两个女儿知道鸟儿每一支歌曲的意思,他们三人夜里遭遇狮子时,威尔逊对着黑暗中的狮子喊话,让狮子走开,得以安全回到家中(Bass, 2016:368)。
自然也是神秘的,人类无法完全知晓。安妮的外祖父曾两次误判自然现象。第一次是坚持认为夜鹰晚上的工作是赶走动物身上的蚊虫,而查波则相信世代流传下来的知识,认为夜鹰晚上会吸干所有动物的乳汁(115-116)。后来的事实证明外祖父错了。第二次是他坚信累积的经验,以为大海的潮汐一定不会靠近他们,而事实证明大海隐藏着惊人的吞噬力,正在步步逼近他们(138-141)。这说明,除了切身感受自然万物,人有时只能凭借直觉去认识自然。由此可见物的神秘不可知,而且人与物均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人在与物的持续内在互动中不断修正对自然的认识。这恰好可以佐证物质女权主义理论家艾莱默和黑克曼为何对巴拉德的内在互动论的高度认可:物质的施动性意味着物质具有不可预测性,不能为人类完全知晓,因此人类没有资格宣称自己是世界的主宰(Alaimo & Hekman, 2008: 248, 250)。的确,巴斯想要强调的是: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在自然面前理应谦卑。
结 语
安妮在与荒野的亲密互动中不断加深对荒野的认知,愈加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于是辞去大学教职,回到农场独居。她发现那些强健或保护自然万物的东西,也在强健和保护着她;而那些伤害它们的东西,也在伤害着她(112-113)。事实上,《天空,群星,荒野》不断强调物质与精神绝非二元对立,人与物有时难以区分,这些均体现巴斯持有与内在互动论一致的观点,即个体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Barad, 2007: 140)。认识到这一点,就等于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联结,认识到两者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这正是巴斯要传达给读者的重要信息。
巴斯某些虚构叙事作品传达了自然独立于人类而实体存在的观点(唐伟胜,2017: 15;唐伟胜,2018:33),而《天空,群星,荒野》则用特别细腻的笔触叙述安妮一家对荒野的无限热爱与亲密互动,这与小说中不少人大肆猎杀动物而导致许多物种锐减甚至消失的行径形成强烈对照,由此凸显了人与自然的联结,强调保护生态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这呼应了巴斯(Bass, 1992: 76)说过的写作意图:以时间顺序记录下(chronicle)重要的,记录下不会永远在这里的,借此才能保持鲜活与感受力(stay fresh and sentient)。他发现,到1998年为止,雅克山谷这处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大陆最野性的地方,仍没有得到任何保护,美国森林服务公司依旧允许砍伐森林以及修筑道路(Bass & Johnson, 1998: 142),这令他非常痛心。事实上,小说里安妮的母亲早逝这一令全家人一直无比痛心之事,可以解读为一种隐喻,意指失去(至亲和荒野)造成的巨大且深远影响。巴斯通过安排安妮讲述失去的故事与自然的神奇,向读者传达了人类对自然应该持有的敬畏以及理应担负的责任,这也正是巴拉德的内在互动论所强调的一个重要信息。
注释:
① 《天空,群星,荒野》的引文均出自瑞克·巴斯的原著,由本文作者翻译。此后仅随文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