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作家的敦煌故事
文 | 兰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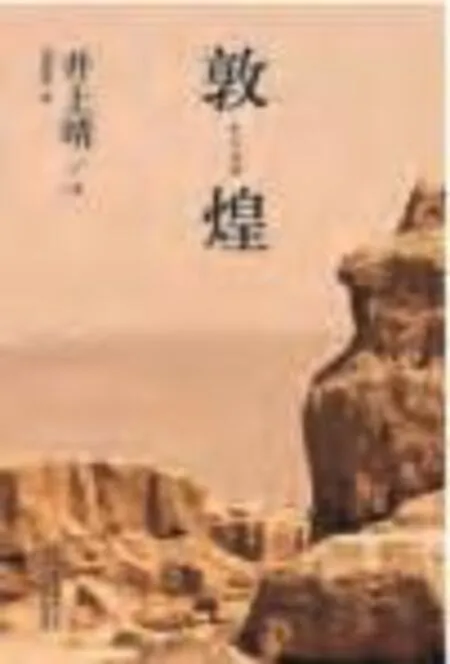
《敦煌》 2014[日] 井上靖 著刘慕沙 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末,日本掀起了一股“敦煌热”。一波一波的日本人来到甘肃,去到敦煌,仰望石窟。这股“敦煌热”的起因是一位日本作家的一本小说——井上靖的《敦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创作《敦煌》前,井上靖从未到过这里。他笔下的敦煌,是由史书记载和他的想象凝结而成的。
1932年,井上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的阅读视野并没有受到专业限制。他读过《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著作,并对中国汉唐文化和西域产生了极深的爱慕和向往,对敦煌,尤其如此。戈壁、星空、峡谷、梵音……这一切素未谋面的景象,经由史书,印入了井上靖的眼帘,他记在心里,后来便付诸笔端。
小说《敦煌》从一位名叫赵行德的殿试落第书生的一次奇异经历开始讲起,以他守护敦煌的经文而告终。
赵行德是谁?
这个名字真实地出现于敦煌经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抄卷后记之中,抄经人正是赵行德。赵行德之生平事迹湮灭不可考,于是有了井上靖为其而创作的小说《敦煌》。
小说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渺小如蚁之人如何在历史洪流之中有所持守,讲述了一个关于“慌乱人生路上的守与藏”的故事。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赵行德落榜后在汴京街头行走之际救下了一名西夏女子,随后便跟随该女子一路向西,直至西域。彼时的西域,民族纷争四起,在遥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中,人如微尘不足为道,人命也因此不值一提。赵行德身处战乱,见过慌乱人生路上的无数死亡。不可避免地,他的生命同样被战事裹挟,人生从此慌乱起来——由开封进入边土,偶然地做了一个西夏士卒,转战边疆各处,后又与汉人反叛西夏王……战事中的他,对生命最大的体验就是“并不清楚”。但他始终没有向残酷现实献上头颅,而是执着于寻找人生方向。
辗转到了千佛洞一座寺庙的藏经库中,赵行徳察看室内,“首先看到的是满目经卷和作废的卷册,以及三名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僧侣,其中两个站立着,另一个则正弯腰做着什么。他们聚精会神忙碌着,并未觉察有人在窥探”,“行德看了一阵才明白这三人在拣选经卷。”原来,他们早意识到,西夏军一旦入侵,佛寺之灾在所难免,必须找到理想的藏经之所,才可能化险为夷。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能撇下经卷逃难”时,这三人脸上流露出轻蔑的神色。仿佛在说,有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于是他学习西夏文字,用一己之力保护敦煌经卷。
然而,后世之人知敦煌者遍布天下,晓赵行德者,唯井上靖一人而已。
是井上靖的《敦煌》把历史上的赵行德形塑在众人面前,并提醒我们:有人这样活过——在他心里,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生时仿佛就已肩负使命,为此而生;死前,也要将之好好安顿。所以,再坏的命运,再慌乱的人生,有所坚守,便不会有比坏更坏的命运、比慌乱更慌乱的人生。
《敦煌》问世23年后,井上靖才真正踏上了憧憬已久的古丝绸之路。
白雪皑皑的天山山脉,澄澈湛蓝的赛里木湖,雄宏神秘的莫高石窟,古诗里的酒泉、玉门关,让他陶醉其间,流连忘返。他感叹:“真没想到,敦煌竟与我想像中的这样相像。”“23年前我就写成了《敦煌》,可直到今天才头一次见到它,却一点儿也觉不出陌生。我与中国太相通了。”
井上靖对敦煌毫无不适感,“每天夜间,我在呼啸的风声中,高枕无忧,睡得十分香甜、安稳”。想着自己写下的《敦煌》,再目睹眼前敦煌的日月轮转,他仿佛穿越了千年,有汉人与匈奴短兵相接烽烟四起,也有驼铃阵阵的商队前来贸易,有丝绸、茶叶、珠宝空前繁盛,也有黄沙漫天寸草不生。历史上的敦煌,仿佛从未离开,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流沙,自古而然,从未变更……
神秘的西域文化令井上靖十分着迷。他一生曾27次访问中国,多次到新疆、甘肃等地实地考察,除了《敦煌》,他还写了与西域有关的《楼兰》、《丝绸之路诗集》。
作为一位日本作家,井上靖却极其擅长讲中国故事,究其原因,还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片深情。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
冰心曾说:“我感谢井上靖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到我们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恐怕这不只是冰心的心声,也是每一个了解井上靖的中国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