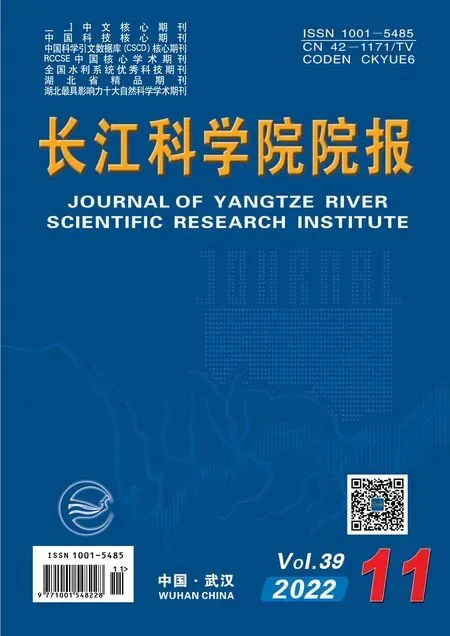公元前887年—公元1911年长江流域水、疫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胡兴涛,杨广斌,石秀雄,崔瀚文,李 蔓
(1.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阳 550025; 2.贵州省山地资源与环境遥感应用重点实验室,贵阳 550025)
1 研究背景
水灾是指因久雨或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或河水泛滥,使人民生命财产、农作物遭受破坏或损失的灾害,我国历史上水灾主要有雨水型灾害和江河洪水型灾害[1]。疫灾是指瘟疫流行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顶级灾害[2-3]。中国古代有“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之说,水灾是中国历史上发生最频繁的灾害类型。在中国历史上的疫灾,绝大多数都是由其他自然灾害比如水灾之后而诱发的次生性灾害[4],在疫灾的灾害链中,水灾与疫灾的相关性在各大自然灾害中最为显著[5]。水灾作为长江流域发生最频繁的大型灾害,对疫灾的孕灾环境、诱发传播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长江流域的水、疫灾害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对防治灾害的叠加效应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有关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疫灾研究主要有:时间上以单个或连续多个朝代史为时间断面,分析疫灾的时空特征、时空演变与环境关系[6-12];空间上以省份或地区为研究区,分析疫灾的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13-15],从季节、年际和朝代变更上分析疫灾在时间尺度上趋势波动和周期变化[16-17],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呈现疫灾的空间分布、趋势走向和冷热点分布[18];水灾方面主要有:以单个朝代史或整个历史时期为时间断面,长江流域的灾害热点地区为空间范围,分析水灾时空特征[19-22]、风险评价[23-25],以及对社会环境的影响[26-31]。
以上研究对于梳理长江流域的疫灾和水灾在时空上的分布特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风险评价具有重要指示意义,但是前人多着重对长江流域单个热点区域以及单个灾种进行研究,且多以单个朝代史为时间尺度,缺乏对整个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时空特征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国先秦至清末历史时期为时间尺度,对长江流域水、疫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探讨,以期为长江流域水、疫灾害防治以及避免灾害叠加效应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2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长江流域流经的“九省二市一区”为研究区域(图1),流域内地势呈西高东低,横跨青藏高寒区、西南热带季风区和华中亚热带季风区[32],气候条件复杂,降水差异显著,水系分支众多。在上游地区,平均海拔高,空气干燥稀薄,太阳辐射强,历史上人口稀少,农业耕种分布面积小,经济脆弱性低,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小或危险性较低[23]。而中下游地区人口密集度高、经济发达、河流湖泊众多,是我国自然灾害高发区域。

图1 研究区行政区划示意图
3 数据来源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文中灾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灾害通史》丛书。提取书中水灾和疫灾数据并对照现今地名进行整理,得到含有发生年份、发生季节和所在市的水灾和疫灾数据,以此摘录长江流域先秦至清代(公元前887—公元1911)共2 798 a以来的水灾数据10 295条,疫灾数据1 392条。
3.2 研究方法
3.2.1 灾害计量指标分析
灾害计量分析,是对疫灾和水灾的时空规律进行客观分析的前提条件。通过参考龚胜生等[13]、张涛[33]的研究成果,采用灾害年数、灾害市数、灾害频度和灾害广度作为水灾和疫灾的计量指标。“灾害年数”是指某一时段内的“灾害之年”的累计个数。其统计方法是,不论灾害流行的时间和强度,只要某年有某个市域发生水灾或疫灾,则确定该年为“灾害之年”。“灾害市数”是指某一时段内,累计发生灾害的市数。“灾害频度”是指某一时段内的灾害之年与该时段所经历年数的百分比。“灾害广度”是指某一时段内灾害流行的行政区国土面积之和。本研究将历史时期分为先秦两汉(公元前887—公元220年)、魏晋南北朝(221—581年)、隋唐五代(581—960年)、宋朝(960—1279年)、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清朝(1644—1911年)8个历史阶段,以2015年省、市政区为参照,对长江流域的灾害指标序列进行计算分析。根据张涛[33]对明代疫灾等级的划分标准,根据灾害广度,对长江流域先秦至清代时期灾害年份的灾害强度进行划分。
3.2.2 全局自相关分析
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 (Moran’sI) 方法对长江流域历史时期水灾和疫灾总体时空格局及演变趋势进行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1)

(2)
统计的莫兰(Moran)值检验值ZI得分按以下形式计算,即
(3)
其中:
E[I]=-1/(n-1) ;
(4)
V[I]=E[I2]-E[I]2。
(5)
Moran’sI指数介于[-1,1]之间,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下,如果值为正则表明灾害呈现空间聚合特征,如果值为负则表明灾害呈现空间的离散特征。当|Z| > 1.96(P< 0.05)时,表明研究区灾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3.2.3 热点分析

(6)
式中xj是灾害区域的j的属性值。且有:
(7)
(8)

3.2.4 统计分析
计算水灾与疫灾受灾区域在同一时空下的交集,能更直观探究两种灾害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运用GIS统计分析中的交集制表工具,计算两种灾害受灾范围的交集,并对其相交的面积进行交叉制表,得到水疫灾害受灾范围在空间上叠加后的重合度。
4 结果与分析
4.1 长江流域水灾、疫灾时间变化特征
4.1.1 朝代变化
长江流域先秦至清末 2 798 a中至少有789个水灾年,水灾频度为28.20%,平均每4 a有一次水灾发生,其中元朝至清末时期不到2 a就有一次水灾发生(表1)。历史时期的水灾具有波动上升的趋势:魏晋南北朝、宋朝至明清时期是水灾发生的两个主要高峰期。从疫灾频度上看,疫灾的高峰期在魏晋南北朝和明朝时期。而疫灾在历史时期至少有201个疫灾之年,疫灾频度为7.18%,平均每14 a就有一次疫灾发生,元朝至明清时期相对更频繁,平均每6 a有一次疫灾发生。从疫灾市数上看,各时期的疫灾流行强度均小于水灾,灾害市数均未超过500个。总体而言,疫灾发生的频次低于水灾。在历史时期,水灾的产生受气候影响为主,而疫灾从发生到传播形成大面积疫病灾害,还需要有利于疫病的传播媒介,如交通便捷性、经济流动量、人口密集度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传播媒介得到提升,疫病致病因子、病种增多,使得疫灾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表1 水灾和疫灾计量指标统计
4.1.2 年际变化
对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水灾和疫灾进行不同尺度计算,得到水灾和疫灾年际变化趋势。10 a尺度下,水灾市数在100个以上的时段有8个,最密集期在1292—1301年,水灾市数301个(图2(a))。世纪尺度下,水灾有两大主要波峰(图2(b)),分别在313—412年和1113—1212年,灾害市数为361个和1 142个,两个波峰期的波动周期都在200 a左右,都是战争频发和朝代更替的时期,第一个高峰期在魏晋南北朝后期,第二个高峰期正值宋元两朝更替。10 a尺度下,疫灾市数在50个以上的时段有5个,最密集期在1472—1481年,疫灾市数78个。世纪尺度下,疫灾波动趋势更为明显,共有6个波峰,波峰的平均波动周期在200 a左右,其中最大的波峰在1513—1612年,疫灾市数179个,且是波动周期最长的一个。综合可知,水灾最密集期在12世纪,疫灾最密集期在15世纪。通过对两种尺度下的水灾和疫灾进行六阶多项式拟合,并对水、疫灾害在10 a尺度和世纪尺度下的趋势线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948和0.927,表明水灾和疫灾在不同尺度下均具有相同的波动趋势。由图2可知,疫灾的趋势线主要在水灾的下方,表明水灾发生频率在同时期下要高于疫灾发生频率。

图2 不同尺度下灾害市数年际变化趋势
4.1.3 季节变化
对有明确记载灾害月份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到各月份在历史时期的水灾市数(图3)。从四季分布来看,春末到初秋时期是水灾频繁期,晚秋到次年的早春时期为水灾稀疏期,其中春季水灾最严重的是5月份,秋季在9月份,夏季是各时期水灾最严重的季节,冬季则是水灾低发时期,冬季各月份受灾市数不足100个。由于长江流域位于副热带季风气候区内,在夏季风的影响下,降雨充沛,因此夏秋季节是长江流域的防汛期。冬、春季节,国内盛行干燥寒冷的偏北风,降雨量普遍减少[34],长江流域也由此进入枯水期,与水灾的高发期与低发期相对应,表明水灾的发生与季节性具有一致性。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及资料的收集完善情况,以下数据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历史时期的实际灾害情况,实际发生的疫灾数量肯定会多于已有记录,但是依然有助于了解把握长江流域历史时期水灾的基本情况。

图3 水灾季节变化
历史时期各月份累计疫灾市数847个,其中春季347个、夏季219个、秋季140个、冬季141个(图4)。从四季分布上看,春、夏季是长江流域疫灾最严重的季节,其中春季最严重的在5月份,夏季在6、7月份,两季合占全年的2/3,属于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灾害市数差异不大,而秋季主要集中在9月份,冬季各月份较为均衡,两季均占全年的1/6,属于疫灾低发时期。疫灾的流行强度和时间通常跟外界温度和卫生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从长江流域的灾害季节性可知,高温、高湿环境利于疫灾的传播,而进入秋、冬季节,随着外界气温的下降和水患灾害降低,疫灾的流行强度也呈逐渐下降趋势。

图4 疫灾季节变化
4.1.4 强度分布
根据长江流域各年份的灾害范围即灾害广度,对先秦至清末时期的水、疫灾害进行等级划分,将灾害流行强度分为5级:轻微型(≤1万km2)、小型((1万km2,3万km2])、中型((3万km2,6万km2])、大型((6万km2,9万km2])、特大型(>9万km2),见表2。由表2可知,长江流域789个水灾年中,以中大、特大型水灾为主,占63.50%,其次是小型水灾,占24.08%。从朝代分布上看,各历史时期的水灾年份均以特大型水灾为主,其中占比最高为元朝52.11%,其次是先秦两汉为46.15%。在长江流域的201个疫灾年中,疫灾以中小微型为主,占68.16%,其次是特大型疫灾,占27.36%。从朝代分布上看,各历史时期的疫灾年份除宋、元时期均以小微型疫灾为主。历史时期的疫灾大多作为次生性灾害,在人口密集地区传播,当人口流动小时,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而水灾一旦发生,常常以河流决溢、山洪暴发的形式出现,以此导致大面积受灾。此外,救灾不及时也是灾害扩大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直至清朝时期才形成相对独立完善的救灾机构以及制度,在以往的政府救灾中,大都以当朝皇帝主持临时救灾小组对发生的大型灾害进行救助。因此在发生大型灾害时,不完善的救灾体制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伤亡以及损失延续。

表2 水灾和疫灾强度分布
4.2 长江流域水灾、疫灾空间分布特征
4.2.1 总体空间格局分布
先秦至清末时期长江流域水灾和疫灾频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灾害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先秦两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灾、疫灾的灾害频度分别为2.35%和1.36%,清朝时期上升至74.16%和15.36%,灾害市数从先秦两汉的249个和132个至明朝时期分别上升到2 619个和422个。历史时期水灾和疫灾发生频率及受灾范围的扩大必然对长江流域市域间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工具计算历史时期的灾害市数,并进行显著性检验(表3)。长江流域水灾、疫灾从先秦至清朝时期的灾害市数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表明各时期的水灾和疫灾的受灾市域整体分布呈空间聚合特征,但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先秦至清朝时期的灾害市数莫兰指数标准化Z值均大于显著性检验临界值 1.96(P<0.05),表明长江流域各时期的受灾市域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受灾严重的市域,其周边市域也会存在较严重的灾害破坏,而受灾较轻的市域周边市域受灾影响也会较小。

表3 水灾和疫灾莫兰指数统计
4.2.2 水灾局部空间变化及其冷热点分布


图5 各历史时期水灾冷热点分布
图5显示,水灾热点高显著区范围主要有2个变化:①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灾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其主要原因为隋唐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在主要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以北地区,而早期的经济重心又是人口密集、兵家必争之地,当遭遇水患时,北方受到的水灾影响相对我国南方较大,从长江流域的水灾高发区来看,也主要以与早期的经济重心接近的省份为主;②魏晋南北朝至清朝时期,由安徽西部向西南方向市域扩大至贵州地区。其中范围最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上海、江西东北部以及湖北东部地区,清朝时期热点高显著区范围最大,分布于长江干流中下游大部分市域。热点中低显著区环高显著区零星分布。西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最频繁的时期,北方遭受到频繁战乱的沉重打击,使得我国的经济重心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向南方转移,直至北宋末年彻底完成转移,随着经济的转移,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和先进的农耕技术[35]。因此南方在经济得到开发时,人口的增加以及产业的转移必然导致环境受到不可避免的破坏,而魏晋南北朝、晚唐时期以及清朝又是中国2 000 a来的3个冷期[36],社会因素与极端气候的出现,使得南方的水患灾害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扩大,在长江流域则表现为不断向中上游扩展。
(2)水灾低发区主要分布于云贵川一带。冷点高显著区的分布主要以四川、贵州和云南为中心向周边市域扩大或缩小。冷点中低显著区从先秦两汉至明朝时期其波及范围总体呈向青海和西藏方向扩大趋势,清朝时期范围最小,主要环冷点高显著区分布于四川、贵州和云南境内。
4.2.3 疫灾局部空间变化及其冷热点分布
(1)疫灾高发区以安徽西部为界向贵州方向扩展。由图6可知,疫灾热点高显著区范围主要有2个变化:①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高发区都集中在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但灾害市数从114个增加到119个,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更加集中频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频更,烽火不断且安徽江苏等地又是兵家必争重地,必然会造成此时期的疫灾集中爆发。②魏晋南北朝至清朝时期,由安徽西部向西南方向市域扩大,灾害市数从隋唐五代时期的79个增加到明朝时期的289个,清朝时期减少到161个。从受灾范围来看隋唐五代时期较为分散,明朝时期集中而广,从灾害市数来看隋唐五代时期最少而明朝时期最多。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唐朝是继西汉以来中国最稳定强盛的时期,且医疗较前有所发展,因此疫灾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有所下降。而明朝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手工业发达,人口稠密,且交通便捷,人口流动性大,为该时期的疫灾传播提供了更快的途径,同时水患灾害在明朝时期最严重,也成为疫灾的重要诱因。疫灾的热点中低显著区环高显著区分布,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西和湖南部分市域,灾害市数较少。

图6 各历史时期疫灾冷热点分布
(2)冷点区从湖南、湖北向青海、西藏方向迁移。疫灾的冷点区主要以长江上游为主,其中冷点高显著区主要有2个变化:①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由四川、云南和贵州向东迁移至湖南、江西和湖北,且范围明显减小,灾害市数均在10个以下;②隋唐五代至明朝时期,由湖南、湖北逐渐向西部的四川、青海和西藏迁移,至清朝时期冷点高显著区范围有所减小,其中灾害市数在元、明时期最多,分别为18个和35个,其他时期均少于10个。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水灾低发区始终以长江上游为主,主要是由于历史时期长江上游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导致人员流动性小,为疫灾传播形成天然屏障,而水患等灾害发生频率低,也使得诱发疫灾的可能性降低。总体来看,疫灾的高发区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市域,低发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市域。
4.2.4 水、疫灾害具有相同的迁移扩展趋势
从总体上看,长江流域水、疫灾害热点区以长江中下游为主,冷点区以长江上游为主。长江流域水、疫灾害随着时代发展,在空间格局分布上均有2个变化:第1个变化发生是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水、疫灾害范围从湖南东部地区向安徽西部区域逐渐缩小,主要集中在安徽、浙江、上海等省(市)。第2个变化是魏晋南北朝至清代时期,长江流域水、疫灾害范围从安徽西部不断向长江中游方向扩展。先秦两汉时期的农业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淮河流域、荆州北部地区以及关中平原地区,因此大量的人口以及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由于人口较多的集中于河岸地区,这也是水灾在先秦两汉时期多点频发的原因之一,而人口密集区和水灾频繁区同样也是疫灾的多发区[4]。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极端气候出现以及中原持续不断的战乱,使得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北方人口大量的迁入南方地区,这些因素导致了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更加容易发生大型水灾等自然灾害,同时温暖潮湿的环境与自然灾害叠加更容易引发北方移民疫病甚至产生疫灾。隋唐五代至清代时期,长江流域水、疫灾害次数及强度总体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由图5和图6可知,长江流域水、疫灾害在空间上也具有相似的分布格局。长江下游成为我国水、疫灾害的热点区,主要是因为降雨丰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东高西低的地形地势、魏晋南北朝直至宋朝的经济重心南移、开垦森林导致生态环境破坏。长江上游的冷点区主要处于青藏高寒区以及干旱少雨区,人口较少且经济活动受到环境局限影响大,因此这些地区的主要灾害类型以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为主,相对于长江下游地区水、疫灾害的发生频度较低。
4.2.5 水灾多发区亦是疫灾高发区
灾害多发区,往往是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区域,在各时期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就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水、疫灾害热点高显著区即灾害高发区进行分析,通过对图5和图6中各时期的热点高显著区进行交集制表,得到水灾高发区与疫灾高发区在空间上的重合度,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的水、疫灾害的高发区在空间上均具有较高的重合度。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灾害高发区重合度达95%以上,重合度最低在隋唐五代时期,为73.04%。由上可知水灾频繁发生的区域同样是疫灾频繁发生区域,而水灾低发区域,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疫灾的诱发程度。

表4 水灾与疫灾热点高显著区域重合度统计
5 结 论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长江流域的水、疫灾害时空特征,可知二者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同频共振性。通过对长江流域2 798 a来的水灾和疫灾进行统计分析,二者在相同时间地点同时发生的次数达360次,占疫灾发生总次数的25%,表明水灾和疫灾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疫灾的发生与水灾具有密切相关性。长江流域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越来越密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只会更加深入,对水灾的治理以及疫灾的防控压力也会加大。因此,只有把握好历史时期长江流域水灾和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才能在应对现代自然灾害时合理降低灾害的影响程度和减少经济损失。
《中国灾害通史》[1]是本文全部的灾害数据来源,本研究通过对书中不同历史时期水灾和疫灾数据进行整理,得到长江上游省域的灾害数据较少,甚至在一些朝代未有记载,特别是西藏和青海等地。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央政府对于疆域的管辖范围都有所不同,并且史料大多着重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央政权管辖区域,西藏和青海又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关于水灾和疫灾的记载相对长江下游自然有所缺失或者描述粗疏,因此实际的灾害数量肯定会多于史料记载的数据,这些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定量结果的精确性,但不会影响研究的定性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如长江流域上游是灾害的低发区,长江下游是灾害的集中高发区,水、疫灾害具有相同的空间迁移扩展趋势,水灾的多发区亦是疫灾的高发区等结论。本文具体结论如下:
(1)长江流域先秦至清末2 798 a中至少有789个水灾年、201个疫灾年,灾害年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水、疫灾害在元朝至清末时期的发生频率为先秦至元朝时期的2倍;在10 a尺度和世纪尺度下二者具有相同的波动趋势,同时期下水灾发生频率高于疫灾。
(2)长江流域水灾和疫灾的波动与季节性变化具有较强相关性,在长江流域进入防汛期的夏秋季节,是水灾的高发期,而进入冬春季节,随着降雨量的普遍下降,水灾也大幅度减少。疫灾高发期主要在春夏季节,秋冬季节属于疫灾低发时期。
(3)从灾害广度上看,各历史时期水灾以大型灾害为主,疫灾以小微型灾害为主,不完善的救灾机制是导致灾害损失扩大的重要原因。
(4)水灾和疫灾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为受灾市域间具有较强的相互影响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空间格局变化上具有相似的迁移扩展趋势;同时期的水、疫灾害热点显著区也具有较高的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