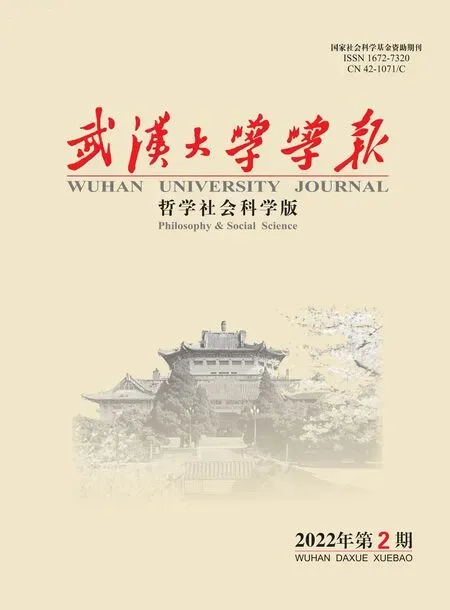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意义阐释
荆世群
2013年,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P21)这一重大命题,深刻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理论自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也是分析、论证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就此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当自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否则就会陷入循环论证。无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集中反映和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主旨、思想结构和精神实质,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支柱,同时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导引。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迫切要求,对我们系统完整地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确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批驳“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早产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增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经典著作和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内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核心、思想结构和精神实质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历来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论证方式和思想力量,是我们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枢纽,澄清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的重要方法。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枢纽。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转变。正是出于这一时代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论证。马克思说:“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2](P295-296)马克思强调,在他那个时代,重要的不是进行一些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严格、系统的科学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论证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系统批判完成的,由此将共产主义理想奠定在现实基础之上,使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向科学的历史性转变。在马克思看来,科学论证的威力比一些零星的实际试验更能抓住人心,更强大持久;“武器的批判”首先需要“批判的武器”“思想的闪电”和“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类解放首先需要“主体觉悟”,“手脚的解放”需要“头脑的解放”;“正是由于头脑的解放,手脚的解放对人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家知道,手脚只是由于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头脑——才成为人的手脚”[2](P188)。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头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趋势的理论把握,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性质和一般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呈现,集中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核心、思想结构和精神实质,即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将之集中表述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从“理有固然”到“势所必至”的理论空间和历史空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不是抽象公式或固定模式,而是一种纵横交错、系统、动态的思考方式和论证结构,需要根据新的问题和条件不断深入理解阐释,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概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研究了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和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前者重在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马克思特别强调,不能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概述抽象为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后者重在探索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晚年根据当时最新历史资料深入探索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表明,即使是在现代世界之中,东方社会也不可能自行发展出或者以被动楔入的方式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前提。东方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在于其不能全盘照搬西欧式的社会发展道路。正是这种差异,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世界中的运动直至产生出扬弃自身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3]。马克思恩格斯既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性,因此,“特别注重开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的双重考察,坚决杜绝社会发展模式的单一化,始终把社会形态的科学探讨置于具体而真实的现实历史语境中,从而极力破除一切超时空的、僵化的‘单一模式’神话”[4]。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区分理论判断和历史判断的重要尺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不是以解释世界为主旨的纯粹逻辑推演,不是抽象的逻辑公式,而是以改变世界为主旨的理论探索和理论介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因此成为改造世界的能动因素,其历史判断和理论判断虽然相互影响,却不可混为一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面目和思想重心并引发激烈争论。俄国学者鲍·斯拉文说:“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判断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逻辑太清楚了,以至于产生了视觉上的特殊误差,即距离上的错觉。这就好像透明的水会使人觉得湖底或河底很浅一样,严谨的科学理论往往使结论提前得出。现实的历史可能会落在历史逻辑的后面,甚至同历史逻辑的最终结论相矛盾,但现实的历史迟早会实现这些最终结论。”[5](P111)在斯拉文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清晰而确定的,马克思的失误之处主要是其历史判断;而马克思之所以产生历史误判,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清晰的理论逻辑造成的“视觉上的特殊误差”即“距离上的错觉”。“马克思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过高估计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借助于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潜在的资源自行发展的潜力;他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作用,过低估计了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命力。但是,这是天才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并没有改变和推翻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的总的预测。”[5](P10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旨在揭示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固有之理”,不可能涵盖或取代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历史进程的误判,比如对欧洲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误判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判。只有深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我们才能准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判断和理论判断,既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臆造所谓“两个马克思”,也不能将之混同起来,将其一时的历史误判视为根本理论错误。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防止和澄清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的重要方法。有些学者因为采取单一理论视野和非辩证的方法来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对它的严重误解、曲解。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一般认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矛盾,即:马克思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信奉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从理论上论证个人行动要取决于外在的集体秩序。”[6](P13)这种将自由与必然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和方法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不在于摆脱必然而遗世独立,而在于正确认识必然,按照必然才能有效行动。又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本人的著述中,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是并存的,并且无法相互还原。如果马克思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当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他的革命主张就只能停留在主观诉求上;反之,如果马克思没有把推翻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关切,他就可能像别的经济学家那样满足于描述事实,甚至也不必采取辩证的方法。至于那种把这两个方面简单说成有机统一的做法,则完全没有理解理论辩证法对意志略去不计和实践辩证法注重发挥意志作用究竟意味着什么”[7](P17)。这种将理论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虽然有助于凸显两者的区别,却将两者割裂开来,不仅会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且势必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
上述理解以单一主题和单一视角,运用非辩证的方法,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机械决定论,就是将之视为唯意志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解为自由与必然的逻辑悖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解为理论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的分离。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决定论与能动论的辩证统一。“正因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之性质的观念既肯定承认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又为自由意志(或者说‘主观能动性’)进而为道德价值承诺留下了空间,马克思对于现实社会和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各种意识、实践的态度,也就既不苟同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论调,或仅仅拘泥于纯粹‘技术性的批判’,也不仅仅是纯粹从‘应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抒发道德义愤,而是一种将价值目标(‘应然’)和既有的客观历史条件为这种价值目标的实现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必然’)相结合的分析批判,是从‘应然’和‘必然’两个维度对‘实然’所做的审视批判。”[8](P32)深入研究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对澄清和批驳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支柱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支柱。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历史过程。对这个理论逻辑的理解运用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成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概括而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回答: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可以说争论得一塌糊涂,其中最著名的两种主张被概括为“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主张,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自然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其前途必然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应程度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因为缺乏阶级基础和社会意义而失败。“一次革命论”主张,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已背叛了资产阶级革命,其必然不能以资产阶级革命而自限,必然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连锁一体而成为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反复自忖,左右摇摆,屡受挫折。“对于导致中国共产主义在1927年灾难性失败的共产国际策略的失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寻求自主性的潮流,而且唤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回到理论源头去的强烈渴望。既已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杂性,中国人现在显然不愿意在苏联领导的指令面前弯腰,他们甚至运用他们最新获得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来挑战莫斯科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官方版本。”[9](P32)正是出于对中国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迷信,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在深刻反思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把革命的阶段论与转变论辩证地结合起来,阐明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挫折、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合理性和理论合理性。有学者认为,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缺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一再遭受挫折,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搞得太早了”,改革开放不过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有学者认为,我们之所以没能够从正面回答上述重大理论问题,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漏洞与尴尬,即一方面,运用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搞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其实,在中国,公有制不是源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是源于国家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手段[10]。
上述观点耐人寻味,激发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逻辑。无疑,仅仅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难以完全阐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同样,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也难以阐明中国何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然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既不能从关于社会主义一般性质的真理中推导出来,也不能从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中推导出来,必须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和世界环境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逻辑,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理论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途径、步骤和方式,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征。“揭示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很好地发展中国的道理,就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实现途径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实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核心内容不能变,社会主义实现途径和实现形式可选择。”[1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不是自我设立、自我封闭的理论循环,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理论把握,不仅要集中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历史发展,而且要集中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构性特征。显然,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基于社会主义实践,两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同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作为以抽象方式对世界的精确描述,而是作为一种对世界作理论化概括的方式,该理论带有任何理论都具有的特征,即在现实与再现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是非常有效的。承认这种差距,就能打开理解理论的另一种方式,即按照世界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先决条件(还有其他条件)去解释世界。它也启动了理论的开放性,接纳基于不同现实检验的不同解释。当然,这也使理论丧失了目的论,丧失了用以指向社会主义未来的确定性。另一方面,这又导致理论与政治现实更为接近。”[12](P96)上述论断一方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另一方面又把马克思主义误解为某种目的论。其实,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目的论,它明确反对教条式地预见未来。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理论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开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中国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历史性距离并将之转化为我们不断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理想正确道路的精神动力。
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研究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研究结合起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范式,才能阐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如果说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范式的唯物史观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唯物史观研究是基于马克思要回答‘西欧时代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的理论问题,那么,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转向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就是基于马克思要回答‘西欧时代性之外’的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13](P22-23)同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立足现实需要,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才能实现实践、理论和制度等系列创新,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是马克思的出发点和归宿。除了从当前的物质条件出发,没有其他通往未来的道路。”[14](P79)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表达,或者说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逻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范式。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为主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实现了一系列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有学者评论说:“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在自身斗争中学习经验,但是同时也把这种经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实现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多种实践方案,并总结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宝贵经验。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概念都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总结,但是它们也反映出对于由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远离与拒斥。”[15](P71)
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导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于它是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不仅要符合逻辑自洽性并自成一体,而且要扎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能导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能获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证实。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始终面临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重心在于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理想,使之由空想转为科学,并积极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以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消除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不良影响。因此,“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必然产生、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产生、社会主义产生以后要经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有什么样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等这样一些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追求者的问题,也就成为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着力阐释和论证的基本问题”[16](P59)。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当时历史条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历史判断,如: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同时发生;俄国在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呼应和支持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可能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序幕,等等。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历史判断并没有得到如期证实,后来马克思恩格斯也已认识到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足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并公开说明其历史判断有误,还由此引发一些怀疑和争论,但这些历史误判实际上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简要地说,这只是具体历史判断问题而没有触及深层的理论逻辑问题。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过程中,其理论逻辑重在理论论证,那么,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向实践特别是制度性实践的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来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主要受到以下两次重大挑战。
俄国十月革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历史判断,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爆发并取得胜利。当时的俄国是一个比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百倍的国家,根本不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俄国却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面对这种似乎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截然对立的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激起了轩然大波,彼此激烈争论,至今余音不息。
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质疑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问题。在他们眼中,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事件。1918年,考茨基指出:“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7](P375)俄国十月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7](P376)。普列汉诺夫则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18](P263)这种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早产论”“反常论”“原罪论”。由于第二国际的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曲解为经济决定论,而将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既误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又曲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人类历史是不可能按照某种理论公式来创造的,“如果只遵循马克思的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无法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进程”[19](P74)。第二国际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当作一种抽象固定的理论公式,自然难以正确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性质。
列宁为阐明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历史合理性、理论合理性,一方面批评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阉割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为了死的教条而牺牲了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根据新的时代条件重新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强调革命群众的首创性、能动性、历史灵活性、世界历史特殊性和先改造社会“上层”后夯实社会“基础”的历史合理性、理论合理性,突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体逻辑、能动逻辑和国别逻辑。从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思想重心从“理论论证”转向“经验探讨”,从论述“革命的经验”转向做出“革命的经验”[20](P221),从“世界革命”转向“一国革命”。正如列宁说的:“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1](P446)列宁通过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时回应了当时的重大挑战。
苏联解体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第二次重大挑战。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历史就这样充满曲折和意外。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曾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典型和希望之乡。如果说苏联以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逐渐消除了人们对其社会主义革命的质疑声音,被视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故乡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那么其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出现愈益严重的问题,并在改革过程中最终走向解体,则再次引发一些人质疑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俄国十月革命70多年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塌,由此又激起轩然大波,再次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反思。有的人旧话重提,老调重弹,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本来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解体正是“马克思的复仇”;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即使侥幸取得一时的胜利也难以持久;列宁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第二国际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迷途和歧路,苏联解体不过是转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常轨道。甚至有学者提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历史就此终结,试图以苏联解体为由全面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由此影射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执迷不悟”。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以便澄清“苏联版马克思主义与原版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苏联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原版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论调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都是错误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回归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什么“马克思的复仇”,恰恰相反,而是其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历史后果。有学者分析说:“苏联东欧的剧变主要是各国党从1987年以来指导改革的思路明显不对头,使改革改变方向,由社会主义急剧转轨到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样改换旗号造成理论改向;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急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立即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经济混乱;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去加快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盲目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造成政局动荡;在思想文化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造成思想迷惘;在对外关系上对西方过于迁就退让,过早过急从东欧撤军撒手,不断丧失阵地。”[22](P468)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二十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二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23](P87)
在一些人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危机、叫嚣“历史终结论”余音未息之时,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就是对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的历史终结论以及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等老生常谈观点的否定”[24](P49)。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却又陷入了深重危机而难以自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激发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动力。无论是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无论是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挑战还是面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都需要我们根据新的实践和历史经验进一步深化理解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法定继承者,但在实现方式上却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判性挑战。”[25](P81)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对我们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把握当代世界变革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 语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具有高度理论自觉和自我意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有大量论述,不同时代、不同人们基于不同的现实基础和个人理解各有不同的把握和阐述。即使在同一时代环境,怀着共同的旨趣,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理解和阐述也各有差异。这种理解差异既取决于个人的思想倾向或解释逻辑,更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正是历史的变迁,带来了理论逻辑与理论话语的变迁。”[26](P15)置身世界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总结和吸收既有研究成果,针对各种误解、曲解,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思考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既是我们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我们把握世界历史大势,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理论课题,更是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正如习近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27](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