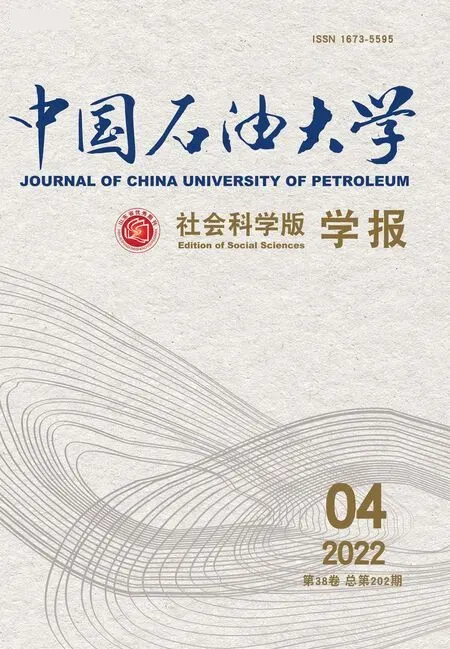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研究
申 伟,彭迎育
(兰州大学 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引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人们享受社会繁荣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在注重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刑法作为法律制裁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预防和制止破坏环境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设置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并将入罪门槛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污染环境罪的刑罚做了修改,将最高刑由原有的七年以下提高至七年以上。
由于环境存在特殊性,生态环境在遭到破坏后,有些影响消除周期较长,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才能修复;有些则永久无法消除。环境犯罪行为不仅会对当代人产生影响,还会对未来几代人的生存环境产生影响。故环境风险常被视为风险社会的典型风险。因此,援用风险社会理论审视刑法对环境风险的应对方案,特别是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如何定位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以及如何设置该罪的主观罪过要素,应有其意义。
二、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之分歧
我国污染环境罪经历了从未有专门规定到《刑法》中设定专门的章节、再到两次《刑法修正案》修订完善的过程,但在其演变过程中立法者并未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该罪的罪过形式,通过具体的罪状也无法将其阐明。由于立法模糊,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发生变化成为重要议题,作为污染环境罪中重要的构成要件,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仍存在争议。
(一)分歧由来:立法模糊
在《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立法者都未阐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对于《刑法》中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学界多从文理解释出发,凭借对“事故”一词的理解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后果,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过失犯罪 ,并逐渐成为主流学说。[1-2]但《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并将法条中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再度引发学界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之争,并逐渐形成了故意说、过失说、混合罪过说三种学说。[3]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2016年相继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污染环境罪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予以明确化,但仍未明确该罪的罪过形式。加之,由于《污染环境罪解释》中所规定的情形既有故意犯罪的表现形式又有过失犯罪的表现形式,学界对于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争论不仅未得消弭,反倒愈加激烈,迄今仍未有定论。[4]
(二)理论分歧
虽然由于早期立法未明确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过失说成为了通说,但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不仅罪名发生了转变,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也发生了转变,对于本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抑或是混合罪过的问题再次被讨论。
1.故意说
以张明楷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应当为故意。张明楷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为过失犯罪,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污染环境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损害结果的产生,即属于本罪的故意[5];从故意的内容看,严重污染环境即为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结果,只要行为人对污染环境的基本结果主观上持有故意即可,并不要求行为人对人本法益的损害持认识与希望或放任的态度[6]17。侯艳芳认为,首先我国刑法只处罚故意共同犯罪,不处罚过失共同犯罪,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认定为过失无法解决该领域中的共同犯罪问题;其次受制于污染环境行为的阶段性以及污染结果产生的累积性,若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认定为过失,那么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性证明将会难度很大,因此,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界定为故意,不仅能够克服我国刑法不处罚过失共同犯罪的障碍,也能解决按照过失犯罪进行处罚证明难的问题。[7]杨宁等认为,从形式上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解释为故意与罪刑法定原则最为相符,污染环境罪不属于“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过失犯罪,如果说在本罪修改前,根据“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事故”“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造成……的后果”的构成要件要素,过失说存在合理性,但《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删除过失的相关表述和结果要件;从实质上采用故意说能够使刑法保护目的处在平衡状态,扩大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减少处罚漏洞,有利于解决实务中的难题。[8]
2.过失说
以冯军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冯军认为,《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并未更改污染环境罪的最高刑期,本罪的法定最高刑仍为七年,这与刑法中其他过失类犯罪规定的法定最高刑相一致,若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则会出现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9]魏汉涛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不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虽然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严重危害环境的后果,但是因其疏忽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产生了严重后果,就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10]姜俊山认为,《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对本罪的罪名做了修改,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仍然是过失,因为故意与过失最大的区别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主观心态,而不是行为人对行为本身的主观心态,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产生所持的态度依然是过失,该法条的修改只是为了解决刑法介入环境污染的滞后性问题。[11]
3.混合说
以高铭暄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高铭暄等认为,污染环境罪在《刑法修正案(八)》修订前是典型的过失犯罪,但不论是从扩大污染环境罪处罚范围的立法意图,还是从修改后的犯罪成立条件来看,都不宜将故意排除在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之外,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为混合罪过。[12]582汪维才指出,从文理解释角度理解,“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罪状的表述表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包含过失,而《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进行修改的目的在于矫正以往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罪过的认识偏差,从立法者的原意可探知该罪的主观罪过包含故意,因此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混合罪过。[13]秦鹏等认为,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沿革、文字表述以及相关的司法裁判来看,本罪的主观罪过在法条修正前后均为混合罪过,不能仅因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改变就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是单一罪;2013年出台的《污染环境罪解释》在保留了过失犯罪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新增了由故意支配所实施的污染环境行为,这进一步表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为混合罪过。[14]李梁通过梳理德国刑法中环境犯罪二元罪过形式的规定,认为消除我国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争议的办法在于借鉴德国立法模式,规定污染环境罪既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15]
(三)实务分歧
不仅学理上对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争论不休,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不同的法院、法官出于对法条的理解不同,对于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形式的认定也不相同。例如,“新疆双龙腐植酸有限公司、武美污染环境案”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卫广民、孔青虎等污染环境案”②,山西省浮山县人民法院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过失;“何宏忠、沈友根、张广山、尹礼飞、赵亮污染环境案”③,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混合罪过。
同时,由于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未明确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许多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对该问题采取回避态度。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发布的2014年1月至2021年7月安徽省审结的267份污染环境罪刑事一审判决书中:251份判决书中法官并未明确说明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的主观罪过;11份判决书中法官将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的主观罪过认定为故意;3份判决书中法官将污染环境罪被告人的主观罪过认定为过失;1份判决书中法官明确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为混合罪过;1份判决书中法官对案件中的五名被告人并未明确其主观罪过,但认定同案另外两名被告人的主观罪过为过失。主观罪过形式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是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刑罚轻重的重要因素。刑法适用过程中若对于行为人的罪过要素不予考虑而仅从客观角度或结果进行论述,不仅违反罪刑法定的要求,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而且容易导致刑罚权滥用。因此,明确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也是现今中国刑事司法实务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确定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之考量因素
罪过形式的确定不能孤立进行,而应依据具体的社会背景、具体法律所保护的法益进行考量。
(一)社会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与生态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孤立于世界的个人为观察对象的人类图像,开始有了改变。[16]对于这一新的社会背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17],他认为工业社会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了安逸的生存环境,但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仅体现为对大自然的破坏,而且还相伴而生对经济、社会、人类生存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18]。对于风险的研究最初集中于社会学领域,后来法学也逐渐开始重视对风险的研究。德国刑法理论界最早对“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回应。[19]19与风险社会理论不同,刑法理论中的“风险”概念更多的是指人类应受处罚的行为对法益所造成的威胁。从概念上来看,刑法理论中的风险被风险社会理论所涵盖,风险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安全刑法或预防刑法的产生。安全刑法最早由德国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提出,他认为:“今天的刑法不仅是对侵害的反应,而且它还有这样的任务:使保障社会安全的基本条件得到遵循。”[20]他还认为:“安全刑法被定义为一个风险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条件。”[21]
风险社会是环境刑事立法和改革的基础。环境风险作为风险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所引发的伤害具有不可逆性。人类在不断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环境的过程中,为后世的生存和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随着环境风险的不断加剧,刑法介入环境犯罪的时间点适当向前调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受传统刑法的影响,出于对人本化、物质化侵害结果的保护,只有当污染行为出现了明确的侵害结果时才会对行为人适用刑法,这也是1997年《刑法》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适用极少的原因。当今社会,环境问题所引发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其结果往往难以预料。针对环境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刑法应当提早介入,规制行为人可能导致的环境风险行为。坚持风险预防与控制原则,在不突破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对污染环境罪进行规制。如果仅仅从侵害的结果入手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则会限缩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
(二)法益定位
法益作为现代刑法的核心内容,是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的刑法观只注重对人本法益的保护而忽视了生态法益,极易导致与之相配套的环境刑法的制定与实施存在缺漏,诸多破坏环境的行为无法得到规制。由此,“刑法提前介入”“法益保护的前置化”逐渐成为理论界的热议话题。
目前对于环境犯罪(包括狭义的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存在三种立场,即人本法益论、生态法益论以及折中的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
1.人本法益论
人本法益论认为,刑法对环境进行保护,其实质是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基础不被破坏,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环境本身不应当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只是作为行为指向的对象;只有当应受惩罚的环境犯罪行为侵害了人类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时,才能构成环境犯罪;在未侵害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即使环境犯罪对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产生巨大危险,也不应当成为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这与传统刑法保护的人本化、物质化观念相吻合。事实上,我国1997年《刑法》中设置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犯罪行为必须产生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导致财产损失的结果,正是人本法益论的体现。
环境犯罪人本法益论的产生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息息相关,将人作为核心,对于一切事物的考量都从人的利益出发。在承认人自身价值以及自然作为人类工具价值的同时,却否认了自然本身的独立价值,即认为人类的利益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与唯一性。[22]由此产生一种观念: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或工具都是可以的,自然环境作为工具也不例外。实践证明,上述观念并不可取,环境以实际行动给了人类惨痛的教训,如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从人的利益出发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环境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损害结果的累积性,一些损害结果的出现往往具有滞后性,在损害行为发生的当时并未能察觉,而一旦发现往往伴随着极其严重的后果。若仍将对人类生命财产产生的损害结果作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很多时候难以使其起到真正的作用。
2.生态法益论
生态法益论与人本法益论相对,侧重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将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以及与环境相关的其他要素进行独立的刑法保护。生态法益论脱离了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起源、发展都源于生态环境,人类作为经过进化的高等生物,仍属于生态环境的一部分。生态法益论偏重于对环境的保护,不再将生态环境视为可供人类任意攫取和破坏的工具,扩张了刑法的处罚范围。生态法益论将环境犯罪的处罚标准前移,突破了人本法益论中出现损害结果才处罚的要求,当环境犯罪行为导致了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人类的权益,刑法都理应对该行为进行处罚。在生态法益论中,环境的独立法益地位被承认。
生态法益论有利于保护环境,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生态法益论将环境作为独立的法益进行保护,当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与自然体的权利发生冲突时,从二者具有的独立价值出发,很难清晰地衡量哪个需要优先保护。环境犯罪所指向的客体比较复杂,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并不是出于犯罪目的,例如,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存条件,捕杀对人类有害的动物。若将此种行为按照环境犯罪进行处罚,必定无法令人信服。这样势必会导致刑法的不当扩张,严重挑战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削弱民法、行政法对环境保护的功能。
3.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认为,水、空气、土壤、动植物作为独立的生态学的法益应当得到认可,但只有当环境作为人的生活基础而发挥作用时,才值得刑法保护。[6]4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论并不偏向于人本法益或是生态法益,而是承认生态法益在刑法保护中的独立价值,但生态法益必须与人类世代生活的空间和条件存在关联性,即通过直接保护生态环境的手段,达到间接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更符合社会需求。不论是人本法益论还是生态法益论,都是单纯地将人与环境割裂开来,忽略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但从生态环境整体角度出发,生态环境除了包括水、空气、其他动植物外,人类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生态学的人类中心观将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的环境伦理观结合起来,超越了狭隘的界分和僵化模式,摆脱了单方面考察所固有的局限性。[23]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人类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实现长久永续发展的价值需求。正如罗克辛所说:“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实现或者目标设定。”[19]15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本身就有利于人类及其自由发展,将生态环境和人类共同作为法益保护的对象并对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有利于生态环境与人类协调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必然会成为趋势,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通过考量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整合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价值需求,对其适用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立足于我国法律实践,《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338条的构成要件由“造成人身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意图将对环境的侵害和对人本法益的侵害都涵括在“严重污染环境”中。[24]这一表述本身就包了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的行为虽未侵害人本法益,但只要对环境本身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二是行为人的行为虽未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但其行为间接地导致了人本法益受到侵害,也应当对此承担责任。这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的内容为:“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这也凸显了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化,我国的环境刑法法益观也发生了改变。
除以上三种观点外,还有学者从刑法体系出发,主张污染环境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应当为环境管理秩序。[12]580将环境管理秩序作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要保护法益,实质上并没有明确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因为环境管理秩序指向的仍然是对环境的保护,我国刑法将其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对环境污染行为治理的重视程度,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环境管理秩序。从逻辑角度讲,污染行为虽然侵害了环境管理秩序,但若没有侵害具体的法益、不足以达到犯罪边界时,仍不能判定其为污染环境罪。[25]
四、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故意说之提倡
综上所述,从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变化出发,故意说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更为契合。
(一)故意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环境风险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刑法对于污染环境的行为由事后惩治转向事前的防治,有效控制了环境风险对人类安全及其生存环境的威胁。风险社会中刑法的目的不在于报应,而在于对安全的保障。为有效防范风险,风险社会中刑罚的配置要采取刑罚轻重与潜在危险性相称的法则。[26]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自然犯罪对法益所产生损害结果的即时性不同,污染环境罪对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的侵害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特点,加之环境治理也需要极高的经济成本,污染环境罪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作出一定的妥协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刑法体系出发,污染环境罪处于《刑法》分则第6章第6节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在这一章节中除污染环境罪外,其他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在学界和司法界均被认为属于故意,而且污染环境罪的量刑幅度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的其他故意环境犯罪的量刑区间基本一致,与本节犯罪的法定刑量刑体系相适应。[27]其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基本犯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或5年有期徒刑,加重犯的法定最高刑为7年或10年有期徒刑,对于侵犯特定对象或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处7年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污染环境罪的三档法定刑分别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与本节中其他犯罪的法定刑处在同一区间内。因此,将故意作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与罪刑均衡相适应。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介入行为的时间提前,使得法益保护前置化,实质上是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在法定刑并未变化的情况下降低入罪门槛,实质上是提高了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28]《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刑法》第338条的修改以及后续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均表明了我国环境立法对于保护法益的转变。2016年颁布的《污染环境罪解释》列举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8种情况,其中既包括对环境本身造成损害的情形,也包括对环境实施违法行为导致人身财产受损害的情形,清晰表明了法益观由人本法益观向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的转变。《刑法修正案(十一)》扩大了该罪的处罚范围,将法条中原有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由“后果特别严重”修改为“情节严重”,吸收了《污染环境罪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将“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重大伤亡”的结果作为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条件,但不再以结果作为构成污染环境罪以及加重处罚的唯一条件,扩大了加重犯的处罚范围。故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认定为故意,既不存在限缩本罪处罚范围的情况,也不会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过失说与混合说批评故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污染环境罪的法定最高刑仍为7年有期徒刑,若将此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则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我国《刑法》中并非不存在故意犯罪法定刑较低的罪名,如第133条之二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第252条的侵犯通信自由罪都是典型的故意犯罪,二者的法定最高刑仅为有期徒刑一年。况且,立法者对于各种罪名法定刑的配置所考量的因素,并非仅有罪过形式一个方面,还包括社会危害性、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等因素,仅从罪过形式出发考虑法定刑的轻重并不合理。前文所述混合罪过说提出的应当借鉴德国环境立法的经验、将故意与过失均纳入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中,虽然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应当从各自的国情与发展水平出发,探索适合本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在我国《刑法》没有进行相应修改之前,将故意与过失均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会使得故意与过失的界限模糊化,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不相符。
(二)故意说符合文理解释
首先,我国《刑法》第14条和15条中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两种主观罪过形式,并明确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即我国《刑法》中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过失犯罪为例外。当法条只描述了客观构成要件而没有规定具体的行为心态时,应当认为该行为只能由故意所构成。[29]污染环境罪并未规定具体的行为主观心态,而是对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应当为故意。
其次,过失犯罪在法条表述上明确将过失作为相关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并强调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一般认为过失犯罪中“法律有规定”在分则条文中表现为含有“过失”“事故”“玩忽职守”等词语。《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在罪状表述中删去了“事故”一词,并修改了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再以出现人本法益论所要求的人类生命健康、财产损失的结果作为构成污染环境罪的要素,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代之。从文理解释出发,这一转变使得过失说的文理解释依据丧失,若将污染环境罪理解为过失犯罪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从司法解释条文表述出发而得出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不排斥过失的混合说也站不住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处罚,司法解释并不是由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而是司法机关为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而进行的解释,其效力并不能等同于这里所说的“法律”。在过失说文理解释依据缺失的情况下,不能仅基于司法解释的条文,就得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的结论。
最后,在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文理解释时应当遵循法益保护目的。目的解释在诸多解释方法中占据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最终都要服从于目的解释,因此,与其说目的解释是一种解释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解释方向。[30]受环境风险的影响,对污染环境罪的事前预防逐渐得到重视,本罪所保护的法益逐渐向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靠拢。“由于刑事立法以保护法益为目标设定构成要件,所以,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意欲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制裁该犯罪的目的得以实现。”[31]正如上文所述,我国《刑法》对于污染环境罪的修改,使本罪的保护法益发生转变,不再局限于人本法益,而是将生态法益也纳入了保护范围。从我国《刑法》第338条的表述可以看出,随着法条和法益保护的变化,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结果已由致使重大人身、财产损害转变为了严重污染环境。只要行为人明知其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却仍然有意实施该行为,那么他对于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产生的主观心态为故意。[6]12
(三)故意说更契合污染环境罪所保护法益
污染环境罪的罪状由行为要素和结果要素构成,对于行为要素违法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理解其中“国家相关规定”的内涵。污染环境罪的“国家相关规定”一般指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这些相关法律,将保护和改善环境、保护公众健康作为立法目的,承认了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通过对环境的保护实现对人本法益的保护。这说明污染环境罪行为要素的违法性在于违反国家对有关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保护的规定。从文字表述上看,行为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是明知的。污染环境犯罪与生产经营活动联系紧密,生产经营活动要受到行政法规的限制,生产经营者对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行为所要遵守的规范和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是有明确认识的,这其中就包括了违反相关规定,随意处置污染物对于环境会造成的严重污染后果。[28]39行为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虽然不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产生,但其明知所处置的物质为有害物质,仍违法处置且不采取任何措施,放任自身行为对环境法益产生危害后果。因此,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当为故意。
《刑法修正案(八)》将“严重污染环境”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使得该罪的保护法益由人本法益逐渐向生态环境法益靠拢。刑法有关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导致保护法益的变化,动摇了将该条确定为过失犯罪的实质根据。[32]《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并删除了“污染环境所造成的重大事故”,若再将过失作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在过失污染环境但未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与我国严格治理环境污染的任务背道而驰。
五、结语
如何发挥刑法作为污染环境罪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是当今学界重要的课题。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形式的确定,对于污染环境行为的定罪、量刑都至为重要。从《刑法》及其后续修正、刑法学理全面考量,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更为妥当。故意说在确保了对生态环境法益严格保护的同时,又严守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注释:
① (2020)新0109刑初44号。
② (2020)晋1027刑初22号。
③ (2019)皖0222刑初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