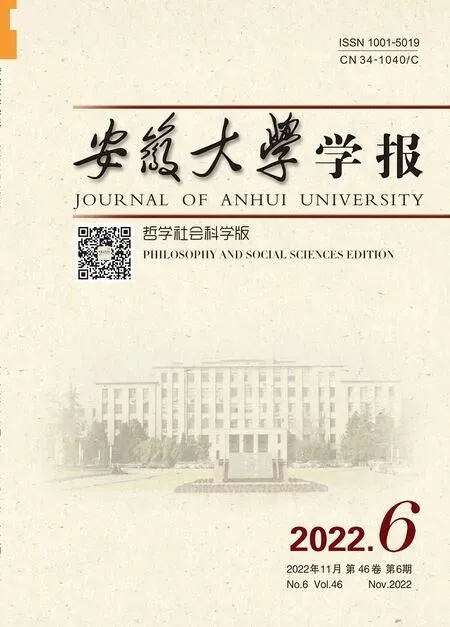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
——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王思豪
桐城方苞是一位理学家,以“学行继程、朱之后”(1)王兆符:《望溪文集序》,见《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06页。的羽翼圣道形象誉洽清代学坛。理学,广义言之,有北宋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朱熹闽学、陆王心学之分;狭义言之,则专指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呈相对之势。清初以来的学坛以尊崇程朱理学为一时风尚,诚如萧一山先生所谓“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2)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94~996页。。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活于康、雍、乾三朝的方苞,以程、朱理学的继承人为行身祈向,清儒唐鉴在《学案小识》中评方苞是“于学术则独守程、朱”(3)唐鉴:《学案小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4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刘声木称方苞“研究程朱学术,至为渊粹”(4)刘声木:《补遗序》,见《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4页。关于方苞尊崇程朱理学的探讨,学界成果甚多,如杨向奎《论方苞的经学与理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暴鸿昌《论方苞与康雍时期的理学》(《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王思豪《地理与学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辨》(《文学遗产》2020年第4期)等。。但以“程、朱之后”自任的望溪先生,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会游于“程、朱之外”,交结非程、朱的信徒,对当时学坛流行的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也发表过精到议论。这些“程、朱之外”的议论常被学界忽视,本文试加掘发,为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望溪学问”略作芹献。
一、友颜李:济于实用
方苞出生于南京六合的留稼村,父亲方仲舒(号逸巢)是明朝遗民,胸无畦畛。方苞自小随父亲和兄方舟(字百川)交游学习,在《与刘拙修书》中曾自述其为学次第云:“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及至京师,交言洁与吾兄,劝以讲索,始寓目焉。”(5)方苞:《方苞集》,第174~175页。这里的“楚、越遗民”主要是指黄冈杜苍略、杜茶村二兄弟及桐城钱澄之、方文等人。方苞在《杜苍略先生墓志铭》中回忆道:“初余大父与先生善,先君子嗣从游,苞与兄百川亦获侍焉。先生中岁道仆,遂跛,而好游,非雨雪常独行,徘徊墟莽间。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则追随,寻花莳,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视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系牵也。”(6)方苞:《方苞集》,第250页。又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追述钱澄之谓“先生形貌伟然,以经济自负,常思冒危难以立功名”,“先君子闲居,每好言诸前辈志节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见,惟先生及黄冈二杜公耳”(7)方苞:《方苞集》,第337页。。可以看出,二十岁前的方苞并不是程朱的尊信者,而是交游于“重文藻,喜事功”的遗民群体中,“目未尝涉宋儒书”。方苞经常追忆这段时光,他在《赵处士墓表》也说:“苞少从先君子后,见三楚、吴、越耆儒,多抱独以销其声。又其次乃好议论,著气节,为文章。尚矣哉,其风教之所积乎!”(8)方苞:《方苞集》,第374页。参见高日晖、路璐《〈后水浒传〉遗民心态与明清之际思想新变》(《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1期)相关论述。这些明遗民绝意仕进,寄情于山水诗文,对理学多持负面态度,视“宋儒为腐烂”。
清初同重“事功”的还有颜李学派,以颜元与其学生李塨为代表,标举“实学”,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程、朱理学相对。一般认为到康熙三十年(1691),二十四岁的方苞至京师、游太学,始“一意为经学”“始读宋儒书”(9)苏惇元:《望溪先生年谱》,见《方苞集》,第869页。。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结交长自己十岁的宛平王源。方苞在《宁晋公诗序》中说:“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与吾友昆绳日夕相过论文。”(10)方苞:《方苞集》,第617页。与王源订交,切磋文艺,引为知己。王源是何许人?方苞在《四君子传(并序)》中对王源有详细描述:“辛未游京师,得四人曰:宛平王昆绳,无锡刘言洁,青阳徐诒孙。……术业之近者,则昆绳、字绿、北固也。……王源字昆绳,世为直隶宛平人。父某,明锦衣卫指挥。明亡,流转江、淮,寓高邮。源少从其父,喜任侠言兵;少长,从宁都魏叔子学古文。性豪迈不可羁束,于并世人视之蔑如也,虽古人亦然。所心慕,独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于文章,自谓左丘明、太史公、韩退之外,无肯北面者。”(11)方苞:《方苞集》,第216~217页。又在《李刚主墓志铭》中追忆道:“吾友王源昆绳,恢奇人也。所慕惟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为迂阔。见刚主而大说,固与共师事习斋。”(12)方苞:《方苞集》,第247~249页。王源少喜任侠、言兵,性豪迈,心慕诸葛亮、王阳明,后见到李塨后,又拜入李塨门下,共习颜元学术。而方苞是将王源纳入“术业之近者”行列,并在康熙三十五年收王源之子王兆符为入门弟子。
更为有意思的是,康熙四十二年在京师王源寓所中,方苞见到了李塨。方苞在《李刚主墓志铭》中描述李塨谓:“李塨字刚主,直隶蠡县人。其父孝悫先生与博野颜习斋为执友,刚主自束发即从之游。习斋之学,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养亲,而以其余习六艺,讲世务,以备天下国家之用。以是为孔子之学,而自别于程、朱,其徒皆笃信之。”李塨是颜元的弟子,关于颜元的学问,方苞了然于心,认为可分为“本”和“余”两个部分:本是“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养亲”,要躬行实践;余是“习六艺,讲世务,以备天下国家之用”,讲求实用,都是出自孔子之学,但是“自别于程、朱”。又曾在《与李刚主书》中说:“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此如张、夏论交,曾、言议礼,各持所见,而不害其并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诋訾哉?”(13)方苞:《方苞集》,第140页。同样认为是颜元“自异于朱子”,在本质上其实与朱子之说无二,都是“孔子之徒”,何必要相互诋毁?
方苞对待颜李学派的态度首先是“理解之同情”。一方面理解颜元的学术亦是源于孔子之学,所倡仅为“自立”;一方面对颜元遭遇报以同情,颜元出生农家,为养祖母守丧差点丧命,仅以行医卖药、教授生徒为生,老来又无子。方苞同情颜元的遭际,将他与汤斌、李颙并称“志行越众”的“三君子”:“当吾之世,志行越众者三人:睢州汤潜庵之母,为流贼所膊;关西李中孚之父,糜烂于战场;博野颜习斋,父流亡,母改适,匍匐万里,始得父墓,见异母之妹,招魂而归。盖功利嗜欲薰铄流毒于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药恶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艰苦杰特之行。”(14)方苞:《书高密单生追述考妣遗事后》,《方苞集》,第131页。又在《刁赠君墓表》中谓:“余少闻燕南耆旧:一为博野颜习斋……习斋无子,其《论性》《论学》《论治》之说,赖其徒李塨、王源,发扬震动于时。……习斋遭人伦之变,其艰苦卓绝之行,实众人所难能。”(15)方苞:《方苞集》,第375~376页。所以,方苞不仅理解之同情颜元的学问和遭际,而且还与李塨、王源、刁再濂等习斋的信徒相互往来,期待一起“共明孔子之道”。
其次,方苞对待颜李学派实施的策略是“同化之改造”。方苞将颜元学术总结为“本”和“余”之论后,接着对李塨说:“程、朱之学,未尝不有事于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静以探其根源,则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颜元之论与程、朱之学都符合“道之法迹”:敬静——探其根源——知性命之理——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都要遵循这样一个次序。李塨听了方苞对颜元学问的理解后“色变,为默然者久之”。对待王源,方苞也实施“同化”之策略。王源一生慨不快意,幕僚生涯饱经风霜,二亲死后,丢妻弃子,漫游山川,不知所踪,突然有一天来到方苞家,对方苞说“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与刚主。而子笃信程、朱之学,恨终不能化子,为是以来”,准备来“化”方苞。方苞对曰:“子毋视程、朱为气息奄奄人!观朱子《上孝宗书》,虽晚明杨、左之直节无以过也。其备荒浙东,安抚荆湖,西汉赵、张之吏治无以过也。”颜李之学重实用,方苞也以朱子之学重事功来调和感化王源,并劝王源“归视妻孥,流行坎止,归洁其身而已矣”,最后王源“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然后方苞又将这番话向李塨说了一遍:“以语昆绳者语之,刚主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因举习斋《存治》《存学》二编未惬余心者告之。随更定,曰:‘吾师始教,即以改过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为口实哉!’”从方苞的叙述角度来看,他对李塨、王源的“同化之改造”策略是成功的。
当然,从李塨及其门徒的叙述视角来看,情况又不一样。李塨撰写《大学辨业》一书,主旨以《大学》之格物为《周礼》三物:六德、六行与六艺,认为朱熹的《格物补传》没有补传的必要。他拿着这本书给方苞看,其《与方灵皋书》记载:“忆癸未春,聚于王昆绳长安寓所,门下执拙著《大学辨业》相提诲,塨因谬陈格物之义,圣学之大旨意,门下称是,深相结而别。”(16)李塨:《恕谷后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34页。方苞面对李塨的新学说是“相提诲”“称是”。李塨门人冯辰、刘调赞看了方苞的《李刚主墓志铭》后,曾论辩道:“窃观灵皋与先生交至厚,而学术不相合,每相与辨学,先生侃侃正论,灵皋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暨先生没,为先生作墓志,于先生道德学业,一无序及,仅缕陈其与先生及昆绳先生相交始末,巧论谝谝,曰:‘以刚主之笃信师传,闻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没先生之学以自见者,此岂能有朋友相关之意乎。”(17)戴望:《颜氏学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3页。李塨门徒的这种回护其师之言,或有过之。方苞对李塨是称誉有加的,曾称其为“北方之贤者”,“及与久故,益信其为人”,充分信任这位挚友。但李塨的乡人却经常非议李塨:一是“是家贫,以适四方造请,干州郡而取饶焉”;二是“妻无子,乃别居”;三是“仓廪充溢,而食必粢粝,子妇执苦身之役”;四是“亲之丧,赴吊者渴饥,皆之逆旅而求宿焉”,因此,认定李塨达不到“贤者”的标准。针对这四点非议,方苞一一为李塨辩护,针对第一条,方苞辩护:“吾闻刚主躬耕,善稼穑,虽俭岁,必有收;未闻以干请也。士友所共闻知者:明、索二势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抚安溪李公称其学行于天子,不往见。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请钓锱铢之利乎?”针对第三条,方苞辩护:“至于食必粢粝,妻妾操作,而子妇从之,则李氏之家法也。”针对第四条,方苞辩护:“亲宾能远赴其丧,何惜旅宿?刚主居湫隘,家无僮婢,创巨痛甚,而责以供具,不亦难乎?”关于第二条“与妻别居”的问题,方苞也不知具体缘由,所以亲自叩问过李塨,李塨答复说“是多言不顺,吾常隐焉。有女早寡,而主张更嫁。吾不忍见,故使别居,既乃合并,而阴绝焉”,根本不是无子的问题,“绝之者何?生异寝,死异穴也。合并者何?生同宫而衣食之,死则葬埋之也”。方苞认为李塨的做法是“此古应出而不行之礼”,根本不可以以这些名目来指责李塨,李塨依然是“贤者”(18)方苞:《方苞集》,第519~520页。。
李塨将自己的家事倾心诉诸方苞,方苞也曾将自己的一些个人情愫疑问告诉过李塨,听取李塨的建议。李塨《甲午如京记事》(19)李塨:《恕谷后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29页。曾记载自己与方苞夜谈“论礼”,方苞说:“苞居先兄丧,逾九月,至西湖,暮遇美姝,动念。先君逝,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期后欲心时发,及被逮,则此心顿息矣。何予之亲父兄,不如遭患难也?禽兽哉!”父兄去世的悲恸,都压抑不住自己“欲心”,而遭遇牢狱之祸,便“此心顿息”,方苞责备自己这还是人吗?李塨劝慰道:“自讼甚善,特是三年之丧,天动地岌,虽属大变,乃人所共有。哀一杀,身一惰,则杂念起。故《鲁论》曰‘丧事不敢不勉’,《仪礼》曰‘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今举族北首,老母流离,身陪西市,几致覆宗,其与居丧常变又殊,故情亦殊也。”李塨将方苞的遭遇分为“常变”与“殊变”,常变是“人所共有”,自然杂念会起,这要以“礼”自省;“几致覆宗”的遭遇是殊变,情当然也“殊”。方苞接着又问:“心动矣,性忍矣,遇事不能咄嗟立办,能何由增?王昆绳尝诲我曰:‘不能办事,幼习程、朱之过也。’岂迂腐非变故所能移与?”也曾怀疑过程、朱之学。又问:“老母日迫罪戾,滋加忧之,奈何?”面对方苞“不能办事”和祸上“加忧”的困惑,李塨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先生请以敬,勿以忧。舜遭人伦极变,而夔夔齐栗,惟将以敬,敬则心有主,敬则气不耗。不能可益,患难可平,祸外加忧,何解于祸”,能否以敬远忧,以敬平难,以敬解祸,这是“圣贤常人之分”,李塨亦在勉励方苞修成“圣贤”。
方苞与李塨、王源虽在学说上有争论,但三人交情之深且笃,在患难中的相互劝慰和释责,恐非李塨门徒所可想见,所以他们单方面的指责也会流于片面。看三人之间的互动:王源评方苞谓“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渊理路”(20)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对方苞学问推崇备至;王源殁后,方苞深情追忆与王源“我行我游,子先我路。我耕我耘,子偕我作。我文我史,子订我误”(21)方苞:《方苞集》,第470页。的美好时光。李塨《与恽皋闻书》曰“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22)方苞:《方苞集》,第254~255页。,视方苞为一生挚友,二人交往三十余年,易子而教,换宅而居,皆为对方母亲作寿序(23)任雪山:《李塨与方苞之交游及其学术意义》,《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乾隆十二年(1747),80岁的方苞作《与黄培山书》说:“告归五年,求一好经书识名义者,与之共学,竟未见其人……愚为先忠烈断事公建专祠,左厢有小屋三间,将以‘敦崇’名堂……亡友四人,曰刘捷古堂、张自超彝叹、王源昆绳、李塨刚主,为‘敦崇四友’。”(24)方苞:《方望溪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65页。方苞友李塨、王源,友颜李学派,这已经不是一般形式意义的友,而是“共学”之友,是以“敦崇”的态度友之。
所以,李塨认为方苞曾接受了颜李的部分学说,这是有可能的。在与李塨多轮的“格物”论辩后,方苞也察觉到当时程、朱之学流于空虚的境况,主张“济于实用”之学。他曾在《传信录序》指出:“古之所谓学者,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25)方苞:《方苞集》,第603页。观方苞集中的诸如《与安徽李方伯书》《与安溪李相国书》《与顾用方论治浑河事宜书》,以及其关于台湾建城、荒政、人才、察吏、酒禁等的奏折,都充满了经世济民之思想,所以民国学者郭声宏曾撰写《方苞之经济思想》长文,谓方苞“于经世济民之学,未尝不覃心精究。读《方望溪先生全集》论农田、水利、屯田、荒政、财政诸文,煌煌巨篇,俱关国计民瘼,惓惓于斯世斯民,其学问之阔大,议论之精密,在清代文人中鲜有及之者”(26)参见郭声宏《方苞之经济思想》(《银行周报》1944年第28卷第13~14期)、《方苞之经济思想续》(《银行周报》1944年第28卷第15~16期)二文。,这种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与方苞争辩一生的李塨,曾称誉方苞:“门下笃内行而又高望远志,讲求经世济民之猷,沉酣宋、明儒说,文笔衣被海内,而于经、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媕娿侯门为名誉,此岂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颂祷,谓树赤帜以张圣道,必是人也。”(27)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又在《复恽皋闻书》中说方苞:“即如方子灵皋,文行踔越,非志温饱者,且于塨敬爱特甚,知颜先生之学亦不为不深,然且依违曰‘但伸己说,不必辨程、朱’。揆其意,似谚所谓受恩深处即为家者,则下此可知矣。”(28)李塨:《恕谷后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49页。在李塨看来,方苞的思想是开放性的,是“知颜先生之学亦不为不深”的,他在讨论学说时,亦可以做到“不必辨程、朱”。在“程、朱之外”,方苞友李塨、王源,汲取颜李学派的“实学”的精华。马积高先生在考察与回顾清代理学演变的历史后,曾总结道“清代的理学乃是一种向实用转化的理学”(29)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在这种意义上来看,方苞可谓是这种“实用转化”的早期实践者之一。
二、不拒王:“毋标讲学宗指”
上文曾引述方苞《传信录序》语“古之所谓学者,将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于用”,说明方苞对待颜李学派是友好同化的策略,取其“济于实用”之学为己所用,这是学术的终极目的;而学术的起点是“明诸心”,以明心来“尽在物之理”。方苞在论理学时,尤爱引用《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他在《与李刚主书》中称颜元的学术“自异于朱子”的地方,“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接下来谓:“《记》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30)方苞:《方苞集》,第140页。方苞的逻辑是颜元学术本质上与程、朱是一致的,都是认可“心与天地相似”学说的代表。
方苞在讨论阳明“心学”时,也引用了《礼记》中的这句话。他在《孙徵君年谱序》中说:
《记》曰:“人者,天地之心。”惟圣贤足以当之;降此则谨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几耳。彼自有生以至于死,屋漏之中,终食之顷,懔懔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无以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艰,较之奋死于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为心,而藉之纪纲乎人道者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将亡,而不可强以仕,此固其所以为明且哲也。……今谱厥始终,其行事或近于侠烈,而治身与心则粹乎一准于先儒。(31)方苞:《方苞集》,第88页。
孙徵君,即孙奇逢,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清史稿·儒林传》载“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32)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0页。,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方苞也写有《孙徵君传》谓:“孙奇逢字启泰,号锺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奇逢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33)方苞:《方苞集》,第213~214页。方苞也是认可孙奇逢服膺“心学”,最起码早、中年是如此。方苞在《孙徵君年谱序》中讨论“心”学,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圣、贤、儒的问题。圣与贤是“人者,天地之心”宗旨的代表,而儒者是“谨守而不失”,一个人从生到死,终其一生担惊受怕的是“无以为人”,所以“操心”“用力”维护“人道”只是一种手段,最终旨归在于“天地所寄以为心”。这也是方苞在《学案序》中阐明王学与程、朱之别时所重点强调的内容:“自阳明王氏出,天下聪明秀杰之士,无虑皆弃程、朱之说而从之。盖苦其内之严且密,而乐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详,而乐王氏之简也。凡世所称奇节伟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奋发,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于死,无一息不依乎天理而无或少便其私,非圣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为宗。”(34)方苞:《方苞集》,第89页。阳明心学之所以盛行一时,在方苞看来,主要在于其“简”与“疏”,不像程、朱之说内“严密”而外“拘详”。简、疏之学,则易于执行,人们也乐于执行,亦容易成就奇节伟行,建立非常之功;但“心”要“依乎天理”,这才是“圣”之所为,也是程、朱学说的宗旨。方苞在《周官辨序》中称:“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于伏藏于事物,则有圣人之所知,而贤者弗能见者矣。”(35)方苞:《方苞集》,第599页。“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这是方苞对“人者,天地之心”的最恰当理解,“理”之存在于人的身心是一致的,而“伏藏于事物”的理,只有圣人能体悟到,贤者都不可及。
第二个是“治身与心”的问题。孙奇逢既有治身“明且哲”的一面,也有行事“或近于侠烈”的一面,这是“一准于先儒”。方苞在给直隶安州人陈鹤龄作墓志铭时说“君姓陈氏,讳鹤龄,字鸣九,直隶安州人。……君既冠,亦好阳明氏及其乡鹿忠节公论学之书而践行之”,在方苞看来,陈鹤龄年青时就喜好王阳明“心学”和鹿善继的学说,他的学术之道首先是在学理,然后践行之,接着又说“余闻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得身”实践是古之学术之道,而“阳明氏为世诟病久矣!然北方之学者如忠节、徵君,皆以阳明氏为宗。其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时从之游者,多重质行,立名义,当官则守节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观之,学者苟能以阳明氏之说治其身,虽程、朱复起,必引而进之以为吾徒。若嚾嚾焉按饰程、朱之言而不反诸身,程、朱其与之乎?然则尚君之行者,盖不必以其学为疑也。”(36)方苞:《广文陈君墓志铭》,《方苞集》,第305页。“以阳明氏为宗”的鹿善继、孙奇逢之所以成功,即在于立身“各有本末”,以身示范,而从游者又重质行,立名义,正直不阿。在方苞看来,这样的人,即使是服膺阳明“心学”,也可以纳入程、朱的门墙,不会被排斥;相反,如果口口声声说遵从程、朱之言,而“得身”不正,这样的人也不会成为真正的程、朱门徒。评价一个人,不在于他服膺谁的学说,而是要看他如何“行”、如何做的。在这一点上,程、朱与阳明氏相通。
因此,方苞依据圣、贤、儒和“治身与心”两个标准来衡人量才。河北定兴鹿氏家学宗主陆、王,至鹿善继以祖父鹿久徵为师,深受家学的熏炙,亦宗陆、王,而对阳明“心学”尤为心契,孙奇逢谓鹿善继“少以祖父为师,小章句,薄温饱,读王文成《传习录》而契之,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37)孙奇逢:《夏峰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1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陈亦谓鹿善继“取《传习录》寝食其中,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而一切著落,皆身实践之”(38)陈编:《鹿忠节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善继以忠正节义、躬行任事闻名,守定兴城死节后,追赠大理寺卿,谥“忠节”,并敕建祠祭奉。方苞作有《鹿忠节公祠堂记》谓“吾闻忠节公之少也,即以圣贤为必可企,而所从入则自阳明氏。观其佐孙高阳及急杨、左诸公之难,其于阳明氏之志节事功,信可无愧矣。终则致命遂志,成孝与忠,虽程、朱处此,亦无以易公之义也。用此知学者果以学之讲,为自事其身心,即由阳明氏以入,不害为圣贤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绪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则背之,其大败程、朱之学,视相诋訾者而有甚也”(39)方苞:《方苞集》,第412~413页。,认为鹿善继以“圣贤”为自己的立身祈向,进入王阳明信徒行列,他的节义之举无愧于阳明氏所提倡的志节事功宗旨,最终以死明志,成就忠孝之义,也是符合程、朱之道的。鹿善继“自事其身心”虽是从阳明之学入,但最终归途仍可列为程、朱圣贤的门徒,鹿善继“遂志”也!
方苞以此标准衡人,在信奉阳明之学的人中,最推崇鹿善继、孙徵君和汤斌。他在《重建阳明祠堂记》开篇就说:“自余有闻见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兴鹿太常,容城孙徵君,睢州汤文正,其学皆以阳明王氏为宗。鄙儒肤学,或剿程、朱之绪言,漫诋阳明以钓声名而逐势利。故余于平生共学之友,穷在下者,则要以默识躬行;达而有特操者,则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标讲学宗指。”(40)方苞:《方苞集》,第411~412页。方苞认为这三人是“真儒”,而那些靠剿袭程、朱之说诋毁阳明之学,以此来沽名钓誉的人,这些属于“鄙儒”。方苞选择“共学”之人,“穷在下者”要“默识躬行”,飞黄腾达者要“有特操”,清正廉明,而并不是看他讲习哪一家的学说宗旨。方苞写这篇《重建阳明祠堂记》有三个机缘:一是在金陵的西华门外曾有一座阳明书院,年久失修,亟需修缮;二是乾隆十一年,安州陈德荣从贵州调任安徽布政使,拜访方苞,陈德荣是崇尚阳明“心学”的陈鹤龄之子,陈鹤龄妻鹿氏,是鹿善继的曾孙女,方苞曾给陈鹤龄写过墓志铭;三是陈德荣与方苞都是“以睢州志事相勖者”,“睢州”指的是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人,曾师从孙奇逢,为官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谥号“文正”,方苞曾言“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41)方苞:《方苞集》,第681页。方苞《汤司空逸事》:“国朝语名臣,必首睢州汤公。公自翰林出为监司,年四十从孙徵君讲学夏峰,质行著河、漳。”,并奏请以汤斌从祀孔庙。基于以上机缘,遂兴复阳明祠堂,也因此方苞在这篇文章中对阳明之学探讨尤为深刻:
嗟乎!贸儒耳食,亦知阳明氏揭良知以为教之本指乎?有明开国以来,淳朴之士风,至天顺之初而一变。盖由三杨忠衰于爵禄,以致天子之操柄,阁部之事权,阴为王振、汪直辈所夺;而王文、万安首附中官,窃据政府,忠良斥,廷杖开。士大夫之务进取者,渐失其羞恶是非之本心,而轻自陷于不仁不义。阳明氏目击而心伤,以为人苟失其本心,则聪明入于机变,学问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远于禽兽。至天启中,魏党肆毒,欲尽善人之类。太常、徵君目击而心伤,且身急杨、左之难,故于阳明之说直指人心者,重有感发,而欲与学者共明之。然则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阳明之节义勋猷、忠节、徵君、文正之志事为何如(42)按:此处或应断为“思阳明之节义勋猷,忠节、徵君、文正志事为何如”。,而己之日有孜孜者为何事,则有内愧而寝食无以自安者矣!又思阳明之门如龙溪、心斋,有过言畸行,而未闻其变诈以趋权势也。再传以后,或流于禅寂,而未闻其贪鄙以毁廉隅也。若口诵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谓失其本心,与穿窬为类者。阳明氏之徒且羞与为伍。(43)方苞:《方苞集》,第411~412页。
首先,方苞看待阳明心学兴起之缘由的视野背景非常开阔,他从有明一代之风教入手,这和他写作《修复双峰书院记》的出发点一致。双峰书院曾是孙奇逢的故宅,年久失修,后来孙奇逢曾孙孙用桢加以修复,请方苞作记,方苞也是“观明至熹宗时,国将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方逆奄魏忠贤之炽也,杨、左诸贤,首罹其锋。前者糜烂,而后者踵至焉。杨、左之难,先生与其友出万死以赴之。……夫晚明之事,犹不足异也。当靖难兵起,国乃新造耳。而一时朝士及闾阎之布衣,舍生取义、与日月争光者,不可胜数也。……明之兴也,高皇帝之驭吏也严,而待士也忠。……故能以数年之间,肇修人纪,而使之勃兴于礼义如此”(44)方苞:《方苞集》,第414页。,从熹宗、晚明、靖难到高皇帝,大致以倒叙的形式阐述明代教化之张弛。而《重建阳明祠堂记》正好相反,采用正叙的方式,从有明开国,到天顺之初、天启中,直至晚明四个阶段。
其次,在方苞看来,“心学”发展历程大致是:从开国到天顺初,大致也就是朱元璋、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统治时期,士风淳朴,文士多有节义;自天顺初以后,“三杨内阁”主理朝政,后又王振等宦官专权,又经历夺门之变等事件,士大夫“渐失其羞恶是非之本心”,所以阳明氏“目击而心伤”,提倡“致良知”之学;从熹宗朝天启中以后,阉党肆毒,鹿善继、孙奇逢亦是“目击而心伤”,感发阳明学说“直指人心者”,发扬光大,其中能够登阳明之堂,“思阳明之节义勋猷”的是鹿善继、孙奇逢、汤斌三人,而入阳明之门但有“过言畸行”的则是王畿(号龙溪)、王艮(号心斋)二人;再传以后,阳明心学就“流于禅寂”了。总体来说,方苞认为服膺阳明心学的人,好的方面是有节操,能舍生取义;差的方面也不过言行奇怪,或者分流禅学,但都不至于“变诈以趋权势”,或者“贪鄙以毁廉隅”,倒是那些日日口诵程、朱而又“私取所求”人,才真正是“失其本心”的穿窬之徒。方苞再一次阐明他所交往的对象“毋标讲学宗指”。
那么方苞如何看待阳明心学与程、朱之学的争论呢?他在《鹿忠节公祠堂记》中进一步申论道:
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昔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忧,盖匪是则无以自治其身心,而迁夺于外物。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途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方其志节事功,赫然震动乎宇宙,一时急名誉者多依托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师承。迨其身既殁,世既远,则依托以为名者无所取之矣。凡读其书,慕其志节事功而兴起者,乃病俗学之陋,而诚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类于恒人。(45)方苞:《方苞集》,第412~413页。
与之前分四段概述阳明心学发展历程不同,这里方苞言简意赅地阐述阳明之学兴起何其勃兴,而怪乱之象又何其之多:阳明之学简易直接,直指人心,适合普通民众掌握和执行,而明代的程、朱之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泛道德化、机械化和教条化,所以阳明之学甫一开始就几乎夺了程朱之学的统绪。但也正因为如此,阳明之学发展到后来,出现一批异端思想家如何心隐、李贽等,诚如刘宗周弟子黄宗羲所说:“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46)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03页。如何来平议程、朱与阳明之争?方苞认为还是要回归孔子之言,《论语》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讲学是程、朱与阳明学术传播共同的途径,只不过阳明之学重在“自治其身心,而程、朱侧重于“迁夺于外物”,二者之别在于途径不同,但“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本原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仅如此,方苞对王阳明推崇甚高,认为“其志节事功,赫然震动乎宇宙,”如果是“急名誉者”学习阳明之学用以自炫,只会连累其师,而“无所取之”;如果潜心认真读阳明之书,“慕其志节事功而兴起者”“诚以治其身心者”,必然会“卓然不类于恒人”。
总之,方苞尊程、朱之学,但并不拒王,也并非诋毁真正阳明之学。方苞在《与李刚主书》中虽有说“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以阳明为例来告诫李塨,但究其话语情境而言,这只是书信中劝谏朋友的一种方式,未必意在诋毁阳明。相反,他对阳明心学的认识是深刻且独到的,对阳明本人也是推崇备至,对鹿善继、孙奇逢、汤斌、陈鹤龄等阳明后学亦是称誉有加,并或为其修祠作记,或为其撰铭纪传,或为其奏请从祀孔庙,不遗余力。方苞的理学思想是开放而非完全保守的,他所秉持的“共学之友”标准不是某人服膺某一家的学说,“毋标讲学宗指”,而是看其躬身实践了什么,节义事功如何,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时至清初,部分学者合程朱陆王为一,但所主不同,或主朱,或主王,望溪盖主朱者,亦吸取陆王。”(47)杨向奎:《论方苞的经学与理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马积高先生认为桐城派的理学“有某种适时调整的特色”,“有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48)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在这种意义上来看,方苞可谓是“适时调整”的先驱之一。
三、“彼家有人”:佛、老可入儒行
方苞的学术取向是友颜李、不拒王。他在《与李刚主书》中说:“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又在《鹿忠节公祠堂记》中说:“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途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在方苞的思想体系中,儒学有“大原”与“小径”之别,无论颜李、还是阳明,都仍不脱儒学“大原”。所以钱基博先生总结方苞学问谓:“观其论学,于明之王守仁,平时之颜元、李塨,皆思有以矫其枉而折衷于程朱。”(49)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954页。但观方苞论学,他对颜元后学李塨、王源和阳明后学鹿善继、孙奇逢、汤斌等采取的都是“共友”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矫其枉而折衷于程朱”;相反,他经常借认真研习颜李、阳明学说的正直节义之士,来讽刺、批判口口声声程、朱而其实却失去本心的假道学之人。方苞对颜李、阳明的态度更倾向于平等“友之”而“共明孔子之道”的意味,那么,他对佛、老思想是如何看待的呢?
首先,方苞将佛、老明确排除在儒家之外。新山东巡抚李觉菴到任,方苞就写信告诫他:“适闻足下改官巡抚山东。……又闻齐、鲁间,盛兴三教祠,虽阙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圣先师塑像,瘗之学宫。其祠仍听合祀释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为迂阔不急之务也,而教化之兴,实由于此。”(50)方苞:《方苞集》,第171~172页。山东民间有将孔子与释迦牟尼、老子共祀一祠的风尚,而且还很盛行,连孔子故里都如此。方苞以为不可,儒与佛道不同,儒家圣人孔子的塑像宜立于学宫,属于官方正统之学,佛、道属于民间学术,可在民间立“教祠”。方苞视佛、道为“孔子之道”之外的学说。
但是,这并不意味方苞排斥佛、道。翻检方苞的诗文作品,写到佛寺、道观的有《隐玉斋》(51)任雪山:《方苞集外诗文六篇考释》,《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年第5期。《游潭柘记》《题天姥寺壁》《重建润州鹤林寺记》《重修清凉寺记》《良乡县冈洼村新建通济桥碑记》《再至浮山记》《重修葛洪庵记》《苍溪镇重修三元观记》等;写到的寺庙、道观有泰州如皋中禅寺、北京潭柘寺、北京寿因寺、浙东天姥寺、镇江鹤林寺、南京清凉寺、北京静默寺、浮山华严寺、北京葛洪庵、南京高淳三元观等;而其所识闻和交往的僧人有浮屠髻珠、释兰谷、沛天上人、彻机上人、黄山老僧中州、浮山宗六上人、扬州学佛者定悟、淮安学佛者古翁等。
其次,方苞选择交往的佛教人士的标准是:“阴辨儒、释而择其可交者”(52)方苞:《重修清凉寺记》,《方苞集》,第433页。。他曾给浮屠髻珠的小像写过一篇赞语,曰:“俗之游而众之嘻,其心则畸;佛之徒而儒之师,其行不疑;吾不见其髠而缁。”(53)方苞:《浮屠髻珠小像赞》,《方苞集》,第783页。这篇赞语不太好理解。在《重修清凉寺记》文中,方苞记其兄方舟语曰:“自明中叶,儒者多潜遁于释,而释者又为和通之说以就之,于是儒释之道混然;儒而遁于释者,多猖狂妄行,释而慕乎儒者,多温雅可近。”所以,方苞所谓“俗之游而众之嘻,其心则畸”,就是俗儒潜遁在佛教中的人,多猖狂妄行;“佛之徒而儒之师,其行不疑”,就是“释而慕乎儒者”,行为多温雅可近。“髠而缁”之语出自韩愈与柳宗元的一场争执,柳宗元《送僧浩初序》:“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髠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韩愈反佛辟佛,多次责怪柳宗元喜好浮图之言,常与浮图交游,而柳宗元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54)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3页。,应该统合儒释,融会贯通。因此,“吾不见其髠而缁”,在方苞眼里,佛家僧人如具有儒行,也可以交往。
于是,在方苞笔下,浮屠髻珠曾在自己同年友王畴五卧疾时,多年视药食饮甚勤,西山诸寺多请为大师,都不忍离去。方苞“感于髻珠所以事畴五之义”(55)方苞:《重修葛洪庵记》,《方望溪遗集》,第114页。,认为髻珠属于“佛之徒而儒之师”之列,这当也是方苞给浮屠髻珠小像写赞语的原因。释兰谷是“九岁授以《学》《庸》《语》《孟》,十三授《易》及《太极图》……其父母未殁时,游必有方。闻丧归殡葬,即庐墓侧……入其室,少长三数人,坐立应对进退皆比于礼……观其志行术业气象,则儒衣冠者多愧矣!”(56)方苞:《释兰谷传》,《方苞集》,第233~234页。自小研习儒家经典,孝敬父母,守礼重行,虽是僧人,胜似儒者。沛天上人是“每人事歇息,辄邀余坐庭阶,玩景光,间及民生利病、并世人物。其胸中炯然,语皆有称量”,方苞感叹他有士大夫的德性与气量,“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养焉。居母与兄之丧,一遵儒书。服既终,颜色戚容尚有异于众人。丧其本师,诚敬亦如之。好士友,羁旅者投之如归,久而不怠”,至孝至悌,尊师重友,“观上人之笃于人纪,不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如此,皆先圣先贤所谆复而有望于后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数数然也”,沛天上人的德性行为,符合儒家圣贤的教导,“朱子尝忧吾道之衰,以为‘性质刚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尘垢而藏身于二氏’。斯言也,盖信而有征矣!故专录其儒行,而推阐佛说以张其师教者,概不著于篇”。方苞笔下的佛僧形象多有儒家士风志行,这也是其给僧人作传、寺庙写记的初衷与原则,也是其援佛入儒的旨归所在。
不过,方苞的文章并非完全不推阐佛说。《沛天上人传》中曾写道:“雍正某年,内府有疑狱,大小司寇会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狱之说,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间耳!’中有以深刻为能者,面赤而色愠。曰:‘方外人何难为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视禄位少轻,则无难矣。’众皆默然。”“一念”即是佛家学说,佛家修行提倡“一念相应”,“一念不生”,空间、时间都产生于“一念”心中。“忍恕”也是佛教“忏摩(梵语Ksamayati)”的译辞。扬州学佛者定悟记录整理其师济生的言语成《济生语录》一书,请方苞作序,方苞有一段对禅宗的论述:
自禅宗既开,凡学佛者所谓守戒律,诵经号,一切皆为末迹,其心之精微非言语文字所能传也。而自唐以后,以禅名于世者,其弟子莫不记其师之所受于老宿,所宣于徒众,以为语录。凡据名山古寺、通都巨刹称大师者,人各一编,不可选记。以其理超于形声法象之外,故其相问相答,可意会而无所稽循,不可究诘,则窃其近似以欺愚俗者亦不少矣。我皇上圣明天纵,灼见性道大原,以佛之理清净可以养心,慈仁可以利物,万几之暇,时用息游,探厥清源,凡自古名僧语录之传于后者,其诚妄浅深、出入离合,毫厘分寸不能逃于圣鉴。余以朝夕承事,得奉训诲,以自治其心性,警觉提撕之下,苦思力索,久之,亦微有见焉。间与佛子语,其胸中实有知见与窃其近似者,亦略能辨之。(57)方苞:《济生语录序》,《方望溪遗集》,第14~15页。
第一,方苞谈自己对禅宗的看法,认为禅宗重“禅定”而不重守戒、诵经,重心传而不重言语。第二,方苞明了禅宗的发展历程,认为自唐以后,禅宗开始重“语录”。第三,方苞认识到禅理的特点是玄妙,“超于形声法象之外”,“意会而无所稽循”。第四,方苞修习禅理是因为皇帝重视禅宗(58)按:疑为雍正皇帝,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登基后,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阅读《指月录》《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并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因日夕侍奉皇帝,亲得皇帝训诲,以“自治其心性”,苦思力索禅理很久,自称“微有见”,且达到能辨别“胸中实有知见”和“窃其近似者”的地步。
当然,方苞交僧学佛,除了受到皇帝影响外,还有个人生活境遇方面的原因。他在《重建润州鹤林寺记》一文中写道:“余少游名山入古寺,见佛相,肃拜之礼亦不敢施,而羁穷远游及难后多与学佛者往还,乃悟退之之亲大颠,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于秘演、惟俨辈,良有以也。”方苞与学佛者交往,主要是在羁旅行役和“《南山集》案”遭难后,而且对韩愈被贬潮州结交大颠和尚事、欧阳修在曼卿死后结交秘演与惟俨和尚事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方苞与浮山宗六上人交游即感悟良多,康熙四十八年,方苞归桐城省墓,至浮山,与宗六上人游:“每天气澄清,步山下,岩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华严寺门庑,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释,莫可名状。将行,宗六谓余曰:‘兹山之胜,吾身所历,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时,士女杂至,吾常闭特室,外键以避之。夫山而名,尚为游者所败坏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祸作,余牵连被逮。窃自恨曰:‘是宗六所谓也。’”方苞陶醉于浮山秀美的风光,“心融神释”,而宗六上人的忧郁之言,也正应验了自己后来的“《南山集》案”祸事。雍正二年八月,归桐城,又过浮山,“既与宗六别,忽忆其前者之言为不必然。盖路远处幽,而游者无所取资,则其迹自希,不系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粤间,与永、柳之山比胜而人莫知者众矣;惟子厚所经,则游者亦浮慕焉。今白云之游者,特不若浮渡之杂然耳;既为众所指目,徒以路远处幽,无所取资而幸至者之希,则曷若一无闻焉者,为能常保其清淑之气,而无游者猝至之患哉!然则宗六之言盖终无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游也。无可记者,而斯言之义则不可没,故总前后情事而并识之。”(59)方苞:《再至浮山记》,《方苞集》,第423~424页。四十年后,方苞再至浮山,经历“《南山集》”祸事,对宗六上人之言,有了更深的体悟。
方苞在处境困顿以求心灵安顿时,不仅求诸佛教,更多情况下是从体悟老、庄之学中汲取力量。康熙三十二年,方苞二十六岁,第二次应顺天乡试,不售,写信给好友王源:“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饥驱宣、歙间,入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泠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60)方苞:《与王昆绳书》,《方苞集》,第666~667页。感慨自己为养家糊口,飘零他乡,见宣城、歙县一带风光悦目,生出庄子、渊明的“逍遥纵脱”之思。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南山集》案”难后的方苞,惊魂方定,友人约谋为潭柘之游,潭柘寺风景宜人:
观潭柘好山好水,感觉自己与此地山水融为一体,有庄子“与天地精神往来”之境界。方苞深于庄学研究,据刘声木记载,方苞曾撰有“《评点庄子》囗囗卷”(62)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第397页。,这一段亦是方苞对庄子“无我”“物化”观念的探讨。至乾隆八年,方苞寻医浙东,曾作天姥、雁荡之游。在天姥山,见到山下有一古树,遭雷破而中分,木身被烧者十之七,而旁边依皮而存者却枝叶蔚然,时年76岁的方苞,经历了宦海的沉沉浮浮,不由感慨道:“物之生也,若骤若驰,吉凶倚伏,颠倒大化中。当其时不自觉也,惟达者乃能见微而审所处。假而兹树非残于雷火,必终归于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远而弥存也。”(63)方苞:《题天姥寺壁》,《方苞集》,第427页。方苞有感于老子“祸福相依”“相反相成”思想,想到此树因雷火而免于薪火,是天命让其虽残于雷火,但全其生命,这犹如自己经历“《南山集》案”后的生命重生。
方苞自青年至老年,都在不断体悟着老、庄的思想。不过其对道教似乎很少关注,只知曾给自己的挚友张自超主持募修的三元观作过记。三元观是南京高淳地区的一座道教圣地,但年久失修,张自超说:“古者射乡、酺蜡、读法宪禁、计耦兴锄各有地,春秋祈报各有典祀,而后世并无之。此地为宣、歙群流入吴之要会,自开永丰、太平诸圩,民惧水败,悫而听于神。凡岁时修筑分植属役,旱潦启闭水门,皆合众成言于此,则过而存之,不亦可乎?……若因农祀之节会,寓以古法,则礼俗可兴。”可惜待三元观修好,张自超已经去世,方苞感叹“无缘一至其地,究观其学者耕者之礼俗也”(64)方苞:《苍溪镇重修三元观记》,《方苞集》,第424~425页。,可见张自超与方苞修观、记观的目的都是恢复古礼,也是在援道入儒。方苞一生交游,惟重“敦崇四友”:刘捷、张自超、王源、李塨。前揭张自超、王源、李塨对方苞的思想都有很深的影响,刘捷亦然,他曾对方苞说:“佛之理吾不信,而窃喜其教绝婚宦,公货财,布衣疏食,随地可安。士之萧散孤介而不欲违其本心者,往往匿迹于其中。故朱子亦尝谓‘彼家有人’。”(65)方苞:《重建润州鹤林寺记》,《方苞集》,第432~433页。后来,方苞在评价沛天上人兴复寿因寺、竭资修建通济桥以及孝母悌兄等节义行为时,也引用了这个观点:“朱子尝病吾道之衰,而叹佛之徒为有人。其有以也夫!”(66)方苞:《良乡县冈洼村新建通济桥碑记》,《方苞集》,第434~435页。佛、老二家亦有人,可以滋补于儒,可以济佛、老而入儒。
四、结 论
首先,方苞卫道,但经过细读他的论颜李学派、心学以及佛道的文献,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并不是如以往所描述得那般保守。尽管他也曾说过一些偏执之辞,但若还原到彼时的语境中去,其实他并不是与李塨、王源、阳明心学信奉者,以及佛僧、道士水火不相容,相反,他与这些人都是彼此相互倾慕的好朋友。他敦崇颜李,期待一起“共明孔子之道”;共友阳明,“毋标讲学宗指”,并不服膺某一家学说;不排斥佛、道,并赞扬其“彼家有人”,以为佛、老可入儒行。总之,方苞秉持着一种开放而包容的态度,维护着程、朱理学的地位。
其次,方苞的经学理路“六通四辟”。韩菼曾评云:“以一心贯穿数千年古书,六通四辟,使程、朱并世得斯人往复议论,则诸经之覆,所发必增倍矣。”(67)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亦可参吕靖波《风气·史实·悲剧性》(《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1期)相关论述。假如让方苞与“程、朱并世”,中国经学理论会更加丰富,这里视方苞已不是“程、朱之后”的人物,而是可以与“程、朱并世”之人。胡宗绪更推崇方苞是“余常谓方子乃七百年一见之人,知言者当不以为过其实也”(68)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5页。,将方苞视作超出理学宋五子、古文宋六家之上,且直接韩愈道统之人,成程、朱之前的人物。
第三,方苞理学地位,究竟是“程、朱之后”,还是“程、朱并世”,抑或“程、朱之前”?韩梦周之说或更为公允:“论文于程、朱未出之前,与论文于程、朱既出之后,其说不同:程、朱以前,圣道否晦,虽有一二豪杰之士窥见大体,未能使此理灿然较著于世……自程、朱出,而圣贤之道复明,学者舍是无以为学,立言者舍是何以言哉?……望溪先生之文,体正而法严;其于道也,一以程、朱为归,皆卓然有补于道教,可传世而不朽;其于所易忽者亦不苟,盖可以识先生之所学矣。”(69)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13册,第197页。韩梦周平议诸说,在肯定方苞“一以程、朱为归”外,“于所易忽者”也加以留心,这才是真正的“(望溪)先生之所学”。
最后,方苞对颜李学派、阳明心学以及佛、老思想的态度以及相关论述,这些属于“程、朱之外”的思想,是“望溪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后来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
--(第一夜 新婚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