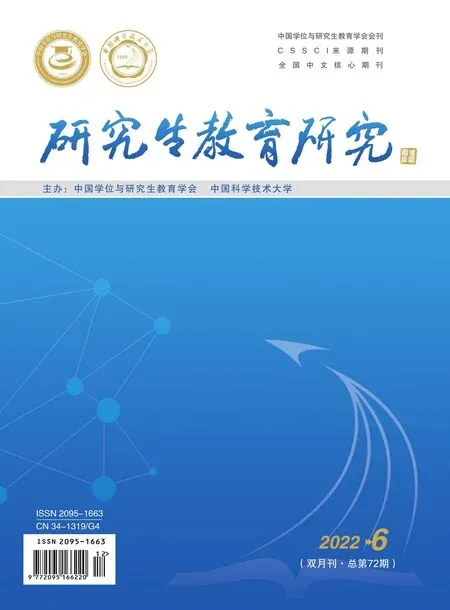培养单位如何为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做准备
——基于全球博士生的调查
付玉媛,韩映雄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一、研究背景
在19世纪德国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下,博士学位及博士生教育主要是为学术职业生涯做好准备,是进入学术职业的“入场券”。[1]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博士生教育是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这一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转变,且这一转变已成为一种常态化情形。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显示,与入学之初的就业取向相比,博士生选择逃离学术职业的比例高达40%左右,而选择回归学术职业的比例仅有20%左右。“学科不再是大多数引导兴趣的问题所在的场所,也不再是科学家们必须回归其中寻找认同或奖赏的地方。”[2]国际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加拿大等诸多国家的博士毕业生进入到学术职业的比例已不足40%。[3]我国博士就业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近三分之一的学术型博士生向非学术部门溢出,虽然拥有学界专业认同的博士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但相当一部分素质优异的博士人才外流到非学术部门。[4]其余针对我国博士研究生的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结果,博士生群体毕业后期望去高等院校的比例也仅为50%左右,[5]并且有超过30%的博士生期望成为实用技术开发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党政人才等。[6]可以说,无论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单看我国,博士生多元化的就业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学术为业”不再成为博士生群体的主要选择,向非学术职业溢出成为博士研究生就业的重要趋势,[7]博士生教育已经呈现出与学术职业“解耦”的状态。[8]
那么,博士生教育该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培养单位该如何实现从单一性的学术本位向多元化的方向转变?这个追问是本研究的原点。
二、文献述评
博士生群体出现多元化就业取向的因素众多,其一,内部因素的“劝退”。高校教师职业环境的恶化、上升渠道的窄化、高度竞争化与指标化等大大降低了学术职业的吸引力,此外,高校教师的人事聘任制度等也由“终身制”向“聘任制”改革,[9]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已经入侵到大学的学术职业之中,竞争、考核以及指标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术职业的重要特点;此外,教师的自主空间不断被侵蚀,教师承受的职业压力也越来越大。[10]这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百年之前在《以学术为业》中提及的学术职业的生存环境不谋而合,“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开始做起;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金钱支配前提的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他有被解雇的危险……”。[11]其二,外部环境的“拉动”。“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训练人员为信息社会服务,工作岗位不会缺乏,但谁来操作这些技术的能力来胜任这些工作?”[12]随着社会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多的行业也呈现出对高学历研究人才的渴望和需要,如研究表明,以企业为代表的诸多单位对工科博士也有较大需求,[13]而这些行业也为博士生群体提供了优渥的职业发展环境以及丰厚的薪酬待遇。因此,大学教师从业环境的“主动劝退”以及社会发展环境的“旺盛需求”成为博士生多元化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成为推动博士生群体由学术职业溢向非学术职业的主要力量。
可以说,博士生就业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既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征,也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本身有其内在的学术性和外在的社会性,而博士生培养也有其内在的学术逻辑和外在的市场逻辑。[14]在此背景下,博士生就业成为一项逐渐得到关注的领域。在有关博士生就业的研究中,影响博士生学术职业取向的因素[4]、导师指导对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或者非学术职业的影响[15-16]、组织支持对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影响[17]以及博士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18]等都有相关的探讨,也有研究对博士生非学术职业就业的特征[19]、博士生整体就业特征[6]等进行了描述。这些研究虽然详细以及系统地探究了博士生就业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等,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第一,已有研究多是围绕“以学术为业”展开,即探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博士生在“以学术为业”上的选择,由于“以学术为业”是博士生教育最经典的培养目标,博士生“以学术为业”也是实现学术职业自给自足的重要表现,因此这些问题值得也需要深入探究,但是在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关注博士生的学术职业就业取向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关注博士生不同的就业取向。第二,已有研究多关注的是博士生个体背景特征、家庭背景特征、学术职业环境和就业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即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博士生的就业意愿或者学术职业选择意愿。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因素属于“先赋性”因素或者外部环境因素,因此是不可改变且较难把控,而培养单位为博士生提供的教育过程因素才是可改变的因素,且这些教育过程因素也才是为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做好准备的根本抓手。因此,在关注“先赋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同时,更要关注“教育性”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致力于探究培养单位提供的教育过程因素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从“教育性”因素的视角为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的提高提出可供资鉴的建设性意见。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的是Nature2019年开展的全球调查数据库。该调查以全球在读博士研究生为对象,剔除无效样本后,共收到6812名有效样本。其中,样本量占比较高的国家依次是美国(1548人,占比22.72%)、德国(528人,占比7.75%)、澳大利亚(193人,占比2.83%)、加拿大(190人,占比2.79%)。我国的有效样本量是765人,其余国家的样本量均少于200人。男博士占比50.53%,女博士占比为49.47%;读博期间没有边工边读的有5486人,占比80.5%;在年龄上,24岁及以下的有816人,占比12.0%;25~34岁的有5261人,占比77.2%;35~44岁的有552人,占比8.1%;45~54岁的有107人,占比1.6%;55岁及以上的有51人,占比0.7%。
就我国样本而言,男博士占比65.5%,女博士占比34.1%;在年龄上,与全球样本相似,位于25~34岁之间的博士也是比例最高的,为78.2%;读博期间没有边工边读的博士占比88.1%,边工边读的博士占比11.9%。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Nature开展的调查多有“不确定”或者“其他”等选项。因此,为了不影响数据分析,本研究将此类选项按照缺失值进行处理。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院校影响因素模型(College Impact Model)关注学校整体环境与学生发展的相互影响,[20]该模型从两大方面分析学校对学生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学生的个体背景特征,包括性别、种族以及学习成绩等,其次是学校特征,包括学校的办学定位、教师与学生共同营造的院校氛围等因素,[21]其本质关注的是教育过程中的活动能否或者如何促进学习者发展的问题。[22]其中,阿斯汀(Astin,A.)的“Input-Environment-Output模型”(简称“I-E-O模型”)即“输入—过程—产出模型”影响较大,也最契合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阿斯汀的“I-E-O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
“I-E-O模型”指出,学生个体的产出与学校环境息息相关。[23]对于博士生群体而言,博士生培养质量也是博士生、导师及培养单位彼此互动、共同建构的过程,个体努力、导师指导以及培养单位提供的支持保障都是提高培养质量不可或缺的条件。[24]而已有研究也表明,培养活动对博士生就业过程及结果有显著影响,[25]具体而言,如博士生培养单位提供的学术支持[26]以及职业支持[27]等是影响博士生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在“I-E-O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探讨培养单位提供的教育过程因素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的影响。其中,个体输入变量和学习投入变量为控制变量,培养单位提供的教育过程因素为自变量,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为因变量,各类型变量的详细含义详见下文。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H0为:培养单位提供的教育过程因素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的准备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研究假设将在下文中予以细化。
(三)研究变量及其解释
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教育过程因素如何为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做好准备,因此,自变量为教育过程因素,因变量为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在考虑Nature调查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教育过程因素操作化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导师层面、院系层面和学校层面。导师指导被认为是影响博士生培养的核心因素,环境因素也是影响博士生培养的又一重要因素。[28]此外,安德森(Anderson)等人指出,导师指导和组织氛围是影响博士生产出的重要因素。[29]对于本研究而言,对导师指导和组织氛围的操作化衡量和解释需更具有针对性。因此,结合具体问题,本研究对导师指导和组织氛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导师层面包括导师的学术指导、就业交流和人文关怀,其中学术指导和就业指导分别是具体的科研指导以及就业交流等,人文关怀则指的是研究生导师对博士生的认可、心理支持以及情感关怀等,这理应成为导师指导的重要内容;院系层面包括院系成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就业交流;学校层面包括学校提供的人文关怀和就业交流。
在就业取向准备度上,本研究并不拟考察某一具体工作的准备度,而是考察不同就业类型的准备度,且这个就业类型并不是采用人口学调查中对就业类型的划分,而是考虑了博士生教育就业的特点。正如上文所述,传统意义上的博士生教育是为进入学术职业而做准备的,因此,本研究将博士生就业取向分为:学术职业就业取向的准备度、非学术职业就业取向的准备度以及跨越产业和学术界就业取向的准备度。需要予以特别说明的是,对研究变量的操作化定义是基于已有文献、研究问题以及Nature调查数据的可获得性三方面考虑的结果。控制变量则为博士生的人口学背景变量以及个体投入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详细解释详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情况的说明
基于以上的阐述,本研究将研究假设H0进一步细化为以下三个假设,分别是:
假设H1:导师层面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的准备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院系层面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的准备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学校层面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的准备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数据与结果
(一)博士生在不同就业取向上的准备度情况
如表2所示,从全球样本来看,学生认为通过博士阶段的学习,自身为从事学术职业、非学术职业以及跨越产业界、学术界做好准备的平均值分别为3.78、2.77和3.07,而我国博士生在这三方面上的得分分别是3.14、2.65和2.80,可以说我国博士生在不同就业取向的准备度上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对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在多大程度上可提高自身就业能力的期望上,我国博士生的期望为4.0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82。这说明,我国博士生是期望通过博士生阶段的学习来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的,但实际结果却表明博士生的学习并没有使我国博士生在不同就业取向上做好准备。

表2 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的基本情况
在群体差异上,不同性别的博士生在从事学术职业准备度以及从事跨产业界和学术界职业准备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都是女博士高于男博士;不同年龄和每周不同学习时间的博士生在三种职业准备度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专业认同度高的博士生在学术职业准备度上显著高于专业认同度低的博士生,但在其余两类职业准备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持有学术动机的博士生在学术职业准备度上显著高于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但是否为学术动机在其余两类职业准备度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异(表3)。

表3 博士生不同职业准备度的群体差异
(二)博士生对教育过程性因素的评价
在导师层面,全球博士生对导师学术指导的满意度均值为4.51,我国为4.08;在是否与导师进行就业交流上,全球的基本情况是有48.8%的博士生与导师交流过未来的就业,我国则是36.9%的博士生表示与导师交流过就业;在导师提供的人文关怀上,全球博士生的基本情况是4.93,我国则是4.88。
在院系层面上,院系成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就业交流都是呈现出我国低于全球的情况。在学校层面上,对于文化氛围来说,我国样本的基本情况略高于全球基本情况,但在就业交流上,我国样本的基本情况略低于全球基本情况,详见表4。

表4 博士生对教育过程性因素的基本评价
(三)教育过程性因素如何影响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
从事学术职业准备度的影响因素。从全球样本来看,导师给予的学术指导(β=0.155,p<0.001)、人文关怀(β=0.112,p<0.001),院系层面的学术交流(β=0.060,p<0.001)、就业交流(β=0.107,p<0.001),以及学校层面的文化氛围(β=0.080,p<0.001)是主要影响因素,且都是正向推动作用。从我国样本来看,导师给予的人文关怀(β=0.103,p<0.05)、院系的就业交流(β=0.103,p<0.05)以及学校的文化氛围(β=0.0158,p<0.001)对博士生的学术职业取向准备度有促进作用,但我国博士生导师的学术指导对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的准备度却没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应高度重视。
从事非学术职业准备度的影响因素。从全球样本来看,导师给予的人文关怀(β=0.094,p<0.001),院系层面的就业交流(β=0.241,p<0.001),以及学校层面的文化氛围(β=0.107,p<0.001)是主要的正向影响因素,但是导师层面的学术指导、导师层面的就业交流、院系层面的学术交流以及学校层面的就业指导等对博士生从事非学术职业准备度都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效应也适用于我国的博士生样本。
从事跨产业界和学术界职业准备度的影响因素。从全球样本来看,导师给予的人文关怀(β=0.127,p<0.001),院系层面的就业交流(β=0.248,p<0.001),以及学校层面的文化氛围(β=0.112,p<0.001)是主要影响因素,以上因素也是正向影响我国博士生从事跨产业界和学术界职业准备度的因素。但是院系层面的学术交流、学校层面的就业指导等博士生从事跨产业界和学术界职业的准备度没有影响,而导师的学术交流对全球样本的博士生从事跨产业界和学术界职业的准备度没有影响,但是对我国样本的博士生从事跨产业界和学术界职业的准备度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表5)。

表5 影响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的因素
因此,总体来看,假设H0、H1、H2以及H3都是部分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导师层面、院系层面,还是学校层面皆是部分因素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准备度有显著影响。此外,在年龄上,我国参加Nature调查的博士生样本都在54岁及以下,因此“55岁及以上”这一变量的回归分析数据是缺失的,此外,我国博士生样本在“是否换专业”上也都是“否”,因此这一变量的数据也是缺失的。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教育过程这一可改变因素出发,探究了影响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的因素。在当前博士生多元化就业的趋势背景下,培养单位要致力于为博士生不同的就业取向做好准备,而不能继续停留在单一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上,这不仅是培养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其在知识生产模式Ⅱ背景以及知识经济时代下实现自我变革的表现。鉴于此,本研究从导师、院系以及学校层面,提出如下建议。
(一)认识到导师人文关怀所具有的无形力量,并落实在导师评价制度之中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对于博士生哪种就业取向准备度来说,研究生导师的人文关怀都能够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导师在博士生就业支持与准备中给予必要且及时的情感关怀的重要性。已有研究也表明,导师的情感支持是影响其指导研究生效果的重要因素。[30]基于深度访谈的结果,已有研究也指出导师的指导应包括接纳和认可、角色榜样等社会心理功能。[31]导师是博士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来自导师的关心、鼓励以及情感关怀等是助推博士生成长的“无声”与“无形”的力量,起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与实质作用。当前博士生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和职业选择困境,对未来就业选择处于迷茫的状态,来自导师情感层面的关系与鼓励虽然并不能直接助力博士生能力的提升,但也能增强博士生的自信心和幸福感。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导师给与学生的帮助和理解有助于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32]因此,研究生导师在对博士生进行科研指导的同时,更要关怀博士生的心理健康,及时给予博士生必要的认可和鼓励,与博士生进行更多的非正式交流与互动。[33]
博士生导师指导需要同时兼顾促进专业知识发展和对学生的关心这两个维度,[34]使研究生导师与博士生之间建构一种有温度、有情感的健康导学关系,让心理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关怀成为导师指导的重要内容。当然,若要丰富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内涵,提高导师对研究生情感的支持度,其本质仍在于要转变对研究生导师的遴选以及评价机制,而不能停留在口头号召层面。现阶段我国高校在评聘或者考核博士生导师时,不仅缺少导师对博士生的人文关怀等内容,以及以科研绩效马首是瞻,[15]而且对导师自身能力的强调多于对导师指导过程的关注。[35]因此,培养单位不能仅要求导师要提高对博士生的人文关怀,更要将导师对研究生情感层面的支持度以及导师指导的过程性质量纳入导师的选拔、评价制度之中,从而使得制度改革成为研究生导师指导内容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二)高度关注我国导师学术指导质量,师生共同助力高质量导学关系的建立
导师的学术指导本应是博士生进入学术职业最基本以及最重要的支撑和基础,但是回归分析的结果却表明,即便对于博士生学术职业取向的准备度来说,我国研究生导师的科研指导都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研究生导师是博士生学术知识、能力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引路人,但是数据结果表明导师的责任履行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国博士生对导师指导在责任感、学术指导、学术修养、指导质量等方面均存在满意度不高的问题,其均值都介于比较不同意与一般之间。[36]可以说,已有研究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博士生导师指导学生的非常态和低质量的现象。一方面,在当前指标化科研成果的导向下,博士生导师会更多地围绕学术成果的产出去指导学生,因此,反思制度怎样使得导师和学生把功利化作为生存之道是十分必然的。[37]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充分反映出我国研究生导师在指导博士生方面的“招而不导”现象,全球博士生样本对研究生导师学术指导的满意度为4.51,但是我国博士生样本对导师学术指导的满意度仅为4.09。对比之下,可见我国导师对博士生学术指导这一基本职责并没有得到较好地履行。而导师指导的时间与深度等是影响博士生学术职业能力、学术职业兴趣与倾向的重要因素。[38]
因此,对于我国博士生教育来说,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学术指导的有效性和质量,并要把高质量的学术指导作为选拔以及评价导师的基本准绳,而非仅关注导师学术指导的时间和频次。此外,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沟通方式也需得到关注,如为了实现导师与博士生之间高质量的学术交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独创了“研究学徒会”,博士生不仅可与导师讨论问题、汇报学业,导师也需要向学生汇报研究成果,双向的互动可有效帮助博士生把握最新的学术前沿动态等,从而强化了导师在博士生学习与成长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且博士生参与“研究学徒会”相当于修读一门课程。[39]因此,我国博士生培养单位要高度关注导师学术指导这一基本职责,不仅要在导师的选聘制度上有所改革,也要思考如何创建新颖且有实效的导学制度。此外,博士生也要注重增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与导师进行学术层面的交流,与导师交流自身学术层面的想法与观点,而不能过度依赖导师的催促,要清晰地认识到博士生学业完成是自己而非导师的分内之事,在高质量导学关系构建中发挥作为学生应有的价值和责任。
(三)发挥同质性博士生群体的力量,改革基于学术本位的人才培养环节
院系成员之间的就业交流而非科研交流是提高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的共通因素,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了要高度重视院系成员之间的就业交流,并要在人才培养环节中予以体现。首先,院系成员之间的交往具有身份地位平等、交流便利性高等特点,这也提高了博士生群体之间沟通的受益度。[40]院系成员之间交往的这一特点也能够解释与导师进行就业交流为何不能提高博士生的职业准备度。基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导师与研究生多为师道尊严下的师徒制关系,这就大大降低了研究生将就业的真实想法反馈给导师的意愿度。研究生导师与博士之间相当于一种契约关系,博士生的职业兴趣和活动理应与研究生导师的期望相一致,但是当这种契约关系被打破时,博士生就需要寻求外部资源来获得职业生涯发展的帮助。[41-42]即便如此,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意在否定导师对博士生职业指导的价值,已有研究也表明,给予职业发展建议是学生最期望获得的研究生导师指导内容之一。[43-44]本研究欲在揭示的是来自导师就业指导的不足之处,更欲在表明院系成员之间就业交流的重要性。
其次,学校层面的就业交流对博士生不同就业取向准备度都没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博士生群体之间的交流是有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即是交流群体要建立在具有相同或者相似专业背景之上。现阶段,博士生就业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仍是“有章可循”的,而“有章可循”的原因,就蕴含在博士阶段的学习具有的高深性和专业性之中。因此,同辈之间经验的分享要建立在具有一定同质性的教育背景之上,这样的求职以及就业经验才会有更多的可采纳性、针对性以及具体性,而这要最终落实在人才培养环节的调整上。院系层面要转变学术性人才的单一化培养目标,不能只开展学术交流,本研究结果也表明院系成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仅对学术职业就业取向准备度有促进作用,所以更要高度重视成员之间的就业交流,如定期在毕业生和在读生之间、不同年级博士生之间等开展就业交流会,充分利用博士生群体自带的资源和力量,使具有相同或者相似学科背景的博士生有常态化或者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并将其置于与学术交流活动同等的地位,对现阶段面临的就业压力进行具有共鸣性的探讨,让同辈之间分享鲜活的个性化就业以及求职经历。
(四)实施多元化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建立包容性的博士生考核与评价制度
在本研究中,学校层面的文化氛围指的是“学校是否为我提供一个学习与生活相平衡的环境”。这说明,当博士生感到身处一种平衡、健康的学校氛围时,也能够更好地在不同就业取向上做好准备,这不由得去反思当前博士生群体失衡与高压的求学状态。过高的考核要求和科研压力是导致博士生群体学习与工作失衡的主要原因,而诸多高校都要求在读博士生需发表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在不发表就出局的现实面前,博士生的压力自然会增加。[45]如若博士生压力过大,自然会影响其自我价值的发挥。[46]正如上文所述,在当前阶段,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生毕业后都期望进入学术职业。因此,在博士生培养上,高校不能仅将学术型人才作为唯一目标,而是要为具有不同就业取向的博士生提供帮助和指导,这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建立多元化的博士生培养目标。此外,人文社科和理工科领域的博士在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也存在巨大差异,[47]因此,多元化培养目标的设定也要注重学科差异。
欧美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改革,如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提出,博士生教育不仅要培养创造性学者,也要为其在政府、工商业界等部门就业做好准备;[48]西方诸多大学并没有对博士生有论文发表的要求,而是更加强调课程的修读、博士生资格的考核、博士论文的写作以及助教经历等。[49-50]而已有研究通过访谈西方大学的博士生发现,在这种无明确论文发表要求下,他们也不会将太多的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在学习过程中锻炼自身的研究能力,这就说明宽松、自由、纯粹以及包容性的氛围可以为博士生留出独立思考和做自己喜欢事情的空间。[39]但是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并未得到足够关注,仍然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对博士生仍有一定的论文发表要求。因此,设置多元化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应是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改革点,从单一性的学术本位向多元化转变,并从博士生考核等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建立包容性、允许自由发展且重点关注毕业论文质量的考核与评价制度,这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总体精神是相一致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提倡导师应注重对博士生加强人文关怀、院系应为博士生之间搭建就业交流平台,还是提倡学校要改革对博士生的考核以及评价制度等,这都是具体行为。培养单位若要为博士生多元化就业取向做好准备,从本质上来说有两点:一是要认识到当前博士群体多元化的就业趋势已经是一种必然,这是意识层面的改变与进步,并要使意识成为行动的先导;二是要改革博士生培养制度,不仅要在培养目标等方面做出改革调整,也根据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各层级培养单位开展相应的人才培养活动或者改革现阶段的人才培养活动,以及要不断改革与研究生导师、博士生相关的制度,使得制度改革与培养目标改革相一致,并使制度改革为培养目标改革保驾护航。
——王永平教授
——陈桂蓉教授
——拜根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