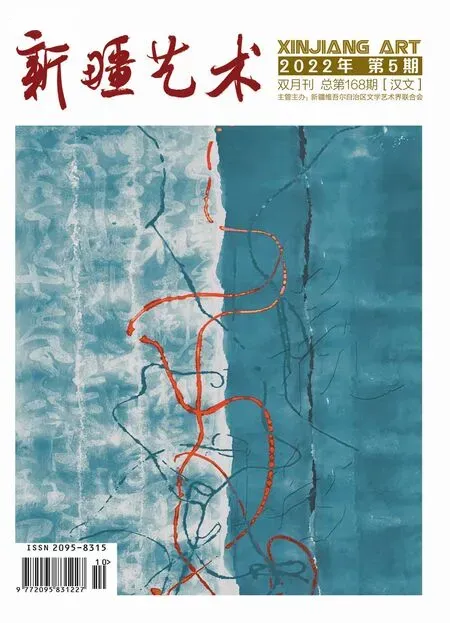新疆影像作者的内在视点表达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摄影札记
□ 柴 然

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剧照
新疆素来是影像创作者的理想之地,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形象和自然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影像创作者前来创作实践。不断涌现的短视频、宣传片、电影在将“新疆印象”图景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大美中国的含义,人们对新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也在这样的建构中不断升华。
在我们积极绘制这张“新疆印象”明信片的同时,作为本土影像创作者,我们应当审慎地觉察到,当我们一想到新疆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山美水美人美的影像,这意味着新疆正在被“景观”化。一切鲜活的东西正在变成一种表象。文化符号的攫取和组合都在满足一个关于“异域风物”的想象,使得本土创作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生情感表达也不免侵染上猎奇的审美趣味,本土创作者也成为了审美上的异乡人。作为新疆本土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摄影师,在我看来,要创作出超越地域性的作品,最根本的是回归自身的本真体验,以内在视点表现出对这片“诗意栖居之地”的深厚情感。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拍摄于帕米尔高原,要形容帕米尔高原的群山,大概只有宋代寇准的“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最为贴切。沿着历代商队的足迹,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作为帕米尔高原东界的塔什库尔干早已成为大美新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我思谋影片的文化形象时,指引我的是童年的记忆,十二岁时我随父亲来此地写生,这浩大的气象就挤进了我小小的瞳孔里。帕米尔高原被誉为“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这里的天空最接近天空的本真,有一种直逼宇宙的真实,清纯的蓝色溶于无垠的幽暗之中,仿佛冰正融于水,这种纯粹的黑蓝色令人震撼。天空下是巨大的山石投下的阴影,茫茫雪原泛着粼粼白光。而更为惊奇的是天地间毫不商量的变幻,记得有一次,我们父子行走于山梁,忽然下起的冰雹打在脸上刺痛,暗沉的天色尽头聚满翻滚旋转的阴云,那是肉眼可见的翻动,忽然云团如万马驶过,露出慕士塔格冰峰,一抹金光像箭一样射来,我来不及闭眼。时至今日,每当想到塔什库尔干,那道亮斑总是挥之不去,那是双眼被拂去尘埃后留下的赤诚,更是至美无法被直视的印证。后来我成为一名摄影师,在视觉上对雄健、极致之物的偏好,对明暗极限的认识,正源于童年的高原之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拍摄对我而言,不是从外部的视角进入他乡的讲述,而是我个人生命经验的涌现。
也正因为这份本真,影片中的影像不再拘泥于既有的帕米尔景观,而是把握到了帕米尔景色的精髓,我开始尝试以无名的山脉冰川传达“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天地之美。
一个人的文化人格是由其成长的文化环境所塑造的。我从小成长于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又经常跟随父亲去新疆各地写生,结识各族朋友,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濡化在我的生活和信念之中。尤其作为新疆电影影像的书写者,我秉持这样一种文化自觉:要充分发挥电影文本的丰厚性和电影技法的丰富性,将多民族文化以更自信、更真情、更准确、更深刻的视觉语言表现出来,借此表达新疆的真实面貌。


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拍摄现场
在我眼中,新疆各族人民所熔铸出的文化品格,远不是他者眼中淳朴热情那么简单,而是更为现实的包容与担当,是在坚守和奉献之后永葆乐观的精神。在此壮美的天地中生活着的是真诚勇敢坚毅的新疆各族人民,他们正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包含主人公拉齐尼·巴依卡在内的时代、民族人物群像的原型。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讲述的是英雄成长的史诗,其中最令人动容惋惜的,是几位英雄的牺牲。这最深沉的部分揭示了我们民族几经波折依旧屹立的灵魂所在——不屈的生命意志;揭示了悲剧之美的终极辩证法——生与死的斗争、勇敢与恐惧的斗争、觉醒与彷徨的斗争,直至以死诠释出一生的全部意义,以死来激起对生最大的热忱,最终,生因死而更具价值。拍摄之前我带着剧本重回圣山脚下,巨大的河谷被高耸连绵的山脉包围,更远处是冰峰和隐约可见的苍穹,体型庞大的牦牛在这宏伟的宫殿中似一粒细沙,山脊上一阵阵风呼啸而过,我恍惚间似乎望见一个小小的人,他走着走不完的路,爬着爬不完的山,他如果倒下了,便会在他倒下的地方长出一颗小树,那是高原特有的从石缝里挤出来瘦小但充满生命力的植物。这小小的生命与巨大环境的互相成全,宣告着生命的意志永存。我的这些所见所想所思,奠定了影片画面沉郁恢弘的基调。
在此基调之上,我希望画面还能呈现一种戈雅、苏里科夫、高更绘画的融合之感。塔吉克族房屋内部总是“矗立”着一根光的柱子,阳光因为房屋坚固的暗部映衬而成为一种强烈的实在物,或者说阳光具有了一种实体性,这让我意识到要通过阴影来赋予光存在的形式。那就需要像戈雅那样,通过光线效果突出画面的戏剧性。我留意到塔吉克族男性饰物中大量的黑色皮毛、帕米尔高原大量裸露在地表的黑曜岩、黑色的牦牛群以及在干燥的阳光下无处不在的硬边缘阴影,以及大地和人脸上斧凿的“皱纹”。而当这种将粗砺的笔触和暗沉的边缘构成电影银幕中人物群像的轮廓时,我就不由地会想起苏里科夫。苏里科夫的巨幅绘画中,那种恢弘苍凉的气质和几乎是超景深镜头才可能呈现的一张张细致面孔,形成了一种庄严而动人的张力,而这也是我心中帕米尔英雄群像该有的张力。继续沿着粗犷沉郁的大地欣赏色彩,复杂的黑色与高原光照下的高饱和纯色相融合时,我便想到了高更。他擅用西洋颜料模仿矿物色调,如赭石、朱砂、石青、孔雀绿等,并通过互补色与过渡色之间的巧妙搭配营造出厚重深沉的效果,这恰好是帕米尔高原的黑色调和过大地的深褐、草滩的土黄、水的碧绿、天空的藏蓝后而形成的效果,正如高更所追求的“和谐并发人深省”的色彩。我试图将后印象派的大胆色觉注入戈雅的激烈、苏里科夫的沉郁,从而混合成的雄浑古朴的神秘力量,这是我心中的帕米尔之美,也是最契合这部影片的画面效果。
而后的关键,就是需要找到一种理念同时是一种可以操作的介质,来将景观、人物和精神统一起来,在我看来这无疑就是光、影和光影关系。从摄影的角度来看,世界本就是一团光影,包含着人的世界是以光影展现自身的,当世界还不可以被言说的时候,光影就已经在“讲述”关于自己的一切。电影故事中的银幕角色对观众来说就是可以忽略一团光影,可以不去觉知蕴含在光影中的更多的信息,但观众的潜意识会不间断地在这一团光影中索取,而摄影师就是要利用光影关系的一切可能来“倾诉”语言和形象所不能及的内容,将精神和情感的全部真相袒露出来,这或许就是阿贝尔·冈斯所言的“画面的灵魂”。

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剧照

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海报
要实现剧本对人的生命意志的深刻表达,以及对生死辩证的深刻揭示,在我看来,首先要让光成为主角,使影成为它的对手,并在光影的斗争关系中展现辩证法的矛盾性和人物情感的丰富性。高原的光与影是具有矛盾性的。光带给万物生命,但它过于强烈时又摧残生命;影常常了无生机,但在夺命的烈日下又能成为生命可贵的庇护所。同时,光固然可以通过颜色、强度的变化表达自己的主张,但更多的时候要通过影来赋予其形式,比如雪雨雾的变幻就可以使光产生或明或暗的“性格”。所以只有在画面中、画面与画面的对照中,清醒地选择和操纵光、影以及光影关系,才能将这些复杂的意味准确地释放出来。
影片开始时,小拉齐尼嬉戏于草垛,明丽阳光晕染出英雄童年的底色,而随即太阳的大特写让人刺眼不适,阳光的意味立刻从美好变为不确定。次日远征队伍出发,红日托举的天初亮,与黑暗的大地分置,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即将展开。队伍行进中,剪影与冲向镜头的强光激烈对抗,被打碎的阳光像万箭齐发,阻挠着队伍的行进。这时需要为日光添加更为复杂的情绪,这需要操纵介质完成,我们使用直径两米的鼓风机将雪原最上面的一层冰晶吹起,这种晶体微妙的折射和反射出一种锐利、闪烁的光泽,光被转化成了风的样子,被赋予了躁动不安的情绪。而当队伍处于路途困顿的迷茫中时,我们创新地在零度左右的温度下采用造雪机,这时喷射出的水雾不会立刻冻结成雪花,而是形成一种冰水混合的雾状物,雾状物遭遇冷空气而忽然迟缓,一种天然的美油然而生。而当光融进这慢动作的雾中,便赋予了光以时间感,产生一种留恋的情绪。人物在这逆光的雪雾中穿行,长长的投影扭曲飘散,这身影恰是他们内心的外化物,迷茫而虚弱,仿佛俄底修斯穿行于塞壬的歌声中。
而牦牛牺牲的场景,我让夕阳给牺牲加上金色的棺椁,一个生命即将消失,光的强度随着气息逐渐微弱,直至太阳落幕生命也随之陨落。在拉齐尼勇救儿童的场面中,施救过程中我主观地加入了很多强烈的直射光,欲将其表现为一场战斗,一场生与死互不相让的角力。而当拉齐尼最后沉入冰湖时,我希望最后留在他眼中的是最美好安详的一幕——一轮红日勾勒出母子的平安,这与影片开始处父辈远征时天边红日的画面相呼应,也与牦牛之死的一幕形成光影上的互文。另外,为了将景观、人物和精神统一在光影中,就必须要把握光线与大地的关系,熟知不同地貌、海拔、气候下太阳的变化规律和轨迹。影片在开拍前,我们就进行了四次勘景工作,历时近半年,跟随护边员向导踏遍塔什库尔干的各种地貌,涉足之处都是从未被拍摄过的险要地段。牦牛牺牲的那一幕,我认为必须在连绵的山脊上拍摄,因为牦牛的脊梁摔断了,但大山的脊梁支撑着它,它的尸骸化入泥土,最终会融入大山的脊梁。同时,在千沟万壑的地形中只有在最高处,才有可能完整地看到夕阳下沉的全部变化,来完成光色运用上的意图。在拍摄的关键时刻,牦牛也仿佛真的领会了剧情,完美地上演了与战友的诀别。
影片最后,悼念拉齐尼的情节,在我的理解中,这是生死混沌的时刻,明与黑调和出一种灰色调,当静穆笼罩一切,光的形式要更加温和隐秘。拍摄当天,刚好是非常阴郁的薄雾天气,阳光仿佛因哀伤而遮住面庞,连同环伺的山脉一同消隐在灰白之中,天地间只留下人,这与全片中烈日当空不断与人斗争相对应。直到众人仰望苍穹,在最高的地方,太阳终于又出现,就像一盏明灯点亮了希望。更让人惊喜的是,这一次出现的太阳,与全片任何地方出现的太阳都不同,在雾气的漫反射下,太阳的形状没有了之前的尖锐感,一圈光环将它围绕,显得分外的神圣辉煌。
最后,所有这些感觉和设计,都需要通过摄影机去实现,摄影师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决定了运镜的特征。我认为,观众必须身临险境,才能体会到英雄的无畏,只有充分地贴近与跟随才能融入英雄的征程。所以无论是扛着机器抑或运用设备,我总是将机器尽量地靠近拍摄对象。随着故事的情绪,这种靠近或是奋不顾身地冲向,或是缓缓地走向,激烈之处甚至让阳光刺进镜头,让冰渣打击镜头,让动物的哈气扑上镜头,让尘土盖上镜头,以此“击碎”镜头玻璃来震动观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摄影工作,像是用一场激情的奋斗回报圣山对我遥远童年的点悟。将英雄的精神融入光影,又用光影将这种精神袒露,让观众透过一幅幅电影画面一瞻高原浩瀚,领略新疆人的赤诚。戏内戏外,各民族相互交织,共担使命的奋斗精神,正是我心中新疆绝美的文化内核。这种超越性的奋斗精神,不正是当今时代的呼唤吗?
一定程度的景观化是影像消费以及媒体构建的现代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促进旅游经济的必由之路,符合我们建构大国文化图景的现实需求。但作为新疆本土影像的创作者,我们应该更多地、自觉地承担起大美影像观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坚守自身作为新疆文化“谨慎判断者和定名者”的身份,努力挖掘独特的文化意象,而不是做既定符号的复制者。努力辨析“大美新疆”文化观念所携带的外在光环,探索新疆人看新疆的内在视点和主体性表达。当我们正深深嵌入大美中国的审美范式时,每一个本地创作者都应该尊重自己面对家乡时的个性化情愫,重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以地域性地发现、探询,探究开掘题材、提炼主题、升华创作,在开阔开放的视野中,切实地认识脚下的土地,以独特的眼光和使命感去创新去突破,为我们文化大国的自信表达注入应有的生动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