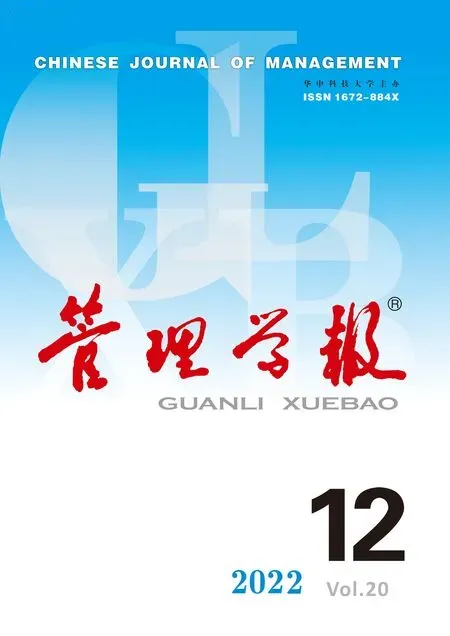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双路径作用机制研究
李 杨 梁宇萱 王 勇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由此可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简称“三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主要标志。为了增强人民的“三感”,就需要从民生入手,而社区商业生态就是满足社区居民综合需求的载体,它能够营造宜居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1]。为建立和维护良好的街区商业生态,2018年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街区商业生态配置指标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并强调根据居住人口数量或以社区为单位合理配置便民商业网点,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的普遍需求。学术界对于社区商业配置的关注也逐渐增强,现有研究对社区商业配置开展了初步的探讨,但多聚焦于某一具体业态形式[2],缺乏对社区商业配置的整体分析。
路红艳[1]发现社区商业能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而THEODORI[3]指出,社区满意度与幸福感有积极联系,那么社区商业配置作为影响社区满意度的因素之一,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幸福感呢?现有研究并未将其与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建立联系。《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商业服务业发展规划》[4]提出,要“持续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让人民群众生活更舒心、更有获得感”。但是什么样的社区商业配置能够真正提升居民的获得感,而获得感的提高是否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提高呢?现有文献难以给出回答。基于此,本研究创新地从社区商业配置的视角来分析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高途径,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来获得民生数据,构建商业配置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模型,并将民生获得感界定为居民通过消费所感受到的物质成果惠及程度,将民生幸福感界定为居民对日常生活的满意程度[5],以期为未来有关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更为政府改善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提供有效的管理切入点。
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2.1 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
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高对我国的改革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民生福祉的改善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国家层面看,提升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6],民众感觉到物质生活的保障,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从个人层面看,获得感和幸福感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同时亦能感染到身边其他人。
目前有关民生获得感的文献比较少,比如李鹏等[7]将其分为经济、政治、民生3个维度,并发现民生获得感与经济收入水平、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同时民生获得感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更多的研究都聚焦于幸福感,具体而言,DIENER[8]认为,主观幸福感是长期形成的、个体根据自身的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MOGILNER等[9]也在试图探索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其中包括与个体相关的特征因素,即人口统计学因素、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10]等;与外在相关的情境因素多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如公共服务[11]等能影响到幸福感。除此之外,个体的聚焦点,如对时间和金钱的关注也能影响到幸福感[12];甚至职场中的八卦[13]、员工的工匠精神[14]也对幸福感有影响。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着重关注个体幸福感的提升问题,但是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整体幸福感有所区别,居民的物质需求是否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是衡量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5],而社区商业生态配置与居民日常消费生活紧密相关。目前,鲜有研究聚焦社区商业生态配置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之间的联系。
2.2 社区商业生态配置
商业生态配置是衡量商业生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学者们多从配置的视角对商业生态的服务设施进行评价[15],进而开展相应的设施规划、空间匹配[16]和空间优化[17]。近几年,学者们试图搭建起社区商业配置的评估体系,例如,李雪等[18]以菜市场为切入点,构建社区便民商业设施配置体系,对等级结构和布局规模优化提出建议;张忠国等[19]将基础型商业配置分为可达性和共享性便民设施,基于丰富度、紧凑度、可达性3项评估指标,对便民设施配置的公平性与完善性进行评估,为优化可达路径提供支撑;江曼琦等[2]选取了商业配置中的连锁便利店进行研究,分析其布局情况,并为加快大城市小区连锁便利店发展提出建议。
同时,商业生态配置也是对社区公共设施和服务评价的重要衡量标准。田敏等[20]利用商业网点服务半径,商业设施配置情况等作为衡量生活便利度、社区服务度的指标,并联合其他变量构建宜居社区的评价指标。肖凤玲等[15]利用便民设施空间布局的形态特征、覆盖率和达标率,对小区空间匹配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李新娥等[21]也注意到了社区商业生态配置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将商业配置作为衡量硬环境指数和居民幸福指数的指标,用来构建幸福家园的评价综合指数。
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对民生幸福感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居民需求满足的角度看,个体有满足自身需求的动机,个体幸福源自于自身需求的满足[22]。商业配置情况越好,居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就越高。RYAN[23]发现,自主需求、关系需求和能力需求对实现个体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同样,虽然鲜有文献研究商业配置对获得感的影响,但是从这个视角也可以解释,当居民感受到自己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时,自然就会拥有丰富的获得感。从另一个角度看,较好的商业配置可以给居民带来方便,节约居民的时间,而时间充裕有利于个体的幸福[12]。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区商业生态配置能够影响民生获得感。
假设2社区商业生态配置能够影响民生幸福感。
2.3 双因素理论下的商业配置与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
赫兹伯格[24]提出的双因素理论最初用于研究员工的满意度评价。该理论认为满意和不满意是两个独立的维度,并将影响满意度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两类。后来,该理论被学者们应用到顾客满意度研究中,SLEVITCH等[25]在研究酒店顾客满意度时发现,核心属性即必须的(如房间的清洁度、枕头的舒适度等),和促进属性即非必须的、即使没有也可以(如个性化服务、良好的公共设施等)是两个独立的维度,它们会引发不同的顾客满意度反应。刘百灵等[26]把双因素理论应用在模型构建中,从保健和激励双重视角探究影响用户移动支付意愿的因素。
目前,鲜有文献运用双因素理论来解释消费者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社区具有服务功能,社区服务以满足村(社区)居民生活需求、提高生活品质为目标,以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包括为社区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服务。虽然社区服务有别于仅以经营为目的的商业服务,但是当社区对居民提供服务时,居民就是社区的“顾客”[27],居民会对社区服务产生预期,对服务体验产生主观评价,这些构成了社区满意度[28],而社区满意度是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主要考核指标[3],所以该理论适合运用到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研究中。
根据《指导意见》,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可分为基础型和品质提升型,其中品质提升型配置主要用以满足居民的消费升级需求。近几年,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基础型商业配置发展速度较快,已经能够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品质提升型配置的丰富性和完善性还有待提升。耿金花等[29]把影响社区满意度的因素分为日常生活、建设管理和服务休闲3类,其中日常生活被居民认为是社区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该研究发现,日常生活方面表现不好会对满意度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但服务休闲方面影响不显著;服务休闲方面的改善会显著提升满意度,但日常生活方面影响不显著。这种特征分别与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相对应。根据该分类的特征,基础型和品质提升型配置分别与日常生活和服务休闲对应,因此本研究认为,基础型商业配置属于保健因素,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属于激励因素。
综上可知,基础型商业配置难以提高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评价和满意度,因为居民认为这些是社区应当配置的;相反,居民会更加期盼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商业配置,由于社区服务评价与总体社区满意度密切相关,因此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能够提高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评价,进而提高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已有研究表明,社区满意度与幸福感有积极联系[3],同时,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能够满足居民相对重要性更高的需求要素,因此享有更高的幸福回报。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能够通过提高社区服务评价来影响民生获得感,但是基础型商业配置无法通过影响社区服务评价而提高民生获得感。
假设4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能够通过提高社区服务评价来影响民生幸福感,但是基础型商业配置无法通过影响社区服务评价而提高民生幸福感。
假设5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能够通过提高社区服务满意度来影响民生获得感,但是基础型商业配置无法通过影响社区服务满意度而提高民生获得感。
假设6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能够通过提高社区服务满意度来影响民生幸福感,但是基础型商业配置无法通过影响社区服务满意度而提高民生幸福感。
2.4 社区类型的影响
社区类型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社区进行分类,比如分为商业制社区与单位制社区,成熟社区与新兴社区,高档社区与低档社区等。社区类型对社区满意度与幸福感有一定影响。
不同社区类型的规划和商业配置发展水平也会存在差异。本研究根据不同社区的特征把社区分为老社区和新社区两类。老社区的商业配置以基础型为主,品质提升型配置较少,属于保健因素多、激励因素少的情况;新社区不仅基础型配置完善,而且品质提升型配置情况也比较好,属于保健因素多、激励因素也多的情况。这种激励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社区类型居民的激励程度存在差异:品质提升型配置对新社区居民的激励作用较小,对老社区居民的激励作用较大,即改善品质提升型配置情况对老(新)社区居民的社区商业评价和社区满意度影响较大(小),进而对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也较大(小)。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相比新社区,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对老社区服务评价和满意度的影响力度更大。
根据上述文献梳理和假设提出,本研究构建了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模型(见图1)。

图1 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和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问卷包含以下4个部分:①社区信息,包括居住区域、居住时间、居住面积、社区类型等;②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包括每个商业网点的详细情况,如是否有便利店、居民到达便利店的时间等;③主观因素,包括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评价、满意度以及对自己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判断;④人口统计信息,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收入等。
问卷选择在北京地区发放,因为北京属于全国较早进行社区商业生态建设的城市,所以其研究结果能够对其他城市起到借鉴作用。问卷通过专业的数据收集平台Credamo进行发放,参与者需为北京市常住人口,每位参与者能够得到一定的现金奖励。通过题目回答的完整性来对样本进行了筛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02份。样本包含了多种背景的居民,符合样本多样性的要求,具体如下:男性占40.2%,女性占59.8%;69.92%的被试年龄在26~40岁之间。样本的居住区域涵盖了北京市所有辖区,即6个城区、6个近郊区及4个远郊区。
3.2 变量测量
除特殊说明外,各变量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的方法,要求被试对相应的问题进行打分。
(1)因变量本研究选取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因变量。民生获得感包含两个题项:“您觉得自己所居住社区的服务点设置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日常消费需求?”以及 “您觉得自己所居住社区的服务点设置是否能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民生幸福感采用单项目自陈方式,题项为“整体来看,您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幸福程度如何?”参考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主观幸福感”题项。得分越高,代表民生获得感、幸福感越高。
(2)自变量自变量为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包括基础型和品质提升型。基础型包括蔬菜水果售卖点、肉蛋水产等类食品售卖点、便利店、早餐店、超市、美容美发、家政服务、洗衣店和便民维修,共计9种商业网点;品质提升型包括药店、花店、健身房、百货商店、大型超市、购物中心、家居卖场、电影院、面包房、书店、咖啡馆或茶馆、宠物店、体育馆(含游泳、羽毛球、篮球等)、中档以上档次的餐馆、棋牌室、儿童艺术类教育机构、儿童体育类教育机构、成人教育机构和儿童游乐场(游乐园),共计19种商业网点。
根据《指导意见》,社区居民到达商业网点的时间应在步行15分钟内,因此本研究以步行15分钟内的商业网点数目作为社区商业生态配置的指标。参与者在问卷调查中对“从您家出发,您需要步行或开车多长时间才能到达以下商业网点”进行评估,并提供从家到每个商业网点花去的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城市道路限速30km/h,公路限速40 km/h),考虑到居住区附近的道路以城市道路和公路为主,调查中开车的速度默认为35 km/h;又由于人平均步速为3~7 km/h,调查中步行的速度默认为5 km/h。在整理数据过程中,为了确保距离和时间以同样的标准计算,把步行和开车的时间按照1∶7的比例进行换算。比如,如果被试称到达某一网点需要开车5分钟,那么就按照步行需要35分钟的时间来换算。基于此,得到测量商业生态配置的指标:从家里能够在步行15分钟内到达的基础型商业网点和品质提升型商业网点的数量。
(3)中介变量本研究选取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社区服务评价题项为“您觉得自己所居住社区的服务点设置如何?”社区满意度采用单项目自陈方式,参考THEODORI[3]的研究,题项为“整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社区生活满意吗?”得分越高,代表评价、满意度越高。
(4)调节变量本研究选取社区类型(新社区为1,老社区为2)作为调节变量。老社区包括单位社区、政策性住房小区、老旧社区、城中村社区、胡同社区和其他类型社区;新社区包括普通商品房社区和高档社区。
(5)控制变量个体层面,本研究选取居民的性别(男为0,女为1)、年龄(18岁及以下为1,19~25岁为2,26~30岁为3,31~40岁为4,41~50岁为5,51岁及以上为6)、月收入(3 000元及以下为1,3 001~5 000元为2,5 001~8 000元为3,8 001~10 000元为4,10 001~15 000元为5,15 001~20 000元为6,20 001元及以上为7)、学历(高中及以下为1,大学专科为2,大学本科为3,研究生为4)作为控制变量。住房层面,本研究选取房子所在位置(二环以内为1,二环到三环之间为2,三环到四环之间为3,四环到五环之间为4,五环到六环之间为5,六环以外为6)、居住面积(60 m2及以下为1,61~80 m2为2,81~100 m2为3,101~120 m2为4,121 m2及以上为5)、居住时间(3年及以下为1,4~6年为2,7~10年为3,11~15年为4,16年及以上为5)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人口统计变量频率分布情况(N=502)
3.3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 25.0软件对变量民生幸福感、民生获得感、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满意度进行信度检验。其中,民生幸福感、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满意度都采用单项目自陈方式;民生获得感的Cronbach’sα值为0.777,高于临界值0.7;CR值为0.821,大于0.6,表明量表信度良好。
3.4 共同方法偏差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将量表中所有题项同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37.675%,小于40%,因此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 25.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验证假设。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分别以民生幸福感和民生获得感为因变量,计算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5,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1 主效应检验
首先,考察商业生态配置的整体情况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构建两个回归模型如下:Y1=a1Z+b1X+e1;Y2=a2Z+b2X+e2。其中,Y1、Y2分别代表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X代表商业生态配置的整体情况,即居民步行15分钟能够到达的基础型商业网点和品质提升型商业网点的数量总和;Z为控制变量,包括参与者的性别、年龄、月收入、学历、房子所在位置、居住面积和在当前房子居住的时间;a1、a2、b1、b2为系数;e1、e2为常数项。数据结果显示,商业生态配置对民生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2=0.117,F=9.334,p=0.000,β=0.261,p=0.000),对民生幸福感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2=0.082,F=6.298,p=0.000,β=0.143,p=0.001),故假设1和假设2成立。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N=502)
接着,分别考察基础型商业配置和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构建两个回归模型如下:Y1=a1Z+b1X1+c1X2+e1;Y2=a2Z+b2X1+c2X2+e2。其中,X1、X2分别代表基础型和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的情况;c1、c2为系数。回归模型的结果见表3。

表3 基础型和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N=502)
表3中模型1和模型3只放入了控制变量,用来检验个体因素对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检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商业配置对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由表3的模型2和模型4可知,基础型商业配置对获得感(β=0.056,p>0.1)和幸福感(β=0.030,p>0.1)的影响皆不显著,但是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对获得感(β=0.227,p<0.001)和幸福感(β=0.125,p<0.001)均具有显著影响。这是由于基础型商业配置无法影响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评价和满意度所导致的。
4.2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运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 000,设置95%的置信区间。首先,选择model 4,对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服务满意度在商业配置与民生获得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区服务评价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16, 0.037],不包含0;社区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06, 0.026],不包含0,因此两个变量均能在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到获得感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品质提升型不仅能够通过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服务满意来影响民生获得感,亦能直接影响民生获得感(coeff=0.025,p<0.001)。同时,增加了社区服务评价和满意度后的模型拟合度得到较高的提升(R2=0.691)。由此可见,社区服务评价和满意度是影响民生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社区服务满意度在基础型商业配置和民生获得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09, 0.051],包含0,也就是说社区满意度无法在基础型商业配置和民生获得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社区服务评价在基础型商业配置和民生获得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14, 0.071],不包含0,也就是说社区服务评价在基础型商业配置和民生获得感之间呈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且当控制了中介作用后,基础型商业配置对民生获得感也有显著的影响(coeff=0.052,p<0.001)。这说明,当以基础型商业配置单独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时,其能够影响到社区服务评价,进而影响民生获得感;但是当基础型商业配置和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同时作为自变量时,基础型的影响效果就消失了。因此,假设3部分成立,假设5完全成立。
同样对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服务满意度在商业配置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区服务评价在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与民生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为[-0.031, 0.067],包含0,同时社区服务评价对民生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coeff=0.028,p>0.1);社区服务满意度在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到民生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为[0.009, 0.037],不包含0。但是,社区服务评价在基础型商业配置和民生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03, 0.014],包含0;社区服务满意度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0.014, 0.071],包含0,因此两者的中介作用皆不显著。故假设4部分成立,假设6完全成立。
根据上述结果,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评价只能让居民“没有不满意”,而无法达到“满意”。企业为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当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提高时,需求得到了满足,满意度相应提高。但是,本研究聚焦的服务提供者是社区,而居民对社区服务和对企业服务的期望是不一样的。
4.3 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上述分析,可确定两条作用路径:①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社区服务评价—民生获得感;②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社区服务满意度—民生幸福感。下面分别考察社区类型对这两条路径的调节作用。依然采用Bootstrap的分析方法,样本量选择5 000,设置95%的置信区间,选择model 7。
路径①的结果如下: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和社区类型的交互作用对社区服务评价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coeff=-0.046,p=0.031)。具体而言,当社区类型为老社区,社区服务评价的中介作用显著(置信区间为[0.031, 0.081],不包含0,coeff=0.054);当社区类型为新社区,社区服务评价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置信区间为[0.005, 0.041],不包含0,coeff=0.022),但是影响效果低于老社区,也就是说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对社区服务评价的影响在老社区中更加明显。
路径②的结果如下: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和社区类型的交互作用对社区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coeff=-0.054,p=0.009)。当社区类型为老社区,满意度在商业配置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置信区间为[0.015, 0.059],不包含0),但是当社区类型为新社区,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消失(置信区间为[-0.013, 0.018],包含0)。换言之,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通过满意度来影响民生幸福感的作用在老社区中更加明显。综上,假设7成立。
5 结语
本研究旨在探讨社区商业配置优化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社区商业配置优化能够提升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②如果社区未配置品质提升型商业网点,基础型商业配置能够通过影响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评价而提高民生获得感,但无法提高满意度和幸福感;当基础型和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同时存在,上述作用会减弱。③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能够影响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评价和满意度,继而影响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④社区类型可调节商业配置对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老社区中品质提升型商业配置优化能够显著提升其评价和满意度,进而影响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而新社区中影响相对较小。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①将社区商业生态配置分成基础型和品质提升型,并基于双因素理论,将其分别界定为保健因素类和激励因素类,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②发现了社区商业生态配置优化能够有效提高民生获得感和民生幸福感,有助于未来从心理机制的视角来解读居民对社区商业网点的选择,并为有关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支撑;③探讨了不同的商业配置对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并从社区服务评价和社区服务满意度两条路径来解释,为有关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前置心理变量研究提供了思路;④检验了社区类型与社区商业生态配置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居民社区服务评价和满意度的影响,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路径边界。
本研究结论为政府生活圈商业配置优化提供以下建议:①重视社区商业生态配置的规划和优化工作,确保居民在步行15分钟内到达所需商业网点,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打造高品质社区商业生态环境;②重视居民的内在心理建设,通过商业网点优化来满足居民的需求,通过改善社区商业生态配置来增强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③梳理商业网点存在的不足,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因地制宜地制定规划,提高商业配置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度,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类型社区存在的问题;④及时梳理老社区可能存在的难点问题,通过提供“小而精”的社区零售网点等方式,实现服务功能集聚集群化,并充分利用线上服务功能,解决场地不足、改造成本高等问题。
本研究尚存在改善的空间:由于中国城市众多且发展和规划存在差异,因此模型和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低线城市,还需要验证。未来研究可通过追踪调研的方式,深入了解社区商业生态配置的优化过程对民生获得感和民生幸福感的动态影响;还可以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推广到特殊情境(如疫情等),同时探讨不同的个体对于两类商业生态配置的需求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