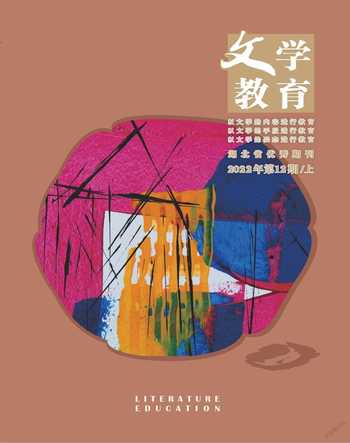《远山淡影》创伤叙事下的人格选择
林欣
内容摘要:本文以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为研究对象,借助创伤理论及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分析小说中描绘的创伤造成的心理伤害、创伤下的人格反应以及创伤后的利益选择。通过对悦子、佐知子等主要人物的剖析,着重关注悦子带景子移民英国这一核心事件,探讨战争后的人格选择问题及人物选择不同人格面具对自身心理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远山淡影》 石黑一雄 创伤叙事 移民文学 分裂人格
石黑一雄是日裔英国小说家,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是一部问世30年仍关注度极高的作品。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主人公悦子的视角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因战争受创从日本移民到英国的妇女在英国以及日本两地的生活。
一.创伤叙事的呈现
“创伤”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原指皮肤被刺破或身体外部的破损,现指一种心理受伤表现。20世纪初,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层面解释了“创伤”,他认为创伤是不愿面对痛苦过去的人在回忆时产生选择性失忆或者自我麻痹的现象。对于创伤群体来说,痛苦的记忆会反复出现,他们试图逃离、打破痛苦却从未成功,于是选择塑造不同的人格,在人格面具的保护下隐藏,试图否认痛苦的存在,从而达到心灵上的慰藉。
《远山淡影》以悦子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二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悦子极力展现经历悲惨创痛后的平静,她这样描述日本:“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长崎,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日子显得平静安详。”[1]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的伤害转瞬即逝,这实在值得怀疑。其实悦子是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典型代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战争后遗症的影响,对于创伤的掩盖恰恰反应了内心的实际感受,越想掩盖、否认,就暴露的越明显。尽管悦子描述的日本已经开始重建,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文章中找到战争遗留下来的惨痛痕迹:他们的公寓是建立在炸弹烧焦后的废墟上的、藤野太太每周都去墓地并且每周都能在那里见到一对悲伤的年轻夫妇、和平公园的白色纪念碑代表那些被原子弹夺去生命的人……
悦子在战争中失去丈夫、家园,而从她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她是一个拥有幸福家庭且马上要迎接新生命的女人,从她毫无逻辑、自相矛盾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透她的逃避、煎熬与混乱,例如她跟藤野太太讲述新生命的到来会使她开心,但实际不然,她内心对孩子有着无限的恐惧,孩子是她痛苦的延续,她的描述中有很多关于小孩的恐怖事件:一个专杀小孩的连环杀人案件、战争中一个母亲亲手溺死了自己的孩子、梦中一个小女孩上吊自杀。悦子的这一恐惧也在后来景子的自杀事件中得到了证实。对于景子死亡带来的创伤,悦子同样选择了逃避叙事,当她和妮基一起散步遇到景子以前的钢琴老师时,她假装景子还活着“我最近没有她的消息”这句话在双方的谈话中出现了两次,看似是对沃斯特太太说的,实际上是悦子对自己的谎言。这种对于痛苦现实的选择性失忆或者说是自我麻痹正是经历创伤后最具代表性的表现。
在景子身上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从而无情地“戳穿”悦子的叙事谎言。小说一开始就宣告了景子的死亡:移民英国后的她越来越封闭自己,与家人关系不好,独来独往,她的记忆只停留在日本长崎,停留在那里所带来的不可抹灭的创伤中,最终她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景子的死是悦子叙述发生转变的重要节点,悦子开始回忆过去,开始试图走出困境,作为母亲的责任使悦子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她把景子的死归咎于自己的过失:对景子照顾不周;不考虑景子的想法自私的把她带离日本;在英国组建新的家庭以后关系不融洽等等。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逐渐意识到悦子一直在回忆叙述她和景子在日本的生活。小说以妮基来乡下看望悦子开头,妮基的到来使悦子不可避免的回想起以前的事情,这个回忆使悦子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带景子移民是否正确,她开始用带有浓厚的哀怨的情绪进行回忆。回忆中的长崎刚被原子弹轰炸过,战争使这个地方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她迫切的、想一刻不停的逃离这个使她悲伤的地方,战争给悦子带来的心理创伤一直在延續,使她在创伤中分裂出不同的人格面具进行自我伪装,而景子的死击垮了她内心所有的矛盾和假面。对于悦子来说,创伤是一直存在的,它不是一直以表象存在,而是由某一些内在或外在因素引发的,只是存在的形式是与原始状态不同的,这种非原始的形式,就是心理创伤。战争给悦子带来的心理创伤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使她在创伤中分裂出不同的人格面具进行自我伪装。
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长崎,经历了原子弹的袭击,民众所受到的灾难也像核辐射一样,由个人反应到家庭再由家庭反应到社会中去,此时的长崎经历着集体创伤,每个人都是创伤的经历者、讲述者,悦子和景子作为这场灾难的代表性个体,她们所表现出来的保持自己的创伤,压抑自己内心痛苦的感情方式,也是那个时期整个日本的现状。
二.创伤记忆中的分裂人格
荣格认为:“人格最外层的面具掩盖了真我,使人格成为一种假象,按着别人的期望行事,故同他的真正的人格并不一致。人靠面具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一个人以什么形象在社会上露面。”[2]个体为了获得心灵上的成熟与慰藉,往往塑造一个或几个具有弹性的人格面具来满足自我与社会相处之间的和谐关系。
悦子不敢直面自己的罪恶,为了掩盖伤痛,她在讲述中塑造了“好母亲”、“好妻子”的形象:她遵从日本传统社会准则,期待新生命的到来,携带者“好母亲”的面具;对丈夫言听计从,携带着“好妻子”的面具,以此维系着家庭的和谐关系。但是在文章的多处细节以及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悦子身上包含“天使”和“魔鬼”的双重人格,她所塑造的人格面具也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逐渐显现。
小说以悦子在日本的生活以及与邻居佐知子、万里子母女的交往为主线,在小说结尾处惊然揭示佐知子和万里子其实都是悦子塑造的人格面具,佐知子就是悦子,万里子就是景子,悦子人格的“天使”性由作为悦子时的她表现,“魔鬼”性则由作为佐知子的她所表现。悦子的人格塑造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母亲时塑造的人格面具;二是作为日本传统女性时塑造的人格面具。
首先是“母亲”形象。即将要做母亲的悦子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天使”面孔,在与佐知子、万里子的交往中,她表现得格外称职甚至越界:关注万里子的打架事件;当万里子消失时,不顾丈夫反对半夜去寻找;得知佐知子要带万里子离开日本移民美国时,她反复追问这么做对万里子是否有利,完美展现了悦子身上作为母亲的和蔼可亲特征。相反,她描述中的佐知子是一个有些专制并且很少陪伴女儿的母亲,她总是以“一切都是为了万里子好”作为自己的借口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她的冷漠主要表现在对万里子的态度上,万里子每次出走她都满不在乎、毫不担心,并向悦子表示“她很快就会回来了。她想待在外面就让她待在外面吧”[1]这表明对万里子的出走佐知子已经习以为常。在战争期间,万里子亲眼目睹了一个女人溺死自己孩子并且自杀的全过程,她反复提起“那个女人”,但佐知子却始终持有不相信、不重视的态度,并向悦子解释这是小孩子惯用的撒谎手段。更令人恐怖的是,小说尾部,佐知子淹死了万里子的心灵寄托——小猫,“她把小猫放进水里、按住。她保持这个姿势,眼睛盯着水里,双手都在水下”[1],与万里子口中的“那个女人”杀死自己孩子的手法如出一辙,这将整个故事以及万里子的反叛情绪推向了高潮。悦子塑造的“好母亲”人格在佐知子身上被完全撕碎,呈现出“恶魔”的一面。
人们在犯下自己不愿承认的错误之后,往往会选择塑造与自己本身性格截然相反的人格面具,在这种人格面具的“保护”下否认或者遗忘自己的错误。我们始终觉得悦子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她塑造了佐知子这一人格面具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悦子其实也是佐知子塑造的一个人格面具,可以将她看作是佐知子不愿面对自己的过去,从而塑造了悦子这一完美形象来掩盖事实。
其次是“日本女性”形象。悦子在叙述中竭尽全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典型的日本传统女性。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描述在日本“等级制以性别、辈分、长嗣继承等为基础,它在家庭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3],即便是夫妻之间也有很浓重的等级制度的存在。作为妻子的悦子,在家庭中扮演着“好妻子”的形象,即使是怀着孕她也依旧要给丈夫端茶送水、准备晚餐,丈夫冷漠、严肃的态度没有改变悦子的传统观念,她严格遵循着传统的等级制度,始终保持着作为人妻应有的“卑微”姿态。
通过小说迷雾的一步步揭开,我们逐渐明了佐知子其实就是悦子塑造的另一个自己,另一个含有反叛人格的自己。佐知子桀骜不驯,不断打破日本女性的封建传统,实际上不留情面地撕毁了悦子“好妻子”、“好母亲”的人格面具。佐知子是一個完全冲破传统束缚的女性形象,在那个年代,别人眼里的她是不可理喻的,是完全叛逆不检点的,她对此却满不在乎,为了结束在日本苦闷、孤寂的困境生活,她又一次在万里子身上展现了她“恶魔”的一面,她把万里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去找弗兰克,以万里子为逃离日本的理由,“对我来说,女儿的礼仪是最重要的,悦子。我不会做出有损她未来的决定”[1],这实际是她为了自己的私欲找寻的借口和支柱。
二十年前的悦子在处理和家庭、社会的关系时选择塑造不同的人物面具来隐藏真实的自己;二十年后的悦子为了逃避战争给她带来的延续创伤——景子自杀,又塑造了双面人格来推脱责任,只有在人格面具的隐藏下,她才有勇气面对接下去的生活。直到小说最后,悦子才开始直面自己的错误,并想努力走出精神上的困境。
三.分裂人格下的自我选择
人格面具认同是个体正常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格是由不同的面具共同构成的,一个面具就是一个子人格。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为各种社会交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格面具的产生,不仅是为了认识社会,更是为了寻求社会认同。
在战争的创伤中,悦子塑造了不同的人格面具,试图在面具下隐藏自己。在战后的选择中,她依旧戴着面具对直面还是逃避的问题进行选择。悦子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别人”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佐知子这一人物是否真正存在,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悦子精心编织这样一个故事网,目的是想在隐藏自己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减轻内心的罪恶和自责。石黑一雄说:“某个人觉得自己的经历太过痛苦不堪,无法启齿,于是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讲自己的故事”[1],这也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叙事方式。悦子在经历巨大的战争创伤后选择逃避,通过回忆与现实交叉的方式,以讲述在日本时的邻居佐知子与万里子之间的故事从而来反映自己在日本的生活。
悦子在战后作为“好母亲”面临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为自己考虑还是为女儿考虑。从佐知子方面来看,她始终觉得带万里子离开日本是完全从女儿的角度出发的,是完全为了女儿好,她戴着“好母亲”这个面具考虑自己的未来,她对这一面具的依赖已经到了难以摘下的程度。
悦子的作为“好母亲”、“好妻子”的第二个选择是逃避还是直面。失去丈夫、家园都使她痛苦不堪,她不愿正视过去,所以她塑造了佐知子和万里子这两个人物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悦子在小说中有两个层面的身份:一个是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一个是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从讲述者层面出发,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件都是通过悦子来讲述的,我们所了解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都是悦子所想让我们知道的。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情节,整片布局分散杂乱,主要通过主人公悦子回忆穿插的方式进行叙述,时间也是在不断跳动的,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条故事线:故事线一的地点在英国,事件发生在现在,讲述了悦子不顾及大女儿景子的利益与想法,执意带着景子移民英国,景子在英国的生活很不顺畅,缺乏关心,与悦子关系不佳,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苦闷中,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故事线二的地点在日本,事件发生在过去,以悦子作为第一视角讲述了悦子的邻居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她们都遭受了战争的创伤,佐知子对万里子毫不关心,不顾万里子的想法,执意要带万里子去美国,甚至溺死了万里子心爱的小猫这一事件。从参与者层面出发,悦子参与了故事的始终,与佐知子、万里子母女有交往的对话,使她编造的故事更具真实性,更让人信服,直至文章最后我们才发现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是悦子为了逃避为了自我解脱而编造的。
石黑一雄曾说:“创伤已经造成了,没有愈合,但也不会继续恶化,但是伤口还存在。世界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你却可以通过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者自己对世界的观念来重组纾解或者适应这个世界。”[4]悦子开始走进景子原来的房间,开始站在景子的角度对自己进行审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对以后的日子保持着她原有的期待,她认为“这里最像英国”,我们可以说这里最像她想象中的英国,有熟悉的家人的气息和自己原先对移民生活的期待。
战争带来的灾难性是巨大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活在战争造成的创伤中,她们都呈现出一种病态心理,悦子努力想扮演“好母亲”、“好妻子”,在严肃的、毫无生活激情的丈夫面前,她温顺、善解人意,展示了“天使”的风范,然而长时间的压抑苦闷生活,最终使悦子“魔鬼”的一面爆发,促使她塑造了佐知子这一形象,由佐知子来代替悦子做她所不敢做的事情。这两种人格的相互交织相互隐藏,使悦子的人格越来越分裂,她想要对此进行反抗,而反抗的牺牲品就是景子。整个故事都充满了真假难辨的趣味,人物的多重性格以相互对话的形式存在,不同的人格都怀着各自的目的。但是不论各个人格所抱有的目的是什么,总体来说人格的存在就是为了协调人的内心,协调内心与世界的冲突,从而达到心灵的平静与和谐。
可见,在构建人格面具时,需要处理好身心结构、自我理想和集体意识三方面的关系,以达到自我与世界、自我与心灵的和谐,避免人格中的不健康成分造成的心理问题。并且对人格面具的使用要适度,不可过度依赖,要能够超越人格面具、回归真实。
参考文献
[1](英)石黑一雄著.张晓意译.远山淡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6,216,110,50.
[2](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59.
[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王纪卿译.菊与刀[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28.
[4]Allan Vorda Face to Face: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Novelists.Houston:Rice UP,19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