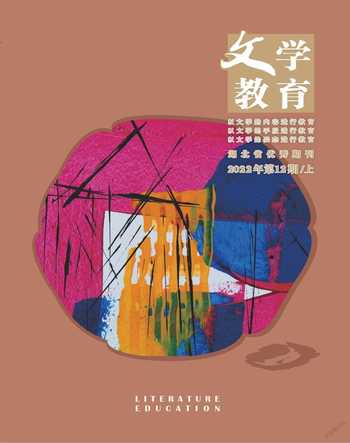杜拉斯小说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朱婉莹
内容摘要: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总是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充满了主观的情感变化和身体感受,她以在殖民地生活的经历为背景写下了《情人》。她在“新小说”艺术上进行了探索,而《副领事》是她探索得来晦涩难懂的结果,她称这本书是她“生命中的第一部”。本文试图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第一世界女性笔下的女性角色进行分析,以探讨她们在殖民社会和殖民文化压迫下的困境。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 《副领事》 《情人》 玛格丽特·杜斯拉 女性形象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蕴含多元文化的理论,是文学批评家们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思和改写中逐步兴起并完善的,更侧重于关注第三世界的男性的妥协与抵抗,沉默与发声,从而第三世界女性的声音沉没在地底。后殖民女性主义是由后殖民主义派生出来的,其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女性主义的崛起,是由侧重于研究族裔中处于“他者”地位的人的的后殖民理论以及发对男性压迫,强调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相结合发展而来。20世纪80年代,灾后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后殖民女性主义开始兴起。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作品《关于中国妇女》中作为西方女性代中国女性言说,并对其进行审视;贝尔·胡克斯指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批评中回避了种族问题,他们的女性主义是白人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指出男权中心主义主观地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臆测,使得其身份与特征“变形”;斯皮瓦克认为“第三世界妇女”其实是被西方的女性主义者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重构的“虚构型”、“自恋型”的他者,这也是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她们都被打上父权化、殖民化的标签。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第三世界女性在历史中是透明人,她们没有属于自身的历史,又在种族、阶级、性别、殖民等多重压迫下,逐渐丧失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利,逐渐失语。后殖民女性主义不同于后殖民的主流思想上对女性声音的忽略无视,也试图消解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白人中心化倾向。本文拟在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照下,探析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和《领事馆》中的女性形象,揭露第三世界女性在殖民中心主义的压迫及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女权主义的隔绝下失语的普遍现象。
一.玛格丽特·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殖民者的身份在法属印度支那生活了十八年,直至在巴黎定居,她才从那种文化夹缝中逃离。作为一个西方人,她在东方出生并在东方的文化环境下成长,杜斯拉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她是居住在殖民地的殖民国家(法国)公民,固守着白人优越至上的价值观;却由于家境贫困,使得她难以融入有钱的白人阶层,甚至通过与富有的华裔男人交往来换取钱财。这样文化边缘人的身份赋予了她的作品以双重视角。
她的父母在殖民区从事教育工作,在玛格丽特七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受当局哄骗倾尽家产买下一块不能耕种的盐碱地,种种变故始料未及,使得这个本就处于底层的白人家庭陷入困境。即使是处于窘困的环境中,玛格丽特的父母始终叮嘱她不能忘记自己的白人身份。“亨利·多纳迪奥在来西贡以前就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他是法国人他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因此必須有那种白人至上的思想。在黄种人面前必须表现出髙人一等的气势。”[1]7在印度支那生活的岁月使得她对那片土地有一种故乡的归属感。“我现在发现这种对法兰西种族,请原谅,对法兰西民族的从属是错误的。……您要知道我们是越南人,而不是法国人。”[2]27但是父母对她的教导、当时她们所处的环境——他们在西贡的住所是白人居住地、她与本地人不同的相貌以及她殖民者的身份一直提醒她,她不属于这片土地。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了“混杂性”这一概念。从杜拉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文化身份的“混杂性”,她的作品不但充满了异国情调,弥漫着浓郁的东方神秘气息,而且还表现出一直在漂泊的无归属感以及流浪的孤独感。她在文化夹缝中艰难成长,她边缘化的文化身份赋予她独特的生活经历与写作视角,这也使得她能够以西方第一世界女性的视角去“凝视”与书写她眼中的第三世界的女性。
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一)《情人》中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体意识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3]96尽管杜拉斯在一开始极力辩解,她并不认为这部小说中有自传体成分,但我们仍可以在《情人》这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她总是带着一顶男士平檐黑色呢帽,因为她发现“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2]14她与大她十二岁却柔弱胆怯的中国情人相恋,她的头脑清醒“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就像这样,总有什么事发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2]27在小说中,“她要”、“她行”、“她知道”、“她懂得”、“她看”的陈述比比皆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上来说,玛格丽特觉醒的女权意识在她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海伦·拉戈奈尔是“我”在西贡寄宿学校唯一的朋友,“我们是这个公立寄宿学校仅有的白人。”[2]17对于海伦的描写更多的聚焦到了她的身体上,“我”瘦弱胸部平坦,没有达到我心中情人的标准,而海伦的身体是“万物之中上帝拿出来最美的东西”“她的双乳浑圆,皮肤红润带有健康的棕色”。“我”因对海伦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有学者认为,海伦是“我”的化身,是“我”的自恋情结。在孤独的境地中,“我”将自己唯一的好友当做镜像,不断地欣赏并陷入爱恋。但是这个角色就如同所有被凝视的第三世界妇女一样,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她没有想法、没有故事,是一个只等待着和“我”的会面,让“我”燃烧欲望的工具,她一直被禁锢在寄宿学校里白白耗费着自己的生命。海伦这个混血姑娘,她的外表因为结合了西方的特点而不同于“我”眼中的东方女人,但她内里却无可避免的属于东方,她“和堤岸那个男人的肉体是同一的……海伦·拉戈奈尔是属于中国的。”[2]19却可以从她最后沦亡的结局中看出,与有着女性意识的白人女性不同,她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在作品中她并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一个陈设品,或者说只是承载欲念的客体,不需要赋予她反抗的本能,所以她永远无法挣脱被摆布的命运。“我做的,她都做不了。”[2]21海伦正是白人女性想象中的典型东方女性形象,她们都失去了言说的权力。海伦这个形象与“我”这个白人女孩产生了对比,从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了玛格丽特作为殖民者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妇女的优越感。
而《情人》中的其他东方女性角色: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的女管家,她没有大名,只有一个绰号一样的名字——阿杜,在女主人公“我”的描述中,她忠心耿耿,即使母亲想抛下她回到法国,即使她付出再多劳力也没有工钱可拿,即使她险些被“我”的大哥侵犯,她也没有选择离开“我”的母亲。与阿杜相关的描述极少,但从寥寥几笔的描述中,她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父母,没有家乡,也没有发言权,她成了一个干活精细的附属品。第三世界的女性就是这样沉没在历史的地表之下,处于“臣属”的处境,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5]58。
《情人》中出现了一个女疯子,这个女疯子于“我”而言是恐惧的记忆,恐惧的程度严重到那个女人用手轻轻碰到“我”,“我”就会“陷入比死还要严重的境地,我就要陷于疯狂。”[2]65这个女疯子也是《副领事》的女主人公之一,作为书中的重要角色她依然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故事是由彼得·摩根这个白人进行叙述的。在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斯皮瓦克提出了她的观点,她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往往无法自己发声,她们不得不被他人代言——以一种扭曲变形的形式。在多重权力的压迫之下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她们受到的压迫不仅仅来源于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操纵与压迫,也来自于西方第一世界白人妇女对想象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殖民化。彼得·摩根用自己的语言代替疯女人说话,“彼得·摩根现在想用自己凌乱的记忆,来取代女乞丐荒废的记忆。”[2]32用自己的想象代替疯女人的经历。因为疯女人是无名的,也是“失语”的,她没有姓名。
无论是《情人》中的疯女人,还是《副领事》中的女乞丐,都是别人给她的称呼。名字作为自我身份的重要标志,被“她”、“疯女人”、“女乞丐”所代替,也象征着她的权利——无论是女性的性别身份权利还是她发声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二)《副领事》中的女性形象
疯女人是一个因未婚怀孕被母亲赶出家门的印度少女,她在印度支那四处流浪,她分不清方向,找不到食物,“白天黑夜,孩子都在不停地蚕食她”[3]35,她被饥饿支配,住在废弃的山洞之中,像一只野兽。在父权制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失贞、失足怀孕是不可原谅的罪孽,于是她因为失贞而被母亲视为耻辱,被家人遗忘抛弃“如果你回来,妈妈说,我就在你的饭里放上毒药,把你毒死。”[3]36带有这种观念的母亲是父权制度下的产物,通常也是由年长的女性充当刽子手,把语言化作利剑,用棍棒将亲生女儿逐出家门。在被母亲辱骂驱逐的过程中,她依然一言不发,没有辩解和解释的权利。女乞丐将孩子像商品一样摆在集市,希望能将孩子送出去,在这个女孩以后,她还生下其他孩子,可都被她丢弃,带着孩子她找不到事情做,即便是没有孩子的时候,她依然找不到活儿,她有时候可以靠着沦为妓女过活,可也养不活孩子。囿于种族的歧视和性别的限制,她没有办法干活养活自己,在四处流浪的旅程中很多情况导致她精神错乱。
在殖民地社会,白人会将种族差异合理化,并且在他们的文化中心理论影响下本能地认为自己比其他人种更为高级,“白皮肤的、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7]40。这样的白人优越论对于殖民地社会中白人来说是共识。玛格丽特的作品中白人对被殖民地的压迫是潜移默化的,他们为了构建自己的权力话语,强化自身意识形态而构建出属于从属地位的他者形象。总是以救世主的形态出现,带着高高在上的怜悯。
将女乞丐的孩子收养的白女人和白女孩在玛格丽特的笔下就是带着圣光的拯救者——拯救次等民族的优等种族,白女孩总是“笑着面孔”,白女人给她皮阿斯特,派遣仆人给她送来饭菜和药。白女人和女孩住的别墅亮着灯光,女乞丐睡在径边的树影下;从别墅里传出话声,女乞丐想起家乡,想起她的母亲在打骂孩子。
《领事馆》中的另一个女主人公——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大使夫人,与疯女人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她身着黑色的双层罗纱紧身长裙,手里揣着杯香按,面含微笑。”“她薄薄的眼皮,眼睛适中明亮,像雕塑的眼睛那样轮廓分明。”[3]65她嘱咐人将剩饭剩菜留下给加尔各答饿肚子的人,她以凝视者的角度将卖孩子的故事讲述给彼得·摩根,彼得又将这个故事插入女乞丐的人生故事中,在这里,彼得是讲述故事的人,他掌握了话语权能够将一切异己的东西凭他的臆断贴上标签,于是女乞丐被贴上疯癫的、可怕的标签。与幽灵似的女乞丐不同,她的穿着举止优雅,人性也闪着高高在上的圣光。西方女人借助东方女人“她者”的存在更清楚地看到了自身:她们的身份、她们的魅力、她们的优势。
杜拉斯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在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之中,作为女性,她受到男性的压迫,尽管她情感层面上对第三世界妇女产生了同情,但这同情并不足以颠覆杜拉斯作为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作为一个在殖民地生活的贫穷白人,殖民地的白人社会并不会接纳她。在这样的夹缝文化影响下,她难以摆脱预见的种族偏见。因此,我们看到杜拉斯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夸大、扭曲东方,使其神秘化、妖魔化,這无疑表现出了她的帝国意识。
在莫汉蒂看来,所谓“女性共同体”只是一个概念,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妇女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可分离性是真实存在的。杜拉斯的创作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当不同的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共存、相遇时,只有去除那些猎奇的、居高临下的、自我中心的目光实现真正平等的交流;只有舍弃中心—边缘、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实现互为主体的对话;只有放弃任何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文化孤立主义,才能使我们的世界向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目标靠近。
参考文献
[1][法]克里斯蒂娜·布洛-拉巴雷尔.徐和瑾译.杜拉斯传[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7.
[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王道乾译.情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王东亮译.副领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李轻松.女性意识[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96.
[5]户思社.痛苦欢快的文字人生—再格丽特杜拉斯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7.
[6]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58.
[7][英]瓦莱丽·肯尼迪.李自修译.萨义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0.
[8]任红红.边缘文化的代言人——杜拉斯《副领事》中的女乞丐形象分析[J].译林,2012(06):194-196.
[9]刘岩.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域:以斯皮瓦克的语境化性别理论为例[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01):293-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