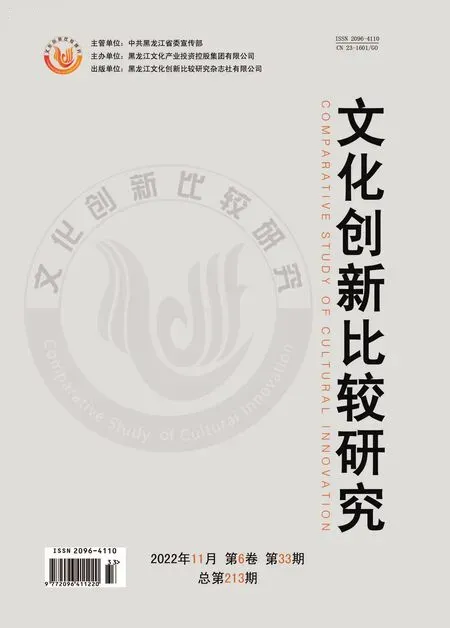比较文学之民族国家视阈研究的深耕与拓展
——评侯洪《诗学生成比较研究:以中法近现代诗学为视角》
陈佑松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四川大学侯洪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诗学生成比较研究:以中法近现代诗学为视角》出版了。该书以中法近现代诗学的缘起与发展之比较作为研究对象。法国近现代诗学起源于16世纪,而中国近现代诗学的兴起却要到20世纪初。两者相差四百年,其可比性在哪里呢?难道竟是坊间嘲笑有些比较文学研究者的“阿猫”比“阿狗”、“关公战秦琼”吗?
稍一浏览,这一疑问便豁然而释。原来作者选择了一个对于比较文学理论来说极为重要且具有历史感和问题意识的视角:比较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关系。分析起来,作者的理论基础有二:其一,现代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充分表征和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涵;其二,比较文学的根基来自民族国家文学(即国别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其实,早在2006年,侯洪教授就“首次将中法两国诗学在整体上加以把握”,“首次将中法诗学比较归结到作为民族国家文学建构上”[1],因为比较文学之比较,首先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学的比较。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之体系内,比较文学才得以成立。
所以侯洪教授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就有两个目标:首先是要论证现代诗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关系;其次通过中法现代诗学生成之比较,证明东西方现代文学思想都存在着 “民族国家建构”这一重要维度。此即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
比较文学的基础是民族国家,但是如果没有世界文学的目标,也无法成形。这也可以说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张力的体现。所以作者分别论述法国和中国现代诗学兴起之缘由,可以说明比较文学的“民族国家认同”要素,而中法对勘比较却可说明比较文学所具有的全球化视野和“世界文学”的内在规定性。所以,本课题的选题对于廓清比较文学的性质与学科发展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接下来我们就上述两个维度进行讨论。
1 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文学的缘起
作者分别选取了诞生于16世纪的法国文学理论著作《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写作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论名篇《文学改良刍议》进行了细读分析。
在讨论《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以下简称《保卫》)时,作者认为:“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法兰西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跨入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大门,这意味着它在思想及知识领域已孕育出一个崭新的形态,故《保卫》被称为法国文论史上‘第一部近代的文艺批评宣言’是理所当然的。”[3]它“在法国近代民族国家文学的形成与确立中,起到了奠基性、开创性的作用”[4]。
现代“民族国家”是人类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组织形式,它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逐渐取代古代“帝国”和基督教普世帝国,最终成熟于19世纪中叶。通常认为,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标志是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于1643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合约”。会议的成果是形成了最初的国际关系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础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合约”确立了均势条件下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要素。虽然“和会”召开的时间是17世纪中叶,但是民族国家的酝酿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除了资本主义萌芽、宗教改革等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兴起。在意大利是14世纪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和《论俗语》,在德国是15世纪末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在西班牙则是16世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法国当然就是17世纪拉伯雷的《巨人传》和七星诗社的《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印刷资本主义”密切相关。随着印刷技术和印刷品市场的繁荣,正是报纸、小说等印刷品的大量扩散带来了民族认同。而这些印刷品的基础正是民族语言文字。人们在阅读相同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体的想象”。
侯洪归纳了《保卫》的几个方面的特点,都指向了现代法语的形成与现代法国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
第一,倡导民族文学的自主性与尊严的文化战略。作者引用了杜贝莱在《保卫》中的论述:“他要人们‘把古希腊、罗马的著作束之高阁……要把死的语言变成活的语言。’”“倡导用‘法语来写作’,用民族语言 ‘完全可以写出我们满意的最好最美的作品’,‘不要使用拉丁或希腊固有名次’,在翻译外国人名字时,尽量用符合本国习惯的译名。”作者对此评论道:“正是《保卫》中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促进了法国俗语文学的勃兴,《保卫》不愧是一步坚定的民族主义诗学。”
第二,对诗歌本质与形式的思考。作者注意到,《保卫》中,“专章论及法国诗歌表现形式的重要元素韵律,与它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它首先指出法国诗歌韵律的特征性,它不同于希腊、罗马诗的格律诗考长短音节的差别,而是靠音节的数目”。
第三,民族语言的现代性创构:语言革命。作者总结认为,“《保卫》中大量的篇幅是讨论民族的新诗的语言。它的重要性在于创建一套有别于拉丁语官方系统的新体系——借鉴淡定的‘俗语’革命之思,让中古法语走向近代发育,注重近代法语诗歌语言层面的开拓。抱着‘使法语高尚化,使其优雅、丰富、完美的努力’,创建本民族的诗歌语言”。
从以上的讨论,读者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晚期,法国已经培育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将为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将为17世纪法国建立集权国家,崛起为欧洲第一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作者对比法国的《保卫》,比较了中国近现代文论的第一部作品——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作者认为,“胡适在此文中倡导的‘白话文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不仅预示着这是一项伟大的语言革命,更是一场全新的文化形态的革命。它意味着中国的全部文化都必须面向现代化这一新的历史图景”。
这一新的历史图景是什么呢?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如果说,民族国家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内生发展的现代国家形态,那么,这对于中国而言,则是外源性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形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朝上国”。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才面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但是,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清王朝才真正理解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在恭亲王的主持下,清政府成立了“同文馆”,翻译西书,特别是聘请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了《万国公法》(《国际法》),让清朝官员了解到世界依然不同,此谓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成立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中国开始了现代转型。此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救亡”运动,其实都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阶段。
按照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中国近代“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上的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便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
侯洪对《文学改良刍议》分析认为:“第一,提出了新文学的本质论——言之有物,这个‘物’针对传统文论的‘文以载道’说。”“第二,确立新文学的认识论基础——进化论的文学发展观,即‘文明进化’和‘历史进化’的意义。”“显示出与严复早期思想,即《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渊源关系。”“第三,推行语言革命与‘活的文学’(白话文学)。”“第四,以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眼光来建构现代文学。”
理解《文学改良刍议》的这几个特征,恐怕还需要理解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之本质。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对勘梁启超与陈独秀的议论,可知梁启超所谓的“知文化的不足”引发了“伦理的觉悟”,即“伦理革命”。而伦理革命就是文学革命的本质。在声援和清晰阐释《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说:“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5]陈独秀在文章中将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并举,并将胡适的“文学改良论”推为“文学革命论”,其目的就是要从“文学革命”着手,展开“伦理革命”。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那么激进,但其通过文学变革实现伦理变革的思路是一致的。侯洪在其论著中所提炼的 《刍议》之四个特征有此意。
第一,新文学的本质论是“言之有物”: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文论的“文以载道”。这就是陈独秀的“革命论”中所言“推到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其伦理意义就是 “世俗化”,即将一种古代儒家天人感应之先验“道”、一种神义论之 “道”转变成为对现实和世俗的世界的关照。而现实关照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个人的权利伦理的确立。按照现代政治哲学的看法,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要素是“主权在民”,而非“君权神授”。这就意味着,个体权利伦理的确立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基础。
第二,新文学的认识论基础是进化论。这是新文化运动,或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内容。古代中国没有进化史观,只有循环史观。现代文学的要改变这样的史观,要确立一种创新的思想、竞争的思想。实则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
第三,推动白话文运动。这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我手写我口”。白话取代文言,是知识民主化的重要路径,这和文艺复兴欧洲的“俗语运动”是一致的。它促动和强化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第四,“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眼光来建构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建立在民族国家文学的基础上的。有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意识,就意味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从比较文学出发建构民族国家文学,同时也是从民族国家文学理解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2 平行比较中法文学现代性缘起的意义
在比较文学研究史中,“影响研究”是一种历时研究,它意味着一种因果逻辑关系,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关系”,是时间发展的结果。而“平行研究”则意味着一种空间的相似性,更注重探讨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的基础就是在某一范式或某一维度下,通过不同国家或文明的文学的比较,可以揭示出一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在这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所谈到的人类“轴心时代”理论可以作为参照。在他看来,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里,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同时出现了重大突破。雅斯贝尔斯正是通过平行比较,发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某种普遍性。
侯洪通过平行比较法国和中国现代文论的起源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其实说明了一种重要的普遍问题:各文明之现代文学的建构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与民族国家建构相辅相成。
詹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一种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6]他谈到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鲁迅的《狂人日记》,透过精神疾病而指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吃人”本质。
詹姆逊强调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时期,第三世界的敏感的民族主义意识。他当然是为了批判这种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不过,如果我们把时间长度放大,我们却会看到,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现代转型的初期,文学都承载了民族国家寓言的重要任务。上述《保卫》和《文学改良刍议》,虽然相隔四百年,但都是现代转型的产物和表征,同时它们也都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17世纪法国通过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成为欧洲的第一强国。法国从哲学到文学建立起了一整套支持国家秩序的理论系统。笛卡尔的哲学虽然看似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却高举唯理主义的大旗,应和着时代的精神气质,与政治理性主义遥相呼应。文学上则是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诗学,主张文艺模仿“自然”,而“自然”是人性和宫廷。不过这里的人性是理性的人性,宫廷则是理性人性的表现。文艺模仿自然就是文艺模仿理性。所以戏剧的形式应该符合“三一律”,应该是理性和责任高于情感,当矛盾不能化解时,君主通过机械降神完满地解决一切困难。通过哲学、文学对政治的支持,法国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法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论的开端同样具有“民族国家寓言”的特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侯洪通过平行比较研究,其实是揭示了世界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的普遍的“寓言关系”。
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细究起来,中法之间现代转型毕竟还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影响关系”。也就是说,在平行研究之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影响研究”。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外源性”的,是在西方殖民势力(包括法国在内)达到高潮的19世纪中叶,被迫纳入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中国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强烈的断裂感是法国没有的。随着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式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文化上也开始经历着一个强烈的震荡过程。“全盘西化”似乎一度成为现代中国的必由之路。与“民主”“科学”相伴随的是思想、文化和学术的西化。所以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与文艺理论之兴起是受到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思想的影响的。
比如,王国维将西方启蒙哲学和美学介绍到中国,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学科的建立。马建忠将西方的语言理论介绍到中国,建立起了西方范式的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胡适、冯友兰等人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起了“中国哲学”。现代新儒学和学衡派则试图熔铸中西,开出新思想。
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的现代转型几乎就是在西方的坐标系下展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转型所存在的困难。姑且不谈殖民和后殖民的问题,就学术本身而言,这种转型本身就有着削足适履的问题。如西方语言学是建立在西方屈折语的语法结构甚至哲学结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语言与之相去甚远,用西方的语言学穿凿中国语言现象,很难完全适合。再如,以西方哲学范式来裁剪中国古代思想材料,强行创造一种逻辑,正是后人对胡适、冯友兰的批评。至于现代新儒学诸家存在的调和中西也存在着许多以西释中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曹顺庆先生首提“中国文论失语症”,激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调。但是从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来看,这绝非无稽之谈。在我们看来,西方思想的根基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古代形而上学认为世界有一永恒不变、不动的根基和本质,以之为逻辑起点,推演为一个巨大的哲学和神学体系,是为“本体论”。现代形而上学从笛卡尔经德国古典哲学(康德、费希特、谢林至黑格尔)完成了“哥白尼式的转向”,将世界的主体转为“人”。这就是现代主体性哲学,也就是“认识论”。
中国思想却从来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结构,就好比中国绘画从来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儒释道三家,都不会执着于实体化的根本“存在者”,反而更接近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但是现代中国思想的转型却深受西方现代认识论哲学及其背后的形而上学系统的规范,一定要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材料推上“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法庭上进行审判,与之不相符合的就会被驱逐出境。这所导致的结果正如曹顺庆先生所言:“套用西方的概念、处在西方的话语和理论模式中的研究,也会产生诸多问题,中国文学与文论原有的深刻内涵无法在这种西化模式的研究中被还原和被理解。”[7]
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思想转型是深受西方的影响的,就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一样,中国的现代话语体系是西方式的,所以,才有学者提出“失语症”的警告。
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中法文学起源和民族国家之关系,从平行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性,即现代化转型中,文学与现代政治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的共同性;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我们则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和政治体制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如何全面地扩展到东方世界。换句话说,平行研究所呈现的现象背后是影响研究揭示的根源。
3 跨文明研究:中法文学比较的新空间
不过,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西方进入后现代,另一方面,则是东方,特别是中国开始崛起,使得国际关系格局和世界文化的多极化与绝对不平等的关系出现了调整与变化。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后,后现代逐渐登场,很快取代“现代性”“主体性形而上学”。人的地位被质疑和瓦解,随之而来的就是形而上学的模式本身被批判和攻击。到今天,批判形而上学几乎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和思想的基本论证起点。如此一来,中西对话就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有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其实早在海德格尔就对中国的道家思想有强烈的兴趣,他和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故事尽人皆知。海氏之所以对中国道家情有独钟,就在于他的现象学存在论力图批判西方形而上学所造成的“对存在的遗忘”,拆除形而上学的大厦正是他的目标,而他发现东方的道家文化竟然从来没有形而上学,那天行健的缥缈之“道”竟然如此符合他所理解的“存在”。
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更是在此领域深耕。从《迂回与进入》到《大象无形》等一系列著作,对中国文学和艺术展开了现象学研究与透视,其目的正是要迂回到西方哲学中,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参照,捣毁西方形而上学的体系。
从文化政治的现实条件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解殖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崛起,其中中国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又率先走出冷战阴影,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西力量对比发生了百年来最大的转变。西方文化不再可能随政治强力侵入中国。而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获得了成长。东西交流,文明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于是,超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跨文明研究”实际上成为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并不意外的是这一阶段的观念由中国学者提出来。2002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会议”上,曹顺庆先生明确提出把几年前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所归纳的“跨文化研究”改成“跨文明研究”[8]。我们认为,曹顺庆先生所提出的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理论强调了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而要真正形成平等的交流,如果没有一种平等的文化政治基础自然不可能,而没有两者在哲学范式上的共同平台,也很难对话。正如我们上面所说,20世纪后半叶,这样的基础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中法文学比较研究也有了新的空间和领域。
对此,侯洪在《诗学生成比较研究:以中法近现代诗学为视角》的结语中,专门讨论了“中法诗学的对望与互鉴”。作者说:“我们还应看到,法国现代诗学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法国文学的危机或诗学的危机症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表现出‘信仰的危机’,故而结构主义诗学兴起;二是传统诗学的‘合法化’危机,故而解构主义及后现代诗学登场,它是对西方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经典传统的反叛,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与现代性启蒙表示怀疑,用审美的现代性来对抗启蒙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过去被遮蔽的应加大力度总结和反思:一是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被无限放大后,所导致的诗学生成维度的薄弱或缺失或单一性或封闭性;二是西方文明的冲击,现代文化的兴起所导致的传统断裂,今天传统儒学的现代性怎样在现代诗学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体现中国特色的重要一极,从而使中国现代诗学参与到现代世界文化意义的建构中去,其现代性的转换(儒家人文精神)与中国诗学的复兴,正是20世纪后半叶新时期以来至今的诗学要努力思考的。”
4 结语
综上,侯洪教授这一学术成果研究视野开阔,从国别文学的比较到文化比较的深层结构,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意识与学术创新意识,将民族国家文学及其文论的生成与发展,与全球现代性的共生性和多样性的历史发展格局相关联,凸显了中法诗学生成的某种同构性症候和各自诗学的独特品格与特征,同时,也敏锐地关注到中法诗学创新发展的边界扩张,即文学艺术的交融与跨界、诗学生成与媒介文化和地缘文化的作用与互动,如此种种无论是在比较文学与文化,还是在世界文学的国别研究中都具有理论创新和现实层面的中外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