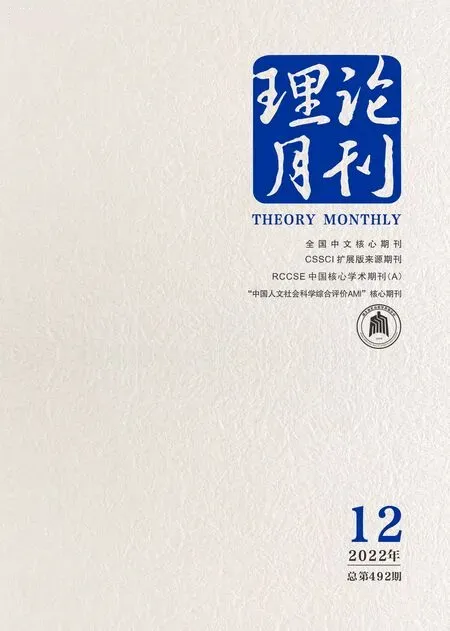论二陆赋学与六朝赋的诗化
□唐定坤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1)
六朝赋的诗化是唐前诗赋互动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文学思想和文体学领域的重要命题,意指在特定的文学思潮中,赋受诗的影响而产生文体的位移和趋同。这一命题可以从诗化表现和时段界定两个维度来理解,目前学界的认识大致相同,就前者而言,约略可分为结构内涵的抒情化、篇幅的简短化、语言的诗化探索三个方面①可参见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28;王琳.六朝辞赋史[M].西安: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2014:23—25.诸家所论略有不同,要不出这三个方面。;就后者而言,则聚焦于汉末至建安的初起和齐梁的成熟两大阶段②此分别以徐公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J].文学遗产,1992(1):16-25和韩高年.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J].文学评论,2001(5):141-148二文为代表;而论建安诸家赋诗化的文章更是多见,此不详列。。论者多就传世诗赋作品的形态和性质进行概括,同时,受近代“文学自觉”说及以抒情为内核的诗学中心文学观的影响,尤侧重于建安时代的探讨,而相对忽略注重形式美学的齐梁时期,庶几无视两晋的“过渡”阶段。其实这种今人“赋的诗化”的看法,未必符合文学史的实情,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厘清:一是论所谓“赋的诗化”主要指向赋的抒情化,尤以五言诗的影响为多。而诗之初始发展本自乐府叙事,至文人拟乐府趋五言整齐化(转抒情),再至文人五言(以抒情为中心)。回看汉代以赋为主,所纠葛者仅在《诗》的经义内容,其中自有骚体赋一脉的抒情传统。二则缘于朝代更替战乱之际的“梗概”时风,使汉末迄建安的诗赋并重抒情,在文体上仍不脱赋主诗从,今人以后起诗学抒情为中心判定赋受诗的影响而始重抒情,实为错置因果。三在曹丕“诗赋欲丽”的理论言说乃是承《汉书·艺文志》“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1](p101)的前代并提传统,且将汉赋风格之“丽”移论于诗,属诗体早期成长阶段的“赋化”命题,明示诗在理论上未完全获得等同于赋的文体自觉。因此考察文学史上赋体诗化的实情,不应受制于作品抒情意涵这一标准,而当首先关注诗赋的辨体自觉和赋体诗化的理论倡导。只要跳出这种建安“文学自觉”说的拘执我们就可以看到,将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2](p99)作为文学史上首辨二体的著名论断固无疑义,且陆机与陆云的赋论和创作皆昭示了本于辨体的有意诗化,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的意义,两晋以下的诗化正是沿着二人的路向发展的;而且,二陆赋学的诗化意涵清理,亦可反向促进对赋体诗化表现于内涵、篇幅、语言形式三个方向的深入理解。这正是本篇讨论二陆赋学之旨趣所在。
一、赋主“体物”的双重导向
我们知道,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及以下分论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八种文体,是承曹丕《典论·论文》“四科八体”而来。但曹丕统论“诗赋欲丽”并将之置于“四科”最后,连并建安时代对诗赋的称序不一,表明彼时赋主诗从且二体地位在诸体中都不突出[3](p89-97),迄陆机变统论为分论,先提诗赋且先诗而后赋,意味着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诗赋地位的提升,当是变建安战乱时代在理论上重文章实用为西晋一统后的重文学艺术;分论诗赋则表明辨体的更进一步,诗已然获得了文体的高度自觉。以此陆机“赋体物而浏亮”的辨体理论,本旨也就不在诗化抒情,而在别立体格作法。然而,讨论《文赋》需要注意一些前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钱钟书所说“《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4](p1206),指明这是作者谈文章创作的体悟总结,并非纯粹的理论建构;今人将之看成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专文,但在陆氏实为赋物赋事的篇章之一,仅以题材的特殊而留下了许多行家经验之谈。嗣后刘勰即指出“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所谓“实体未该”就是“辨文体之异同则未该备也”[5](p1632),这可以看作站在理论思辨角度的通达批评。如此陆机的诗赋论则就可能有辨体的逻辑漏洞。再看其“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内容表达方式,乃是“文体+技法+形容”的骈举组构,其中“技法”导向标举出了用作创作轨则的体格,“绮靡”“浏亮”等的“形容”则属于体格导向下具有时代新义的审美风格理想;显然这里并不存在“互文”[2](p131)的表达,他所要分异的本是创作的体格切入角度,而非泾渭分明、互不杂越的文体畛域。即诗赋分别以“缘情”(功能)、“体物”(题材)为体格,“缘情”和“体物”分别是写作诗赋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绮靡”“浏亮”亦当作此理解。换言之,诗赋二体在创作技法导向下的体格标举和体格导向下的风格标举,都不排斥彼此的交越互用。如此一来,尽管陆机《文赋》在主观上并无赋体诗化之意图,但创作体悟式的骈文谈辨毕竟伏下了这种可能。具体而言,其无意诗化主要有以下两重导向:
(一)修辞“细切”的诗化
陆机“体物”之说,首先具有系联于书写对象的修辞策略指向。此说本来源于对赋体初起的物的题材标举,延续的是荀子《赋篇》分赋五物立体进而形成“荀、宋始赋庶物”[6](p728),及至班固所称“感物造耑”[7](p1755)、王延寿所谓“物以赋显”[8](p168)的前代传统。但汉人论赋重“称《诗》以谕其志”[7](p1755-1756)的《诗》学经义,由“物”而“事”的题材旨趣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内,所以陆机的“体物”体格标举乃是就文学而论文学的重大抉发。关键是“体物”的技法导向不同于荀赋以下的客观咏物,而具有了诗化的可能。“体”字指明了面对“物”题材的取法路向,其书写注重体察物象的起源、形貌,以切于“物事”本身,获得“期穷形而尽相”的结果。刘勰《文心雕龙》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刻形镂法”[9](p135,136,588),沈约表彰“相如巧为形似之言”[10](p1778),都是从这一角度获得对体制的理解,所以刘熙载才将赋之“体物”总结为“赋取穷物之变”“赋以象物”[11](p461,462)。但仅描摹物事本易导向葛朴所称的“汪秽博富”[12](p155),在汉代,只以《诗》义讽颂的拘执,赋的铺陈在宏大叙事下乃能“义尚光大”;一旦离开了经学功能批评的牵制,其辞章艺术得到大力张扬,所谓“体物为妙,功在密附”[9](p694),就容易走向客观细节的烦琐描绘,以获得体物的妥切为要。清人李元度《赋学正鹄》曾专列“细切”条云:
细切类者,陆士衡云:“赋体物而浏亮。”不细不切,断不能体物也。有双关题宜细切者,有咏物题宜细切者,须用比例法、串合法、映带法、刻画法、双管齐下法。有数目题宜细切者,有干支题宜细切者,须用核算法、掩映法、衬贴法,总贵有巧思,而复运以妙笔。[13](p719)
真是方家法眼,指明文学纯然的“体物”必然要做到有“巧思”的“细切”,“细切”就是以精细化、技巧化的描摹而达成切于咏物形貌的旨趣。这里先不论精细化的作用,看其所列各类体物方法,“比例法”“串合法”“映带法”“刻画法”“核算法”“掩映法”等,皆是极细致的描写技巧。所以李元度才会进一步总结:“若夫修辞以炼字炼句为要,尤以六朝人为宗。”[13](p720)在今见陆云给陆机的三十多通书信中,也数次讨论到赋的用韵、句式、字数等细节问题,是为明证。“体物”“细切”以炼字的修辞指向辞采绮丽,炼句的修辞指向骈偶精工,且二者相辅相成,导向的正是语言形式上的修辞诗化。辞采绮丽则如陆云《与兄平原书》的评价:“《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兄往日文虽多瑰铄。”“益不古,皆新绮,用此已自为洋洋耳。”[14](p1111,1089,1047)骈偶精工即陆机《文赋》“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2](p145)的“绮合”追求,系上下二句相合的“俳偶”的当代表达,表现于同位结构上的类对,上句有彪炳之辞,下句仍之;而称“藻思绮合”则表明骈偶与辞采的合一。又陆云在第15通书信里说“然靡靡精工,用辞纬泽,亦未易”“近日视子安(成公绥)赋,亦对之叹息绝工矣”[14](p1079),“精工”“绝工”可联系于他评乃兄的“《漏赋》可谓清工”[14](p1112),玩摩文意,“工”除了“体物”之“工”外,必有“俳偶”二句骈对之“工”在,而且他明推“兄文过子安”,成公绥的赋本也好用骈,亦为佐证;其论“工”与“靡靡”“纬泽”合用,又表明骈偶与绮辞的相辅相成。何以二者会导向诗化?刘勰评宋初文坛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9](p67),实际上就是发端于陆机“体物”描摹以雕琢的结果,注重字句修辞,类于以诗艺营构诗境。即如清人俞琰所称“穷物之情,尽物之态”“体物者不可以不工”[15](p2)。以字而论,在于推敲关键词的艺术张力,借以生发审美意境。以句而论,则在以虚字连接的六字句的大量运用,这是陆赋及至晋赋句式形态的独特标志。该句式凭借句腰虚字的强调和召唤,一句足意便于描述和形容,颇能促进炼字之功;也易于导出另一句的表意骈举,有利于安排体物描写的层次,形成两句骈举相互映带的诗意审美空间。如陆机得到其弟陆云“清工”称赞的《漏刻赋》,炼首起字“伟”“妙”,遂使开篇能振起,以下“激悬泉以远射”炼“激”字,“顺卑高而为级”炼“顺”字,兼有力度感和动态之美,庶几如诗语炼字之有张力;又“笼八极于千分,度昼夜乎一箭”并炼起首一字,骈举时空而极尽形容,还能产生阔大的艺术想象空间,与诗境之营造相侔。不仅如此,赋的这种“体物”修辞的“细切”写法还直接影响于诗,宋人张戒论诗称“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16](p450),明示赋之细切自陆机乃始;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称“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钟嵘推许“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五言诗“滋味”说的技法途径,皆本于此。这同时从另一个层面也佐证了六朝赋在写物的语言修辞方面由陆机始而诗化的发展轨迹。
(二)“体物”而“感物”的诗化
“体”与“物”的组合同时也统摄了主体的情感运思。《广雅》:“体,身也。”[17](p486)即“总十二属”的身体,动作化后引申为以身体来感知,所谓体察、体验。《礼记·中庸》:“体物而不可遗。”[18](p3532)明言体物,或为陆机所本。但《世说新语》载二陆“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19](p381-382),他所称“体物”本指向玄风浸润下的体察物理,实属时代思想影响下的赋学话语。正始以下的赋渐受玄学影响,嵇康《琴赋》、成公绥《天地赋》、张华《鹪鹩赋》皆有所反映。陆机《遂志赋》称“惟万物之运动,虽纷纠之相袭。随性类以曲成,故圆行而方立”[20](p91),题旨虽写个人情志,于物却从其“运动”“纠纷”中获得“随性曲成”的处世之方,是借物以取玄理的典型代表。又其《漏刻赋》:“伟圣人之制器,妙万物而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远而不之。”陆云《愁霖赋》:“考幽明于人神兮,妙万物以达观。”[14](p99)皆足此义。问题在于,由“体”及“物”的延伸指向并不明确,“体”“物理”的组合在实际创作中很容易转向“体”“物情”。陆机自己也确认了这种逻辑发展的可能。按吴棫《韵补》所收陆机遗诗:“物情竞纷纭,至理自宜贯。达观傥不融,居然见真赝。”[21](p693)他讲“物情”,又谓“至理自宜贯”,首先道出了物中蕴含有情、理的可能性;其次,“竞纷纭”显然视物情一体,“宜贯”表明了物与理之相通,内含了主客一体的追求。如此观物体物,必然引发主体和物象的交融,从而导向赋体物的玄思诗境化,及至导向于物情诗境化。又其《豪士赋》序:“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与上例大略相同,前取玄理,后返庄生万物之“有情”,明显体现了从物理推及物情的“物”主题抒写思路。所以我们不难在其赋中读到径表“体”“物情”的写法,如《感时赋》:“伊天时之方惨,曷万物之能欢。”《述思赋》:“观尺景以伤悲,抚寸心而凄恻。”
从理论上看,显然“体物”的“体”字发挥了“体察”“体悟”“体验”的主体切入功能;而“体”“物”的组合,则经由理性客观的“体物”(观物及理)向感性主观的“体物”(感物及情)转变,由此形成了“体物”而“感物”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主体情感的强烈介入和突出抒写。何以人能“感物”?陆机给出了具有文艺心理学原理性质的“物感”解释。按其《怀土赋》序所言:
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赋。[20](p97)“何物不感”的强调,不仅指出了万物皆可感人而入之于赋,还将创作中万物情态与主体情感的交融描述了出来。恰如《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自然本身具有生命而能感于人,物在作家眼中成为物象,实与心象相关,物、象、心在创作过程中融为一体;从“感”的性质来讲,物、象又是与情相联系的,所以“物感”说的理论揭橥本就伏下了发摅的意味,从而具有抒情意涵的诗化倾向。不同于建安曹丕《感物赋》在抒情时风下的无意书写,陆机基于“物感”理论意识的赋体创作,自然就构成了其“体物”论的另类抒写。试观下例:
(1)“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赋》)[20](p5)
(2)“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历四时以迭感,悲此岁之已寒。”(《感时赋》)[20](p51)
(3)“感亡景于存物,惋隤年于拱木。”(《怀土赋》)[20](p98)
(4)“羡品物以独感,悲绸缪而在心。”(《行思赋》)[20](p102)
(5)“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伊我思之沈郁,怆感物而增深。”(《思归赋》)[20](p106)
(6)“览万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远。”(《愍思赋》)[20](p111)
(7)“寄冲气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罗。”“穷览物以尽齿,将弭迹于余足。”(《应嘉赋》)[20](p113)
(8)“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寻平生于响像,览前物而怀之。”“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叹逝赋》)[20](p134-142)
(9)“顾万物而遗慨,收百虑而长逝。”(《大暮赋》)[20](p146)
例子不胜枚举。陆机所称“瞻物”“睹物”“感物”“品物”“触物”“览物”“顾物”,其义皆近,都是统摄物情发论,从感物导引出情感变化或从抒情推及于感物;《叹逝赋》《应嘉赋》《思归赋》多次运用这种写法,更不要说感于具体之物的抒写了。这些词的反复出现,正体现了作者作赋重“体物”而“感物”的创作路向,即将强烈的主观情感融入“物”之主题,以“感物”为标的,达成心物合一、物情合一的境界。这实际上就是以抒情内涵为旨趣的诗化写法,可以看作“体物”而“缘情”的体格借用,从属于诗赋超越于辨体层面的体格交越书写,已然大不同于建安赋的抒情。尤其“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一例,打破了诗之“缘情”和赋之“体物”的界限,“事”“物”“情”三者互为指涉,是赋体抒情性的张扬和凸显;“体物”“缘情”的圆融无碍几无体格借用的痕迹,庶几一如赋的当行作法,具有主客一体的诗境化意味。当然,“感物”的写法本就属“缘情”之诗的题中要义,故诗中遍见,如“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东宫作诗》);“感物多远念,慷慨怀古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拟〈庭中有奇树〉》);“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拟〈明月何皎皎〉》)。所谓“何物不感”,“感物”抒写似已成为贯穿其诗赋创作而念兹在兹的观念。
二、“情本”理论的抉发催化
同代夏靖《答陆士衡诗》评价陆机“为物之主,为士之林”[21](p694),明确意识到了陆机对“物”题材的执着,足见其“体物”书写的影响。但有趣的是,全诗都是围绕他的才和德来表述的,并无一词提及其“感物”主情,似乎陆机逞藻而不及情。实际上,陆机确实也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揭橥赋体的抒情性,今惟见《遂志赋序》评前人“岂亦穷达异事,而声情为变乎”隐有此意。其中原因,应该缘于他对“体物”“缘情”的诗赋体格分疏:如再对赋“感物”以扬情的写法作强调,则势必因诗化而进一步消解或遮蔽其赋“体物”的体格认定;另一面却因“物感”理论的确认和“感物”抒写的诗性吸引力,促使他信笔“体物”而导向“感物”,从而在创作实践中呈现出了相反的一面。这种潜在的诗化理论,刚好在其弟陆云手中得到抉发和互补。
陆云自称“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14](p1044),他主要的心思在作赋上,理论意识中便没有了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强烈体格分疏意识,当然也就没有了赋“体物”的体格拘执,可以直截了当地道出“情”的重要性。从现存资料看,在陆云与其兄长陆机共计三十九通书信里,竟然无一字涉及赋“体物”。今人大都注意到陆机《文赋》属晚年之作①杜甫以为《文赋》作于陆机二十岁,今人多不认可,逯钦立、饶宗颐皆有辨,以为系陆四十岁以后的作品。逯钦立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421—434;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M].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2003:495—496.,系平生文章写作的深入总结,故见胜义纷披;但陆云《与兄平原书》提到《文赋》:“《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14](p1111)却带有明显的批评意味。他仅从“辞”的角度切入,说明此文进入陆云视野时,是作为一篇论作文题材的赋文来接受的,其中分论十体特别是诗赋的体格标准都未得到特别的重视。陆云若对陆机“体物”之说有赞赏甚至异议,按理在与其兄大谈赋文创作的三十多通书信里不会无一点痕迹;又从陆云的信来看,陆机也有不少回信,可惜今已大都佚失,除《晋书·左思传》里所收一条评价左思作《三都赋》的文字外[22](p2377),便再无一词关系到回应其弟论诗文创作。史载陆云“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22](p481),则陆云持论多而精,陆机作赋多而发论反之,二子各以不同的文学特长影响时人。陆云不提赋“体物”,我们甚为意外,合理的猜测就是:陆云大量强调“情”的重要性,乃是深思之后的理论强调,使得他从根本上无视陆机“体物”“缘情”的体格分疏;同时,从前代赋物传统及夏靖称陆机“为物之主”来看,陆机称赋“体物”可能是当时赋家创作的常识,所以才不值得褒贬。而二陆并称,长于“持论”的陆云,其赋作的文坛影响,在当时也不弱于陆机多少②在第29通书信里,陆云谓自作《喜霖赋》而“此间人呼作者皆休”,可见其赋当时亦有影响。可见[晋]陆云.陆士龙文集校注[M].刘运好,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129.又从他批评陆机赋来看,似乎当时陆机赋的地位和影响并不是独秀一枝,尤其《文赋》的理论内容。陆机在当时为人称颂的是有才而难追摹,陆云则善于“持论”而多示门径。,所以他在理论上对“体物”论的无视和对“情”的强调,必然会冲击陆机的观念和创作。
按陆云在信中反复提到赋主“情”:
(1)“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为欲作十篇许,小者以为一分生于愁思。”(第4通)[14](p1044)
(2)“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第8通)[14](p1056)
(3)“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前登城门,意有怀,作《登台赋》。”(第12通)[14](p1067-1068)
(4)“愁邑忽欲复作文,欲定前,于用功夫,大小文随了,为以解愁作文,临时辄自云佳。”(第13通)[14](p1071)
在《义务课标2001》“统计观念”的基础上,章飞提出统计观念是统计意识、统计技能和统计评判质疑能力的统一体[7].在《义务课标2011》“数据分析观念”的基础上,童莉认为数据分析观念是学生在有数据的统计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对数据分析的某种“领悟”,是关于数据分析内涵、思想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的综合性认识[5].另外,李金昌将统计素养描述为人们掌握统计基本知识的程度、统计理论方法水平及运用统计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所具有的统计世界观[8].惠琦娜认为统计思维是人们自觉运用数字对客观事物的数量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描述、分析、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方式[9].
(5)“情言深至,《述思》自难希。”(第15通)[14](p1078)
(6)“省《述思赋》,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第23通)[14](p1111)
(7)“忧邑聊作之(指作《愁霖赋》),因以言哀思。”(第29通)[14](p1129)
(8)“视仲宣赋集《初征》《登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第35通)[14](p1141)
陆云论赋不称“体物”而极力提倡“情”,这与他追求“清省”“洁净”的文章审美有关系,所谓“小者以为一分生于愁思”,篇短而抒情为当,实本于一整套理论体系的考虑[14](p1031-1034),在此不遑展开。无论是对赋文的高下赏评,还是对赋体的功能要求,他都以“情”为关键批评话语来展开,可称“情”本之论。他以此来评价乃兄之赋,因此极力推许《述思赋》的“情言深至”“深情至言”。从今天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述思赋》的抒情实不如《豪士赋》的深沉蕴致,也远比不上《文赋》的理论贡献,但这些反而是当时的他所不重视的。他评价自己的《岁暮赋》同样如此:“倾哀思,更力成《岁暮赋》,适且毕,犹未大定,自呼前后所未有,是云文之绝无。”[14](p1146)认为此赋为平生最佳,关键在于“情”本体的“倾哀思”。如此论赋作赋,无视诗赋的体格分疏和赋的“体物”之格,一律以抒情性为标准,似乎赋之抒情功能才是其体格的关键,无疑会对“体物”之说造成消解。可惜我们现在见不到陆机的任何回应痕迹,也无法知道陆机当时的反应了。
将二陆对赋“感物”扬情而诗化的不同处理方式置于此前赋史的诸家流变中来加以考察,当能看到其中的价值所在。按《汉志》列四家赋,后人理解分岐,从现存汉赋形态看,其实不过三类:承宋赋铺陈的班、马、扬、张等“京殿苑猎”类骋辞大赋;承屈骚发摅情志的各类骚体物;承荀赋四言咏物流衍的宴飨雅玩类短制。其中第三类起源最早而以体例的“演而未畅”[23](p29)最为后代忽视,虽然第一类是汉赋的绝对主流,以其经义批评形成宏大叙事而对后二者造成了一定的遮蔽,但屈赋一脉仍是不容忽视的潜流;《九章·惜诵》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24](p73),首标赋义,迄贾谊《鵩鸟赋》、冯衍《显志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刘歆《遂初赋》等流变为“述行序志”之作,大致都是私人情感领域的抒写,构成骋辞大赋的重要补充。迄建安经学式微,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影响及作家“梗概而多气”[9](p674),重视抒情复成为一时之文学思潮;这也表明建安赋的“感物”书写是抒情浪潮之下的无意识行为,且本于诗文创作总是关系到物我主客的交融、互动,乃是一种普遍的文学原理在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就很容易将潜在的骚体抒情传统变为显流,所以刘熙载才说“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11](p435),明指建安赋抒情是自变传统所导致的结果,此与诗化何关!但迄陆机则不仅承荀赋分异《诗》赋写作的体格轨范和审美风格,还在《遂志赋》序中梳理了屈赋以来冯衍、班固、张衡、蔡邕、张升等人的情志抒写这一传统,则表明他的“体物”说是衡之于前代诸派的流变后,对建安赋抒情浪潮的理性审思和反拨;其赋作有一半即属题举“体物”者,适可印证。然而径表抒情者也不少,如《感时赋》《思亲赋》《述思赋》《遂志赋》《怀土赋》《行思赋》《思归赋》《别赋》《叹逝赋》《愍思赋》《大暮赋》《感丘赋》《怀旧居赋》等,这乃是在实践中对“屈心”抒情传统和汉魏以来时风的兼取。谓之时风者,需与陆云合观。陆云既与陆机一样跳出了经义衡赋的拘执,又不提“体物”的技法导向,且又不直接表明承续骚体传统,则其抉发“情”本之论,显然是有意的理论强调。不过既不受制于辨体意识,当然也就不在乎诗化与否。至此我们则可以下一结论:陆云之说,乃是赋学史上明确的诗化理论话语;陆机之论所伏下的潜在诗化可能,及至创作的种种呼应,则是这一理论意涵的必要补充。
上引陆云自视甚高而“倾哀思”的《岁暮赋》序可以推出其诗化理论的两重意涵,非常值得注意:
余祗役京邑,载离永久。……自去故乡,荏苒六年,惟姑与姊,仍见背弃。衔痛万里,哀思伤毒,而日月逝速,岁聿云暮。感万物之既改,瞻天地而伤怀,乃作赋以言情焉。[14](p52)
陆云既无视赋的“体物”,而且在其诗赋中又有大量的“感物”创作,特别是与其兄的通信中对“情本”理论的表彰,无疑会影响陆机的创作观念。陆机的“体物”论本就隐含有“感物”的因素,这使得他很容易接受陆云的“情”本说和“感物”创作,从而触发其赋体创作的诗化转向。换言之,陆机诗赋中的“感物”抒写,应当与陆云主“情”的理论抉发有着重大关联:他的赋中并存“体物”之作和抒情诗化之作,并非是“变调处理”[26](p171)那么简单,而是暗含了深思熟虑之后的文体观念坚守,以及对陆云理论与时风的接受和调整。如果说陆机在理论上以“体物”强调赋的体格,在创作中喜好赋的“感物”,陆云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旗帜鲜明地强调赋的“情”本功能,这就含有将陆机的体格说转变为功能说之意,完全在理论层面将赋的诗化合理化了;但不管是暗中诗化还是理论的明显张扬,都能从他们的诗赋作品中找到“感物”抒写的呼应,姑不论这种多以宏观抽象出发的“感物”书写能否达到较强的诗境化意味。同代人郑曼季《答陆士龙诗四首》的首篇《鸳鸯六章》有:“感物兴想,我心长忧。”“感物兴想”四字出自陆云《赠郑曼季诗》的“感物兴想,念我怀人”,此诗序又谓“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21](p719),则可视为并答二陆之作。这与前引夏靖评价陆机“为物之主,为士之林”一样,不仅表明二陆之说在当时已引起文人之注意,还反映了“感物”抒写已成为一种诗赋并用的明确创作观念,并逐渐影响当时的文坛。下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将所有赋都置于从《诗》学经义到诗化之“情”的功能性批评之下。他总结咏物小赋:
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9](p135)。
此时“体物”赋有所消退,咏物诗却兴盛了起来。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触兴致情”的创作实情,还从物情互动的角度提出赋的“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与后世情景诗学中的物情互兴论庶无区别,既是对二陆以下赋体诗化后的创作现象之总结,又是对二陆赋论的进一步发展;表面上是要在题材之“物”和主体之“情”两者间建立起新的平衡,实际上却带有时代取向而极力强调赋体应具“抒情”之功能。显然,从二陆之论到刘勰,其中隐含了一条赋的“体物”体格如何发生文体位移(从题材强调到功能强调)而诗化的演进路径。
三、“浏亮”“清约”的规限导引
如前所述,“浏亮”是陆机“赋体物”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其实陆云也有“清约”的类似提法。风格追求会反过来规限和导引文章的写法,由此造成体貌之变;在二陆赋学,则主要指向影响到赋的“体物”或曰“感物”写法,其间蕴涵了强烈的诗化因素,在语言和篇体两方面皆有明显表现。这一命题可以从规限的背景与可能、规限与导引的具体展开两个方面来观察。
(一)规限的背景与可能
本来,陆机赋“体物”的题材技法抉发,就是在经学式微语境下的文学自觉之论,缺少了《诗》学批评的牵制,铺陈物事之赋就容易在体物中导向修辞的细切化。不仅如此,这其实还影响了赋物的据形征实和篇幅的曼衍无际。细切的肖象修辞本就具有征实化的可能,左思《三都赋》序称“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8](p74),指明体物而依本,故推出“宜本其实”,虽承续有东汉赋由虚转实的传统[27](p45-52),但仍隐含了由体物而征实的文学逻辑。陆云谓当时“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14](p1089),又极力宣称“文实无贵于多”;挚虞批评赋之四害谓“假象过大”“丽靡过美”[28](p819),虽持经学的立场,亦从侧面证明当时不少赋作有篇幅曼衍的态势。这些都可与陆机“期穷形而尽相”“其遣言也贵妍”的体物肖象修辞论参合理解。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才提出“浏亮”的美学特征来加以规限。换言之,“体物”和“浏亮”之间暗含了导引失体和反向制约的复杂关系,体现了陆机《文赋》所提出的“物”(题材对象)—“意”(运思取向)—“文”(文体表达)三者间的联动和平衡,意味着要围绕“以物象的描摹刻画”为核心而追求“圆照契合的‘清明’之境”[29](p403)。
按李善注陆论中的“浏亮”:
浏亮,清明之称。《汉书·甘泉赋》曰:“浏,清也。”《字林》曰:“清浏,流也。”[8](p241)
张凤翼释“浏亮”为“爽朗”,方廷释为“达而无阻”,皆与李善“清明”之解释相近,足见无所争议。关键在于许文雨所云:“谨按陆氏诗赋二条,止用新义。”[2](p112)曹虹注意到“浏亮”一词与玄学的渊源,如嵇康、阮籍便有“体亮”“亮达”“体清”“淑清”之表达,这些说法和“明”字都用于描述“体道”过程及其境界[26](p163-167)。据此,则“浏亮”作为风格术语指向“清明”之境,意谓“体物”的宗旨是要将其物及其背后的理、情表现出来,达到一种清妙明亮的境界。可以说,作为风格术语的“浏亮”,蕴含了一种主体描写物之形貌和情理相统摄的境界,这正是经由玄学之思的浸润,应和于“体物”中蕴含的体道玄学。陆机这一“新义”的提炼概括,足可代表时风。《文心雕龙·才略》称:“张华短章,奕奕清畅。”[9](p700)“清畅”便和“浏亮”“清明”相近,二陆又是受张华影响的。陆云在与陆机的通信中也大量提出类似说法,他曾批评陆机:“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14](p1056)又称赞其《述思赋》“实为清妙”。此外,信中还有“清省”“清美”“清绝”“清约”“清工”等说法。而刘勰则评价陆云“雅好清省”[9](p544),皆意旨相近,指向于行文的雅洁清新,简约高妙,应和于魏晋玄学,透露出一种玄妙精简而能生发想象的玄思境界。按鲁迅谓《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30](p56),其实正是玄学表征于文学的特点,有此等学方有此等人,方有此等人的言行及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浏亮”的“新义”专属于玄学浸润后的魏晋以下之赋,胡应麟《诗薮》:“马扬诸赋,古奥雄奇,赘涩牙颊,何有于浏亮?”便明确意识到陆机此说乃“六朝之赋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31](p141)。谢榛《四溟诗话》也说“‘浏亮’非两汉之体”,皆表明“浏亮”之说指向于两晋以还的时代审美风格。恰恰正是这种“浏亮”“清约”作为赋体风格追求所融涵的玄思意涵,规限着赋在捐弃《诗》学经义后,其“体物”细切征实和曼衍无际的极端化,引导了晋赋自二陆以下的诗化发展。
(二)规限与导引的展开
规限的另一面是导引,先看对语言细切征实的展开。首先,玄学主于辨抽象名理,注重本体的体悟,汤用彤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32](p19-20)赋“体物”的体格要求从文章学上讲恰恰需要究心于“具体事物”而达到体物之细切,这就与时代风气相乖;而彼时虽已辨体,在赋上却未形成文体的稳定形态,远不如后代(以明代为代表)的定格之辨,这就使得不稳定的体格容易让位于时代风格,所以“浏亮”作为审美风格要求,就必然规限和制约“体物”语言修辞的精细化、琐碎化倾向,导向即物而出情理的“神理之妙用”。其次,玄学重虚无,起于无象无名的“道”本体推论,所以“其言循虚”[33](p319),可以制约赋物肖象的征实化发展。章太炎对学问之病下了一个有趣的判断,认为学者病于实当施泻,病于虚当补实;汉学家的考据烦琐亦即实,而必以玄理之虚“涤荡灵府”[34](p28)。拟之于赋,则“浏亮”的玄学要求会洗涤和冲淡体物执着于细节的“征实”“病实”倾向,而注重于导向表达情理之“虚”,这就和“神理之妙用”结合了起来,导向了即物而出情理的诗境化书写。在二陆的理论话语中,陆机讲“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2](p145),陆云讲“了不见出语”“但无出言耳”[14](p1047,1052),“警策”“出语”“出言”,都有这种意味:一篇之中需要有振起的句子,能够超越当下体物描摹的同一维度表达;从另一面看就是对细节琐碎化、征实化的规限和反拨,显然应和于玄学超越“具体事物”而期于“循虚”的“神理之妙用”。陆机诗称“物情竞纷纭,至理自宜贯”,陆云《岁暮赋》序称“感万物之既改,瞻天地而伤怀,乃作赋以言情焉”,其所应和的即物贯理、感物抒情,也表明了超越肖象细节的“体物”警策语与主体情理这二者相融涵的逻辑可能和书写意趣。我们可以将这种重神理虚化的“警策”称为“炼意”——由于它本身是在“体物”修辞细切的语境中滋长的,自然就统摄了炼字炼句。典型如陆机颇为陆云推崇的《漏刻赋》,不仅注重描写漏刻之肖象准切,而更注意以“既穷神以尽化,又设漏以考时”“信探赜之妙术,虽无神其若灵”这类跳出体物的形貌实写、注重锻炼的艺术张力、容涵有诗境意味的虚化想象语来间破,自属“警策”“出语”,固有“神理之妙用”。再如《鼓吹赋》“放嘉乐于会通,宣万变于触类”“惨巫山之遐险,欢芳树之可荣”,《瓜赋》“感嘉时而促节,蒙惠露而增鲜”“芳郁烈其充堂,味穷理而不䬼”,皆属容涵有“理”“情”的警策骈语体写,能在“体物”的语境中营构起以虚灵不昧为旨趣的诗化意境。元人祝尧批评陆机的“警策”说,认为“辞之所以能动人者,以情之能动人者,何待以辞为警策,然后能动人也哉”[13](p49),分解了辞和情,便是未明白陆机此说的时代意味,是基于对体物滞实细节的超越,是玄学视阈中“物”与“情”“理”的融通,不可割离“情”“辞”而视之。再次,“浏亮”“清约”既作为审美风格的轨范准则,必然会导引语言的使用风格。典型如陆机作品,其《漏刻赋》无一大赋常用的奇僻难字、绝少同类联边和复杂联绵;《羽扇赋》追摹宋玉《风赋》,却几无《风赋》的僻难书写痕迹,中有“翮媥媥以微振,风飉飉以垂婉”两句类于大赋的描写,但紧接着却以“妙自然以为言,故不积而能散”的“出句”虚写以间破,惟恐古奥僻难的用字影响了“浏亮”的风格,如此简约化的处理,则更易于诗化。后来刘勰称“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9](p624),实亦有着自陆机而下的发展轨迹。
再看对篇体的规限和导引。章太炎《五朝学》称:“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33](p319)汤用彤亦以为玄学以“名学之原则”为“首要之方法”[32](p21),其功能的关键在于“言意之辨”所形成的思维,犹如Occam’s razor(“奥卡姆的剃刀”)可以削除一切芜杂[32](p181),故其能综核名理,以简破繁,此王弼能以之廓除汉人解经烦琐之因。所以“浏亮”才能规限体物表现在篇幅上的曼衍无际,而约之以短篇为上。陆机《文赋》一面提“穷形尽相”,另一面也提“制邪禁放”,这一看似矛盾的双向强调,其实正好应对了赋“体物”体格和玄学时风之间的紧张和平衡;特别是他提出“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讲得最为明白不过,慎防“冗长”而取“辞达”,“理举”二字本就从玄学的综核名理中来,即体现了玄学对长篇的约束。二陆明明知道大赋易传世,如陆云写信劝陆机:“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云谓兄作《二京》,必传无疑。久劝兄为耳。”[14](p1079,1082-1083)但另一方面,陆云不仅自己不作,称“大文难作”[14](p1054),而且在面对陆机的《文赋》时又予以“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的批评,其理也在于此。至于左思《三都赋》巨制,乃因作者出身寒门,欲以之干谒功名,在篇幅形态上已然是特殊的个案。以此证二陆及当时的赋家作品,表现最为明显的正是句式和结构。今见陆机咏物本色的作品,《漏刻赋》48句,《鼓吹赋》42句,《羽扇赋》主体部分48句,《瓜赋》48句,《浮云赋》40句,《白云赋》50句;又其《桑赋》24句,《鳖赋》20句,这两篇都有两句散佚出自后人注本,足见非为完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赋句数比题表抒情的赋要稍多,其抒情赋多在30句之间,与其诗的20句左右相类①王琳《六朝辞赋史》曾作过统计,其抒情赋除了《叹逝赋》92句外,从10句到42句不等,以30句左右为多;其乐府诗则从20到40句不等,以20句左右为主。考虑到六朝赋的散佚,今天所见大都极可能不是完篇,因此仅取概数以为参考。王说见王琳.六朝辞赋史[M].西安: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2014:24.。至于陆云《岁暮赋》《愁霖赋》《登台赋》《寒蝉赋》等不管属哪一类,句数均略多一点;而其五言数量本就为少,无以观察取证。“体物”类篇幅的50句左右自是“浏亮”规限导引的结果,然而为何抒情类的赋和诗的句式大致相当,似无人注意。赋句不能再少,诗句从后代的角度看则反亦为多,这应该是赋以“体物”的铺陈展开为要,以及对“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的担心,篇幅太短则无法“应”(乃《文赋》“故虽应而不和”之“应”);诗的篇幅应该是改写乐府长篇的惯性使然,一以“缘情”为主,但以辨体须别诗赋体式,二者句数不可等同,惟以抒情类赋与诗的句数最相接近,更见诗化的形式表征。此皆与两汉动辄鸿篇巨制的大赋风气去若霄壤,且这种变化也表现在结构的处理上。陆机《羽扇赋》可为典型,该篇模仿宋玉《风赋》,主要写楚王、宋玉的对话,后又加入唐勒的赋物,完全是散体骋辞大赋的结构,内容却是短篇写法,其中宋玉咏羽扇部分计48句,正是该赋主体。也就是说,体物的巨幅篇制已然得到了警戒于“冗长”的规限,尽管保留了大赋的结构框架,实际上已向简约化的短篇靠拢了。这种情况,在潘岳《沧海赋》、潘尼《东武馆赋》《西道赋》、仲长敖《覈性赋》、张协《玄武馆赋》、张载《濛汜池赋》中,皆能找到呼应。这些本当属于可以写成巨制的题材,却最多保留了大赋的框架,而出之以简约化的短篇。总结二陆“浏亮”玄思审美旨趣下的“体物”本色之作,我们可以说,40—50句左右,是咏物赋的大致篇幅,一方面句数略多于抒情类题材是为了保持“体物”的体格特征;另一方面远较大赋为小,精减篇制必然会导致重心转移到体物语言的修辞策略上。以此举凡短篇统摄下的炼字、炼句、炼意,以及短篇形制与写“愁思”内容的两相结合等问题,都体现了作赋慎于“冗长”、主于“清省”而终趋于诗化的规限和导引。
四、余论
将二陆置于整个唐前文学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无论在理论的标举还是他们都擅长的赋体创作方面,其差异其实都可以忽略不计,论家也多统摄二子以质之于六朝赋学的地位和贡献。在赋体诗化的命题上,同样具有这种特征。然仍可见出不少差别,也正是这种需要互补性理解的异同辨析,才能更清晰地折射出赋的诗化原理和演进轨迹。诗化的抒情意涵、篇幅形制、语言探索三个方面,往往是互为因果影响的。其中抒情是最根本的原因,却最易被人歧解。盖赋中本有屈赋骚体一脉,在汉代用于“私”领域,故无须借诗之抒情而变;汉魏之际抒情的凸显变为时风,如祢衡《鹦鹉赋》、王粲《登楼赋》等名篇,与关注战乱现实的三曹七子之诗皆是其表现,最明显如曹丕《感物赋》,仅关涉题材,尚无理论的只言片语。诗化必以文体的自觉为前提,所以真正的赋体诗化非要等到二陆时代的理论标举;于焉此前的骚体赋特别是建安抒情赋,都只能说是为此准备了充分的诗化条件,谓之充分者,即亦不可忽视其作用,陆云能理直气壮地拈出“情”本之论,便断然离不开此一背景。但在二陆的赋学理论中,陆机辨体自然只是无意中开出诗化,关键是“诗缘情”“赋体物”的辨体格伏下了交越互用的可能,“体物”的题材标举统摄了“抒情”功能,内含了由玄学之“体物”而诗学之“感物”的逻辑进路,何况还基于对“物感”理论的着力表彰和对抒情时风的不舍;陆云没有了辨体拘执,其鲜明的“情”本抉发就显得相当重要,由此延及物情一体的诗境化写法或许对陆机的创作有所影响,但抒情意涵作为诗化核心质素的完全确立,却至刘勰时明确强调抒情的功能性位移方才完成。至此,荀子以下的咏物赋固有承续,但“体物”的标举却无意分化出了诗化一脉,凡体物皆易感物,从强调物事题材为赋之体格到强调抒情功能为赋之体格,两皆不分轩轾,凡重于后者即具更深之诗化程度。
篇制的问题相对简单,汉代宫苑狩猎之赋乃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学代表。后代固然无此帝国气象,文士献赋与王侯好尚之风不存,拟作难免每况愈下,如东晋庾阐作《扬都赋》献庾亮,谢太傅便曾发出“屋下架屋”“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19](p226)的批评。但文学自有其内部的发展理路,建安抒情时风之下虽亦多短篇,但晋代玄风的制约仍为其关键,要等到二陆“浏亮”“清约”的理论标举,篇制诗化的导向才见明确。或许短篇在陆机而言只是“禁邪制放”“辞达理举”“无取冗长”的形式问题,但陆云说“小者以为一分生于愁思”,却引出了篇章短小如何产生文学艺术魅力的问题。由此便将短制形式和抒情技艺结合了起来,篇体越短小,越要注重感物扬情,甚至导向与玄风结合开拓出物情一体的诗境化境界。二陆之外,如潘岳《悼亡赋》《寡妇赋》、谢万《春游赋》、湛方生《秋夜赋》、王劭之《春花赋》等,都有这种表现。下迄宋齐梁陈,风气已成,长篇不多,短制成为主流,其书写的艺术探索也就越发丰富,如“以情为里,以物为襮”[35](p20)的谢庄和鲍照之赋,主用“骈体,间多散行”[36](p3)而善变句式的庾信小赋,皆可视为这一发展的典型。
语言艺术的追求最为复杂,凡一切形式及内容上的讲求皆与之相关。赋体诗化语言大致可分为句式的骈偶化和声律化、表达的物情化、炼字炼句的诗境化等,这些追求在实际创作中又是彼此交融在一起的:陆机“体物”的细切导向字句的修辞,如骈偶追求、警句炼字、声律句数等;而“浏亮”“清约”的提出本就基于“体物”细切的文学语境,所以其规引了篇幅的缩短和语言的诗境化,自然与“体物”细切化下的字句修辞融合为一。在句式骈偶方面,赋自东汉以来即已由散趋骈,迄曹植更有转向,但总归陆机为集大成者,表现为追求语言的精工,沈德潜说他“遂开出排偶一家”[37](p134),孙梅《四六丛话》也称“左陆以下,渐趋整练”[38](p69),足见其对赋风转变的影响。赋用骈偶注重炼字炼句,更有诗的艺术张力。不唯如此,晋以还的赋家还从骈偶出发,推及文章组句构篇的修辞,如夏侯湛《夜听笳赋》:“南闾兮拊掌,北阎兮鸣笳;鸣笳兮协节,分唱兮相和;相和兮哀谐,惨激畼兮清哀。”[28](p714)数句接连用顶针格,造成流美之效。又如潘岳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不仅《悼亡赋》用顶针:“入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又其《寡妇赋》“廓孤立兮顾影,块独言兮听响。顾影兮伤摧,听响兮增哀”[39](p94-97),运用分承形成交叉回环之效,加强了抒情性。凡此恐怕已经不是简单的赋的诗化,而当属于以诗的精妙思维来作赋了,最终则在南朝小赋中发展为成熟的诗境化写法。又《文赋》有“音声”“迭代”之说,影响了后来沈约等人的声律论,但诗赋主要是赋在诵读写作中发展声律,此一阶段之说并非诗化,要到齐梁“永明体”成熟后,影响及律赋,才可归入此列[40](p73-89)。至于表达的物情化,是“体物”而“感物”的逻辑运思和“情”本理论的抉发共同作用的结果,及至发展为自物事题材而抒情功能的文体位移,庶几可视为后世情景诗学的前奏。而炼字炼句则受制于骈偶形态,又服从于“体物”出之以情理的“浏亮”规限原则,所以其最诗化的部分,乃是那些具“神理之妙用”的“警策”“出语”,往往以炼意统摄炼字炼句而最富有虚灵不着的诗化意境。只是这种诗境化主于玄学之浸润,颇具时代特征。下迄刘宋齐梁之际,伴随着诗的艺术造境的成熟,如江淹《恨赋》、谢庄《月赋》、沈约《丽人赋》,虽偶见玄理意境之作,亦有“浏亮”影响所在,实已演变为以情感统摄诗境的独特追求了。
总之,赋体的诗化在理论上完全是以二陆为标志而展开的,征之于他们的创作及此后的赋学史,这种演进的轨迹或显或隐,足以辨其条理。譬诸“体物”论赋,固然影响及刘勰定义赋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谢朓《酬德赋序》评沈约赋颂“得尽体物之旨”[41](p1),但恰如清人魏谦升《赋品》从“体物”出发列“浏亮”一品,称“微辞奥旨,无弗弃捐。体物一语,士衡薪传。光明白地,濯锦秦川”[42](p28),点明体物的言约意丰本就可导向诗境化,所以下至萧纲《昭明太子集序》称“至于登高体物,展诗言志”[43](p127),才会借“体物”以论诗,将之转变成明确的诗学理论话语。只是诗境化的玄思命题迄齐梁则融进诗艺试验的大潮中,略无痕迹。及至齐梁“永明体”在声律的轨范下走向诗句的“句法”化,以之入赋形成颇有抒情意境的“诗化赋”,如萧绎的《荡妇秋思赋》《采莲赋》,庾信和萧悫的《春赋》等,又将赋的诗化推向另一个极端,所谓“七言五言,最坏赋体”[13](p210),由是形成了赋的失体及与诗的趋同混同。凡此现象,无一不能通过回视勾连陆机诗赋的辨体省思,以及陆云“情”本理论的抉发位移等赋学理论,获得关联性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