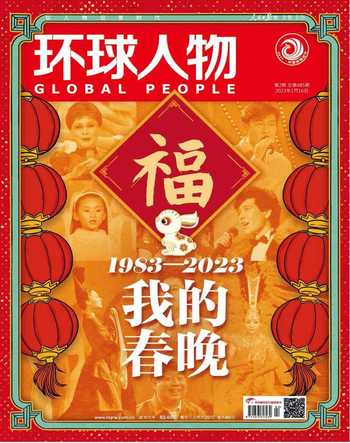笑的迭代
朱东君

國家一级编剧石林清晰地记得1988年年底的那个冬日。他从家骑着自行车赶往央视春晚剧组所在地,从南三环到北四环,“整骑了两个钟头”。这位72岁的老牌喜剧人一开口,便透出一丝幽默感。
他是去投稿的。那时他是北京市曲剧团的创作员,与人合作写了一个小品剧本。石林早年学写相声,后来又写戏曲,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小品创作。结果团里没用,他在报上看到央视向全国征集1989年春晚的小品稿件,便把作品送了去。门房接过稿纸,转身丢进麻袋,“我一看完了,这事也就算了。”没承想,之后便接到了央视的电话。在当时提交的剧本上,石林标注了一句话:此作品若选中,建议由中国评剧院赵丽蓉老师出演。
于是,这就有了1989年春晚上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英雄母亲赵丽蓉遇上了要宣传典型的电视台记者侯耀文,也就有了“司马光砸缸”“司马缸砸缸”的经典对白。
当《英雄母亲的一天》在春晚舞台上上演时,还是孩子的郑猛津津有味地守着电视机。“那时可看的东西少,基本上一进腊月就开始盼着春晚,确实也不会让你失望,尤其是那些相声、小品,把你逗得哈哈大笑,是让人非常珍惜的体验。春晚前几天《中国电视报》会发布节目单,不过正式播出时节目可能有调整,我还会对照着去修改报纸上的节目单,就那么大瘾!”如今已经是喜剧评论人的郑猛回忆着自己的春晚情结。
郑猛踩着上世纪70年代的尾巴出生,1986年家里买了电视,1987年,他拥有了记忆中第一届春晚。“最喜欢的肯定是《虎口遐想》,尽管当时还不完全理解姜昆说的内容,但我知道这肯定是挺好玩的一个事,一个年轻人没有搞对象,掉进动物园的狮虎山。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相声是梁左写的,那也是他第一次和姜昆合作。”
当时梁左与姜昆相识不久,姜昆正处在事业上的瓶颈期,原先合作效果很好的搭档因病离开舞台,他得与新搭档寻找新的表演定位。初识姜昆的梁左说起自己的几篇小说,其中一篇就是掉进老虎洞的故事。姜昆感到这可能会是个相声题材,要来小说底稿回家反复看了二三十遍,好似发现了宝贝。后来一排演,效果相当好,最终演到了春晚的舞台上,大获成功。有了这次成功经验,梁左又和姜昆在春晚上合作了好几次,创作了《电梯奇遇》《学唱歌》等作品。几年后,离开春晚舞台的梁左成为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编剧之一。这是后话。
1987年的春晚还有一个相声也让郑猛印象深刻,就是马季带领着几人表演的《五官争功》,当中就有第二次登上春晚舞台的冯巩。“为什么印象深刻?一是当时一看就理解了;二是那时春晚播出后还会出磁带,我爸买了1987年春晚的磁带,这个相声我反复听了几十遍,基本上能背下来了。”

1984年春晚,马季表演相声《一个推销员》。

1987年春晚,姜昆(左)和唐杰忠表演相声《虎口遐想》。

1987年春晚,马季(中)等人表演相声《五官争功》。

1990年春晚,陈佩斯(左)和朱时茂表演小品《主角与配角》。
马季是把相声从舞台推向电视的关键人物。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已成名,当80年代电视在中国普及开来时,他便思考把相声由听觉艺术改造为视觉艺术。1984年春晚上大放异彩的《一个推销员》,便是他尝试的成果。人们后来习惯叫这个作品为《宇宙牌香烟》。
电视的普及和春晚的出现无疑是相声一度兴盛的重要助力。“早年人们都是通过广播听相声的,没见过这些演员。你现在听上世纪80年代马季等人的相声,他们常常一开场就说:‘以前很多人只在广播里听,没见过马季什么样,今天让你们看看,欢迎参观,请勿拿走。’通过电视,人们看到这些演员的样子了,形象更立体,影响力也不一样了。”郑猛说道:“尤其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侯耀文、姜昆这样已经成名的相声演员,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当时还不满30岁的冯巩也是凭借春晚一夜成名。”
不过,随着小品的兴起,相声在春晚舞台上逐渐式微。作为春晚小品的编剧,石林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者之一:“与小品相比,相声在题材和表演形式上有局限。相声只能是叙说,小品可以有矛盾、有事件、有环境,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表现;再者相声的包袱手法小品都能用,反之则不行。”石林后来做过春晚的总策划、总撰稿,“每年抓节目的时候,相声数量越来越少,尤其是联排的时候,与小品一比效果就弱得多”。
1994年春晚小品《打扑克》中,两人用名片打牌,一人出“科长”,另一人出“处长”,一人出“处长”,另一人出“局长”……一人出“相声演员”,说“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另一人出“小品演员”,说“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现场哄堂大笑,春晚相声的黄金年代落幕了。
春晚上的小品,继而成为又一代中国人的喜剧启蒙。1990年出生的许子谅便是由此爱上了喜剧,他现在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喜剧编剧还珠。“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和同桌演春晚上的小品。那些小品我会反复看,电视上一重播就看,也搭上咱记忆力好点,最后台词都能背下来。那时我抢不过同桌,就总演宋丹丹、高秀敏,老太太的样子我是真学。还记得第一个完整背下来的小品是《昨天今天明天》,现在你说上句我还能接上下句。”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被普遍认为是春晚历史上第一个小品。这个作品根源于观察生活练习,是戏剧学院里最常见的一种训练学生的方式,原来只是内部教学使用,没想到放在春晚上意外成功,人们觉得新鲜有趣。陈佩斯早期的春晚作品《羊肉串》《胡椒面》都属于这类观察性的小品。《胡椒面》中陈佩斯表演吃馄饨,抢胡椒面,甚至几乎没有台词,全靠表情和动作惹人发笑。
石林说,后来的小品就不再只是简单地观察生活,越来越像独幕剧、小话剧。“小品开始有主题,有戏剧结构了。”
这与郑猛的感受相映照。“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春晚上的小品开始更突出语言而非动作了,比如赵丽蓉的小品。好编剧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比如何庆魁写了很多东北题材的小品。那时大年三十晚上看完春晚,第二天又会看重播,还会再看历年春晚相声小品的合集。再看多少遍,还是觉得那些经典作品挺好。”
不少作品至今仍能带来滋养。有一次许子谅和几个人熬夜写现在新喜剧的剧本,“实在想不出来了,咋办?就一个接一个看当年的小品。从《卖拐》《卖车》《心病》《拜年》,看到《红高粱模特队》,看到《牛大叔提干》。至少在那一刻,大家能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什么想做喜剧这件事。”
“是为了给别人带去欢乐吗?”记者问。
“对。把别人逗笑的那一刻,就像魔法一样,是很神奇的一刻,是自己也超级开心的一刻。”许子谅说。

要让观众笑,演员与编剧,最好是珠联璧合。
石林与赵丽蓉就是這样的关系。
“我们不乏中国母亲的形象,温顺、坚毅、忍辱负重,这样的演员多极了,但幽默诙谐的很少。当年我看了赵老师很多评剧,比如《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就觉得这老太太挺有幽默感。赵老师从小就生活在戏班里,培养了她以苦为乐的性格,私下里就好玩极了。”
第一次见面,石林不满38岁,赵丽蓉已年过60。赵丽蓉不认识字,石林就一句一句把《英雄母亲的一天》剧本念给她听。“听完了,老太太抽着根劣质的卷烟说,作者你这是啥意思?我就跟她说,赵老师你想想生活当中,咱们是不是有不实事求是、肆意拔高的现象,我举了好些例子,老太太就联想起来了。我说这个戏您看看您儿子是一名普通工人,偶然跟歹徒搏斗受伤了,所以被评为英雄,您就是英雄母亲。‘三八’妇女节快到了,电视台要宣传您儿子的事迹和您,来的这位导演为了达到宣传目的,给您想出了您的一天,但您这一天不是这么过的,您要按照他的要求过,真与假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我就这么一点一点给她讲,加上她对生活的阅历,老太太就全进去了。”
刚开始排演这个小品,与赵丽蓉搭档的是一位名气不大的演员。距离春晚开播还差半个月的时候,有一位老艺术家说,老太太表演太厉害了,她“吃人”,就是根本看不到另一个人了。石林便临时找来侯耀文搭档,成就了春晚上的这一经典作品。事实上,此前一年,赵丽蓉曾在春晚上参与过一个小品节目,但没有太大反响。“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就了老太太,她也成就了我。一下子各个电视台的导演就扑上来了,各种约稿应接不暇。那时我就觉得小品是一种立足社会需要的形式。”石林回忆说。
赵丽蓉与巩汉林这对经典搭档也是石林促成的。“1991年,央视要准备一台庆祝建党70周年的文艺晚会,我给赵老师写了一个小品,有一个儿子的角色,找谁来演儿子,当时费了劲,要是跟赵老师配不上,这个戏就完了。巩汉林之前演过一个小品,扮演一个南方人,我有印象,就说要这个演员。这一合作,就延续下来了。”在1992年春晚上,赵丽蓉和巩汉林搭档演出了《妈妈的今天》。其中,赵丽蓉贡献了精彩的“探戈”表演——“探戈儿就是蹚啊蹚着走,三步一蹿,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腰,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蹚啊蹚着走。”
“这句台词就是写到这里就有感觉了。”石林说:“喜剧有很多技巧,‘司马缸砸缸’用的是相声的谐音技巧,而这一句用的就是变形技巧。不变形是正剧,一变形就是喜剧。本身60多岁的老太太唱起来就可笑,再加上唐山口音就更可笑了。还记得这个小品演完,第二天大街上都是‘探戈儿’,都是‘蹚啊蹚着走’。”
赵丽蓉和石林的合作大获成功后,也有人给赵丽蓉出主意,说别总跟一个人合作,给她介绍了其他编剧,结果那年赵丽蓉在春晚上的小品就没能出彩。这之后,赵丽蓉便认准了石林。1995年春晚《如此包装》、1996年春晚《打工奇遇》、1998年春晚《功夫令》、1999年春晚《老将出马》,都是两人合作的成果。
“《如此包装》获得了1995年‘我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小品类一等奖,所以1996年春晚筹备的时候,我就和老太太商量,说好事不能连着走,咱也没那么大能耐,就休息一年。结果春晚的领导和各方面人紧追不舍,央视文艺部的主任夜里10点多还给我打电话,说我应该来。于是我又赶紧联系赵老师,第二天就一起讨论,但折腾来折腾去,否定之否定,也没讨论出来,突然我想到一个点子,我说要不您来演慈禧?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形象好玩,但创作还是要从生活出发,我们就要找逻辑,开始推理,假如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准备开饭馆致富,到大城市学习开饭馆的经验,碰到一个没有任何商业道德的商家……那时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不货真价实,搞噱头,提高价。所以我们结合生活的感受,一点一点就成形了。”
石林想不到过了几十年,现在自己一刷短视频,还能看到好多人在模仿这个小品。“为什么有生命力?我想一是它本身娱乐性强,二是它反映了社会现实。一说起这个台词,人们就很有共鸣。你看‘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到最后就是讽刺,‘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喜剧创作并非易事。“春晚需要的基本是纯喜剧,这个其实很难。写一般题材的小话剧,符合创作规律就可以了,但喜剧的素材要求更苛刻,要能引发笑声。我们这一代人创作,习惯从生活中筛选素材。这就像淘金,一般性的题材,淘一两吨沙子,就能炼出金子,喜剧小品得淘10吨20吨沙子,才能炼出这点金子来。”
小品的创作之难,另一位喜剧编剧束焕也有同感:“年轻时老觉得写小品是练手的机会,后来才发现其实小品比影视剧还难写。因为小品是一个即时发生的故事,没有转场,没有时间跨度,舞台上的12分钟,就是生活中的12分钟,在这12分钟里要写一个完整的事件,人物关系要发生变化,最难的是还需要让观众笑得出来。”
在春晚的舞台上,束焕作为编剧一直是与蔡明合作的,从2009年到2019年。“刚开始合作那会儿,也是春晚参与人员最稳定的一个时期,按人头算节目,比如冯巩一个,郭冬临一个,郭达和蔡明老师一个,再加上年轻人的、重要行业比如部队的,再加相声,语言类节目基本就够了,这个稳定期大约持续了10年。”

石林(左)与编剧冯俐(中)、何庆魁在策划1997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受访者供图)

蔡明(左)和乔杉在排演2019年春晚上的小品《“儿子”来了》。(受访者供图)

1991年春晚,蔡明(右)表演小品《陌生人》。


2022年春晚,贾玲(左)表演小品《喜上加喜》。
蔡明第一次上央视春晚是在1991年,与巩汉林搭档,演一个夜里碰到陌生人的小姑娘,当时的编剧正是石林。在石林眼里,蔡明机智、反应快,她的很多包袱也是建立在机智上的。机智的形象,贯穿着蔡明近30年的春晚生涯。
在2013年的春晚小品《想跳就跳》中,束焕为蔡明写了一个“毒舌”人设。“我们想塑造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太太形象,但其实又特别有正义感,不双标,对谁都一样‘横’,挺可爱。其实我们当时一直没有想到‘毒舌’这个词,是在那天春晚直播之后,我们发现评论区都说这是‘毒舌’,我觉得挺好,把这个人设说准了。”
在束焕看来,春晚是角儿的艺术,一切都是人物。“这个人物,一半是作品中塑造的角色,一半是演员本身。在我们剧本初稿完成后,演员的二度创作非常重要。春晚喜剧作品很多是在不断地排练、磨合、否定之否定中,才创作出来的。有的小品剧本到了最后一稿时,第一稿中的一句话都没了,全部改过了,它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2022年,束焕与春晚有了新的交集。他是今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统筹,从去年夏天开始,他就忙着这件事,阅读候选剧本,跟节目主创沟通,帮他们寻找题材,对每个作品提供一些建议,帮着参谋。
与束焕刚参与春晚时相比,如今春晚语言类节目的主力军已大大不同。“在春晚的舞台上,你可能会觉得今年和去年没什么不同,去年和前年也没什么不同,但拉长时间看,稳定的阵容已经新陈代谢好几拨了。如今小品的领军人物是沈腾,公认的。”
沈腾是2012年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表演小品《今天的幸福》。那个节目让郑猛感到了新意。“当年看春晚直播的时候,家里热闹至极,我还没太看明白,这个人怎么从电视里钻出来,又非要从电视穿越回去。如此魔幻的剧情不太可能出现在之前春晚的小品里。沈腾和开心麻花是演舞台剧尤其是舞台喜剧出身的,他们充分利用了戏剧的表现手法,只要情绪对,要表达的东西对,这个事儿是不是那么符合现实不重要。这种新意能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欣喜。另外,沈腾表演的是都市题材,这和前一阶段乡村题材、地域特色的小品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春晚舞台与演员相互加持。继《今天的幸福》之后,沈腾连续三年登上春晚舞台,都是与马丽搭档,“沈马组合”开始有了国民认知度。2015年,两人主演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一举成为当年票房黑马。此后,沈腾春晚电影两开花,既是春晚常客,又有一部部喜剧电影接连上映,观众在影院里收获笑声的同时,也对他在来年春晚上的表现更加期待。
2022年,许子谅也与春晚有了交集,从纯粹的观看到尝试春晚语言类作品的创作。这年,他参加了央视的一档喜剧类综艺,节目组就是负责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团队。“节目组找来很多人,有做脱口秀的,有拍短视频的,有写电影的,有写情景剧的。可以看出,他们很希望通过这种碰撞,做出一些新的东西。”

2020年8月,北京一场线下脱口秀的演出现场。
许子谅也是带着“新”的标签参加节目的,他是sketch(素描喜剧)的编剧,属于当下正火的新喜剧范畴。高中时,许子谅偶然看了一集美国的喜剧电视节目,第一次接触sketch这种喜剧形式,大受震撼,“原来喜剧还能这么演”。与传统小品相比,sketch更为片段化,时长短,笑点密。2014年大学毕业后,许子谅便义无反顾投入喜剧行业,先是说脱口秀,后来又成为中国最早一批sketch综艺节目的编剧。
2020年网络综艺《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出了圈”,让看脱口秀线下演出成為时兴的文化消费方式。2021年,打着新喜剧概念的网络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又火了,sketch等喜剧形式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了解和接受。许子谅明显感觉到,“能接到的活多了,可以挑一挑了。”
虽然平台多了,但无疑,央视春晚的舞台仍是最有吸引力的那一个,“那就是最大的舞台”。
受所参与的央视喜剧综艺节目组邀请,许子谅也为春晚写了一个相声本子,以及几个围绕同一主题的小品大纲,但感觉完成得并不好,自己还越写越焦虑了。不同于给其他节目创作,给春晚写起来“感觉好难,即使写出点东西也自觉哪儿都不对”。首先是素材上,“春晚不是光给年轻人看,也是给我爸妈、我姥姥姥爷这个岁数的人看的,他们对新喜剧的接受程度还不是很高”。其次是技术上,“新喜剧综艺的表演舞台都很小,有的不过四五米,观众离得近,摄像机也给得很近,节奏快,转播出来就很好看。同样的东西,放在大了几米的舞台上,整个节奏就都不对了,包袱也不响了”。
“我们向很多新喜剧人都发出了邀请。”束焕说,他一直关注着脱口秀和新喜剧在国内的发展,《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一季录制时,他也坐在评委席上。束焕认为脱口秀和新喜剧对春晚是有加持的。“早先我也想在春晚舞台上来一些颠覆,但后来发现春晚还是有自身一些特定的创作规律,要是直接把新喜剧的优秀作品搬到春晚舞台上,也会很奇怪。所以我们会借鉴新喜剧的长处,糅到春晚的作品里。比如抖包袱的方式,他们常说,‘理不歪,笑不来’,有一些创意不会遵循纯现实生活的逻辑,而是对生活高度的概括,这些会给你启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剧偏好,但毫无疑问,每个年代的人都需要笑。从收音机到电视,从网络到线下,人们接触喜剧的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喜剧市场上的供给也越来越丰富。
最近,郑猛去看了一场脱口秀专场演出。“台下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对于笑点特别敏感,只要台上人的哪句话多少有点精彩,他们就会笑一笑,特别精彩的就会鼓掌,现场气氛非常好。当代年轻人的压力也大,脱口秀会刺破、讽刺一些社会现实,对他们来说特别解压。现在脱口秀的市场逐渐建立起来,全国的脱口秀厂牌有几十家,剧场也多了,年轻人能轻松获得很好的喜剧体验。”
与此同时,今年春晚正进入最紧张的彩排阶段,束焕也参与其中。“我们挑选的剧本,首先要符合喜剧的规律;二是能跳出以往的一些套路,比如近年很多作品习惯用误会法,还有都是大团圆结尾,我们希望能尽量回避。”至于挑选演员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会演喜剧。演喜剧就是演节奏,这个节奏感不是真正的喜剧演员就很难掌握”。
束焕希望观众能从今年的春晚节目里获得最简单纯粹的快乐和放松,最好,再有点共情。“这个共情可能是观众看完之后,觉得有一两句话还真是自己想说的。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嘴替’,能做到让观众觉得,春晚上这人真是我的‘嘴替’,我觉得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