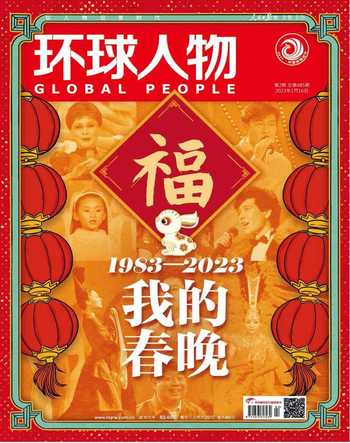让老百姓过个欢乐年
杨学义 陈娟

2012年春晚,在舞台科技的衬托下,杂技《空山竹语》美轮美奂。
我们清晰地记得那些春晚舞台上的动人旋律、欢声笑语,但总有一些有关春晚的人和事,台前的,远去了;幕后的,不知名。但这些人同样不可或缺,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成就着经典,“雕刻”着春晚,年复一年。
作为主持春晚次数最多的女主持人,周涛曾17次在除夕之夜与全国观众见面。虽然已经离开春晚的舞台,但她依然对当时的演出细节记忆犹新。
“5点半了,头发差不多做完了,下面该化妆了。”“7点了啊,该换衣服了。嗯,再过一会,主持人该候场了,演员们该准备了,谁从4号门进来,谁从观众席里出现,还有导播开始检查了,一号机、二号机……”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她摸了摸自己的手心说:“这些环节,熟到像我手心里的纹路。”
周涛曾说,她在央视工作期间,是最年富力强的阶段。更幸运的是,她又恰好遇到时代的东风:“我赶上了中国电视大发展、大繁荣的20年,等于我跟着中国电视一步一步走向它最辉煌的时刻。”
这20多年里,她見证并参与了春晚主持人的新老交替。当她1996年首次登上春晚舞台时,正是倪萍和赵忠祥这对“黄金搭档”最稳定的时期。而当她2016年最后一次担任春晚主持人时,李思思、尼格买提等曾经的“新生代”也成为国民熟脸了。

1983年首届春晚开场动画和四位主持人,左起依次为:王景愚、刘晓庆、姜昆、马季。

2018年6月24日,周涛接受本刊专访。从1996年起,她一共主持了17届春晚。(本刊记者侯欣颖 / 摄)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荣幸成为别人记忆的一部分。因为春晚,我成了大家记忆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一份功德。”说起往事,周涛满怀感激。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在春晚40年历程中,主持人已经成为记忆的重要载体。
1983年首届春晚,主持人以一种极具创意的方式和大家见面。一则1分29秒的动画短片拉开了春晚帷幕,主持人王景愚、刘晓庆、姜昆、马季分别以漫画的形象亮相,并变身寓意大丰收的馒头、桃子、玉米、小猪。其实,如果按当年的常规操作,应当用报幕员串起整台晚会,但晚会现场开通了点播电话,“我报你听”的方式不能让观众参与其中,导演需要应变和互动能力强的人来串场。靠“现挂”等即兴发挥艺术技巧吃饭的相声演员很快进入导演视野,马季和姜昆的入选也顺理成章。不过,两个人无法支撑5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于是加上了演员王景愚。可三位男主持人难免单调,导演又请来热映电影《小花》的女主角刘晓庆,不仅解决了单调问题,还用明星效应吊足观众胃口。
当时的主持风格和现在大相径庭,有时候甚至分不清主持人是在主持,还是说相声。他们机智、活泼、幽默的风格赢得了全国人民发自肺腑的笑声。整个上世纪80年代,马季、侯耀文、姜昆等相声演员继续担任春晚主持人,“专业主持+著名演员+相声演员”这套模式延续很多年。
进入90年代,春晚主持人越来越专业化,大多是从播音员或演员转型而来,长期从事综艺节目主持。从1991年开始,倪萍和赵忠祥便成为一对稳固的组合,两人也成为那个时代春晚的一大标志。
与全民关注一同而来的,是春晚主持人越来越大的压力。周涛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春晚上,在零点钟声敲响之前空出了1分48秒,加一首歌太短,添别的节目更不现实。有人拿着一沓电报找到周涛,让她念到一个时间点马上停止。她一看才发现,这一沓电报有传真纸、打印纸、手写纸,有的字迹都不清晰。作为当时的春晚新人,周涛没有多少时间熟悉电报内容,就被人匆忙叫上去了,刚上台时,她甚至都不知道站在哪里。“我心里非常干净,完全专注于手里那沓字迹不同、多处修改的稿件。”最终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观众并未意识到这个环节突兀,也正是凭借这样的救场表现,让她在后来的春晚被赋予了更多重任。
与刚诞生时不同,春晚主持人和演员的服装造型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1983年刘晓庆主持完春晚后,红彤彤的“晓庆衫”成为一阵潮流,甚至一度脱销,但刘晓庆穿的毕竟是日常衣服。1990年之后,春晚主持人的舞台装和生活装不再混为一谈,不仅色彩极为绚丽,裙装领口甚至开得很低,发饰开始新颖别致。1994年春晚,首次出现主持人换装的情况,倪萍开场穿了一件露背设计的大红旗袍,后来又换上绿装黑裙。
这样的改变,是为了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要求。“每年春晚的服装也是女主持人最重视的一个环节,因为那是一个全国性和合家欢的最大舞台。实际上我们认真准备,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春晚舞台的尊重。”周涛说,每个主持人都想把最好的形象奉献给全国观众:“我参与的每一届春晚,基本上都是3套礼服的体量,4个半小时的晚会总时长,几乎每一个多小时就换一套礼服。”
进入新世纪,无论主持人风格还是形象,都朝着越来越庄重大气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观众对字正腔圆的发音、华丽宏大的主持词越来越熟悉,主持人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失误都被成倍放大了。2007年春晚的零点倒计时阶段,6位主持人的口误、抢话等尴尬,就被称为“春晚黑色三分钟”。
“越是大舞台,你越不可能随心所欲去做一些事,你要完成一些既定的东西。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就依依不舍地和它说再见了。”和周涛交流时会发现,无论在回忆央视,还是在回忆春晚时,她都流露出一种坚定和留恋交织的复杂情绪。其中最强烈的,是她对春晚观众的一片真情。“无论是演员,还是主持人,一定要尊重观众,把最真诚、最质朴的状态呈现给观众。要打动观众,不要去引领观众,‘拿’着观众往前走。”或许,这就是在不断面对挑剔和质疑时,春晚依然能够经受住时代考验,持续前行的重要原因。
从1998年春晚开始,2000平方米的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开始启用,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是央视春晚的常驻地。从那一年到2022年,导演已经换了一个又一个,但除了2020年,美术总设计一直是陈岩,他称得上是春晚“铁打的营盘”了。

多届春晚美术总设计、双奥核心主创团队成员陈岩。

1986年春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小品《羊肉串》,背景是孔雀开屏造型。
不少观众依然对1986年春晚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羊肉串》记忆犹新,同时也记住了他们的身后“孔雀开屏”的鲜艳舞台背景。陈岩与春晚的首次结缘,便是从那些孔雀羽毛开始。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很快就担任春晚美术助理。从舞美角度来说,那时的春晚更像一个小型联欢会。陈岩清晰地记得,算上他,春晚剧组的美术、道具一共只有4个人负责。导演派他们几个到上海买孔雀羽毛,陈岩和同事非常兴奋,“首先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二是有中央电视台的身份,第三是要做春晚。可以说是‘膨胀’到了极点”。陈岩心底知道,他们做的只是把羽毛插上,“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舞台不会这么简单,我们会把它做成产业。”
后来的春晚舞台的确有很多探索和进步。1990年春晚,舞台灯光和背景层次都更加丰富、现代了。1993年春晚,将现场改造成包厢式,大厅中间为舞台,三面为观众,观众席还被设计成两层立体场景,不仅拉近了和舞台的距离,还丰富了视觉场景。1994年春晚,舞台面积扩大了,占到整个演播大厅的2/3,舞台中央还出现一个12米的大转台,恢弘大气。
不过这一时期,陈岩到欧洲留学,与春晚渐行渐远了。直到1997年,他突然接到国内电话,春晚导演组邀请他担任美术总设计。他首先是不敢相信,紧接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邀请。“他们问我:你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吧?我肯定得说没离开。其实我当时在国外赚钱就靠送报纸,然后还得学习。就这样,我吹着牛就回来了。”
当时负责春晚的领导提醒他:你可得想好后果,失败了怎么办。陈岩回答:“我都没成功过,干吗怕失败啊?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还对领导说:“您可得想好了,如果用我,可就再也下不去了。”陈岩之所以敢这么说,是深谙舞台规律:“整个春晚的发展,不是在于每年更换一个艺术家,而是要建立一个体系,再建立一种风格。”
首次进驻一号演播大厅,春晚可以施展的空間变大了。陈岩的最大目标就是让舞台动起来,他把工业时代的机械亮点带进来。晚会开场缓缓打开的龙柱、中央的喷泉,特别是机械升降台,都成为那届春晚的亮点。
陈岩一直说,春晚和其他晚会不一样,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审美应当符合中国人的特点,就像吃年夜饭,就应当四世同堂都照顾到,虽然每年就是那些菜,但必须还得有。”具体来说,就是要红红火火过大年,舞台要以红色为主,一些传统的民族元素也不能少。
1999年春晚以中国传统的大红门为背景,醒目的九颗金门钉紧扣“九”的概念,象征着新世纪大门即将叩开。2000年春晚将舞台设计成球状,有“团圆”和全球化的双重寓意。圆形架子上方,有镂空巨龙图案,寓意龙年祥瑞。2004年春晚,用现代科技将舞台变成了大红灯笼的形状,又通过搭建开合阶梯,形成三层表演区域。

2007年春晚,舞蹈《小城雨巷》。

2012年春晚,王菲(右)和陈奕迅演唱《因为爱情》。
在此基础上,陈岩也有一些大胆的尝试。2002年春晚,舞台首次打破稳定结构,采用错落有致的“非对称”设计,同时加入了不少中国结元素。2003年春晚,舞台根据具体节目搭建不同场景,比如歌曲《让爱住我家》,一家人在前景温馨献唱的同时,一组演员在后景营造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境,丰富了舞台信息量。
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熟的舞台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观众需要了。陈岩看到,升降台出来时,观众已经不再鼓掌了。2004年,陈岩看了席琳·迪翁的演唱会,在后台看到LED屏幕时,他大为震撼。回国后,他凭着记忆在《梦想中国》栏目中做实验,没想到观众反响很热烈。于是这项技术就用在了2005年春晚上,LED大屏幕开始在春晚地面和侧幕中使用,这标志着春晚从机械舞台走入现代舞台。
从此,陈岩将精力用到了LED屏的视频制作上,以便用LED大屏幕的加持,来完美配合节目。这的确让不少节目取得成功,2007年春晚删除了舞台上稍显累赘的装饰物和两侧不透明隔断,营造出舞台后区和两侧的一面超大电视墙,让舞台简约、大气。舞蹈《小城雨巷》就让观众第一次看到视频与舞蹈的完美融合。这些勇敢的尝试,还帮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放异彩。作为开幕式美术总设计,陈岩将LED屏用在了地面徐徐展开的画轴上。而奥运会开幕式的技术探索又进一步促进了春晚舞美的发展,2009年春晚吸纳了不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班底成员,LED大屏幕与节目更加深度地融为一体。在舞蹈《城市变奏曲》中,演员与大屏幕中高楼林立的北京城形成互动,展现了城市的飞速变化,达到了虚实相生的效果。

2012年春晚,杨丽萍表演舞蹈《雀之恋》。

2009年春晚,舞蹈《城市变奏曲》。
2012年春晚,是陈岩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全息LED首次大规模应用,地面、天棚、舞台正面及两侧全部采用全息LED屏幕,三维立体效果让科技与节目的关系更为紧密。陈岩的看法是,科技虽然已经成为节目的一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艺术的情感,如何使科技帮助演员更好呈现情感,应该是重点思考的问题。那一年的春晚上,有两个节目就是他思考的结果。一个节目是杨丽萍的《雀之恋》,当舞台后方大屏幕呈现的孔雀开屏画面与杨丽萍呈现的造型融为一体时,舞者塑造的孔雀形象更加饱满了。另一个节目是王菲和陈奕迅演唱的《因为爱情》,两人最初是一前一后隔很远站着,音乐一响,舞台中间升起一座全息影像的桥梁,整个舞台飘起了全息影像构建的花瓣。配合音乐,“桥梁”“鲜花”构建了唯美的爱情意象。
后来,陈岩让越来越多的“黑科技”上了春晚。2017年春晚,舞台可升降屏幕达到了创纪录的173块,其中地面132块、天空41块,为观众呈现出天地浑然一景的场景。2019年春晚,又首次实现了全媒体传播,在4K、5G、VR、AR、AI等多方面进行技术创新。
不过,陈岩还是很冷静,始终将科技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而不是艺术本身。他说:“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唱歌的人光为了(舞台)漂亮,那挺可怕的。”在他的概念里,西方美学是“三维”的,而中国美学是“二维”的,通过看似有限的“形”传递更多的“意”,这才是他的追求。中国人不一定要建造世界最大舞台,但一定要创造最能激发人无限遐想的舞台,这才是科技对舞台的意义。
长期研究春晚的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宫承波在其主编的《春晚三十八年》一书封面上,特意加上了一个副题:伴行改革开放,欢乐国人大年。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阐述春晚的发展意义。“伴行改革开放”决定了春晚要把体现时代元素的时事、科技、潮流等融合进去;“欢乐国人大年”决定了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春晚都应当将老百姓的欢乐放在重要位置。在春晚的发展历程中,始终都在寻求这对关系的共融与平衡。
宫承波曾跟访首届春晚导演黄一鹤,让他印象极深的是黄导的坚定初心:“我们不止一次聊过,当初为何要办春晚?他说其实很简单:让老百姓过一个欢欢乐乐的好年。”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1983年和1984年春晚大获成功后,黄一鹤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将1985年春晚的举办地搬到四面环座的北京工人体育馆,让春晚场景从“茶座式”变成气势恢宏的“场馆式”。“1984年,我看了国庆阅兵式、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再也坐不住了。我们是国家一级的电视台,晚会节目应该符合身份,向世界展示我们的繁荣,让人民看到希望。另外,连续两年搞茶座,模式谈不上创新,观众容易厌倦。”从黄一鹤的回忆可以看出,他想要办出大国气势。
不过,现实并未如他所愿。由于体育馆环境超出了导演组驾驭能力,观众距离演员非常远。舞台上精心布置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景观也没被摄像机拍进去,观众看到的是一片黑压压的背景,与过年热闹喜庆的氛围很不相称。问题还有很多:彩排准备不够、港台风太浓、广告太多……后来主管领导和导演团队总结,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电视规律,也没有根据自身科技实力准确把握春晚动向。
雖然1985年春晚有很多遗憾之处,但整个80年代的春晚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宫承波认为:“从艺术魅力的角度来讲,真正大美的、富有感染力的东西,都是朴实自然的。”这也给了后来者启发,不能丢掉春晚最宝贵的东西,“不管科技如何发展,春晚都不能单纯炫技,这样就不温暖、不真实、不真诚了”。

2006年春晚,舞蹈《俏夕阳》。
后来的春晚有很多形式上的探索。1988年春晚以北京演播室为中心会场,同时穿插广东、四川、黑龙江三个省台的实况转播,首次突破了地域限制,将春晚舞台放到全国多地。1990年春晚,评书演员田连元、小品演员朱时茂等明星以队长身份,率领队员开展除夕夜比拼,串联起整场晚会。1996年春晚,北京、上海和西安首次实现“三地联演”。通过卫星实时传输,演员通过大屏幕实现了三地隔空联演,打破了单一会场的单调。直到1998年春晚到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举办后,形式相对稳定下来。
但这种稳定又带来千篇一律的模式化问题。“文艺创作永远要抓住时代的脉搏,最怕失去生机活力,变得老气横秋。”宫承波认为,春晚日益成熟的同时,也迎来新的挑战。“既然模式化了,就要不断突破模式;既要走向成熟了,还要走出成熟,保持生机和活力。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回归人民群众,老百姓的现实生活需求永远是创新源泉所在。”
“开门办春晚”就是突破模式、“走出成熟”的大胆尝试,催生出大量经典作品。2005年的《千手观音》是“开门办春晚”取得强烈反响的第一个节目。2006年春晚,以唐山皮影为灵感的舞蹈《俏夕阳》走红,一群基层老太太形神兼备的表演具有独特视觉冲击力。
随后几年,越来越多的“草根明星”通过春晚舞台大放异彩。2008年,盲人歌手杨光演唱一首大气磅礴的《等待》,令人格外动容。初出茅庐的王宝强在《农民工之歌》和小品《公交协奏曲》中两次以农民工形象出现。2011年,在专门开辟的“我要上春晚”版块上,西单女孩任月丽、旭日阳刚组合、深圳民工街舞队轮番登场。2012年春晚,“大衣哥”朱之文唱了一曲《我要回家》,还很青涩的开心麻花演员沈腾、艾伦首登春晚舞台。
在“开门办春晚”的浪潮中,主持人也被吸纳进来。2014年春晚上,演员张国立加入主持人队伍,以接地气的语言和插科打诨的方式与观众互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春晚的主持人司仪化风格。甚至有人说,这很像是首届春晚风格的复归。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新人因走上春晚舞台被观众熟知。宫承波说,这正是春晚的可爱之处。无论是主持、舞美,还是节目编排,春晚能够一直向前走的秘诀依然是真诚。宫承波说:“实际上,植入广告、过度炫技这些问题,就是不真诚导致的。”情感才是春晚连接观众的唯一桥梁,春晚之所以能够在今天依然打动我们,就是因为这座情感的桥梁依然稳固,带我们越过每一年的浪潮澎湃、际遇起伏,在这一晚准时回到家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