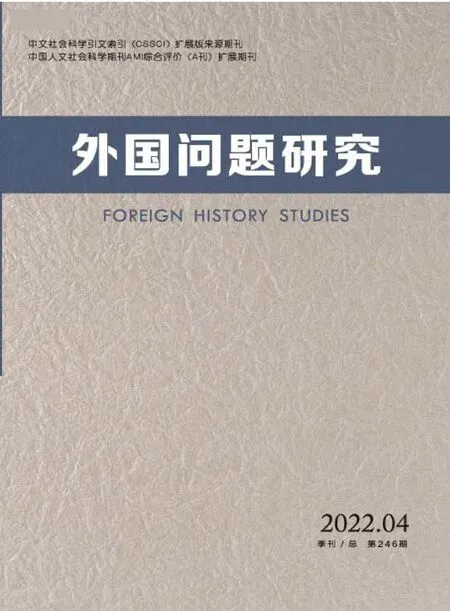“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公学堂历史教科书的变迁
谷丽伟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觊觎由来已久,甲午战争清军陆、海战皆败,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日方除了索要巨额军费赔偿,还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由于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将辽东半岛有价偿还,这令当时身在旅顺的德富苏峰“愤懑无比”,“捧了一把旅顺港外的沙砾,用手绢包起来”,当作日本“仅剩的一点辽东的版图”带走。(1)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 七十八日游记》,刘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82页。其后日俄战争爆发,最终缔结《朴茨茅斯和约》,约定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让与日本,南满铁路及支线、附属地也归日本经营,“出兵一百万,糜款十五亿”,(2)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東京:緑蔭書房、2005年、第39頁。日本终于攫取到垂涎已久的特权和利益。
为了经营南满,1906年日本撤销各地军政署,改关东总督为关东都督,掌管旅、大租借地。同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成立,经营包括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矿、农、林等东北的重要产业,假股份公司之名,行政府机关之实。此后,日本不断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并进行殖民渗透,在修筑铁路以控制东北经济命脉、鼓动日人移居东北的同时,如何对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人加强殖民化宣传与教化,以扶植亲日势力,也被提上日程。作为日本在东北的主要行政机关,关东厅与满铁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不断修复、扩建公学堂,(3)“关东州”及满铁为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儿童开设的小学称“寻常小学”,所用教科书与日本国内一致,“公学堂”指日本殖民当局针对中国人在城镇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设立中、高等教育机构,以收容中国学生,堂长人选自不必说,“教员也尽量聘用日人”。(4)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大連:大連文教社、1935年、第118頁。对于“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各级教育的基本情况、特点及影响,其他学者有宏观性的研究,(5)谢忠宇:《满铁附属地学校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年;刘振生:《近代东北人留学日本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但在关乎历史的细节处,论述尚显笼统与模糊,有学者就认为,“‘满铁’附属地公学校的教学科目、教材和课时安排与‘关东州’的公学堂基本相同”,(6)刘振生:《近代东北人留学日本史》,第75页。显然未虑及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州”与满铁附属地所面临的不同形势。本文即以“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公学堂所用历史教科书的变迁为视角,考察日本当局如何根据中日关系以及两地的局势变化来调整其殖民教育策略,进而揭露日本试图切断东北与其他地区的渊源、将中国东北历史与日本历史嫁接的企图。
一、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州”公学堂的历史教科书
日俄战争之后,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关东州”被日本视作“准殖民地”,“如同台湾、朝鲜的感觉”,(7)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岩波書店編:『岩波講座教育科学第十冊』、東京:岩波書店、1932年、第23頁。因与清政府签有《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域内环境相对简单,“在白仁长官(‘关东州’都督府首任民政部长白仁武)时代已实行纯然的同化政策,公学堂唱‘君之代’,施行日本式训练”。(8)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23頁。1916年,关东厅设立旅顺师范学堂,(9)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93頁。目的是为公学堂培养符合日本殖民当局意愿的中国教员。在公学堂的科目设置上,为避免激化当地人的民族情绪,1906年3月“关东州”民政署民政长官石塚英藏氏发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第一条“生活必需的智识技能”止于汉文、算术两科,缺少地理、历史、理科等日常生活最必要的科目。(10)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119頁。1915年3月修改公学堂规则,废除六年学制,分置初、高等科,修业年限分别为四年、二年,并于高等科教科目中加入理科、地理,(11)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121頁。历史科仍付阙如。1920年、1922年分别有“朝鲜教育令”“台湾教育令”改革,“台湾”、朝鲜开始增设课程“日本历史的大要”,直接将台湾、朝鲜人视作日本国民,讲授与日本内地学校相同的日本史。在这一背景下,1923年3月,公学堂规则第三次修改,首次于高等科中加入历史科目。(12)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121頁。
历史既被列为正科,由于中华民国发行的历史教科书不符合“关东州”及满铁的教育方针,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遂着手编辑教科书,1923年10月发行《公学堂历史教科书》(稿本)卷二;1925年发行《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一;1930年发行《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二;1932年3、4月分别发行修订版《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一、卷二。卷一为中文版的中国史(附日译文),卷二为日文版的日本史。公学堂高等科第一学年讲授“中国历史的大要”,由中国教员担任,第二学年讲授“日本历史的大要”,由日本教员担任,每周与地理科共占三个小时。
《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一(1925)大致遵循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脉络,从中国太古时代讲起,直到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但有意增加女真、契丹人的分量,凸显女真族三次建立独立政权的事迹,如第十二课上代满洲、第十六课渤海、第二十课金、第二十九课清之兴起。至于金朝灭亡的原因,在于“自迁都燕京后,百官皆学汉字,衣汉服,风尚日趋靡弱,惟在满洲金人率质朴”。(1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28頁。不止如此,在“渤海”一课中,除了提到渤海国与唐朝修和交通,“夙遣朝贡使于唐”,还专文述及渤海国与日本的历史渊源,“与日本屡次修交,以取其文化……其使日本者亦多长诗文之才”,(14)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25頁。意在为日本当局宣扬的“日满提携”提供历史依据。另一方面,日本也为其在南满具有特殊权益的帝国主义立场辩护,称甲午战争是“清廷派兵朝鲜,有所违于《天津条约》,遂与日本启衅”,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占据东北,在鸭绿江沿岸修筑炮台,“足以危东亚之局,固为所不忍默视”。(15)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38—39頁。
1932年3月发行的《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一与1925年版内容基本相同,但文体从文言变成了白话文,可能是“被日语学习占据太多时间,中国学生的国文水平降低难以理解文言的缘故”。(1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東京:緑蔭書房、2005年、第212頁。事实的确如此,据1906年“‘关东州’公学堂规则”第一条,“公学堂以教授中国人子弟日语、施以德育以及传授生活必需的智识技能为宗旨”,(17)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119頁。将教授中国儿童日语当作教育上的最要紧事。1917年,深谷松涛、古川狄风兄弟踏查“关东州”,留宿村庄时,便不止一次遇到学习假名并能够灵活使用日语的儿童。(18)深谷松涛、古川狄风:《满蒙探险记》,杨凤秋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4页。1922年4月创立的大连西岗子公学堂,初等科四年期间中国文、日本语每周讲授时数分别为八九九九、六六七八,高等科两年皆为七,(19)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144、145頁。日语学习时间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一(1925)若隐若现、煞费苦心地试图切断“满洲”与中国的历史渊源,1923年《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二(稿本)“日本历史的大要”则与之相唱和,大幅宣扬日本建国的神话与历代天皇的“仁德功业”,意在潜移默化地将日本的“皇国史观”植根于学生心中。
1930年修订发行的《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二同样以关于天皇的记述为中心,但与1923年的稿本相比增加了明治以降的现代史比重,对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国内尊王攘夷论的盛行、甲午战争前清日在朝鲜的角力等皆有明文叙述。时隔七年,新版之所以作此改动,据日本学者竹中宪一推测,是由于1928年末张学良“东北易帜”,排日运动高涨,神话教育在政治上失去“效力”。与其对中国学生进行神话教育,不如增加现代史部分,令其理解当前殖民地政策的“正当性”更重要。(20)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215頁。
二、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公学堂的历史教科书
满铁针对东北地区中国人设立的初等教育机构最初亦称“公学堂”,1931年4月改称“公学校”,但两者在性质、内容上并无太大差别。(21)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368頁。相较于“关东州”,满铁附属地被中国人的居住区包围,“犹如大海中的小舟”,是“庭石般的存在”,(22)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23頁。很容易受中国政局变动的影响,成为排日运动的对象,“不只是日本人,也针对上日本人学校的中国学生”。(2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172頁。因此,满铁当局以“日中亲善、共存共荣”为号召,“日人教师多为留学中国者,中国人教师也不特别培训,多采用他们中的读书人”。(24)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24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20年代之后排日运动高涨,1923年奉天教育界又针对满铁附属地展开了教育权收回运动,故可以1923年为限,将满铁附属地公学堂所用历史教科书的情况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1923年前满铁附属地公学堂的历史教科书
盖平公学堂是满铁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所中国人学校,早在1909年成立。在仅以“通知”形式发布的《盖平公学堂规则》中,历史课程被列为教学科目,不过未标明讲授课时。(25)満鉄地方部学務課編:『満鉄教育沿革史』、大連: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1937年、第1564頁。1914年3月公布《附属地公学堂规则》,自高等科开始,历史、地理每周共讲授三课时,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 新历史》与中华书局的《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由中国教员以中国语讲授。(2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209頁。1917年,满铁在教育研究所内设立教科书编辑部,负责满铁管辖范围内日、中各学校教科书的编纂,(27)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562頁。面向中国儿童的公学堂尽量“选择采用文部省台湾总督府及上海等编纂的教科书、参考书”。(28)広島高等師範学校編:『大陸修学旅行記』、1915年、第162頁。当时经民国教育部审核采用的教科书主要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出版,教育研究所教科书编辑部删除其中的三民主义及排日记事,经关东厅长官核定后方准发行。
1920年关东厅设立教科书编纂委员会,负责“关东州”教科书的编辑,“狭小的地域内,(‘关东州’、满铁)各自编辑教科书,颇费人力、财力,导致难以提供价廉质优的教科书,儿童转校时也多有不便”。(29)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562頁。鉴于此,关东厅、满铁协议合署办公,组成两家合作经营的编辑部,设在南满洲教育会内,计划自1922年起,“州内、满铁编纂、使用同一教材”。(30)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368頁。然而,这一设想在日益高涨的排日运动形势下未能实现,一直到1932年伪满政权建立前,满铁附属地公学堂未能如“关东州”一样讲授“日本历史的大要”,日本史仅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讲授。
既然与“关东州”使用同一教材的计划难以实现,满铁当局便尽可能减少讲授中国历史的时间,1923年4月满铁公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公学堂规则》,历史、地理作为高等科社会科目,每周由三课时缩减至两课时,课程为“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大要”“中国及世界地理的大要”,(31)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378頁。采用中华书局的《新式历史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历史教科书》。(32)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209頁。由于满铁附属地公学堂使用民国教科书,日本学者竹中宪一据此认为,“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内针对中国人的初等历史教育与中国其他地方无太大差异”,(3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172頁。但这仅就教科书而言,由于满铁辖内的公学堂堂长皆为日人,同时在补充教材的选择,以及教学实践中也大有可操作的余地,因而针对中国儿童的殖民化教育仍在日益深化。比如,盖平公学堂在开校典礼上便让学生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以至于村民怀疑学校建立是为了培养日本士兵。(34)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379、380頁。
日本的殖民化教育令东北教育界产生亡国灭种的忧思,时任奉天教育厅厅长的谢荫昌深怀警惕:“今南满铁道横贯我之中心,其所设附属公学,以日本语言文字编写历史、地理教我儿童。年号则用日本的‘大正’,唱歌行礼则三呼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之声彻于霄汉,我之昆季谓他人之父兄为父兄者,有不为之痛心疾首者乎!”于是,谢荫昌呼吁“奉省教育上应着手从事者,即收回南满铁道用地国民教育权是也”。(3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第39页。他就此问题数次向代省长王永江提议,并派省视学会同教育会调查日本各学校的情况,通过报刊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主张在满铁附属地内开设中国人自办的学校。
(二)1923年后满铁附属地公学堂的历史教科书
1924年,奉天教育厅倡议收回教育权,抵制日本同化式教育的文化侵略,奉天当局向日本总领事提出要求,“希望日本方面明年度起停止招募公学堂学生”,(36)中国社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编:《大事史料长编草稿·一九二四年五月》,1961年,第49页。遭到关东厅及满铁拒绝;1925年6月上海五卅惨案;1927年5月田中内阁第一次出兵山东;1928年5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田中内阁第二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一系列的事件致使东北各地学生排日运动高涨,1927年9月,熊岳城、公主岭农业学校、营口、辽阳商业学校等,或相继废校,或着手改革,于是满铁内部出现了放弃对中国人实施教育的“悲观论调”。(37)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854頁。为了避免激化中国人排日的民族意识,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于1923、1925年编纂的《公学堂历史教科书》卷二(稿本)、卷一不仅未能在满铁附属地施用,反而不得已在既有民国教科书删改版中加入孙文、青天白日旗等内容。(38)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856頁。即便如此,南满洲教育会仍于1929年出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有高严氏辑录的《满洲历史教授资料》,作为“满洲初、中等学校以及一般诸学校讲授东洋历史的参考书”,(39)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143頁。该书目次为:古代的满蒙、渤海、辽、金、元、明与清初、近代满蒙。观其目次可知,在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满铁附属地公学堂表面上采用的是中华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删改版,但在具体讲授中已在灌输“满蒙独立于中国”的殖民意图。
1928年末东北局势更为紧张,张学良宣布“易帜”,东北四省降下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凡学校或聚集场所,必张贴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与遗嘱”。(40)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5頁。自1929年初,东北政务委员会制订新规,“寒假后东省各级学校开学均须施行党化教育,改用党化教科书籍”,(41)《核阅党化教科书》,《盛京时报》1929年1月27日,第5版。自小学开始设“党义”科目。在三民主义的宗旨下,“教育者逐渐从日本留学生转向欧美留学生,一切的学制由日本改为美国制”,(42)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5頁。“排外教科书也传播至东北四省,(满铁)周围的中国侧学校一律使用”。(43)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854頁。
根据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1929年9月发行的《中国排日教材集》,国民政府治下教科书中的排日内容比比皆是,力图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如《新中华历史课本》高级用第四册第十七课称“日本民族本是好侵略的民族”,又谴责日本两次出兵山东,是“国民的奇耻大辱,不能一刻忘记”。(44)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96頁。《新时代高级小学 历史教科书》第二册讲甲午战争,与“关东州”使用的《公学堂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截然相反,指责日本“首先吞并琉球,不理中国的抗争”,硬称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屡次煽动内乱”。(45)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65頁。正式教科书之外,另有宣传抗日的各种国耻教材、唱歌集,《国耻读本》第二册《黄大》一文将中国喻为懦弱无能的村民黄大,日本是侵吞黄大房产的奸诈租客,《小学党化教育唱歌集》中有《五七国耻纪念歌》:“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他并吞了……又提出灭国条,无公理蔑人道……最伤心四年五七噩耗,为奴为仆眼前到,这国耻何时消。”(4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98頁。在悲壮的抗日情绪中,日本的形象不再是“中日亲善”的主导者、东亚和平的维护者,而是曾向中国朝贡,屡蒙中国文化恩惠,经近代维新洗礼,不知反哺却落井下石、同根相煎的暴发户。排日教科书的对象是十岁左右的少年,联想到十年后彼等将成为激烈的反日派,满铁当局“寒心不堪”。
铺天盖地的抗日宣传、激荡的民族情绪,未使日本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却步。东亚经济调查局一面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一面警告主张“认同关税自主,放弃沿岸、内河的航行权,则日中亲善可实现”的某些“考虑轻率”的日本人,如果按照排日教材所言,满足现代及今后的中国人,意味着补偿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切损失,“关东州”的返还自不必说,甚至必须放弃朝鲜、琉球,归还台湾,“若失去上述地方,日本只有灭亡一途”。(47)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94頁。
面对措手不及的新形势,满铁召开中国文教科书调查选择会,摸索相应对策,最初的权宜之计是修改、复刻旧版教科书。1930年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发行《新学制 历史教科书》,便是先取得商务印书馆的许可,将商务《新学制 历史教科书》中的五色旗以及北京、辽阳等地名进行修改。同时,不但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内,不准中国施行任何教育,即便中国境内学校之邻近两地者,亦常被日警干涉校内行政:1929年春日警屡次前往辽宁省海城南台小学,禁授三民主义;1930年5月,日警禁止铁岭小学悬挂国耻地图及三民主义图解;1930年秋,日警干涉吉林省长春小学校悬挂三民主义大纲。(48)吴瀚涛:《东北与日本之法的关系》,北平: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第68—69页。
三、九一八事变后的新版《历史教科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撤出关外,翌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形势巨变,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遂于1932年4月发行《历史教科书》上、下册,上册为“满洲史”,下册分为东洋史、西洋史两编,中国、朝鲜、日本皆列入东洋史范畴。新发行的《历史教科书》适用于“关东州”内外,(49)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138頁。南满洲教育会当初谋划在“(关东)州内、满铁编纂、使用同一教材”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不止如此,因伪满政权建立仓促,直到1935末,“国定”小学教科书才由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纂告竣,在此之前,南满洲教育会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作为“审定教科书”暂时使用,以清除“东北易帜”后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排日教科书的影响。
新版《历史教科书》上、下册与以往满铁附属地公学堂使用的民国教科书修改版截然不同,凸显“满洲”主体性的意图也比“关东州”的《公学堂历史教科书》更加昭然若揭。上册直接设置为“满洲史”,不再讲授中国通史,而从上古满洲族“肃慎”讲起,课目依次为:肃慎、万里长城、汉人的移居南满、挹娄和夫余、高句丽的兴亡、渤海的建国、辽的兴起、金的统一、蒙古的勃兴、蒙古的盛世、元的盛衰、清的创业、清的黄金时代、清的满蒙政策、俄国南下政策和清国“满洲”实边策、“日清战争”和俄国的经略“满洲”、日俄战争与“满洲”、清的灭亡和革命的争乱、最近的“满洲”。如此的叙述脉络下,似乎东三省与东蒙地区自古以来上演的只是女真、契丹、蒙古族的政权更迭,汉人被描述为无足轻重的外来角色,“因着(汉)武帝的东征,汉人就逐渐地移居于南满,开垦耕地”,(50)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76頁。“清朝虽然限制汉人入满洲境,可是他们仍然注目到柳条边墙及万里长城外,继续着向满洲广野移住,更有汉人想不到的福音,是清朝为遏止俄国的南下,才有奖励汉人移居满洲的一件事”。(51)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0頁。传统中国通史的叙事方式,中原、东南地区是中心,东北是边疆,日本殖民意图下的“满洲史”则恰好相反,“满洲”是具有独立国家主体性的核心,长城以南的汉人成了外来的“他者”。正如《中国排日教材集》增订本《打倒日本》的监修者保保隆矣所言:“将满洲原为东夷北狄这一历史事实巧为理论化,是教科书编辑上的重要技巧。”(52)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49頁。
新版《历史教科书》上册夸许清朝开国的事迹与极盛时代的文功武略,以提升伪满洲国的存在感,称清太宗改国号为清,“是要使人心振刷一新,并表示综合满、汉、蒙各民族,创成大帝国的大雄图”,将金国改称“满洲”,“这是满洲二字最初出现于东洋史上的”。历史上“满洲”与日本有“两情相悦”的往来,当下的日本被鼓吹成勇于革新、值得信赖的盟国与救世主,“清国当着北受俄,南受英法两国压迫的时候,日本从久行锁国的梦中惊醒,成了明治维新。明治大帝之治世时,国运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颇为昭著,又是世界人人惊叹的时代”。(5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2頁。日俄战争被宣扬为“满洲”的“乾坤再造”,日本“为保持极东的和平,和自卫上着想”,更为“清国的领土保全,韩国的自由独立,以及东亚的和平”,“不得已,才布告宣战”。由于日本的“这一次大牺牲”,“清国才免去瓜分的大祸,且能使轻视有色人种的欧美人等,从良心上反省,并促进亚细亚民族的奋起,实在都是依赖日本胜俄的成绩”。(54)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3—94頁。至于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教科书辩称“欧战后日本把青岛还附民国,以表示没有领土上的野心”,完全抹去要求中国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时的蛮横,而条约中妄图分割满蒙的侵略行径,也被日方粉饰为善意之举,“在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地,因为有铁道的便利,经济和文化都能发展得很快,将来或能建设理想生活的区域”。(55)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6頁。
不止如此,由于“东北易帜”打乱了日本谋取东北的计划,中国形式上得到统一,修建“满蒙新五路”、临江设领事馆、课税等“满蒙悬案”成为日方唯恐避之不及的“国际问题”,“满洲史”遂对张学良父子极力贬低。“皇姑屯事件”乃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教科书却描述成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结果,“蒋、冯、阎三派就组织国民革命军,协力压迫他,他不得已,才向奉天退归,途中被炸弹击毙”。(5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6頁。张学良爱国抗日的民族壮举,被污化为“忘敌事仇……不知持盈保泰,但极力扩张军备,储蓄私财,充实自己的势力”,“忘却和睦邻邦的大义,遂蹂躏日本在满洲的各种权利,并迫害鲜农”。(57)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7頁。九一八事变是在关东军的授意下,满铁“守备队”力图打破“现状”的自导自演,却栽赃嫁祸成东北军炸坏南满铁路线、击射巡察路线的日本兵而引起的不幸大冲突,日军将东北军从“满洲”驱逐,“满洲”人民才得以从虐政中被救得更生。紧接着1932年春,“完全脱离国民政府和旧军阀等关系”,“尊重民意,努力治安,使三千万民众享最大幸福的新国家”的“满洲国”便粉墨登场。(58)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7頁。
包藏祸心的“满洲史”既然将“满洲”从中国分离,于是在《历史教科书》下册中,中国史便被划入与西洋史对等的东洋史大范畴,与朝鲜史、日本史并列。在“最近世的东洋”两节课中,日本俨然以“共图东洋的和平”的盟主自居,日俄战争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令之飘飘然自画自赞,“从此以后,日本占有亚细亚大陆中的坚固地步,东洋诸国,仰望日本作指导者”。(59)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国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117頁。
结 语
通过梳理“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公学堂历史教科书的变迁,可知日本对东北儿童的历史教育与其近代以来侵略满蒙的长期国策相一致。首先根据“关东州”、满铁附属地的不同形势,设置两套平行的教育体系,“关东州”几乎不受中国动荡局势及学潮的影响,即便讲授以“皇国史观”为核心的日本史,也较少遭受反对。满铁附属地公学堂则处于可进退伸缩的前沿,历史教科书根据各方势力的消长适时做出改动。其次,在公学堂历史教科书不断调整的脉络下,日本试图将“满洲”从中国分离的主调始终未变,从开始的小心翼翼,到九一八事变后的明目张胆。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伪满洲国建立的近三十年间,日本在东北地区苦心经营以扶植“亲日派”,进而攫取土地、资源等巨大利益。1914年成立的四平街公学校,首批毕业生大都任职于满铁控制下的四洮、洮昂铁道,(60)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385頁。另据统计,1932年后在伪满洲国政府任职的原留日学生中,原籍为东北地区者占总数的90%,担任伪满洲国政府大臣的大多数是“关东州”或奉天出身,(61)刘振生:《近代东北人留学日本史》,第110页。他们多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末或20世纪初,其童年正与日本开始在东北攫取教育权、实施同化政策的时期相重合。1920年代,中国人排日情绪高涨,一些日本人开始对在东北的殖民教育感到踌躇,1928年安藤基平在《满洲公论》上回应这一消极态度:“日本人开口即言为中国人教育投入了巨资,然与日本在满洲获得的利益相比,不值一提。”(62)島田道弥:『満洲教育史』、第850—851頁。可以说,安藤氏口无遮拦的自白无疑是日本意图吞并东北、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