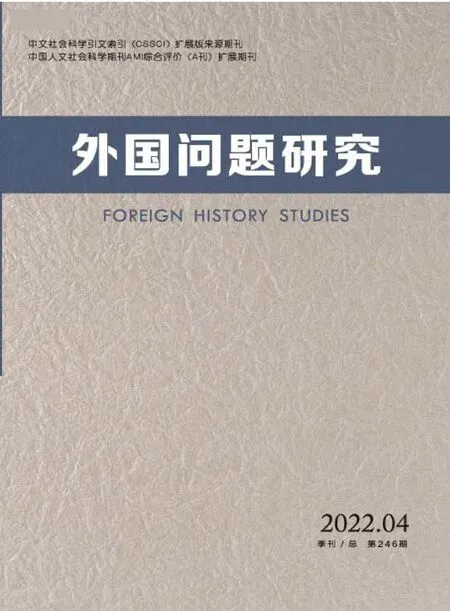古埃及早期王权发展与地方标志性建筑的关系
——以埃里芬梯尼城为例
赵 艺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长期以来,古埃及的王权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议题。英国埃及学家贝恩斯(Baines)认为古埃及人通过对相关符号的展示和语言的表达来灌输王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1)John Baines, “Kingship, Definition of Culture, and Legitimation,” in David B. O’Connor and David P. Silverman, ed.,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 Leiden: Brill, 1995, pp.3-48; John Baines, “Origins of Egyptian Kingship,” in David O’Connor, ed.,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 Leiden: Brill, 1995, pp.95-156.法兰克福(Frankfort)则通过分析与王权有关的宗教铭文以及法老的加冕仪式,认为神性是埃及王权的重要组成因素,进而强调国王的神性高于他的人性。(2)Henry Frankfort, Kingship and the Gods. A Stud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Religion A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 & Nature: An Oriental Institute Essa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雷德福(Redford)主张王权的概念由三个部分组成:国王是伊西斯神和奥西里斯神的儿子荷鲁斯神,国王是太阳神的儿子以及国王是一个英雄。(3)Donald Redford, “The Concept of Kingship During the Eighteenth Dynasty,” in David O’Connor, ed.,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 Leiden: Brill, 1995, pp.157-184.由此可见,对于王权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其表达方式,以及属性、构成等方面的讨论,并且所依据的资料也多为宗教性质的铭文以及壁画,反而较少关注王权意识形态的发展对建筑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远离统治中心的地方建筑发展的影响。作为古埃及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核心,王权意识形态扮演着为国王统治埃及各地提供合法性来源的重要角色。而它的出现和发展也必然会影响到地方建筑的兴建与消亡,对于埃里芬梯尼这类位于边界之处的城镇更是如此。因此,本文以埃里芬梯尼城为例,通过对当地标志性地理建筑的分析来探讨埃及早期王权的变化发展以及其对地方发展的影响。
一、王权统辖边界的确立及表现载体的变化
王权意识在埃里芬梯尼的发展主要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国王通过在埃里芬梯尼城建造要塞来确立王权统御的地理范围,也即王权的边界意识。在早期铭文中,埃里芬梯尼城大多作为南部的边界出现。如在第五王朝时期的铭文《大臣乌尼传》中,就曾提及埃及南部的范围是“从南到埃里芬梯尼,北至阿佛洛狄忒坡里斯(Aphroditopolis)”。(4)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p.140.铭文的主人乌尼作为埃及南部管理者所管辖的范围也同样是南到埃里芬梯尼,北至阿佛洛狄忒坡里斯。此外,埃里芬梯尼城作为埃及南部边界的定位还体现在对它的称呼上——“南部大门”。(5)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 p.167, note. d.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不少埃里芬梯尼城的贵族或者长官诸如扎乌(Zau)等,都被授予“南部大门的守卫者”这一头衔。(6)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1, p.171.一直到中王国时期,埃里芬梯尼城都一直作为埃及南部的边界出现这一时期的铭文中。
从地理上来看,埃里芬梯尼城位于上埃及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也是该区域最大的一个定居点。瀑布对于尼罗河航道的阻绝,使其成为一道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将埃及与努比亚地区分割开来。除了地理方面的因素外,埃里芬梯尼城之所以成为埃及南部的边界所在,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建造于第一王朝时期的泥砖要塞。(7)要塞坐落于岛上地势较高并且靠近最佳登陆口的地方,可以俯瞰通向第一瀑布通航通道,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从遗迹来看,要塞为51米×51米的方形布局,由东西两面约高3米的墙构成,要塞的西墙挡住了更古老的赛泰特神庙的入口。要塞拐角处有方形或半圆形的,由碎石填充的塔楼,塔楼顶部并无明显的建筑无痕迹,或许是直接与某个建筑物相连, 参见:Martin Ziermann, Elephantine XVI. Befestigungsanlagen Und Stadtentwicklung in Der Frühzeit Und Im Frühen Alten Reich, Mainz: Zabern von, 1993. pp.33-34.泥砖要塞的建造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第一阶段(国家建立初期)王权地域观念发展的初步体现,即对王权统治边界的强调。
从涅加达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开始,埃及与此时占据下努比亚的A群体文化(A-Group)就有着很频繁的物品贸易交换。(8)努比亚的A群体文化这个概念最早来自赖斯纳用字母顺序的方式来定义第一瀑布以南的非埃及文化,除了努比亚的A群体文化之外还有努比亚的B群体文化(B-Group),努比亚的C群体文化(C-Group)和努比亚的X群体文化(X-Group),上述几个群体文化分别与埃及的历史时期相对应,参见:G. A. Reisner,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Report for 1907—1908, Vol.I, Cairo: National Printing Department, 1910, pp.313-346; Maria C. Gatto, “The Nubian A-Group: A Reassessment,” Archeo-Nil, Vol.16 (December 2006), pp.61-76. 后来一些学者试图改变赖斯纳的命名方式,用“早期努比亚人”(Early Nubian)和“A层”(A-Horizon)来命名,但并未获得广泛采纳,参见:B.G. Trigger, History and Settlement in Lower Nubia, New Have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1965; William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pp.118-382.通过与埃及之间物质文化交往过程中,对埃及文化的吸收借鉴,A群体文化不断进步,尤其依靠其作为贸易中介的角色,逐渐垄断了埃及与南部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导致埃及想要获得努比亚南部地区甚至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物品都必须通过这一群体。但随着埃及国家的统一,国王权力的壮大,国王迫切需要为其权力的执行划定一个空间范围,以维护王权威严。但是占据下努比亚地区,甚至蔓延至上埃及的A群体文化,毫无疑问是早期王权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外部障碍。它对埃及与努比亚地区之间的物品流通的垄断,更是挑战了国王在获得和分配外国物品上的独断性。因此埃及必须对其南部的贸易关系进行根本性重组,首先就是用新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领土边界代替埃及以前的界限不明的民族边界,以便确立王权行使的范围。要塞的建立则正是这一需求的产物。
在要塞建造的过程中,对于之前已经建成的当地神祇赛泰特神庙,国王并没有因为它是地方崇拜中心而给予其应有的尊重,甚至因为建造要塞而侵占了原本属于神庙的地界。(9)W. Kaise and G. Dreyer, Stadt und Tempel von Elephantine, 15./16, Grabungsbericht, Mainz: von Zabern, 1988, p.156; Martin Ziermann, Elephantine XVI, Befestigungsanlagen Und Stadtentwicklung in Der Frühzeit Und Im Frühen Alten Reich, Mainz: Zabern von, 1993, p.30.从这一建造活动可以看出,要塞的建造并非由当地人组织的,具体建造过程的实施者也非当地居民,而是完全由埃及中央政府组织实施。显然,第一王朝的国王们在埃里芬梯尼城建造一座泥砖要塞的目的是以此为界,确立埃及疆域的范围。同时这座要塞也是埃及面向南部努比亚地区的一个贸易中心,从而为之后通过武力手段驱逐消灭A群体文化在下努比亚的统治,直接与南部地区进行贸易奠定基础。
在第二阶段,通过在埃里芬梯尼建造一座金字塔,进一步确立了王权对于此地的统治权。1908年,柏林博物馆组织的考古队在埃里芬梯尼西北部寻找更多的纸莎草纸时,意外发现一座由花岗岩建造的建筑,由于考古证据的缺失,最初这座建筑被认为是城墙的一部分。(10)W. Kaise et al., “Stadt Und Tempel Von Elephantine. Achter Grabungsbericht,”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Vol.36, 1980, pp.276-280.直到1978年德国考古学家君特·德雷尔(Günter Dreyer)对其进一步地挖掘才证实这座建筑是一座三层阶梯式金字塔。(11)金字塔位于岛屿西北部,侧边长约35腕尺(18.46米),现存高约5.1米,但原来的高度在20到24腕尺(10.46—12.55米)之间。为了应对不规则的地面,金字塔建在一个边长4腕尺(2.37米)的粗碎花岗岩块方形平台上,通过剥落其西侧岩石的突出部分平整地面。金字塔的朝向与岛屿的西岸平行,有一个核心结构,周围环绕着两层厚4腕尺的石头,使用本地粉红色花岗岩作为建筑材料。后来,高蒂尔为探索金字塔的内部结构,在其北面挖了一条直达中心的沟壕。参见:S.J. Seidlmayer, “Town and State in the Early Old Kingdom: A View From Elephantine,” Jeffrey Spencer, ed., Aspects of Early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pp.119-120.同时,人们还在金字塔北面的一个墓地中发现一个刻有铭文的长约1.46米的锥形花岗岩石块。最初,石块上的铭文被拉科(Lacau)解读为“国王胡尼的加冕城堡”,后来德雷尔根据其最末尾的宫殿限定符“aH”,认为应将其释读为“sSd njswt HwD”,即“国王胡尼的王冠”。(12)C. Seidlmayer, “Die staatliche Anlage der 3. Dyn. in der Nordweststadt von Elephantine.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Probleme,” in Manfred Bietak, ed., Haus und Palast im Alten gypten. Internationales Symposium 8-11. April 1992 in Kairo, Wien: Verlag der ÖAW, 1996, pp.119-120;S.J. Seidlmayer, “Town and State in the Early Old Kingdom: A View From Elephantine,” p.120.这一带有国王胡尼名字的岩块很可能是某一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而唯一符合标准的候选建筑物就是位于附近的金字塔。所以,很可能它曾经属于这座金字塔,是这座金字塔的标牌。(13)这种功用并不常见,但在托马斯(Tomos)采石场附近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例子。这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有HAm.t xwfw,是这一区域的名字;也可以参考尼乌塞尔的太阳神殿和萨胡拉(Sahure)葬祭庙的河谷神庙,同样有献祭石碑的铭文中提及建筑的名称,参见:Reginald Engelbach, “The Quarries of the Western Nubian Desert and the Ancient Road to Tushka: (Survey Expedition, February 1930,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r G. W. Murray, Director Topographical Survey),”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tés de I’Égypte, Vol.38, 1938, pp.369-390; Hermann Kees, “Die Grosse Festdarstellung,” in Friedrich Wilhelm von Bissing, ed., Das Re-Heiligtum des Königs Ne-Woser-Re III, Leipzig: 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8, p.47.从其所显示的国王的名字来看,金字塔的建造者应该是第三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胡尼。
从规模来看,埃里芬梯尼城中的这座金字塔,要远远小于同时期左赛尔王(Djoser)的阶梯金字塔。(14)第三王朝国王的左赛尔金字塔由6个马斯塔巴组成。最初高 62.5米,底部为 109米×121米。从其功能上来看,它也并非丧葬建筑,其内部缺少用于存放尸体的墓室,况且也很难想象胡尼的尸体会被埋葬在远离孟菲斯的地方。阿诺德(Arnod)认为这座建筑的名字为“国王胡尼的王冠”,这使得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节日——王冠日(festival of the diadem,埃及语为Hb-sSd)。(15)Dieter Arnold, Der Tempel Des Königs Mentuhotep Von Deir El-Bahari, Vol.I, Architektur Und Deutung,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 1974, p.76, note.309; Hans Goedicke, “The Pharaoh Ny-SwtH,” 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81, 1956, p.33.巴尔塔(Barta)认为王冠日的庆祝仪式是加冕仪式的其中一个环节,在这个仪式上国王被赠予带有羽毛的头带和其他礼节性的物品,参见:Wolfgang Helck, Lexikon der A-gyptologie, Band III, Horhekenu-Megeb,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0, pp.531-532; 王冠日和塞德节非常相似,二者都是关于国王加冕的节日:两者都在节日的庭院和宫殿中庆祝,而且在两个节日中国王都穿着塞德节的长袍,参见:Alexandre Moret, Du Caractère Religieux De La Royauté Pharaonique. Paris: Leroux, 1902, p.89.这个节日曾在帕勒莫石碑中的谢普塞斯卡弗(Shepseskaf)第一年的加冕仪式中被提及:“……月的第11天,双王出现,统一上下埃及,巡视城墙。王冠日,创造两个开路者(16)埃及语为wp-wAwt, 豺狼神,在正式场合站在国王前面,象征着在统治者之前“开路”。在这里这个词语的限定符号被写了两次,以此表达形象相同的两个神被创造出现。反映了贯穿王权意识形态始终的二元概念,如“双王出现”和“上下埃及的统一”。参见:Toby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0.的(形象);在统一两土地的众神之王之后……”(17)Toby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p.149.在戴尔·艾尔·巴哈瑞神庙(Deir el-Bahari)的有关哈特舍普苏特加冕仪式的描述中,也提及过这个节日,“第一季的第一天,新年,上下埃及之王的和平年的第一天,两女神所爱之人,游行北部城墙之人,王冠日……”(18)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p.99.虽然铭文有所缺损,但能清晰辨认出王冠日的字样。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头戴双王冠从“aH”宫殿(19)aH宫殿通常是wsxt建筑群的一部分,在仪式期间作为国王的休息或者更换衣物的场所,参见:Jr Ogden Goelet, Two Aspects of the Royal Palace in the Egyptian Old Kingdom, Columbi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2, p.530.进入卡纳克神庙,接受阿蒙神的加冕。(20)Giulia Pagliari,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Egyptian Royal Palaces from the Middle Kingdom to the Saite Period: A Lexicographical Study and Its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the Archeological Evidenc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h. D Dissertation, 2012, p.235.之后,又身着塞德节期间穿的衣服,前往“王冠日的大厅”(court of the festival of the diadem,埃及语为wsxt-Hb-sSd)。由此埃里芬梯尼城中的这座金字塔作为王冠日的宫殿,它的建造可能与国王有关的某种崇拜仪式有关。
相反,在涅加达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与当地居民关系最为密切的赛泰特神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成为国王宣扬王权的场所。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赛泰特神庙作为当地人举行宗教崇拜活动的中心,在埃及国家统一之前已经存在了。但是第一王朝时期埃及在此地修建要塞时,神庙非但没有被圈进城墙之内受到保护,反而因城墙的建造而被侵占了部分区域,神庙的入口也遭到了城墙的遮挡。除此之外,赛泰特神庙的外观并未发生什么变化,规模也很小,神殿里只有一个由3个巨大花岗岩组成的天然神龛。从神庙内所发现的祭品来看,埃里芬梯尼城中的赛泰特神庙一共出土了约497件来自早王朝和古王国时期的捐赠器物。这些器物中90%为陶制器物,石制器物则非常稀少。(21)Richard Bussmann, “The Social Setting of the Temple of Satet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in Dietrich Raue et al. ed., The First Cataract of the Nile. One Region-Diverse Perspectiv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3, p.23, fig. 5.相较之下,位于希拉康坡里斯(Hierakonpolis)的地方神庙(荷鲁斯神庙)中所发现的器物则高达810件,石制器物的比例也远高于赛泰特神庙。(22)Richard Bussmann, “The Social Setting of the Temple of Satet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p.27, fig. 9.除数量上的差距之外,这些物品表面的装饰等也不尽相同。赛泰特神庙出土的捐献物大多不符合早王朝以及古王国时期的王权形象的外在表现特征,与王权并无联系,其制作非常粗糙,由普通百姓所捐赠。而在希拉康坡里斯早在零王朝时期便已有器物刻有国王名字,并且其早期神庙的布局和早期王室葬祭庙也十分相似。(23)Barbara Adams, Ancient Nekhen: Garstang in the City of Hierakonpolis, New Malden: SIA Publishing, 1995, pp.19-80.
事实上,早王朝和古王国前期,国王不把地方神庙作为宣扬王权意识形态的场所,完全忽视地方神的现象在埃及十分普遍。相较于越来越复杂、宏大的王室丧葬建筑,献给地方神的神庙或神殿建筑以及捐献物都显得十分寒酸。除了王室陵墓之外,也很少能发现其他与王权有关的宗教建筑,即便是在希拉康坡里斯和赫里奥坡里斯(Heliopolis)等地方,现存的浮雕装饰也着重强调国王作为神庙建造者和众神追随者的角色。国王所追求的并不是承认这些神庙在意识形态上所扮演的角色,而是侧重于强调王权自身的神圣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神如荷鲁斯神和拉神的重要性。地方神庙并不是国王用来彰显其王权意识形态的地方,也没有必要使用一种可见的、持久的形式如雕刻、建筑元素等表现二者之间的关联,因此地方神如埃里芬梯尼城的赛泰特神等被忽视也在所难免。
如上所述,位于埃里芬梯尼城的金字塔而非赛泰特神庙才是彰显王权的核心场所。除了埃里芬梯尼城外,埃德福、希拉康坡里斯、阿拜多斯、扎杰特-艾尔麦提(Zawjet el-Meitin)和塞拉(Seila)等地也有与埃里芬梯尼城的金字塔类似的建筑。(24)G. Dreyer and W. Kaiser, “Zu den kleinen Stufenpyramiden Ober-und Mittelagyptens,”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Vol.36, 1980, pp.53-55.基于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散布在埃及各地的金字塔可能都是在同一时期被计划建造的,由第三王朝国王胡尼建造,而埃里芬梯尼城的金字塔则是这一系列金字塔的最南端的一座。胡尼在上埃及共建造了7座小金字塔,借此表达这地区在王权辐射之下。
第三阶段则与第二阶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阶段国王开始更多地关注地方神祇,试图将自己与地方神祇联系在一起。相较于在早王朝以及古王国早期赛泰特神庙几乎没有来自王室供奉物品,(25)根据赛德梅尔的结构性历史模型,早王朝时期,也就是王权观念确立的初期,国王只对那些与王权有关的神庙感兴趣。从古王国早期到古王国的巅峰期,国王们忽视当地的神庙,而只专注于自己的丧葬崇拜。第五王朝后期,国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神庙,并对当地的宗教信仰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参见:S. J. Seidlmayer, “Town and State in the Early Old Kingdom: A View From Elephantine,” p.118-119; Richard Bussmann, Die Provinztempel gyptens Von Der 0. Bis Zur 11. Dynastie: Archäologie Und Geschichte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Institution Zwischen Residenz Und Provinz, Leiden/Boston: Brill, 2010, p.lxxxvi.在古王国末期,埃里芬梯尼城中王室活动的痕迹明显增多。从赛泰特神庙来看,国王的活动痕迹最早可追溯至第五王朝时期,且大多集中在佩皮一世(Pepi I)到佩皮二世(Pepi II)统治时期。
在国王对赛泰特神庙献祭的物品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由佩皮一世供奉给赛泰特神的花岗岩神龛。神龛两侧的铭文中出现了佩皮一世的名字,以及“赛泰特所爱之人”的字样。(26)Christiane Ziegler, Catalogue Des Stèles, Peintures Et Reliefs égyptiens De L’Ancien Empire Et De La Première Période Intermédiaire Vers 2686-2040 Avant J.-C: Musée Du Louvre, 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0, p.50.佩皮一世的名字以及“赛泰特所爱之人”的表述毫无疑问证明了王权对于赛泰特神的关注。佩皮一世的继任者麦然拉同样将自己的名字刻写在了神殿两侧。德国学者理查德·布斯曼(Richard Bußmann)推测神龛位于神庙前院的泥砖台子上,佩皮一世的雕像则矗立在这个神龛之中。(27)Richard Bußmann, “Der Kult im frühen Satet Tempel von Elephantin,” in H. Roeder and J. Mylonopoulos, ed., Archäologie und Ritual, Auf der Suche nach der rituellen Handlung in den antiken Kulturen gyptens und Griechenlands, Wien: Phoibos, 2006, pp.29-32. 巴斯曼认为泥砖台的泥砖并不是以顺砖砌合的方式黏接在一起,而是放置在边缘从而形成辊砖(roll brick)。辊砖是典型的地基建造样式,很明显这里需要有一个比较重的物品置于台子的上方。泥砖台大小为1.60米×1米,而神龛的大小刚好非常适合置于台子之上,台子地基的底部分别比神龛的四边宽出20或者40厘米。通常而言,作为卡之屋的神龛是国王在地方神的崇拜场所安置自己雕像的地方,象征着王权的永恒,人们在这里定期举行对已故国王卡雕像的祭祀活动。
除了对当地神庙进行祭品捐赠外,这一时期的国王在埃里芬梯尼城留下的铭文数量也有所增加,且这些铭文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地方神出现在铭文中。并且这些地方神出现的语境也大多相似,都是采用了“mry+GN”格式,(28)GN是英语“god name”的缩写,mry为埃及语,意为“爱”。即被某神所爱之人,借以宣告国王是地方神所爱之人,进而建立起与当地神之间的关系。根据在第五王朝国王尼塞拉(Nyuserra)捐献的彩陶板上残存的埃及语mry,以及彩陶板出土的位置,我们推断这句埃及语也属于上述格式用语,mry+GN。虽然彩陶板上的铭文未保留下具体神的名字,但应该是指赛泰特神。此外,第五王朝国王乌纳斯在这一区域的岩石铭文中也提到乌纳斯是“外国土地之主……,克奴姆所爱之人”。(29)Nigel C. Strudwick, Texts from the Pyramid Age, p.133.
古王国末期,随着埃及王权的逐渐衰落乃至崩溃,以及地方贵族势力的崛起,位于孟菲斯的中央政府逐渐丧失对地方的控制,为此,国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自己的权威。因此,王权不再像以前一样着重刻画对国王本身的崇拜,而忽视其与地方神祇之间的联动。此时的王权将重点放在地方神庙——这些原先与王权并无交集的地方宗教中心。首先,国王开始用门楣、柱子、石碑、浮雕等来装饰地方神庙,并用大量的捐献物来供养神庙,使之与地方贵族形成统一信仰。阿拜多斯的神庙里有许多属于第五和第六王朝王室的门楣,这座神庙甚至成为上埃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且,国王供奉的地方神也越来越多。此外,国王还自称是地方神所爱之人,使之成为自己的守护神,从而使王权与地方神产生联系。通过这些地方神祇,王权更加地深入到其治下的各个地方,并且无形之中增强地方官员对王权的忠诚度。其次,从第五王朝后半期开始,大量的王室雕像进入地方神庙,并在此树立王之屋,从而将纪念性艺术形式转移到地方神庙,以此唤起地方贵族对于王权的敬畏,从而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王权经济属性对标志性建筑物的影响
除了上述三座建筑外,埃里芬梯尼的早期地方建筑,还实现了对当地资源的掌控。首先,设立如王之屋这样的行政管理机构来管理国王在当地的地产。在金字塔的以北40米的一座建筑废墟中的纸莎草卷里,附有一枚印章图案,其上写着“下埃及的王之屋(30)在王室和私人铭文中,王之屋经常作为向私人或其他机构提供捐献物的来源地,但所涉及的捐赠往往是以国王的名义,按照国王的要求来进行的。王之屋中的王并不单指某个特定的国王,也不局限于某个区域。相反,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术语,指的是在统治者控制下的一种财产,并在其统治期间始终存在。这些特点是王之屋被认为是为丧葬财产提供捐献物的理想机构的原因。王之屋的财产种类同样多种多样,包括工场、牛群和土地。的持印者”(xtmw-mHw wDa-mdw pr-njswt)和国王sA nxt(31)sA nxt,第三王朝时期某一国王荷鲁斯名,但其身份还未被明确勘定,可能是奈布卡(Nb-ka)、奈弗尔卡拉(Nfr-ka-Re)或奈布卡拉(Nb-ka-Re)中的某一位,但肯定的是胡尼的某一位前任,参见:Ludwig Borchardt, Das Grabdenkmal des Königs Ne-user-re, Leipzig: Hinrichs, 1907, p.79; S. J. Seidlmayer and Werner Kaiser, “Stadt und Tempel von Elephantine, Neunter/Zehnter Grabungsbericht,”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Vol.38, 1982, p.304.的荷鲁斯名字。此外,这里还发现了其他24枚印章。这些印章上都刻有人名,这些人持有的头衔都是诸如书吏(sS)、工人(mjtr)和管理人(iri xt)之类的,(32)S. J. Seidlmayer, “Die staatliche Anlage der 3. Dyn. in der Nordweststadt von Elephantine,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Probleme,”pp.200-201.由此可知,发现的这座建筑为岛上的一个行政中心,即王之屋。
此外,在这个建筑附近还发现2个带有铭文的啤酒罐。铭文用黑色墨水写在罐子上,虽然破损严重,但仍能分辨出是在逐年记载物品的交易。(33)Nigel C. Strudwick, Texts from the Pyramid Age, p.74.铭文都是先写了人的名字以及头衔,然后列出了货物的数量。货物以谷物为主,其数量也与个人的生产或消费有关。事实上它们更类似于简短的摘录,为之后绘制更大的食物分配表做准备。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尤以储物罐的数量为最多。面包模具和啤酒罐的数量也不少,仅在一个废墟中,每一种就发现有10 000件以上。很显然,这是一个准备和分发口粮的地方。(34)S.J. Seidlmayer, “Die staatliche Anlage der 3. Dyn. in der Nordweststadt von Elephantine,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Probleme,” pp.202-203.
以上物品都与经济活动有关,从而揭示出这个行政中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它是一个地域的行政管理中心,即王室地产的管理部门,在当地收集、核算以及储存谷物等物品。部分作为薪酬重新发放,部分则上交给国王,用来为金字塔、神庙以及国王所组织的各项远征活动提供物质支持。并且,这种物品的流通似乎是单向的,并不存在接受来自王室馈赠的迹象,换句话说,埃里芬梯尼城这个行政中心,从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供给王室而设立的。
除埃里芬梯尼城的这个王之屋外,古王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王之屋和类似的机构,如大胡特(xwt-aAt)、胡特(xwt)等。“大胡特”一般设在土地数量庞大的地区,由王室直接控制,(35)J.C.Moreno García, “Administraion territoriale et organisation de l’espace en Egypte au troisième millénaire avant J.-C. (III-IV): nwt mAwt et Hwt-aAt,” 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125, 1998, pp.38-55; Moreno Garcá, “Hwt et le milieu rural égyptien du IIIe millénair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Égyptologie, Vol.337, 1999, pp.233-238.而“胡特”主要建在上埃及地区,由地方贵族定期审查,并且可以用于私人活动。它们之间并非独自存在的,而是作为各地的王室地产管理部门被整合到一张网络之中,从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以王室为核心的经济运转体系。这种模式最早见于弯曲金字塔葬祭庙壁画上所描绘的丧葬队伍中。丧葬队伍中有男有女,并且每个人的头上方都有一个埃及地名。(36)K. Sethe, Urkunden des Alten Reiches, Leipzig: Hinrichs, 1933, p.236.他们作为埃及各代表,为国王带来各地的物产,用以维持金字塔的日常运转。
从第一王朝末期开始,埃及就已经设有供应王室丧葬物品的工坊及相关下属部门和机构,但每个机构负责的地区有限,这是这一时期经济体系的特点,直到第三王朝时期才发生了变化。(37)S.J. Seidlmayer, “Die staatliche Anlage der 3. Dyn. in der Nordweststadt von Elephantine, Archä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Probleme,” pp.212-213.就中央政府而言,古王国早期非王室的国家官员比重有所增加,虽然权力最大的行政职务还是由王子们担任,但王子们不再是国王唯一的代表,非王室成员也能够拥有以前只属于王子们的头衔。国王也逐渐从小型统治集团中的绝对君主逐渐变为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的首脑,这也是国王第一次将权力下放给官员。就地方而言,左赛尔时期,阶梯金字塔的建立不仅需要调动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处理国王的丧葬建筑等事宜,还需要为更多的人提供食物,这也使王室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财富。斯奈夫鲁统治时期,大型金字塔的建造,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这一时期国王希望建立更多的地方机构,同时合并和整合现有机构,以使越来越多的地区参与为中央政府提供供给。根据王室年鉴的记录,仅在统治的一年中,斯诺夫鲁就建立了35个胡特或者大胡特以及一些养牛中心。(38)Toby Wilkinson, R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 p.143.这些新机构的建立,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机构加入国家行政中来,听从中央的统一支配。通过在各地设立的胡特、王之屋等王室地产,王权掌握的经济资源也大大增加,因此才能够支持金字塔等大规模建筑项目的进行。而到第四王朝末期,岛上的王之屋逐渐被废弃,国家经济体系再次发生改变,之前不受国家重视的地方神庙逐渐参与王室地产机构的管理,并且成为经济管理网络体系中的主要构成。(39)Helen Jacquet Gordon, Les noms des domaines funéraires sous,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62, p.81.
三、王权的衰落与地方精英墓葬的出现
作为埃及与南部努比亚地区之间的边界,埃里芬梯尼一直都是埃及与南方进行贸易的重要中心,甚至其地方长官在一定程度上管理着埃及与南部之间的贸易活动。在王权强盛时期,这种利润丰厚的贸易活动自然轮不到地方贵族阶层的参与,而是掌握在王室手中。(40)Bettina Schmitz, Untersuchungenzum Titels sA-njswt “Königssohn,” Bonn: Habelt, 1976, pp.159-170.所以虽然地处埃及与努比亚贸易的中心,但埃里芬梯尼的地方官员并不能从与努比亚地区的贸易中获得更多的财富以及更高的地位。因此第五王朝以前,在埃里芬梯尼并没有发现地方精英阶层存在的痕迹。
第五王朝时期,随着国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神庙,各地方精英也从王室给予地方神庙的捐献物和土地中获得巨大的利益。(41)参见:W. Helck,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n gypten im 3. Und 2. Jahrtausend von Chr, Leiden/Köln: Brill, 1975, pp.52-55; Peter Der Manuelian, “An Essay in Document Transmission: Nj-kA-anx and the Earlies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45. 1986, p.2; Helen Jacquet Gordon, Les noms des domaines funéraires sous, pp.80-163; Hans Goedicke, “Cult-Temple and ‘State’ During the Old Kingdom in Egypt,” Edward Lipinski, ed., State and Temple Econom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from the 10th to the 14th of April 1978, Leuven: Department Ori⊇ntalistiek, 1979, pp.118-120.但遗憾的是,埃里芬梯尼城的地方精英似乎并没有从中获利。首先,埃里芬梯尼城的地方长官没有祭司长的头衔,也就是说,地方长官并不能以祭司的身份从神庙捐赠中获利。(42)Naguib Kanawati and Ann McFarlane, Akhmim in the Old Kingdom, Part I: Chronology and Administration, Sydney: Australian Centre for Egyptology, 1992, pp.253-254; Elmar Edel. Die Felsengräber Der Qubbet El Hawa Bei Assuan,Vol.II: Abteilung. Die Althieratischen Topfaufschriften Band 1: Die Topfaufschriften Aus Den Grabungsjahren 1960, 1961, 1962, 1963 Und 1965,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0, pp.88-89.其次,即便埃里芬梯尼城的地方长官拥有祭司身份,其获得的利益也远远小于其他地方的精英。岛上的赛泰特神庙虽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王的关注,但国王的捐献物数量非常少,质量也很差。在这些捐赠物中,并没有发现半宝石制作的雕像等贵重物品,只有少数红玉髓制作的珠子。佩皮一世捐献给赛泰特神的石制狒狒器皿也只是一件粗糙的仿制品。捐赠物中的象牙制品和权标头都非常小,且权标头为木质,显然是早先献祭物品的仿制品或复制品。(43)Richard Bußmann, Die Provinztempel gyptens von der 0. biszur 11. Dynastie, pp.494-497.相反,第五王朝时期的行政体系改革使国家的重要官职不再只局限于王室成员,国王开始委派更多的官员前往努比亚进行贸易。而埃里芬梯尼的官员显然拥有更多的优势来承担此项任务。他们作为远征军的首领,带领商队前往努比亚并在远征贸易中获得巨大的财富。而且随着王权的衰落,他们也拥有了更大的独立性。
因此,在更大的权力以及财富的支持下,这一时期的埃里芬梯尼岛上突然出现了以马斯塔巴建筑为主的地方精英群体的墓地。从此地发现的一个装饰物上的铭文可以看出,这个装饰物属于第五王朝远征商队首领尼安胡敏(Niankhmin)。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第五王朝时期的一块石灰岩制小雕像碎片和一个石灰岩制的三角锥。这些文物都证明这一时期埃里芬梯尼存在一个装饰较为简单的精英墓地。(44)Dietrich Raue, “Éléphantine: Cinq Campagnes De Fouilles Dans La Ville Du IIIe Millénaire Avant J.-C,”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Égyptologie, Vol.163, 2005, pp.8-26: S. J. Seidlmayer and Martin Ziermann, “Eine Friesinschrift Von Einem Mastaba-Grab Des Alten Reiches Aus Elephantine,”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 Vol.48, 1993, pp.161-175.但这些官员在埋葬后不久,墓地便遭到破坏,仅一两代人之后,属于他们的丧葬纪念碑就被清理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第五王朝时期,埃利芬梯尼城已经出现社会分化,地方精英阶层形成,但他们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记忆,更没有引起国王更多的注意。
随着第六王朝王权的崩溃,居于孟菲斯的王室很难再有多余的精力控制与上努比亚地区的贸易,以及对下努比亚各种金属矿产资源的探寻。于是,身处埃里芬梯尼城的地方精英则全权承担起了与努比亚地区之间贸易远征的角色,如赛布尼(Sabni)、梅胡(Mehu)和哈胡夫(Harkhuf)等。根据铭文记载,哈胡夫曾4次带领远征军南下,前往努比亚进行贸易,进而开辟出一条新的贸易之路”。(45)Hans Goedicke, “Harkhuf’s Travel,”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40, No. 1 (Jan. 1981), p.19.远征军领导人完全控制着埃及与努比亚之间贸易活动,而王室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之前高级官员以埋葬在金字塔周边为荣的丧葬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家乡建造陵墓。为此埃里芬梯尼城的远征商队首领也选择在尼罗河西岸的崖壁上开凿自己的陵墓即现今埃里芬梯尼岛对面的墓地——库伯特·艾尔哈瓦(Qubbet el-Hawa)。与服务于国王的官员选择埋葬在金字塔旁一样,之前服务地方州长的官员则选择埋葬在其曾经服务过的地方州长墓葬附近。由此可以看出,地方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之前国王的角色,成为当地社会关系的核心。(46)在1996—1998年考古季中,发现的一组神龛是献给赛布尼和梅胡等人。在H2区域的圣殿也发现了很多神龛和一个木质的小雕像,进而证实了赛布尼、梅胡、索贝霍特普(Sobekhotep)和海卡布(Heqaib)等个人崇拜的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第六王朝末期远征军领导人海卡布。他死后被神化,成为赛泰特神之外的另一个地方神,他与中王国时期地方统治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保护神。
库伯特·艾尔-哈瓦精英墓地的建立,标志着埃里芬梯尼城社会分化的加剧,城中精英文化群体的墓地也与埃里芬梯尼城的居住区正式分离。第六王朝末期,游离于王权之外的埃里芬梯尼地方贵族甚至修建了之前金字塔陵墓才拥有的连接尼罗河与墓地的堤道,从而进一步将地方精英与城镇居民区分开。这表明是地方统治者试图死后依旧与城镇保持密切关系。
结 论
通过对不同阶段埃里芬梯尼岛上建筑物发展和演变的分析可以发现,王权的发展与演变对于地方建筑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古埃及国家刚刚统一之时,国王就迅速地在埃里芬梯尼岛上修建了一座带有城墙的要塞,目的在于确立王权统治地域的边界,并取代之前与A群体文化之间较为模糊的边界。同时也以此作为基地,直接控制与努比亚之间的贸易。此外,由于早期王权更侧重于对本身或与之联系密切的神祇如荷鲁斯、拉等神明的崇拜,并不注重将王权的神圣性与各地地方神相联系,因此在埃里芬梯尼,我们并没有看到古王国早期来自王室对于地方神赛泰特的关注。相反,第三王朝国王胡尼修建的金字塔成了宣扬国王崇拜的中心场所。到第五和第六王朝时期,国王开始更多地借助其与地方神祇之间的关系来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以此得到埃及各地民众拥护。于是,赛泰特神庙这座之前一直被国王忽视的地方神庙也自然引起了国王的关注。除了捐赠祭祀器物外,国王还在神庙内部修建用于供奉国王卡的神龛,宣称自己是“赛泰特所爱之人”。
除了王权的边界意识以及表现载体的变化对于建筑发展的影响外,作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方面,经济上的考量同样也影响埃里芬梯尼的建筑发展。于是在埃里芬梯尼,我们看到王之屋这种典型的王室地产管理机构成为王室在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心。与其他王室设立在埃及各地的地产管理机构一样,王之屋为国王进行各项建筑活动、神庙的祭祀以及远征等活动提供经济支持。但是随着古王国末期王权的衰落,地方贵族势力崛起,与王室或国王有关的建筑开始逐步退出当地,或者由地方官员所掌握。从埃里芬梯尼的具体情况来看,此地地方贵族的崛起更多地依靠控制与努比亚地区的贸易。通过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财富以及利用第一中间期王权衰落之后遗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埃里芬梯尼的贵族开始在当地修建豪华陵墓,其规模甚至要超出同时期的国王陵寝。而这些陵墓的建造,也就成为王权式微的最佳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