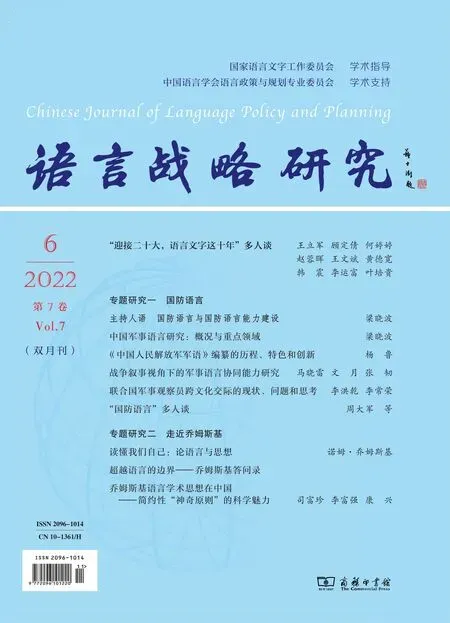战争叙事视角下的军事语言协同能力研究
马晓雷,文 月,张 韧
(1.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2;2.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提 要 语言的交锋是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与非语言手段的协同运用能够有效发挥管控危机、遏制对手、塑造态势、赢得优势的作用。以往研究大都聚焦军事语言能力本身,较少关注语言与其他战争手段的协同关系。看待军事语言协同能力不能采用孤立的视角,而应结合战争叙事的总体框架,考虑语言运用在实施战争行为、描述战争进程、组织战争行为和影响受众认知中的作用。理想的军事语言协同策略应以知识共享为基础,充分了解战争参与各方的行为意图,力争实现己方力量优劣互补的总体效应。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可以看出语言运用在标定关键节点、框定发展脉络、策应军事行动、营造感染效果等方面对战争叙事推进的协同效应。建议未来应加强军事语言协同机制、军事语言能力生成和军事语言能力建设方案研究。
近年来,语言对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抵御外来威胁的过程中,除了硬实力的对抗,以语言为代表的软实力间的交锋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宣示主权、阐释立场、驳斥对手、争取支持等诸多环节,都离不开语言的参与。有些情况下,语言博弈甚至可以取代硬实力对抗,在赢取战争优势中发挥更加关键的重要作用。然而,战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任何手段的运用都不是孤立的。以往研究大都是从被动防御和语言本体的视角关注语言能力问题,注重话语权的建立、国家形象的建构、官兵语言能力的提升等,却较少从管控危机、遏制对手、塑造态势、赢得优势的角度探讨语言能力运用与其他战争手段间的协同关系。本文旨在梳理现有军事语言能力研究的现状与不足,从战争叙事的视角探讨军事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协同机理,并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说明语言协同能力运用在战争博弈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军事语言能力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以往研究在探讨军事领域的语言能力建设与运用问题时,主要使用军队语言能力、国防语言能力、军事语言能力等概念。我们认为,军队语言能力更侧重于强调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组织所应拥有和发展的语言能力,国防语言能力更侧重从综合调用国防体系各方力量的角度探讨语言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军事语言能力的重点则在于如何运用语言能力实现军事斗争的目的。三者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我们倾向于使用军事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大致来看,该领域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看待军事语言能力问题。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马晓雷,庞超伟2019)。美国政府反思“9·11”事件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语言情报人才缺失是威胁国家安全和影响反恐战争进程的重要原因(GAO 2002;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2004;戴曼纯2012;张天伟2016)。美国国防部出台的《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等都以“9·11”事件作为重要理据(文秋芳,苏静2011;文秋芳2011)。当语言问题同国家安全紧密关联,加强语言能力建设也就有了强有力的理据(李宇明2010;文秋芳2011;王建勤2011;赵世举2015;张天伟2013;梁晓波2018;陆丹云2019;梁晓波202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建议包括制定国防语言政策、建立语言人才数据库、加强外语人才培养等。
(2)从履行使命任务的角度看待军事语言能力问题。在各项涉外任务中,语言能力的高低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任务实施的过程与结果(Brecht & Walton 1993)。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中国逐渐从“本土型”发展成为“国际型”国家(李宇明2018)。中国军队参与反恐、维稳、护航、撤侨、联合军演、对外援助等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频次日益增多。然而,目前我军官兵的外语能力还存在不足(傅岩松,彭天洋2014;李洪乾,梁晓波2018),突出表现在无法独立使用外语完成工作任务、无法有效通过外语开展合作交流等。美军也面临类似问题,对当地语言、文化和区域知识缺乏了解是影响美军作战能力的重要方面(文秋芳2011)。从这一角度研究军事语言能力,更侧重关注提高军队人员的外语能力水平、加强军事外语教育、建设军事语言资源、强化语言服务保障等方面。
(3)从国际话语权争夺的角度看待军事语言能力问题。所谓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军队在国际上“说话”的权利以及“说话”的有效性和威力(Foucault 1969;岳汉景2017)。在国际舞台上,话语的运用反映并建构权力关系,是意识形态、政治格局、利益诉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甄妮2015;李战子2017;施旭,李婧2021)。话语不仅是安全问题的呈现形式,也可以建构安全感知,甚至导致安全危机(孙吉胜2019)。以往国内有关军事话语权的研究,大都是从军事外宣和军事外交的角度,探讨如何扭转“中国威胁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效力,让中国军队得到更大范围的接受和理解,建构起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4)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西方军事语言霸权问题。该领域的研究同话语权研究紧密相关,但关注焦点不是话语权的建构,而是揭露西方军事霸权话语的本质。美国尤其擅长利用话语建构发动战争的合法化理据。Asad(2007)指出,美国有关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话语体系中充满了虚伪。美国政府通过丑化对手、美化己方、建构恐惧未来等方式,影响了民众对于发动反恐战争的看法(Chang & Mehan 2008;Hodges 2011;Flint & Falah 2004;Jackson 2005;Silberstein 2002;庞超伟2013)。这一领域的研究尤其关注战争话语的合法化问题,以及隐喻、框架、及物性、语篇世界、隐含意义等语言手段的运用策略。
此外,军事语言能力研究还包括战争创伤中的语言障碍问题(Bulmer & Jackson 2016)、军事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Baker 2010)、军事语言能力的指标体系建设问题(肖蓉,梁晓波2021)等。应当说,以往围绕军事领域的语言研究范围广阔、选题丰富(梁晓波,等2016),为更好地理解军事语言的特点规律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也存在以下需要改进的方面。
(1)偏重以被动防御的思维看待军事语言能力的运用问题。以往研究大都是从传播、宣传、外交的视角探讨提升话语权、建构军队形象、破解霸权话语等问题。随着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军队要维护自身利益和世界和平,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要从让别人“愿意听、听明白、相信了”,逐步发展到“帮腔呼应、设置话题”(李宇明2018)。从军事博弈的角度来看,要充分关注军事语言冲突性和对抗性的一面(李苏鸣2020)。尤其应关注语言能力与其他软硬手段的协同,厘清其对于战斗力体系的贡献价值。
(2)偏重从语言本体的角度看待军事语言能力问题。目前,国内军事语言研究主要在语言学界展开,在国家安全、军事战争等研究领域内仍处于边缘地位(施旭,冷唐蒀2020)。研究者的目的大都是揭示军事语言本身的特点与规律,或提出针对语言能力本身的建设性意见。然而,军队作为一个特殊体系有其自身的组织运行特点,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对抗样式也有其自身的发展演进规律。如果仅是孤立地看待语言能力问题,就很容易导致研究结果“自说自话”,难以真正融入战斗力建设的各项环节中。近些年虽然军事语言研究成果丰硕,但相关提议仍未能有效落实为具体的建设举措(马晓雷,等2018),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从军队战斗力生成的视角来看待语言能力建设问题(陆丹云2019)。
二、战争叙事视角下的军事语言协同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综合力量的比拼,语言手段只有在与其他战争手段的协同中才能发挥应有价值。看待军事语言协同能力,不能采用孤立的视角,而应将其放置在战斗力生成的框架中,用体系思维的视角剖析其作用机理。
(一)战争叙事中的语言运用
所谓战争叙事,是指通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展现战争事件的背景、起因、进程、走向、冲突、高潮、结局等,核心目的是影响目标受众对战争的认知并使其接受叙事方的立场与行动。
作为战争手段之一,语言具有使用面广、方式灵活、效果可控、成本较低等特点,毕竟军事、经济等手段牵扯的资源投入和风险代价都相对更高。如果能够只通过语言就实现预期目标,显然比武力征服更加经济。从效果上看,语言能力运用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肉体上的摧毁,而是精神上的征服。借用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界定,就是“要让对手按自己的方式思维”(Nye 2004)。以上特点使得语言天然具备与其他战争手段协同发生效应的基础。当然,对目标受众进行认知塑造必定是一个需要精心设计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人的立场、喜好、思维习惯都是在特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中逐渐形成的。即使武力上彻底征服,也并不意味着思想上可以完全改变。这就意味着,战争手段的综合运用应能建构起一套有利于影响目标受众认知的逻辑、框架和体系。换句话说,就是要用有力的战争叙事促成认知塑造,而语言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之所以强调叙事的重要性,是因为人们生活在故事中,用故事的形式储存记忆,也用故事作为框架理解现实(Marcellino et al.2022)。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叙事的手段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应涵盖几乎所有可供使用的战争手段。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战争行为都可以传递特定的信息和意图,都在参与整体战争叙事。如果仅靠语言而脱离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的运用,那么战争就是在打嘴仗,而口头上的攻击是永远无法真正赢得战争的。实际上,人类社会对语言的运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包含丰富的语境和语用信息。例如,在表达认可的同时可能会点头,在表达愤怒时可能会挥舞拳头。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把实施制裁看作挥舞的拳头,那么警告和恐吓就是协同的语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战争的叙事进程。因此,从战争叙事的视角来看,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手段都是叙事的工具,共同服务和服从于影响目标受众认知的总体目标(Marcellino et al.2022)。
在战争叙事的总体框架下,语言主要发挥着以下功能。
1.实施战争行为。语言本身就具备行事的功能。战争中的很多环节都是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如警告、通牒、宣战、求和、谈判等。这些语言行为往往是战争叙事中的关键节点,甚至在部分时段可能成为博弈的主战场。
2.描述战争进程。现代战争不仅要打,而且要面向全世界直播。参战各方都会有选择地将有利于本方的战场态势、进展和损失等信息传递出去。有些媒体尤其擅长对战争进行报道,或遮掩或强化战争残忍的一面,以达到将其战争意志合法化的目的。
3.组织战争行为。虽然非语言的战争行为可以传递特定信息,但毕竟是间接的,且存在被赋予不同解读的可能。仅靠非语言的战争行为本身很难形成具有内在逻辑且对观众友好的叙事。这就需要利用语言将各战争行为的理据用意说清楚,将战争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发展脉络讲明白。有了语言的组织,各种战争行为才更容易被组合在一起,形成协同的合力。
4.影响受众认知。语言的另一大功能是建构人际意义。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即使是连贯完整的,也很难打动观众。语言的运用可以对战争动机、人物形象、战争场面等进行策略性包装,从而激发受众情感、引发受众关注、促成受众认同。
总之,正是有了语言手段的协同,战争的叙事才完整,各战争行为的用意、理据、进展才得以强化。此外,战争叙事一经形成,也主要是以语言的形式进行传播。
(二)军事语言的协同策略
所谓语言协同,是指语言能力运用需要与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手段相互配合,通过“言行一致”的叙事实现塑造认知的整体效果。然而,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要确保复杂战争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实现有效协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从3个方面来探讨如何形成理想的军事语言协同策略。
1.建构共享知识。有效协同的前提,是各种手段应当在同一个框架体系内运行。正如任何一种语言行为都离不开语境,对各战争行为的解读与预测也必须结合特定的情境和背景知识。脱离了彼此认知的共同基础,就很容易出现误判甚至误解。因此,建构有利于促进协同的知识基础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应包括3个方面:(1)关于自我的知识。主要包括己方的战略目标、战术安排、优势劣势、过往经历、规则制度等。(2)关于对手的知识。主要包括对手的战略意图、战术动向、优点缺点、交锋记录及其行为特点等。(3)关于总体态势的知识。主要包括战争的起因、发展阶段、走向和格局等。在共享知识基础上,要形成己方战争叙事的总体目标、框架和策略,从而为后续促成语言与其他手段间的协同奠定基础。
2.感知行为用意。在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参与战争的各个部门都在飞速运转,面临的情况、处理的难题可能各不相同。要确保协同,就要对彼此行为的动机和目标有准确的预测。一方面应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行为的原因、动机和目标。如前文所述,任何一个战争行为都是目标、意志的体现。这就需要打破语言和非语言的界限,在同一个框架内思考“言外之意”的问题。例如,一次火力打击传递的信号是什么,可以实现的效果是什么。另一方面应坚持结果导向,反推和预测各行为在实现最终目标过程中的作用与功能。只有对各战争行为的用意有充分的理解,才能确保语言和其他手段之间产生类似共振的协同效应。
3.规划互补策略。在感知基础上,要设计形成语言能力运用的方案。方案规划应按照“实现目标需要做什么”的思路,并充分考虑合作对象的行为意图。谁来说、何时说、说什么、怎么说、在哪说、对谁说等策略选择,都需要与其他手段互补,力争实现延展己方优势、削弱对手优势,弥补己方劣势、放大对手劣势的总体效应。同时,应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让语言能力运用的用意被合作对象所接受、理解和支持。总之,语言能力运用必须建立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要充分了解合作对象的行为意图,进而形成诸多手段优劣势互补的局面。
三、军事语言协同的案例分析
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通过战争叙事实现预定目标的典型案例。回顾这场战争,美国通过语言手段与军事手段的相互协同,建构了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伊拉克战争叙事模式。本研究系统收集了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和国外主流媒体发表的新闻报道约500篇,从中提炼梳理战争各方的言语行为,并结合战争进程探讨语言协同的作用与机理。为确保数据分析客观公正,论证过程力求建立在多种来源材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之上。
(一)伊拉克战争中的叙事要素
以往学者对叙事要素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人物与性格、目标与动机、冲突与问题、风险与细节等(Haven 2014;Marcellino et al.2022)。
人物是叙事中的行为主体,不同特点的人物性格刻画能够直接影响目标受众的观点态度。在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叙事中,萨达姆被塑造为独裁、残暴、充满野心且谎话连篇的赌徒。美国将自身刻画为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挑衅、逐渐失去耐心且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主持公道者。联合国被描绘为一个效率低下、优柔寡断、难以有效惩戒流氓国家的组织。法国和德国被认为缺乏国际战略思维、在利益问题上精打细算。俄罗斯被刻画为一个可能为伊拉克提供军事支持的潜在威胁。叙利亚被塑造为一个可能窝藏伊拉克领导且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国家。总之,每一个利益攸关方均被赋予了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为整个战争叙事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目标与动机是引发叙事主体实施战争行为的起点。只有正义的动机才有可能赢得目标受众的支持。早在2001年,美国政府就已经下定决心推翻萨达姆政权(Kaufmann 2004)。布什总统为这一目标提供的理据是伊拉克可能协助恐怖分子获取生化武器甚至核武器,并进而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这一战争动机显然需要得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支撑,而后续事实证明这一指控是缺乏依据的(Kaufmann 2004;Lule 2004;Lewandowsky et al.2005;Choulianaki 2005;Speer 2017)。
冲突与问题是叙事得以展开的重要动力。一帆风顺的叙事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也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冲突与问题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反应和持续关注的意愿。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营造了要求萨达姆限期承认拥有并主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冲突,敦促联合国授权解除伊拉克武装的冲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冲突,美英关于战后伊拉克重建中联合国作用的分歧,搜寻萨达姆藏身之地的波折,等等。正是这些冲突和问题助推了故事情节发展,将整个战争叙事不断推向高潮。
风险是营造悬念的重要手段。在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中,美军面临的潜在风险包括气象条件和战场环境对精确制导和夜战能力的影响、伊拉克革命卫队在巴格达开展巷战的威胁、俄罗斯可能为伊拉克提供GPS干扰技术的威胁、叙利亚可能包庇萨达姆及其他伊拉克政府高官的风险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叙事的悬念,也可以激发目标受众的紧张情绪。
细节是确保叙事情节饱满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拉克战争中对战争场面的转播、对精确制导武器性能的刻画、对萨达姆藏身之地的描绘、对疑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的报道等,都让整个叙事过程充满了看点。
总之,伊拉克战争就是一场类似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大片,有特定的剧本、塑造的人物、设定的情节。这一叙事模式不仅是为了改变伊拉克民众的认知,也是为了赢得世界观众的认同。如果接受这一叙事安排,就很容易接受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据。
(二)语言协同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
虽然语言在叙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叙事并不仅仅是以语言为手段。伊拉克战争中,叙事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语言和非语言手段的协同。
1.标定关键节点。伊拉克战争中的关键节点,往往伴随有关键人物的关键表态。例如,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9月12日,布什在57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敦促联合国制定针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2003年3月18日,布什发表讲话,对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4月9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萨达姆政权接近“土崩瓦解”;4月1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布鲁克斯准将表示美英联军已控制伊拉克全境;4月16日,布什宣称萨达姆政权已不复存在;5月1日,布什宣布结束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以上警告、通牒、宣战、止战等语言行为直接构成了战争中的标志性节点。同时也应注意到,以上语言行为的发生都离不开其他战争手段的协同。例如,开战前美英联军就已经在海湾地区完成20万兵力部署,美国已争取49个国家支持绕开联合国对伊动武,布什政府的舆论引导已将国内支持动武的比例从2002年8月的50%提高到了66%。正是由于军事、外交、舆论等手段的协同,才令语言行为产生了“言既出行必果”的威力。反观伊拉克,虽然包括萨达姆在内的政府官员也在尽力持续发声,但由于缺少其他战争手段的有效支撑,“言行不一”的问题逐渐暴露,其权威和公信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2.框定发展脉络。孤立的战争行为只有被组织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叙事。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例如,早在2002年1月,美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倒萨作战计划,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后组织论证了20个作战方案。正式开战前,战争剧本就已经定形。2003年3~5月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英国国防部、美国中央司令部、英军驻卡塔尔司令部以及各作战部队都在持续不断发声,实时介绍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正是由于以语言为主的同步直播,战争进程被串联起来并以可传播的方式呈现在全世界观众面前。再如,早在2003年1月,美国就已经成立了“伊拉克重建和人道主义救援办公室”。战争期间,布什与布莱尔多次会晤,核心议题都包括战后重建问题。这一系列语言行为,既在不断预设和预告战争的走向,也在配合主力战场的进展,以表明美国赢取战争的信心和决心。又如,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语言活动也贯穿了伊拉克战争始终。美英联军不时爆出“炭疽夫人”“细菌先生”“废弃防毒面具”“疑似化学工厂”“可疑化学液体”“化学武器检验阳性”“配备化学武器的中程导弹”“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移至国外”等报道。这些语言行为不断反复强化伊拉克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也作为一条暗线不断提醒观众美军实施系列军事行动的内在动因。可以说,语言行为与军事行动相互配合,共同勾勒出若干条明晰的战争主线,巩固了美国刻画、解读和定性战争进程的主导权。
3.策应军事行动。语言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牵制、迷惑、敲打对手的效果。伊拉克战争中,关于开辟北方战线的报道就是对南方主要军事行动的策应。按照最初制订的计划,对伊拉克的攻击应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但由于土耳其议会未能同意美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通过其领土进入伊拉克北部的请求,南北夹击方案落空。尽管如此,有关北方战线的爆料不时传出,例如特种部队士兵被运送至伊拉克北部苏莱曼尼亚机场、第173伞降旅空降至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中突击师抢占伊拉克北部机场等。其间,鲍威尔还首站专门访问土耳其,并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双方已达成提供后勤支持的协议,同时暗示将向土耳其提供10亿美元援助。事实证明,美英联军在北部战线的军事行动并不重要,但与其相关的语言协同策略却对南部战事起到了一定的策应效果。再如,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支“数字化”师的美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原计划从土耳其北部进入伊拉克,随后又机动部署至科威特,直至战争接近尾声才参与攻击萨达姆老家提克里特。这支被包装为世界上最具战斗力、最现代化、可进行全频谱作战的“铁骑师”何时参战、如何参战始终被赋予了一层神秘色彩,有效起到了迷惑、牵制、震慑伊拉克军队的效果。又如,巴格达被攻陷后,布什、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沃尔福维茨等政府高官密集发声,影射叙利亚可能包庇潜逃的伊拉克官员,并暗示必要时将实施越境抓捕。这一系列语言上的敲打,也是为了配合主力战场对萨达姆等伊拉克政府高官的追逃。
4.营造感染效果。语言与非语言的协同,还可以营造出特殊的战争效果。开战前,伴随着军事力量调动和军事联盟扩大,美国也在不断围绕3月17日这一“最后期限”造势。2003年3月9日,鲍威尔称联合国如果不能在3月17日前通过解除伊拉克武装的决议,军事行动就可能提前。3月11日,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将“最后期限”延长一个月。3月12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格罗蓬特强调只会给“最后期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短的延长期。同日,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斯托克要求安理会当天下午6点前就英国修订的“最后期限”条款举行磋商。3月14日,白宫发言人再次拒绝由智利等国家提出的延长“最后期限”3周的建议。3月15日,布什指出无论联合国如何决定,美国都已做好进攻伊拉克的准备。同日,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说伊拉克可用于解除武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3月16日,美国副总统切尼称关于延长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3月17日,鲍威尔宣布美国、英国、西班牙放弃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进行表决。3月18日,布什正式向萨达姆父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以上语言行为环环相扣,配合军事施压营造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倒计时氛围,不仅给伊拉克军队施加了巨大压力,也令全世界观众不断感受到日益紧张的战争氛围。又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对先进军事技术的渲染也是语言与军事行动协同的结果。战争爆发前,美空军在佛罗里达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常规炸弹试验。美国媒体将美国这颗最大的炸弹渲染为“巨型空中爆炸弹”,拉姆斯菲尔德随即直言该武器试验的目的是展示美军实力、迫使伊拉克军队放弃抵抗。整个战争期间,美军方不间断宣布发射巡航导弹、投掷炸弹和出动战机的数量,其目的也是在强调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和战争场面的宏大。再如,美军在军事行动命名上也颇有讲究,“震慑行动”“斩首行动”“树威行动”“切断蛇头计划”“铁锤战略”“碉堡克星”等命名方式也是为了瓦解伊拉克军队的抵抗意志。
(三)美军促进语言协同的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语言与其他战争手段的协同是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叙事的重要特点。在涉及诸多部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战争环境中,要将语言与非语言的手段捏合在一起形成叙事合力,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缺少内部资料,我们无法深入探讨美军内部实施协同的细节。仅从公开新闻报道中,我们认为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叙事充分体现了美军促进语言协同的策略,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特点。
1.建立战争叙事共识。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经过精心准备和包装的战争。战争叙事的框架、脉络、重点从一开始就进行了一体化设计并被严格贯穿全程。这必定需要建立在战争系统内部的广泛共识基础之上。早在2001年,布什政府就下定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决心,并指示情报部门收集伊拉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组织的关联证据。经过将近两年的外交博弈、情报编集、舆论宣传,在战争开始前“反恐战争”的叙事框架就已在美国国内达成共识(Speer 2017)。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战争的性质、背景、目标和规划都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这为语言和非语言手段的协同奠定了基础。事实也证明,美国战前、战中、战后的语言行为都在配合着军事、外交、舆论等领域共同强化“反恐战争”这一叙事框架。
2.管控战争叙事渠道。建构一体化的战争叙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语言行为的消息源和发声渠道。伊拉克战争是首场允许记者进行“嵌入式”报道的战争。2003年2月,布什签署命令成立了“全球宣传办公室”,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协调战略宣传工作,将美国官方观点辐射渗透至全球媒体。战争期间,美国防部邀请了全球500多名记者随军采访,但这些记者的报道内容和范围都被严格限制。实际上,随军记者的消息源大都来自美军各部门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某种意义上,这些随军记者发出的也是经过美军筛选的信息。其间,美军还剥夺了部分记者的报道权,原因是他们发布了不利于美军的新闻报道。
3.利用战争叙事窗口。在主体战争叙事框架上达成了共识,美国政府和军队各部门及官员在处理新情况、新问题时便有了目标牵引和发挥空间。例如,各支作战部队都将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证据作为重要目标。即使只是发现了一点可疑迹象,也会迅即发声,协助不断强化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再如,战争初期,美国宣称情报显示伊拉克获取了俄罗斯公司提供的卫星定位技术。美国国务院随即召见俄罗斯驻美大使,指责俄罗斯在军事上暗中帮助伊拉克。此外,美国在宣称获得所谓叙利亚为伊拉克提供军事装备的情报后,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都先后对叙利亚发出警告。这些语言行为,无论是预先设定的还是随机突发的,都是建立在对战争整体发展态势的感知基础之上,服务和服从于战争叙事的总体目标。
四、结 语
战争是体系间的对抗,军事语言协同是其重要特点之一。作为一种重要的战争手段,语言能力运用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需要与其他战争手段协调一致,才能在相互借力中建构有力的战争叙事。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拥有语言人才的数量、对语言资源的管理水平和利用语言完成任务的能力,更体现在“语言+”中产生的合力。未来军事语言能力建设还应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第一,军事语言协同机制研究。可以关注语言手段与其他软硬实力各方面的相互支撑关系,语言手段延展优势、弥补劣势的运用时机、媒介、策略方法等。第二,军事语言能力生成研究。可以从军队组织结构运行的视角,探讨军事语言能力从规划到运用的方法、过程、框架等。第三,军事语言能力建设方案研究。可以从机制、组织架构、训练教育、工具资源、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等不同维度探讨军事语言能力的建设方案、举措、路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