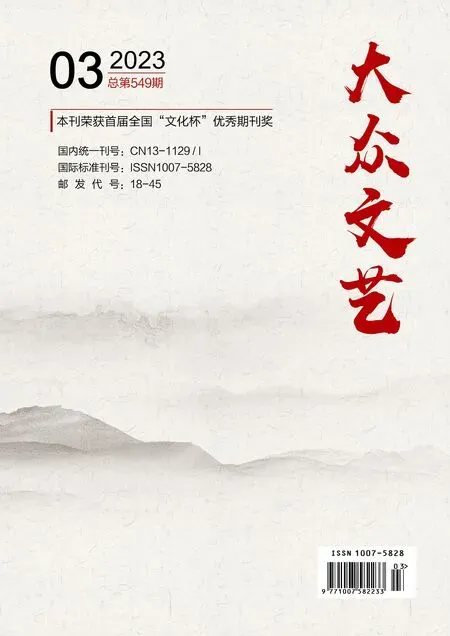“法”与“化”的辩证统一
——以明代波臣派为例
刘雨欣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 100048)
石涛在《画语录》中所论述的“无法而法”是艺术家都需要深入思考的观点,这一点关乎着艺术创作是否能体现出艺术家的创新。深受石涛“无法而法”理论的艺术家也不在少数,如与石涛并称“清初四僧”的其他画家,均以新奇与个性的画风著称;扬州八怪的艺术风格也是以此观念作为深厚的基础;近现代的画家也多支持此理论,齐白石曾评价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
本文将以波臣派为例,来论述石涛的绘画观念中所体现出的“法”与“化”之妙用。
一、“法”及其来源
(一)“法”的含义
在石涛的绘画理论《苦瓜和尚画语录》当中,“一画”理论是最具有特色的,同时也是较难理解的。而有关“法”与“化”的理论是其“一画”论的具体体现,因此理解其所谓的“法”与“化”及二者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
“法”即法则,是指人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和确立的他们认为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法则,而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在艺术中,所谓“法”是指法度,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实践所确立的艺术方向上的法则。根据石涛的《画语录》可以发现,他认为“法”分为三层含义,这三层含义也体现了无与有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衔接,即技法、理法与道法间既矛盾又统一的构成[1]。
第一层为笔墨等相关的技法之法,这是绘画需首要解决的问题。技法是形而下的,也是实际而基础的,在绘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达到“无法之法”所必需的支撑。“以有法贯众法”,技法体现着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也承袭传统,是艺术创作向前发展的基石。王羲之用池水洗笔,最终将水洗成墨色的故事即说明了技法的重要性。
二为有法,即理法。“无法生有法”,即太朴散后天地万物的生成,而导致的世界从虚无转化为有,从而理与法则建立。
绘画当中的“理法”这一层次表示画家在掌握技法的基础上注重从其中提升出的规定的法则。如南齐谢赫的六法论,成为历代画家们对一幅作品的创作与鉴赏标准。
第三层为其根源所在,也就是开宗明义的“太古无法,太朴不散”的无法状态,其中有“道法”的含义在,是以老庄哲学当中“道生于无”为背景的,暗含了“无法而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说技法是表面的、形而下的,那么道法则是一种心灵体验。
庄子通过庖丁之口阐发:“道也,进乎技矣。”表明了他推崇在技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道法。若只是单纯遵循理法,套用技法,就会被其客观性与规律性所限制,而无法认识到“法”的深层意味。因此要做到真正的“无法而法”就必须达到其最高境界,即“道法”。
(二)“法”的来源
“法”的出现是不是凭空的,石涛在《画语录》中认为“太古无法”,因此法则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当中逐渐产生的。
石涛认为,山水画描写的客观对象即是生活,而生活的规律即为理。“法”来源于生活,是人们从实践活动当中获得的,在经过实践的检验后证明其在具体条件下能够较好地解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隋末时期的姚最曾提出“师造化”说,石涛亦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都说明了艺术创作的法则应从生活当中提取。
“法”也来源于大众审美水平。群众的审美水平在不断提高,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绘画的法则也应当不断发展变化,在此同时也应起到继续提高群众审美水平的作用,这就是艺术接受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以及艺术创作对于大众接受水平的塑造作用。
美学意义上的“隐含的读者”实际上就发挥着大众审美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作用[2],如达·芬奇在创作《最后的晚餐》时将人物并排放在桌后,而不是和之前艺术家一样安排为围桌而坐的闭合结构,这是考虑到了观者的视角,将大众的审美因素融入艺术创作当中。
二、“法”与“化”的辩证关系
(一)“化”的含义
“化”即为“变化”“权变”。石涛在《画语录》当中进一步提出:“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只要有“经常”就一定会有“权变”,那么事物有法则也就一定会有变化。“化”的前提是“了法”,石涛提出:“古人未立法之前,不知古人法何法?”前文提到,法则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因此画法也是在绘画实践中慢慢总结出的。因此法也是“自我立”的,是具有创造性的,所以“化”是在以此为前提的情况下产生,如此才能在创作中达到“画可从心”。
唐代画家张璪曾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观念,这个观点便是将“得心源”这种“化”的过程建立在“师造化”的“法”的掌握之上。在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中,画家在表现鹊山和华不注山时即是根据现实景色,但在布局整幅画面时却是增加了更多主观的因素,这便是在原有的法则基础上进行“权变”,是作品达到既表现客观对象,又“画可从心”的境界。
此外,石涛所认为的“化”还有第二层含义,即“迹化”,这是来源于“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的天人相合的境界。“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这道出了“物”与“我”的契合融通关系,这种关系使得艺术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界限淡化,从而达到“神遇”和“迹化”。而能够进一步达到“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前提便是“搜尽奇峰打草稿”。要融入自然,便要先观察、感受自然。
(二)“法”与“化”的关系
由前文可见,“法”与“化”是不可分割的,有了“法”,就需要进一步作出变化,而“化”存在的前提也必须有“法”的存在。在绘画当中,拥有运用法度的变通性和灵活性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绘画中的“法”与“化”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石涛主张“借古以开今”,反对“泥古不化”,他不否认绘画传统应当得到继承,但艺术家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借助古法来发展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实际上,人们接受古法都是很容易的,但若要变通古法则需要灵活的思维和创造力。每个人在从事艺术活动时想要表达的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遵照“法”的同时要将自己的“化”融入其中。这也是石涛所提出的“我用我法”。
宋代黄庭坚评价苏轼的书法时说:“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他认为以古法为标准来评价艺术的高低是片面的。
当“法”与“化”的统一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即是艺术创作达到“无法而法”的境界。画家将已有的绘画法则与自己主观思想的变通力与创造力灵活地运用、相融合,这种“无法而法”,也是“我用我法”的极致表现。
(三)“无法而法”
1.“无法而法”的含义
“无法而法”是“法”与“化”统一的最高境界,是一个从无法到有法,再从有法到无法的内化过程。其中“无法”是指不受前人成法的限制,同时也指不为自己创造的成法限制。石涛所主张的“无法而法”是强调发扬主题个性、提倡师心的,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充满了革新精神。
石涛所提出的“无法而法”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3]。在第一个层面中以“自然法”的状态呈现,也就是“道法自然”,一方面这是要求艺术家从生活当中来提取“法”,另一方面是指在艺术创作的时候应追求情感、语言和方法的自然表达,例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过艺术创作忌讳面面俱到,他认为“自然者上品之上。”
第二个层面中的“法”应当能够以“无迹之法”的状态呈现。这便是将“无法”与老庄哲学思想相结合。老子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因此“无”的境界才是大美境界。在这一层面当中,“无法而法”的思想精髓是强调以“无”化“有”,在无限中包含丰富的有限。绘画也是如此,在看似毫无章法的画面中实则能体会到画家对法则的融会贯通。这便是“法”与“化”的辩证统一,因此说“无法而法”是两者融合到极致的结果。
第三个层面要用画家在运用“法”的时候要做到“我自用我法”。石涛认为,并不是只有古人可以立法,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不同来确立不同的“法”。因此“我自用我法”也要求画家不拘泥于古人或是其他流派的法则,而要将习得的“法”内化,再依据自身的心境来运用自己的“法”。
2.“无法而法”理论的意义
石涛的理论对于他自身和后辈的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其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他的作品有很多创新之处,笔墨也变化多样、用笔娴熟。例如他所创作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其中山川起伏连绵,点、皴法挥毫大胆,一气呵成,无处不体现着他对于冲破教条的主张,彰显着“无法而法”的豪情。
石涛在对于“法”的总结与创新之上也有着过人之处。他创造了很多种点法,比如当头劈面点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种点法的用笔直截了当,干脆利落。除此之外,他还创造了截断式构图法,不同于南宋的“一角”“半边”的大块留白式的构图,他截取最具代表性与美感的一部分。
石涛在取法自然的同时仍不忘吸取古法,在继承古法的同时也勇于创新,自成一家,这些都是对其理念的最好的实践。
此外,他的理论在前人的艺术创作当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南宋的马远和夏圭为凸显意境而创新的“一角”“半边”式构图;吴道子、曹仲达在人物画中形成的“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自家样式;明代徐渭在写意花鸟画的基础上创新的“大写意”花鸟等等。而后文将以明代波臣派为例,分析其人物画当中所体现的“无法而法”理念。
三、波臣派
(一)波臣派之“法”
波臣派[4]的创始人是明末时期的肖像画家曾鲸,曾鲸以绘制肖像画谋生于江浙地区,后拜师学艺,挟技北上。在他北上的这段时间里正式他肖像画艺术初成的时期,52岁时他创作了《王时敏像》(图1),此时他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图1 《王时敏像》
曾鲸的艺术在当时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师从者甚多,并形成了波臣派这个重要的肖像画艺术派别。曾鲸及其波臣派的特点即是在已有之“法”的基础上加以“化”之,形成自己的风格。
曾鲸以何“法”为基呢?从《国朝画征录》中可推测,曾鲸早期深谙江南派[5]的画法,或许与其有着师承关系。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葛一龙像》,便是曾鲸运用江南法的粉彩渲染绘制而成的。
其次,曾鲸后期也善用墨骨画法,先用墨骨出形,然后再层层渲染、罩色。在此过程中,他也吸收了西方绘画中的明暗画法,以表现人物面部结构的凹凸。清代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评价利玛窦带来的西域天主像说:“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在描述曾鲸的肖像画时用了类似的词语:“磅礴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可见曾鲸的画中吸取了西方造型的元素[6]。
(二)波臣派对“法”与“化”关系的处理
曾鲸及其波臣派借鉴吸收了多种绘画之“法”,但与此同时也有所创新,对其“法”进行“化”,这符合石涛所认为的“有法必有化”。
曾鲸作肖像画以墨骨法为主,先以墨出形,再层层渲染面部的结构凹凸,最后再用色罩染。这种方法又与传统的高染、低染法不同,它不是柔和的过渡形态,而是较强烈的墨色色阶变化。
如《王时敏像》,此图是曾鲸肖像艺术进入鼎盛时期之作,画面中对人物面部结构的刻画细致入微,将一介文人的温雅形象表现得生动形象。在这幅图中,画家在对人物面部结构的处理上吸收了西方的画法,但并未完全沿用西画强调光影的方法,而是以面部结构为依托,在此同时也保留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写意精神,将人物的神态也表现得很到位。
同时,曾鲸的肖像画注重对神情的描绘,这和传统肖像画中将服饰也具体刻画的衣冠华丽而面貌庄严的习惯不同,在这方面曾鲸也对画面的主次关系作出了创新,这也是他不拘泥于古法的表现。如《张卿子像》中对人物的服饰刻画简洁朴素,衣纹也只有寥寥数笔,而重心则放在了人物面部的刻画,使得整个人物的主次关系变得更加明确。
在创作时,曾鲸与对象相对晤谈,在此过程当中发现对象的真性情,从而使自己产生对人物的感受。在面对人物的客观样貌时,没有选择照抄形象,而是根据内心的主观感受来创作,这也做到了“法”“化”相融,“无法而法”。
结语
综上所述,石涛的“无法而法”理论不仅影响着后人,在前人的绘画中也可窥见一斑。前文所述的曾鲸与其波臣派便是一个例证。
“无法而法”理论在现代仍有着重要意义。不论是艺术创作过程还是艺术接受过程都应结合“无法而法”的方法论来进行。它将“技”“法”“道”三者统一,既注重了技法的传承与运用,又强调了创新与自我的重要性,这样主体在艺术活动中才能具备感悟性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