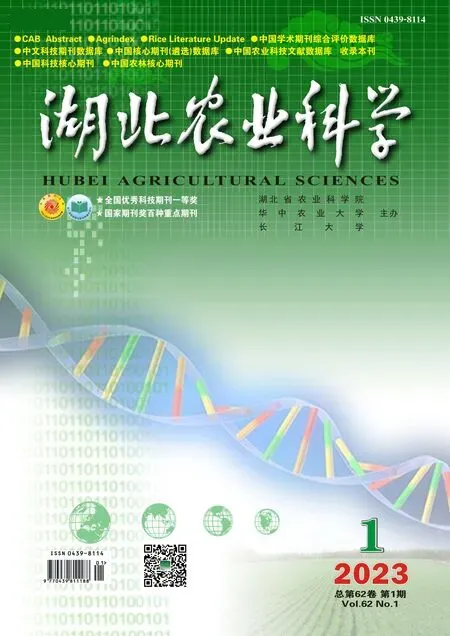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农村空间转向研究
——以JX 省D 村为例
丁雪丽
(上饶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江西 上饶 334001)
“十一五” 规划提出了以发展生产、生活富足、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1],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农村建设由单维度的要求转变为多维度的综合要求。农村空间的重要性及其认识也需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要突破传统空间认知。农村空间往往被视作乡村人口及各项经济、社会活动发生的场所, 多是具象化为田地、菜园等生产场所, 房屋、巷道、广场等生活场所。农村空间是一种狭义的地理资源, 是一种实体的物化概念, 常常是孤立隔绝的。在这种空间认识指导下, 农村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也陷入误区:农村建设就是拆旧房修新楼, 甚至限制房屋面积与外观样式;农村建设就是加宽加厚道路, 新修活动广场、休闲服务中心。结果农村建设陷入对物质空间大改造的怪圈, 忽视文化与社会空间等软实力, 农村的发展进程缓慢。
现有研究对农村空间的分析开始于农村空间内涵的探讨。李家清[2]认为农村空间是由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电力网络构成的。农村空间又被认为是随着生产方式变化的居住空间布局[3]。在农村空间内涵的基础上, 衍生出对空间结构、空间形态的研究。空间结构是点、线、网络和域面四要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而成, 农村空间结构是一区域内某时间点上村庄数量、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的静态对比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状态, 以及不同时间点上动态空间变化[4]。空间形态演变受到城市化快速扩张[5]、新农村建设政策[6]、自然生态、近代工业化、国家意识、乡镇工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7]。随着人文地理学社会与文化的渗透, 受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影响, 空间由实体概念发展到观念概念, 空间发生了转向[8]。空间不仅是承载物质的地域单元, 还具有社会性, 是对社会和人的行为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的动态实践过程。然而对于农村空间的研究从内容上以空间物化实体概念为主, 忽视空间观念概念, 缺少对农村空间丰富社会性的关注, 减少了对空间问题复杂性的关注, 一定程度上难以精准看到农村空间变化的实质;从视角上多是用具体空间概念深入分析, 少有运用系统理论视角剖析农村空间的研究, 削弱了空间理论研究的高度和深度。这一系列不足有必要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系统研究, 用新的思维重新审视空间转向问题。
因此, 本研究将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 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法, 对中部省区一农村空间生产进行分析, 旨在认识农村空间转向特征。
1 相关理论与调查情况
1.1 相关理论
1.1.1 空间生产理论 历史上空间被定义为被填充的容器, 实证主义地理学影响下形成一种物化的空间理论, 是一种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9]。20 世纪70年代开始,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地理学、城市学结合, 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空间不仅是承载物质的地域单元, 而且因置于其中的人和物的各种复杂而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关联系统被赋予丰富的社会内涵。空间的社会本体论和空间概念成为研究的核心[10]。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是空间生产理论的首创者。列斐伏尔批判了将空间视作容器和场的传统观点, 开创性地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要从关心 “空间中的生产” 转向 “空间本身的生产” , 赋予空间生产社会关系[11]。他融合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形成空间三元辩证法来解析空间生产的问题, 建构了一个由 “空间的实践” “空间的表征” 和 “表征的空间” 组成的空间本体论三元一体理论框架。
空间的实践属于社会空间被感知的维度, 社会成员通过使用、控制、改造等进行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是具有物理形态的社会空间;空间的表征属于社会空间被构想的维度, 是科学家、规划者、社会工程师等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空间, 部分群体通过控制空间语言符号及知识体系形成隐形空间权力进而干预影响空间建构;表征的空间属于直接经历的空间, 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 处于被支配地位, 充满矛盾与抗争, 是人们试图改变与占用的空间。其中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是对立的, 即支配与被支配的空间。而空间的实践是空间的表征指向表征的空间的转换地带, 是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三者同时共存, 相互作用。
1.1.2 农村空间生产 农村空间生产将突破传统观念中只将农村空间视为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的观点, 否定农村空间是地域单元的单一认识。农村空间生产不仅关注到农村空间物质属性, 即空间中不仅是被填充的物质, 还关注到其社会属性, 关系空间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 主要命题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农村空间本身的生产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生产, 而生产关系体现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 于是空间就成为社会关系弥漫的场所。
农村空间和农村社会互相构建, 空间不仅是社会的产物, 也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农村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社会行为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12]。在这过程中可分为3 个层面:空间的实践是感知的空间, 是人们使用、控制、改造的物质空间, 如房屋、街道、庭院;空间的表征是构想的空间, 是知识与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文化空间, 如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表征的空间是生活的空间, 是人们试图改变和占用的社会空间, 如社会关系、冲突矛盾。文化空间同社会空间相互对立, 抽象的权力系统和鲜活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对立, 而物质空间作为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换地带, 其中空间行动者不断使用、控制和改造, 促进农村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农村空间与生产是辩证统一的, 社会空间由社会产生, 同时生产社会。
1.2 调查对象
空间生产理论引入空间维度解释社会经济现象, 构建了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三元辩证分析法, 对诸多现实发展问题的解析提供新的视角。空间生产理论开始运用在城市的研究, 分析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及动力机制等方面。随着城市化扩展到周边农村, 该理论也运用到农村的研究中, 提出乡村空间三元分析框架、探索乡村空间生产可持续的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本研究对象A 村是位于中部省区JX 省赣东北地区的一个近郊乡村。该村位于320 国道北侧, 距县城16 km, 10 km 距离内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成为当地村民就业的一大来源。全村共有11 个自然村, 26 个村民小组, 1 178 户, 人口5 416 人, 水田面积146.67 hm2, 山林面积400 余公顷。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 盛产茶油。村内人口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 依据姓氏聚居。村民由大量外出务工逐渐返乡, 在经开区及县城实现本地就业。村中的建筑大多是新建的楼房, 外观崭新, 样式从平楼到别墅, 越来越现代化。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通过实地调查与A 村村民零距离接触, 观察村子状况及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在观察交流中选取7 名村民和1 名村干部作为访谈对象, 重点探讨对村子近些年空间变化的感知, 包括居住状况、交通条件、文化氛围、制度风俗等。从对村干部的访谈了解基层政府农村、农地政策带来的影响及具体管理情况。依据录音整理和现场笔录的材料形成本研究的主要依据。调查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表1 所示。

表1 调查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2 空间生产理论下的农村空间三元分析
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将农村空间分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3 个层面, 3 层空间共存且相互作用, 形成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融合的空间三元一体框架。农村空间由社会产生, 同时也生产社会。
2.1 物质空间利益化
物质空间是具体的空间存在, 是承载物质的地域单元, 主要表现为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围绕A村村民生产生活行为活动构成 “室-庭-道-田” 的空间格局, 具体空间单元从点到线再到面, 刻画出最常接触、最为主要的活动轨迹。近些年村庄的房子由土、梁木建造的祖屋迅速变成一幢幢独立高大的楼房, 房屋选址远远突破了传统宅基地的地理限制, 通过土地置换、购买等交易行为, 村民的房屋越来越靠近主干道, 道路两旁房屋伫立。道路两旁的房屋因其位置优势常会转变成商铺, 能够赚取一定租金收益。村子里房屋紧邻, 通过共享的道路延伸至各家庭院、房屋, 共享的空间和私有的空间难以明确界定, 继而出现村民不断扩大私有庭院、房屋面积挤占共享空间的现象。随着汽车的增多, 村民对更大通行空间的需求成为必然, 这时挤占而来的私有空间就成了置换、交易的商品。有车的家庭如果想要通行就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换取邻居私有空间的退让。生产空间主要是田间地头, 大多数村民进城或外出务工, 大量田地不是荒废就是承包给规模生产的农户。能够承包出去赚取微薄的收益是更好的选择。
2.2 文化空间同质化
文化空间是由科学家、规划者、社会工程师等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支配, 具备构想性、象征性。该空间通过具体的生活、娱乐等方式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概念呈现出来, 形象化空间生产与生产关系。文化的传承性与融合性决定了文化再生产的持续可能。A 村文化空间受到城市化进程、乡村新政策的影响, 空间建构过程中被干预。物质文化方面, 主要表征为村民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和交通工具。随着乡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 村民的服饰、饮食购买愈加便捷, 尤其是因在近郊随意进出城市购买也成为了一种可能, 逐渐趋同于城市居民。房屋建筑受新农村建设政策影响, 村里的房子屋顶被要求统一用琉璃瓦筑成三角顶, 墙体统一刷成白色。注重房屋的整齐划一, 对标城市小区楼房。汽车家庭拥有量逐年提升, 几乎是家家户户有车。
制度文化以节庆、丧葬制度为主要表征。除去国家法定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 村子传统惯例还会庆祝元宵节、中元节和重阳节。城市化工业化提供大量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充斥了村民的闲暇时间, 节日氛围逐渐消散, 偶有的休闲时间村民们也是涌向城市, 逛街、看电影、观光等。村民对历来已久的土葬制度有深深的执念, 也有崇高的敬畏。然而, 火葬政策的严格推行, 村子里也出现公墓, 丧葬活动也相对简化。
精神文化是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逐渐显现的精神内在追求。乡村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文化方面也愈加多元。电子产品旁的影视游戏迷, 围坐桌前的牌友, 广场上活力满满的舞蹈队, 健身器材上姿态各异的健身人, 池塘边沿护栏伫立的交谈人, 滑板跑鞋上奔驰的儿童……乡村的夜不只是孤寂宁静, 还有喧嚣热闹。
2.3 社会空间冲突化
社会空间是人们直接经历的生活空间, 处于被支配地位, 充满矛盾与抗争, 是人们试图改变和占用的空间。空间生产过程中, 村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不同于乡村空心化、空巢化现象, 村子中青年劳动力(原本居家的、返乡的)都选择居家就近工作。10 km距离范围内的经济开发区成为村民早出晚归的通勤圈。能营生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 给社会关系带来变化:村子社会流动小, 小家庭为主, 大家庭观念淡化;差序格局下大家庭中邻里互动越来越多的体现为团体格局下兴趣伙伴、工作伙伴关系。因此, 在面临空间利益不公时, 兴趣、工作伙伴关系松散, 难以有组织有行动地表达空间需求。新农村建设政策以示范点形式推进, 邻村首次成为示范, 增添了广场、健身设备、文化活动馆, 翻新了宗族祠堂, 平整拓宽了道路。但是后续几年该村又多次成为示范村, 新建的广场、文化活动馆等又开始新修, 道路又开始维修。示范点推广形式成了只建设示范点, 甚至是短期内多次翻新, 其他村子则毫无进展。该村村民对邻村的变化欣羡不已, 私下议论邻村公共财产的浪费, 对村干部行为有些许愤恨, 但也只能默默期盼, 期盼新农村建设能够在本村实施。终于在周边村子全部建设完成甚至弃置后轮到了该村, 该村才有了活动广场、平整道路。在政府权力主导的空间规划中, 村民被规训, 没有协商话语权。但是村民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强烈, 衍生出一种非正面的、滞后性的反抗, 对基层政府不信任、不配合, 通过集体行为另谋公共空间。如在发现一家私企侵占村子山林时, 集体协商谈判要求该企业为村子铺设路灯。
3 结论与对策
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 工业化、城市化影响下农村空间不断生产和重构, 成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 不仅有实体的物质属性还兼具抽象概念的社会属性。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分析农村空间的转向, 突破传统的空间物化概念, 从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组成的三元一体框架构建空间观念概念, 展现农村空间丰富多元的社会属性。研究发现农村的物质空间趋向利益化, 知识和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化空间农村和城市同质化, 直接经历的社会空间中存在官民矛盾, 冲突化明显。
因此, 农村建设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村空间的多元社会属性。针对目前农村三元空间展现的特点, 可以从3 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①树立空间共享理念。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相互依存, 此消彼长。农村空间使用需要树立空间共享理念, 共享才是空间利益的最大化体现。②保护空间独有文化。城市建设一度陷入千城一面的境况, 农村空间也越来越趋同于城市必然会给农村面貌带来巨大的损失。农村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保证农村有享受城市便捷多元权利, 也要保护好农村独有文化。③开展空间协商治理。农村空间治理长期以来是政府主导的, 村民缺乏平等协商、利益反应的渠道, 埋下了官民冲突的隐患。农村建设发展需要开展空间协商治理, 构建官民沟通的良好渠道, 发挥官民合力作用, 推动农村建设和谐稳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