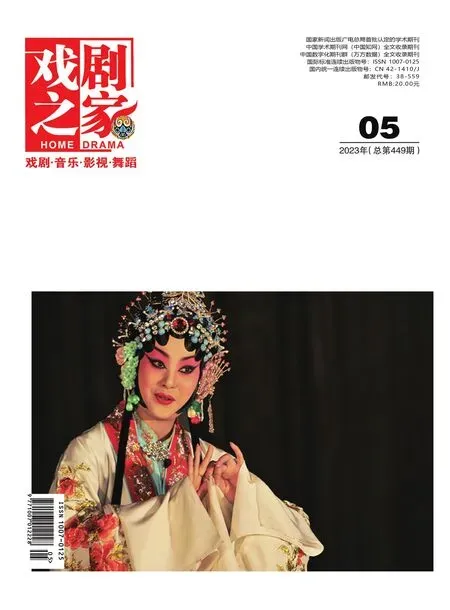《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对人主体性的解读
赵君宇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 100088)
伊日·门泽尔(1938—2020)是20 世纪60 年代捷克新浪潮电影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擅长用喜剧的方式进行严肃的政治反思,辛辣尖锐的同时又充满无限的悲悯和同情。伊日·门泽尔执导的大部分电影作品都改编自赫拉巴尔的小说,他与赫拉巴尔首次合作的影片《严密监视的列车》获得了1968 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除此之外,门泽尔还改编过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以及《失翼灵雀》,是名副其实的“赫拉巴尔电影专业户”。门泽尔曾说:“假设赫拉巴尔也从瓦夫拉教授那里学会制作电影,我会尽力按照他会采用的方式去制作电影。在改编电影时我一向带着这份谦虚,只要我改编作品,我就尽我所能去了解作者,理解他表面下的本质。”①《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原著小说以老年杨·迪特的视角展开叙事,以自传体回忆的第一人称叙事结构全文,依时间顺序分为五个章节。在电影的叙事中,伊日·门泽尔以老年迪特出狱后在偏远山区修路隐居作为电影的现在时空,并用蒙太奇的手法插入前面四个章节的叙述,形成一种回望和反思的视角,以此来揭示赫拉巴尔小说中蕴藏的哲理。
一、金钱和欲望对人的异化
在《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伊日·门泽尔将严肃的存在主义反思同诗性品格巧妙结合起来,运用排比、反复,以及隐喻和象征的手法,揭示了青年迪特在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的双重控制下持续异化的人生处境。
首先,小个子迪特的侍者身份是一个十分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隐喻象征。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异化”即人把自己降低到被决定的物的地位,失去主动选择的可能和自由。他通过咖啡馆侍者的实例来说明人是如何进行“自我欺骗”的:咖啡馆侍者殷切满足顾客的一切要求,成为他人所希望他成为的侍者的时候,他就将自己异化为客体了。“他把他自己应用于拴住他的活动……他给予他自己以物的快速性和物的无情的急剧性”②,咖啡馆侍者将自己异化成了“服务员”的存在,成为他人眼中的客体。影片中,青年迪特对自己的侍者身份深信不疑,他习惯并接受了这种异化的价值观念和生存准则,最后逐渐迷失自我。迪特的终极目标虽然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旅馆,但其实质还是服务人的侍者。为了实现他所谓的梦想,迪特不惜出卖自己的道德灵魂。他靠小聪明抢走本属于自己上司的荣誉,最后为了获得自己想象中的身份地位,不惜背叛自己的国家,与德国纳粹姑娘丽莎结婚。同时,来自他者的注视又加强了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异化关系。迪特每天穿梭于精英权贵之间,时常被他们随便对待,得不到基本尊重,在上流社会的人的世界观里,他不过是一块不起眼的边角料。
金钱和女人是青年迪特确立自身存在和建立身份认同的两个重要意象。做侍者的所见所闻使迪特领略了金钱的“美妙”之处。影片中不断重复着一个视觉主题:迪特总是趁人不注意时洒下一把硬币,于是,听到硬币落地声的人们,就全然不顾礼节尊严,趴在地上哄抢零钱。从平民火车站到巴黎饭店,这一荒诞的场景在不同环境中出现了四次,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上流人士,都为这几个零钱弯腰低头。矮小的迪特仿佛在那一刻高大了起来,似乎拥有了掌控他人的权力。
其次是女人,影片中总共出现了四次关于迪特与女人性爱场景的描写。青年迪特首次使用金钱和天堂艳楼的美丽妓女雅露什卡做爱,他还用花朵精心装饰雅露什卡的胴体,让雅露什卡也欣赏自己的美丽。通过这种物化女性的方式,迪特找到了另一种确认自身存在感的方式。第二次是和宁静旅店的女服务生,第三次是和巴黎饭店的尤林卡,这两次相似的场景刻画起到了强调和推进的作用,表面上看是迪特的“百万富翁梦”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实际上暗示了他自身不断加深的异化处境。第四次是迪特和德国纳粹女孩丽莎,之前迪特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这一次则十分被动。迪特与女人的身份发生了调换,他在追逐金钱和权势的路上完全异化为两者的奴隶,丧失了自我。
宁静旅馆是影片中体现“人被异化”这一主题的另一个重要意象。迪特认为“旅馆本身就像一台自动风琴,有人突然丢了一个铜板,一切就会自动开始演奏”。不论权贵人士何时到来,宁静旅馆中的侍者总能不知疲倦、事无巨细地提供各种享乐服务。侍者们如同宁静旅馆里精美的家居摆件一般被物化了,他们一切都听从金钱指挥,失去了自由和选择的权利。
二、从荒诞出发到反抗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另一个要讨论的存在主义命题是如何直面人生的荒诞。荒诞是指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的灵魂深处竭力追求清晰合理之间的冲突,一个人一旦产生了荒诞意识,他就会觉得自己与生活格格不入,一切看似合理的东西都会对立起来,变得荒谬。影片通过迪特、将军和首席服务生卡雷尔三个人物展现了不同人面对荒诞的态度。
首先是经历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选择直面荒诞的迪特。迪特历经千辛万苦,靠不义之财买下了宁静旅馆,成了百万富翁,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空虚感,“我的目标曾是当百万富翁、买旅馆,而我两个都做到了……接着我不知道还可以怎么花钱”。随后,迪特的饭店被没收了,所有百万富翁都被关进牢里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十分热烈地希望自己也以百万富翁的身份关进去。然而,即使在牢房里,那些上流人士仍然拒绝迪特和他们平起平坐。迪特终于认清这一荒诞的事实,他所生活的世界突然变成了一个“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其一生关于“百万富翁等于尊严和幸福”的信仰也随之崩塌。在这种情况下,迪特终于开始正视荒诞,他选择做一个西西弗式的英雄。
迪特说:“努力修复一条无用的道路,我渐渐把修复道路,当成修复人生”。这与《西西弗的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西西弗被罚永生推巨石,但就在他即将把石头推上山顶的时刻,石头滚回山下,他又要开始新的劳动,循环往复,没有尽头。西西弗选择和注定失败的命运作斗争,在面对荒诞时没有逃避,而是勇敢与其共存,这样他就获得了自由,生命价值和尊严在与荒谬的抗争中有了意义。加缪认为,西西弗接受这个惩罚不是不幸的,反而是幸福的,“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所以,西西弗是幸福的”③。同样的,迪特说,“我的幸福往往来自我所遭遇的不幸”。迪特如西西弗一般拥有正视荒诞并与其共存的勇气,他并不认为在偏远山区修复一条无用的道路是不幸的。迪特在经历虚假的繁华之后沉淀下来,严肃地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和叩问。他将修复道路比作修复人生,在看似不幸的当下却拥有了清醒认识人生荒诞的自由,对没有意义的生活的坚持就是对荒诞的反抗,反抗将生命的价值赋予人。
其次是选择否定、逃避和自杀的卡雷尔和将军。卡雷尔是巴黎饭店的首席服务生,用杂技一般优雅的方式上菜是他的绝活。一次上菜表演中因失误当众出丑,使得他干脆自暴自弃,直接丢掉整个托盘,并且打砸饭店里的其他器具。卡雷尔的侍者尊严荡然无存,他与世界突然对立起来,此刻他虽感受到了荒诞的存在,但还是选择以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方式逃避荒诞。将军也是如此,从前他依靠手中的权力可以在捷克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但是面对德国纳粹的入侵及自身权势和地位被剥夺,他选择开枪自杀。正如加缪所说,选择自杀的原因是感觉到生活没有意义,人的存在没有任何理由。
相较于高高在上的将军、技艺精湛的首席服务生卡雷尔,反而是最底层的迪特有勇气直面荒诞,正因如此,迪特才能真正摆脱金钱对他的物化,实现人生由不自由向自由的转化。发现荒诞不是终点,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荒诞,如果我们因为荒诞觉醒而选择自杀,就是毫不挣扎地向荒诞认输。对荒诞有所觉醒的人应该拿出勇气正视荒诞。
三、老子哲学的熠熠光辉
米兰·昆德拉曾评价赫拉巴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作家”。20 世纪20 年代,捷克语译本《道德经》在捷克首次出版,赫拉巴尔由此开始接触老子哲学思想,其之后的作品创作也深受其影响。他在创作《过于喧嚣的孤独》时,不仅借主人公汉嘉之口表达老子“天地不仁”的哲理,还多次将老子和耶稣放置在一起,进行中西方两种思想的对比。《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也蕴含着老子“祸福相依”的辩证思想和“无为”的思想,而门泽尔作为最能走进赫拉巴尔内心世界的导演,总能够运用最恰当的影像表达出原著小说中所蕴含的老子哲学思想。
老年迪特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我的幸福往往来自我所遭遇的不幸”,这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辩证哲学观念。迪特从最低等级的旅馆学徒一步步走到顶级饭店的领班,每当他小有成就之时,马上就会遭受挫折与失败,然而这些受挫的经历又铸成了他向上攀升的契机。正如他所说,“我的幸福往往来自我所遭遇的不幸”。门泽尔巧妙地运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表现老子“祸福相依”的辩证思想,两条叙事线松弛有致,蒙太奇的运用使得青年段落的明亮鲜艳和老年段落的低调沉着形成了强烈对比。其中一条线写“祸”,表现青年迪特受金钱和权力所奴役的前半生;另一条线写“福”,表现出狱后的老年迪特历经磨难,重拾做人的尊严和自由,终于看清了人生的真相,回归自然,获得了生命的平静。
老子所主张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强调节制,反对“有为”中对于名利的盲目追求和滥用。在《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门泽尔通过反讽的艺术手法对盲目追求金钱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用幽默包裹严肃的现实,使得影片增添了举重若轻和积极乐观的诗意。首先是影片中丑态尽出的奸商和政客,他们滥用金钱的力量满足自己的欲望,或是投机取巧牟取暴利,或是挥金如土胡作非为。而迪特黑色幽默般的悲剧性人生,更是构成了对人生存境遇与命运的一种隐喻。正是由于青年迪特对名利的盲目追求和滥用,造成妻子意外身亡,儿子痴呆,而他自己最终也锒铛入狱。因此,在金钱万能的逻辑下,金钱成为衡量世界的尺度和标准,人会沦为金钱拜物教的牺牲品,或是利用金钱奴役他人,或是因为金钱成为被人操控的奴隶,从而丧失作为人的主体性。
海德格尔曾经认为老子的思想非常精妙,还尝试着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不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还是老子都对生命本体的存在状态进行了反思。存在主义对“现代化”和“技术化”进行剖析,认为技术使人生存在非本真状态中,成为物的奴隶。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生存方式,反对利欲观念,追求自然无为的生存境界,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存在相同之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将存在主义和老子思想之间的哲学对话用影像表达出来。迪特前半生盲目追求名利不懂得适可而止,未曾获得真正的尊重和自由。在意识到这是何等荒诞之后,迪特选择归隐山林,远离人群,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诗意地栖居,终于收获了做人的尊严和宁静的生活。因此,面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失落,人类首先要有勇气直面荒谬和虚无的存在,同时选择在“无为”中成为自己,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生存境界。
注释:
①任义.灵雀与珍珠——“捷克新浪潮”与伊日·门泽尔的电影创作[J].电影艺术,2009,(02):142-149.
②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M].重庆出版社,1989.209.
③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M].杜小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