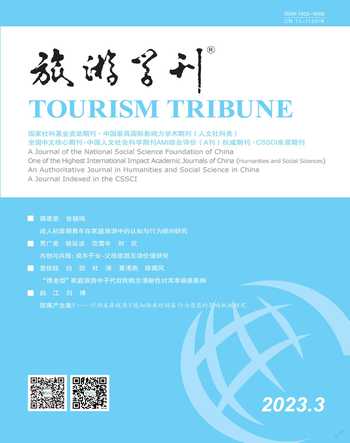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进展及学术贡献
——基于10本英文期刊载文的分析
李默涵,陈钢华
(1.广东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地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2;3.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引言
新冠疫情(以下亦简称“疫情”)给全球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1]。作为一个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包括学者、期刊、学术组织等)针对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做出了迅速的响应。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以英文期刊为主导发表平台的全球学界[1],快速地出现了一批旨在及时分析新冠疫情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的文献[2-6]。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旅游研究也仍在继续,不断有新成果发表。有学者通过在Web of Science 和Scopus 上检索,发现截至2021 年3 月31 日,在英文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1303篇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 论 文[6]。2021 年12 月28 日,笔 者 在Google Scholar 以“COVID-19”和“tourism”做检索(限定2021年1—12月发表的成果)发现,累计有53 900条结果;而将发表时间限定为2020年1—12月做同样的检索,结果为36 100 条。那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到底关注到了哪些更加具体的主题领域?采用了何种研究进路以及资料/数据收集渠道?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关注特殊情境或受突发性公共健康危机事件影响的领域,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是否做出以及做出了哪些方面的学术贡献(包括理论贡献、方法论贡献等)?
截至2021 年12 月29 日,至少有5 篇综述论文已经较为详尽地回顾了最晚截至2021 年3 月31 日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7]。然而,这些综述论文尚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缺憾:其一,所回顾的论文均发表于2021 年3 月31日之前,分别截至2021 年1 月7 日[2]、1 月11 日[3]、2月①该文没有注明论文检索时所使用的截止日期,但该文发表于2021年2月。因此,该文检索论文时所使用的截止日期不晚于2021年2月28日。[4]、3月7日[5]和3月31日[8]。因此,所回顾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在新冠疫情早期开展的[3]。在2021年3 月之后,全球旅游学界又涌现出了大量的有关新冠疫情的研究成果。其二,更重要的是,上述综述论文局限于对研究领域、方法等做梳理和分析,缺少对所回顾论文的学术贡献(包括理论贡献、方法论贡献等)的评价。正如Tribe所指出的,理论创新才是旅游研究乃至整个旅游学科长足发展之道[9]。实际上,关于旅游研究的学术贡献(包括理论贡献、方法论贡献等)近年来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0-14]。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1月,有国内学者对发表于8本英文期刊且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旅游者行为研究进展(主题、理论、方法)做过较详细的梳理,且对它们的学术贡献做了简要评价,但仅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旅游者行为研究[7]。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尝试对发表在英文期刊上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进行检索,梳理它们在研究主题、研究进路、资料/数据来源等方面的进展,重点评价它们的学术贡献,并对导致学术贡献现状的原因给予解释,以期抛砖引玉,为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出于对样本选择代表性和便利性的考虑,本文在10 本旅游类英文SSCI 期刊进行文献检索,具体期刊名单见表1。选择这10本期刊的原因是:其一,在Clarivate Analytics 于2017 年至2021 年陆续发布的5份《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中,这10 本期刊曾至少一次位列Q1 区,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二,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成果散见于旅游、休闲、经济、管理和环境等领域的期刊,数量众多、主题庞杂。例如,有学者统计,仅在2019 年12 月1 日至2021 年3 月7 日之间,在同行评议的旅游与酒店类英文期刊上,累计发表了417 篇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论文[6]。另外,有学者发现,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之间,在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1303 篇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论文分布在旅游、酒店、休闲、运动、经济、管理、城市研究、环境研究和商业期刊上[8]。这一状况可能会给识别真正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综合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取样的便利性,2021 年9 月,笔者在上述10 本期刊分别以“COVID-19”和“COVID”“pandemic”“epidemic”“coronavirus”和“corona virus”作为篇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发表日期截至2021年8月31日。经过逐一筛选、确认,累计获得245篇符合要求的论文。

表1 样本论文在10本期刊的分布Tab.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articles in 10 journals
如表1 所示,这245 篇论文在10 本期刊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发表相关论文最多(74 篇,30.2%),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46 篇,18.8%)紧 随 其 后,Tourism Geographies(30篇,12.2%)则位列第3。在所有245篇论文中,发表于2021 年、2020 年的论文分别为169 篇(69.0%)和72 篇(29.4%);另有4 篇(1.6%)在检索时就已安排在2022 年发表。从论文类型看,160 篇论文为研究论文(research article,65.3%),24篇论文为研究笔记(research note,9.8%),8 篇为案例研究(case study,3.3%);其他类型的论文(例如评论、观点、给主编的信等)有53篇(21.6%)。
论文的编码和数据处理工作由两位笔者分工完成。具体而言,245篇论文按序号对半分。首先,由两位笔者分别对122篇、123篇论文进行基本信息(例如年份、期刊、作者、单位、论文题目和研究主题、研究进路、资料/数据收集渠道、投稿日期和在线发表日期等)的摘录工作。各自摘录完成之后,再交由对方逐一核对。在核对过程中,并未发现错漏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建立的研究主题分类框架是两位笔者在分别对两组论文进行阅读并形成初步的分类框架后再经由双方讨论确定的。之后,两位笔者再依据这一分类框架对论文进行编码工作。
其次,两位笔者分别对这两组论文进行学术贡献(主要包括理论贡献)评价和编码工作。在组织与管理学界,Colquitt 和Zapata-Phelan 基于理论检验和理论建构两个维度,建立了一个评价研究论文的理论贡献的框架[15]。具体而言,在理论检验方面,Colquitt 和Zapata-Phelan 将论文的理论贡献分为5 个等级,分别记1~5 分;类似地,在理论建构方面,每一篇论文也都可以从5 个等级进行评价,也分别记1~5 分[15]。在Colquitt 和Zapata-Phelan 的分类框架中,根据理论贡献的差异,共识别出5 种类型的论文,分别是“报告型”论文(reporter)、“理论建构型”论文(builder)、“理论检验型”论文(tester)、“合格型”论文(qualifier)和“理论拓展型”论文(expander)[15]。
另外,笔者还基于Tribe有关旅游领域的知识生产与组织的论述[12],提出了一个旨在评价论文的学术贡献(包括理论建构、理论检验和方法论创新等)的框架,对纳入分析的245 篇论文的学术贡献做出另一轮评价和分类,即分为如下7 个类别:S1(解决异常复杂的理论/实际问题)、S2(方法论创新)、S3(引入新的视角)、S4(对原有理论框架中的已知变量/变量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S5(只是引入/改变某个变量,并未对现有框架、概念做出重大改变)、S6(只是验证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对现有框架、概念做出重大改变)和S7(单纯应用现有理论,力图用现有理论解释新现象)。在各自编码完成后,同样交由对方逐一核对,在对其中有异议的6 篇论文(2.4%)进行讨论后最终做出评定。
2 研究进展:研究主题、研究取向及资料/数据来源
2.1 研究主题
如表2 所示,245 篇论文可以按照研究主题分成7 类。从发表论文的数量看,最受关注的主题是“旅游者行为”(83 篇,33.9%)。这一主题的论文主要关注居民风险感知、出游意愿、态度与感知、出行决策以及在目的地的实地旅游行为等。“国家/地区层面”的研究(49篇,20.0%)主要关注新冠疫情在国家/地区层面对旅游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这些影响主要涉及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就业、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客流等的影响。类似地,“目的地层面”的研究(20 篇,8.2%)主要关注新冠疫情在目的地层面(不包括国家尺度的目的地)对旅游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企业/行业层面”的研究(33 篇,13.5%)则涉及新冠疫情对特定旅游企业/行业(例如酒店)的影响、新冠疫情期间的旅游企业/行业管理,以及企业层面的应对策略。

表2 样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分布Tab.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of sample articles
同时,也分别有32篇(13.1%)和16篇(6.5%)论文关注到“旅游发展反思与展望”和“旅游研究/学科/方法”等议题。“旅游发展反思与展望”主题的论文多见诸Tourism Geographies组织的一期专刊——受邀作者就某一个特定话题来讨论新冠疫情的影响,并对某领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展望。最后,还有12篇论文无法归入上述6个主题。它们关注到了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教学、沿海国家健康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舆情传播等。
2.2 研究取向、资料/数据来源
如表3所示,在所有纳入分析的245篇论文中,从研究取向看,定量研究占多数(132篇,53.9%),定性研究、混合研究分别有50 篇(20.4%)、49 篇(20.0%)。另外,还有14篇(5.7%)是概念研究(包括文献综述)。

表3 样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取向Tab.3 Research approaches adopted in the sample articles
相对应的是,从资料/数据获取渠道来看,除有58 篇(23.7%)没有明确告知资料/数据来源外,其余187 篇(76.3%)都明确汇报了资料/数据来源。在这187 篇论文中,有164 篇(87.7%)基于单一资料/数据,其余23 篇(12.3%)运用了多种资料/数据来源(多种定性资料或定量数据,或既包括定性资料也包括定量数据)。
更进一步,如表4所示,在164篇采用单一资料/数据来源的论文中,问卷调查是数据收集的主要渠道和方式(61 篇,37.2%),二手统计数据(55 篇,33.5%)紧随其后;使用访谈和网络文本作为资料/数据来源的论文也分别有17 篇(10.4%)、16 篇(9.8%);采用实验法(包括采用实验设计但使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的论文有11篇(6.7%)。

表4 单一资料/数据来源的论文(164篇)的资料/数据来源Tab.4 Data resources of articles which are based on a single data source(164 papers)
3 学术贡献评价与解释
3.1 基于Colquitt和Zapata-Phelan框架的评价
基于Colquitt和Zapata-Phelan的框架[15],在所有纳入分析的245篇论文中,有141篇(57.6%)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导向/理论问题;104 篇(42.4%)则明确不属于理论研究类型,即并没有提出或回答/回应一个理论性的研究问题。对这141 篇论文的理论贡献的分类和详细阐述(尚无“理论拓展型”论文)见下文。
(1)“报告型”论文。在141 篇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导向的论文中,如表5所示,有74篇(52.5%)属于“报告型”,即在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两个方面得分都很低(在5点评分中得1或2分)。具体而言,在理论建构方面,这类论文尝试检验在以往的理论建构尝试中已经检验过的关系或效应,或者重复以往研究已经证实过的关系/效应;在理论检验方面,这类论文是归纳性的,或者将假设(预测)建立在逻辑臆测上,或者将假设(预测)扎根于对以往研究的简单参考中(所谓的以往文献往往成为“烟雾弹”)[15]。例如有学者[14]利用风险感知理论[15],通过在线问卷调查,研究了新冠疫情发生后消费者购买机票行为的变化。他们将“提前购买机票行为”分为6 类(1 周内、1 周至1 个月、1~3 个月、3 个月以上、无固定模式、不乘坐飞机),并在“过去3~5年”和“未来一旦回归常态”两个情境下,分别统计并比较了受访者的实际购买经历和预期购买行为[16]。虽然作者宣称基于风险感知理论,但实际上并没有在新冠疫情和机票购买情境下发展出相应的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并且,基于风险感知理论的命题,在新冠疫情作为一种公共健康危机事件/风险的情境下,消费者态度必然会做出改变。需要指出的是,在已发表的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报告型”旅游研究中,绝大部分的研究都将以往文献或理论作为“烟雾弹”,并没有从现有理论中实质性地发展出假设,且绝大部分是检验以往研究中已经证实的关系/效应。这类研究固然可以让业界和学界在第一时间了解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验层面的影响,但它们在理论检验和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则是十分有限的。

表5 理论导向型论文(141篇)的理论贡献类型Tab.5 Types of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eory-oriented articles(141 papers)
(2)“理论检验型”论文。在纳入分析的141 篇论文中,有65篇(46.1%)属于“理论检验型”,即在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很小(目的并不在于进行理论的建构;在理论建构的5点评分中得1或2分),但在理论检验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理论检验的5点评分中得4或5分)[15]。这种较强的理论检验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假设/预测深深地扎根于现有理论中[15]。例如Karatepe 等[18]基于资源保护理论[19],研究了作为压力源的新冠疫情对酒店员工行为(上班迟到倾向、旷工行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且以心理健康问题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的感染风险会加剧员工心理健康问题,从而导致上班迟到倾向加剧、缺勤增加,以及较低的生活满意度[16]。资源保护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保存、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19]。因此,不论是潜在的资源损失威胁,还是实际的资源损失,都会引发个体的紧张和压力[19]。相应地,当面临资源耗尽时,个体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将会触发,会表现出一些具有攻击性和非理性的行为[19]。因此,不论是在酒店,还是在其他企业,不论是新冠疫情,还是其他的健康危机事件,或者其他类型的危机事件,都可能引发组织成员的紧张和压力,从而诱发自我保护的机制,产生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因此,类似研究,与其说是理论检验,不如说是理论应用。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中,本文所界定的“理论检验型”论文,大部分实则是理论应用——在新冠疫情作为一种外部扰动、危机的情境下,看待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例如游客、员工、居民、政府部门)的行为及其变化或者有关概念(构念、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3)“理论建构型”论文。仅有1 篇(0.7%)被界定为“理论建构型”,即在理论检验方面的贡献很小(目的并不在于对现有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检验;在理论检验的5 点评分中得1 或2 分),但在理论建构方面却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5]。这种较强的理论建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检验了之前未曾有研究检验过的关系/效应/过程;其二,引入了新的构念,或实质性地重新概念化了现有某个构念[15]。Kock等开发了一个基于进化认识论、基本进化动机和行为生态学的进化旅游范式,并通过“海洋和岛屿模型”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且在新冠疫情如何改变游客心理这一情境下得到了检验[20]。具体实证检验过程是,通过在MTurk 平台招募年满18 岁、家庭收入超过30 000 美元且在过去两年的旅行经历超过70 英里(约等于112.7 千米)的美国人(n=912)参与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并在两项研究中,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新冠疫情(疾病传染性感知)如何改变游客心理(例如仇外心理、拥挤感知、民族中心主义、购买保险意愿、目的地忠诚等)的概念模型[20]。
(4)“合格型”论文。同样遗憾的是,仅有1 篇(0.7%)被界定为“合格型”,即在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两个方面的得分都符合基本要求(在5 点的评分中得2.5 或3.5 分)。一般而言,这种论文在理论建构方面会在原有的关系或效应的模型中,引入新的有意义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在理论检验方面则会将假设(预测)深扎于现有研究结论的概念性冲突、矛盾、争论中,或者深扎于现有理论模型中。Biraglia和Gerrath通过实验研究检视了作为健康危机事件的新冠疫情对访客关于企业赞助的真实性的感知的影响[21]。他们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访客更愿意接受企业对博物馆的赞助;访客对来自中小企业的赞助(相比于来自大企业的赞助)表现出更高的参观意愿和支付意愿,因为他们感知到的真实性损失更低[21]。该研究通过识别两个边界条件(危机显性和赞助商规模),对现有关于公众对企业赞助博物馆的行为的理论解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属于“合格型”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卡方检验(交叉表分析)发现,141篇论文的理论贡献类型在论文类型(研究论文、研究笔记、案例研究、其他(评论、观点、给主编的信等))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earsonc2=14.167;df=9;渐进Sig.(双侧)=0.117)。亦即,纳入分析的141篇论文所做出的理论贡献的类型并不受它们的文章类型影响。类似地,141篇论文的理论贡献类型在研究主题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Pearsonc2=23.240;df=15;渐进Sig.(双侧)=0.079)。
3.2 基于Tribe框架的评价
本文基于Tribe 对旅游领域知识生产和组织的论述[12],提出了一个旨在评价论文的学术贡献的框架(包括理论建构、理论检验、方法创新等),并对纳入分析的245 篇论文的贡献做出评价。在所有245篇论文中,有156 篇(63.7%)被界定为有实质贡献(即在理论建构、理论检验或方法创新方面有所贡献),其余89 篇(36.3%)则被认定为不符合界定标准。与上文分析结果(3.1部分)比较类似的是,如表6 所示,在所有156 篇论文中,属于S6 类(只是验证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对现有框架、概念做出重大改变)的论文近一半,为74篇(47.4%)。上文所提及的Karatepe等[18]的研究就属于此类。

表6 有实质贡献的论文(156篇)的贡献类型Tab.6 Contribution types of articles with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156 papers)
S7 类(单纯应用现有理论,力图用现有理论解释新现象)和S5 类(只是引入/改变某个变量,并未对现有框架、概念做出重大改变)论文紧随其后,分别有45 篇(28.8%)和13 篇(8.3%)。例如在S7 类论文中,Wassler和Talarico应用主客关系理论,通过访谈来收集资料并运用主题分析方法,对疫情防控期间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与形象感知进行了分析,发现新冠疫情使得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感知形象急转直下[22]。
在S5类论文中,El-Said和Aziz[23]的研究是典型的案例。他们基于一系列理论和模型(理性行动理论、技术接受模型、保护动机理论、保护行动决策模型),试图识别和验证人们在危机时期采用虚拟旅行作为临时替代方案的影响因素[23]。结果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和保护行动决策模型中的前因变量(例如,虚拟旅行的有用性、易用性、享乐性,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风险感知,虚拟旅行与风险相关的属性)能够有效预测受访者使用虚拟旅行意向[23]。这一研究虽然整合了技术接受模型和保护行动决策模型,且引入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变量,但并没有对现有的理论框架做出重大改变。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S2类(方法论创新)论文只有11篇(7.1%),S4类(对原有理论框架中的已知变量/变量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论文也只有6 篇(3.8%),而S3类(引入新的视角)和S1类(解决异常复杂的理论/实际问题)论文分别只有4篇(2.6%)和3 篇(1.9%)。例如Zenker 等利用美国和丹麦样本,开发并验证了一份旨在测量旅行者(和非旅行者)个人内部焦虑的量表——大流行(新冠疫情)焦虑旅行量表[24]。这是在旅游者行为领域的心理测量学意义上的重要贡献,属于S2(方法论创新)方面的贡献[12]。上文提及的Kock等[20]的研究则属于S3(引入新的视角)方面的贡献[12]。
同样,通过卡方检验(交叉表分析)发现,156篇论文的实质贡献类型在论文类型(研究论文、研究笔记、案例研究、其他(评论、观点、给主编的信等))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Pearsonc2=26.887;df=18;渐进Sig.(双侧)= 0.081)。亦即,纳入分析的156篇论文所做出的实质贡献类型不受它们的文章类型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这156篇论文的实质贡献类型在研究主题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earsonc2=143.498;df=36;渐进Sig.(双侧)= 0.000)。具体而言,45篇S7类(单纯应用现有理论,力图用现有理论解释新现象)论文较为均衡地分布在“国家/地区层面”(10篇,22.2%)、“目的地层面”(9篇,20.0%)、“企业/行业层面”(9篇,20.0%)和“旅游者行为”(13篇,28.9%)等4个主题中(另外,还有4篇,8.9%关注“其他”主题);在74篇S6类(只是验证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对现有框架、概念做出重大改变)论文和13篇S5 类(只是引入/改变某个变量,并未对现有框架、概念做出重大改变)论文中,“旅游者行为”研究都占主导地位,分别为46 篇(62.2%)、10 篇(76.9%);在6 篇S4 类(“对原有理论框架中的已知变量/变量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论文中,亦是“旅游者行为”研究占主导地位(5 篇,83.3%)。上述结果,一方面固然表明,需求侧视角的“旅游者行为”研究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前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旅游者行为研究在学术贡献上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3.3 可能的影响因素:大学制度、期刊与学者
以上结果表明,虽然目前涌现出了一大批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但它们一方面主要还是致力于应用现有理论来检验所假设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对现有理论框架、概念做出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力图用现有理论解释新冠疫情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旅游现象。因此,这些研究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十分有限。理论知识的生产既具有系统性,也具有网络性[25]。换句话说,在集群理论的视角下,理论知识的整个生产过程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由多个因素相互交织的集群[26]。基于集群理论视角及与旅游知识生产相关的文献,下文将从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的大学制度、期刊和学者3 个关键因素着手,分析、讨论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
(1)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的大学制度。Tribe提出了“知识引力-场域模型”(the knowledge forcefield)[27]。他认为,知识生产从来都是一个权力博弈的过程,受到机构、制度、学者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28]。这里,首先分析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的大学制度对知识生产的影响。20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得知识的经济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也成为全球大学的新常态[29]。换句话说,现在很多大学对教职人员的研究项目的评价制度也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以理论创新为导向逐渐转换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30]。同时,教职人员的科研压力也随之上升。Mountz 等[11]在研究大学制度对学者的发表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当前全球各个大学对论文数量而非质量近乎苛刻的要求以及“非升即走”的职称晋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学者,尤其是对绝大多数女性学者和年轻学者,施加了“权力”[31];甚至,用Falcon 和Philipose 的话来说,施加了一种“学术暴力”[32]。换言之,身陷权力博弈的旋涡,很多学者现在早已难以独善其身——无论是在论文选题、研究取向选择,还是在研究周期的制订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和控制。他们缺乏自由与安全感[7],担心自己的研究课题与主流研究相去甚远,害怕研究周期过长、申请不到基金、论文又被频繁拒稿,因而不能获得终身教职[33]。因此,研究周期短且迎合社会热点的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也就顺势成为“新宠”,在学术界形成一种“快餐文化”。这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纳入本文分析的245 篇论文中,定量研究所占比重超过了50%。学者们用现成的量表、公式可以快速地测算出新冠疫情对旅游业(酒店/接待业)的冲击[34]以及游客动机、旅游行为及其对目的地感知的变化等[35]。更有甚者,可能为了尽量提升论文的产出效率,一些学者选择以篇幅较为简短的研究笔记、短通讯或“给主编的信”等形式快速地发表他们的研究。这一点也反映在Yang等对现有研究的反思中。他们发现,这3类论文在所有样本论文中占据的比例比预期高许多[3]。相比之下,视角新颖、有创造力、理论性强的研究因周期长、出产率低和“经济性”较差等原因,在学术界反而可能颇受冷落,甚至可能逐渐被边缘化。长期来看,这种学术“快餐文化”现象,无论是对理论创新,还是对旅游学科自身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2)期刊。Tribe 和Liburd 认为,期刊在旅游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25]。一方面,期刊(尤 其 是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和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等几家旅游领域的顶级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为学者间的跨地区/跨学科合作、交流,以及共同解决极其复杂的难题提供了可靠的平台[36],进而促进了整个旅游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期刊是微观的权力竞技场,限定甚至规训了学者的研究活动[11]。特别是,期刊主编、编委会成员以及同行评审都充当了“看门人”(gatekeepers)的角色,对知识生产的过程加以引导、干预。他们的品位、想法,甚至学术偏见,往往会左右很多学者对研究主题与取向的选择[37]。换言之,Becher 认为,期刊主编、编委会成员以及同行评审形成了多个“学术部落”(academic tribes),他们握有对论文的“生杀大权”,决定了可以录用哪些主题/类型/研究取向的文章[38]。因此,对绝大多数学者而言,在投稿甚至在进行研究设计之前,选定目标期刊、查看期刊的规定及已录用论文、预估自己所选题目能发表的概率,已成必要之举[9]。而期刊主编组织的专刊、特刊往往能在短期内吸引大量稿件。前文提及的Tourism Geographies组织的“新冠疫情”专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刊的组织鼓励学者对新冠疫情期间或后疫情时代的旅游发展展开反思与展望,即便这些论文实质上可能并没有理论贡献[3]。
(3)学者。理论知识的生产离不开学者的主观意志[29],尤其是他们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知。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 可能影响整个研究的设计[39-40]。本文发现,在有实质性贡献的156篇论文当中,76%的论文要么单纯应用现有理论,力图用现有理论解释新现象,要么只是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对现有框架、概念做出重大贡献(表6)。“报告型”与“理论检验型”两种类型的论文占主导的现象,可能与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26]以及他们对新冠疫情的影响的认知有关。实际上,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新冠疫情这一全球重大公共健康危机事件的影响深远,可能已经改变了旅游业,乃至整个世界的秩序[41]。虽然有学者指出,这种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可能是片面的,即可能已经夸大了疫情所产生的效应[42],但一种相应的观点——学者应该致力于研究、解决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干巴巴地“纸上谈兵”,或建构理论——却就此流传开来。Hage 指出,纯粹的理论研究,既不会扭转局势,也不能“救全球人民于水火之中”[43]。相比之下,专注于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则更切实际,更能体现出学者的社会责任。Hage 的观点看起来虽然有些极端,但很可能却道出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心声(例如下文将提到的部分拥护自我民族志的学者)。毕竟,在全球面临重大灾难之际,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应,收获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国际旅游学界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时所表现出的“及时性”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正面评价[44]。疫情期间,随着世界各国(地区)政府制定社交距离倡议、限制行动、进行封锁,许多国家(地区)的游客数量直线下降,旅游业遭受“灭顶之灾”。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评估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自然就成了许多学者的选择。例如Dube 等[45]调查了新冠疫情对全球餐饮业的影响,发现新冠疫情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因此,他们建议对餐饮业采取非常规的财政和其他支持措施来减轻新冠疫情的影响。Rasoolimanesh等[46]的研究发现,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以及疫情之后的出游意愿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例如信任、社会隔离、医疗系统以及风险管理)。相比之下,游客的经验在形象感知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上述研究都是典型的解决实际问题之作,虽然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可能十分有限,但的确可能有助于旅游行业解决燃眉之急。
当然,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知或许还受到研究者所处学科的规则、研究范式与知识框架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哪些社会现象最值得关注,而其他则是应该被忽略、摒弃的。这一点在其他很多研究中已有详细讨论[36],本文不再赘述。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对截至2021年8月31日发表于10本SSCI旅游期刊且与新冠疫情相关的245 篇论文展开分析,有如下基本发现:(1)从研究主题来看,新冠疫情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旅游者行为),新冠疫情在国家/地区层面、目的地层面及企业/行业层面对旅游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是较受关注的领域。相比之下,较少有论文反思和讨论旅游研究、旅游学科以及研究方法与范式在这场影响深远的全球危机中何去何从。(2)从研究取向来看,定量研究占主导。与之相对应的是,问卷调查是数据收集的主要渠道和方式。这与当下国际旅游研究的基本趋势一致[47-48]。(3)与其他关于新冠疫情与旅游研究的综述论文[2-7]不同的是,本文系统地评价了这一领域论文的理论贡献。本文发现,在纳入分析的245 篇论文中,具有重大理论贡献的论文寥寥无几。具体而言,据Colquitt 和Zapata-Phelan 两位学者所建立的旨在评价论文的理论贡献的框架[15],本文发现,虽然超过一半的论文有较明确的理论导向,但绝大多数(98.6%)属于“报告型”或“理论检验型”,在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十分有限。只有各1篇论文分别属于“理论建构型”与“合格型”,在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另外,据Tribe提出的评价体系[12],本文发现,在纳入分析的245 篇论文中,有156篇(63.7%)被界定为有实质性贡献。然而,只有24 篇论文(15.4%)分别属于S1、S2、S3 或S4 类,即具有较大的理论贡献。其他的132 篇(84.6%)的理论贡献相对较弱,亦即它们要么单纯应用现有理论,力图用现有理论解释新现象,要么只是对原有理论做出较小范围的改动。
4.2 讨论
知识生产从来都是一个权力博弈过程,受到机构、制度和学者等人与非人因素的影响[28]。本文认为,期刊、学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的大学制度这3个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游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纳入分析的论文的理论贡献。特别是,期刊与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的大学制度这两个因素都在论文选题、研究取向选择,以及研究周期的制订方面,对学者进行了引导、规训和控制。除了这两个非人因素外,学者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新冠疫情影响的感知与判断,也使得一些学者采用了较为“急功近利”的方式来展开研究,专注于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而非理论贡献。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研究是否需要有理论贡献或创新,或者需要哪种类型的理论贡献或创新,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迄今仍饱受争议[49],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部分拥护自我民族志的西方学者(例如Ellis和Bochner[50])早已提出,理论的本质是对世界的驯化与抽象化,比起执着于提出新的理论或有理论创新,关心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并试图舒缓甚至解除他们的疾苦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创新早已构成了科学研究的重要传统,可以将科学与艺术、文学等其他同样可以产生社会效益的领域区分开来[51]。换句话说,没有源源不断的理论知识的话,科学的独立性与客观性都将受到挑战(实际上,自我民族志因其弱化研究的理论贡献一直以来都饱受质疑[52])。当然,旅游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25],也不例外。
虽然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时期着手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显得尤为注重要,但长远来看,理论创新才是旅游研究,甚至整个旅游学科的长足发展之道[9]。事实上,从Scott Cohen 与Erik Cohen 两位学者长期观察的结果来看,虽然近年来社会学的一些较为成熟的概念(例如原真性、游客凝视、行动者网络理论、流动性/移动性)频繁用于旅游研究[10],但遗憾的是,旅游研究迄今未能反哺母学科,即并未对这些“舶来”概念的理论建构与补充做出实质性的贡献[8]。因此,比起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旅游研究仍处于弱势地位,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话语权还有待提升。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大学与旅游期刊(尤其是国内大学和旅游期刊)而言,应充分发挥制度、规则和平台等的作用,适当抑制旅游研究中的“快餐文化”;或者,应该推广一种更重视研究原创性的“慢学术”文化(slow scholarship)[11],以减轻学者们的科研压力,让他们更有动力和耐心从事周期长、出产率低、“经济性”虽较差但视角新颖、有创造力且理论性强的旅游研究。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也应以更长远的眼光,注重梳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能够采用新颖的视角与方法,客观地研究新冠疫情与旅游发展之间多重复杂的关系,并致力于通过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旅游研究来促进旅游领域的理论发展和知识积累。
4.3 研究局限与后续研究展望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出于样本代表性和取样便利性的考虑,仅对10 本旅游类英文SSCI 期刊进行文献检索,纳入分析的论文的发表日期截至2021年8 月31 日,在样本选择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的研究亦可以针对某个特定主题,对论文的学术贡献展开更加细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