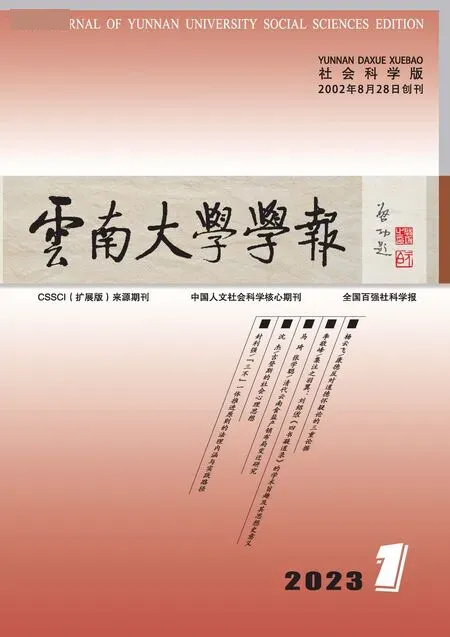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敬峰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10119]
乾嘉时期,是汉学日炽、宋学渐微的时代,依然能够以宋学自居,挺立朱子学的可谓凤毛麟角。而这其中,刘绍攽无疑是颇具典范意义的学者。刘绍攽(1707—1778),字继贡,亦字九畹,陕西三原县人,与杨鸾、吴镇和胡釴并称为“关中四杰”。绍攽“自束发受书,即知古圣贤非异人。任于六经、诸史、天官地理、礼乐兵农,宋、元、明诸大儒之书,无不熟读而切究之”(1)刘绍攽:《卫道编》,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1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早年拜师陕西督学王信芳,而王信芳乃清初庙堂理学的代表李光地的高足,他恪守光地为学宗本朱子的学术旨趣,亦以羽翼朱子学为务。受其师王信芳的影响,刘绍攽“其学以朱子为宗”(2)钱仪吉:《清代传记丛刊》第113综录类(3)碑集传(08),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123-139页。,“潜心集注”(3)白遇道著,白金刚等点校:《重刻〈四书凝道录〉序》,《白遇道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成为清代中期卫道朱子的典范人物。绍攽所著《四书凝道录》完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共计十九卷,篇幅巨大,卷帙丰富,在体例上先录四书原文,再录朱子注解,或随文注解,或广引群说,或施加按语,可视为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再诠释。绍攽自述是书创作缘由道:
(朱子)生平所尤致力于者莫如《四书集注》,训诂本之汉唐,义理一宗二程,复参稽于游扬吕谢及诸老……是书之广大精微,诚非一蹴可跂,不敏少从王信芳先师,窃闻大义,壮岁驰驱,与当世有识之士游,遍考诸家之论说,恍然若有所见,辄就是书指实言之,颇有乖于引而不发之义。(4)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自序,《四书凝道录》,光绪二十年泾阳刘文在党刊本,第1页。
绍攽高度肯定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析理之粹、补备之精、释诂之准,但是书并非没有缺点,多有引而不发之处,使晚生后学难以问津是书大义。故而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这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从反面的视角而言,绍攽指出:
是世之读是书(《四书章句集注》)者流弊有三:一则帖括之习,不能尽众论不同之极致;一则糟粕六经,指讲说为支离;一则是汉非宋,援旧章以滋议。自非学有本原,鲜不为其所惑。(5)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自序,《四书凝道录》,第3页。
在刘绍攽看来,乾隆时期学界研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呈现出三种流弊,一是为应对科举考试,只是口诵四书集注;二是蔑视经注,指责朱注为支离;三是崇汉抑宋,拿旧说来妄议朱注。这三种流弊严重误导学者对朱注的理解和信从,削弱朱注的权威,故而必须矫正时弊,重新梳理、推明朱注。更为忧心的是,即使那些尊奉集注的学者亦陷入到“尊朱者,守其一说,不知兼综众说”(6)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第10册)卷206,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37页。的窠臼。正是这些原因,迫使以道自担的刘绍攽倾力著述《四书凝道录》,以期抉发朱注本旨,重塑朱子学的权威。绍攽对是书颇为自信,自认其书“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精粗得失”(7)刘绍攽:《答邱省斋论〈易〉书》,《九畹续集》卷一,乾隆间刘传经堂藏版,第45页。,同时,学人亦借“昔人谓有天地不可无四书,有四书不可无《集注》,有《集注》不可无是编”(8)据载:“因出向所为《四书凝道录》三十卷,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精粗得失,附以西河而审辨焉。杨公见之,握余手曰:“昔人谓有天地不可无四书,有四书不可无《集注》,有《集注》不可无是编。”(刘绍攽:《答邱省斋论〈易〉书》,载《九畹续集》卷一,第45页)来高赞其羽翼、发明朱注之功。而后的白遇道亦有类似判断:
广采诸家之说,节解支分,梳栉而证明之,名之曰“凝道录”,如经之有传,注之有疏,总靳有合于阐明圣道之旨,则亦集注之羽翼,吾道之捍卫矣。(9)白遇道著,白金刚等点校:《重刻〈四书凝道录〉序》,《白遇道集》,第21页。
白遇道不唯以更加明确的“集注之羽翼,吾道之捍卫”来定位《四书凝道录》,更以“广采诸家之说,节解支分,梳栉而证明”来详细描述是书之特质,这就精准而详细地将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贡献提揭出来。下面就深入文本当中,一一提揭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以期由此具体而鲜活的个案窥探清代中期朱子学的学术面貌和演进趋势。
一、推阐朱注
在“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10)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9-250页。的清代中期,朱子学的地位已与清初的独尊之姿难以相提并论,呈现渐趋式微之势。刘绍攽对此深表担忧,以高标清廷的尊朱政策来重倡朱子学:
我朝际五百年之运,极治教之隆,进朱子于十哲,纂《全书》以颁行,所以推崇之者至矣。(11)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自序,《四书凝道录》,第4页。
这是绍攽对清廷国是的高度概括,准确道出清廷尊奉朱子学的文化策略。他将这种国是应用和贯彻到对朱注的诠释当中,反复申明“集注确不可易”(12)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四,第29页。。具体而言,刘绍攽主要遵循“义有未显者,为之证明;解有未备者,为之补充”的原则,来彰显这一学术情怀。首先是以朱证朱。刘绍攽在诠释《集注》时,大量引用《朱子语类》中的原文来对集注中的话进行再解释,以求义理详备。如在解释朱子《大学章句》的注文“安谓所处而安”时,绍攽直接以《朱子语类》卷十四中的“朱子曰‘安只是无臲卼之意’”(13)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大学》,第3页。下注,来对“安”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以求用“不纷扰”这种更为简单化、口语化的方式推明朱子的意思。如在解释《中庸章句》的注文“愚谓以三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时,绍攽同样引用《朱子语类》卷三的“问:‘鬼神便只是此气否?’曰:‘又是这气里面神灵相似’”(14)刘绍攽:《四书凝道录·中庸》,第25页。进行注解。如此事例,在其书中不胜枚举,显示出刘绍攽借朱子之言来推阐集注的用心。当然,刘绍攽亦非随意、盲目采用《朱子语类》,而是经过慎重考量和选择,择取与集注当中意思最为切合的条目进行解释。其次,标明朱注。绍攽在是书中,将朱子自己所加的按语皆注明出处,使研习之人能够知其来源,明其出处。我们同样举例来说明这一取向,如在《四书凝道录·孟子》中,刘绍攽将朱子注中取自汉代赵岐《孟子注疏》中的主张,但并未标明出处的地方全部下“赵注”说明其出处,达百余处,如在朱注“深墨,甚黑色也”,标明“赵注”,(15)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5页。在朱注“载,亦始也”,标明“赵注”,(16)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45页。在朱注“盈之,亦宋之大夫也”,标明“赵注”,(17)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51页。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绍攽标明“赵注”的地方,既有名物制度,亦有义理论说,这实际上是将朱注推向更加明确和清晰的境地。当然,标明出处的地方并不限于赵岐的注解,还涉及“本郑注”(郑玄),如在朱注“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标注“本郑注”,(18)刘绍攽:《四书凝道录·中庸》,第51页。在朱注“大甲商书顾谓常目在之也”,标注“此古注语”,(19)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大学》,第8页。在朱注“或曰审也”,标注“此广韵注”,(20)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大学》,第8页。在朱注“盘沐浴之盘也”,标注“本孔注”(孔颖达),在朱注“蔽,遮掩也”,标注“本邢疏”(邢昺),(21)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九,第8页。在朱注“礼,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标注“见《曲礼》”,在朱注“小则吮痈”,标注“见《汉书》”,(22)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九,第12页。在朱注“舔痔”,标注“见《庄子》”(23)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九,第12页。等,仅从这些事例中可见绍攽标注之广、之细。最后,演绎朱注。绍攽认为朱注多有简略含糊之处,因此,需要进行更为清晰的解释。如在朱注“欲世子笃信力行以师圣贤,不当复求他说也”,刘绍攽解释道:“注中笃信力行是要立志以端其始”,(24)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13页。在此,刘绍攽重点以“立志以端其始”来为笃信力行作注解,明确了“笃信力行”的下手和落脚处。在解释朱注“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时,刘绍攽指出:
《注》意将戒惧自励处说起,如有所感触而惧,自此而收敛之以至于未发时一无偏倚,而工夫不间断则极其中矣。(25)刘绍攽:《四书凝道录·中庸》,第7页。
在此,刘绍攽对朱子所谓的如何达到“极其中”进行了详细地阐释,认为须从戒惧工夫做起,在有感而生戒惧之时,收敛内心,做到未发时的无所偏倚,如此便可达到“极其中”的境地。在解释朱注“口腹虽所当养,而终不可以小害大,贱害贵也”时说:
《注》意谓非恶夫小体之养也,恶其养小而有以害大也。是反言以决养小者之必有失。(26)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六,第29页。
在绍攽看来,朱子的意思并非要人舍弃口腹之养,而是不能以满足口腹之养妨碍心性的修养,这是朱子正话反说,意在表明满足口腹这类的事情,必然会有所失。绍攽的解读与朱子之意如出一辙,只不过更加简明易解。在解释朱注“当道谓事合于理,志仁谓心在于仁”时,绍攽说:
事合于理,所谓遵先王之法;志在于仁,所谓格君心之非是也。合之则一,分之则二,此处孟子分言,故《集注》分释之。(27)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六,第54页。
刘绍攽对朱注进行了拓展性的解释,朱子只是提出“事合于理”,绍攽则给出解释,认为“遵先王之法”就是“事合于理”;提出“志在于仁”,绍攽认为“格君心之非”就是“志在于仁”。两者合在一起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分开就是两层意思,而朱子显然是袭取孟子分而言之的主张。绍攽的解释是否属于诠释过度仍可再论,但将朱子之意提揭明白确是不容否定。由上分析可见,绍攽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绝非只是简单地绍述,更多的是充实和抉发朱注的内在义理,使其更加简明和完备。
二、折中百家
“广采诸家之说”(28)白遇道著,白金刚等点校:《重刻〈四书凝道录〉序》,《白遇道集》,第21页。是刘绍攽《四书凝道录》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征引诸家解说,共计923条。而汉、魏、梁、唐四代学者的记说,一共只引了75条(汉60条,魏4条,梁1条,唐10条);其余848条皆为宋儒之说。而在这848条中,二程夫子之说计为304条”。(29)陈铁凡:《〈四书章句集注〉考源》,载《论孟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39-67页。而刘绍攽在《四书凝道录》中征引诸说则达6558次,其中,引古注280次,引朱子357次,引程子333次,引陆陇其265次,引李光地164次,引张载50次,引王信芳44次,引徐世沐42次,引薛瑄37次,引饶鲁、高攀龙、王应麟各17次,引李二曲14次,引蔡清《四书蒙引》323次,引朱熹《四书或问》146次,引《史记》67次等。(30)浩小艳:《刘绍攽〈四书凝道录〉之审美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由此可见,刘绍攽引证之多而广,已非朱子所能企及。这一方面当然与刘绍攽为后出学者,与朱子相差600余年,有足够的史料可供其选取有直接关系,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刘绍攽“集思以广益,历选儒先之说”(31)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自序,第4页。的治经取向。当然,“广引”只是刘绍攽治经的手段,他绝非只是将这些材料进行文字堆积,而是对诸家之说进行裁断和取舍,以期平衡诸家,择优选用。根据刘绍攽的自述,在折中百家的过程中,既有取舍,亦有综合。首先,就取舍来讲,在对朱注“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的解释时说:
《春秋》道名分,故《集注》以父祖释之,旧说正百事之名,《大全》、吴氏、饶氏因之,已与卫事不切,毛西河至以为名法之名,更失之矣。(32)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七,第3页。
注中所涉及的典故是卫国后庄公蒯聩与出公辄父子二人争夺王位导致的名实混乱之事。绍攽认为旧说、《四书大全》、吴棫、饶鲁皆不顾卫国事实,将“正名”解释为“正百事之名”,与事实相悖。而毛奇龄解释为“名法之名”更是离奇。绍攽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对正名的解释,唯有朱子依据卫国事实将其限定在人伦一域,这就遵循了经典诠释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朱注“三年之丧”的解释中,他说:
当时古礼不行,老氏之教渐渐流传,如原壤母死而歌,宰我目击时弊,疑而问之,后世遂为口实,独不思三年之丧,至今不废者,宰我一问之力也。《蒙引》疑《集注》引尹氏短丧一段,替宰我回护者,误也。(33)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九,第18页。
在绍攽看来,古礼不行于世,老庄之学流传渐广,出现母死而歌的现象,幸宰我有心关注,致使三年之丧不废。但蔡清则质疑朱子引用尹焞之说是替宰我辩护,这是错误的。由此可见绍攽一尊朱注之意。再如,对“回也不改其乐”朱注的解读中,绍攽说:
袁了凡谓“人都说孔子称颜子安贫”,愚谓实取颜子之精进,盖语之不惰,无所不悦,乃所以乐之根也。(34)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三,第35页。
这里,绍攽显然是不赞同袁了凡所认为的孔子称赞颜回只是取颜回的“安贫”境界,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小看了颜回。绍攽认为孔子看重颜回,是取其“精进”之精神。绍攽之说显然优于袁了凡之意,更进一步将颜回之乐的根源揭示出来。
由上述例子可见,刘绍攽完全是以朱子学为据对他注进行反驳和裁断。
就综合的角度而言,在对《论语》“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朱注进行解读时,刘绍攽指出:
讲家多谓夫子以不可移言,程注以不肯移言,似有不合朱子谓人性本善,虽至恶之人一日而能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然则不可移者,只是不肯移耳。只有学便可移,然其肯学亦是其气质好处,语似异而理则同也。(35)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九,第3页。
这段注文是关于“不可移”与“不肯移”的争论。绍攽则认为两者是相通的,因为“不可移”就是“不肯移”,只要肯学便是可移的,所以,程颐的注解与朱子是没有矛盾的。这就透露出刘绍攽折中融合他注之意。在阐释朱注“格物”时,绍攽指出:
程子谓“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譬如登山要亲到此山,方知此山景物”,吕东莱释天寿平格之格为通彻无间,深得至也之意。郑注训来亦本祖考来格。……吕与叔必穷万物之理同出于一为格物。谢上蔡以求是为穷理,杨龟山以天下之物不可胜穷,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胡五峰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胡文定以物物致察宛转归己,则皆与程朱不异。(36)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大学》,第5页。
晚明刘宗周曾指出:“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37)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大学杂言》,《刘宗周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57页。这就道出“格物”问题的复杂性。绍攽则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说进行综合研判,他认为朱子之说祖述程颐自不用说,而吕祖谦的“通彻无间”也是“至”的意思,郑玄训“来”亦与程朱之意不相违碍,其他如吕大临、谢良佐、杨时、胡宏、胡安国等的注解皆与程朱语异而理同。平实而论,诸家解说之间并非与程朱是高度趋同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绍攽之所以将其归并为一恰恰是其卫道程朱学术取向的直接反映。再如对《大学》今、古本进行争论时,刘绍攽指出:
愚按近儒多讲古本《大学》,谓不必分传分经,亦不必补传,曾细考之,古本原自可通,其有错简与否未可知也。朱子改本与二程不同,其果合于古亦未可知也。但其所言之要则与孔门一脉相承,故今从之。(38)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大学》,第8页。
二程首开《大学》文本改动之举,朱子仍之,不仅将《大学》划分为一经十传,更补《大学》“格物传”,视为“今本《大学》”,且赖朝廷功令的夹持,成为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的经典文本。后阳明为挑战朱子义理系统,否定朱子的《大学》改本,改尊古本《大学》,从而在学术史上形成一个聚讼不断的学术公案。绍攽从文献和思想两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回应。在文献方面,绍攽对今本还是古本给予存疑的态度,认为两说皆无据可证。但从义理的角度来说,程朱的今本《大学》则与孔子的意思相近,故他选择遵从程朱的改本。绍攽的这种取向与那种简单地否定古本,显得更具说服力。因为改本更能为扩大理学思潮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完善的哲学教本。(39)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三、批判阳明
刘绍攽所处的乾隆时期,阳明心学已处在极度衰弱的境地,已经很难对官方哲学朱子学构成威胁。但这并不是说心学就毫无声音,它依然有支持者和拥护者。从统治者角度来看,整个清代,始终未取缔阳明从祀孔庙的政治礼遇,不唯如此,乾隆于1751年南巡期间,专谒阳明祠,后在1784年再度南巡期间,诏令修葺阳明祠,并御赐“名世真才”匾额。上层态度的松动,为阳明心学留下一线生机。从士大夫角度来看,早在乾隆初年,李绂(1675—1750)就刊刻《陆子学谱》,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刘原道刊刻《阳明先生年谱》等。这种情形很容易导致心学再度复燃。因此,此时批判阳明心学仍有它的必要性。刘绍攽在《四书凝道录》中有意识地对阳明心学进行批判,以期卫道程朱。下面我们试举几例,来一展刘绍攽的这一学术特质。首先,就学界批判最为集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来讲,绍攽指出: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即是此意,告子虽小变前说,然不悟水性而须决己与杞柳戕贼者相类,而不得为顺其自然矣。(40)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六,第2页。
不同于顾宪成等认为阳明“无善无恶”相异于告子“无善无恶”的论断,刘绍攽显然是因袭了清初朱子学者熊赐履的“晦翁以象山为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为明之告子”(41)熊赐履著,徐公喜、郭翠丽点校:《异学·告子》,《学统》卷四十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51页。的主张,同样将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告子“无善无恶”说相等同。这实际上是对阳明之意的误读,因为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所要讨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伦理学上的善恶问题,而是指良知作为情绪主体具有虚、无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良知不会使自己“着”在哪一事物上,而使之成为良知流行无滞的障碍。(42)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
其次,刘绍攽亦着重批判阳明的“格物”思想,因为这是朱子、阳明争论的核心焦点,决定着两者的工夫路向。刘绍攽对此回应道:
按格物之说不一,涑水谓扞御外物,象山云格去物欲,姚江云去其不正以归于正,皆与致知二字不洽,近儒多从王心斋格其物有本末之物,王丰川因以物即指身心意知,谢梅庄以物即指身与家国天下,总缘致疑物无尽,格亦无尽,殊不知程朱非教人玩物丧志也。(43)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大学》,第5页。
明德在己,新民在人,人己相形故曰物。此物字即物格之物,但此以物之大纲言。格物乃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王心斋牵合为一则有一本而无万殊矣。(44)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大学》,第4页。
从前述可知,刘绍攽在“格物”的理解上悉遵朱子,以此为基准,他首先批判心学一系的王艮、王心敬对“物”的理解,他认为他们对“物”的理解过于狭窄,仅仅指向“身心意知”,这与朱子的“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45)朱熹著,朱杰人等编:《大学或问》,载《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7-528页。之意相比,明显偏于内在。尤其是王艮将“物”视为一,与朱子所讲的“物”主要是千差万别之物相违背,出现只有“一本”之理,而无“万殊”之理的情形,殊不知朱子的“格物”正是“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46)朱熹著,金良年译:《四书章句集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页。强调的是下学上达,教不躐等。绍攽进而批评象山、阳明所解释的“格物”之意难与后面的“致知”形成理论自洽,他们说的“格物”皆是意识领域内的事,与“致知”主要指向“知识之知”的意义(47)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88页。不相融合。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三大命题之一,在其学术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刘绍攽对此评价到:
当时以仁义为外烁,故为指出固有之良,欲人察识而扩充之,非谓可废学也。且孟子以知能并举,推本仁义,《象山语录》偶云“生知”,盖谓有生以来浑无陷溺,无伤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尔,殊也。阳明遂拈良知二字以为宗风,却不言始于象山。(48)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七,第16页。
刘绍攽批评阳明的角度与他人不同,他主要从“良知”的思想渊源上切入,认为在孟子之时,多以仁义为外在,孟子为矫正时弊,指出此乃是不依赖于任何条件而先天就拥有的,具有“直觉性”和“当下即是性”。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学”,恰恰是需要通过“学”来察识和扩充。后陆九渊接续和发挥孟子这一认识,指出这是人有生以来即存在的,除强调它的先验性,更指出它的普遍性。再后来,阳明标揭“良知”以为学术宗旨,但却忽视了陆九渊在此问题上的创发地位。刘绍攽对阳明的这种评价过于夸大了陆九渊对“良知”的提揭之功。换而言之,陆九渊对“良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和阐释,将阳明此论追溯到陆九渊,与事实并不相符合。
我们再来看一下刘绍攽对阳明在卫国一事上态度的评判,他说:
阳明谓“令子迎其父,父让其子,辄仍得国,养父于宫,如后世太上皇之类”,此世俗之见。圣人绝不为此以夷齐太伯之事观之,圣人唯有感发其天良,让聩而去,聩亦不可立也。(49)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七,第5页。
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这段引文的历史背景。卫国太子蒯聩与卫灵公夫人南子交恶,欲谋杀南子,计划泄露,出逃宋国、晋国。灵公四十二年,欲立少子郢为国君,少子郢推辞不受,遂立蒯聩之子辄为国君,即卫出公。后蒯聩返归卫国,就任国君,即卫后庄公,而卫出公则出逃至鲁国。就这段事实,阳明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出公把其父后庄公迎接回来,奉为太上皇,而作为父亲的后庄公应该让位于出公,让其继续执掌国政。这在绍攽看来乃是世俗之见,与圣人之说不类。因为在圣人看来,后庄公欲杀母,得罪其父灵公,出公拒接其父,父子二人皆是无父之人,都没有资格就任国君。若就之乃是背弃人伦,名不正言不顺,正确的做法应该仍然让少子郢即位,方得人伦之正。可见,阳明的主张是更为务实的做法,绍攽的主张是就应然层面而讲,以期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两者角度不一,差异自然难以消弥。要之,绍攽的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将阳明从圣人之列中剔除出去。
由上述分析可见,刘绍攽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基本是围绕学界争议已久的问题展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超越前贤,但他在阳明心学有复燃迹象之时,积极介入进去,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
四、不废训诂
在清代,乾嘉汉学更多的只是江南一域的学术现象,并不具有全国性的意义。(50)艾尔曼著:《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页。进一步来讲,关学自张载创立以来,一直沿袭和尊奉张载所开创和奠定的“心解”之法,根本不重视训诂在经典诠释中的作用。而刘绍攽则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关学这一传统,在注释四书时,沿袭的恰恰是朱子注释四书的方法,他明确指出:“读书要字字挑剔……无穷道理俱在里面”,(51)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六,第12页。强调文字训诂在诠释经典、阐发义理方面的重要性。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于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5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5页。的境遇下,他在《四书凝道录》中,凡名物制度、草木鸟兽、山川湖海无不引经据典,加以翔实考证,以期为义理阐释的正确性提供最为基础的保障。我们试举几例,一观其详。首先,刘绍攽详细考证朱子集注当中所引用的人物。我们知道,朱子引用他注只是标为“某氏曰”,没有直接点出人名。刘绍攽认为这样容易为研习者留下不明就里的隐患,必须一一点出,使后学者知其出处和渊源,加深对四书的理解:
例1:如对“刘聘君”,绍攽指出:“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53)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四,第12页。
例2:如对“孔氏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中的“孔氏”,绍攽解释到:“名文仲,字经文,临江人。”(54)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一,第16页。
例3:如对“赵氏曰:‘八口之家’”中的赵氏,绍攽解释到:“名岐,东汉常陵人。”(55)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一,第32页。
例4:如对“丰氏曰:‘因民之恶’”中的“丰氏”解释到:“名稷,字相之,四明人。”(56)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七,第12页。
例5:如对“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中的“胡氏”解释到:“名安国,字康侯,建安人。”(57)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54页。
其次,绍攽亦对地名、山川进行详细考证:
例1:在对叶公的考证上,绍攽指出:“叶,楚县名,故城距今南阳府叶县治二十里,中有沈诸梁祠。”(58)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四,第15页。
例2:在对魏国都城大梁考证时指出:“魏故都安邑,惠王时,秦屡败魏,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59)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一,第1页。这就非常贴合事实,交代了魏国都城变化的历史和缘由。
例3:在对“雪宫”的解释上,绍攽指出:“元《和郡县图志》:雪宫,故址在青州临淄县,即齐故都东北六里。”(60)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一,第41页。
例4:在对“岐山”的解释上,绍攽说:“雍录,岐在今凤翔府东五十里。”(61)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一,第48页。
例5:在对“九河”的考证上,绍攽指出:“九河之名,本之《尔雅》,汉唐叙传亦然。”(62)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23页。
最后,再来看一下绍攽对制度的考证:
例1:在对“三十年为一世”的考证上,绍攽说:“邵子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三十年则有十二万九千六百辰,故至此更变其云甲子,甲午为世首者,六十年一甲子,中间三十年而一甲午也。”(63)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七,第10页。
例2:在对“居南宫”的解释上,绍攽借用阎若璩的考证来为自己的观点佐证,指出:“阎百诗曰:‘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故《仪礼》言‘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世之氏某宫者以此。’”(64)刘绍攽:《四书凝道录·论语》卷三,第11页。
例3:在对“分田制禄之常法”的解释上,绍攽指出:“居民制田以四八为法,如八家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是也。”(65)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14页。
例4:在对“枉尺而直寻”的解释上,绍攽借用他注说道:“周制十寸八寸皆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是,故十尺曰丈。”(66)刘绍攽:《四书凝道录·孟子》卷三,第34页。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绍攽考证得非常详细和精确,每下一字必有考究,择其精良者以为注文,使得朱注更加清晰和明确。绍攽的这一取向既是对朱子学不废训诂的承继,亦是乾嘉汉学风波的体现。但总体来讲,刘绍攽是“汉宋兼采”,但属于立足宋学而兼采汉学,而非立足汉学去兼采宋学,故应该在“宋学家而通训诂者”的角度来看待刘绍攽的“不废训诂”之举。
小 结
朱子一生精力尽力于四书,而刘绍攽一生则尽力于《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清代中叶朱子学式微之下为数不多的羽翼朱注之作,刘绍攽的《四书凝道录》深以师祖李光地的“名为尊程朱,何尝有丝毫发明”(67)李光地:《榕村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85页。为戒,尊朱而不述朱,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汉学兴盛的乾嘉时期,刘绍攽依然以尊奉程朱理学为务,并未随波逐流,彻底卷入到汉学的洪流之中,成为卫道宋学但不废汉学的标杆人物之一,延缓了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从关学角度而言,刘绍攽的《四书凝道录》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关学并非铁板一块不重训诂,它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从四书学史的角度而言,刘绍攽的注解是对朱注的推阐和演绎,较之其他同类注解,绍攽的注解引证之广,考证之精,推阐之细,皆是难得一见的,呼应和助推了清代中期四书学发展的新动向——义理阐释的纯粹、考证方法的精密,以及内容的切实,(68)周国林、涂耀威:《“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5期。进一步佐证了王国维“乾嘉汉学精”(69)王国维:《王国维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3页。判断的准确性。
——《四书释注》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