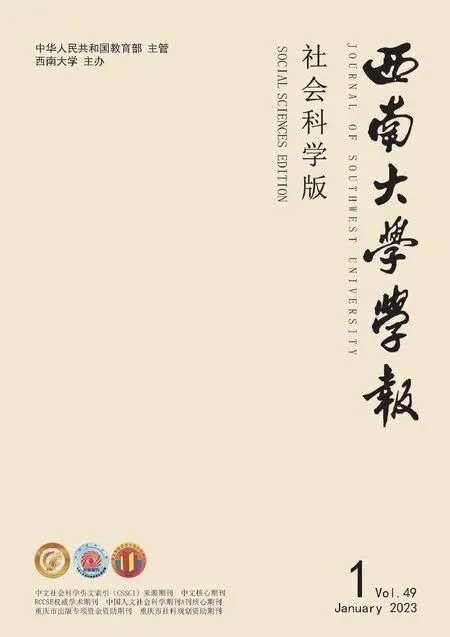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多族群融合及身份认同
董 晓 佳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拜占庭帝国脱胎于罗马帝国,因此早期拜占庭帝国(1)早期拜占庭帝国也就是指拜占庭帝国早期发展阶段。著名拜占庭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早期阶段的拜占庭帝国实际上仍然是罗马帝国,其全部生活都充满着罗马元素。这一时期确实应当既可以被称为晚期罗马也可以被称为早期拜占庭。”(George 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anslated by Joan Hussey,Oxford:Basil Blackwell,1956,p. 27.)。国内外拜占庭研究者大多将公元4至6世纪视为拜占庭帝国历史的早期阶段。的发展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晚期罗马帝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后继者,因此拜占庭帝国居民始终自称为“罗马人”;而后世拜占庭学者则往往称其为“拜占庭人”。由此,“拜占庭人”的形成及其内涵也就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埃夫里尔·卡梅伦认为,拜占庭人并不是任何民族意义上的“人民”,拜占庭帝国并非由一个民族群体发展而来,也不是崛起于某个具有特定民族背景的人口所占据的一个地区,其特征是发展自之前数世纪以来的历史与开拓定居,同时拜占庭帝国的特征也是对之前这多个世纪的历史与开拓定居的回应[1]8。徐家玲教授指出,晚期罗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文化共同体,而实现基督教统一世界的概念,长期以来都是拜占庭人念念不忘的目标[2]171。有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的两根支柱正是罗马帝国的遗产与正统基督教的信仰[3]3。陈志强教授认为,在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居民成为社会主要成分,其主要人口构成是讲希腊语的“东方人”,这一时期官方文献虽然继续使用拉丁语,但希腊语是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语言”,不仅在民间流行,并且很快成为官方语言,并最终取代了拉丁语的正统地位;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廷帝国”(2)“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廷帝国”两个名称均为国内学者所使用,且同一学者在不同论著中可能采用不同的名称。本文采用“拜占庭”这一中文名称,在涉及到不同名称的使用时,以直接引用的方式注明,下同。
一、新到族群融入帝国经济与军事生活
早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着蛮族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这一压力继承自罗马帝国时期。至3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国所经受的周边民族压力日增。4世纪后期,纷至沓来的日耳曼人(the Germans)、匈人(the Huns)、阿兰人(the Alans)等群体相继出现于多瑙河(the Danube)北部地区,并导致这种军事压力达到高峰,从而成为早期拜占庭帝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正是在帝国政府的应对过程中,拜占庭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多族群融合共存的局面,同时共同的身份认同也在逐渐形成。随着各种蛮族群体不断通过边疆地区以战争或和平的方式进入拜占庭帝国,在早期拜占庭帝国出现了新到蛮族与帝国当地居民共同生活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定居于帝国内部的各个族群逐渐融入帝国的社会生活,同时新来者对帝国的身份认同也在逐渐形成。
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帝国政府同意来自于边疆之外的人群定居于帝国境内的原因,除了希望通过这种在帝国控制之下的和平定居,可以减轻蛮族对边疆安全所构成的压力以及为帝国军队补充军力之外,新到族群作为劳动力可以为帝国经济和财政提供的贡献也是考量之一。拜占庭帝国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就曾大规模在帝国边境地区安置大批蛮族,利用其人力开垦荒地[5]10。376年,当瓦伦斯允许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时,不仅命令当地官员给予哥特人他们所需的食物,而且要求为哥特人分配用于将来耕种的土地[6]105。显然,当瓦伦斯同意哥特人进入帝国境内时,也在期望哥特人在将来可以成为帝国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补充。亚得里亚堡之役后,接替瓦伦斯皇位的塞奥多西一世于382年设法与哥特人缔结和约[7]152。根据382年和约,哥特人被授予在色雷斯、马其顿尼亚等地的土地上耕种的权力,耕种土地的哥特人需要向帝国缴纳赋税[8]158-159。
拜占庭帝国政府接纳部分蛮族群体定居于帝国的目的之一是招募蛮族进入军队,以增强帝国军力。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在历任拜占庭帝国皇帝治下,蛮族士兵均为构成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亚得里亚堡战役后,当面对哥特人劫掠巴尔干半岛的严重局面时,为了补充军力,塞奥多西一世仍然在不断招募哥特人进入军队[9]29-30。可以说,正是因为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帝国军队受到惨重损失,因此招募蛮族从军的需求就更为迫切。哥特人士兵在塞奥多西一世军队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在379年,当皇帝及其将军专注于平定色雷斯地区并消除对君士坦丁堡与亚得里亚堡的直接威胁,为帝国服役的哥特人将军莫达雷斯(Modares)在色雷斯取得一些胜绩[7]151。在一次战斗中,正是由于军队中哥特人士兵的倒戈与逃跑导致帝国军队战败[7]151。上述例子从正反两面显示了哥特人士兵在塞奥多西一世的哥特战争中的重要性。
蛮族士兵的重要性并未随着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暴动的结束而消失。在帝国政府与哥特人签订382年和约后,被允许定居在色雷斯的哥特人有其自己的领袖,当皇帝提出要求时为帝国军队提供兵员[10]37。根据左西莫斯的叙述,西部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被将领不列颠伯爵(comes Britanniarum)马克西莫斯(Maximus)所杀[11]86-87。在格拉提安死后,马克西莫斯控制了不列颠、高卢、西班牙;而意大利、潘诺尼亚与阿非利加则仍忠诚于格拉提安的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375—392年在位)[9]37[12]158。马克西莫斯于387年率军突然进攻意大利[12]159。瓦伦提尼安二世与其控制朝政的母亲查士丁娜(Justina)渡海逃至塞萨洛尼卡,向塞奥多西一世求助,塞奥多西一世随后出兵进攻马克西莫斯[11]91-92。在这次内战中,塞奥多西一世的军队包括哥特人、匈人与阿兰人在内的大量蛮族士兵与蛮族将领,在塞奥多西一世军队中匈人与阿兰人骑兵的快速进攻下,斯西亚(Siscia)这一交通要道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即已在塞奥多西一世军队的进攻下失守[9]62-63。马克西莫斯本人于388年8月28日被处决于阿奎莱亚[13]107。4年后,西部地区再度发生内乱,将领阿尔博加斯特(Arbogastes)杀死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立尤格尼乌斯(Eugenius)为帝[14]85。塞奥多西一世在出征西部前为增强军力,大量征召哥特人等蛮族从军[15]24。在战斗中,这些士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6]29-31。实际上,直至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哥特人、匈人、阿兰人、格皮德人、保加尔人等各个蛮族群体时常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士兵出现于各个战场,参与帝国的大小战事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蛮族将领融入帝国政治与社会生活
正是由于蛮族士兵大量加入帝国军队,蛮族将领在帝国政治中的地位也日益升高。在塞奥多西一世时期,曾任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3)军事长官是帝国野战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一职的16人中,至少9人出身于日耳曼人[16]10。在早期拜占庭帝国,军队在政治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常常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军队中蛮族将领的增加必然导致蛮族将领参与到帝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并开始干预帝国政治。
395年,趁皇帝阿尔卡迪乌斯检阅军队之机,塞奥多西一世第二次西征军的指挥官之一盖伊纳斯的部下当众杀害了帝国政府首脑鲁菲鲁斯(Rufinus)[11]102[14]95[17]85-87[18]112-113。继鲁菲鲁斯执掌朝政大权的寝宫总管(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a)尤特罗匹乌斯,也由于盖伊纳斯的干预而先被放逐至塞浦路斯(Cyprus),后又被处决于卡尔西顿(Chalcedon)[18]129-132[19]62-63[20]442-443。但盖伊纳斯本人最终也在政治斗争中落败。400年7月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色雷斯,君士坦丁堡市民趁机暴动,关闭城门,数千名哥特人被杀[7]169[18]133-134。盖伊纳斯企图经由赫勒斯滂前往小亚细亚,但是被忠于帝国的另一位哥特人将军弗拉维塔(Fravitta)所败;此后,盖伊纳斯越过多瑙河,被匈人国王乌尔丁所杀,其首级作为赠给阿尔卡迪乌斯的礼物被送至君士坦丁堡[7]169[9]152[18]134-135[21]814。塞奥多西二世时代,哥特人普林萨(Plintha)于419年成为执政官并担任军事长官超过20年,大约与此同时,阿兰人阿尔达布里乌斯(Ardaburius)也成为军事长官[22]30。塞奥多西二世统治后期至利奥一世统治时期,阿尔达布里乌斯之子阿斯巴依靠日耳曼人士兵的支持长期执掌大权,并成为利奥一世即位的主要推手[20]167。
蛮族群体定居于帝国疆域内并积极融入拜占庭社会的经济活动、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必然导致蛮族与帝国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处与互动,并在这种共处与互动中逐渐出现了血缘上的联系,这主要通过在帝国内定居的蛮族与帝国当地居民的通婚实现。
虽然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无法统计新到族群成员与帝国本地居民之间通婚的具体数据与比例,也无法统计这种通婚所产生的后代的具体数量,但是,即使是从并不关注也无法计算上述数据的同时代史家的零星记载中,至少可以看出这种通婚现象在早期拜占庭帝国上层社会相当普遍,并为时人所接受。拜占庭帝国塞奥多西王朝著名将领斯提里科(Stilicho)便是出身于这种婚姻的后代。根据史家记载,斯提里科的父亲是汪达尔人,在皇帝瓦伦斯时期进入帝国军队服役,担任军官,斯提里科的母亲则是帝国居民;斯提利科本人在大约383年时成为一名军团将官(Tribunus Praetorianus Militaris),此后他娶了皇帝的侄女兼养女赛琳娜(Serena)为妻,至392年他可能已经成为色雷斯两军军事长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 per Thracias);此后他在塞奥多西一世再次统一帝国的内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394年被提升为御前两军军事长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 praesentalis)[21]1957[23]352[24]237[25]853-855。从斯提里科的仕途看,显然他的汪达尔人出身并未阻碍他的升迁。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塞奥多西一世的大力拔擢,与他此后成为皇帝的侄女婿兼养女婿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能够缔结这桩对他今后的事业有莫大帮助的婚姻也证明皇帝并不介意他是汪达尔人与帝国居民的后代,从而可以间接证明当时上层社会对这种婚姻的接受程度。此后,斯提里科又先后将他的两位女儿玛利亚(Maria)与塞尔玛提亚(Thermantia)嫁给塞奥多西一世的次子霍诺留(Honorius)为妻[25]857。虽然斯提里科两女与霍诺留的联姻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安排的政治联姻,但是,直至斯提里科最后垮台,他安排的这两次婚姻也没有被他的政敌当成攻击他的口实,再次从反面证明帝国社会对这种婚姻的接受程度。塞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尔卡迪乌斯则娶了法兰克人将军巴托(Bauto)的女儿为皇后[11]100[14]93[20]441[25]780。利奥一世时期执掌军政大权的阿兰人将领阿斯巴曾经企图为其子帕特里修斯(Patricius)与利奥一世之女阿里阿德涅(Ariadne)联姻,但利奥一世却将女儿嫁给了另一支蛮族伊苏里亚人(Isaurians)的一名首领泽诺(Zeno)[10]98[14]467[20]838。显然,这一事例再次证明蛮族与帝国居民之间的通婚本身在早期拜占庭帝国并不受限制,因为利奥一世的选择泽诺而非帕特里修斯为婿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由于介意帕特里修斯作为蛮族后代的身份。
三、蛮族对帝国认同的形成
随着移居帝国的各个族群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日常生活中与早期拜占庭帝国社会的深度融合,帝国出现了多族群融合的局面。与此同时,蛮族群体逐渐形成了以政治认同、宗教认同与文化认同为核心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最终导向对于帝国本身的认同。
首先,移居帝国的蛮族群体在积极参与和融入帝国政治与军事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于帝国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主要体现在蛮族首领积极寻求在帝国政治框架内的晋升。在早期拜占庭帝国,皇帝们将为帝国军队服役作为接受边疆之外的族群在帝国定居的基本条件之一,而移居帝国的蛮族实际上对此并无抵触,加入军队的蛮族士兵与将领借此机会追求自己的帝国社会中的政治发展。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据记载3世纪曾经出现过如阿拉伯人腓力(Philip the Arab,244—249年在位)这样成为皇帝的“蛮族”将领[26]435-441。至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加入帝国军队的哥特人将领绝大多数则是试图融入帝国并在帝国政治体系中争取个人利益。之前提及的盖伊纳斯危机在本质上也只是帝国内部常见的围绕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盖伊纳斯并不是想要推翻帝国对哥特人的统治,也不是想要颠覆帝国的政治制度,而是希望在帝国政府内部提升自己的权力乃至控制帝国政府,从而实现自己在帝国内部的政治野心[27]。如前所述,与盖伊纳斯同时期的哥特人将领弗拉维塔,也并未因为与盖伊纳斯同为哥特人而在这场斗争中站在盖伊纳斯一方,与此相反,弗拉维塔凭借击败盖伊纳斯的战功而得以在帝国政治结构中得到晋升,最终成为执政官。上述两位哥特人将领事业的发展证明,对于移居帝国的哥特人首领及其追随者而言,无论是如盖伊纳斯那样在帝国内部以军力威胁帝国政府的方式获取权力,还是效仿弗拉维塔通过为帝国政府的忠诚服务而取得体制内的荣誉与官职,其政治认同始终是以帝国为中心的,始终是将帝国及其政府视为合法性的来源。
阿拉里克的事业也证明了这一点。最终于410年攻陷罗马城的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Alaric)早年就加入了罗马军队[28]15。395年,阿拉里克率领部下的哥特人士兵发动暴动。根据佐西莫斯的记载,阿拉里克之所以暴动,是因为他在参与塞奥多西二世的第二次西征后对于自己未能得到更高军职而感到愤怒[11]101。此后君士坦丁堡政府安抚他的举措之一正是任命他为伊利里库姆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11]124。从408年至410年,阿拉里克三次围攻罗马。在哥特人军队最终攻入罗马城之前,阿拉里克在与西部帝国政府谈判中所提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希望得到两军军事长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这一军职。为得到这一职务,他甚至还曾经于409年拥立官员阿塔鲁斯(Attalus)登上皇帝宝座,并由后者任命阿拉里克为军事长官[11]129[14]163[29]158。在前述潘诺尼亚哥特人、色雷斯哥特人与拜占庭政府之间的冲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当阿斯巴垮台后,色雷斯哥特人首领塞奥多里克·斯特拉博就向帝国提出包括继承阿斯巴军职在内的诸多要求[14]407-409。在利奥一世拒绝后,塞奥多里克·斯特拉博分兵两路进攻帝国,夺取亚得里亚堡[14]409。473年,帝国政府为了结束战事,最终同意任命他为阿斯巴曾经担任过的御前军事长官[18]320。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首领、阿马尔家族的塞奥多里克的要求与塞奥多里克·斯特拉博相似。为达到目的,塞奥多里克在482年率潘诺尼亚哥特人劫掠巴尔干半岛多个行省,当时的皇帝泽诺被迫在483年同意授予塞奥多里克以御前军事长官的军职与执政官职务[30]28。
其次,移居帝国的蛮族群体逐渐接受了帝国流行的基督教信仰,从而形成了对于帝国的宗教认同。自君士坦丁一世采取支持与保护基督教的政策以来,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逐渐取得了实质上的国教地位。正如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言,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决定该帝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正是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信仰融合统一在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才出现了后世称之为“拜占廷帝国”的历史现象;基督教取得胜利和帝国政治中心最终迁至希腊化的东方地区,这两大事件标志着“拜占廷”时代的开始[31]23。6世纪时,“印度航海家”科斯马斯在其著作中将拜占庭帝国称为“第一个信仰基督的帝国”,它在世界上与基督同在,只要世界延续,帝国就不会毁灭[32]7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基督教的认同与对拜占庭帝国的认同几乎是一致的。虽然基督徒并不一定都生活于拜占庭帝国皇帝治下,但拜占庭帝国皇帝自诩为所有基督徒的保护人,而信奉基督教也成为拜占庭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早在376年之前,基督教已经在哥特人中流布,有记载的最早在哥特人中传教的是乌尔菲拉(Ulfila),他是在4世纪早期在哥特人的劫掠中被俘虏的帝国居民,从卡帕多西亚被带至多瑙河北岸地区,他在那里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社区,并在哥特人的更为广泛的皈依中扮演了关键角色[33]196。乌尔菲拉在基督教上的突出贡献是发明了哥特文字母,并将《圣经》的大部分译成哥特语[34]31。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时期,乌尔菲拉被按立为哥特人的主教,虽然现在认为他所宣讲的教义属于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派的信仰,但是,在他向哥特人传教的时代,这一派别属于帝国基督教的主流派别,也因此招致哥特人首领的怀疑与迫害:乌尔菲拉及其追随者遭受放逐[35]60-61。但是,乌尔菲拉的传教事业并未就此失败,他所播撒下的种子仍然茁壮成长。随着大量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等族群移居帝国境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渐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无可否认,这些移居帝国境内的蛮族所信奉的大多仍是基督教的异端派别,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并成为了基督徒,也就意味着从信仰的角度而言,他们可以被视为拥有了身为拜占庭人的宗教身份,只要他们继续作为帝国居民居住于君士坦丁堡政府治下。与此同时,在基督徒的共相之下,保持对于阿里乌派或其他基督教异端派别的信奉,也成为移居帝国的蛮族群体的个性化特征,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的宗教认同。
最后,蛮族群体逐渐接受了帝国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对于帝国的文化认同,这主要体现在姓名与语言等方面。姓名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某种类型姓名的使用者在其所处社会中希望被视为何种身份。某种语言的接受与日常运用不仅影响着使用者对其生活环境的认知能力,也反映了使用者主动融入所身处的语言环境的愿望。
如前所述,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拉丁语仍是官方语言,同时希腊语又是东地中海地区使用广泛的语言,因此,在这一时期蛮族将姓名更改为拉丁式或希腊式名字的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在蛮族精英群体中更是如此。莫尔黑德指出,数个世纪以来,罗马对日耳曼人的吸引力已经从日耳曼人对于采用罗马式名字的热情所展示,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这样的例子,并且这一趋势至古代晚期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一世是首位晋升“蛮族”至执政官职位的皇帝,但是目前已知由君士坦丁一世所任命的执政官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非罗马人的姓名,很可能被君士坦丁一世任命为执政官的蛮族将名字改为罗马式人名[36]24。4世纪后期,忠于帝国政府并击败盖伊纳斯的拜占庭帝国哥特人将领弗拉维塔也曾经担任执政官,他为自己取了拉丁式的名字弗拉维乌斯(Flavius)[15]100[37]214。前述法兰克人将领巴托之女、皇帝阿尔卡迪乌斯之妻名为尤多西亚(Eudoxia),这是典型的希腊式人名。斯提里科的两位女儿分别名为玛利亚与塞尔玛提亚,她们的名字显然也消除了蛮族特征。5世纪后期,一位名为塔拉斯科迪萨(Tarasicodissa)的伊苏里亚人首领被时任皇帝利奥一世提拔为帝国将领,并将公主阿里阿德涅嫁给了他,而塔拉斯科迪萨则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希腊式人名泽诺,并在此后帮助利奥一世铲除了阿兰人将领阿斯巴的势力,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皇帝[14]467[18]318-320[20]1200-1202。
“蛮族(barbaros)”一词的起源本就与语言有密切联系。古希腊人最早使用该词,本为拟声词,后用于指不使用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族群[38]108[39]1[40]。因此,能否使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同样是区分蛮族群体与帝国居民的重要因素,也是新到蛮族群体是否接纳了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明成就的主要载体与成就本身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蛮族是否形成了对于拜占庭帝国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关于这一点,虽然史家并未留下太多记载,但是,以下一些判断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加入帝国正规军团队的蛮族士兵必然能够听懂军营中所用的拉丁语军事术语,并且应当能通过在军中服役逐渐学会在驻地生活中日常使用的语言,正如随着时间推移与代际交替,在帝国内部定居的蛮族农民家庭应当能够逐渐学会并使用定居地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语言一样。在帝国军队或政府中逐级上升至高级官职的蛮族精英必然能够使用军队和政府中通行的拉丁语,否则他们就将无法与非本族出身的同僚交流,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同样的理由,这些蛮族精英及其家庭成员很可能也懂得使用希腊语,因为他们的生活中显然并不仅仅只有政府和军队事务,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与东部帝国上层社会成员的交往中,希腊语显然也是一种必备的能力。最后,幸运的是,有一位拜占庭帝国史家为我们提供了蛮族出身的学者掌握与使用拉丁语的确切例证,这位史家就是用拉丁语写作《哥特史》的哥特人后代约达尼斯。
综上所述,面对纷至沓来的各个族群,除了军事手段之外,早期拜占庭帝国政府较为积极地采取了吸纳可供利用的蛮族群体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以不同方式进入并定居于帝国内部的各种蛮族群体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融入帝国社会,同时新来者对帝国的政治认同、宗教认同与文化认同也在逐渐形成,由此令新到族群逐渐融入拜占庭帝国社会之中,并成为后世所称的“拜占庭人”的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