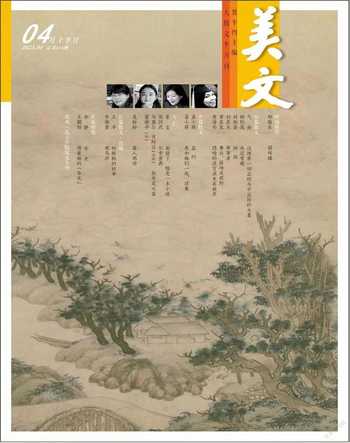余光
余静
九莉的幻灭
几年前读张爱玲的《小团圆》,读不下去,人物如走马灯,琐碎。最近又拿起来看,竟迷进去了,为九莉不值。花花公子邵之雍,怎配得上她的眼泪。
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是胡兰成。离开上海二十多年后,在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小公寓里,张爱玲开始写《小团圆》,彼时她55岁。大约作家都会有一本自传性的东西,自己写也好,授权别人写也罢,总是个交待,省得身后被一些不相干的人说三道四。
不知张爱玲写的时候有没有犹疑,完成后她倒有些小心了,一度想销毁它,原因竟是不想让那个人得意。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所以矛盾得厉害,一面补写,别的事上还是心神不属。”
55岁的张爱玲已经能够站在远处看自己,一如她躲在绛红色帷帐后露出的幽深的、冷冷的目光。年轻时的冷是冰,化成水,到底是流动的;现在的冷是幻灭,爱情、恩情终抵不过世事流转,沧海桑田。
“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这是张爱玲的洒脱,也是无奈。她知道她与胡兰成的情爱必将成为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文字里没有避讳。九莉与邵之雍由相识、相恋到结婚、分手,其间两人的芥蒂、猜疑、闺阁里的小秘密,都以张爱玲式的笔法呈现出来,写得很淡很淡,如加多了水的墨痕,只轻轻一点,就轻易渗透纸面,在背后变成泪。
九莉的心理描写,张爱玲常说一句话:“像被针扎了一下。”没有剧烈撕扯的疼痛,就是被扎了一下。你可以说这是张爱玲惯有的冷漠,但我心疼她,她总是被“扎了一下”,早已满身针孔了吧。
张爱玲的好友宋淇夫妇是《小团圆》的第一批读者。他们有两个担心:一是胡兰成会利用《小团圆》的出版而大占便宜,亦不会顾及到张爱玲的死活;二是九莉不是个讨喜的角色,自私、冷漠,读者的反感也许会波及张爱玲。但张爱玲还是这么写了。她坚持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她宁愿不出版,也不想改动一个字。
幸运的是,我们读到了完整的、没有删改的《小团圆》。从1976年小说完成到2009年出版,历经30年之久。这期间,胡兰成去了,张爱玲去了,代理这部小说的宋淇夫妇也去了,所有他们曾经担心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时间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化一切于无形,谁还能争辩什么呢?
张爱玲大概早就明白这一点,她在小说里借九莉的口说,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
生在那样一个显赫的家庭,却没有得到多少爱。母亲出国,父亲吸鸦片,整日无所事事。张爱玲和姑姑生活在一起,两个女人茕茕相对,既亲密又疏离,想来让人不寒而栗。也因此,小说里的九莉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三姑、母亲、同學,什么都要和他们分得一清二楚。尤其钱财,不会少给一毛,也绝不多占一分。她不落别人的“人情”,也不会送给别人“人情”。对与她无关的事,她更是漠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日本投降了,外面在放炮,消息传来,九莉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偏偏这样一个“冷酷”的人,遇到了邵之雍。她独对他有期待,想和这个男人白头到老。就算知道他有“二美”“三美”,她也尽量让自己理解——一个身处动荡中的人总要有些短暂的安慰。她甚至不顾自尊,千里迢迢去找他,让他做一个选择。但他到底不愿选择,说“牙齿好好的为什么要拔掉”。九莉觉得这是疯人的逻辑。她一直微笑着,不再问他,背地里却流眼泪,“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
其实以九莉的聪明,或许早就看透了,只是不想戳破。
小说第九章,张爱玲鲜有地用一整个章节描述一出戏。我以为这是《小团圆》的华彩。
戏的名字不知道,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公子和小姐私定终身,有了云雨之欢,公子去赶考,途中艳遇另一人家的小姐,一见再钟情。结局大团圆,公子考中,迎娶二美。
九莉坐在凳子上看戏,旁边不断有人嗤笑,说台上的戏子“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台上演一段,底下就有人笑,“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一句话重复了五次之多。
没有任何九莉的心理描写,但“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让人心悸。在邵之雍的理想世界里,三美团圆,九莉是其中一个。九莉为自己难堪:她居然想说服自己这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实是血淋淋的“难看”。
九莉看不下去了,站起来往外挤。她要的不是“大团圆”,而“小团圆”更是奢想。九莉终于明白了她和那些女人的区别。
“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在这密点构成的虚线画面上,只有她这翠蓝的一大块,全是体积,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出去。”
这一段真是精彩。九莉“挤出去了”,对邵之雍的期待也幻灭了。
现实的情形是,1944年,张爱玲和胡兰成缔结婚约。胡兰成在婚书上写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他没有给张爱玲一个安稳的现世。时局动荡,人心离散,他在逃亡中也不忘处处留情。最可笑又可气的是,他写信给张爱玲,常忍不住津津乐道于别的女子对他的爱,还责怪爱玲不会嫉妒。他真是将爱玲当作精神伴侣了。他用《聊斋志异》中的《香玉》打比方,说“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腻友也”。他是想把张爱玲放在“腻友”的位置上。他欣赏张爱玲的绝世才华,享受他们的灵肉相通,同时也割舍不了世俗的爱。一个是仙境,一个是凡尘,他妄想上天入地,二者兼得。
张爱玲不是个传统的女子,但也向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胡兰成的那套逻辑很反感。后来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以“无赖人”代称胡兰成,可见她的态度。
张爱玲24岁跟了胡兰成。最美的年龄。以她的桀骜、清高,却说遇见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直到尘埃里开出了花……
花还是萎谢了。多年以后,她孤身一人,在洛杉矶的一间小公寓里写《小团圆》。因为酝酿得实在太久了,写得非常快。她说: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吾宁爱与憎
台湾作家李敖,2018年去世之前,曾发表过一篇公开信。那个骂了一辈子人的李敖,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温柔起来,邀请他的友人和仇人见“最后一面”。他说,希望这次会面是真诚的、坦白的,“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相杀”。
无论友人仇人,李敖说,想和他们一起吃顿饭,合一张影,带他们看看自己养的猫。
人生光阴匆匆几十年,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一笑泯恩仇吧。
想到《射雕英雄傳》里的一个故事。
宋徽宗年间有个叫黄裳的,受皇帝委派,带兵剿灭一个叫“摩尼教”的民间教派。“摩尼教”里有不少武林中人,黄裳是混官场的,不懂什么武林规矩,一通乱打乱杀,得罪了很多名门正派的高手。这些人说,好,你不按规矩来,那我们也不要规矩了。跑到黄裳家里,把他的父母妻儿杀了个精光。黄裳寡不敌众,逃到一处穷荒绝地躲了起来。他把敌人的一招一式皆记在心里,苦苦思索破解之法。终于有一天,他想通了破解的法子,就算这些高手一齐上,他也能对付得了。
黄裳于是走出深山,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到了。但奇怪的是,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黄裳四处寻找,终于找到其中一个仇人,当年跟他动手时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老太婆。
原来,黄裳在深山里潜心钻研武功,日思夜想,浑然忘我,不知不觉竟已过了40年。那些仇人当年大多已四五十岁,又过了40年,岂不是都死了么。
黄裳看那老太婆躺在床上,只剩喘气的份儿,不用他动手,过不了几天也就死了。积压在他心底数十年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黄裳释然了,给他唯一的仇人——那个老太婆喂饭喂药,像对待亲人一般。
每个人都难逃一死,四十年长吗?在时间的洪流里不过一瞬而已。人的仇恨有多深?是一盆水那么深,一口井那么深,还是海那么深?如果仔细想一下,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为我们答不上来。仇恨没有形状,没有质量,它是因名存在的一个东西,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把它称作“仇恨”,它就成“仇恨”了。我有时乱想,如果最初的最初,那个命名的人用另外一个字代表“仇恨”,比如“爱”,那这个世界会怎样?你觉得会颠倒吗?
放心,当然不会。因为“爱”已经被定义为“仇恨”了呀,你不会因为别人对你说“我爱你”而高兴。可见这个因名存在的东西是很不靠谱的,它常常变化,却装出一副恒定的、煞有介事的样子,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让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想想看,从小到大,有多少恨曾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辗转反侧、夜不能眠?现在呢?还不是风吹云散了。恨,心旁一个艮,艮是《易经》八卦中的一卦,代表山。把山放下,心就轻松了。
木心先生一生坎坷,十年动乱期间被捕入狱,囚禁18个月,所有作品被烧毁,三根手指遭折断。在狱中,他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狱中笔记》,谈文学、谈艺术、谈生活,就是不谈悲苦;他手绘钢琴黑白琴键,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做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晚年,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那时,木心已是望七之年,蜗居在纽约一个叫“杰克逊高地”的街区。他在这里为一群中国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陈丹青是听课学生之一。陈丹青回忆,当年,就在这窗台里,先生满心狂喜,谛听彻夜的鸟鸣,写下《杰克逊高地》。
“……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和蔼,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就在那个五月的傍晚,在远离祖国的杰克逊高地,这位异国的流浪汉,一个孤单的老头,在心里原谅了一切。
在距木心先生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有位叫李商隐的诗人,说了一句和“不知原谅什么”很相近的话——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李商隐登山访僧,遍寻不见,黄昏时分看到一位僧人靠着一枝青藤,正在独自敲磬。万籁俱寂,纤尘无染,李商隐顿感世界的静谧与安详,发出了“吾宁爱与憎”的感叹。大千世界俱在微尘之中,人也是因缘聚合的产物,微不足道,还有什么爱和恨呢?
人生最难是释怀,但有时候释怀却是一瞬间的事。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裳,恨了四十年,仇人都死了,他想原来自己也会老,也会死,与其整日在仇恨和不甘中纠缠,不如把平生所学所悟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那本震动武林的《九阴真经》。
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刚确诊的时候,她很崩溃,成天想,为什么是我?我没干过亏心的事,为什么偏偏是我?老天爷不公平啊!劝她、安慰她都没有用,她较劲的对象是老天爷,病生在她身上,你无法感同身受。一段时间之后,她看似平静了,但我知道她没有释然,因为你不能跟她提那个病。她的痛苦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她不能原谅为什么是她生这个病,她竟然觉得,得病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我很明白她。她骨子里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疾病击垮了她的自尊。所以,这事不能劝,只能自己救自己。直到两年后的一天,她对我讲起一次经历,我看到她眼里的泪水,知道她释怀了。
她说,她和一群驴友登山。她平常很少登山,况且身体还在恢复中,山没有名,也不算高,但路极其难走。她坚持爬到了山顶,之前一直阴沉的天突然亮起来,远处群山起伏,云雾缭绕,太阳倏地从层云里跃然而出,金光一片。一瞬间,她泪水横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春花秋月,夏雨冬雪,世事流转,沧海桑田。人多么渺小,谁会为你停留片刻?
人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才会痛苦。学会释怀,释怀是与自己、与生活、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释怀是放下,不是放弃,是自我认识清醒后的重新出发,是直面心灵的自我救赎,是冲出迷雾的豁然开朗。我们要原谅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
说话恐惧症
对于说话这件事,我是有阴影的。
上学时最怕老师提问。坐在座位上佝着背,恨不得缩到地下去,眼睛低垂或游移不定,不敢与老师的目光相撞。偏偏有些老师自以为神武,专叫一提问就低头的学生。于是站起来,于是脸红心跳,于是语无伦次,于是满堂哄笑。
最让我感到痛苦的不是被老师叫起来,而是明明知道问题的答案,一旦站起来,那个正在说话的就不是我了。那个人曲解我的意思,扰乱我的邏辑,以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笑声为荣。我那支离破碎的语言像廉价的玻璃碎了一地,那时的我恨不得捡起一块玻璃做匕首,插入那些嘲笑者的胸膛。
如果你认识我,你一定想不到我的学生时代有这么惨痛的经历。现在的我貌似会说话了,但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恐惧的。
为什么?我试图找到答案。
从医学角度解释,这一类人患上了一种病——赤面恐怖症,属于心理障碍的一种。当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场合或与重要的人交往时,就会紧张、激动,从而反射性地引起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去甲肾上腺素等儿茶酚胺类物质分泌增加,使人心跳加快,毛细血管扩张。
——够了,让百度上这些听不懂的名词见鬼去!我好好说话。
我的看法是,不要期许赞美。说话是一种表达,但人们往往不仅仅满足于表达,人关注的是表达之后的反应。正确的、错误的、有价值的、无意义的,这些由谁来判断呢?当然是听者,它可以延伸为与你有联系的人,再往大了说,是社会。
好了,由于我们过分关注同学、同事、陌生人、单位甚至社会的评价,无形中我们内在的压力增加了,和家人聊天时的自如感消失了。因为我们在和家人说话时不会在乎他们作何反应,我们是真实的,没有期待的。
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对未知事物都会有恐惧心理,别人的心思、别人的反应也是未知事物,也许是最难破解的未知事物。
为什么我们如此期许赞美?不好意思,我发现我被自己绕进去了。深究一件事就像拔萝卜,难免会带出泥来,因为不带出泥就找不到它的根。
我是肉联厂长大的孩子。那会儿是计划经济,虽然校长和老师都要找关系凭条子买肉,但我们厂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获得优越感,反倒屡屡因为“出身问题”遭到语言暴力的打击。诸如,“笨的,是不是猪肉吃多了”“你个猪脑子”“猪头”,等等。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产生怀疑,自我的认知遭受重创。我想要更多的赞美来证明我不是“猪脑子”。有时心里有一万句反驳的话,每一句都精彩无比、逻辑严密,可一旦面对实战,反应总是慢半拍,生生把自己憋成内伤。
每一个恐惧说话的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痛,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这些“痛”解密。据说国家情报机关有一个“解密日”,通常是在特殊任务执行的十年之后,这一天,所有的秘密重见天日,可以谈论和传播。我有一个发现,有些痛苦一旦解密,简直比笑话还要笑话。
好在我已经挖出我恐惧说话的根源,接下来就简单了。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自我麻醉,俗称精神胜利法。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不会说话的人用这几句聊以自慰,可你要明白,老子所说的这些圣人、贤人,他们不是不会说,而是藏着不说。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有人拿这几句话评价你,他一定只是随便说说,多少带着点溜须拍马的性质,千万不要昏了头,真以为自己大智若愚了。
中国有一个时代特别牛,只要你肚子有货,想说会说,说得有水平,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不小心还能青史留名。这就是战国时代。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策士,或称纵横家。他们往来于诸侯之间,以三寸不烂之舌奔走游说、出谋划策,著名的有苏秦、张仪、司马错、唐雎、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不胜枚举,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好舌头”。
魏国人张仪还没有做秦相的时候,生活潦倒,有一次被人打了,妻子又气又恨,说:“你要是不到处游说,怎么会受这样的屈辱呢?”他不以为然,反倒问妻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妻子说:“舌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噫嘻!一个人对自己会说话如此自信,这不光是自身的底气,也是那个时代的底气。
张仪并不是战国策士里我最服气的人,我最服的是范雎。《史记》和《战国策》都记载了他和秦昭王的一次对话,简直可以作为“如何说话”的教科书,现在网络平台上那些“说话的艺术”“一天内教会你说话”什么的,都弱爆了。
范雎,魏国人,客居秦国等秦昭王接见,等了一年多,秦昭王都不理他。没办法,范雎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秦昭王看后大喜,立即派车去接范雎。这回轮到范雎摆谱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秦昭王长跪着请求说:“先生教我吧。”范睢“嗯嗯”了两声,没说话;秦昭王再次请求:“先生请赐教。”范睢还是“嗯嗯”。这样连续三次。秦昭王说:“先生是不肯教寡人吗?”
每回看到这里我都不由得感叹,范雎太牛了,真能沉得住气。接下来就是堪称“说话教科书”的史实。我们看看范雎是怎么步步为营,让秦王信服的。
首先,范雎说,我不是不肯说出我的主张,实在因为我是个羁旅之人,与大王关系疏远,而我想要面陈的,又都是纠正您偏差错误的事,我愿意献上自己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大王连续三次询问我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
牛吧,先打个预防针,如果我一会儿说的话让您不开心了,您要相信我是出于一片赤诚。
接下来,继续“自虐”,加深秦昭王的印象。
范雎说,我不是害怕不敢说,就算今天说明天死了,只要对秦国稍微有些益处,就是我的最大愿望。连五帝这样的圣人都要死,我又有什么担心的呢?
是不是很感动?难怪秦昭王快招架不住了。
范雎绝对是个逻辑控,层层递进,一步一个坑,让秦昭王不知不觉掉进自己的坑里。
范雎又说,那我在担心什么呢?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因为谏言死了,天下贤士看到臣子尽了忠反遭到死罪,从此锁住了嘴,裹住了脚,没人愿意到秦国来了。
第二个担心是,现在您上面害怕太后的威严,下面被奸佞臣子的惺惺作态所迷惑,自己身居深宫禁院,离不开左右近臣的把持,没法洞察奸佞。长此下去,往大处说国家覆亡,往小了说您孤立无援,岌岌可危,这才是我所担忧的。至于说穷困、屈辱、处死、流亡之类的忧患,我是从不害怕的。如果我死了而秦国得以大治,那我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
这段记载就是个开场白,核心谋略一点儿没说,已经让秦昭王心服口服,甚至称“范雎的到来是上天赐恩于先王而不抛弃他的儿子啊”!
范雎后来没有让秦昭王失望,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统一霸业奠定了基础。这是后话,不在今天探讨范围之内。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需要经过多少思想的沉淀和梳理,经由大脑转化为语言,反复练习,才能够把说话变为艺术。
说话需要练习,这是肯定的。除过生理因素,说话恐惧症患者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没有思考;二、没有将思考转化为语言。转化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在心里,一个是在纸上。我们不是范雎,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记忆力、表达力和逻辑性,那我建议你还是将思考转化到纸上更靠谱些。因为无数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那些在心里构建、练习了很多遍的话,一旦从嘴里吐出,就变得词不达意,甚至面目全非了。
人的过分自信有时是带有欺骗性的。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将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照着念。这不丢人。
(责任编辑:孙婷)

余 静 资深媒体人、策展人,出版长篇小说《墨色》。长篇纪实文学《易俗大先生》入选“陕西省出版基金精品項目”,入选第十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名家笔下的陕西文化旅游名篇佳作”;散文作品入选四川文艺出版社“花样女人”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