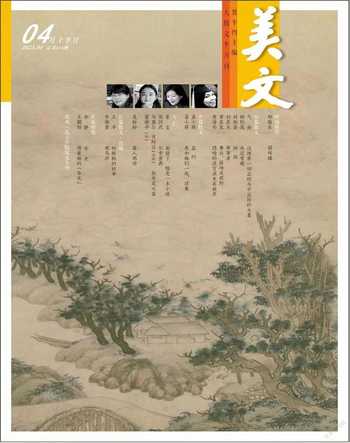鸿儒白诗朗

何云燕 壮族,广西天等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12-2013年美国波士顿大学“联合培养博士”访问研究员,2016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访学学者,2018-2019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曾发表数篇散文作品。
一
历史上,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曾经有过非常著名的“波士顿儒家”,代表人物主要是当年生活工作在美国波士顿学界的三个人: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和白诗朗(John H. Berthrong)。当时南乐山任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院长,白诗朗是副院长。不少人将曾长期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近些年活跃于海外汉学界并受聘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的安乐哲(Roger T. Ames)误称为“波士顿儒家”的创始人和代表,大概源于他和南乐山的中文名字中都有一个“乐”字,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安乐哲现任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这个身份容易与“波士顿儒家”的“儒”字重叠而令人产生联想。
说到误解,可能国内很多人对“神学院”也多有误解,往往一听“神学院”就会联想到教会和修道院之类教牧和修道场所,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受到过往一些文学作品或电影作品的影响。的确,最初的神学院是教会设立的,但最初的大学、医院也都是与教会有关的,很多大学、医院都是教会设立的,而且与国内大学、科研和医疗机构等广泛开展合作交流,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泰国易三仓大学,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等等。简单讲,如今国外的神学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神学院;另一类是与综合性大学一体的神学院。前者如美国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纽约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等,后者如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耶鲁大学神学院、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神学院等。前者主要培养教牧人士,与综合性大学的关系有的疏远有的亲密;后者主要培养与人文宗教及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型人才,学科方向设置与大学其他院、系、所类似,遵循同一模式。这种情况下,前者和后者的关系也是有的疏远有的亲密,这主要取决于前者的态度和倾向,比如许多较为保守的独立神学院就认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神学院过于自由和世俗化。其实中国国内情况也大致类似,为教会培养教牧人员的独立神学院如北京的燕京神哲学院(天主教)、燕京神学院(基督新教),南京的金陵神学院等;与之相应,伊斯兰教有自己的经学院;佛寺则有佛学院,等等。而国内高校则没有神学院,却有类似于宗教文化研究院的相关机构,这些机构除了不培养教牧人士之外,其基本功能跟国外与大学一体的神学院的学习和研究功能相当。
所以,尽管白诗朗长期执教于神学院并荣任副院长,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学者,一位儒家学者,或者说是一位海外汉学家,一位鸿儒。可以以他出版的著作为证:《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1994)《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比较研究》(1998)《儒家之道的转化》(1998)《简明儒学导论》(2000)《过程的扩展:中西方哲学与神学转化的探索》(2008)等等。当然,白诗朗的学术著作远远不止这些。2011年初,白诗朗在将受聘为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前,曾提供给该校一份长达25页的简历,其中主要列述了自己的教育背景,所受奖励,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清单等,均与海外汉学、中国学密切相关。这次来华访问,应该是白诗朗在2010年9月应邀参加第一届世界尼山论坛会议后,紧接着再次来华与中国大陆相关领域的学者近距离大范围地接触。
白诗朗生于1946年3月美国威斯康星,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文和哲学;后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分别为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和宋代新儒家。经历了完整、系统的学习之后,白诗朗一直从事着与中国哲学有关的学术事业,直到2022年8月在加拿大去世。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留校任教的教师,应邀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他看到参会者当中有不少在读博士生,非常活跃地发言、点评和主持会议主办方安排的小组讨论时,很受吸引和鼓舞,随即萌生了到美国读博士的愿望。于是,他向前来参会的一位美国学者询问申请到美国读博士的途径,这位美国学者就推荐了当时并未出席这次会议的白诗朗,并留下了白诗朗的联系方式。北京大学这位教师会后给白诗朗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很快即收到白诗朗的回信。回信表示愿意接受这位北大教师赴美跟随自己攻读博士,并详细介绍了申請、签证、赴美和入学程序。当年,北大教师顺利入读波士顿大学跟随白诗朗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在读和毕业之后,他均受到白诗朗先生多方面帮助和鼓励。那个时候,美国学习中文的人很少,但波士顿大学却有专门印有汉字校名的文化衫,白诗朗先生专门买来送给北大教师,他很自豪地穿上在校园向大家“炫耀”,至今仍保留着作为美好纪念。
经这位北大教师介绍和推荐,白诗朗在二十世纪末10年和本世纪初10年的20年间,陆续邀请并支持国内十几位学者赴波士顿大学学习和访问,有的是读博士学位,有的是作访问学者。一位清华大学的学者在读书年代学习的外语是德语,在她拿到邀请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时,美国签证官发现她英语交流有困难,就用中文问她到美国后如何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时,她跟对方讲述了“波士顿儒家”的“故事”,签证官很高兴地就批准了她的申请。
2011年11月中下旬,受聘为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举行仪式时,白诗朗应时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执行院长张华教授邀请到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讲学、访问,学校还专门举办了“儒学传习与中西学术”研讨会,白诗朗先生讲授了他一生致力于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对话的经历与思考,分享了许多中西人文学术交流的心得。也是在这次活动中,白诗朗答应从北京语言大学接收几位在读博士到波士顿大学进行联合培养,首批共三位,王雅鸽、娜仁格日勒和我。北京语言大学国内外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009年挂牌以来,支持举办了众多硕士博士参加的赴外国际会议和硕士层面的联合培养项目,我们这一批是一次派出博士最多的。白诗朗先生此前接收过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但同时接收多位博士联合培养的“访问学生”还是第一次。
因为即将要去波士顿大学参加“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访学,我有幸作为白诗朗教授北京之行的陪同翻译。白诗朗到北京后第一站探访之地是五道口边上的万圣书店。彼时我是一个初入京城的壮族女子,对偌大的北京还不是很熟悉。白诗朗教授熟门熟路地步行把我带到万圣书店。路上他一直跟我强调,万圣书店在很多中外学者中颇具名气,之前他的朋友也带他来过几次。有一次美国东西海岸的几位儒学学者到孔子故里曲阜开会,还专门停留在北京一日,为的就是到万圣书店找中国学者的最新儒学研究成果。“可见万圣书店多么了不起!”白诗朗不禁感叹。听罢,我对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好感倍增。
到了万圣书店,白诗朗很认真地找寻他曾经坐过的位置,并找到那个最喜欢的靠墙座位,坐下来打开电脑,然后一脸俏皮地轻声告诉我:“每次我们来总是有人盯着我们看,中国人对外国人来北京书店可能是比较好奇,可能是怕我们做坏事。但是我可是好人哦!为了避免尴尬,我就躲在这角落里,这样就不太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了。但不是每次来都能遇上这个角落空着。如果有人坐着,我就希望他或她能快点走。今天没有人跟我抢这个座位,我真是太高兴了,能请你陪我一起坐下来看书吗?我想整理一下明天的讲座稿。”边说边露出憨憨的笑容。没有想到一个国际大学者竟然这么平易近人,让我初见他的紧张情绪一下就放松了。
接下来的数日,除了在北语做讲座和开会,我还陪同白诗朗走访了清华、北大,并有幸见到了刚刚从哈佛大学回国到北大人文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的杜维明先生。赫赫有名的杜维明先生携家人和同事宴请了白诗朗,并专门为他点了烤鸭。白诗朗像孩子一样,饶有兴趣地看着厨师在餐桌边上切鸭肉薄片,又兴致勃勃、略带笨拙地自己用面皮卷烤鸭片,然后很自豪很满足地品尝起来。我们所到之处,只要有孔子像,他就会挨着站,像中小学生一样挺直腰、双手合于腹前,神情庄重地跟孔子像合影。白诗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是溢于言表的,更是根植于内心的。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寻找时机推动、促成中美学者尤其是中美青年学子的交流与合作。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个即将成为我“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外方导师充满了敬意,也消除了我人生中首次出国学习的诸多忧虑。我最难忘的是我们那次在圆明园迷路的“事故”。由于那时我们都还没有智能手机,我只能靠地图和问行人来确定路线,结果阴差阳错绕了很远的路。本来腿上有旧伤的白诗朗在半道上突然扭到了脚,加之他身材比较高大、年岁稍高,使得他走路变得艰难了起来。眼见天色渐暗,路上行人稀少,找不到任何援助,我急得团团转。他看出了我的焦急和恐惧,不停地安慰我,还特地讲了很多故事和笑话,硬撑着走了很久。到达目的地之后,见到了他的朋友和学生,他哈哈大笑,说看到我急得快哭了,让大家不要责备我。后来我们到了美国,他也不忘记时不时拿这事来调侃我。
三
白诗朗对学生的关爱是颇具中国传统风范的。王雅鸽、娜仁格日勒和我没有到波士顿之前,就介绍他的几个中国学生给我们认识,希望她们协助我们租房。等我们搭乘飞机过来的时候,他考虑到我们人生地不熟,专门请一个中国来的博士生到机场迎接我们,把我们带到预定好的住地。他说是因为波士顿的公交系统不发达,出行基本靠贯通大波士顿区的铁路,但是铁路系统又比较复杂,担心我们拿着沉重的行李走迷路。得知我们顺利到达并安顿好之后,他专门在办公室等我们,为我们大致介绍了波士顿大学(BU)的基本情况,并为我们引见了两三位老师,欢迎我们去听他们的课。
随后他开车带我们到波士顿学院(BC)参加学术会议,希望我们早日融入波士顿的学术研究环境。路上,他告诉我们,波士顿学院虽然名称是“学院”但是其排名在很多方面比波士顿大学强;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隔着一条查尔斯河,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去对面的大学看看,如果需要去旁听,可以写信去问问任课的老师,得到允许之后就可以去了。“大部分美国人都很热情大方的,你们直接问就好,很多人喜欢自己的思想和知识被别人认可。就算有老师拒绝你们,那也没有关系,大波士顿区好的大学和老师多得很。还有中国学者云集的燕京学社,那里有很多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和会议。” 临了还教我们用波士顿口音读“Boston”,并不忘戏谑美国各地口音的巨大差异。白诗朗就是这样,总是提供给我们希望和动力,鼓励我们积极乐观应对机会和挑战,给我们示范如何轻松幽默地面对各式各样的境况。
我们到达波士顿两个月之后,美国的大学基本进入漫长的暑假,意味着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就没有课可以去旁听了。白诗朗带着几个波士顿大学的硕博研究生开起了一门课,让我们都去旁听并参与讨论。我们到了之后发现,除了一个年近60的白人女博士生,其余基本都是中国人。他指导的一个中国硕士生跟我比较熟悉,她悄悄地告诉我,美国教授几乎没有人用自己的假期补课、开课的,白诗朗很明显是专门为了你们仨才暑假开班的。听罢我很感动,下课之后趁着没人在旁边就此问他,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们如果是九月份起始,就可以旁听很多课。四月份到就很快遇上暑假,有点可惜,因为你们才有十个月的时间。但你们也不得不考虑中国那边的学习期,早来就可能早点拿到博士学位。”我说,少听课没有关系,放假我也正好可以全天泡图书馆,因为我们都开题了,可以充分利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收集博士论文材料、撰写初稿。当他得知我对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编排和开放安排很满意时,喜笑颜开。
在美国教授一般很少跟学生到饭馆聚餐,但是为了照顾我们的风俗习惯,白诗朗每隔一段时间就利用中午陪我们到中餐馆吃简餐。美国中餐馆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给每个到来的客人一个福饼(fortune cookie,也称幸运饼干或签语饼),即菱角状的小脆饼,里面有一条小纸片,印着一句温暖美好的话。白诗朗经常跟着我们兴高采烈地拆福饼,轮流读出自己得到的吉言良语,在欢喜中相互开玩笑。另一个有趣的事是,每次白詩朗跟我们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大门前,我们几个女生中总有人习惯性地抢着去帮他开门,他基本是顺从地配合通行并表示感谢。这样的情形在美国很容易引来异样的目光,他就会讪讪一笑,然后向周围人解释:帮忙开门是中国人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无论男女,这是中国的一种礼仪。
无论在哪里,白诗朗总竭力给予我们最大的扶助、理解和包容。遇到这样的老师,我们都深感幸运。文章标题用“鸿儒”一词,来自我和老师们在圆明园风和楼的一次聚会,餐厅正中的匾额上清人所书“鸿儒”两个大字。白诗朗乃一代异国“鸿儒”,言传身教让我们体悟到什么是儒学、什么是儒者。我把自己对儒学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写进了对美国经典作家梭罗的研究之中。2014年我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之后,彼时还在清华任教的王宁教授感慨地对我说:幸亏你去一趟波士顿,受波士顿儒学的熏陶,要不然这论文你没有办法写好。我诚恳地点头赞同,想起白诗朗亲笔签名送给我的几本书。
2013年初回国之后我再也没有跟白诗朗见过面,但是一直保持通讯联络。2018年我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在网络上跟他汇报了在英的学习情况。他告诉我,他退休之后离开了波士顿,搬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疫情期间我给他发过问候电子邮件,但是不知何故没有收到回复。疫情还没有消散他就去了天国。
想起白诗朗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会深深印刻在脑海里的,至少两点:一是他对学术的认真执着态度。他对神学研究是如此,对儒学研究是如此。这俨然已经化成他的个人风格。做一件事,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去做好。二是他的儒雅和豁达的性格。一想到白诗朗先生,脑海里就出现他温暖的笑和幽默的话语。在学术争论面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爱智慧,保持包容、博大的胸怀。和南乐山一样致力于探寻全球现代思想的丰富资源,世界多元主义的支持者。中美学界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白诗朗先生离开我们远行了,我们会认真读他的书,永久怀念他。只要有书在,他就是常留在我们身边。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