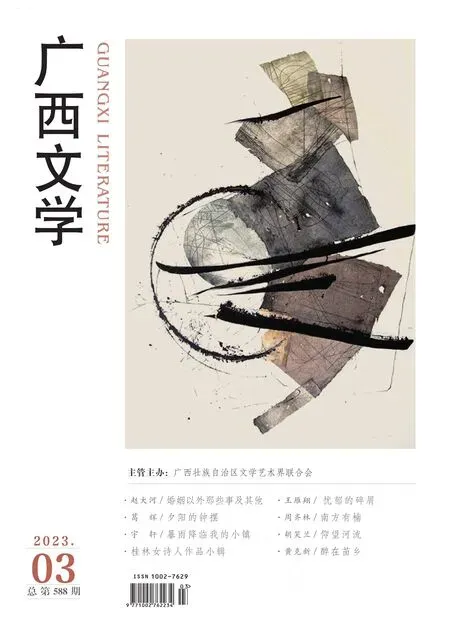柜中人
肖不洒
赶在日落之前,我爸和二叔已经把爷爷的棺木刷上了黑漆。乌黑透亮,泛着吓人的光芒。很快,天也被他们手上的刷子刷黑了,整个葱岭仿佛被一块巨大的棺材板盖住了。
就在早上,爷爷的病情突然恶化,被城里大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大人们只好办了出院手续,花大价钱雇了一辆救护车,急匆匆把爷爷从城里拉回乡下来了。就好像葱岭人骂人常说的那句话,赶着去投胎啊。爷爷就是赶着回来死,赶着回来投胎。这是葱岭的风俗,人生一世,无论走多远,最终都要回到家里,不能死在外头,成为孤魂野鬼。
好在爷爷安全回到葱岭来了,他是活着被抬进家门的。大人们长吁一口气。从中午到现在,爷爷一直躺在他那张陈旧的木床上,一动不动。床头挂着几大瓶点滴,药水通过透明的塑料管慢慢注入爷爷身体。他的下身连着一条导尿管,末端是尿袋。一进一出,看起来有些奇怪。
我爸、大姑和二叔,加上我和堂哥,寸步不离守在爷爷床前,等待爷爷的召唤。爷爷的嘴巴微张,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大姑坐在床头,一遍又一遍在爷爷耳边问:“爹,饿了吧,吃点稀饭吧。”问也是白问,爷爷已不能开口说话,可能连听觉也丧失了,更不要说进食能力。爷爷没有回应,大姑只好用滴管往他嘴里滴上几滴白糖水。大姑说,白糖水是最好的营养液,说不定能把爷爷救过来。对此,我和堂哥都表示怀疑。
说得残忍点,大人们在等着爷爷死去,等着料理后事。奶奶在十五年前就走了,送走爷爷,大人们就算完成了使命。可爷爷像在跟他们作对,就是不咽气。我念小学四年级了,从书本上学到了一些有关生死的道理。比如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之类的。可想到爷爷即将死去,我心里还是充满恐惧和悲伤。我希望爷爷突然活过来。就像好多次他躺在床上装死,吓我和堂哥。像现在这样直挺挺躺在床上,任凭我和堂哥怎么喊他,他都一动不动。直到我们被吓哭,他才猛然从床上弹起来,冲我们哈哈大笑。他总是说,爷爷死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是被死人这件事吓哭了,还是为我的死伤心而哭?我们就破涕为笑,在他身上一顿猛捶,骂他是骗子,是坏蛋。
现在,除了二姑,大人们都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了。
我爸是家里的老大,大姑排第二,底下是二叔和二姑。我爸在城里的初中当老师,教历史,戴着眼镜算是个文化人。大姑嫁到我们H县县城边上的农村,这些年被征地拆迁搞开发,洗脚上岸成了城市人。据说她家征地得了不少钱,在开发区买了三套房。跑得最远的是二姑,他们一家很早去了广东,在电子厂打工。如今在那边定居,彻底变成广东人了。二叔在家务农,爷爷也就顺理成章跟他过日子。
当然,我还有个小姑。如果她还在的话,还不到三十岁呢。
天黑之前,得到信儿的亲戚朋友陆续赶来,来跟爷爷告别。他们到爷爷床前看一看、站一站,跟大人们聊上几句。他们说,昨天还见老头儿好好的啊,怎么突然成这样了?大姑就一遍又一遍讲述事情的经过,像专业的讲解员。大姑说,昨天一早还欢天喜地上县城买手机,中午时分一头栽倒在街头,送到县医院说不行了,赶紧送市里。到了市里大医院一查,说脑溢血了,马上手术。手术还算成功,我们还想着很快就能好起来,接回家来静养呢。可今天早上医院突然下了病危通知,脑出血了没办法了,趁早接回家吧。人啊,就是这样,还不如一只蚂蚁一蔸野草。大姑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到最后就只剩下哭。来客们赶紧安慰她说,这就是命,你们老子还算有福气,要是在床上躺个三年五载的,那就是活受罪啊。
现在,一拨又一拨的亲友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一家人。
沉重的夜幕从天上垂下来,大地上黑得让人窒息。房间里静下来了,一盏枯黄的白炽灯悬在头顶,灯光微弱,如一泡黄尿,渗入黑夜深处。爷爷直挺挺躺在我们面前,像摊在床上的一把干柴。我第一次发现爷爷如此枯瘦、矮小。
大人们像丢了魂,除了唉声叹气,没一点办法。
大姑对我和堂哥说:“天黑了,你俩快喊住爷爷,不要让他走远,爷爷最听你们的话了。”
我跟堂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开口。
“快喊爷爷。”二叔催促堂哥。
“爷爷,起来吃饭啦!”堂哥冲着爷爷喊道。爷爷没有反应。
“你也喊啊。”我爸催促我。
“爷爷,起来喝酒啦!”我冲着爷爷喊道。爷爷还是没反应。
“嗓门大点,声音太小了,爷爷睡着了听不见。”
我和堂哥都知道爷爷的耳朵向来很好,平时我俩在背地里说悄悄话,讲他的坏话,他听得一清二楚。可眼下我们不能跟大人争辩,于是齐声大喊:“爷爷,爷爷。”
爷爷没有醒来,像是睡熟了,又像是装睡,在跟我们开玩笑,在吓唬我们。
大姑又哭起来了。好像哭泣和眼泪能把爷爷唤醒一样。
“你们看,爷爷变成这样了。昨天还活蹦乱跳像个猴子,还跑到县城去卖旧手机,那一袋子手机还在这呢。”大姑拿起床头的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给我们看。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旧手机,什么样的都有。”
地上散落着八九部旧手机,有老式的诺基亚、翻盖摩托罗拉,也有苹果机、山寨机、老人机。
“昨天早上还听他说一部手机能换一个盆,九部手机九个盆,这么多盆一辈子也用不完。”二叔说。
“晓得他有高血压,你还让他一个人乱跑?”我爸板着脸冲二叔说。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这一切都怪我?”二叔很激动。
“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爸红了脸。
“你就知道嘴上说,这些年你管过他吗?”
目前,两大全国性雕塑双年展就看到中国美协艺委会主导的“雕塑双年展”和中国雕塑学会主导的“中国姿态雕塑大展”交替举行,轮番登场。再加上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雕塑展以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雕塑部分,雕塑展的盛况令雕塑家目不暇接,过去那种雕塑展荒芜的情形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经常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同样的艺术家,同样的作品到处赶场,更多的雕塑作者在感叹应付参展都忙不过来了。
“我怎么没管?我按时给生活费。这回倒好,为了几个破盆把老命搭进去了。”我爸不依不饶。
“给几个钱了不起?这是你的义务!再说他也不需要你那几个臭钱。”
“臭钱?你又给过多少?”
“既然你这样说,那从今天起我跟你换,我出钱,你来服侍他。”二叔甩出了狠话。
“现在说这些晚了,没用了。”
“别吵了,要是让爹听见了,他会怎么想?你们真要让他老人家死不瞑目?”大姑赶紧出来劝架。在这个家里,数大姑最有主见,说话的口气最响。
“大哥,你也来喊喊,可不能让爹这样睡过去了。”大姑说。
我爸坐到床前,握住爷爷那干柴一样的手,柔声细语跟爷爷说话。他说:“爹啊,为你准备了好酒呢,快起来喝两杯呀。”
说着,我爸从床底翻出两瓶酒来。那是他带回来的老桂林洞藏三花酒。爷爷爱喝酒,每次回来我爸总给爷爷带两瓶酒。
我爸打开一瓶,酒香瞬间四溢开来。我爸对着瓶口咕噜咕噜喝下一大口,对爷爷说:“爹,你尝一口,这些年我带给你的酒,你可是一瓶也舍不得喝呢,全藏在床底下呢。”
我爸又喝下一大口,看着爷爷,不再说话。
晚上九点多,二姑终于赶回来了。几年不见,二姑也老了不少。她没顾得上我,进门就跪在爷爷床头一阵哭,说自己在外打拼,没尽到孝心,不配当儿女。又说得到消息,连夜赶动车,转班车,一路马不停蹄往葱岭赶,还以为见不上你老人家了呢。
“总算回来了,爹等着你呢,你看他活得多痛苦,你不回来,他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大姑说。
大姑又转头对爷爷说:“爹啊,二妹回来了,你开眼看看呀。大家都回来看你了,陪你了,你开开眼呀。”
现在,一家人都到齐了,就连过年都没这么整齐。大伙儿守在床前,阵阵呜咽响起。
挂在床头的五个药瓶打光了,像五个走气的白气球,无精打采。大人们又手忙脚乱去拔针头,贴止血贴。最后二叔把药瓶和针头扔到屋后的垃圾场去了。床头空落落的,顿时像缺少了什么。
“现在怎么办?还要叫医生来挂药水吗?”二姑说。
“医生说打完拔掉针头就行了,没必要再打针了,一切都没用了。”
大姑一声叹息,又拿起滴管,往爷爷嘴里滴了几滴白糖水。
晚风轻拂,秋夜有了丝丝凉意。大姑替爷爷盖上了薄被。被子是老式的,床单和被套上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道是牡丹还是别的什么花,隐隐透出平安富贵的气息。
“东西都备好了?”二姑又问。
“差不多了,也没什么要准备的。”二叔说。
“都是爹自己备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连遗像都挑好裱好了,一整套,全在衣柜里呢。”大姑抢过话来。
于是,大伙儿的目光全投向房门边的那个老衣柜。是那种传统的旧式衣柜,有一人高,漆成暗红色,在夜里看起来有点泛黑。底部的四只脚向外支棱,构成优美的弧度。两扇柜门上用彩漆描了竹子、牡丹、凤凰等图案,边上写有“花开富贵”“竹报平安”。
“那年开春娘生了细珠,爹一高兴就说要打一批家具,要让家里像一个家的样子,这柜子就是那年打的。”二姑说。
“那时我挺羡慕细珠的,爹为她打了那么多家具,我们几个都没那待遇,爹就是太偏心。”大姑说。
一说到细珠,大人们又沉默了。那是一个不可触碰的雷区。
细珠是我小姑。在我们家,小姑就是一个谜。大人们都说我长得像小姑,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对小姑的印象早就模糊了,像一个泡影。我只记得她跑过几年班车,那时我才七八岁吧。
小姑父是开班车的,那种乡镇常见的灰头土脸的中巴车,每天在我们五排乡跟县城之间来回跑。听说小姑就是在那趟班车上认识小姑父的。他俩好上之后,小姑就成了班车上的售票员。胸前挂一个小挎包,靠在车门边的钢管上,嘴里嚼着泡泡糖,上来一个乘客就收一份钱。那时候,我还挺羡慕小姑的,觉得她的工作轻松,还能免费坐车。有年我从城里回到葱岭过暑假,吵着闹着要跟小姑坐班车。我爷爷死活不让,他说车上那么多人,上上下下的,把你弄丢了我可负责不起。小姑父说,没事,就让他系上安全带,保证丢不了。小姑也说,这么大的孩子,哪那么容易丢,你就放心吧。我爷爷还想说什么,小姑父拉起我上了车。后来,我才知道爷爷不喜欢小姑父。对于小姑的婚姻,他也是极力反对,所以不想让我跟他们过于亲近。
印象中,那是我跟小姑相处最亲近的一次。到了县城,小姑父和小姑带我在县城中心广场的儿童游乐园玩了好半天,还吃了冰棍和棉花糖。小姑长得漂亮,出手也大方,不像我妈那样抠搜。中午,我们在车站附近一家饭店吃饭,小姑点了好大一桌菜。小姑不停地劝我多吃点儿,等下次你再回来,小姑就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到时你到我们家来玩呀。我说,好呀,下次我还跟小姑坐班车。小姑就笑了。她说,傻孩子,班车有什么好坐的,又脏又臭,以后我们坐小轿车。没多久,小姑就不开班车了。我也陷入了紧张的学业,我妈给我报了各种兴趣班,寒暑假也极少回葱岭了。偶尔逢年过节回葱岭,也没见到小姑。
突然有一天,小姑就死掉了。怎么死的,我不太清楚,只听见大人们在背后悄悄议论,说是服毒自杀。那时候,喝农药自杀在农村并不是稀罕事。可我实在没想到小姑会喝农药,她那么漂亮,那么要强,怎么可能会喝农药自杀呢。我问我爸,他总是回避。他说,小孩子管那么多干什么,读你的书去吧。那时候我还为小姑叫屈,家人怎么都不关心她呢?小姑的死也不能让爷爷知道,怕他接受不了,大人们都瞒着他。那时爷爷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脑子有问题,稀里糊涂的,老忘事。但忘事归忘事,他总惦记着小姑。逢年过节,家里人凑得相对整齐,唯独不见小姑,爷爷就问细珠呢,怎么老不回家。大人们说,客运生意好,每天都要跑好几趟,钱都赚不完,哪有时间回家。如此反复几次之后,爷爷就起了疑心。他跑到公路上去等,去拦开往县城的班车。他拦下一辆熟悉的班车,发现司机是一个陌生的光头佬,不是我小姑父。卖票员换成了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妇女,不是我小姑。我爷爷问那光头佬司机,师傅,韦小海呢?那位光头佬司机告诉他,韦小海不开车了,把车转给我有大半年了,他跑到海南捞鱼去了。我爷爷又问,那张细珠呢,她不当卖票员了?光头佬司机说,她啊,早就死了。爷爷本来还想问些什么,听那光头佬这么说我小姑,就很生气,他也骂了娘。那卖票员不耐烦了,冲着我爷爷大喊,喂,你究竟搭不搭车,不搭就下去。爷爷碰了一鼻子灰,被轰下了车。
爷爷一路骂骂咧咧回到家。质问二叔是怎么回事。又给我爸打电话,要他在城里找找关系,好好教育教育那光头佬司机。眼看纸包不住火,大人们只好顺势编了个新的谎言。他们说小姑跟人到海南捞鱼去了,海里全是鱼,赚大钱去了。爷爷居然也相信,于是满心期待着某一天小姑从海边回来,为他带回各种海鱼。他总是说,我真吃不惯海鱼,又腥又臭,太难吃了,味道远不及葱岭河沟里的土鱼。然而,有时他又会抱怨小姑。他说,不是说在海南捞鱼吗?大海里那么多鱼,就舍不得寄几条鱼回来?真是白眼狼。过后没多久,家里果然收到了来自海南的包裹,全是各种腥臭的海鱼干。这回爷爷满意了,笑着说,这还差不多。
可我爷爷还是担心小姑。每次说到小姑,他总是摇头、叹气。他说,细珠真是傻,天底下好男人那么多,多得就像海里的鱼一样,她非要找一个小混混,往后怕是要吃亏,看来细珠是个苦命人。
果然,一语成谶。
“难道爹是在等她?”房间里沉默了很久,大姑突然发话。
“谁?”
“还能有谁,细珠啊!”
大姑这话让全家人为之一惊。大家又去看爷爷,好像能从他脸上看到答案。爷爷像一根蜡烛,弱不禁风,但又极其顽强,豆大的火苗在风中摇摆却始终不灭。
“要是细珠还活着就好了。”
“细珠啊,如果你在天有灵,就给爹托个梦吧,让他安心地走吧。”
“或者,你化成一只蝴蝶,回来看看爹吧,爹在等你呢。”
大姑走向房门边的旧衣柜,打开柜门,从里面翻出一个木框。那是一个旧相框。发黄的玻璃底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相,都是家人们的照片,有全家福,也有单人照,好些已经模糊不清。
大姑打开相框,从中取出小小的一张相片。那是小姑的相片,确切地说是小姑小时候的相片。这也许是相框里小姑唯一的相片,八九岁的模样,扎着两根小辫儿,脑门光溜溜的,显得圆头圆脑,还挺可爱。
大姑把相片送到了爷爷面前。“爹啊,你看看,这是谁?你的细珠回来了,就在你面前呢,你看她在冲你笑呢。”
爷爷没有反应,他的呼吸更加艰难了,喉咙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整个上半身都被牵扯而不停抖动,像一台即将报废的旧机器。他的额头、脸上不断沁出细汗,仿佛连汗水都在逃离爷爷即将枯萎的身体。
“两天没吃东西了,哪里还有这么大能量。”
“爹真可怜,到了最后还要受这份苦。”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大姑说,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得找个人扮成细珠哄哄爹,反正爹也看不见了。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由我来假扮小姑。因为我跟小姑长得实在太像了。最近两年,就连爷爷也常把我当成细珠。他是老糊涂了,每次我从城里回葱岭,爷爷都说,细珠啊,你怎么回来了?下午不上课了?我赶紧向他解释,我说,爷爷,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不是小姑,我是你的孙女啊。爷爷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拍着自己的头说,哎呀,你瞧我这记性,我真是老糊涂了,连亲孙女都认不出了。尤其是每次离开葱岭回城的时候,爷爷总拉着我的手不放。他说,你才在家住几天啊,就要走了?我说,学校要开学了,我得回去了。爷爷一脸迷茫,他又仔细看看我说,回去?回哪里去啊,这不是你的家吗?我这才明白爷爷又错乱了,又把我当成小姑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想挣脱他的手。爷爷说,细珠,你别走啊,我不跟你吵架了,你走了我不知道上哪去找你呢。
“你就跟爷爷说说话,叫他安心地走,别再记挂着我们了。你看他现在这样多痛苦啊,看着都心疼。”大姑泣不成声,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眼睛像两只熟烂的毛桃。
其实不用大姑说,我也能体会爷爷的痛苦。有次我被鱼刺卡了喉咙,吐半天吐不出来,吞也吞不下,我想现在的爷爷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大人们七嘴八舌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已经失去了知觉,跟木偶一样,看见一张张嘴巴在我面前一张一合,我一个字也听不清。
我没法拒绝,如同一个怯场的演员被推上了舞台。实际上,我在语文课上演过课本剧《小英雄雨来》,演戏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在这样的场合出演小姑,实在显得怪异,或者说恐怖。
大人们纷纷站起来,为我让出一条道来。我感觉自己在大人们的目光中慢慢走向前,头顶有一道光始终追随着我,让我眩晕。我在众人的注视下,坐到了爷爷床前。
“爹,你开眼看看呀,细珠回来了,你不要担心她了,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大姑拉了拉爷爷的衣襟,轻轻地告诉他。
大姑把我的手塞进爷爷的手心。爷爷的手冰凉,僵硬,汗津津的,像一块被冷雨打湿的冬天的石头。
“爹啊,细珠同你握手了,你摸摸看,是不是你最喜欢的细珠啊。”
“细珠啊,你也跟爹说说话。”大姑对我说。
“你出去那么多年不回来,总得向爹赔个不是吧。其实,这也不能怪爹,当初爹要跟你断绝关系,只是气话,那是因为他爱你,担心你,希望你好。你懂吗?你怎么能怨他呢。”
我眼里一片茫然,一会儿看看爷爷,一会儿看看大姑。
大姑又说:“你知道吗?爹很快就后悔了,好几次要去找你,他说要跟你和好,我们没让他去。没多久他的脑子就不好了,糊里糊涂的。再后来你就干了傻事。这怨不得谁,这是你自找的。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当初我们大伙儿都像爹那样关心你,也许你不会走那条道。”
“爹啊,细珠现在不跑班车了,她赚钱了,开上大奔了。”
“细珠啊,这些年你都上哪去了,你跟爹说说啊。”
“细珠说她在海南打鱼呢,她还说在海南买了楼,等你身体好些,让她带你上大海边去看看啊。你还没看过海呢。”
我突然感觉到爷爷的手动了一下,像是用力抓了我一把,瞬间又松开了。我赶紧把手抽了回来。
“叫爹,快,叫爹。”大姑眼巴巴看着我,像在命令我,更像在乞求我。
我不知所措,身体像被人控制住了,像被点住了穴,好久都开不了口。
“快呀。”有人在旁边催促。
我感觉自己的嘴巴动了两下,声音却没跟上来,仿佛被我自己吞掉了。我又用力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后来,我的身子不听使唤地抖动,连呼吸都困难起来。
“爹啊,你看细珠哭了,她知道错了,向你认错了,她要跟你和好呢。”
“是不是?细珠,是不是啊?”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所有的压抑从胸腔深处冲上喉咙,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我伏在爷爷身上号啕大哭,我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泪水涟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出于悲伤,还是因为恐惧,也许二者兼有。等我在大人们的安抚下渐渐平静下来,恍惚间看见爷爷眼角沁出两滴眼泪,在灯光下一闪,很快消失在斑白的鬓发间。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走向门边的旧衣柜。我拉开柜门,一头钻了进去。
就在前些天,爷爷还跟我们玩过衣柜游戏。他最喜欢跟我们玩衣柜游戏。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玩法,无非是在柜子里躲猫猫。堂哥总躲在房门背后,很容易被找到。我喜欢藏进衣柜。柜子里黑乎乎的,给人安全感。每次爷爷都蹑手蹑脚走到衣柜前,隔着柜门大喊,我来了,你是不是躲在里面啊。呀,我看到你了,你跑不掉了。隔着木板,我似乎能听到爷爷的呼吸,既兴奋又紧张。然后,柜门被慢慢拉开一条缝,一道白光闪进来,将我暴露在爷爷面前。
爷爷说,你小姑小时候也喜欢藏衣柜。高兴的时候躲进去玩,躲猫猫,让大人们找不着。遇到事情伤心难过了,也把自己关进衣柜,在里面哭,生闷气,一待就是大半天。后来,只要在家里找不到细珠,大人们就去衣柜找。每次拉开柜门,小姑总躲在里面。
今夜的衣柜显得比平时更空旷,无边无际。我坐进柜子里,慢慢关上柜门,让黑暗彻底吞没我。我已经没有力气哭泣,也感觉不到恐惧,我只感觉到疲惫,从未有过的疲惫。
衣柜将我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隔着柜门,我听见大人们在跟爷爷说话,语气从未有过的温柔,充满绵长的爱意。我听见我爸在喊我。他说,你没事吧,快出来啊,里面太黑了。我没有理他,我往黑暗深处靠了靠,想在衣柜里大睡一觉。我实在是太困了,几乎是一闭眼就能睡过去。慢慢地,我感觉自己飘了起来,柜子里像灌满了水,把我整个人托起来了。
我在黑暗中渐渐漂远了。恍惚中,我听见有人在敲衣柜门。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那是爷爷的声音。他说,我来了啊,你是不是藏在柜子里啊,我要开门了。哈哈,我就知道你藏在这里。
“吱呀”一声,柜门开了,钻进来一个人。我费力地睁开瞌睡眼,竟是小姑。许久不见,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几乎看不出变化。小姑风尘仆仆,提着大袋小袋,像是出了一趟远门,又像出门逛了一趟超市。她在我身边坐下,我赶紧往边上挪了挪,给她让位置。小姑没理我,对我视而不见。我刚想叫她,我已经很多年没叫过她了,有些生疏。没想到她却抢先说话了。她说,爹啊,我回来了。我愣住了,她这是跟谁说话?然后,我听见爷爷的声音从柜子外钻进来。那个声音说,细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天都黑透了,全家人都在等你呢。小姑说,你不知道我赶了好远的路,一大早就出发,马不停蹄现在才到家。爷爷又说,人回来就好了,带那么多东西干吗,尽浪费钱,下次别买了。小姑又说,都是买给你的,怎么能说是浪费呢,以前没怎么给你买东西,是我不对呢。爷爷说,你这丫头啥都好,就是脾气差,不听劝……一定饿坏了吧,快出来吃饭吧,我们一大家子都还没吃饭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一阵急促的鞭炮声惊醒。我惊坐起来,喘着气,浑身冒出豆大的冷汗。过了好一阵,我才发现自己睡在堂哥家的客房里。我翻身下床,窗外仍是漆黑一团,葱岭像一个巨大的衣柜,柜门紧闭,密不透风。这时,我听见有人嘭嘭嘭敲门。然后,堂哥冲进房来。他跑得气喘吁吁,半天说不出话来。堂哥站在那里,显得高大,我突然发现他长大了,我有些怕他。我说,怎么了?堂哥一声不吭,拉着我向爷爷房间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