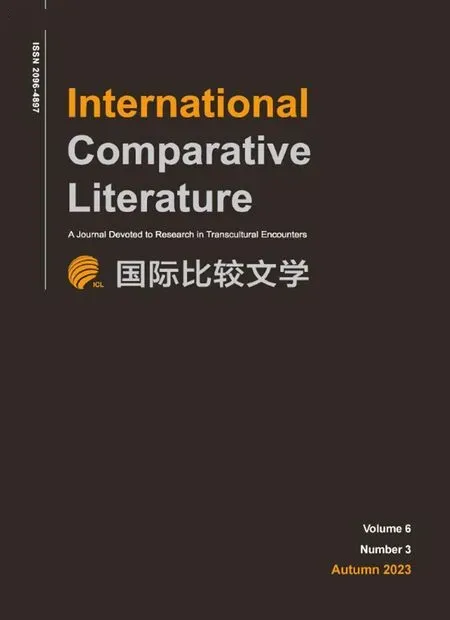“历史终结”抑或“历史重新开始”?
——解析达伦多夫冲突理论的思想架构和现实意义#
张庆熊 复旦大学
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2009)的“冲突理论”又风靡起来。人们回想起苏联和东欧解体时期他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争论。福山把柏林墙倒塌视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对以苏联为轴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而标志“历史终结”。达伦多夫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指出冷战只是掩盖了社会困局,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西方社会的各种内部冲突势必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而解决这些社会内在的冲突和矛盾才是历史尚待完成的真正任务,因而与其说“历史终结”,毋宁说“历史重新开始”。
达伦多夫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建构上,他还用他的冲突理论分析欧洲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如1968年欧洲的学生运动,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随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达伦多夫也参政议政。1968年,他任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自由民主党副主席;1969年他当选联邦德国议院议员,任外交部议会国务秘书;1970—1974年,他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1974年他移居英国,先后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和牛津圣·安东尼学院院长。达伦多夫的主要著作有:《透视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中的正义观念》(MarxinPerspektive:DieIdeedesGerechtenimDenkenvonKarlMarx,1952),《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SozialeKlassenundKlassenkonfiktinder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1957),《社会学的人》(HomoSociologicus,1958),《社会与自由》(Gesellschaft undFreiheit,1961),《走出乌托邦之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著作》(PfadeausUtopia:Arbeiten zurTheorieundMethodederSoziologie,1968),《现代社会冲突:论自由政治》(Dermoderne sozialeKonfikt.EssayzurPolitikderFreiheit,1994),《1989之后:道德、革命和公民社会》(After1989:Morals,Revolution,andCivilSociety,1997),《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DerWiederbeginnderGeschichte:VomFallderMauerzumKriegimIrak,2004)。
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吸纳了马克思的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学说,融合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论和波普尔(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具有广阔的包容性和思想深度。并且,达伦多夫是一位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社会理论家,他对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冲突和其他尖锐的社会冲突非常敏感,他关注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局势的演变。他的许多见解发人深省。本文以达伦多夫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批评为契入点,展示他的冲突理论在世界局势分析中的现实意义,然后解析他的冲突理论的思想框架,最后结合他对西方社会困局的诊断评述为何他的冲突理论相比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有助于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
一、达伦多夫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评
达伦多夫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的著作,今天读起来尤感发人深省。这一书名显然有意为之,针对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达伦多夫在该书序言中点明了这一点:“一位美国著作家发表了1989年标志‘历史终结’的论点,这简直骇人听闻。这一论点同时包含两个错误。”1R.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From the Fall of the Wall to the War in Iraq) (München: C.H.Beck, 2004), S.12.他认为这两个错误的理论核心是“历史目的论”和“非开放的历史观”。他指出:“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看,它遵循黑格尔的假设,即历史辩证地朝着一个必然的目标前进,这个目标虽然没有(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通过后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国家得以实现,但也随着西方的规划在1989年取得胜利而得以实现。”2Ibid.他指出福山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从背后观看”而不是从开放的前景看待历史事件。福山把1989年“看作几十年冷战的结果,看作冷战成功的结局”,而没有看到正是核武器笼罩下的冷战阴影掩盖和暂时冻结了对立双方各自存在的内在的社会矛盾,而冷战的结束使得这些内在的社会矛盾浮上水面,并开启了尝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新的历史进程。在此意义上,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标志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并不标志“历史终结”,因为历史总是面对新的问题和对新的尝试开放的。他批评福山持一种非开放的历史观,没有看到1989年的转机对人类历史带来的新挑战,因此他宁愿用“历史重新开始”来取代“历史终结”的论断。3Cf.Ibid., S.12-13.
“历史终结”这一提法出自福山在1989年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的终结?》。后来福山把这篇文章和相关的讨论合在一起发表了一本书名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论集。在该书“代序”中他重申:“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4(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Francis Fukuyama, Lishi de zhongjie ji zuihou zhi ren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rans.HUANG Shengqiang,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1.]并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福山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的那样,援引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论证他的政治观点。他坦承“对历史的这种领悟与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5参见同上书,第2~3页。[Ibid.,2-3.]
在此我们看到,达伦多夫与福山持两种针锋相对的社会历史观。福山的社会历史观是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他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具有合法性,所以它能够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现今的共产主义体制。福山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方式看待历史,他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而是从观念演变的逻辑出发。按照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寻求个体自由与社会整体秩序之间的平衡。以往的社会表现为主人拥有自由,奴隶被剥夺自由,但主人也要依赖奴隶的生产而生活,而奴隶则通过反抗企图颠倒这种主奴关系,历史就处于这种对抗和动荡之中。只有到了基督教新教的普鲁士国家,才赢得社会整体的秩序和公民个体自由之间的最佳平衡,从而社会历史完成了克服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对抗而达到自由与秩序之间的辩证统一。福山否定了马克思用历史唯物论对黑格尔的思辨历史观的改造,而采纳了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对黑格尔历史观的解释,即把主奴之间的对抗关系解释为社会各阶层为赢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在进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之后获得一种和平而有序的方式,从而能通过协商和选举等方式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因而社会历史从原则上说已经看到了终点。他认为,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模式相对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世界政治中的所有矛盾都将被克服,从而“历史终结”。
达伦多夫对福山的批评集中在黑格尔式的目的论的、非开放的历史观上。达伦多夫自称他不是像福山那样求教于黑格尔,而是“受教于波普尔”,他接受波普尔的开放的历史观,主张“历史总是对新的尝试开放的,这些尝试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6R.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From the Fall of the Wall to the War in Iraq), S.12.按照目的论的历史观,历史是由预先存在的那些观念或因素决定的,随着这些观念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展开和实现,随着这些因素导致的社会矛盾最终得到解决,历史将达到终极目标而宣告终结。按照开放的历史观,过去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理论对人类的行动会产生影响,因而对历史进程会产生影响,但不是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社会现实是基础,人类社会总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总会有新的事件发生,人类的认知总是有限的,人类总会推翻以往的知识理论而建构新的知识理论,总会不断更新自己对世界的意义的认识并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因而,历史与其说由已经存在的观念和因素决定,毋宁说是由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又不得不面临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开启的。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根本就没有终极目的,也永远不会终结。
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开放的历史观的分歧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1)是把意识形态或政治原理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社会现实放在第一位?(2)是把已经发生的过去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开放的未来放在第一位?(3)是用意识形态掩盖现实的社会问题还是直面社会实情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方案?
在福山的社会历史观中,政治原理处于第一位。福山并不是没有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但他把意识形态或政治原理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只要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决定性地确立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柏林墙倒塌标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从而“历史终结”。福山在其论文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序言中对他的“历史终结论”做了这样的辩解:“这并不是说当今美国、法国或瑞士等国家的稳定的民主体制已不存在不公正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则是因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并非原理本身的缺陷。或许当代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有些国家可能会倒退回其他更原始的统治方式,如神权政治或军人独裁,但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7(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第1页。[Francis Fukuyama, Lishi de zhongjie ji zuihou zhi ren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rans.HUANG Shengqiang, et al., 1.]
尽管从政治立场上说,达伦多夫与福山一样拥护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但他们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大不相同。达伦多夫不是从政治原理或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的现实问题出发。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为社会实际的阶级冲突等问题服务的,有时甚至会起到掩盖社会内部问题的作用。在他看来,柏林墙倒塌并非像表面看来那样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因为实际的社会结构问题要复杂得多。苏俄十月革命确实受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呼唤和推动,但列宁过世和斯大林当权之后,原先的那种共产主义的平等理念已经被暗中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获取特权和获得特供的等级制的官僚队伍的建立。在斯大林时期通过高度集中的权力和高效运作的官僚体制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得到提高,国民的收入在总体上是提高的,因此尽管普通的工人农民与特权阶层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国民在总体上还抱有希望。但是这种集权管理体制具有自身的严重问题:一方面要建立一支坚守政治纪律的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又要把具有专业知识的精英人士吸纳进来。但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顺从的和教义化的政治用人标准往往与具有独立思考和首创精神的人才标准相抵触。然而任何放松控制都包含着高度的政治风险,这就意味着不可能真正建立一支充满活力和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建设的管理队伍,从而不能不断更新先进的生产力和推动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苏联的后期阶段,官僚队伍中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官僚队伍成为一个只知道享受而缺乏高效工作积极性的特权阶层,这导致苏联后来在与西方高科技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这时戈尔巴乔夫搞改革运动,他企图把言论自由和经济结构重组结合起来,但是他失败了。他提倡“透明化”,这一下子把伤疤揭开(透明化)了,原来共产主义的平等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装饰品,在人民公仆名义下的特权阶层才是社会事实,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就这样自行崩塌了。
同样,西方社会也存在非常尖锐的内部矛盾。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存在尖锐的劳资冲突,后来西方国家通过福利社会等政策改善劳资关系;但新的社会矛盾又出现了,因为高税收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资本转移到低成本的第三世界国家,外来移民与本国居民争抢工作岗位。西方的政治领袖在冷战的名义下鼓励内部团结,把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鼓吹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想以此平息和拖延社会内部矛盾的解决。在达伦多夫看来,1989年苏维埃帝国及由它统治的卫星国的终结标志着现代史上的一个深刻的转折点,人们从此应该把目光转向解决社会内部矛盾上去,转向重整世界秩序和妥善处理种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新问题,并着眼于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达伦多夫在《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的序言的第一段中表明了这一观点:“1989的革命标志着现代史上的一个深刻的转折点。……突然间,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开放的社会的前景打开了。接下来的年代,无论从内部看还是从外部看,都受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化’过程的强烈影响。经济和社会条件必须存在于一种动态的光芒中,这种动态从根本上挑战了1989年之前几十年相当静态的期望,产生了巨大的希望和恐惧,创造了新的富人和新的穷人。在国际上,强权与弱势的轮廓越来越明显。像欧洲联盟这样的不稳定联盟试图与美国的霸权并肩作战,反对激进的反西方势力,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世界又处在动荡中。”8R.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From the Fall of the Wall to the War in Iraq), S.11.
尽管福山和达伦多夫都没有预见到眼下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和新的冷战威胁,但从他们对1989年事件的分析看,可以了解他们看待世界局势和社会政治的不同方式。下面我们转入解析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的思想框架,以便在最后一节结合他对当前西方社会困局的诊断,评述他的冲突理论相对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对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的现实意义。
二、阶级的概念和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的思想架构
拉尔夫·达伦多夫既是一位社会理论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出生在德国汉堡,他的父亲古斯塔夫·达伦多夫(Gustav Dahrendorf)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著名政治家。他出生那天他父亲正在发表劳动节演讲。纳粹时期他全家遭受迫害。这样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对德国社会矛盾、社会动荡、世界大战的观察和反思,催生了他的冲突理论的思想观点。他的社会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帕森斯和波普尔。马克思的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学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是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的思想构架的三个组成部分。达伦多夫把这三种思想资源融合起来,既表现出他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表现出他的思想中存在很大的张力。达伦多夫从马克思那里吸纳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用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只讲社会整体的和谐而忽视社会内在的冲突;他也是波普尔的学生,采纳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达伦多夫的这些观点是否能够彼此融通,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的地方。
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因为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学说是达伦多夫冲突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有关这一学说,达伦多夫从马克思那里汲取良多。达伦多夫区分“阶级”和“阶层”这两个概念。在他的用法中,“阶级”指涉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分类和承担的社会角色,而“阶层”指涉人的社会地位以及收入、威望、生活方式等社会状况。尽管“阶级”和“阶层”所涉及的对象是相同的,即都是社会中的人,但是对其进行社会考察和理论分析的视角是不同的。“阶级”是有关社会结构的重要概念,社会结构中阶级关系的改变将决定社会制度的改变。因此,阶级冲突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逻辑线索。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人存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宗教信仰、职务等级等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对这些差异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和描述是社会学家通常做的工作。但是如果社会学家的工作仅仅停留在对各社会阶层的状况做描述性的研究上,而不结合社会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功能和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那么他们的社会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阶级会从不显眼的社会角色上升为在社会结构的演变中起主要作用的社会角色。如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和农民是那时社会结构中的两个主要阶级,但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时期,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城市工商业主就跃居重要地位,他们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主导那时社会结构的演变进程。同样,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工会组织与企业家之间的斗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绝非工业化初期可相提并论。这也就是说,对阶层的社会学考察只有上升到社会结构的维度,即上升到“阶级”的维度,才具有社会历史的重大意义。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社会结构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会在其自身内部永久地、系统地创造出一些决定其变化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某些群体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现有价值观和制度的改变。”9R.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59), viii.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达伦多夫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有关阶级和阶级冲突的社会学研究受益于马克思开启的作为社会结构因素的阶级概念。他写道:“为什么我用《阶级和阶级冲突》作为这项研究的标题呢?也许有必要做一个解释:至少有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即卡尔·马克思,已经在上面谈到的思路上使用了阶级的概念。”10Ibid.
达伦多夫用这个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批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在他看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是一个人工的系统,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非一个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帕森斯没有看到社会结构的内生动力,没有看到社会结构内部滋生出社会阶级和社会冲突,没有认识到阶级和阶级冲突是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帕森斯设计了一套社会结构功能合理化的美好方案,但它缺乏现实的生命力和难以实现,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是靠权威来维系的,社会人不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总是在权威的压力下去承担某种社会角色,无论这种权威是当权者的直接的发号施令,还是借助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机制的隐形力量。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总有某个社会集团处于支配权力的位置上,通过强权来调配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居于支配地位者总想维持现状,而被支配者总想打破现状。当权者总会声称和论证自己的权威是合法的,而被支配者会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社会总是处于冲突中,权威的合法性总是朝不保夕的,社会冲突推动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权力关系的重组。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还有一个问题是只看到社会结构功能之间的协调的积极意义,没有看到社会冲突在社会结构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冲突理论主要从这一角度批判结构功能论。他们批评帕森斯只认可秩序、规范、共识、团结在社会中的功能,不认可冲突、失范、异议、矛盾在社会中的作用。殊不知后者并非全然是消极因素,没有后者就不能推动社会朝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进。社会结构并非本身是合理的,而是在社会冲突中通过社会改革才变得较为合理。在社会中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不公正现象、压迫现象。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和占据资产上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那些受压抑的社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他们的诉求被认为逾越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有碍于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受到打压。工人工资过低,农民税赋过重,少数族群受到歧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声,掌权者往往是听不进去的。社会功能关系不能替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由于权力关系的存在社会功能不可能得到自动的合理调节,社会结构功能的合理化在历史上一再是通过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革命的方式实现的。
达伦多夫采用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渐进的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来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反对社会改造中的“乌托邦工程”(utopian engineering)。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是与证伪主义的科学观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理论,一个学说,是否能被视为科学,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否被证伪。近代以来,人们接受科学和拒斥形而上学,并非因为科学成为一种高于形而上学的永恒真理,而恰恰是因为科学家把任何科学理论视为一种可证伪的假说。科学理论建立在观察事实和相关条件的基础上。由于观察事实总是有限的,相关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出现新的观察事实,发现变化了的相关条件,已有的科学理论就要被修正或推翻。这种情况对于社会理论尤其如此。这是因为自然界的条件尽管也在变化,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在社会中,由于人类行为本身所造成的社会条件变化经常是不稳定的,这就使得长期预测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社会系统是一个超大规模、超级复杂的混沌系统。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变量,这些变量交织在一起,影响社会局势的变化。这犹如气候变化,要预测台风的路线、风力、雨量等,要及时观察和计算相关的变量,才能做出准确的预报。虽然气象学家难以预告一年之后什么地方要发生多少级的台风,但是根据近期生成的台风气团及其流动趋向,还是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报的。同样,在社会领域中,对社会变化的长期预言非常困难,但在短期和局部的范围内,只要相关的社会条件相对稳定,依据对相关的社会因素的定性和定量的观察和分析,社会科学家还是能够在某个专门的范围内做出一定程度准确的预言,制定处理的方案。这也使得社会科学理论能够得到观察事实的检验,从而淘汰被证伪的科学假说,建立和接受得到验证的科学假说。有鉴于此,科学的社会理论是与“乌托邦工程”格格不入的,因为“乌托邦工程”罔顾客观条件,仅仅抱着美好的愿望对整个社会提出宏大的改造或革命的工程,这将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对于社会改革应采取“渐进的社会工程”,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随时观察其效果,并及时根据新出现的变量纠正偏差,调整方案,逐个地和逐步地解决社会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理论不要研究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和发展趋势,而是要警惕用思辨哲学来取代科学研究。按照达伦多夫的看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变革的逻辑假说”。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清楚地指出了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结构的弊端。他对国家阶级性质的分析也有很多意义”。11R.Dahrendorf, Pfade aus Utopia: Arbeiten zur Theorie und Methode der Soziologie (Paths from Utopia: Works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ociology)(München: Piper,1968) , S.330.但是达伦多夫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依然包含很多黑格尔式的正题、反题、合题的思辨哲学的成分,马克思的社会变革逻辑中包含历史目的论。具体地说,这就是社会历史被解释为一个从原始社会的平等到私有制社会的不平等再到公有制社会的平等的思辨的发展过程。在这种历史目的论的支配下,马克思主张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将导致工人阶级的壮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和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达伦多夫看来,在此把“平等”的理念放在历史终极目标的位置上,导致共产党人的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并以革命理想的名义拒绝对这一理论作社会实践成效上的检验。社会条件是非常复杂并不断变化的,人的价值观念也是多种多样的。平等固然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平等并非决定一切,社会正义中还包含自由等其他的指标。当实现平等的尝试危及自由时,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平等。
达伦多夫虽然承认阶级冲突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因素,但否认阶级冲突必然导致社会历史的进步。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大部分阶级矛盾的激化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是无谓的消耗,除了巨大破坏和流血牺牲之外一无所获。只有当阶级冲突与社会结构改良的契机相配合时,才能推动和实施有效的制度性改革,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和公民的权利职责,平衡地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使得社会大多数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真正实现社会进步。在很多情况下,社会阶级的成员并不一定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不很清楚应该如何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达伦多夫区分隐性的利益团体和显性的利益团体。隐性的利益团体的成员还不清楚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还不知道应该如何通过社会结构的改变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到后来,随着一些情况的发生,这些利益团体中的成员才逐步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特别是,当一些精英人士参与到这些利益团体的活动中之后,成为这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其组织性和思想观念的明确性就大大加强了。这时他们就组织成为显性的利益团体。他们能明确地阐发自己的利益诉求,能通过民意代表、法律申述、游行集会、媒体宣传等等方式表达和争取自己的权益,推动社会结构改革向符合他们自己目标的方向发展。在达伦多夫看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及其为追求各自权益的合法斗争。在人类的历史上,阶级冲突是推动社会结构改革的力量,但也是一再造成社会破坏乃至毁灭的力量。如何使得阶级冲突的损失最小,如何引导其有序、和平和明智地向着推动社会结构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是社会学家应该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课题。
达伦多夫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其中的一些新现象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这对我们具有参考价值。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指出达伦多夫依据这些新出现的社会情况对马克思的一些批判毫无道理。达伦多夫观察到在后工业化社会产业工人的数量减少和依据信息科技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人员增加,从而批评马克思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和产业工人领导革命的判断。我觉得这些新出现的情况在总体上仍然符合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社会关系变化的观点。至于在一百年之后将有什么新科技(如互联网)会发明出来以及会引发何种新的社会现象,这是谁也做不到正确预言的事情,没有必要苛求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依据新发生的情况做出新的分析。
三、达伦多夫对当前西方社会困局的分析
达伦多夫不仅应用阶级的概念对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做了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而且善于运用社会调查的数据对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现代社会冲突:论自由政治》(1994)12该书已有林荣远的中译本,见(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Ralf Dahrendorf, Xiandai shehui chongtu (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An Essay on the Politics of Liberty), trans.LIN Rongy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1989之后:道德、革命和公民社会》(1997)和《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2004)这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社会当前面临的困局的考察。发表在《利维坦》(Leviathan)杂志的《世界的衍生化及其后果——拉尔夫·达伦多夫80寿辰访谈录》(“Die Derivatisierung der Welt und ihre Folgen Ein Gespräch mit Ralf Dahrendorf zum 80.Geburtstag”)是我所见达伦多夫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该访谈录以2008年金融衍生品引发的次贷危机为切入话题讨论了这种危机的社会根源和相关的国际秩序问题。以下主要以这三本书和这篇访谈为依据,评述达伦多夫对当前西方社会困局的分析和他的冲突理论的现实意义。
按照达伦多夫的看法,政府的治理要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凝聚力”和“政治自由”这三个目标。在西方社会,这三个目标互相之间存在张力:要促进经济繁荣,需要通过减税等措施增强企业的活力;要增进社会凝聚力,需要提高社会福利,这需要加税,增加政府开支;要坚持政治自由,需要维护工会等组织的罢工、集会、游行等自由的权利,而工会等争取权益的运动推动增加工资和提高社会福利。这意味着三个目标互相之间存在牵制关系,很难同时实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凭借工业和科技的优势获得高盈利,有一定的实力采取福利国家的政策平息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凝聚力,有过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而目前西方社会已经积累很多问题,经济实力在下降,社会矛盾在增加,西方的社会决策面临困境:高福利因缺乏财政实力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又因激化社会矛盾而遇到阻拦,这使得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就像“圆的求积”那样难以实现。达伦多夫写道:“新的经济增长机会要求消除旧的障碍,并通过经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政策来放松僵化的条件。其中包括福利国家的改革,这使社会团结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面对这些挑战,自由社会的民主结构面临压力;威权主义的迹象越来越多,最大的问题是: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繁荣与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答案不亚于圆的求积,这也意味着它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往往在三个目标中只达到了两个,而第三个目标成为代价。”13R.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From the Fall of the Wall to the War in Iraq), S.103.
达伦多夫揭示了西方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困难问题,并从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党关系、国际秩序、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念的演变等角度对西方社会的难局进行了分析。我归纳了一下,大致可以罗列如下10个,但它们从深层次上说是交织在一起的。
(1) 后工业社会和新的社会分层原则
在二战结束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中,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其标志是社会生产向着一种由信息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发展。在那里,农业人口大都已在10%以下,有的在5%以下;同时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也在大幅下降;整个从业人员的 50%以上是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工作。如果社会是以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活动来表示其特征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已经为服务社会取而代之了,多数派阶级也是一个服务阶级”。14(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林荣远译,第178页。[Ralf Dahrendorf, Xiandai shehui chongtu (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An Essay on the Politics of Liberty), trans.LIN Rongyuan, 178.]在此,服务业这个概念有些混乱,它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指餐饮、商贸等服务业,而主要是指与知识与信息有关的服务业。由此可见,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社会的分层原则也发生了变化,早先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比重及其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下降,而掌握知识和信息的服务阶级成为一种新生力量,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业已变成了一种根基稳固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范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市场经济不再被视为一种由看不见的手左右的经济,而成为一种由进行管理的服务阶级根据知识和信息加以计划和调整的经济。高科技和信息化似乎为后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启无限美好的前景,但在达伦多夫看来社会分层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不同社会阶级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的不同,不仅会引起社会中的财富、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同时也需要调整与其权力相应的责任感。西方国家在经济布局、文化心态和国际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及时处理好,面临严重困局,这在根基上与这种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态势有关。
(2) 失业和劳动社会的问题
当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失业和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达伦多夫通过一组百分比数据说明这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在今天的大多数欧洲国家,从总人口看,大约有20%的人们未达到劳动市场向他们开放的年龄,另外20%处于退休的状态,有10%的人在教育机构里度过他们的时光。在所剩下的50%的人口中,有些人找不到真正职业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总是不能工作;如果设想这两部分人共计占15%极可能是不会错的。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还有10%失业,那么就只剩25%的工作人口了。而这25%的人扣除休假日一年大约有一半的日子是在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度过的。达伦多夫询问:我们还真正生活在一个劳动的社会里吗?
(3) 债务危机
当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希腊债务危机、意大利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等等,层出不穷。政府靠借债度日,政党领袖为了选票习惯于许诺增加工资,提高社会福利,当年财政收入不够,就用未来作抵押,靠负债填补当下的开支,这样政府的负债就越积越多。相当多的国家当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高达10%以上,而累积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则高达100%以上。这意味该国公民全年不吃不喝也还不清债务,而这终有一天会引爆危机,彻底压垮国家。
(4) 赌赛资本主义和金融危机
当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实体经济虚化和投机资本泛滥的严重问题。经济界人士不安心办实业,而涌向金融市场搞投机,滥用金融衍生品,终酿苦果。在达伦多夫看来,这种赌赛资本主义是靠负债滋养的,必须拿未来作抵押,而不是靠实体经济做支撑。借贷资本不是在被诚实的买家使用,而是在被投机者使用。随着金融衍生化的恶性发展,这种投资与实际价值的距离达到惊人的地步。银行家自己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包裹里有什么,交易员也不知道,它们已经无法测量了,因为它们是来自不同来源的碎片,然后被打包在一起。这样进行的期权和期货的交易终有一天会踩雷而暴跌,因为人们终会发觉这类虚空的未来价值不可能兑现。2008年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引发的次贷危机正是这种赌赛资本主义和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
(5) 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
当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危机。在达伦多夫看来,勤俭节约、艰苦劳动和先苦后乐等新教伦理促进了数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而最后却毁灭于当今的一种消费主义的消遣文化。不是生产,而是分配,不是创造,而是销售,主宰着当今西方人的生活。经济增长是要建立在努力工作和生产效益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消费主义会鼓励铺张浪费。当今的西方文化已经变成为基本上是享乐主义的文化,它与玩耍、逗乐和炫耀性的消费相联系着,而不是与勤劳、敬业和节俭等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相联系。这导致在当今西方国家生产成本很高,实体经济向劳动成本低的国家转移。
(6) 民主的阶级斗争和社团主义的官僚化
当今西方国家继续存在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呈现一种新的形态。在达伦多夫看来,在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阶级斗争表现为各派政党之间在议会等政治体制中的合法的斗争,因此他采纳了“民主的阶级斗争”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些政党依然具有阶级的基础,其中有的政党建立在下层阶级的基础之上,有的政党建立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基础之上。这种政党斗争原则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人们不是作为单一的个人行动的,而是作为多种形式的政党、工会、社团的成员参加行动的。斗争是由这些团体开展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继续存在的,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具有破坏性,也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等方式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既然是民主的抗争,就不应该称为“阶级斗争”。但达伦多夫认为这种政党斗争仍然有阶级的基础,并涉及改变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再分配,因此“为了民主的抗争也还要坚持阶级概念,这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15(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林荣远译,第142页。[Ralf Dahrendorf, Xiandai shehui chongtu (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trans.LIN Rongyuan, 142.]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种以政党或社团的民主抗争表现出来的民主阶级斗争很容易蜕化变质为一种“社团主义的反常行为”,“社团主义太过于容易同官僚体制进行结合”,它们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利益的卡特尔”,共同分配“一块大蛋糕”,尽管这是在民主体制监督之下的分配。“最后,政治党派、经济团体、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包括要求代表‘纯粹的消费者’的团体)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机构,构成一个惟一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大麻团,它们发现,如果它们不参与,将对它们不利。公民再也不知道,谁得到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的,虽然对于那些一定必须知道的人来说,有高工资的参谋顾问,对于那些很乐意知道的人来说,有政治学家。”16同上,第145页。[Ibid.,145.]这也就是说,当民主的阶级斗争退化为一种官僚化的社团主义的斗争之后,除了那些高工资的参谋顾问和政治家之外,广大公民实际上成为搞不清真实情况的民主的局外人,民主的阶级斗争变得与广大公民不相干了。
(7) 社会失范的风险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社会失范的风险。“失范”(Anomie)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 Durkheim)创立的一个社会学术语,描写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危机社会的规范失去效力。失范带来无序,失范的结果是人们失去一切约束,怀疑一切和对一切无把握。在达伦多夫看来,当前西方社会的失范是由于长期失业的人数众多、下层阶级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和文化结构崩溃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年轻人往往找不到工作,外来移民没有融入本地社会、文化虚无主义等因素导致文化结构崩溃。有鉴于西方社会的“博弈规则”(市场经济的规则、民主政治的规则、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和奖罚措施)主要是由中上层阶级制定和在主流社会中运行的,下层阶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感到他们没有参加进去,社会蔑视他们,社会不需要他们,警察和法庭都是用来对付他们的。而在多数派的主流阶级眼里,这批人贫困、懒散、游荡、犯罪;如果他们消失了,对社会有益无害。这些边缘群体抱怨记恨,不时起来反抗,街头暴乱,抢劫商店,焚烧汽车等等。失范经常发生在年轻人中,由于年轻人往往沦为失业者,对个人前途丧失信心,不去关心官方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而倾向于从边缘群体中引发出他们对社会的偏激和沮丧的看法。在达伦多夫看来,这种由于失范而发生的社会冲突不是有纲领有计划的社会革命,也谈不上是“民主的阶级斗争”,而是无序的动乱。西方的政治领导人对此感到头疼,但很少采取切实的措施阻断这种社会失范的社会根源。
(8)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运动和世界贫富两极分化
当今世界步入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但也出现逆全球化的运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是伴随世界范围的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如今生产资源、生产技术、金融、知识和信息都走向全球化,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和全球互联互通的格局。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和致富之路,它给一部分人带来巨额财富,然而也引发许多问题。这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采,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有可能我们正在把我们所赖以生活的星球变得无法居住。我们还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一部分国家的增长使另一部分国家落后了。相对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有了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大多数人的日子还是过得比较舒适的,只有少数人被排斥在外。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就世界全部而言仅仅是人类的少数,相当多的国家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很艰难,享受不到社会福利。跨国公司在原则上总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有的甚至贿赂当地官员。这与其说是在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不如说是在帮助独裁者们大发其财。还有一些跨国公司损害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生存条件,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当然,也有一些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发起改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状况的宏伟计划。但这些计划往往收效甚微,并未真正惠及广大下层阶级。在一些国家,由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复杂关系,全球化已经面临原教旨主义的(在错误意义上的“民族的”“宗教的”)极端主义的挑战。海湾战争、“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显然是与这种民族和宗教冲突相关的。在1989年之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和转型过程十分艰难,震荡疗法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引发寡头聚集财富和贫富差距扩大等新问题。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一旦出现经济萧条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抬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形成两种对抗势力。
(9) 对世界秩序的态度从康德哲学倒退到霍布斯哲学
当今的世界秩序面临困局,走上从康德哲学退回到霍布斯哲学的道路。这里的康德哲学指康德在《论永久和平》等著作中提出的通过建立国际法和世界公民社会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构想。这里说的霍布斯哲学指“丛林原则”。在达伦多夫看来,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国际规则目前不是在加强而是在遭到破坏。人们看到,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由权力而不是由法来决定。各强权国家都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其自己的利益,哪怕这样做要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西方世界的三大经济力量,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进行市场竞争,同时却很少关心规则。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和转型的过程产生种种阵痛,以前被压制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又爆发出来。一些伊斯兰教的极端势力在宗教名义下采取行动,旨在回复到原教旨的和现代之前的价值观中去。大多数国际组织相当脆弱。它们是一些“晴天组织”,在国际局势风平浪静时它们能发挥一些协调作用,做一些提供援助或贷款的工作,而当世界形势严峻时,它们就被排挤在一边。一旦面临大的利益纠纷,强权国家有不同意见时,它们就戛然止步。规则不是漂浮在空中,规则需要权力基础。国际组织的活动和规则的执行要靠财力和权力来维持。实际上,“二战”以来的许多国际组织以及相关的国际规则是在美国的策动下建立起来的。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认为它们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出钱出力支持它们。如今相当多的美国政客认为它们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就在美国利益至上的口号下,越来越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采取消极的态度。达伦多夫指出:“美国离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骤然结束国际海洋法会议的谈判,对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予理踩,降低它在很多国际组织里的代表级别,威胁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如果后者不能更好地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限制世界银行的自由,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机构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哪怕它们是由它在战后亲手创建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康德哲学又回到霍布斯哲学;民族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由权力而不是由法来决定。”17(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林荣远译,第157页。[Ralf Dahrendorf, Xiandai shehui chongtu (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An Essay on the Politics of Liberty), trans.LIN Rongyuan, 157.]
(10) 领导阶层、知识分子和全球精英的公共责任感及其丧失的危险
领导阶层、知识分子和全球精英的公共责任感问题,是达伦多夫非常关心又备感担忧的一个问题。晚年的达伦多夫谈到:“我个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我以前也关心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责任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如何让那些知道自己责任并根据责任行事的领导阶层承担责任,即对那些被托付给他们的人承担责任,这些人是直接受雇的人,但也包括利益相关者,现在更广泛地说,包括整个社会。”18Ralf Dahrendorf, “Die Derivatisierung der Welt und ihre Folgen.Ein Gespräch mit Ralf Dahrendorf zum 80.Geburtstag”(The Derivat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Consequences: A Conversation with Ralf Dahrendorf on His 80th Birthday), Leviathan 37 (2009): S.184.
达伦多夫对现时代的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他希望现时代的知识分子继续承担启蒙的责任,要在公共领域发声,关心现实的社会生活,为世界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分忧解难。他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反对对启蒙的新恐惧》的文章中写道:“知识分子要有公共责任感。凡在他们保持沉默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就失去前途。纵然知识分子中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在党派争论中选边站,纵然如果他们都扎堆站在某一边,那么事情就可能出错了,但知识分子有责任直言不讳,去发表关乎现实生活的考验和磨难的观点。到了二十世纪末,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启蒙契约也许不像以前那样具有魅力,但它作为一种自由的力量一如既往意义重大。”19Ralf Dahrendorf, After 1989: Morals, Revolution,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7), 112.就这种公共责任感而言,达伦多夫推重和称赞哈贝马斯的所作所为,尽管他们在建构社会理论的思路上有所分歧:“哈贝马斯作为学者的声誉使他为‘宪政爱国主义’或反对‘德国标签的民族主义’的呼吁变得更加重要。事实上,近年来,当德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受到挑战时,他在他的国家做得比其他的人更好。”20Ibid., 118.
达伦多夫在一篇名为《全球阶级和新的不平等》(“Die globale Klasse und die neue Ungleichheit”)21此文在2000年11月发表于 Merkur: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Denken (Merkur: A German Magazine for European Thought), 第54辑, 第1057~1068页,后收录于R.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From the Fall of the Wall to the War in Iraq) (München: C.H.Beck, 2004)。的文章中指出:全球化在加速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富国与穷国之间、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全球化正在培育全球阶级和引发新的不平等。在这过程中“全球精英”(globale Elite)责任重大,因为信息和知识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重要生产力,“全球精英”掌握最广泛信息和最高端的知识,引领全球的先进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全球精英”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跨国企业等经济部门,也适用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机构、大学、体育协会等部门。“全球精英”是当代社会中的一个动态因素,他们策划变革,推动变革。当然,这些主要是指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变革,旨在为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然而,对于全球精英的公共责任,达伦多夫感到失望。特别是当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批全球精英成为普通民众谴责的对象:他们拿着高工资,一派高人一等的气势;他们只对董事会负责,不对他们的员工和当地民众负责;他们在待遇和享乐方面互相攀比,躺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喝着香槟酒,策划金融骗局。在《世界的衍生化及其后果——拉尔夫·达伦多夫80寿辰访谈录》中,达伦多夫承认他过去的判断有所失误:“今天我不会完全这样看待它,因为很明显,那些推动金融资本主义的人,从某一点开始,走了一条与经济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的道路,导致了现在已经破灭的泡沫。”22R.Dahrendorf, “Die Derivatisierung der Welt und ihre Folgen: Ein Gespräch mit Ralf Dahrendorf zum 80.Geburtstag”(The Derivat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Consequences: A Conversation with Ralf Dahrendorf on His 80th Birthday), S.177.
有关达伦多夫对当前西方社会困局的分析,我罗列了10条。我在最后一个条目中谈达伦多夫对领导阶层、知识分子和全球精英的公共责任感的关注和担忧。有关公共责任感的问题看起来不显眼,但在达伦多夫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一旦丧失了这种责任感,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就会失去实践意义。我在本文第二节中谈到,达伦多夫的社会理论有三个组成部分:(1)社会结构功能的理论;(2)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3)科学的试错法和社会渐进改革的理论。有关社会结构功能的理论,达伦多夫从帕森斯那里学了很多东西,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和功效要通过社会结构功能的合理化来实现。但是社会结构功能的合理化不能仅仅通过人工设计的方式加以实现,因为社会的基础是阶级,社会结构的调整涉及阶级的利益冲突,是经由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方面,达伦多夫从马克思那里学了很多东西。然而,达伦多夫又认为,阶级斗争并非一定导致社会结构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阶级斗争,特别是暴力革命的阶级斗争,也往往成为社会的一种破坏力量。为此,需要知识分子采用科学的方法认清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引导不同的社会阶级认识到它们各自在现实许可的条件下可能获得的利益,从而使得社会财富的蛋糕适当地加以分配,如此才能既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又激发社会各阶层积极工作的活力。达伦多夫在此所说的“科学的方法”主要是指波普尔的“科学的试错法”。波普尔主张人非圣贤,人的本性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求全责备。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没有谁知道全部的答案,也没有谁知道哪些回答必定正确。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防止让答案教条主义化。在社会改革中,需要遵循错误代价最小化的原则,以社会实践中成效优劣的事实来检验我们的社会理论或方案的可取性,并在一个渐进的、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加以改进。最后,在达伦多夫把这三方面的学说的结合中,认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错误代价最小化的原则是要靠科学的认知来实现的。领导阶层、知识分子、全球精英,是关键的少数,他们起着认识非常复杂的世界和引领社会前进的关键作用。如果他们失去了责任感,那么达伦多夫的整个理论体系就遇到屏障,就失去了在实践中的价值。
我在本文第一节中把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做了对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挂帅,把坚持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正确的标准,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由意识形态的斗争决定的。达伦多夫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犯了历史目的论的错误,不能正视现实社会,而是起到掩盖社会内部问题的作用。毋庸否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受到当权的西方政治家的青睐,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发动“冷战”之类的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从而调动和联合西方世界各个阵营的力量,并掩盖他们的国家所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相比之下,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更重视全球化等现实的社会问题,并把务实地解决这些问题看成是真正的历史发展。他明确指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不止一个方面是荒谬的。事实相反,冷战停止了历史,而历史在冷战结束后才随着全球化进程重新开始。”23R.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From the Fall of the Wall to the War in Iraq), S.331.
我在本文的最后一节归纳了达伦多夫所看到的当前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达伦多夫坦言解决这些问题困难重重,犹如“圆的求积”那样难以圆满解决。事实上,当今世界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能成功地既提高了公民的身份地位,也增进了社会的凝聚力,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大多数晚近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经常被困扰在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频发的痛苦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理想化的善的王国和恶的王国,通向幸福的现实道路总是漫长而长满荆刺。这导致现代社会冲突不可避免地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主题。但他认为看到问题和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一切真正的科学理论正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达伦多夫的一句名言是:“社会学家总是忐忑不安的,但这也是由于社会生活对其来说总是忐忑不安的。”24R.Dahrendorf, Pfade aus Utopia: Arbeiten zur Theorie und Methode der Soziologie (Paths from Utopia: Works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ociology), S.94.达伦多夫自认为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行动的社会研究者。他自认为从社会冲突的现实中得出的最需要警醒的经验教训是:社会学家的工作与其说为建设美好的社会而提供蓝图,毋宁说为在社会冲突中寻找最少损失而在试错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
——电影《郭福山》主题歌(男中音独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