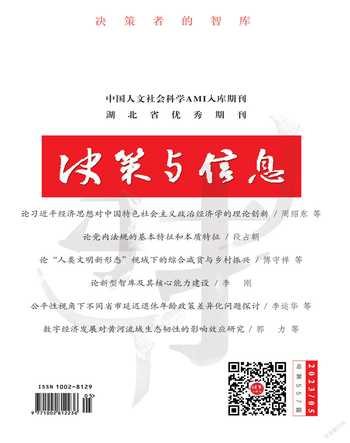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综合减贫与乡村振兴
傅守祥 魏丽娜
[摘 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的减贫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贫困、散点贫困、偶发贫困、能力贫困、代际贫困和精神贫困等成为“后脱贫”阶段的治理重点,治理方式向“综合减贫”转型,进入这一阶段,需重视后扶贫阶段构建“动态脱贫”机制、强化“精神扶贫”作用的问题,探索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民族地区的“绿色发展、生态减贫”。从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与长远战略来看,立足生态文明,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要结合地域特色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塑造减贫和乡村振兴的性别理念,将非遗文化与“女性赋权”相结合,为既有减贫模式提供补充和改进。乡村振兴要从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重塑与内生能力的逐步培养等角度持续发力,注重发挥各类新乡贤的积极作用、培育新乡贤文化,引导他们体现公共精神,顺应现代法治、引领地方发展。要遵循乡村变迁规律,让乡村的自然资源、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独特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当前,我们党以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生态文明转型,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和新发展理念,努力在更高层面追求共同富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乡村振兴;综合减贫;特色发展;新乡贤;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D2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5-0030-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2]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口众多,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存在,农业发展仍须持续提档升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因此,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的基本国策,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这一基本国策的有力抓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不断消除各种贫困现象,大力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时代责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政策演变,特别是精准扶贫方略实施后的脱贫实践成效显著、成就巨大。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全国上下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完成了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3],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4]的“脱贫攻坚精神”。随着减贫工作进入新阶段,针对民族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人口特征,我国还将采用超常规手段与创新机制结合,短期、长期帮扶结合的策略,短期内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长期帮扶的重点是解决现存贫困人口的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具有山高路远、资源匮乏、远离市场等特征,民族群众发展条件落后、贫困程度较深。因此,少数民族分布地区与深度貧困地区常常杂糅叠加,使得少数民族脱贫减贫及乡村振兴等任务艰巨。简言之,我国少数民族受区域地理、历史文化等影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制定适合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减贫脱贫新路径是一项重要课题。因此,我们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优越性,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构建互利共赢扶贫合作机制,坚持共享发展,全力推进综合减贫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实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进步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不但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低限”大幅度提高,不断创造“文明新形态”,而且在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可以说,中国“精准扶贫”的理念与实践,为全球减贫事业注入了信心、探索了路径,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实践提供了可靠经验。
一、“后脱贫”阶段的综合减贫与绿色发展
以2020年为界标,中国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难题,进入了缓解“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即“后脱贫”阶段。“后脱贫”阶段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绝对贫困”并非永远消失,它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死灰复燃”和暂时反弹,因此,巩固脱贫成果特别是与乡村振兴全面衔接意义重大;其次是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相对贫困”难题,其任务重心指向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即常说的“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产业扶贫更加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和特色化。毋庸讳言,有些脱贫户基本生活虽然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遇到风险变故仍有可能返贫。巩固脱贫成果,还需要政策和制度配套上的“扶上马、送一程”或“打通最后一公里”。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7]。
在“后脱贫”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形成的贫困治理框架中的许多理念和方法仍应坚持,但需要根据贫困的相对性等特征进行细致调整和完善。回顾历史以总结经验,中国的反贫困实践中仍然存在“精神贫困”问题突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解决“三农”问题与精准扶贫之间“缺位”的现实挑战等。立足新阶段反贫困实践的历史定位,必须要始终强化“精神扶贫”的作用,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和构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联动机制[8]。同时,扶贫理念应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消除“相对贫困”转变,构建“动态脱贫”机制;推进扶贫政策与农村发展政策融合,建立口径一致的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扶贫主体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转变,发挥各类主体作用。
毫无疑问,2020年是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时间节点,然而,贫困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贫困群体已经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物质贫困转为精神贫困,收入贫困转向支出贫困等。我国扶贫开发政策未来应坚持“兜底保障是基本,创新发展思路与方法是核心,补偿型政策是补充”的三大导向。因此,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的扶贫路径需要创新思维方式,开发新的扶贫模式,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民族地区扶贫将面临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经济增长的相对减贫效应大幅下降的难题,“福利依赖”及扶贫政策、低保政策衔接异化,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导致更多贫困人口从扶贫政策中漏出,以及文化的差异持续对民族地区贫困的减缓产生不利影响等挑战。
简言之,2020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后,减贫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相对贫困、散点贫困、偶发贫困、能力贫困、代际贫困和精神贫困等六类成为“后脱贫”阶段治理贫困的重点,新时期扶贫工作应从“精准扶贫”向“综合减贫”转型,扶贫机制从临时性、阶段性的政策性扶贫向常态化、法制化的制度性扶贫转变。为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该通过建立贫困标准动态调整、城乡减贫联动、扶贫社保融合、减贫良性互动的“四项机制”,提升贫困对象稳定增收、市场竞争、融入社会、抵御风险、自我觉醒的“五项能力”[9],力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综合减贫体系。
我国进入“后脱贫”阶段,改变贫困群众的传统活法,实现心态转变对贫困群体的正向形塑,切实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在精准扶贫中,“文化扶贫”要进一步加强,因为它发挥着“扶志”和“扶智”的重要功能,所以,未来的“文化扶贫”要紧密结合精准特点,首先做到目标精准,满足农民主体真实诉求;其次做到制度精准,构筑全面合理保障机制;再次做到措施精准,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真正实现文化软实力带动下的贫困村脱贫致富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建设目标。
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乡村振兴就是精准扶贫的升级版,只有通过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与精准扶贫微观施策的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因此,要统筹做好摆脱各类型贫困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衔接,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和无缝对接。当前,中国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与综合减贫“两手抓”,不能有偏废、搞取舍,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做好两者的统筹与衔接,才能更好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10]。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1],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会和过渡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12]。同时,只有抓紧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从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与长远战略来看,推进全面脱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立足生态文明,依靠绿色发展,突出生态启农、绿色兴农、质量富农,统筹考虑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农民生活,围绕着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创新体制机制,抓稳农民就业、农民增收。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13]。
在“后脱贫”阶段,像贵州、云南这类民族地区还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原则,因地制宜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切实有效地带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升级。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
二、脱贫实践衔接乡村振兴的文化产业与特色发展
在中国,人们已经很熟悉用文化产业“撬动”和助推脱贫攻坚;在“后脱贫”阶段,文化产业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依然作用巨大。2021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提供有力支撑[14]。乡村振兴离不开各方面力量的参与,作为产业扶贫与文化扶贫“交集区”的文化产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政策、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要素驱动下,文化产业以产业的强渗透性和民众的高认可度,通过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探索创新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构建完善乡村文化产业支撑体系、融合体系和共建体系,使农民共享全产业链增值的收益,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13]。
打造乡村文化产业最忌讳走同质化、复制化和低俗化的路线,要力求精准而有层次地把握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和时代性,注重地域文化的特色,保存乡土文化的味道,既要留得住青山绿水,又要记得住乡情乡愁。乡村文化产业主要围绕乡村民间文化传统和独特文化资源,利用现代经济理念和产业经营模式,发展相应的文化产业。首先,应该立足于当地的特色小镇、农业遗迹、历史文物古迹等,特别是那些具有厚重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古镇村落、传统建筑,建造一批特色博物馆、展览馆,提升乡村振兴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气质。其次,依托当地名人历史、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俗礼仪、传统手工藝等,打造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精品工程。此外,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除了依托乡村别具一格的原真文化特质,还要融入现代元素,使乡村文化重新焕发新的魅力。简言之,增强创新意识,积极探索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模式,要推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当前消费需求相一致,构建起集“山水观光、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商务会议、康体养生”等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化新业态,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美[15]。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优秀的农村题材影视作品为农村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宣传和带动作用,譬如近两年播出的《山海情》《阿坝一家人》《遍地书香》《江山如此多娇》等。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把文化旅游与精准扶贫、农业产业开发、农民就业增收等有机结合起来,助力脱贫攻坚,创新乡村振兴路径。特色乡村旅游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个重要突破口。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带领无数的乡村走向振兴,乡村旅游带来的市场经济效益,让农村的变化在短时间内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总和。在此背景下,各地方纷纷出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庄、特色小镇、乡村民俗和精品酒店等出现快速增长。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多限制性因素,因此,民族地区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注重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是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路径,对于提升整体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效率具有突出作用。
“互联网+”时代作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数字化赋能”是农村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推力;借助现代传媒兴起的直播平台,作为一种受众获取信息和特色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崭新方式,也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世代相传、与各民族人民实际生活密切联系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它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文化遗产。因此,开展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等产学研活动,培养非遗文化创新创意人才,是非遗文化活态传承和教育精准扶贫可持续、可复制的有效发展模式[14]。
从长远来看,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民族地区“非遗传承与女性赋能”的精准扶贫实践和特色开发探索,是将乡村全面振兴引向深入的成功案例。在不少民族地区,譬如湖南通道侗锦1,已经成功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女性赋能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传统女性的角色在家庭与社会中因侗锦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而发生微妙变化,进而推动形成人群扶贫、区域扶贫和经济薄弱村重点帮扶协同发力、互促共进的良好格局。
面对2020年后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减贫新阶段,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应引入性别因素,以应对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的现实要求,并释放贫困女性的减贫动能。“女性赋权”减贫作为当下国际学术界和减贫机构的普遍共识,在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积极的效能。该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也说明了其适用性,但如何在减贫政策的设计中加入性别因素、如何在赋权女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过程中应对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积极塑造减贫和乡村振兴的性别理念,加强“女性赋权”减贫理论的中国化,并在精准扶贫、综合减贫基本方略的指导下设计“女性赋权”减贫的相关政策,继而将“女性赋权”减贫作为一种嵌入机制,为既有减贫模式提供补充和改进,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完成。
三、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乡贤助力与共同富裕
除了精准扶贫将乡村振兴的低限大幅度提高之外,推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持续助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构建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体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就可以确保乡村振兴的顺利实现[16]。乡村振兴是新的发展阶段,一直持续到2050年,因此,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前面几十年的脱贫实践。
乡村振兴要从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重塑与内生能力的逐步培养等角度持续发力,遵循乡村变迁的规律,让乡村的自然资源、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独特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未来的乡村会是一个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一个高颜值的生态空间,一个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做事业的关键在人。精准扶贫靠能人,乡村振兴靠各界贤达,特别是各类新乡贤。新乡贤可以说是赓续文化传统、完善乡村治理的有益力量。要立足乡村实际,创优体制机制,搭建新乡贤议事平台,鼓励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公共事业建设,打造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促进乡村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与公序良俗的形成[17]。
乡贤文化植根乡土、贴近百姓,蕴含着见贤思齐、尊贤敬贤、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乡贤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乡贤文化则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千百年来,乡愁牵动乡贤,牵引着多少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重回故乡,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乡民树立榜样;他们散发的文化道德力量泽被乡里,成为凝聚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18]。
2015年和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条目;而“新乡贤文化”则分别被写进“十三五”规划纲要和2017年、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传承创新“乡贤文化”、留住乡村的“灵魂”已成为最近五年间的社会共识,“乡贤文化”与“新乡贤文化”成为全国关注的话题,“新乡贤文化”更被认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驱动力和人才支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新乡贤,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乡贤,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离土乡贤”,他们多是幼年在乡下长大,后来长期在外地甚至境外工作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科技精英、商务人士等,由于父母亲属的关系,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影响远且间接。第二类是“在土乡贤”,有一定文化基础,长居乡间,人品较好、威望较高。第三类是,生于乡下,后來求学、招工、招干后就在当地担任领导干部或从事其他工作,经常返乡,办事方便,照顾更多,影响近且直接[19]。第三类新乡贤包括那些当今乡村里公认的民意领袖,他们享有公共话语权,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群众很信任;他们通过服务村民、致富经营、参与乡村治理等,在乡民邻里间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塑造了良好口碑[18]。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是人才和文化的问题,应该特别关注这些“乡村草根英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民描绘了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20]的美好愿景。乡村振兴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跋涉,不仅需要资金、政策、人才,也离不开乡土文化灵魂的代代相传。乡村振兴的一项要义在于文化,文化传承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如何结合乡村实际,传承、弘扬与创新乡贤文化,实现传统“乡贤文化”向现代“新乡贤文化”的转变,重构乡村文化并助力乡村振兴[21],是值得不断思考和力行的。
当下建设“新乡贤”文化,还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乡贤应体现“公共精神”,以服务于大众的主观意识,对“乡民”起到良好的道德示范效应。二是新乡贤应顺应现代法治,从角色功能而言,新乡贤优势是借助非正式制度的民俗、道德、习惯、传统等资源而参与治理的。三是新乡贤应引领地方经济发展,面对现代化的飞速进程,新乡贤运用自己的学识、阅历、智慧和技能使自己和周边的人富裕起来。他们应利用其经济网络,撬动社会资本,选择正确行业,采取正确的方法发展经济;以规模效应引导周边的人效仿跟进,促进本乡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基层经济重组与发展[19]。
可以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形式由传统的维持乡村自治和实现礼俗教化,转变成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坚实的人才支撑。新乡贤不仅为乡村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而且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内驱力[21]。当然,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与建设,既要有开放视野,也要有不可或缺的底线思维;既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等市场鼓励措施调动积极性,同时,又要避免完全的功利化。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既要积极提倡、正面鼓励与有效保护各类新乡贤的“义举”,又要严防各类乡村恶霸或黑恶势力的出现。当然,提升乡土文化内涵,除了热心的志愿者和乡贤们外,还要发挥专业文化队伍的作用[17]。
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明新形态与共同富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2]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精神境界的历史性跃升、制度文明的全新缔造,以及社会有机体的有序运转[23]。同时,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2]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论断,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全新论断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实践基础、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探索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数亿人脱贫、全面实现小康只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中国目前仍然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精物差距”(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从社会治理层面上说,社会主义的最大吸引力就是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最大优势就是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共同富裕,实施更公平、更安全、更有尊严、更可持续的民生政策。事实表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们党正以“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带领各族人民持续向生态文明转型,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和新发展理念,努力在更高层面上追求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14]、创造“文明新形态”。
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24],其基本特征是富裕、均衡、文明、幸福,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多维图景。全国各地众多乡村将在实干、巧干、创新干中用源源不断的案例、素材、经验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实践范例,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探索新路、提供示范。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成为当下中国的发展目标之变。要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找跑道、定目标、建体系、抓改革”,强化“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忧患意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群众有感、可示范推广的标志性成果[27]。从物质富裕到保障富足、精神富有,我国乡村正瞄准各层次需求同步发力,打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通道,形成边探索、边实践、边回测、边迭代的良性发展生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7.
[2]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求是,2019,(11).
[3] 共鸣.大力弘扬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J].老区建设,2021,(3).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0-10-29.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2.
[6] 焦梦,孙芳,徐林,杨霄霄,陈路帆.国际权威人士点赞中国扶贫[J].民生周刊,2019,(4).
[7]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N].人民日报,2021-12-27.
[8] 邢中先,张平.新中国 70 年来的反贫困实践:历程、经验和启示[J].财经科学,2019,(9).
[9] 欧阳煌.精准扶贫战略落实与综合减贫体系构建思考[J].财政研究,2017,(7).
[10] 劉遵峰,张春玲.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N].经济日报,2020-09-15.
[11]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3-06.
[12] 王茜,卢东琪.立足绿色发展 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N].学习时报,2020-09-16.
[1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2-21.
[14] 魏丽娜.多样化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02.
[15] 孙喜红,贾乐耀,陆卫明.乡村振兴的文化发展困境及路径选择[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16] 魏丽娜,傅守祥.乡村振兴的文化产业与特色发展[J].当代贵州,2021,(49).
[17] 傅守祥.新乡贤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N].中国文化报,2019-04-15.
[18] 王婷.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浙江弘扬乡贤文化综述[N].浙江日报,2015-05-21.
[19] 傅守祥.乡村振兴视野中的温州乡贤文化创新发展[J].创意城市学刊,2019,(3).
[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21] 张百顺.传承创新乡贤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N].广西日报,2018-12-04.
[2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4).
[23] 项久雨.美好社会: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展开与演化图景[J].中国社会科学,2020,(6).
[24]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议[N].浙江日报,2021-07-21.
[2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6] 袁家军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上强调:勇担使命 塑造变革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N].浙江日报,2022-02-08.
[27] 张静,邢鑫.在高校思政课中讲好共同富裕的三重逻辑[J].决策与信息,2023,(2).
[责任编辑:甘小梅]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之新疆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培育项目“以‘文化润疆’深入推进新疆综合减贫和乡村振兴”成果。
[作者简介] 傅守祥(1970-),男,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文艺学研究;魏丽娜(1982-),女,安徽铜陵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与比较文明研究。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scattered poverty, occasional poverty, ability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and spiritual povert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governance in the stage of "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mode has transformed to" comprehensive poverty reduction ". At this stage, it is required to build a " dynamic poverty alleviation "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role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xplor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istantly align efforts to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in all-round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effort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realize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overty reduction” in regions inhabited by ethnic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long-term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to fully tap loc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and take the road of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It is required to develop loc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ies based on local features,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sm through poverty red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combining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s and women’s empower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poverty reduction mod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stant efforts should be taken to encourage the positve roles of country squires and models in their demonstration of public spirt, ,compliance to modern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leading lo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ultivate the culture of new country squires and models, while consider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entir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gradually fostering endogenous impetus.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pattern of rural changes and fully demonstrate the unique value of rural natural resources, custom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t present, tak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our Party leads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to continue to transform in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ully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 of new development, and strives to pursue common prosperity and creat a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at a higher level.
Keywords: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 rural revitalization ; comprehensive poverty reduction ;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 new squire ; common 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