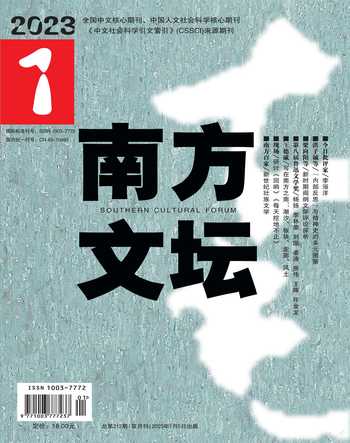幻术与索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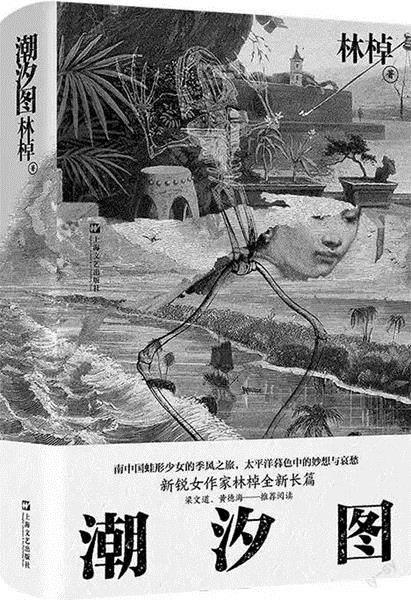
一
自称为“虚构之物”的巨蛙讲述了一个横跨广州、澳门、伦敦三地的魔幻故事,于是,便有了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如果说虚构是历史、现实的影子,那么这个用混杂的语言(普通话、粤语、皮钦英语的白话形式)讲述的时空交错的故事,已经用充沛的想象力化解了大多数可能追索至现实和历史的提醒。故事主角巨蛙曾说过:
万物有影子。浮槎是行星的影子。群岛是恒星的影子……
万物有影子。泪痕是旧事的影子。梦痕是新禧的影子。①
可以说,林棹用叙事幻术营造了一个奇幻与酷烈交织的平行世界。看到影子会探寻实物,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实物重要,而是因为需要某些参照来稳定视角,方能更好地审视影子的鬼魅和多变。正如在平行世界里偶然看到其间漂浮的疑似另外一个世界的碎片,抓住它才能不至于在审美中眩晕、迷失。有时审美也需要一种具有离心力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倘若“虚构”被视为某种幻术或障眼法,那它需要偶尔露出一些马脚或破绽,那是引领读者进入一个迥异世界的诱饵;而诱饵或引导同时也是某种拉开审美距离的平衡力量。因此,面对《潮汐图》这样高度依赖叙事幻术的作品,辨识审美风暴中诱惑与方向感之间微妙的反讽、张力关系便显得非常重要。所以,理解《潮汐图》不妨先从林棹主动释放的一些片鳞半爪的信息开始。
旅程已经结束。有时我会想念远方巨蛙。也会想念篝火旁的袋狼、猕猴、粉头鸭。一种被称为“自然”的巨大整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短促得我们只来得及取一瓢尝。
这是小说后记里的最后一段话。林棹怀想的是小说里的一个场景:雪夜桥洞下的篝火边,几个动物在聊天。
“人被咳嗽打败了,”粉头鸭说,“人大撤退。”
“人?撤退?诸位的屁股所在位置正是人的地盘。”
猴子和怪狗笑啊,笑啊。猴子笑得滚倒在地,怪狗笑得哮喘、舌头歪耷。“人撤退回恐惧洞穴,抱紧自己,”粉头鸭说,它的左脸对着我,“恐惧是万物的故乡。人走出去太远,忘了本。”
还在疫情中步履蹒跚的现实世界大概会让这样的魔幻场景显得过于讨巧、直白。但是这样过于急切的投射未尝不是审美褊狭的结果。BBC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The Year Earth Changed)。开头的旁白极其简洁地概括了主旨:
March 2020.A deadly virus sweeps around the world.Overnight,our lives are put on pause.But as we stop,remarkable things start to change in the natural world.Cleaer air.Cleaner water.And animals starting to flourish in ways we hadn’t seen for decades.(2020年3月,一种致命的病毒席卷全球。一夜之间,人类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随着我们人类停下脚步,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情。空气更清洁了。水更干净了。动物开始以我们多年未见的方式繁衍生息。)
简单说来,这部片子非凡之处在于,它试图恢复一个真相:人类退场之后,或者当人类的进程被相对抑制之后,万物和自然的样子及声音被重新发现。尽管从未说出口,这部片子的潜台词却始终穿行于影音之中:人类既不是自然,也不属于万物。人类被排除物种分类之外,是自然的天敌和入侵者;所以,在人迹消失或暂时中断的地方,鲸歌、鹿鸣、豹吼重新充盈了生命的欢愉和奔放。从这里再回望那个动物夜谈的场景,它所以显得魔幻,是因为有些真实一直游荡于我们狭隘的经验范围和审美边界之外;它之所以被急切地投射于现实,也是源于人类只关心自己的命运和生死。有趣的是,在这场魔幻的对话中,动物们还未完全将人类排除于万物之外,只是看到了人类背影渐行渐远。所以,当林棹感叹“一种被称为‘自然’的巨大整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时,她的眼光早就越过当下,投向一个并不太久远却恍如隔世的过去——那个时候,人类发明的“现代”还在小心翼翼地在试探,还未生长成垄断这个世界的不可撼动的权力和秩序。那个时候,已经见识过庞大的三桅帆船的巨蛙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还深深地陷在被“一块巨铁逆风疾行的景象”暴击后的困惑与震惊之中。
巨铁涅墨西斯号逆风疾行,一根黑亮巨管从她腰间冲天凸起,想要轰天!但没有轰天,只是持续地喷吐黑烟。她发着一种破天荒的怪声越逼越近,一连七夜,那怪声回荡在所有人的梦里。
…………
我们一路顺风……但终究未能躲开困惑。铁块如何能够逆风疾行?那就是风和帆的终点了。
晚年的巨蛙偶尔撞见了两个时代的擦肩而过。木质巨舟、三桅帆技术,是大航海时代最后的辉煌。“巨铁”与“黑烟”关联,所隱喻则是铁甲和蒸汽机结合而成的“工业革命”机械巨兽。航海史上“蒸汽时代”对“风帆时代”的覆盖,即是“风和帆的终点”,其实亦是“现代”呼啸而来的一个侧影。虽然要等到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的轮廓才逐渐清晰。但是在那一刻,巨蛙依然瞥见了庞然大物主宰未来的样子,这对于她的时代而言,确实“有如世界末日”。
其实不妨对一些影影绰绰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廓清。林棹自陈运送巨蛙的“世界号”原型是“邦蒂号”(HMS Bounty)。稍做检索,便不难发现,HMS其实是Her or His Majesty’s Ship的缩写,意为皇家舰船。当然,对于很多爱国者来说,它还是Huawei Mobile Services(华为移动服务)的缩写。这艘服役于18世纪末的舰船之所以扬名至今,除了因为它的传奇性轰动了整个欧洲,还因为它的兵变故事曾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克拉克·盖博(1935)、马龙·白兰度(1962)都曾主演过《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的不同版本,梅尔·吉布森、安东尼·霍普金斯、丹尼尔·戴·刘易斯、连姆·尼森都还比较籍籍无名时也曾联手演绎过这个题材(the Bounty,1984)。了解了这些,好奇心会继续发酵,“巨铁”被命名为“涅墨西斯号”意味着什么?它有原型吗?涅墨西斯是Nemesis的音译,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恰好,有一艘名叫“复仇女神号”②的英国皇家军舰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更重要的是,“复仇女神号”还是英国的第一艘铁壳战船,且是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军舰,而这艘军舰恰恰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建造。林棹不是还提到小说人物H“脱胎于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群像”吗?
这里并不是要通过种种钩沉和索隐来谈论林棹如何将历史变形、重组,而是为了说明林棹营造的奇幻氛围与这些背景或者说历史的碎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便其间的关联气若游丝,那也是把形态缥缈的故事相对塑形的有效途径。幻术需要边界,魔法也有限度。由此反观,小说里“世界号”与“涅墨西斯号”的相遇显得意味深长,这部始终悬浮于奇幻氛围里的故事终于有了历史锚点的牵绊。所以,“巨蛙”其实是那个预见新世界即将不可避免地来临,却又见证了旧世界最后的风景。这样的时刻后来在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确认。
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疑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如此。大约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的较晚时期,人们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③
这里并不是要给一部虚构之作划定确切的历史边界,而是要为一个不断飞翔的故事建造可供其偶尔停歇的驿站。有了这些驿站,那些过渡时期风景、故事中丰富、驳杂的意味才会相对清晰地展示出来,这其实也是一种提醒,越过那些驿站之后,有的故事便永远不会发生了,有些风景也就彻底消失了。
二
叙述者巨蛙自称为“虚构之物”,但是层层叠加的幻术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所有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皆是虚构之物,不管其形象是否为人。在幻境之中,草木鸟兽、魑魅魍魉皆能开口说话。因此,叙述者的腔调和形象设定首先是个技术问题,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如何富有成效地进行内容输出和意义传达。比如,巨蛙的生死大限、来源和归宿、形象变化、语言天分等方面的模糊性恰恰是叙述中复杂的时空切换所需要的。但是,所有的技术问题都无法独立存在,终将服务于故事形态及其隐喻的生成。
当巨蛙在小渔村被捕捞出来的时候,那些围绕着她的诸如来源、性别、名称等属性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有叙述者开始讲述古粤之地的故事。大概是因为属性模糊而散发的神秘性,使得巨蛙被视为通灵异兽,并成为粤地祈福消灾的巫术中的重要法宝。正是在这些仪式性的场景中,古粤之地的风俗、语言、自然和日常得到了戏剧性的呈现。所以,当供奉在祠堂船上的巨蛙断尾消失时,其实也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观的消失。
断尾失踪在一八三二年。那时我已远在澳门了。
这个年份是旧风景开始消失的时刻。在被带到澳门之前,巨蛙被海皮的英商捕获。“海皮”在粤语中是海边的意思,而有着“十三行街”的海皮则为有着特定历史意味的地理空间,只是这里的“海”指的是珠江。明白了这些含义,便理解了何以断尾的消失其实便是风景的消逝的隐喻。
在《海皮自然史》的段落里,林棹写道:
……旗人骑土马而来,给海皮抹一种全然独特土层。……旗人在街口、桥头建哨所,又向江边摆设税馆。他们给草包套制服,插向海皮吓人。
海皮住客有:红毛鬼、白头鬼,花旗鬼、荷兰鬼,瑞国鬼、马拉鬼,佛朗机鬼、法兰西鬼,个个在海皮开公司,被立夏南风吹来,被立冬北风打去……
有十三行商行夷馆,收留寰球番鬼和番鬼公司。有海皮四街……有让人大开眼界的一切,唯独无番鬼婆。
一些历史的棱角还是在这个依然充满绵密修辞的章节中破土而出。所谓“旗人”涂抹的“独特土层”,提醒着特定的历史实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广州是晚清政府唯一对外贸易通商口岸。所谓“十三行”是对朝廷特许从事中西贸易的垄断性中介机构的习惯性统称,这些行商半官半商,在贸易上居于中外商人之间,在外交上居于清廷与外商之间④。外商來到广州只能居于由十三行开设的行商会馆(“夷馆”)中,且行动要受到种种监管。乾隆二十五年(1760),《防范外夷规条》颁布,其中规定“夷商在省住冬,永行禁止”⑤,就是说,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于是,便有了引文中的“被立夏南风吹来,被立冬北风打去”。这些规定在执行过程可被酌情处理为暂居澳门。小说的第二部分《蚝镜》也就从历史的枝丫中长出。嘉庆二十四年(1819),则有禁止外国女性进入“夷馆”但可以居留澳门的规定⑥,这其实是对此前相关禁令的重申,所以,熙熙攘攘的海皮“唯独无番婆鬼”。值得一提的是,同年颁布的禁令中还有一条是禁止外商乘船游河。这便解释了H和他的同伴何以要装扮成当地人模样、鬼鬼祟祟地穿行于珠江。正是那一次冒险,他们撞见了巨蛙,故事从此有了新的转折。高蹈的想象力和繁复的修辞相互缠绕的虚构之作,总是在历史的奇崛处轻轻借力并继续飞腾,这正是《潮汐图》的迷人之处。
由此再回望巨蛙断尾消失的时刻,其实那是中国进入条约制度之前华洋杂处相对平和的短暂时光。这样的过渡时分,同时也是古粤之风注定消失的前兆。就像H与巨蛙初次相遇时说的那样:
你知道吗,蛙,你的掘尾,你的疤痕,即将蜕去、与你永别。你将要失去它,似失去故土那样失去它。
这样的话看似是压抑好奇与兴奋的轻声细语,其实暗含贪婪、攫取的侵犯意味。如果说,巨蛙暧昧不清的身份和起源,在敬畏神灵的古粤之风中多少意味着通灵异兽;那么在帝国冒险家H眼里,它只是有待识别的未知物种。这样的相逢,其实是两个世界开始交接的时刻,崛起的新世界开始对旧世界进行吞并和祛魅。
“H即将到埠。”
“哪个H?”
“哎呀,从来只有一个H——那个H。”
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半数番鬼出离楼面、涌上广场。珠江面上船挤船,艇挤艇,连成平原街市。……等到H本人,滋悠淡定,搭女猎手号入黄埔,换驳艇,溯江而上在海皮渡头泊岸,广场上已站满四方番夷并一支业余管弦乐队。
H登陆海皮时的盛况与其说是因为其个人经历的传奇性,倒不如说是其传奇经历所隐喻的帝国扩张的形象。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地理大发现主要由葡萄牙、西班牙完成。因此,16世纪和17世纪,它们分别具有在东方的优势。直到18世纪,才开始了英国头角峥嵘的时代。”⑦于是,H在海皮的出现更像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新世界景象和秩序的降临,只不过此时的帝国野心还需要无畏生死的冒险家和求知若渴的博物学家这些形象来修饰。货架、博古架、解剖台、谱系树以奇异的方式拼凑着帝国彼时的表情,正如那些商船其实都是经过改装的军舰。
巨蛙撞见了伪装掉落的过程:她发现博物学家对新物种的痴迷和冒险家对新发现的兴奋最终都落实于标本。在行商会馆的标本仓库里,巨蛙曾感叹:“人颇费了些心力智力忤逆天然、维持那种罕见的干燥。”她也看到“以科学为名”如何使血腥的场景面变得“合法正当”。
欢迎参观我的尸体、我的脏器,和这一套加诸我身上的酷刑。
真相的震荡让巨蛙昏厥,清醒紧随其后。按照通常的理解,“科学”是“现代”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及其制度构成的重要部分,它起步于对“不朽”的祛魅和批判,从而获得了历史进步性。然而“标本”却揭开了“科学”对“不朽”的戏仿、改造这种隐秘而荒诞的真相。严格说来,“标本”的原始起源与古典关于精神“不朽”的敬畏和追求有关,是在生命和自然停止之处的继续探寻。而“现代”标本的制作前提恰恰是以“科学”为名对生命的主动杀戮和对自然的强力遏制。以知识传播为名的保存和展示,掏空了生命和肉身;原始、野蛮意义上对战利品的占有和炫耀重新装饰了标本的光鲜形象:它们互为表里,让标本成为可流通的象征性占有和炫耀,成本昂贵却需求强烈。于是,作为替代性的“不朽”,标本便成了殖民贸易中的重要物品之一。这样看来,新世界商业文明的源泉和动力竟源自旧世界的暗黑的心,在这里现代的知识和教化毫无用武之地。用巨蛙的话来说:“野心家们做梦都想将神爷火华制成标本,卖个好价钱哩。”“爷火华”是“Jehovah(耶和华)”的音译,最初来自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中文译本《神天圣书》(1823年)⑧。如此看来,大概“标本”是最能代表“现代”弑神本性的象征物吧。所以,野心家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就像能够弑神的人之间的相互致敬。正如H对一位标本制作师的无限怀念:
老鲍啊老鲍,你把一生赌在谁也讲不清楚的东方,为帝国搞到近千件标本,还有上百件不走运的活体(包括那十六只从美国人手上买得、星星般震颤的蜂鸟)死在海上,而你死在苏门答腊。尸体好歹弄了回去:用橡木桶装着,用朗姆酒浸着。
在19世纪的上半叶,福尔马林还未被发明出来。所以,殖民者通常采取一种比较古老的方法,把需要运回故国的尸体浸泡于烈酒中。想象一下帝国乘风破浪的三桅帆下的真实场景:标本、死亡的动物和客死的冒险家排列于货仓,如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放于货架。帝国的荣耀来自商业的繁荣与死亡的堆积之间的隐喻关系。每一件标本都意味着一次杀戮和死亡,同时也会成为被掠夺之地的记忆见证和历史创伤。而那些浸泡于烈酒之中的冒险家们和他们的事迹固然会被帝国视为历史的英雄和“现代”的伟业,却仿佛在为历史的刽子手和“现代”的罪恶保留鲜活的罪证。制造、收集创伤并将其展现为“现代”的进步勋章,大概就是帝国成长之路的秘密。
三
多年以后,H死于澳门,仿佛是老鲍的故事的再次上演。稍有不同的是,老鲍热衷于搜集尸体,而H倾心于“炫耀性圈养”,他建造了“好景花园”来安置那些从世界各地捕获的动物。“好景”这个名字大概是根据澳门比较古老的名字之一“蚝镜”的谐音而虚构,而巨蛙的澳门故事亦被命名为“蚝镜”。
巨蛙在“好景花园”里终于获得了明确的生物学身份:Polypedate giganteus,用巨蛙自己的话来说:“他它是一道印黥,使我暴露,使我永恒区别仍然隐匿的万物。”这个命名与小说中提到的瑞典人卡尔·冯·林奈的生物学著作《自然系统》有关。林奈开创了“纲、目、属、种”生物分类法和“二名法”(又称“双名法”)物种命名法,其中的合理之处至今还被沿用。Polypedate giganteus盡管是林棹虚构,却遵循了标准的二名法:前者为属名,是拉丁名词,对应于英文polypedatid,在这里不妨简单地理解为“树蛙”;后者则是种名,是拉丁形容词,对应于英文gigantesque,可以理解为“巨大”“巨型”。这便是中文“巨蛙”的来源。这种命名建立于分类等级从谱系树根部自下而上的逐级细化。倘若把Polypedate giganteus逐步追溯到更大的分类范畴时,它将依次遭遇“无尾目”“两栖纲”。可是,巨蛙明明有一条尾巴,只是被契家姐砍断了,且H初次见到巨蛙时,便注意到她身上残留的“掘尾”。“掘”在粤语中有“秃”或“断”的意思。
这便意味着巨蛙获得命名和身份的时候,她的尾巴再次被砍断,这次是以知识的名义:断尾消失于知识中。“现代”依凭知识分类及其命名权对世界进行了重新辨识和解释。依凭各种知识体系重建秩序的世界看上去透明、清晰且不失复杂和多元。这里固然存在着“现代”的进步性,但是,“现代”看不到自身的局限和知识的傲慢:世界在知识中生长,是“现代”的自我想象——“帝国梦想重新发明世界”。就像巨蛙观察到的那样:“(谱系)树有自发的热望:伸张直至吞下宇宙万物。”因此,被感知、被呈现的世界,哪怕再丰富,也是被知识打磨、切割、重新塑形的结果。世界与被知识包装过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深渊。那些居于标准、秩序之外的事物,或者说无法被知识解释、塑形的未知,要么被削足适履地强行收编,要么被抛回幽暗之处。
巨蛙第一次被断尾无疑是种残忍的肉身伤害,虽然这与对神秘、未知的敬畏相关,但毕竟是野蛮、粗暴的行径,它们共同指向某种与“自然”相通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景观。所以,不妨将那截断尾的消失,视为“现代”对“自然”改造的结果。尽管这样的事情在巨蛙的记忆中充满伤怀的怀旧气息,但依然多少包含着“现代”的历史进步性。而巨蛙的第二次被断尾则是无形的、象征意义上的抹除,体现着“现代”的狭隘和知识的残暴。这是“现代”将在往后岁月里逐渐展现的另一面。“现代”将携带着他引以为傲的知识和秩序,信心满怀地对世界潜在的可能和隐秘的未知进行无知无觉地清除,在这样的过程中,“现代”及其知识、秩序扩展自身边界、反省自身局限的很多机会也会消失于无形。当“现代”变得愈发刚愎自用、沾沾自喜的时候,当知识丧失对隐秘、未知的好奇和敏感这些动力时,世界也就成了知识牢笼里奄奄一息的死囚。当然,在“现代”目空一切的眼光里,那可能就只是一只躁动不安、有待驯化的野兽,也可以是闲暇时可供赏玩但并无多少神秘感的奇观。
于是,在巨蛙成为Polypedate giganteus之后,便有了专职饲养员,毫无意外地成了动物、宠物和玩物。巨蛙把一切看得通透:“我和寰球之蛙将组成风景,供智人远眺、自恋。”巨蛙的澳门时光里唯一值得留念的地方在于:在某些时候,她尚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华人画师冯喜结伴夜游。巨蛙半人半兽的暧昧状态,对应着“现代”与“自然”最初遭遇时的那种混沌状态。巨蛙被标识为动物之后,也就意味着她被“现代”踢回了“自然”,以“现代”为名的物种区别和等级设定,使得巨蛙成为有待征服的对象或有待驯化的目标。所以,H的情人明娜会对巨蛙进行种种礼仪培训、服饰装扮,并教会她如何通过表演来讨好主人和客人。直到巨蛙与她的专职饲养员在伦敦(小说中所谓的“帝国心脏”)的帝国动物园分别被标注为“巨蛙太极”和“满大人”。澳门时光里由“一条锁链”所建立的驯化关系,便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臣属关系,种族、文化优劣等级关系的预演。至此,那些最终掌控整个世界的“现代”的种种知识和秩序已经基本显现轮廓。
巨蛙从海皮到澳门再到伦敦的地理空间位移,本是一个从“自然”逐渐靠近“现代”起源地或“文明中心”的过程,巨蛙的身份识别却经历了逐步降格:从通灵异兽到人类伴游再到豢养之物。两个过程并不矛盾:巨蛙在地理空间里流转及其遭遇,不正是对“现代”迅猛而嚣张的历史时间进程的空间化展示及其意味深长的隐喻吗?
四
巨蛙在帝国心脏度过的最后岁月被命名为“游增”。“游增”是佛教用语,意为“地狱”。“现代”诞生于“自然”,却把“自然”囚禁。对于被围困在铁栏中丧失行动自由的巨蛙来说,这确实是遥遥无期的地狱之旅。直到一场瘟疫降临帝国心脏,动物园无人看管,巨蛙才重获自由。这是个稍显戏剧性的转折。开头提到的那场动物雪夜篝火围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这并不是林棹被当下分神的表现,这个背景的原型大概是17世纪60年代那场席卷伦敦的鼠疫,它让伦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减少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个瘟疫之年被往后挪移了二百年左右,在这趟魔幻旅程的尽头完成了对“现代”的想象性报复。只是巨蛙的断尾再也回不来了。断尾处隐隐作痛或许是刺激、保存记忆的一种方式,多年以后,便有了故事的第一句话:
我是虚构之物。我不讲人物,我有过许多名字,它们一一离我而去,足以凑成我的另一条尾巴。
巨蛙那截断尾早就与“自然”一起退回世界的幽暗处。巨蛙怀念它,需要讲述失去它的前因后果。于是,海上的腥风和街角的血雨、城市的火光和港口的喧嚣、季风的狰狞和烟筒的嘶吼、饕餮客的狂笑和暴怒与流浪者的迁徙和停留……所有这些层叠的风景与往来的人事都散落于两个时代相遇时的漩涡之中,最终汇聚为巨蛙的那条无形之尾。有形之尾或成化石不可解,而无形之尾却是野蛮生长的怀旧故事。
我们讲故事,因为……在这人世间,除了故事,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把故事留给亲爱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遗产。
一个善良的人类曾如此告诉巨蛙。然而人类终究擅长遗忘,但是巨蛙却因为疼痛而一直记着。她的记忆是“自然”留给“现代”和人类最后的礼物。就像巨蛙对另外一位善良的人类说过的临别赠言:
我只求,未来日子,你去每座港口每家酒店饮落每一口酒,都有今夜的一滴。
【注释】
①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此后,凡引自该书的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②参见安德里安·G.马歇尔:《复仇女神号:铁甲战舰与亚洲近代史的开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③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4页。
④⑦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八四〇—一九四九)》,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第34-39、34页。
⑤梁嘉彬:《广州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00页。
⑥向达编《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第131頁。
⑧张英明、徐庆铭:《论〈圣经〉马氏译本对洪秀全的影响——以“上帝”译名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方岩,辽宁大学文学院、《思南文学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