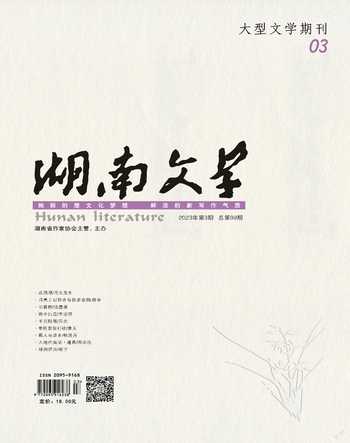羁人与原乡
韩浩月
一
“昨日草枯今日青,羁人又望故乡情”,唐代文人方干的这句诗,如风滚草一样,距离春节还有近一个月时间的时候,就开始在心头滚动。方干诗中写到的季节是春天,而我极少在春天返乡,回去最多的季节是冬天,而到达我出生的村庄时,迎接我的,往往是寒风、冰雪。
方干诗中,“羁人”这两个字,是风滚草叶面上的刺,干枯又硬冷。从十几年前开始,我就意识到了羁人的身份,把自己当成了故乡的游客、旅人,来的时候充满好奇,经历整个过程的时候浑身疲惫,走的时候不舍,必须要带着点残忍才能迈开脚步。可正是这样的自我身份认定,使得我与原乡之间的关系,显得清晰、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我的县城文友们,把我当友人,也把我当客人。但在他们面前,我一直没有用过“羁人”这个说法,它有点儿古老和矫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我不愿意这个词所包含的那层羁绊情绪,束缚住自己,绊住自己的手脚。毕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做到云淡风轻地来来回回,浓度过高的情感,已经让我开始有所顾忌,继而逃避。
进入县城域内,收到的第一条信息,是文友发来的。这几年,返乡的第一次聚会,是和文友见面,这已成习惯。以前返乡第一顿饭,通常是和堂弟、表弟、妹婿们一起,后来文友们取而代之,原因无他,是文友更在意“接风洗尘”这件事,文友们心有古意,不可辜负。
有了微信群之后,家乡文友联系密切,有人发表了文章,会把链接发到群里供大家欣赏,有人早起锻炼,遇到路边野花野草野菜,会拍照发来让大家辨认,他们偶尔小聚,也会把照片发到群里给我看,闲聊时已经约了无数次,等我回来,大聚。
群主管兄,提前问了我的行程,然后在群里发了聚会消息,又单独与每个人电话联系——山东人讲究礼仪,邀请人喝酒也是如此:通知具体的时间、地点,先集体通知,再逐一确认,问能来不能来,不能来有没有什么话要嘱托、要带到,虽稍显繁琐,但确显情意。
路灯亮起的时候,打车前往聚会地点,街上挂满了红灯笼,年的味道已经很浓,但透过车窗,看见路边餐馆里,食客并不多。我们聚会的饭店,也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多年好友刘兄,戴着N95口罩走进房间,说县城里的饭店,在奥密克戎感染过峰后,刚开业了三四天,人们还心有余悸,暂时不敢来。
落座后的第一轮话题,自然是有关感染后的症状表现,以及现在的康复状况等,彼此小心翼翼地问候家中老人的状况,得知基本没事后都不禁长舒一口气,然后又提醒还得加强防护,等待春暖花开。
说好了这次聚会,要少喝点酒,点到为止,微醺即可,但都是多年老友,又长时间未见,不免要多喝一杯,两两捉对敬酒时,握手搭肩,说到一些更适合单聊的事情,有喜笑颜开,也有长吁短叹,这次聚会,多少都带点“劫后余生”的味道,大家一致认同,感染的事情,大家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经历,如今还能聚在一起长聊,颇不容易。
我把自己和好友合著的打印诗集,送给了家乡文友,酒过三巡,每人选了一首诗来朗读,这已经是多年来家乡文友聚会的保留节目,读读诗,在诗中辞旧迎新,能安慰人心。
二
过春节,上年坟。从县城到我出生的村庄,有三十多公里地,腊月二十三这天下了大雪,但日子已定,不好更改。家乡风俗,年坟要在小年前上完,天气预报说,寒潮已至,雪后道路结冰,去村庄的路会不好走。
给一直住在村子里的三叔打电话,他在镇上的店铺里卖下水,怪我没有提前通知他,又说雪大,劝我改天。他的儿子,我的三弟,开大货车去重庆送货了,今年三弟不能陪我去上坟。我要自己找到祖坟那里去了,有点心慌,往年都是三叔或三弟带路,我只顾在后面跟着走,这次发现自己有可能找错坟头,有些自责,觉得自己四十多岁了,有些事还是做不好。
好在三弟的大兒子晨曦上了高中,已经是小大人了,他带我和妹妹两家人一起去上年坟。我们都离开村子三十多年了,平时都是晨曦和他爸爸、爷爷去上祖坟,已经很熟悉道路。给祖坟磕头的时候,晨曦行的是大礼,节奏缓慢,直腰弯腰,双膝落地,匍匐在雪地里,让我大为震撼。
往年回村庄上年坟,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不愿多停留一分钟。每年同来的孩子们,冬天习惯了待在暖气房里,连穿秋裤的习惯都没有,到了农村的冰天雪地,没几分钟浑身就被冻透了,我跟孩子们说,这才是真正的冷,受一下教育也好。
三婶接到三叔的电话后,就开始包饺子、做菜,为了加快速度,还请了村里的亲戚帮忙,那个亲戚记得我小名和小时候的样子,说我应该称呼她“婶子”。三婶每年都会在我们来上年坟的时候,做满满一桌子菜,有时候赶着在天黑前走,一口不吃就走了,有时候站在桌边,象征性吃了三两口就走,三婶也不生气,依然年年准备这么一桌子饭菜。
今年在三婶家的这顿饭,是历年来吃得最多的一次,原因是没吃早午餐,到了下午时分,大家都饿得厉害,另外三婶请来帮忙的婶子,包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实在好吃,不到半个小时,七八个人就风卷残云般把一桌子饭菜消灭光了。三婶很高兴。
进村的路上,有一排长约五百米的电子花圈,几十道电子显示屏,滚动显示着逝者和纪念者的名字。女儿说,这挺赛博朋克的。和包饺子的婶子聊天,她说村里这个冬天,走了六位老人。在说到死亡的时候,她不带任何特殊的情感,像说天气、庄稼等事情一样淡然。她对病毒只字不提,在村庄,压根没人谈论奥密克戎以及与它有关的预防和治疗方案,都说那是“感冒”。
婶子还说,我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村子边缘盖的房子,已经被转手卖掉三次,最后这次,宅基地和院子一分为二,被上一家主人卖给两户村民改建成了两处新房。新房我在开车拐往三叔家的时候看到了,门前屋后栽了一片竹子,冬天还有未掉尽的叶子挂在竹竿上,在寒风中微微摇曳。
三
没想到会去参加一场葬礼,而且是必须要去的葬礼。年轻时代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的奶奶去世了,在我回乡的第二天,接到我们共同好友打来的电话,说送殡的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五,我们在这天,需要早一点过去,说说话。
和这位朋友,在县城驻地的镇上一起工作过,是彼此青春的见证人,有过一些难忘的友情,又因一直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往来,继而又多了些兄弟般的情意。近些年因为一些事情虽然渐行渐远,但遇到葬礼这样的大事,心脏还是会被重击一下,觉得逝去的也是自己的亲人。
定好了花圈,请花圈店的人帮送了过去。本来要打一个安慰电话,问需不需要过去陪着在夜里守灵,但通讯录点开了,又关闭了。按照老家风俗,他会二十四小时守在棺木所在的堂屋里,白天向前来祭奠的亲戚、邻居、朋友跪拜回礼,晚上则睡在旁边的草席上。
我经历过这样的时光,持续三四天,漫长又难熬,如果这样的时候,能有好友各自陪伴一段时间,说说话打发时间,会好过些。我之所以没有打这个电话,是担心自己说的话太套路、太苍白,也怕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有一些孤独和哀伤,是必须要一个人承受的。
定好了早晨八点的闹钟,洗漱完毕后去接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去那个多年前曾去过的村庄。忘记了上次去那个村庄的缘由,但车轮一拐进村子的道路,往事历历在目,迎面扑来,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无忧无虑,还有现在这个年龄的沉重无言,有许多发不出来的感慨。
村子里有几户人家,同时在办葬礼,我们已经无法找到朋友在村子里的家,下车打听了三次,才找对。耳朵边听到了欢快的哀乐——我家乡的风俗,达到八九十岁的大龄老人去世了,算是喜丧,可以放节奏欢快的流行音乐。院子里摩肩接踵都是人。排着队挤进灵堂,看到了跪在棺木边的朋友,他也一眼看到了我们三个,跪下给老人磕完头之后,和他握手时,都泪光闪烁。
等待领孝服的十多分钟里,蹲在棺木旁边,和朋友说话,他说奶奶高龄一百零二岁,是村里第二长寿的老人,家中已经五代同堂,这么说的时候,屋中有穿着大红色孝服的孩子走来走去,那应该是家庭中的第五代人。
穿上孝服,在年龄大的朋友的带领下,在临时搭起来的奠堂向去世的老人行礼。结束后再奔堂屋向老人行告别礼。朋友央人带我们去“坐席”,吃饭在另外一个大的院子里,里面的每一张桌子上都热气腾腾,饭菜的种类、品样繁多。我们在院子边缘站了两三分钟,等到管事的人离开,我们便也离开了。时间是上午十点多钟,不是吃饭的时候。
回来的路上,在车里聊天,一位朋友说我们三个中午可以简单喝一杯,我说不用了,确实不是喝酒的时候,他们说也好。年底大家都忙,一个要去给自己的店开门,一个要去讨要建筑公司拖欠几十人的数十万工钱。自己人不必客套,没事了一起吃饭很有必要,忙起来的时候不吃饭也没关系。
四
萍又召集大家喝酒了,今年我们聚了三次,创造了一个新的聚会频率记录。初中同学原来有一个微信群,经常有同学通过群联系,三五成堆地偶尔聚餐,我回老家的时候遇到聚会,也会过去扎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群解散了,同学的联系就又零落了。
四五年前,这位叫萍的同学横空“杀”了出来,成为组织聚会的活跃分子。我上初二时,班级除了体育课的集体成绩好,其他主课成绩年级垫底,原因是班里调皮捣乱的男生女生太多,校领导一气之下把我们班“解体”了,一分为二,所以,在初中,我有两个班的同学,有不少同学我没印象也记不住名字。
萍是我记忆里比较模糊的一个身影,据她自己说,她那时不像女生,像个“猴子”,经常飞跃于课桌上,进出教室很少走门,都是从窗户跳进跳出。她还说,如果觉察到自己的袜子里被塞进了一团东西,不用低头看便知道,是男生委托她转交的情书到了,“信使”便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把信送到收信人那里。当然,萍对我印象也不深,只记得我个子小,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门的角落里,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或是为了强化几个同学对她印象不深的缺憾,萍在这几年成为饭局召集人。以前每次回县城,都是一位开了集团公司的同学在他自己的饭店里请客,多年下来,从开始的不好意思,也逐渐习惯成自然了。今年同学的建筑公司,没能从县政府那里拿到工程款,被欠了几个亿,年底要东拆西借给员工与工人发工资,烦不胜烦,这次年底的聚餐,他没能来,萍说,他来不来不重要,不能耽误咱们吃饭。
萍组织的同学饭局,要随叫随到,不来是万万不行的,要背负不小的舆论压力。萍经常在饭桌上,对被邀请但却没有到场的同学,用电话“开炮”,能感觉到接电话的那人,背部在冒汗。但萍对我却客气,一直用温和的语气,她说对文化人要温柔,我说不必,咱们都是拿同一个学校初中文凭的人,不用在意这个。
萍能喝酒,但比喝酒能力更强大的是劝酒,她酒量大,劝酒的词也多,男同学都不是对手,哪怕拿出来超过平常的酒量,也会被一一放倒。不喝酒的女同学,萍不劝,但如果能喝一点儿,那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大家怕了她,又依赖她,觉得没她在场,气氛活跃不起来,只要有她在,哪怕只有四五个人聚,她也能把包间闹出掀翻天的气势。
那天各自喝了七八两酒之后,我们来到了同学的办公室,他的公司离我们吃饭的地方并不远。推开门,看见同学正把头埋在电脑面前愁眉不展,看到我们来了,才换上轻松的面孔,招呼人上水果、泡茶。萍对没来喝酒的这位同学大为不满,连珠炮般地发出一连串攻击,他俩熟,沟通方式也是连喊带咋呼,有时不免还带出几句脏话,但仿佛又因此增加了亲密度。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唇枪舌剑,我们边喝茶边嗑瓜子,像看二人转演出,有人推门进来签字报销,他们两人会瞬间安静下来,等办公室的门被关上,又继续吵。
萍说,本来同学可以不用聚这么勤的,她这么强势,是为了联络大家的感情,以便以后老了,还能来往,吃吃饭,聊聊天,不感到那么孤独。她还计划在山上租一块地,盖十来间简易房子,等老到一定的时候,又不想麻烦子女,就到山上住,过集体生活……这样的设想,我在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的饭桌都听到过,没人觉得这会变成现实,但说的时候,都开心异常,觉得就像真的可以实现一般。
五
前一天晚上喝多了,临近中午才醒来,走路有些打晃,但用热水洗把臉之后,觉得好了许多。中午有场酒局是必须要参加的,他们是我的发小,是认识了三四十年的朋友。
走在大街上,阳光晒得背部有些发烫,脚上穿着的是黑色透气的运动鞋,也吸收了大量的太阳热量,走起路来,像是踩了风火轮。去吃饭的饭馆,已经开了三十多年,换了不少任老板,但饭店地址和名字一直都没有换,和发小们的饭局,多年来也一直固定在这里。
这个饭店,我上初中时在这里过过一次生日,请了几位发小和同学,大家都到了,我却迟迟未到,迟到的原因是,直到最后一刻,才筹足这顿请客吃饭的饭钱。那顿饭,大家喝了不少酒,喝完酒便会哭,独自哭,双双抱着头哭,哭累了换一个人再继续哭,类似的戏码,上演了多年,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委屈和眼泪。
现在聚会的发小们,都四五十岁了,哭是哭不出来了,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形形色色,但眼眶都变深了,藏得下眼泪,过去没委屈会哭,现在有了委屈反倒会笑,眼窝里发酸、发烫,就是滚不出热泪了。
一个发小,是从信访局来的,他承包的工地,到了年底了,结算不出来工资,几十名建筑工人跟他要钱过年,他没有办法就只能和他们一起去上访。现在的上访,也是文明上访、守法上访,不吵不闹,不拉横幅,到了信访局,选出几个代表进办公室去谈,剩下的在院外安静地等。这个发小在走进饭馆屋子里的时候,说喝完酒之后还得办正事,继续上访去。
今年聚会聊天的主题是“要钱”。县城里的三角债状况严重,不仅官方如此,民间也如此,你欠我钱,我欠他钱,他欠你钱,说不清的债务关系,聊不透的还钱话题,桌上的人,举起杯提酒敬酒,放下杯就刷微信要欠账,偶尔有人出去接电话,谈的也是还钱的事。
也不是没好消息,酒席间,一个人的微信响了一声,他打开看后说到账了两万块,其他几位说快分分。没有账本,没有核对过程,他六千,他八千,他两千,他三千,最后这位发小说,给我留一千块钱,过年给孩子发红包、买鞭炮吧。他们平静地分着钱,说着事,既不兴奋,也不伤感。
在这个酒局中,我有些恍惚。我在外省,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遵守着规则,尤其是把商务规则分得很清楚,不会出现整个饭局都在聊钱的事情,好在,他们也无视我的存在,更不在乎我内心的翻江倒海。
六
二弟打来电话,说定好了县城里最大的饭店包间,每年一度的大家庭聚会,今年由他来组织,时间定在我生日那晚,他也会提前定好蛋糕。我犹豫了一下,心底有些不情愿,大家庭的聚会,有长辈,有晚辈,孩子一大群,加在一起人数有三四十人,并不适合突出我的生日。再者,我对过生日这件事,一直有抗拒心,童年和少年时代,就算在亲人那里,也一直躲躲藏藏,并不愿意被关注到,现在年龄已经大到一定的程度,但本性依然没变。
但我还是答应并感谢了二弟,一是不忍打消他的积极性,拂了他的好意,另外也觉得,这多少算是个小小的心理障碍,要越过去。还有一点,那么多小孩子有大蛋糕可以吃,他们一定会开心。
二叔、六叔坐在主位上,三叔在乡下没法赶来,五叔在昆明打工,也只能通过观看和转发群里、朋友圈里的视频来参与了。我的父亲和四叔已经永别于人世,他们缺席在这个大饭桌上已多年,但酒杯碰撞间,总有人提及他们。姑姑本来应该也坐上座,但她不愿意,六十多岁的她,和孩子们挤在一起,并不关注喝酒的弟弟、子侄们,等到有人喊她时,才笑吟吟地回应一下。
最尴尬的环节,最先开始。二弟把蛋糕摆在我的面前,我以为点的是传统的生日蜡烛,但用打火机点着之后,发现是两小丛烟火喷射出来,孩子们开始唱生日快乐歌,那是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手里拿着塑料切刀,开始分蛋糕,按照年龄辈分,逐一地把蛋糕切成小块分出去。
这样的家庭聚会,欢乐又祥和,亲情是主旋律,已经有七八年没有吵架的事情发生了,过去的大家庭聚会,往往是以欢乐开局,悲伤收尾。想了想原因,长辈的衰老,大概是新局面形成的缘故,他们已经不再计较过往,也更期望晚辈在一起能好好地过个年。长辈们的话说得越少,晚辈们就越放肆,气氛就越活跃。喝掉了三四瓶白酒,又喝掉了两箱啤酒,我趁去洗手间的空,想偷偷地把账结了,被表弟发现,一把把我抱着推了出去,说今年他们几个弟弟请客,我不能抢着付钱。
“这个年要好好地过”,这是家庭聚会达成的共识。约好了吃完年夜饭后,到一个宽阔的地方集合放烟花,今年县城不再绝对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在除夕、初一、元宵节,可以敞开了燃放,我也趁着酒后,说今年要带着孩子,去长辈们家拜年,过去因为我大年初一经常要离开,要么返京,要么外出旅游,已经缺席了十多年的初一拜年,今年初一哪儿都不去了,要带孩子们去长辈那里拜个年。二叔听了这个消息很开心,低声和我商量,要给孩子们准备多少红包,每个红包里装多少钱。
我有五个堂弟,两个妹婿,加在一起有十几个堂妹、表弟、表妹,见到他们各自的孩子,经常鬧出叫不出名字的笑话。孩子们在年终聚会的饭桌上,一年年长大,每过一年,都有新的人口出现在饭桌上,小孩子的名字,今年记得了,说不定明年又忘了,得抱起来重新问。也没有在意谁的记性好与不好,能坐在一个大桌子上吃饭,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人。
返回外省的寄居地之后,整理半个月来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有一条十来秒的视频,被我反复看了十几遍。视频里呈现的是一条田间小路,那是上年坟时的必经之路,小路上布满冰雪,特意穿着的靴子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过这声音在呼号的寒风中显得微不足道,手机的录制格式,也改变了当时环境的色彩与音调,使得视频格外像一部电影的片段。
我在这段短视频里,感受到了“羁人”的那份孤独与渺小,还有身不由己。四十多年了,这个村庄,这条路,像是根本没有变过。虽然我变了,且变化很多,但是每一次走在这条小路上,我都会被打出原形,那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他心怀苦楚,对着清冷的天空发誓,一定要走出这个地方,再也不要回来。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