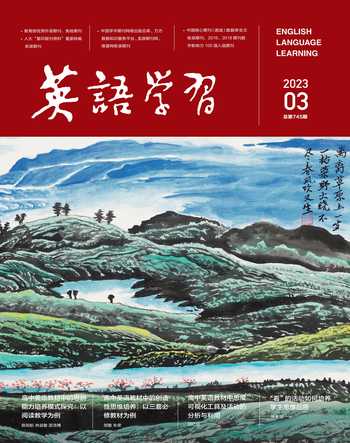他者的社会化:哈克贝利·芬的成长
摘 要:《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通过一个未成年人的旅途成长经历探讨成长的社会性和建构性本质。哈克因“非人”的芬老爹,成了小镇社会中的“病人”—— 一个有自杀冲动、沉默的他者。哈克在旅途中通过角色操演参与岸上生活,在反复实践中成长为兼具社会审美认同和道德认同的书写者。但哈克未抵达旅程的终点就重新启程,他的成长是一种持续的建构。
关键词:《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他者;成长;社会化
引言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是一部经典的成长小说,讲述了小流浪汉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顺流冒险的成长故事。旅途中,哈克时而在河上,时而在岸上,“上岸—离岸”构成小说情节的主要单元,为哈克的成长勾勒出时间和空间的轨迹。哈克每次上岸,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乔装打扮一番,使用虚构的身份融入岸上生活。一路走来,哈克虚构身份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他的伪名上——莎拉·威廉姆斯、玛丽·威廉姆斯、莎拉·玛丽·威廉姆斯、乔治·彼得斯、乔治·杰克逊、汤姆·索亚等。无论扮演谁,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岸上暂得栖居。那么,为什么哈克只能以虚构的身份在岸上暂得栖居呢?
《哈克》中,马克·吐温把一个成长因子置于“岸上—河上”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如同在一个培养基中投入一粒种子,一边培育,一边观察,看看它到底如何成长。小说中“成长”的内涵向来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张德明(1999)结合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探究小说中的成人仪式原型结构和哈克成长的关联,他肯定“岸上—河上”二元对立的存在,借用荣格心理学术语阐述“河上的世界代表了哈克的‘自性,而岸上的世界代表了‘他性”,而哈克的成长是不断返现“自性”与“他性”,最终“达成个人与社会、内心与环境的平衡”。显然,此处的“自性”与“他性”之说关照的是哈克的内部经验,而未充分关注哈克的社会身份。郭晶晶(2017)提到吐温多部小说中的易装情节,认为哈克的易装策略体现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但其笔墨之少让人意犹未尽。要探究哈克成长的本质就必须同时关注“种子”与“培养基”。小说的“岸上—河上”二分世界中,岸上是小镇的栖息地,是社会主体之所在;而河上是哈克的避难所,是他者的栖居所。芮渝萍(2004)认为,“成长……意味着一个人从他者和边缘的地位走向主流文化的中心,实现了他者的主体化和边缘的中心化”。孙胜忠(2020)指出,“成长小说中,社会化的实现往往被视为主人公‘成熟的标志之一”。可见,成长小说中往往存在成长的社会化维度,成长对象的社会化过程常构成作品重要的叙述内容,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点的关注不够。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哈克》通过哈克这个未成年“他者”的成长经历来探讨成长的社会性和建构性本质。
小说中存在他者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他者哈克在社会中的成长是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囿于原生家庭,哈克生而为他者,在社会中陷入存在的困境。但是,通过他者的角色扮演,他者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得到释放,他者以虚构身份在社会中暂得栖居,哈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社会接纳。小说中,哈克被社会的接纳并不意味着旅程的终点;他的重新启程,意味着他的成长是一种持续的建构。
他者在社会中: “非人”“病人”“自杀”“沉默”
小说开篇,哈克讲述了在寡妇道格拉斯家的生活:一天的教养和训诫结束后,哈克回到房间,静坐窗边,本想刻意想些让自己快意的事情,却徒劳无果,他难掩内心真实的声音:“真闷得慌,我想死掉算了。”(吐温,2000)“死”字从哈克嘴里脱口而出,显示了哈克潜意识中的自杀冲动。涂尔干认为,自杀是“集体疾患”的表象(转引自赵立玮,2014),也就是说,自杀的根本原因要去社会中寻找。哈克在文明的训诫中流露出向死之心,不得不使我们关注他的社会处境。《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写道,“镇上所有的母亲都实实在在讨厌哈克贝利,也害怕他,因为他不务正业、不守规矩、举止粗俗、行为恶劣,还因为所有孩子都羡慕他,喜爱私下跟他交往,希望自己敢于像他那样自由放任”(吐温,2004)。显然,哈克是小镇上的问题少年,是小镇生活的他者。哈克之于小镇社会即是边缘他者之于主体现实。
“他者”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中常提及的术语。“他者”存在于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比如,女性是男性的他者,东方是西方的他者,自然是人类文明的他者。一面是主体、中心、权利、话语,而另一面是客体、边缘、义务、沉默。小说中,密西西比河造成的地理分割恰恰象征一个二分的世界,岸上是群体小鎮的所在,而河上是边缘人的避难所。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小说中存在诸多边缘人物,他们在岸上难以栖身,无不与密西西比河联系密切。哈克和吉姆是陆地逃亡者,只能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生活。骗子“国王”和“公爵”也是陆地逃亡者,他们与哈克在河上相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哈克的父亲芬老爹(Pap Finn),他仿佛只是一个河边暂住者 ,但是他的尸体浸泡在密西西比河中。而岸上世界则是要“文明化”哈克,要制裁吉姆、骗子和芬老爹的地方。王楠(2015)认为,权力把个体塑造成知识的主体,规训身体,使其臣服和吸纳社会规范,而欲望的主体为了存在只能选择服从, 并在对权力/律法或社会规范反复吸纳和引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一个屈从的主体。小说中的岸上小镇是主体与权力的容器,也是规训个体并生产主体的社会性空间。作为不完全屈从的越轨个体,那些边缘人在岸上世界势必会遭遇坎坷。借用伯格和卢克曼(2019)的比喻,“如果把日常生活至尊现实比作生活的‘白日,边缘情境就构成了生活的‘黑夜,它在日常意识的四周不怀好意地埋伏着”。社会的至尊现实对他者“不怀好意”的埋伏不会置之不理,他者要么被治疗,要么被虚无(认为它不存在)。换言之,社会的越轨者在日常生活中要么是需要治愈的“病人”,要么是根本没有资格接受治疗的“非人”。“病人”和“非人”均体现他者在社会中的存在困境。
伯格和卢克曼(2019)说:“一切个体都出生在某个客观的社会结构中,在这里他遇到了负责自己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重要他人将世界中转给他,并在中转过程中对这个世界进行修改。”哈克的他者身份之因要追溯至他生命之初的重要他人——芬老爹。芬老爹与小镇之间的矛盾从出场就已昭然若揭。他无视小镇的律法与规范,欺凌法官、诋毁学校、偷走哈克,并公然向小镇宣战,最终是他管住哈克。芬老爹是社会里的“撒旦”,而哈克是“撒旦”的继承人;或者说,芬老爹是第一代他者,哈克是第二代他者。
第一代他者芬老爹是小镇中的“非人”。王楠(2015)将巴特勒作品中“less than human”的表达译作“非人”,指“一类被变成主权/法的例外但又被包含在国家之中的主体”(王楠,2016)。小说第五章,新上任的审判官想教芬老爹重新做人,吐温小说原文的表达是“…he was a-going to make a man of him”(吐温,2008)。言外之意,“he is not yet a man”;或者说,“he is less than a man”,他是“非人”。审判官煞费苦心地把芬老爹带回家,准备耐心教育他,芬老爹也积极表现,诚心坦白,承诺戒酒。这不仅感动了审判官,更感动了芬老爹自己,二人相拥而泣。可是,一天不到芬老爹就原形毕露,酩酊大醉时还险些丢了性命。审判官幡然醒悟:能让芬老爹改变的恐怕只有火枪了——这一结论恐怕是镇上其他人早已认同的了。火枪能做到的无非就是断了芬老爹的气,让他从人变成尸体。显然,真给芬老爹一枪是行不通的,但这结论已然给他判了死刑,芬老爹在小镇人看来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非人”的判决不只来自小镇,芬老爹在潜意识中与小镇共谋,也非人化自己。芬老爹是嗜酒如命的酒鬼,如哈克所见,“每次他拿到钱就喝个烂醉,每次醉了就到镇上到处惹事,每次惹了事就被关起来。这对他正合适,这种事情他最拿手了”(吐温,2000)。芬老爹酗酒是一种自我麻醉,酒醉下的芬老爹是谵妄的精神错乱者,他的不安和恐惧常常在酒后爆发。在恐惧的鬼影前,芬老爹感觉自己遭到追杀,只能无奈大喊“让一个可怜的家伙自己待会吧!”。芬老爹在被幻觉干扰时,把流着自己血液的儿子看成了死亡天使的化身,一心要消灭他。芬老爹的弑子行为是一种自杀表现。精神错乱的芬老爹既被追杀又在自杀,芬老爹也是手持火枪的人,芬老爹的自杀实则表明他其实内化了岸上世界的观念,潜意识之中对自己进行非人化,他实则是岸上世界的同谋者。
在共谋的他者和小镇社会之间的第二代他者哈克也表现出种种病症,他则是有待被治疗的“病人”。这些病症其一便是语言的失效或沉默。哈克在寡妇家时,时常发生语言的误解。比如,道格拉斯说他是“一只可怜的迷途羔羊”(吐温,2000), 他却以为人家在骂他是牲口。哈克索性放弃了语言沟通,所以当华森小姐教训他时,虽然他内心有想法,却不会说出来。当哈克在寡妇家中感到焦虑时,汤姆·索亚的出现立刻让他摆脱了绝望和死亡的气氛。汤姆和其他孩子是小镇的正常孩子,他们的世界并不像成年人那样封闭,他们为哈克与社群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哈克在和镇上孩子们玩耍时,基本上是个沉默的角色。孩子们与大人不同,他们在一起时会有更多的肢体交流,仿佛身体是无意识领域,比语言领域更公平。即便如此,哈克和汤姆之间仍存在裂缝。小说第三章,当哈克试图与汤姆交流想法时,出现了这样一段:
“我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他说如果我不那么无知,只要看过一本《堂·吉诃德》的书,不用问就会明白了。他说那都是魔法变的。他说那里有好几百名士兵,还有大象和财宝等,有魔法师和我们为敌,他们把那些东西都变成了一所儿童主日学校,完全是出于恶意。我说好吧,那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找那些魔法师了。汤姆·索亚说我是个笨蛋。” (吐温,2000)
哈克继续与汤姆争论了一番,但最终汤姆制止了争论并骂哈克是“一个标准的大笨蛋” (吐温,2000)。 汤姆表现得像华森小姐一样,当他和哈克意见不合时,便勒令其闭嘴并辱骂他;而哈克对汤姆也像对华森小姐一样,即便心里不能认同,却也缄口不语。“语言构成了社会化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化最重要的工具”(伯格、卢克曼,2019)。哈克身在小镇社会之内,实则在小镇社会之外,语言的失效和沉默恰是他游离在小镇社会系统之外的表现。此外,同芬老爹相似,哈克也被某种不可名状的自杀冲动诱惑着。他在寡妇道格拉斯家不时感到窒息般的孤独感,顺口说“死掉算了”。他更是在逃离小镇之际,布置了自己被谋杀的血腥现场,完成了“自杀”,而这场仪式上的“自杀”恰是哈克自救之旅的开始。
他者在成长中:“操演”“审美”“道德”“书写”
正如伯格和卢克曼(2019)指出,原生家庭使个体经历初级社会化,而个体进入社会时会经历次级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最终得以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社会化使哈克从他者转向主体。哈克在小镇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是不停地表演。哈克在陆地上通过乔装打扮、改名换姓的“角色扮演”参与小镇生活。如毛亮(2015)所言,在现实建构过程中,个体意识会对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赋形”与“赋意”。哈克的角色扮演正是其“赋形”与“赋意”的实践。这种实践用巴特勒的话语来说,即是“操演”。操演指向的是建构性,如巴特勒所言,性别角色之所以被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因为它一再被重复,最后被自然化了(Butler,1999)。可见,操演是参与和实践,其结果是吸纳、接受、融入,是社会化。
哈克的旅途成长经验伴随“赋名”和“赋形”,是重复性操演的实践,目的是用“替身”隐藏“真身”。随着旅途的深入,重复性操演的实践使哈克的隐藏能力得到发展。在旅途伊始,哈克造访朱迪思·洛夫图斯夫人家。由于演技拙劣,他进行了三次更名,从莎拉·威廉姆斯到玛丽·威廉姆斯到莎拉·玛丽·威廉姆斯又到乔治·彼得斯,最后被洛夫图斯夫人戏称为莎拉·玛丽·威廉姆斯·乔治·亚历山大·彼得斯。流落到格兰杰福德家时,哈克变身为乔治·杰克逊,这次哈克要比之前谨慎得多,为了防止露出破绽,他巧妙地从巴克口中学会名字的拼写,并反复练习、烂熟于心。随着哈克角色扮演经验的累积,他虚构身份的能力越来越强。伯格和卢克曼(2019)认为,“‘隐藏能力的发展,是成年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历渐长的哈克在社会中逐渐由不适变得舒适,成长为兼具审美认同和道德认同并且不再沉默的准社会青年。
当哈克误打误撞进入格兰杰福德的地盘时,他扮成一个迷路的男孩,轻而易举地被格兰杰福德家所接纳。格兰杰福德家如同圣彼得斯堡一样,但待哈克进入格兰杰福德家时,他已不似早先在寡妇家那般感到百般难受了。当然,格兰杰福德家与寡妇家不同,但此时的哈克相较于之前也发生了改变。在格兰杰福德家,哈克写道:“这是很可爱的一家人,他们住的房子也可爱至极。我从前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一所这么精致、这么有派头的房子。” (吐温,2000) 哈克竟然赞美起房屋的气派来,他如同一个参观藝术展的青年,仔细欣赏着房屋装饰的细节:摆件、桌布、书目、图画。特别是这家已故女儿的画作和诗作,让哈克着魔一般地被吸引。他仔细研究过许多次,对所有细节了然于心。他坦言:“有好多回被她的图画弄得闷闷不乐,我无法理解她的心情,我就无精打采地来到她原来住过的那间屋里,拿出她那本老剪贴簿来,认真地看了一遍。我很喜欢那一家人,连死的都包括在内,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隔阂。”(吐温,2000)此时的哈克俨然一个忧郁的艺术青年,与格兰杰福德家达成审美认同。“审美认同就其根本语义而言,指的是人们在对于什么是 ‘美以及如何接近、表达和通达此‘美等方面所达到的观念和行为方面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向丽,2014)。可见,审美认同指向观念和行为方面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不仅如此,哈克想到这女孩生前给别人作诗,死后却没有人给她作诗,于是他绞尽脑汁尝试为她创作几首诗。虽然创作以失败告终,但哈克的表达冲动被刺激和唤醒,而这背后的动力是满足公平性的道德诉求。
如果说审美认同是哈克成长表现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哈克的道德认同。李萍(2019)认为,道德认同包含两方面意义:“其一是指道德主体与通行的社会理想道德要求的一致性或相同性,这可以视为道德社会认同;其二是表明道德主体(道德行为者或当事人)与道德自身的关系水平,这揭示了道德主体自觉自愿地与道德不离不弃、始终如一的状态,这一层面的道德认同其实就是当事人的道德自我认同。”道德是社会的观念力和情感力之所在(杨修业,2021),无论是道德社会认同还是道德自我认同,都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化。
《哈克》第十九章到第三十三章大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其中“国王”和“公爵”两个人物操纵着哈克的旅程。“国王”和“公爵”对岸上比对河上更感兴趣,但他们因败坏的道德与失范的行为受到岸上世界的驱逐。哈克离开格兰杰福德家后,决心过木筏漂流生活,但“国王”和“公爵”的闯入使哈克被动上岸,并被赋形为无名的随从或帮手。哈克早就轻松识破两个人的骗子身份,且对两个骗子的欺诈恶行和败坏的道德嗤之以鼻。但正如他所言:“假如我从爸爸那儿没学到别的什么的话,至少我是学会了这么一手: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吐温,2000)显然,哈克在道德上鄙视骗子,行为上却对其放任不管。他对骗子的否定说明他具有道德社会认同;但他做骗子的帮凶,说明他还不是与道德不离不弃、具有道德自我认同的人。善良的姑娘玛丽·贞是让哈克从帮凶到揭凶的关键人物。哈克在受到玛丽礼待后,反复三次自责:“这位姑娘多么好啊,她的钱眼看着就要叫那个老坏蛋抢走,我却袖手旁观!”(吐温,2000)最后他终于良心发现,骂自己不作为是“下贱、缺德、不是人”(吐温,2000),决定帮玛丽把这笔钱拿回来。哈克在作出决定之际,反复感叹“这位姑娘多么好啊”。“好”在哪里呢?这个模糊的“好”字饱含着青涩的初恋般的含蓄,含蓄到哈克自己都不自知。哈克回想起玛丽时说:“自从那一回我看着她走出房门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尽管如此,我总是时时刻刻地想念她,想了不知多少遍,我永远记着她说要替我祷告的那句話。”(吐温,2000) 或许很难说清这个暧昧的“好”具体指什么,但它一定不是骗子的那一类,而是与之对抗的力量。在对玛丽“好”的肯定下,哈克在道德认同上又进一步,而这种牵念的情愫和延续的冲动往往昭示着成熟的到来。
小说最后一章,哈克抵达菲尔普斯农场时,被误认为圣彼得斯堡的汤姆·索亚。菲尔普斯农场是一个与圣彼得斯堡有亲缘关系的小镇。经过漫长的旅程,哈克仿佛回到起点,扮演起了汤姆——“他是一个很体面的孩子,教养又好,又有身份,家里的人的身份也都好;而且他人很聪明,并非傻头傻脑的;懂得是非,绝不稀里糊涂;既不卑鄙,又有好心……”(吐温,2000)。就是这样的汤姆·索亚,哈克演起来并不费心,甚至可以说他顺利被菲尔普斯接纳。哈克或许把顺利的融入归因于菲尔普斯夫妇的热情和轻信;但从另一面看,又何尝不是因为他对这场表演驾轻就熟呢?与在圣彼得斯堡不同,哈克在菲尔普斯不再抱怨文明化的生活了,他已经适应了。
正如伯格和卢克曼(2019)所言,“语言构成了社会化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化最重要的工具”。那么,成长到小说结尾部分的哈克已然是掌握语言工具的人。如果说在圣彼得斯堡时,哈克在汤姆面前常常是沉默或被斥责的被动状态,到菲尔普斯农场时,哈克显然不再被动,而且已成长为一个比汤姆更有知识的人。当哈克与汤姆交流时,他自信满满:“我一句话不说,因为这正和我预料的一样,不过我非常清楚,一旦他的主意拿定,那就不会有任何异议”。(吐温,2000) 他不仅教汤姆如何不给萨莉姨妈惹麻烦,更开始向汤姆提出建议,甚至说服汤姆接受其中一部分,而汤姆也开始时不时询问哈克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哈克已成长为一个作者。在小说“就此停笔”(吐温,2000)之前,哈克写道:“汤姆现在已经快痊愈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可是我还是感到很开心,因为如果我早知道写一本书这么麻烦,我就不会动笔,以后也不会再写了。”(吐温,2000)小说之初,哈克在圣彼得斯堡学习阅读文字;在格兰杰福德家,他受到艺术的启蒙,开始有书写的冲动;而在菲尔普斯农场,哈克终于完成了书写。
持续的建构
小说结尾,哈克说:“可是我想,我得在汤姆和吉姆出发前先到印金地区去走走,因为萨利姨妈想要收我做干儿子,好教我做人学好,那种事我真是受不了。我早就尝过那种滋味了。”(吐温,2000)哈克的旅程尚未结束。哈克作出放弃定居生活而选择河上旅居的决定在小说第十八章已出现。哈克在离开格兰杰福德家时感叹:“归根结底,在筏子上比哪都好。别的地方实在太别扭、太闷气了,可是木筏就不一样。坐在木筏上,你会感觉到又轻松、又自由、又舒服。”(吐温,2000)在此,我们有必要再考究一下哈克在格兰杰福德家的经历。在格兰杰福德家,小男孩巴克(Buck)不仅名字拼写与哈克(Huck)只有一字之差,性情也与哈克相似,他与哈克仿佛孪生兄弟。从很多方面来看,巴克就是哈克。如果不是家族世仇和血腥屠杀摧毁了格兰杰福德家和巴克,哈克或许会定居于此。这里,巴克的“被杀”照应哈克在旅途之初的“自杀”。哈克在小镇社会的煎熬,让他以“自杀”开启逃避之旅;而当到了旅程后半部分,哈克可以安于一地的时候,他却遭遇“被杀”。巴克是哈克在小镇里的“真身”,他不用改名换姓,不用佯装表演,可是他却被世仇传统所杀。马克·吐温不甘心让哈克的社会化变成“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童话。“真身”是彻底的社会化、是终点,终点的覆灭当然是揭示性的。哈克并未抵达成长的终点,他还要继续在探险的旅途中寻找自己。哈克的现实建构是能指延展的链条,不可抵达“超验的所指”。操演的虚构是“替身”,是叙事,是身体实践,是社会主体与社会他者之间的中介,是二元对立之间的中间之地。
伯格和卢克曼(2019)认为,虽然“个人······出生在一个客观的社会世界中”,但“主观生命并不完全是社会的。个人既把自己看成社会之内的,也把自己看成社会之外的”;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主观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并非源自社会化的因素,比如那些先于任何社会理解的过程,并且与之脱离的个体对个体身体的感知”。哈克的旅程始终与吉姆相伴,关于吉姆是否为人,哈克的感知与社会的告知并不是统一的,相信自己还是相信社会正是哈克旅途中要不断自我追问的。“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的对称永远不是静态的,不是一旦达成便一劳永逸的事情,而必须总是实际地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个人与客观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持续寻求平衡的行为。”(伯格、卢克曼,2019)在这个意义上,《哈克》这部小说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它回应了人(而且是每个人)在社会中如何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M]. New York, NY: Routledge.
彼得·L. 伯格,托马斯·卢克曼. 2019.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M]. 吴肃然,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郭晶晶. 2017. 马克·吐温作品中的身份转换策略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吐温. 2000.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M]. 刁克利, 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马克·吐温. 2004. 汤姆·索亚历险记[M]. 潘明元, 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马克·吐温. 2008. 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毛亮. 2015. 自我、自由与伦理生活:亨利·詹姆斯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萍. 2019. 论道德认同的实质及其意义[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57—63
芮渝萍. 2004.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胜忠. 2020. 西方成长小说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王楠. 2015. 从性别表演到文化批判:論朱迪斯·巴特勒的政治伦理批评[J]. 妇女研究论丛, (2): 81—89
王楠. 2016. “非—人”的伦理难题:巴特勒与卡夫卡[J]. 国外文学, (4): 44—51
向丽. 2014. 他者视域下的审美认同问题研究——兼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理念[J].思想战线, (6): 66—71
杨修业. 2021. 涂尔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论《自杀论》中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J]. 社会学评论, (2): 241—256
张德明. 1999.《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与成人仪式[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 91—97
赵立玮. 2014.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 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J]. 社会, (6): 114—139
赵静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