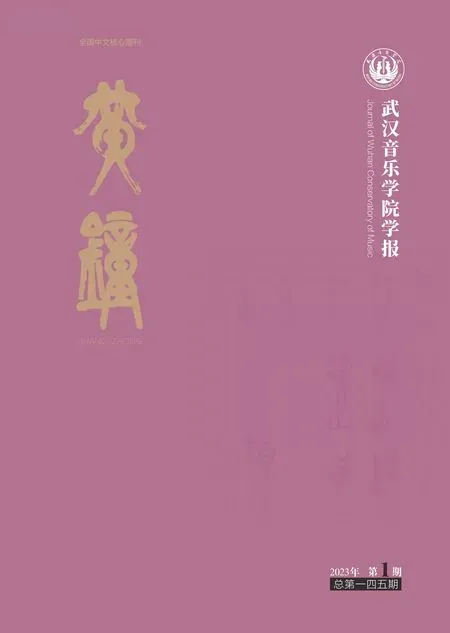传统史学基础上首次新的通史性学科知识建构
——顾梅羹《中国音乐史》述评
修海林
顾梅羹的《中国音乐史》①顾梅羹(1899—1990),本名顾焘,字梅羹。所撰《中国音乐史》正文首页,署名“华阳顾焘辑述”。所见手书上版石印本,除扉页有“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印,另于正文首页首行盖有“山西祁县图书馆珍藏”印、封面盖有“乐正斋图书记”私人收藏印。,是近代中国伴随着社会文化重构与古今、中西文化冲突,于艰难曲折文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第一部中国音乐史通史著作。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与近代中国音乐史学科课程发展有关的机遇,即在近代文化和学术转型背景中,中国音乐史学科课程建设的第一步,是由传统文化田园中的一位琴人迈出的——他的一只脚踩在传统史学史料地基上,另一只脚迈进了近代史学论域,进行了新的学科知识建构。这一步,可谓接续古今,续本源而开新局②此“开新局”,虽有一定社会影响和文化传播空间,但仍属局部效应。。
一、关于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成书与撰写年代
1.成书的知识储备
顾梅羹先生撰写《中国音乐史》的机缘,始于受聘并担任山西育才馆和山西国民师范学校雅乐班古琴教师、中国音乐史教师的历史机遇。顾梅羹于1978 年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中的自述,包括1918 年至1978 年这60 年期间,“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区何部门任何职”的内容。该表前三栏的内容填写文字见表1。

表1 顾梅羹1918—1924 年履历表
这是顾梅羹1924 年考入湖南建国大学学习政法之前的三段社会就职经历。有必要提及,就顾梅羹先生的社会经历而言,他在1924 年秋考入湖南建国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攻读政法专业,并于1927 年暑期毕业。其后约二十年,职业虽有变化,但就其社会、文化身份来说,一是曾长期以公务员身份任职于不同的政府机构,二是作为琴人参加琴社活动。③顾梅羹1947 年受聘于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授职,授古琴、古代文学、中国音乐史。1956 年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特约通讯研究员;1959 年到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古琴。但是,在1924 年之前,顾梅羹19 岁到25 岁三段社会任职、琴人活动所需要的文学修养、历史知识和古琴才艺,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却是我们认识和看待顾梅羹撰写《中国音乐史》时需要关注的问题。在音乐史研究中,除了对音乐史著作本身的关注,撰著者的知识储备、学术能力和文化意识的形成及其特点,同样是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面。虽然我们现在仅了解顾梅羹先生6 岁便于私塾接受童蒙教育,自幼诵读经史;12 岁正式随其父顾哲卿与叔父顾卓群习琴;④据顾梅羹:《琴学备要(下)》第六篇《论说》,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版,第918 页。顾梅羹之琴学渊源,可上溯至其先祖父顾少庚。其家传华阳顾氏《流水》百瓶斋抄藏本,是先祖父顾少庚于清咸丰六年(1856)与欧阳书唐、谭石门诸人于成都青城山学琴于张孔山时,由张孔山亲授的谱本。21 岁时与彭祉卿、沈伯重同赴上海,与各地琴人共聚晨风庐琴会,其演奏获琴人很高评价,在琴界崭露头角、遂有声名……并且我们也并不完全了解他19 岁之前,除接受私塾教育之外,还接受过哪所学堂的教育,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青年顾梅羹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若没有传统经史学养方面相当突出的知识积累以及研读、构思、写作能力,是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这样一部《中国音乐史》通史性教材的。正是有了在传统经史、乐书、琴学、笔记诸方面厚实、宽博的知识积累,青年顾梅羹才有能力撰写这样一部《中国音乐史》。其相关知识储备与专业修养,实际上是在学堂、大学教育之外的私塾、家学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当然,身处时代变革中的顾梅羹,也并非没有接受新学的影响。实际上,正是由于受到新学的影响,并有推陈出新的勇气和能力,他才能够建构这样一部具有新的学术视野和观念的《中国音乐史》⑤由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第一编“绪论”中“音乐之系统”“音乐与政教”“音乐与文学”“音乐之分类”“音乐史上之时代区画”诸章节分设及书中所论,便可知这本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推陈出新”的意义。。
2.撰写机缘与成书年代
关于顾梅羹《中国音乐史》一书的撰写机缘与成书年代,丁纪园以学生身份,撰文专作介绍称:“那时我已听说,顾老师是那个世纪最早编写《中国音乐史》的人,但在给我们上课时,并没有见过顾老师编写的音乐史教材。于是我就问顾老师,他说那是他20 岁时到山西育才馆教授中国音乐史课而编写的教材,翌年初春即石印成书。”⑥丁纪园:《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发现经过及内容介绍》,《音乐研究》2015 年第3 期,第5—11 页。丁纪园于同文中,又引用顾梅羹育才馆同事孙森的《元音琴社回忆录》的文字,以证其是于1919 年20 岁时到山西育才馆和国民师范教授古琴、中国音乐史和古典文学。孙森在《元音琴社回忆录》中记录的相关年份与人物、事件的表达,一是“缘民国七年,以论画而识南海布衣招学庵”;二是其后所言:
次年⑦此句中的“次年”,所据时间座标是前文所言“民国七年”。前文虽言“立琴社之名为元音”,但在叙述方式上并非以琴社创立之年为与前文呼应的座标。阎锡山“谋振兴雅乐”则为“次年”所为之事。当道谋振兴雅乐,顾君⑧指顾梅羹的叔父顾卓群。与张公芹荪,推荐吉安彭君祉卿、浏阳杨君友三、杭县沈君伯重、并顾侄梅羹,由长沙相偕莅晋,济济一堂。育才馆设雅乐班,有志复古者,争先恐后,投入肄习。彭、杨、沈、顾各出所学,撰述乐理讲义,分门别类,既详且尽,并授琴操指法。……雅乐班三年有成,彭、杨、沈、顾,皆一时之英才,怀抱不凡,各有素志,正乐不过出其余绪耳,于是功成而去,从此天各一方。⑨孙净尘:《元音琴社回忆录》,载今虞琴社编:《今虞琴刊·记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年影印版,第21—22 页。
这里提供的材料,在山西“当道”阎锡山办育才馆“谋振兴雅乐”,顾梅羹等人赴晋,“各出所学,撰述乐理讲义,分门别类”,“三年有成”诸事实的认定上,与其他材料相同,皆无疑问。唯顾梅羹赴晋三年担任山西育才馆、国民师范学校雅乐班古琴和中国音乐史授课教师的起始时间,所述不同。前文提到的顾梅羹自填履历表中,这段时间为1921 年9 月至1924 年暑期;丁纪园撰文自述听顾梅羹说其赴晋年份是20 岁(即1919 年),同时征引孙森《元音琴社回忆录》中的记录,与其所闻互证。孙森所记“次年当道谋振兴雅乐……济济一堂”这一段,由文字表述看,可以理解为皆为同一年(民国八年,即1919 年)发生之事。但是,这段所记之事,包括了阎锡山谋求振兴雅乐之举,顾君、张公推荐顾梅羹等来晋,再至彭、杨、沈、顾一行“由长沙相偕莅晋”最终成行,其实有一个提倡、推荐、相约、同行、赴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1919 年的当年全部完成,还是只记了一个开头的时间,至于过程中的实施和最终成行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表述,或可存疑。更何况,这与顾梅羹履历表填写的时间,差别较大,仍有一个存疑、甄别和如何对待的问题。就历史文献的研究而言,同一事件或对象的存在,有不同的史料记录,是经常碰到的问题。但是,并非所有的史料都具备同等价值,这方面,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确凿的文物史料与文献史料、当事人慎重记录的史料与他人记录的史料或传闻史料、具有多重证据支持的史料与孤证史料、无利害关系态度客观的史料与具有主观好恶倾向的史料等等,都需要在研究中有所甄别、判断乃至取舍。当然,判断不同的史料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并非意味着相比较而言价值较低的史料就没有可使用价值,对于史学家的学养和智力而言,问题只在于如何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恰当地择选并使用史料。对于顾梅羹《中国音乐史》一书的撰写并成书时间而言,其人何时赴晋任职山西育才馆和山西国民师范学校雅乐班,从事中国音乐史课程教学,是一个必要也是硬性的条件。而顾梅羹亲填履历表上的记录,应视为直接史料来对待,同时也可以通过他人的文字记录或回忆作为以资佐证的间接材料来进行梳理、分析和判断。
这方面,吴昊的《“育才馆”附设雅乐专修科音乐史事考(1921—1924)》⑩吴昊:《“育才馆”附设雅乐专修科音乐史事考(1921—1924)》,《中国音乐学》2018 年第1 期,第73—82 页。一文,对山西育才馆雅乐科诸事项的考察,可谓史料详实,分析有据,本文不作赘述。
据吴昊文中介绍,育才馆成立于1918 年1月5 日,是年4 月1 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⑪所据为山西洗心总社刊印的杂志《来复》1918 年4 月7 日,第1 号。转引自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中华民国山西通史》,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 年版。笔者注意到,吴昊文中曾征引的泉圣撰《阎锡山的“育才馆”》⑫笔者查阅到,泉圣撰《阎锡山的“育才馆”》(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编:《文史研究》1991 年第2 期,第43—50 页)一文关于育才馆成立时间,称“1917 年暑假后,‘育才馆’正式成立、招生。校址设在今山西省人民政府大院西南处。‘育才’二字,取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是印刷有误还是知识来源有误,待考。但大环境讲得通。一文则称“1917 年暑假后,‘育才馆’正式成立、招生”。该文开首即介绍育才馆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动因,称1916 年袁世凯死后,山西督军阎锡山周旋段琪瑞门下讨得省长头衔,从此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1917 年提出“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同时办育才馆,为推行新政而培训行政管理人员,美其名曰:“培养能适应现时行政自治及社会事业之用人才。”从现有材料看,育才馆成立后,并未立即成立雅乐科。这方面,吴昊在其文章⑬吴昊:《“育才馆”附设雅乐专修科音乐史事考(1921—1924)》,第74—77 页。中依据不同的材料指出,“1921 年秋,在阎锡山的主导与倡议下,育才馆成立雅乐专修科”;顾梅羹“1921 年受邀任教山西育才馆雅乐科”的结论,与顾梅羹自填履历相合,自当可信。
由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首先可以认定的是,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成书,当在其赴晋任教育才馆雅乐科之后。关于这本书的具体成书,吴昊撰写的两篇文章均有考证,且有详细介绍。⑭参阅吴昊:《“育才馆”附设雅乐专修科音乐史事考(1921—1924)》,第74—77 页;吴昊:《也谈“第一部〈中国音乐史〉”》,《人民音乐》2018 年第5 期,第64—66 页。大致的情况是:杨树森等最初编写的《山西育才馆雅乐专修科讲义》(1922 年由育才馆雅乐科刊印),设有乐理、礼制、乐谱、礼乐图考、琴学、琴歌、琴谱、中西乐之比较诸内容,共十万余字,五卷。此初编讲义尚未有《中国音乐史》一册。
1922 年夏,因早先编写的《雅乐讲义》“且编且习,急就成章”,杨树森、彭祉卿、顾梅羹三人对其进行重修,此《重编雅乐讲义》设乐理、琴学概要、歌曲练习、中西乐律比较、中国音乐史、乐器图考、礼器图考、礼制、佾舞、乐章、诗歌、琴歌、琴谱、瑟谱,计十四门,六卷。此套重编雅乐讲义中有《中国音乐史》一册。
问题是,“重编雅乐讲义”中所设《中国音乐史》一册,其成书时间能否判断是“1922 年8月20日国师雅乐科新生入校之后”?笔者以为,1922 年秋季开学,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雅乐科新生入校之时,顾梅羹的《中国音乐史》确实可以认为已经刊印成书,但并非意味着该书的成书时间就是此时,而应是此前。另外,目前所见顾氏《中国音乐史》扉页上所盖“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朱印,可证此书为该校所藏并用于教学,并非确定成书时间之证。如果将1922 年夏《重编雅乐讲义》作为顾梅羹《中国音乐史》撰写的起步,而当年8 月20 日雅乐科新生入校已见此书,仅就其文献阅读、查询及辑录的工作量而言,就需要化费相当时间;若再加上撰写成书、手书刊印的时间,显然难以完成。就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成书而言,其刊印运用的是清末民初时的石板印刷术,可谓“手书上版石印本”,此可以由馆所、院校自行印刷,不必交由出版社发行,更不受限于书号。就其成书时间而言,由于作者没有在书中说明,我们无法确定一个成书的时间点,因此,在对此书成书时间的判断上,我们可以依据相关史料进行分析,确立一个撰写成书过程的时间段。
就顾梅羹《中国音乐史》一书的成书背景与过程而言,在目前的认知范围内,这册书虽因重修雅乐讲义而加入系列教材,但由于重修雅乐讲义之事,如吴昊文中所说,正是为了克服初编教材“且编且习,急就成章”和“阅时未久,何敢言精”的问题,才有杨、彭、顾三人悉心考订之为。⑮参阅吴昊:《“育才馆”附设雅乐专修科音乐史事考(1921—1924)》,第78 页。而这本书的撰写,因其史料阅读面太大,再加上古代音乐史学科知识的建构在当时几乎无有参照的情况下,其撰写的难度也可想而知,所以不太可能在1922 年夏季重修雅乐讲义时提出增修原来没有的《中国音乐史》,而于当年夏季便完成此书。⑯据泉圣《阎锡山的“育才馆”》一文的介绍,山西育才馆“定为每年9 月开学,翌年7 月毕业,实际学期10 个月”,寒暑假期各1 个月。夏季能集中使用的时间只有1 个月。因此,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成书时间⑰就“成书”而言,基本含义是指“写成书”;“刊印”“刊行”则指刊刻、排印出版。,当早于1922 年8 月20 日雅乐科新生入校。其撰写工作的准备和开始,当在顾梅羹1921 年秋到山西育才馆雅乐科任教之后,应是其在重修雅乐讲义之前已有积累并准备之事。因此,顾梅羹着手撰写《中国音乐史》的时间,估计在1921 年秋季之后;而完成撰写并刊印成书的时间,可判断为1922年秋季开学之前。
本问题的讨论,自然会关涉到“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著作产生的问题,这里自然需要就顾梅羹和叶伯和的两部《中国音乐史》作一个对比(这里不作详论,只是作一个简单的比较)。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成书时间,吴昊认为《中国音乐史》作为国民师范雅乐专修科的课堂讲义,“其成书时间应该在1922 年8 月20 日国师雅乐科新生入校之后”⑱吴昊:《也谈“第一部〈中国音乐史〉”》,第65 页。。本文认为,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撰写当在1921 年秋季之后,其撰写完成并刊印的时间应在1922 年秋季开学之前。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其上卷于1922 年刻印,采用陆续发表的方式,于同年11 月至次年元月在上海《益世报》连载;下卷则于1929 年在《新四川日刊副刊》发表,其成书过程长达7年。另外,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下卷更像是一个提纲,不具备音乐史著作的基本形态,甚至作者本人也表示该书“决不敢说是一种著述”。因此,相比较而言,称顾梅羹的《中国音乐史》为近代第一部中国音乐史通史性著作,是符合实际的。
二、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撰述特点
近代中国音乐史的通史性撰述,始于顾梅羹的《中国音乐史》。就青年琴家顾梅羹而言,撰写中国音乐史,自有其历史机遇。琴人写史,古有北宋朱长文开《琴史》撰写之先河。顾梅羹虽为琴人,然其所撰《中国音乐史》,体例框架,通贯上古近世,列述诸代之乐,专论雅乐、琴学、燕乐、戏曲等,呈现了一种新的乐史建构,其材料虽主要来自经史,然决非翰林编修撰写一朝一代乐史之为,而是不弃传统礼乐、琴道的新文人所为。其文化眼光,虽坦言国粹,然其人既关注中国音乐历史变迁之形迹,又以西学为鉴,沟通交流,以为借石他山之助;既辑述古乐数千年大观,又期望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探究中国音乐之本义。其所在意者,在于乐教、琴学传统的传承而非复古。只是面临深刻的文化转型、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不弃礼乐琴学文化精神,取保守立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并非弃旧学便可称新文化,习中乐便可谓甘落伍。顾梅羹以乐教、琴学陶冶性情、移风易俗之功能为重,传授琴学、编纂教材、教授中国音乐史,百年之后,仍可见其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价值。因而,顾梅羹所为,当属新文化中志在传承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之文人所为。
顾梅羹《中国音乐史》一书的体例,由目录可知。全书分设五编(第一编绪论、第二编上古音乐、第三编中古音乐、第四编近古音乐、第五编近世音乐)。如作者在该书“结论”中所说:“故本编之作,主于纪事,分为四期,而以绪论总其端,都五编四十四章。其中纲领,区为雅乐、琴学、燕乐三大项。”全书各章所设标题,主要以朝代体为基本框架,标识历朝历代音乐,亦有具体到某一朝代之年号,如汉代的“惠帝至武帝时之音乐”“元帝至平帝时之音乐”,以及唐代“开元天宝间之极盛”。各章标题,亦有以各代之“雅乐”“琴学”“燕乐”以及“戏曲”来命名,亦有以“诗词学与音乐之关系”为标题。在各章标题中,“琴学”出现6 次,“燕乐”出现4 次,“雅乐”出现3 次,“戏曲(昆曲)”出现3 次,“诗词学”出现1 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对历代音乐种类的重视程度。
除绪论,所设诸编,再设章分述各代内容。可以看到两种历史分期体例的结合,即受近代新史学影响而采用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历史分期方式与传统史学中采用的朝代体历史分期方式的结合。顾梅羹在“绪论”的“音乐史上之时代区画”一节中,对此历史分期的设定,专有说明。所言“音乐史上之时代区画,就历史上之天然界限,可分为四期”,所谓“天然界限”,可视为顾梅羹在传统的朝代框架之外,对中国音乐历史发展大势与形成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主要特点,通过历史分期反映出来的一种认识。该书二至五编,下设诸章分述各代音乐的主要类型及内容。其中的第二编以“上古音乐”命名,包括传说时代的伏羲、唐虞至秦朝的音乐,设有五章;第三编“中古”包括汉至隋的音乐,设有十二章(今本缺四、五章);第四编“近古”包括唐至明的音乐,设有十九章;第五编“近世”包括清代音乐,设有三章。“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一类历史分期法的运用,虽然并不少见,但少有人追究此类分期法的依据是什么。但好处是大处着眼、繁中求简,比“二十五史”的框架更简洁。其背后,亦有“分久必合”“大一统”观念与以强盛、长久朝代的认知有关。如周秦之际、秦汉之际、隋唐之际、明清之际,顾梅羹称其所作历史分期是一种“天然界限”,与其注意到这些问题有关。至于他专将清代划为“近世”,是就“有清一代,若存若亡,兼之西乐东来,尤为一大改革”而言,此分期特别关注到“西乐东来”,视为中国音乐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并以“改革”相称,所论应是以清代洋务运动新式学堂的建立,设立唱歌课,推行学堂乐歌,欧式军乐兴起,社会上以西乐为新乐的变革为背景。
顾梅羹的中国音乐史分期“四期”说,并非只关注政权更替,而是也关注到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现象和趋势。如其“绪论”中所言,上古音乐发展的主要内容和节点,是雅乐(即礼乐文化)的“发达于成周而摧灭于赢”;中古音乐的发展特点,则在于音乐文化的变迁,即所谓“音乐之道逐渐变迁”,“而琴学独立,胡乐流传,实为音乐中之一大关键”,此将作为文人音乐的琴学的独立(形成独特而自足的人文品格)、胡乐的流传以及必然相伴的文化交融和变迁,作为这一时期音乐发展的重要特点;近古音乐的发展特点,是“汉讫隋唐宋”(也包括元明)历代宫廷音乐中“极为发达”的燕乐。至于将清代称为“近世”,“绪论”中所谓“若存若亡”,语焉不详,但对于清代音乐特点,除提到“西乐东来”,正文中亦设三章分述清代之雅乐、琴学、戏曲;“结论”中讲历代音乐文化之变迁,亦提到“六变而有元明戏曲之勃兴”,对元明清三代戏曲兴盛的特点有所把握。
顾梅羹《中国音乐史》一书所作历史分期以及对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可以说是从文化变迁看历史、写历史。顾梅羹的这一历史撰述人文视角,与叶伯和撰写提倡的“进化论”显然不同(虽然其撰述并未有所体现)。顾梅羹以“文化变迁”视角审视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是因其历史价值观,即以音乐“陶冶性情,发舒心灵”,“能收移风易俗之效”为中国音乐文化之本质与特点(而非仅以“听”为音乐之本质),是以此礼乐文化观为中国音乐文化核心价值观。顾梅羹在史学观念上以“文化变迁”建构中国音乐历史发展之主线,其认识集中反映在该书“结论”之首段。这是顾梅羹在完成此书正文撰写之后,就历代音乐之“变迁”,对全书所述而做的一个概括性表达:
中国音乐,阅四千有余年。其间一盛一衰,一开一阖,变迁之形,蕃赜极矣。综其大者言之,则皇古之草创,一变而有姬周之完备;再变而有周末之陵夷、赢秦之摧灭;三变而有汉之乐府、琴学、魏晋之清商;四变而有六朝之杂乱、隋氏之统一;五变而有唐宋燕乐之繁盛;六变而有元明戏曲之勃兴。
对于促成每一历史时期音乐文化变迁的原因,青年顾梅羹写道:
凡每一个变迁,或与其国势有关系,或与其文学相表里,或与其风气为转移,要莫不各有其特色与其精神,诚可谓极世界未曾有之钜观,而为音乐史上可大书特书者矣。
其中所谈,以其宏观眼光,概言影响每一历史时期或朝代音乐文化变迁的原在,其中既谈到音乐文化变迁的外部环境、如朝代兴衰之“国势”对音乐发展的影响,又谈到音乐在与其他艺术的共生关系中、如与诗词音乐的结合中成就的音乐发展和繁荣,还谈到音乐因社会文化风气的改变而形成新的变迁,而中国音乐每经历一次新的文化变迁,就都会形成新的乐种、乐类之特色以及新的文化精神。顾梅羹“结论”中有关中国音乐文化变迁的论述,虽然言简意赅,但是未能展开,原因是其正文的撰写,主要是依历代官修史书中的基础性音乐史料辑录、撰述而成,其所述重在对构成中国音乐史基本内容和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建构,若要将这些认识通过具体事例的分析再作展开,则需要通过一些专题研究才能做到。但这仍然不妨碍我们将此作为顾梅羹的音乐史观来对待。
顾梅羹在中国音乐史撰述中形成的,以宏观视界对中国音乐发展变化特点以概括、认识的“文化变迁”论,可谓一种音乐历史文化发展观。其既言主要现象、特点并分期、分类,又言形成诸现象的社会文化动因,其所论虽言简意赅,仅为提纲挈领之论,但其所论却有其针对性,并非无学理考量。其主要的关注点,是中西音乐史治史眼光之不同。在当时对西学难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所谓中西音乐治史眼光,也只是以传统史学为根基与刚接触到西学皮毛的中国学者之间的眼光之不同,但即使是在浅层、皮毛的接触中,中西音乐观念之间的某些差别,已经影响到其音乐史观,却也是事实。这也恰恰表明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存在,并在其碰撞、交融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了。⑲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价值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自近代以来是不断加深乃至完善的,并且也形成有同的音乐史观以及音乐哲学观念,此处所言,仅仅是就顾梅羹当时面对的情况而言。从顾梅羹在“结论”中所言可知,撰写中国音乐史应持何种音乐史观的争论,在近代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著作的产生过程中就已经产生。其中反映的是当时学人面对中西文化时,对中西文化不同的认知和态度,甚至学理认知上的差异。
首先要说明的是,顾梅羹是认可并肯定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他在《中国音乐史》“结论”中说,“自清代海禁大开,变政兴学,葡人徐日升、意人德礼裕以西乐流传中国,列于学科,一时有识之士,趋之恐后。其初意盖主于中西音乐之沟通而冀得借石他山之助也”。其所言概括的是一个过程,如“列于学科”,当指清末“变政兴学”,学堂乐歌列为学校课程,设为学科。并认为学习西乐,确有“借石他山之助”的功效。但是他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醉心欧化者流,遂反变本加厉,一唯西乐是崇。凡中乐旧有之典章文物,则以为无一可取,诽谤诋毁,不遗余力,间有一二留心及之者,又皆以西乐眼光强制牵合,于中乐之本义,毫无所知”。这里情感上的不满,溢于言表。
尝见某君主张,谓音乐乃艺术之一,不能与政教相通,中国各书所载音乐之事,皆为帝王家谱,非学者所发明,无音乐史之价值,须将中国以清音乐上之一切旧观念尽行打消,再以科学哲学上之新眼光观察审定,更须将西洋之时代互相比较,如此弃取,始得谓之音乐史云云。
其中所说“某君主张”之见解及音乐观念,至今犹存,对于吾辈而言并不陌生。关于传统史学之所载音乐史料有无音乐史研究之价值,不必在此讨论、展开。但与音乐史观相关、与认识音乐存在相关的学理依据,却是顾梅羹尤其强调并关注的学理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即音乐究竟是声音的、或曰纯艺术的存在,还是文化的存在。顾梅羹在“结论”中针对“某君主张”,就中西音乐之不同,做了一个学理的区分,他说:
夫中国音乐,原非艺术,本由人心而生,不可以为伪,所以陶冶性情,发舒心灵者也。故古人以之为化民致治之具,而能收移风易俗之效,与西洋米有塞克(music)之根本完全不同。米有塞克者,纯属于耳,无关于心,乃释放觉官之门户者也,故西人以之为激刺感觉之具,而与移风易俗无关。盖彼此性质不同,学术各异也。近西人某音乐家论其区别详最,其不能适合,昭昭甚明。
此中对中国音乐的认识,显然来自《乐记》中的传统儒家音乐思想,认为中国音乐占主流的求真致善观念和导向,具有情感上“陶冶性情,发舒心灵”的功能和教化作用,认为中国音乐(即“乐”)如其所言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而“原非艺术”,与“music”之“根本完全不同”,亦是被确定的。这可以说是近代最早有关中西音乐本体认识差异或比较的表述。虽然这些认识及其观念的表达并非那么思辨,但是却把握住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中认识音乐本质最核心、也是起主导作用的观念。
关于顾梅羹《中国音乐史》正文之内容,如作者在“结论”中概言:“史之为言,所以纪事。”其所记之事,主要来自历代官修正史以及琴论、戏论著述等。除记述历代乐事、乐类、乐律、乐调、乐曲、乐器等,其撰写亦时有所论。顾梅羹的撰写,对史料出处,疏于证引,此或与当时传统史学记述方式有关。顾梅羹在该书首页对其撰写方式自称“辑述”,此或言该书的内容主要依据并辑录现有史料,经修纂成文而用于教学讲述。顾梅羹各章之辑述,如其所说:
凡历代升降之原,沿革之迹,以及源流之终始,派别之异同,均已觕其端末,虽剪裁穿插之间,或不免有乖漏之处,然其大体,初不外是使学者亦知中国数千年来固有国粹,原曾有如许之大观,不致随二三末俗之子同声附和、一概抹煞,是则编者之隐衷也。
在顾梅羹自己看来,这本六万多字的《中国音乐史》对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包括其“历代升降之原,沿革之迹,以及源流之终始,派别之异同”,只是做了一个粗略的梳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觕其端末”的作为,不但足以满足当时国民师范教学之需,并且也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科系统知识,在这近代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著述中得到基本的呈现,并且也足以让后人为这部近代早期中国音乐史著作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以及所建立的近代中国音乐史著述第一根标杆的品质而深感庆幸。
顾梅羹先生作为曾于国民师范院校从事教师教育的中国音乐史教师和古琴教师,作为近代第一部《中国音乐史》教材的编撰者,其人其作,其教其业,虽机缘短暂,然为使学者“于中西音乐之沟通而冀得借石他山之助”,于文化激荡中阐明中国音乐文化之本质、著录中国数千年音乐文化之大观,承国学以开新学,足以让吾侪后学心生敬意!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
-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第六届“长江之韵·世界知名音乐艺术院校交流展演季”成功举行
- 二十世纪欧美中国音乐研究学位论文述要(上)
- 论工尺谱起源与唐代文字谱的关系①该文是耐尔森教授据他在东洋音乐学会东日本支部的第41 回例会(2009 年)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文章收录于矶水绘编:《文学与音乐史论集:诗歌管弦的世界》(「論集 文学と音楽史:詩歌管絃の世界」),大阪:和泉书院2013年版,第65—93 页。译文已获作者授权许可。
- 虽密尚能走马,虽疏犹不透风:记倪秋平先生
- 一种革命
——论中国交响音乐创作之于奏鸣曲式刚性原则的弱化 - 从作品曲式的框架分析到音乐元素运动逻辑的解读
——对罗伯特·舒曼《第一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分析的教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