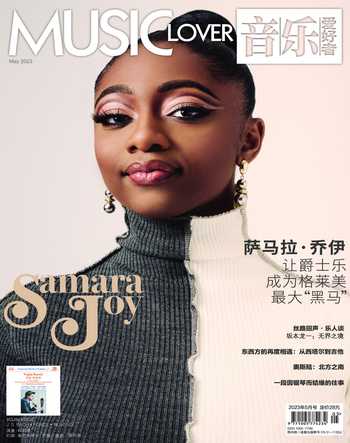海上歌调钩沉录(三)
俞一帆
东进随想曲
2022年暑假的时候,宣传部门抽调本市几位音乐史料研究者去江浙一带采风,收集革命音乐历史资料,编撰一本大型的献礼书,我也有幸忝列其中。接到通知后,我匆匆收拾了一下,第二天一早便随着一行七人乘坐中巴出发了。
一路很顺当,下午三点就到了天目山。地接老张提议,不如趁这时间去附近景区转转,穿过梅溪镇村庄,没走几百步路就是了。
如今农村真是大变样了,一幢幢二层楼房造得像小宾馆一样精致玲珑。每户门前还有个小花园,桃红柳绿地妖艳着。不知是谁发现有一家花园的大树上,竟结出了绿色的柚子,翠叶粉墙相衬,煞是好看。大家忍不住停下脚步,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这时,我们听到二楼半开的窗户里传出小提琴演奏的《新四军军歌》,尤其是最后一句“东进!东进”,双音与和弦的华彩句显得气势悲壮而豪迈。大家正在诧异从未听到过这首乐曲的无伴奏小提琴改编版,正想从头听听看,作品却换成《托赛里小夜曲》了。这首曲子由钢琴伴奏,柔美的琴声略带一丝哀伤和缅怀之情。

这两首曲子放在一起也太不相干了。听得出演奏者的功力很不错,然而这样的琴声响起在偏僻乡里,倒是令人浮想联翩呢。老张见我们拍完照还不想走的样子,看出我们这伙人的好奇心,笑着说:“哦,这是我们李老师在拉呢。”接着,他又低声自言自语道:“真是的,怎么没想到他呢?”他看看手表,对我们说:“不如就先去采访他吧。”
原来,他说的这位李老师就是梅溪群众文化馆的老馆长,已退休多年。他的父亲曾是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据说跟随来华的小提琴家卫登堡学过几年提琴,抗战时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和这首《新四军军歌》的作曲者何士德还是同学呢。1939年,他亲眼目睹了陈毅的诗词是如何被谱写成军歌,又如何不胫而走,四处传唱“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而成为中国的“马赛曲”的情景。

“李老师的父亲曾与何士德一起,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里教战士们唱歌。许多年轻人加入新四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唱这首军歌。在皖南事变中,李老师的父亲不幸受了重伤,队伍也被打散。他只好隐匿在当地老乡家中养病,后来就在当地的学校里教音乐了。”
老张边说边推开花园的栅栏,高声呼喊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开门,看着我们一行人,一脸惊讶。听老张说明来意之后,老人立刻热情地招呼我们上楼,让我们在大房间安坐。这便是书房兼客厅了,靠钢琴一边的墙上挂着一幅身着威武戎装的军人照片,想必就是李老師的父亲了。两边是一副对联:
携琴心勇铸剑胆
怀侠骨以咏诗情

短短的十四个字,概括了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坐在琴边的小男孩挺乖巧,见客上门,立刻到厨房备茶去了。小鲍瞅见书橱边的写字台上放着一本《新安旅行团歌曲集》,眼睛都亮了。她早知道有这本书,那里面有很多当年新安旅行团创作的歌曲。前两天她想找陶行知作词的《三万里路跑回来》(任光曲)、《儿童节歌》(贺绿汀曲)、《锄头舞歌》,但是找不到这本文献,正在犯愁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一行人中年纪最大的孙教授说:“太好了,新安旅行团的资料可以说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了,他们当年的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知道。”

为实践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苏北创建了一所新型实验学校——新安小学,新安旅行团便是1935年在此诞生的。从抗战开始,这群十多岁的孩子就告别家乡,奋勇踏上了一边游学、一边宣传抗日救亡的行程,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课堂中唤醒民众。新安旅行团的队伍前后达六百余人,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大革命历史阶段,十七年里沐风栉雨,行程五万多里,奔走在炮火弥漫的二十二个省份,用歌声作为武器投入战斗。
这些“小先生们”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歌咏队教广大群众唱爱国歌曲、组织乡村教育活动。许多革命艺术家,如田汉、洪深、冼星海、吕骥、张曙、蔡楚生、贺绿汀、王洛宾等都给予了新安旅行团切实而有力的帮助指导。塞克和王洛宾为他们创作了《新安进行曲》,田汉、张曙为他们写下了团歌:“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的家破产了,我们的国遇了盗。听啊!到处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1936年10月,由任光协助、冼星海指挥、百代乐队伴奏,新安旅行团在上海演唱、录制了唱片并行销全国。还有冼星海的《救国军歌》等歌曲也是经过新安旅行团孩子们的试唱后才定稿发表的。
“今天是家父忌日,”见我们对老歌谱爱不释手,李老师又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新四军歌曲》递给我们,“我刚才拉的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两支曲子。”我们这才注意到琴上有个小巧的香炉,插着一炷细细的奇南香,一缕青烟正在袅袅飘散。
我们围着大圆桌而坐,边聊边传阅歌曲集。里面有许多熟悉的名字,原来投笔从戎的那些音乐前辈们,如任光、贺绿汀、孟波、章枚、沈亚威等,给我们留下了几百首革命歌曲。赖少奇、何士德的《渡长江》表达了“我们要渡过长江,获得更大的胜利”的决心,流行于皖南、皖北、江南、江北一带;任光那支雄壮的进行曲《别了,皖南》(又名《新四军东进曲》),作于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北移前夕,“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歌声充满了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但令人无比沉痛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音乐系的任光,一位极有音乐才华、为我们留下优美的《渔光曲》的音乐家,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
新四军七个师曾横跨苏、皖、鄂、豫、浙、赣、湘等广大地区,在陈毅、叶挺的关怀下,极其重视文艺工作。文工团伴随部队作战,参与根据地建设,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歌咏活动。它的影响力非常大,不仅创作了丰富的军旅歌曲,还培养了吕其明、龙飞、胡士平等一代音乐家。1941年,新四军在苏北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刘少奇兼任院长,贺绿汀、何士德、章枚等均在该校任教),同年在淮南二师创办了中國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化大队(黄粲等兼任音乐教员)。1942年,贺绿汀应二师政治部的邀请为其“抗敌剧团”进行了音乐整训(排练合唱、讲授音乐理论和音乐分析等),当时其他师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有关音乐的学习。
听李老师说起《托赛里小夜曲》,孙教授悄悄和我解释,“抗战胜利的时候,这首《托赛里小夜曲》和德尔德拉的《纪念曲》是当时最风行的曲子。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欧美宣战,这几首刚在欧美走红的曲子立刻在沦陷区被禁了。”

同来的老黄接上话茬:“所以抗日战争结束,上海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和逸乐电台就整天播放这两首曲子。这是人们在借这些歌扬眉吐气啊!”
“这胜利也来得突然,其实那阵子不可能有事先专门为迎接胜利而写的歌。”小鲍很理解地说。
李老师点点头:“但是家父也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改变自己的音乐生涯。他总是按照组织给他的任务,及时地让人们知道我们革命队伍在解放战场上的形势和胜利消息。”李老师一边收好小提琴,一边说:“刚才拉的这首根据《新四军军歌》改编的《东进随想曲》就是他写的,苦闷的时候家父就会轻轻地拉给我们听。”李老师招呼我们喝茶,继续说:“在学校里他还会悄悄地教孩子们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是民主青年》那样振奋人心的歌。”
“是的。”孙教授也记得那时的歌咏活动如火如荼。他兴致勃勃地说:“来来来来来,你来我来他来,我们一起来唱歌。一个人唱歌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唱歌使我们勇敢向前进,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孙教授唱的这首是由舒模创作的《大家唱》,后来因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一个教唱的片段被许多人记住而四处传唱。
老黄回忆道:“还记得那时我和大哥一起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大家唱活动。我们举着‘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的横幅,大哥在游行队伍里扮演投机倒把的奸商,大家指着他骂,‘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想到当年的画面,老孙不禁笑了起来:“这首歌好像就叫这个名字吧。”他记得舒模后来还写过《跌倒算什么》,同一时期流传的还有劫夫写的《蒋匪帮一团糟》以及《别让它遭灾害》(蒙沙词,李淦曲),等等。
“等到这里一解放,家父立刻联合附近几个中学的音乐老师,组织歌咏队,高唱《解放区的天》,上街欢迎入城的部队了。”
“说起入城部队,”教近代音乐史的钱老师说,“他们一边走一边唱许多部队歌曲,我第一次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朱践耳先生的第一首歌曲《打得好》,莱芜战役后成了解放区军民人人传唱的经典曲目。”
大家又把话题转到李老师身上。“您的琴拉得真好,把我们都吸引住了!令尊衣钵真传,国立音专的琴艺传统也后继有人了!”孙教授指着又回到琴边听我们聊天的小男孩说:“他也在学琴吧。”
李老师笑笑:“他能够学下去就好了。”
墙上的挂钟敲了六下,我们起身告别李老师。离开之前,大家提议在李老先生像前合个影,一起唱《新四军军歌》,表示我们对李老先生光辉一生的敬仰,告慰所有为今天的美好献出生命、献出理想的英烈们。当我们老中青三代一同唱起这支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的歌调时,剑胆琴心、侠骨大义的浩然正气仿佛从血液深处涌上每个人的胸膛。
东进!东进!
东进!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