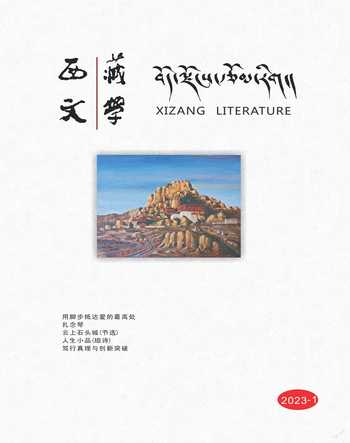扎念琴

平措朗杰,西藏日喀则人。1991年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院,2013年入伍,现就职于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散文、小说、诗歌陆续在《边防警察报》《西藏文学》等刊物发表,著有《樟木戍边情》《桑曲之恋》《雪山鹰笛》《消失的高原红》《消失的高原红》等;2021年短篇小说《消失的高原红》获西藏“新世纪”文学奖。
阿爸的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远方的雪山顶上洒落下,融化了一夜的寒意,将温情洒在青翠的玛多草原上。在地平线的尽头,一个披着藏袍的身影出现在天边的薄云之间,头上还戴着一顶奇形怪狀的帽子。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如同为他镀了金身,又像是为他披上了传说中战神格萨尔王的金色铠甲。
从金红色的朝霞里走来的是一个青年,和青年一同从天边越来越近的,还有他悠扬的歌声。
清晨的草原还没有完全苏醒,勤快的女人就开始挤牛奶、打酥油茶、揉糌粑,大多数的牧人则裹着厚实的藏袍睡在帐里,尚未离开甜美温暖的梦乡。大部分牦牛和羊群随意地卧在草地上,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零星几座帐篷上升起的白色炊烟,反而使这片草原更显空旷。
边走边不停说唱的青年似乎并不介意听众的缺席。事实上,他正唱着格萨尔大王的威仪雄姿给才从雪山上升起的太阳听;他唱岭噶草原上袅袅的桑烟给尚未来得及消失的月亮听;他将森姜珠牡的美丽唱给开满五颜六色鲜花的草原听;他将贾查的赤诚唱给被朝阳加冕了金冠的雪山听;他将查香丹玛的英勇唱给涓涓流淌的河流听。
太阳、月亮、雪山、草原和河流,都是他的听众。而随着天光越来越亮,更多的听众,也渐渐地在他周围聚集起来。醒来的牧人们被流浪艺人的说唱吸引,对他们而言,格萨尔的故事百听不厌,更何况这位神授艺人②的说唱尤其精彩。
聆听说唱的人群里,挤着一个看起来格外幼小的身影。那个六岁的男孩儿一双黑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竖着耳朵听艺人的说唱,脸上充满了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深沉表情。
流浪的艺人这次给玛多草原上的牧人们说唱的是少年觉如《赛马称王》③的故事:因为楚通从中使坏,岭国年幼的王子觉如④与母亲郭姆被驱逐。然而忠心耿耿的岭国老总管绒查擦根却记得天神的预言,与嘉洛家族一起暗中支持觉如得到了宝马江噶佩布。楚通⑤的诡计终究不能得逞,神子觉如也必将获得胜利,成为岭国的雄狮大王。这个故事每个格萨尔艺人都会说唱,只是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直到太阳高高地升起,人们投在地上的影子只剩下一天中最小的那一团时,《赛马称王》的故事才讲完。格萨尔王如愿登上了宝座,嘉洛的公主、草原上最美的姑娘森姜珠牡也嫁给了雄狮大王。草原上的骄阳如同格萨尔王的功绩一般明亮,天空一片湛蓝,没有一丝云彩。而围着艺人听说唱的牧人,也豪爽地将糌粑、酥油和牦牛肉送给说唱 艺人。
人们渐渐散去,唯有那个六岁的男孩依旧呆呆地坐在草地上,仿佛沉浸在故事中激烈的赛马大会上,没有回过神来。神授艺人多杰注意到这个小男孩,对他友善地一笑,便被几个牧人拉扯着去他们的帐篷喝酒去了。
男孩依旧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一个声音将他唤回现实:“格桑——格桑多杰——回来吃饭了——”
格桑多杰回过神来,看看四周早已散开的人群,神授艺人也早已不见了踪影,他这才带着几分遗憾地“哟”的应了一声,从草地上爬起来,不舍地看了看刚才说唱艺人站着的位置,循着阿妈嘎玛卓玛的呼唤,飞快地跑回自家的 帐篷。
回到帐篷里,格桑多杰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把阿妈捏好的糌粑团蘸着辣椒酱吃,嘴里还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位出现在玛多草原上的格萨尔神授艺人和他说唱的《赛马称王》的传奇故事。
嘎玛卓玛将儿子面前的酥油茶碗添满,望着兴奋的儿子慈爱地笑了笑,想要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却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声轻叹。格桑多杰听到阿妈的叹息,正捏着糌粑团往嘴里塞的手忍不住停了下来,疑惑地抬头看向阿妈。
嘎玛卓玛注意到儿子格桑多杰的目光,便放下了手中装满酥油茶的茶壶,揉了揉格桑多杰的肩膀。随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格桑多杰像是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喃喃道:“如果你阿爸唱的话,一定比任何人都唱的好。”嘎玛卓玛的声音轻得就像空气,轻到似乎吹不起一片羽毛。
阿妈的这番话,格桑多杰听得似懂非懂。他端起碗,喝了一大口酥油茶,又伸出湿润的红红的舌头将沾在唇边的酥油舔干净,问道:“阿妈,阿爸在哪里?”过去的六年里,格桑多杰从没有见过自己的阿爸,他已经习惯了和阿妈相依为命的生活,仿佛这才是理所应当的。况且牧区的草原上,没有父亲的孩子也不只有格桑多杰一个。
这是格桑多杰第一次问起自己的阿爸,嘎玛卓玛并无心理准备,一瞬间竟慌了神,短暂的愣怔之后,嘎玛卓玛回过神来,迟疑了一下才说:“你的阿爸,也许是在……”说到这里,她的语气突然笃定起来,仿佛是要说服自己,“在回家的路上。”
对于才六岁的男孩来说,嘎玛卓玛的语气和表情变化并未让他有所察觉,因此,格桑多杰不假思索地继续追问:“那阿爸还要多久才能够回家?”
看着儿子黑亮的眼睛里单纯的目光,嘎玛卓玛脸上的神情柔和下来。她往面前的碗里加了一勺白糖,捏了一块糌粑递给格桑多杰,然后才轻声回答:“阿爸什么时候回来,恐怕只有雪山后面的云才知道。”
格桑多杰接过阿妈递来的甜甜的糌粑,掰了一块塞进嘴里,眼睛却依然疑惑地看着嘎玛卓玛。嘎玛卓玛看出儿子的疑问,便安抚道:“格桑多杰,快快长大吧,长成像你阿爸一样正直勇敢的男人。到那时等你阿爸回来,你就可以像个男子汉一样和阿爸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一起唱歌、一起放牧了。”
听着阿妈的话,格桑多杰喝了一口酥油茶,将口中的糌粑都吞了下去。不知为何,他隐约觉得阿妈仿佛是在透过自己,寻找另一个人的影子。
也许是阿妈的目光让格桑多杰感到太陌生,也许是那目光的焦点太遥远,格桑多杰眨了眨眼睛,心中的疑惑依旧没有散去。于是,他再次开口发问:“阿妈,阿爸一定会回来吗?”格桑多杰对“阿爸”这个词汇并没有太多的幻想,然而直觉告诉他,在阿妈的心中,有一个只属于她和阿爸的世界,而格桑多杰也开始渴望了解那个世界。
面对儿子的问题,嘎玛卓玛想都没想便脱口说出:“会的,他……一定会回来。”她的目光突然从遥远的地方收回来,带着坚定和踏实,令格桑多杰感到阿妈终于从遥远的云端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突然想起了什么甜蜜的往事,嘎玛卓玛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她起身将格桑多杰的酥油茶碗添满,然后温柔地替格桑多杰整理了一下皮袄,再捏了一块糌粑递给格桑多杰。
注视着吃糌粑的格桑多杰,嘎玛卓玛在儿子对面坐下来说:“你的阿爸将他最心爱的扎念琴留在了家里,所以,他一定会回来,回到他最心爱的扎念琴和最心爱的儿子身邊……”“回到他最心爱的女人身边。”最后这一句嘎玛卓玛没有说出来,她的脸上微微发烫,双颊升起两朵红云。
阿爸离家去远方的时候,格桑多杰还在阿妈的腹中。阿妈的话说得如此笃定,令格桑多杰心中也暖暖的,对自己从未谋面的阿爸也多了几分好感与好奇。他咽下一口糌粑,又继续追问:“阿妈,阿爸的扎念琴在哪里?”
那把扎念琴,嘎玛卓玛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仿佛将琴藏好了,那个男人就必定会回到她的身边再也不会离开她似的。
嘎玛卓玛起身洗了手,认真地点起藏香,随后在若有若无的香气中打开了家里那只自格桑多杰的阿爸离开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的箱子,取出了用羊皮包着、用氆氇裹着、最外面还系着哈达的扎念琴。
带着如同朝圣般虔诚的表情,嘎玛卓玛将琴从层层包裹中解出来。格桑多杰被阿妈的专注和虔诚所感染,也郑重地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琴,拨动了一下琴弦。
随着清脆的声响,格桑多杰感觉到自己心中似乎也有一根弦被拨动了。他隐约感到琴弦里仿佛有种神奇的魔力,而他不知此时此刻自己的命运之弦,也已经和扎念琴的琴弦紧紧缠绕在了一起,再也解不开了。
少年的歌
时间像骏马般一年又一年地飞驰而过,十三岁的格桑多杰褪去孩童的稚气,多了少年的清秀。他的嗓音里渐渐有了从他阿爸那里继承的悠扬的磁性,而且已经能够像模像样地弹着扎念琴唱歌了。不仅如此,任何旋律他只要听一遍,就能准确地哼唱出来,玛多草原上的歌曲,没有一首歌是格桑多杰不会弹的,没有一首是格桑多杰不会唱的。
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格萨尔王传》的曲调。只要一有机会,他总会对着远处的雪山,或是天边羊毛般的云朵,拨动着扎念琴的琴弦,弹唱格萨尔王的故事。听过格桑多杰弹唱的人都说:“他有一副金子一样的好嗓子。”
夕阳就要沉入到地平线了,格桑多杰将家里的羊群和几头牦牛从放牧的草场上赶回家后,站在帐篷旁,抱着扎念琴弹唱起了他最喜爱的曲调。
嘎玛卓玛在帐篷里不紧不慢地打着酥油,不时照看一下煮得滚烫的热茶,听着外面传来的歌声和琴声,她脸上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忽然,某些往事闪过脑海,手上的动作也不觉停了下来。直到一声“阿妈”突兀地在耳边响起,嘎玛卓玛才从神游中回过神来。帐篷外的琴声和歌声都已消失,而格桑多杰正一边用哈达将扎念琴小心翼翼地裹起来收好,一边有些兴奋地喊:“阿妈,我饿了,可以开饭了吗?”
大概是因为刚才唱得太久,格桑多杰的声音带着沙哑,红扑扑的脸上带着笑容。看到活泼健康的儿子,微笑又回到了嘎玛卓玛的脸上,她说:“晚饭马上就好。先喝点热茶休息一下。”
格桑多杰端起碗喝了两口,舔去嘴唇上的茶沫,又开口道:“阿妈,我今天放羊的时候,又听到了新的格萨尔王的故事!”
这时,嘎玛卓玛已经将两大碗面片端上了桌。她从一只小铁皮罐里舀出了一勺辣椒,将大部分添进一只碗里,剩下的添进另一只碗里,随后,将辣椒少的那一碗递给了儿子。
面片的热气和香味充满了整个帐篷。放了一天的羊也唱了一天歌的格桑多杰陶醉地深吸了一口气,将面片马马虎虎地拌了两下,学着阿妈的样子向三宝和祜主祈祷后,便迫不及待地抱起碗开始狼吞虎咽。
嘎玛卓玛看着吃得香甜的儿子,不由得又想起了格桑多杰的阿爸。当年那个弹着扎念琴唱着山歌的英俊青年,最爱吃嘎玛卓玛做的面片,却很少加辣椒。他说自己是草原上的歌手,而歌手爱惜自己的嗓子,就像狮子爱惜鬃毛、雄鹰爱惜翅膀一样。
正当嘎玛卓玛有些出神时,格桑多杰的声音再一次将她从回忆里拉出来。“阿妈,我已经十三岁了,我能成为仲堪⑥多杰那样的格萨尔神授艺人吗?”因为嘴里塞着食物,格桑多杰的声音有些含混,然而他的眼神却带着清亮的期待,盯着嘎玛卓玛。
“我们的小格桑多杰继承了阿爸的好嗓子和唱歌的天分,长大以后,一定能和阿爸一样唱出草原上最动听的歌。”嘎玛卓玛笑着又说:“到那时你唱起《格萨尔王传》来,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尊敬。”
听了阿妈这番话,格桑多杰的眼睛亮了,他高兴地扒了几口面片,迫不及待地说:“阿妈,我们母子两个,就像觉如和阿妈郭姆一样。”他喝了一口茶将口中剩下的面片吞下去,又补充道:“阿爸不在身边,家里全靠阿妈。我长大以后,也要像觉如一样,让阿妈有享不完的福。”嘎玛卓玛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儿子,目光中带着宠爱,由衷地微笑起来。
时间如同奔腾的河水,永无止息。青翠的夏天一转眼就如野马般脱缰而去,却静悄悄地令人听不到马蹄声。转场的牧人收拾起全部家当,骑着马,赶着牦牛和羊群,牦牛绳上系着的秋天愈来愈短,当白色的冬天降临在玛多草原,牧人们也来到了新的牧场。
当草原被雪织成的银白氆氇覆盖时,就快要到藏历新年了。
随着藏历新年的临近,格桑多杰不知为何,一天比一天焦躁起来。他在帐篷里经常心神不宁,也常常跑出去一整天待在外面,嘎玛卓玛也不知道他这一天都去了哪里,而儿子出神地盯着天空的神情,又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的降临。
藏历除夕那天,玛多草原上也迎来了辞旧迎新的景象。五彩经幡在山上飘扬,仿佛为山披上了五色的衣袍。嘎玛卓玛像其他草原上的女人们一样,在帐篷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准备好过年的风干牦牛肉、推⑦、人参果、油炸点心和酥油。
在每一座帐篷里都弥漫着喜悦与欢乐的时候,格桑多杰却紧锁眉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然而没有人发觉他的异常。直到临近午夜,嘎玛卓玛喊儿子吃点心、换新衣的时候,才发现格桑多杰已经不在帐篷里,甚至不在帐篷 周围。
一时间嘎玛卓玛有些慌了神。草原冬夜的寒风,就连成年人都难以抵御,如果格桑多杰就这样在外面一整夜,恐怕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变成一座再也不会呼吸的冰雕。嘎玛卓玛披着皮袍,拿着并不十分明亮的手电筒,借着月光向帐篷周围搜寻格桑多杰的身影。
幸好,发现格桑多杰的地方距离嘎玛卓玛的帐篷并不算太远。只见儿子裹着自己的皮袍,嘴唇冻得乌紫,在一座玛尼石堆旁缩成小小的一团,靠着许多摞在一起的石头瑟瑟发抖。
看到冻得话也说不出的格桑多杰,嘎玛卓玛心疼地将他背回了帐篷。回到帐篷里,嘎玛卓玛为儿子倒了一碗滚烫的酥油茶让他慢慢喝下去。看着儿子的脸色渐渐开始恢复红润,嘎玛卓玛才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冷的晚上跑到帐篷外面去。
“阿妈,我……”格桑多杰看出阿妈的担忧,有些愧疚地想要解释什么,然而一张口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他故意想要睡在帐篷外面,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梦中能够看到岭国天神来赐予他说唱的能力。今天是格桑多杰十三岁的最后一天,如果依然没有天神找到他并告诉他被选中,他大概再不会有机会成为一名神授艺人了。
格桑多杰不知该如何向阿妈解释自己的期待和期望落空后的失望难过,低着头沉默了半天,才小声道:“阿妈,我已经十三岁了,格萨尔王还没有选中我,是不是因为我……天赋太差,或者前世做了什么坏事?”
说完这句话,格桑多杰的头又低了下去,几乎要埋在他刚刚喝完酥油茶的碗里,他用力地眨了眨眼睛,努力忍住了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
嘎玛卓玛假装没有看到儿子眼中星星点点的泪光,说道:“格桑多杰,你听过那么多格萨尔王的故事,现在还记得吗?岭国的勇士当中,有丹玛这样最初就被格萨尔王选中、追随格萨尔王的,也有辛巴那样,经历了一番曲折才成为岭国勇士的。但是,他们都是勇敢的大将,同样被格萨尔王器重。”
“可是,阿妈……”
“别着急,格桑多杰。也许格萨尔王已经派出了他的大将来找你呢,说不定现在还在路上呢。”
“就像阿爸还在回家的路上一样吗?”
听到这句话,嘎玛卓玛的心中一紧,然而随即她用温柔的声音坚定地回答:“对,就像阿爸一样,一定会来的。”
这一夜,格桑多杰睡在自己家的帐篷里。格萨尔王派来的大将依旧没有找他,他却睡得比以往每个晚上都更加香甜踏实。
离家流浪
自此,格桑多杰不再为没有听到格萨尔王的召唤而忧愁了,他总是抱着阿爸留给阿妈的扎念琴,弹唱著听来的格萨尔王的故事,还有那些流传在草原上的歌曲。
每当有唱着格萨尔王故事的艺人出现在玛多草原上时,格桑多杰总会着迷地聆听,而若是当听到格外喜欢的故事时,他甚至会追随在艺人的身后走出很远很远。每一次他不得不目送艺人的身影消失在玛多草原与天空交界的尽头时,他心里总会萌生出做一名草原流浪歌手的愿望。
每一天的太阳,从草原东方的边缘升起,划过无际的天空落入雪山的背后;每个月的月亮,从一弯纤细的新月到雪亮的一轮圆盘再到残月如钩,时光如同草原上追风的江噶佩布⑧飞驰而去,格桑多杰能够说唱的格萨尔王的故事也越来越多了。
格萨尔王一直都没有眷顾他,格桑多杰没有在梦中见到他所敬慕和仰望的格萨尔王,然而哪怕只是讲述那些他听过的、其他艺人说唱过的故事,他的琴声与歌声也是飘飞在玛多草原上最动听的旋律,吸引了无数牧人驻足聆听。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格桑多杰也渐渐明白了阿妈对阿爸的思念与等待。
他愿意相信,阿爸的确像阿妈说的那样,就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他是和格萨尔王派来寻找自己的岭国勇士结伴而行,而现在……他们或许正被热情好客的雪山之神挽留着,喝着香醇的青稞酒呢。
每每心中这样想着,格桑多杰总是忍不住望向天边的雪山方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格萨尔史诗。
草原上相熟的牧人们都说,格桑多杰快要成为一名格萨尔说唱艺人了。他们乐于邀请格桑多杰去他们的帐篷里或是牧场上弹着扎念琴说唱格萨尔史诗,然后将新鲜的酥油或是牛肉赠送给他,表达对他歌声的赞美和感谢。
偶尔也有从他乡回来的人,见过了城市里的舞袖笙歌,对格桑多杰说凭他的嗓子和琴声,他完全可以去参加电视上的那些唱歌节目。
每天,嘎玛卓玛挤奶、打酥油、捡牛粪、照顾幼小的牛羊、做家务,从清晨一直忙到天黑;而格桑多杰除了放牧家里的牛羊和帮助嘎玛卓玛做一些家务之外,就抱着扎念琴对着阿尼玛卿雪山,或是给邀请他说唱格萨尔的牧人们弹唱。日子就在《格萨尔王》史诗说唱中循环往复。
这样的生活在格桑多杰十六岁那年的冬季里某一天戛然而止了。
嘎玛卓玛的病毫无预兆。白天她还在像往日一样,煮好了酥油茶,又在炉火上烤了几个饼子,等着出去放牧牛羊的格桑多杰晚上回来吃晚饭。嘎玛卓玛还做好了一罐新的辣椒,又晾了许多新鲜的奶渣作为接下来几天的零食。她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因为辣子的缘故,那日她的晚饭比平时多吃了小半碗。
然而就在当天夜里,午夜时分细碎的月光朦胧地洒在草原上的时候,嘎玛卓玛突然发起烧来。她的喉咙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灼热的感觉就如同烈日炙烤沙漠一般。嘎玛卓玛不想吵醒熟睡的儿子,便挣扎着起身想去为自己倒一杯水。
当她努力起身的时候,嘎玛卓玛才感觉到自己仿佛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双臂软绵绵的,甚至撑不起身子,而双腿更是好像不属于她自己一样,完全没有一点知觉。嘎玛卓玛只得靠在垫子上喘息,歇息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攒了几分力气,伸手摸到桌上的杯子。
杯子里面睡前喝剩下的半杯茶水已经凉透,嘎玛卓玛顾不得许多,将半杯冰凉的茶水一口气灌下去,重又躺下,用被子将自己紧紧裹住。尽管并不安稳,嘎玛卓玛还是再次睡着了。
嘎玛卓玛从来没有想到,从那个晚上起,她就再也没有能站起来。
格桑多杰是被透过门帘缝隙挤进帐篷里的阳光晒醒的。他有些不习惯阿妈没有一边端来早餐一边叫他起床,但随即他就发现依旧在睡梦中的嘎玛卓玛脸色的异常。
在接下来的许多天里,格桑多杰为阿妈请过医生,也求过仁波切念经加持。他为阿妈放生了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甚至还请过咒师,盼望咒师的法术能够驱赶掠夺嘎玛卓玛生命的妖魔 鬼怪。
然而这一切,终究都没能留住嘎玛卓玛的生命。
按照藏族的传统,因患传染性疾病而逝去的人,是不能被天葬或者水葬的,否则可能将疾病传染给秃鹫或水中的生灵。格桑多杰遵守着古老的传统,请来了僧人为阿妈诵经超度。
青稞、黑豆、稻米、竹段,一捧捧、一盆盆地被泼洒在跳跃的火焰之中。格桑多杰立在一边,表情虔诚,透过袅袅升起的桑烟,他看到坐在火堆前吟诵经文的喇嘛,随着时浓时淡的桑烟忽而模糊、忽而清晰。
火堆旁边的架子上,许多盏酥油灯微微摇曳。嘎玛卓玛和格桑多杰在玛多草原上没有太多的亲人,这些酥油灯大都是草场的牧人或者他们的朋友为嘎玛卓玛所点亮,还有一些,则是喜欢听格桑多杰说唱的牧人特地从远方赶来点亮的。
在酥油灯的火光中格桑多杰仿佛看到了阿妈的身影。他用力地眨眨眼,试图将阿妈的身影看得更清楚。然而只有一盏盏酥油灯,静静地守在那里。
愣怔了许久,格桑多杰才意识到自己的脸上似乎有些发痒,仿佛有小虫正在慢慢爬过他的脸。他抬起手,感到湿润的触感,看到指尖的水迹,才发觉原来不知何时,泪水已经悄悄滑过他的 脸颊。
格桑多杰将脸上的泪用力地抹去,随后他重新抬头看向酥油灯,想要再看一眼阿妈。然而这一次,他没有再看到嘎玛卓玛的影子,却仿佛看到了骑着火红色宝马在草原上飞驰的格萨尔王和岭国的千军万马。
为嘎玛卓玛做完法事后,格桑多杰将家里的大部分牛羊都送回到了嘎玛卓玛的娘家,又将剩下的一些东西分赠给了帮助过他的朋友们以及草原上的其他牧人,他只给自己留下了一匹马,还有那把扎念琴,以及嘎玛卓玛生前经常戴在身上的一颗绿松石和藏银手镯也留下来作为纪念。
做完这些事,格桑多杰骑着马,背着扎念琴,只带了一些路上必需的口粮,便开始了在草原上的流浪生活。
央金姑娘
离开了家的格桑多杰成了玛多草原上的流浪艺人,弹着扎念琴,说唱《格萨尔王》史诗,四海为家。除了格萨尔王的故事,他有时也会唱其他的一些草原上的歌曲,然而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他当作一名《格萨尔王》闻知艺人⑨。他们热情地邀请他说唱,也慷慨地将青稞、酥油或者肉干送给他。
每当朝阳东升时,格桑多杰从没有想过他究竟要去往哪里,只是信马由缰,到了晚上,他便披着一身月光,蓋着藏袍,枕着洒满星辉的石头或是马鞍,露宿草原。从前他和阿妈相依为命,阿妈去世后,他最心爱的便只有阿爸留给阿妈、阿妈又留给他的扎念 琴了。
究竟在草原上流浪了多久,格桑多杰并不十分清楚。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有一两年甚至更多的日子,草原上的牧人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
他只记得有一天,金色的太阳没入雪山的背后,只留下一缕红黄的余晖,为万里无云的深蓝色天空镀上一抹淡淡的金边。他拴好马便坐在草原上,对着被夕阳染上金顶的雪山弹了一段扎念琴,唱他最喜欢的那些歌曲。
不知不觉中,天色愈发暗下来,格桑多杰也已经裹着藏袍,怀里抱着扎念琴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的格桑多杰感到自己仿佛身处一片广袤无际的草原,青翠的牧草深深浅浅地反射着太阳的光辉。而草原尽头的地平线上,则耸立着连绵的雪山。格桑多杰不记得他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景象,然而这片草原在梦中却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就在打量着周围景色的时候,格桑多杰突然看到眼前出现了一顶帐篷。他无法确定那顶帐篷究竟是凭空出现,还是一直都在那里,然而无论如何,那顶帐篷仿佛带有某种奇异的吸引力,让他身不由己地一步步向着帐篷的方向走过去。
随着格桑多杰离帐篷愈来愈近,那顶帐篷却突然一下从他的眼前消失了,他下意识地低下头看了看脚下的青草,再抬起头的时候,却看到在原本帐篷矗立的位置上,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
那姑娘身上的藏袍看起来十分朴素,头上却戴着绿松石、天珠和蜜蜡编成的华丽头饰,额头正中则是一颗鸽子蛋大小的红珊瑚。姑娘的长发梳成许多条辫子,辫子里还缀着五颜六色的彩线。格桑多杰注意到,姑娘的耳环和手镯上,也都镶嵌着绿松石和红珊瑚。
梦中的格桑多杰觉得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瞬间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他呆呆地盯着姑娘看。姑娘对格桑多杰微微一笑,明艳的笑容使得格桑多杰挪不开眼睛。
看着年轻人痴呆的表情,姑娘的笑容更加深了几分。她轻盈地站起来,头饰和耳环随着她的动作摇曳。她伸出一只手在格桑多杰眼前晃了晃,说:“格桑多杰?”另一只手轻轻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袖,又喊道:“格桑多杰,快回到人间来吧!”
被姑娘这样一喊,格桑多杰回过神来。他看着眼前的姑娘,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顿时红到耳朵后面,热得几乎能够烫熟饼子。没等他意识到为什么从未见过面的姑娘会知道自己的名字时,姑娘已经笑着告诉他,她的名字叫 央金。
格桑多杰无意识地将姑娘的名字喃喃重复了一遍,只觉得央金的声音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仙乐,而她的名字,则是世界上最婉转美妙的音节。
“你……从哪里来?你的家在哪里?”格桑多杰急忙追问道。然而话音未落,格桑多杰又觉得似乎过于唐突,唯恐冒犯了央金姑娘,心中着急,脸上更加地烫红,神情也有些窘迫。
央金看着格桑多杰涨红的脸和不知该放在哪里的双手,忍不住捂嘴轻笑起来。格桑多杰有些尴尬,但同时也放松了不少,他觉得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才张了张口,央金似乎就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抢先道:“玛多草原上的著名歌手格桑多杰,你的琴弹得真 好听。”
听到姑娘这句赞美,格桑多杰脸上原本已经渐渐消退的红晕又突然加深了。他犹豫自己是否应该谦虚几句,但央金伸出一根手指抵在他的唇边让他不要说话,随后便拉着格桑多杰一起坐在了草原上。央金面朝雪山的方向坐着,静静地看着蓝宝石般的天上慢慢变幻着形状的白云。
格桑多杰咽下了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话,安静地坐在央金的身边。他循着央金视线的方向看着天边的云朵,只是不知不觉中,他的头便微微地偏过来,专注地盯着央金的侧脸,完全忘记了移开目光。
这个美丽的梦最后就定格在了央金美好的侧脸和她凝望着白云时恬静的目光中。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格桑多杰有些恍惚地四处张望,发觉自己并不在梦中看到的那片草原,才意识到央金姑娘原来只是他的一个梦。
格桑多杰不由得感到一丝失落。梦中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使那个梦显得如此真实。格桑多杰抱着扎念琴坐在草原上回味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来,就着风干肉吃了几口糌粑,又将藏袍重新穿好,背起扎念琴,跳上马背,继续他不知终点在何处的 旅行。
那时的格桑多杰还不知道,在梦中邂逅央金姑娘只是一个开始,从那以后,许多个夜晚的梦境中,央金都会出现。她有时会拉着格桑多杰一起轻盈地跳起欢快的锅庄,或是用悠扬悦耳的嗓音为格桑多杰唱起动听的山歌,有时,他们只是肩并肩坐在草原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或者什么都不说,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雪山、草原和云朵。
对于格桑多杰而言,只要和央金坐在一起,不用说一句话,时光就已经足够美好。醒着的时候,格桑多杰总是渴望知道央金究竟从哪里来。然而,格桑多杰始终没有梦到过自己询问姑娘家乡或者住处的情节,仿佛在梦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在一起唱歌、跳舞、聊天,而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问出来。
根据央金唱的山歌,格桑多杰猜測她大概是个安多姑娘。但格桑多杰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头上的头饰又分明是康区特有的风格。然而无论醒着的格桑多杰想得再多,在梦里与央金共度的那些时光当中,他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
央金唱过的那些山歌,格桑多杰在梦中只听一遍,就可以弹着扎念琴一点不落地唱出来。此后在流浪的路上,除了说唱格萨尔王的故事,格桑多杰唱得最多的,就是梦里央金唱给他的那些歌。终于有一天的梦中,格桑多杰问出了在他头脑中盘桓已久的问题:“央金,你的家在哪里?”
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格桑多杰和央金正手拉着手坐在草原上,央金靠着格桑多杰的肩头。这一次央金没有像她第一次出现时那样完全无视这个问题。她站起身对着格桑多杰一笑,笑容如同青藏高原正午的阳光一样明亮、热烈,她说:“来追我吧,追上了,我就告 诉你。”
姑娘的话音才落,格桑多杰就跳起来想要追央金,但却被央金阻止了。她伸手指了指格桑多杰的身后说:“骑着马。”格桑多杰顺着央金指的方向回头,发现两匹马在他身后踱步,就如同凭空出现在那里一样。
不等格桑多杰回答,央金已经笑着拉过两匹马的缰绳,随后在白色那匹的马鞍上一撑,敏捷地跳上了马背。她将另一根缰绳向格桑多杰一扔,格桑多杰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接住,随后也跳到马背上。
格桑多杰在马背上还没有来得及坐稳,央金便一甩不知何时出现在她手中的鞭子,双脚踩着马镫在马肚子上用力一夹,白马扬起前蹄一声嘶叫,便带着央金如离弦的箭般冲了出去,洒下一路银铃般的笑声。格桑多杰也不甘示弱,急忙催着栗色马向央金追去。
两匹骏马驮着两个年轻人,在广阔无际的草原上一前一后飞驰。牧区的人们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即使是如央金般的年轻姑娘,骑马的本领也绝不逊于 男子。
最终自己究竟有没有追上央金,格桑多杰醒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了。他只记得他们策马奔驰在草原上,央金姑娘的笑声清脆悦耳。回忆着梦中的场景,格桑多杰没有意识到,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起来。
格桑多杰决定走遍青藏高原上的广袤草原,只为找到梦中的央金姑娘。
野牦牛队
决定为寻找央金而走遍整个青藏高原之后,格桑多杰的旅途不再是一场只有起点却不知终点的、纯粹的流浪。他的终点就是有央金在的地方,哪怕是在最高的雪山之巅,哪怕是在最宽广的湖泊对岸。即使再遥远,格桑多杰依旧坚信自己总会离那个终点愈来愈近。
已经二十出头的格桑多杰完全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原本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也显出了高原汉子分明的棱角。格桑多杰依旧会在梦中见到朝思暮想的央金,他弹着扎念琴说唱着《格萨尔王》,几乎走遍了三江源,甚至去过甘南的玛曲和四川的若尔盖草原,但却始终没有找到央金的身影。
尽管如此,格桑多杰并不着急,毕竟央金依旧常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而且他有一辈子的时间用来寻找。
海拔近五千米的昆仑山口,就像是从青海到西藏的一道关卡。高原的阳光毫无遮挡地照着无边无际的戈壁滩,青藏公路从这里穿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边界也从这里开始。
格桑多杰来到可可西里,不仅仅因为他准备从这里去往圣地拉萨,更因为他隐约感觉到,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力量,召唤他走向那片神秘的土地。
这种预感很快得到了验证。格桑多杰唱了一段格萨尔王的故事,又弹着扎念琴唱央金曾经唱给他的山歌。他唱完,便盯着玉珠峰想着心事,手中无意识地拨动琴弦发出一些单音符。当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时,正出神的格桑多杰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一个大概和他阿妈年龄相仿的男子站在自己身后,那男人穿着藏袍,两只袖子都系在腰间,衬衣袖子挽起一半,露着肌肉结实的手臂。
男人留着长发,和一束红色的绳子一起编成的辫子缠在头顶,辫子里还系着一颗鸡蛋大小的蜜蜡,他的面部线条硬朗,专注而犀利的目光锁定在格桑多杰的扎念琴上。格桑多杰礼貌地开口:“阿库⑩,请问刚刚您是和我说话吗?”
“普11,你的琴还有你刚才唱的歌……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个朋友。”男子重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声音低沉浑厚。他将目光从格桑多杰的扎念琴上移开,上下打量了一下格桑多杰,问道:“普,扎巴伦珠……或者嘎玛卓玛,是你的什么人?”
格桑多杰从未听过扎巴伦珠这个名字,但是当他听到嘎玛卓玛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嘎玛卓玛……是我的阿妈。”他的声音有些滞涩,像是含在喉咙里的呢喃。
面前的男人听清了这句声音不大的回答,便皱起眉头又打量了一下格桑多杰。随后他叹了一口气,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坐在地上的格桑多杰平齐,追问道:“你的名字……叫格桑多杰,对吗?”
听了这话,格桑多杰不由得瞪大了眼睛。男人看出格桑多杰眼中的意外,没等他将心中的疑惑问出来,男人便解释说:“我叫达瓦次旦,扎巴伦珠是我的朋友。他曾经说过,他离开玛多跟着我们一起来可可西里的时候,他的女人嘎玛卓玛已经怀了孕。扎巴伦珠走的时候,就告诉嘎玛卓玛,无论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名字都要叫格桑 多杰。”
“我的名字叫格桑多杰。”格桑多杰低下头,低声告诉蹲在对面的达瓦次旦。他努力压抑住声音中的哽咽,“我的阿妈,几年前,就……”
格桑多杰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还是没能说完这一句话。达瓦次旦听懂了格桑多杰话中的意思,又叹了一口气,随后站起来,上前几步,在格桑多杰身边坐下,一只手用力地拍了拍格桑多杰的手臂。
达瓦次旦的手很粗糙,却带着令人安心的温度和令人信任的力量。格桑多杰从未见过自己的阿爸,但此刻他相信这大概就是父亲给人的感觉吧,尽管这种感觉对他而言十分陌生。
“阿库达瓦次旦啦,那个时候,我的阿爸为什么离开阿妈呢?”自从阿妈离开人世,格桑多杰就从未有意地去想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始终埋在他的心底,从来没有真正地忘记过。
达瓦次旦皱起眉沉默了一下,才加重了语气说:“格桑多杰,你的阿媽是天上的度母,你的阿爸是人间的 英雄。”
当年的嘎玛卓玛是玛多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她的眼睛就像夜空的星星一样明亮,脸庞犹如皎洁的满月一样光彩照人。不仅如此,嘎玛卓玛还十分勤劳能干,能够打出玛多草原上最香甜的酥油、织出最细致精美的黑牦牛毯。
嘎玛卓玛成年以后,就按照草原上的风俗,每天晚上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帐篷里。无数大胆的年轻人在月色与星光下,在她的帐篷前唱情歌或是情意绵绵地说一些赞美的话,渴望能够换来她的笑容,得到她的允许走进她的帐篷。
然而面对这些小伙子们的殷勤,嘎玛卓玛不为所动。只有当她心中牵挂的那个伴着扎念琴声的歌声出现的时候,嘎玛卓玛才会专注地听着帐篷外唱给她的山歌,同时又忍不住幻想着唱歌的人该是什么样子。
终于有一日当那歌声告一段落时,嘎玛卓玛也鼓起勇气,唱起情歌回应着帐篷外的那个人。
得到了回应的人儿似乎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再唱歌给嘎玛卓玛的时候,声音里便带了几分受宠若惊。而其他的追求者们明白他们已经输给了那个弹着扎念琴的青年,便渐渐地自动退出竞争,只留下嘎玛卓玛与帐篷外的年轻男子你来我往地相互唱和。
当这对青年男女的歌声愈发默契、唱的内容也愈发直白大胆后,嘎玛卓玛在一个月亮隐在云后的夜晚,将沐浴着漫天星光歌唱着的歌手迎进了自己的帐篷。然后她就知道了那个用琴声与山歌敲开了她心扉的英俊青年名叫扎巴伦珠,拥有他家乡草原上最悦耳的 歌喉。
扎巴伦珠的家乡离可可西里不远,他的家里不缺兄弟姐妹,于是他就留在了玛多草原嘎玛卓玛的帐篷里。而当他接到了达瓦次旦的消息,得知昔日生死之交的兄弟们大都加入了野牦牛队,守护着高原上的净土可可西里时,扎巴伦珠便决定暂时回到兄弟们的身边,加入到保护青藏高原生灵的队伍中。
离开玛多草原的时候,扎巴伦珠信誓旦旦地对嘎玛卓玛说:“嘎玛卓玛,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到你和我们的孩子身边,请你等我一段时间好吗?”嘎玛卓玛含着泪点点头,于是扎巴伦珠将从不离身的扎念琴郑重地交给嘎玛卓玛说:“曾经有位仁波切说这把琴是阿尼玛卿雪山神赐给我的礼物,我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日子,就让它陪着你吧。”
然而扎巴伦珠这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他已经长眠在了玉珠峰的脚下,达瓦次旦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的身后是几只鲜血已经开始凝固的藏羚羊尸体。而扎巴伦珠的身上,浸透了暗红色的血,随身的藏刀上同样满是凝固的血迹,刀鞘则扔在另一边。他的手中紧紧攥着一支猎枪的枪筒。至于枪的主人,无论是否还活着,大概都已经被他的同伴带走了。
达瓦次旦讲着讲着,便说不下去了。他紧紧抿着唇,双手握起拳头,手上的青筋因为用力而突起。格桑多杰反而显得平静许多,他用力地揉揉眼睛,随后抬起头迎着达瓦次旦的目光开口道:“是这样啊!……阿妈终于可以见到阿爸了。阿库达瓦次旦啦,请带我一起参加野牦牛队,好吗?”
可可西里
或许是被格桑多杰眼神中的坚定打动,达瓦次旦盯着年轻的格桑多杰看了一阵,终于点了点头,同时伸出手,再次用力地拍了拍格桑多杰的后背,表示鼓励:“你和你阿爸一样,是英雄!”
格桑多杰跟着达瓦次旦到了被民间称为“野牦牛队”的公路巡山队,成为了一名巡山队员。这里的人大多数都认识扎巴伦珠,对扎巴伦珠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儿子自然也会格外关照。而达瓦次旦更是宣布扎巴伦珠的儿子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说完还灌下了一大口青稞酒,像是在强调一般。
成为野牦牛队一员之后,格桑多杰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却有些琐碎。这一支没有编制的民间队伍的确缺乏人手,几乎每个方面都需要补充新的血液。因此,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像他的阿爸或者阿库达瓦次旦那样,做最危险的工作。
大多数时候,格桑多杰只是和同伴一起例行巡逻,定期向他们的队长——一个来自玉树的康巴汉子汇报情况,或者在可可西里腹地的帐篷里孤独地住上一段时间,唯有视线尽头长年头顶银盔的玉珠雪峰与他做伴。
平时只要有机会,格桑多杰依旧会弹着扎念琴,唱起格萨尔王的故事。玉珠雪峰顶的冰雪在高原的阳光下,融出许多条细细的银线闪烁。一股股雪水汇成细流,滋润了可可西里的大地。哪怕格桑多杰身边没有同伴作为听众,也有玉珠雪峰脚下的潺潺水声日复一日地为他伴奏。
除非是一个人面对雪山和戈壁,他很少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唱央金曾经唱给他的那些歌了,央金是他的秘密,而他不想要和任何人分享这个秘密。
野牦牛队的队员都是藏族,其中大都来自草原,因此,他们同样也热爱着格萨尔王的英雄传说。每当格桑多杰说唱起来的时候,手头没有事情的队员都会围在格桑多杰的身边,随着他的琴声和歌声,想象岭噶的草场和岭国的英雄,仿佛身临其境地看到了出征的格萨尔王检阅他雄壮浩大的军队。
再一次梦中见到央金的时候,格桑多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央金。他已经作为野牦牛队的一名队员在可可西里一段时间了,而这是他到了可可西里之后,央金第一次出现在他梦中。
事实上,格桑多杰并不确定他究竟是否应该告诉央金,免得她担心,就像当年阿爸对阿妈那样。然而在梦中,似乎并不是每件事他都能够完全掌握,而且有时格桑多杰也会怀疑,就算他什么都不说,央金也什么都知道。
当两个年轻人手拉手坐在草原上的时候,尽管央金什么都没有问,他还是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央金姑娘。草原上的微风拂过他们的耳畔,就像是远处的雪山在对着他们讲悄悄话。
对于格桑多杰加入野牦牛队这件事,央金并没有反对,然而也没有掩饰她眼中的担忧和不舍。她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着点点头,神情忧伤地用水汪汪的眼睛注视着格桑多杰。格桑多杰觉得央金的眼睛就像传说中的玛旁雍措湖水,而他自己,几乎就要溺死在湖水 之中。
格桑多杰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景,他只是突然产生了一种将央金姑娘拥在怀里的冲动,于是在头脑能够思考之前,他已经遵从了本能,猛地伸出手臂,紧紧地揽住了身边的姑娘。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拥抱,央金并没有挣扎,而是调整了一下坐姿,将自己的手臂环在了格桑多杰的腰上,头枕在格桑多杰的肩窝,温热的呼吸便若有若无地吹在了格桑多杰的颈间。
这种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令格桑多杰一时间有些恍惚。他抱着央金的手不知不觉收紧,仿佛要将央金融化在他火热的胸怀之中。央金的头埋在格桑多杰的怀里,格桑多杰看不清她的表情,却感觉到她的心跳和他一样加 快了。
湛蓝的天空,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澄澈剔透,纯粹的颜色如同羊卓雍措沉静的湖水,一望无际的草原如同延伸的绿毯,一直铺到大地的尽头,在远处与蓝天交融。而这散发着清香的柔软绿毯,就是一对年轻人的婚床;远处的雪山和头顶的白云,就是他们拥有了彼此后那些海誓山盟的见证。
草原上的微风如同耳语,拂过相拥躺在草原上的两人。格桑多杰的一只手抱着央金让她枕在自己肩上,另一只手则温柔地抚上了央金的后背,爱惜地摩挲他最重要的珍宝。突然间,格桑多杰的手顿住了,他在央金的背上摸到了一道伤疤,虽然很浅,却很长。格桑多杰有些心疼,抱着央金坐起来,这才看到央金的背后,有一道很深的伤痕。他确定自己是第一次看到央金的身体,却隐约感到那伤痕看起来有些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想不起来。
醒来的时候,年轻的草原歌手仍有几分恍惚。他用力揉揉眼睛,坐了几分钟,才意识到自己现在并不是在和央金缠绵的草原上,而是睡在巡山队员的帐篷里。清晨金色的阳光透过帐篷的缝隙洒在帐篷里,就像一条条金线。
带着几分回味和隐隐的失落,格桑多杰收拾了一下,烧水打酥油茶吃糌粑。随后,他就背起扎念琴,带上干粮和藏刀,离开帐篷开始巡山。
太阳升到穹顶的中央,又滑向西方的天际。夕阳从山峦的缝隙中流泻出来,头顶雪盔的玉珠雪峰则在渐浓的暮色中,如同披上了深藍色的轻纱。巡山路上的格桑多杰怀抱着扎念琴,对着夕阳的余晖再次弹唱起了格萨尔《赛马称王》的故事。寂静的雪山与草原在聆听艺人的说唱。
突然之间,一声响动打断了沉浸在岭国赛马大会中的格桑多杰。琴声戛然而止,格桑多杰疑惑地将怀里的扎念琴举到眼前查看,才发现六根琴弦中的一根琴弦莫名其妙地断开了。
看着断掉的琴弦,格桑多杰还没有反应过来,手中的琴却突然被不知什么东西击中,而他自己也因为冲击力倒退了几步。待格桑多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却发现扎念琴已经碎成了几块,一颗尚未冷却的子弹从扎念琴碎裂的地方掉出,滑落在草丛之间,明晃晃地反射着红色的夕阳。
一别永诀
当附近的其他巡山队员听到枪声赶来的时候,便看到呆呆跪在地上手中捏着子弹发愣的格桑多杰。年轻的草原歌手的身边,是已经碎裂的扎念琴。格桑多杰的眼中含着泪水,可是那泪水比扎念琴碎得更彻底,甚至已经无法变成完整的泪水流出来。
“我们遭遇了偷猎者。”领头的达瓦次旦皱起眉头,沉声开口,紧锁的眉头显出康巴汉子特有的深邃。几个队员抬起头看向他,唯有格桑多杰仿佛已经听不到世界上任何声音,依旧跪在地上,连姿势也没有变一下。
“这一带最近有藏羚羊出没,偷猎者一定是想要解决了巡山队员之后大规模围歼藏羚羊然后就地剥皮。但是他们没想到除了巡山的格桑多杰之外,我们也在附近。”达瓦次旦说着,露在藏袍袖子外的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握起拳头,因为用的力气太大,便有狰狞的青筋从他手背上浮起来。
一边说着话,达瓦次旦一边向前几步,在格桑多杰身边蹲下来,伸出手用力拍了拍格桑多杰的后背。见格桑多杰依旧茫然地呆愣着没有反应,达瓦次旦便抓着他的肩膀使劲晃了晃,又开口道:“格桑多杰,你的琴救了你一命,一定是格萨尔王在保佑你。”
听到格萨尔王的名字,他抬起头看了看达瓦次旦,目光里依然没有焦点。达瓦次旦试图拉他站起来,但格桑多杰却沉默着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开始捡地上扎念琴的碎块。
见格桑多杰这般样子,达瓦次旦也不再勉强,就放开了格桑多杰,后退一步,默默地看着年轻艺人徒劳地试图将碎块拼在一起。格桑多杰拼凑着扎念琴,他拾起琴的两块残骸,小心翼翼地将断茬对在一起看了又看,然后他的动作突然间便停住了。
格桑多杰看到,他的扎念琴背面有一道不知何时出现的划痕,他以前从没看到过。电光石火之间,格桑多杰突然想起,在那个旖旎的梦中,他摸到和看到的,央金光洁的背上那道伤疤。
如果不是因为弹唱的时候琴弦突然断开,格桑多杰就不会将琴举到眼前,那么,那颗被扎念琴挡住的子弹,或许就要夺走格桑多杰的生命了。想到这里,格桑多杰仿佛被抽空了全身的力量,泪水终于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达瓦次旦和其他的野牦牛队队员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的草原歌手跪在地上,流着泪将碎裂的扎念琴残骸抱在怀里。格桑多杰抱着琴,喃喃地重复着一个名字“央金”,泪水打湿了藏袍的衣襟,也打湿了破碎的扎念琴。
不知哭了多久,在众人关切的目光中,格桑多杰捡起地上所有的碎片,小心翼翼地展开哈达将碎片包了起来。随后,格桑多杰抱着哈达裹成的洁白的包裹站起身,竭力使声音显得平静:“偷猎者一定还会活动,我们……继续巡 山吧。”
随后的几天里,再也没有人听到过格桑多杰说唱《格萨尔王》史诗了,玉珠峰脚下的雪水依旧在流淌,雪山和戈壁却再也不知道水声究竟是在为什么伴奏。在一个休息日,格桑多杰抱着用哈达裹起来的扎念琴碎片,上了天 葬台。
天葬台上空无一人,偶尔有一只秃鹫在低空盘旋着掠过,随即又远去,像一个愈来愈小的黑点,最终消失在天的尽头。
格桑多杰慢慢地蹲下,小心翼翼地将裹在哈达中的扎念琴放在地上,又将哈达展开。阳光洒在琴的碎块上,如同为扎念琴镀了一层金。格桑多杰跪下来,双手在胸前合十,为央金念了一段经文,随后他向着玉珠雪峰的方向,认认真真地磕了三个长头。
做完这些之后,格桑多杰站起身,退后一步,抬起头对着太阳微微眯起眼,神情虔诚而专注,不知在想什么。没有被琴压住的洁白哈达一角,在高台的风中飘舞,如同岭国黑帐篷前升起的浓浓桑烟。
这样伫立了片刻,格桑多杰转过身,背对着扎念琴,向着阿尼玛卿雪山的方向喃喃地祷告了几句,随后便开始放声唱了起来。
格桑多杰已经不记得《格萨尔·地狱篇》当中的这段《地狱救妃》是什么时候从谁那里学会的。然而其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从来都没有成为神授艺人,然而这一次,格桑多杰却仿佛感觉到,他似乎就像神授艺人一样,在说唱的时候,看到了故事里的场景。
唱着唱着,两行泪水沿着脸颊滑落,泪珠坠在地上碎裂的瞬间,就如同水晶在一瞬间化为齑粉。
那是闻知艺人格桑多杰最后一次说唱《格萨尔王》,也是他唯一一次说唱的时候没有弹着他心爱的扎念琴。而这一次的听众,只有远处沉默的雪山、碎裂的扎念琴以及天空偶尔盘旋的 秃鹰。
虽然没有秃鹫带走央金的身体,格桑多杰依旧相信,他梦中的央金姑娘,已经回到了永久的乐土。
从天葬台回来,格桑多杰再没有向任何人提他的扎年琴,他也将悲伤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再没有向别人说过。格桑多杰像从前一样巡山,有时还会和队友说笑,甚至就连达瓦次旦,也没有看出格桑多杰有任何的变化。
是日,野牦牛队得到情报,几个偷猎者准备趁着藏羚羊繁殖的时期,围歼一群几乎没有抵抗能力的母羚羊。野牦牛队准备伏击偷猎者,格桑多杰主动请求参加。
如此危险的任务,年轻的格桑多杰以前从未参与过。达瓦次旦沉吟了一下,还是同意了格桑多杰的请求。毕竟,雏鹰总要飞出巢,才会在风雨中历练成为傲视苍穹的雄鹰;生在草原的年轻人总要经历考验,才会在荆棘中砥砺成为坚韧挺拔的康巴汉子。
偷猎者开着进口的越野车,装备着精良的武器。论硬件,他们比装备简陋的野牦牛队高过不知多少个等级,然而这些守护着可可西里的格萨尔王的后裔,从不会畏惧或退缩。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可可西里,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加忠诚地护卫着青藏高原上的這一片 净土。
没有人知道格桑多杰是如何比其他人更早地得知了偷猎者的准确位置。他和另一个康巴小伙子一起,与偷猎者“狭路相逢”。格桑多杰让同伴赶快去通知达瓦次旦,自己则留下来与偷猎者周旋。
达瓦次旦得到消息带人匆匆赶来的路上,远远看到他们目标的那个方向突然腾起一团火光,如同一飞冲天的金翅大鹏鸟。与此同时,一声爆炸的巨响,整个可可西里的大地都在颤抖。
当野牦牛队的队员们赶到爆炸现场的时候,便发现偷猎者的进口越野车已经炸得只剩下零碎的残骸,汽油燃烧的味道弥漫在空气当中。
突然之间,达瓦次旦注意到,脚下的泥土中,嵌着一半被炸断的藏银手镯,尽管沾满了泥土和暗红的血,达瓦次旦还是一眼就认出,那镯子就是扎巴伦珠曾经送给嘎玛卓玛的那只。
达瓦次旦抬起头,听到声声鹰啸从天边传来,和着可可西里的风声,如同《格萨尔王》史诗的歌咏,又像出征的鹰笛号角。
注释:
①扎念琴:藏民族的一种弹拨乐器,有六根琴弦,也叫六弦琴;
②神授艺人:是指通过梦授神传而得说唱史诗格萨尔技艺的艺人;
③《赛马称王》:是《格萨尔王传》中非常经典一部;
④觉如:是《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称王之前的小名;
⑤楚通:是《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的叔父,是作品中的一个反面人物;
⑥仲堪:藏语,说书艺人;
⑦推:藏族的一种用奶渣、酥油、红糖所做的一种食品;
⑧江噶佩布:是《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的坐骑,著名宝马的名字;
⑨闻知艺人:是指通过听闻记忆,说唱史诗格萨尔技艺的艺人;
⑩阿库:藏语,指叔叔;
{11}普:藏语,指小子。
编辑导语:一把扎念琴,不仅见证了阿爸阿妈的爱情,也成为了主人公最大的精神寄托。万物有灵,与扎念琴相伴的岁月里,哪怕以天为庐地为席,也可泰然处之,年深日久,扎念琴也成为了保护自己的灵魂伴侣,唯美动人。
责任编辑:索朗卓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