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的栖居姿态——论朱朱诗歌中的空间诗学
程倚飞
自出版第一本诗集《枯草上的盐》以来,诗人朱朱一直保持着缓慢而坚定的写作节奏,并不断扩大诗歌中的视野,从江南小镇延伸至异国文化。作为观察者的书写,朱朱的诗歌通过抽象的“词物”逻辑对客观物体进行再现。光线作为朱朱诗歌中的一个特定意象,代表了诗人作为观察者对被观察物体的再现,是其观察特性的具体体现。此外,朱朱在诗歌中营造的空间场景,无论是江南小镇还是异国他乡,都呈现出不同的空间诗学表达。这体现了“流动”的姿态,与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不谋而合。本文运用了空间理论等分析朱朱诗歌中存在的空间。无论是光线的空间还是生存的空间,体现了诗人在表达过程中对空间的重新组合,最终目的是让主体找到诗意的栖居空间。
一、“光线”意象在诗歌中的表达
在诗歌中,诗人通过创造“内部光线”的手法来塑造作品的视觉效果。这种光线并非外部世界的光线反射而来,而是由诗人自身发出。“鲁奥的画证明,灵魂具有一种内部光线,‘内部视觉认识这种光线,并在色彩绚丽的、阳光照耀的世界中转化出来。”([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巴什拉也曾探讨过内部“光线”的概念,他认为诗歌的内部光线与观察者的视线产生共鸣,这是诗歌能够产生丰富深度的原因之一。在朱朱的诗歌中,对“光线”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诗人通过对内心光线的呈现,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一)光线与视线
在創作诗歌时,诗人的视觉观察早于语言的形成。在诗歌语言形成之前,诗人通过视觉观察来确定客体在诗歌中的地位,同时也通过视线的观察来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诗人的目光和想象为中心,近似于透视法对光线的使用,朱朱的诗歌将光线的内在化,正是诗人在诗歌中的刻意安排。正如“它是以观看者的目光为中心,统摄万物,就像灯塔中射出的光——只是并无光线向外射出,而是形象向内摄入。那些表象俗称为现实。透视法使那独一无二的眼睛成为世界万象的中心。一切都向眼睛聚拢,直至视点在远处消失”([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所说,通过理解经典的透视法,诗歌中的光线与透视法的光线相似,朱朱的诗歌中的光线由诗人所接收,形成内在的视线,用以把握物体的特征。在朱朱的诗歌中,光线和热火紧密相关。诗人是光线的接收者和发出者,“光线”代表了诗人目光的指向,如在诗歌《路过中》所写:“我脆弱如树影,在路过的水洼里,感受着被车轮碾过的疼痛;我冷是因为对面没有光,/人们相见时,都是捻暗的灯笼。”诗人通过观察路过的水洼和捻暗的灯笼,隐含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表达了对光和热的向往以及对现代繁忙的人们内心深处的失落。因此,诗歌中的光线不仅是一种物理现象,更是一种文学意象,用以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丰富了诗歌的内涵。
光与暗的相互依存与共生,体现了文明本身内在的特征,即“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最早谈论了“阴影”,烛光所带来的影子展示了光与暗的互动。朱朱的诗《车灯》进一步探讨了人造光的象征意义:“另一次晚归时/我看见车灯直如一把尺子,/丈量着这片土地。汽车的轮胎在滚动中/面对一块黑布的巨大尺幅,尺子太短了,只有分段地进行。”随着技术的发展,电灯逐渐成为文明和现代的符号,而黑暗则是前现代的代表和象征。在这首诗中,现代文明的“车灯”象征标准化的生产途径生产完美、合格的产品,而“土地”和“黑布”则代表着有情感连接的大地,是原始文明的象征。通过“车灯”和“土地”之间的对比,朱朱重新思考人造的光线所蕴含的例外状况,并表现了诗人对现代标准的人造性光源的思考。朱朱在诗歌结尾写“而我就是那不完美者……最起码我以笨拙面对真实”,表达了诗人对人造光线的反思。
(二)光线与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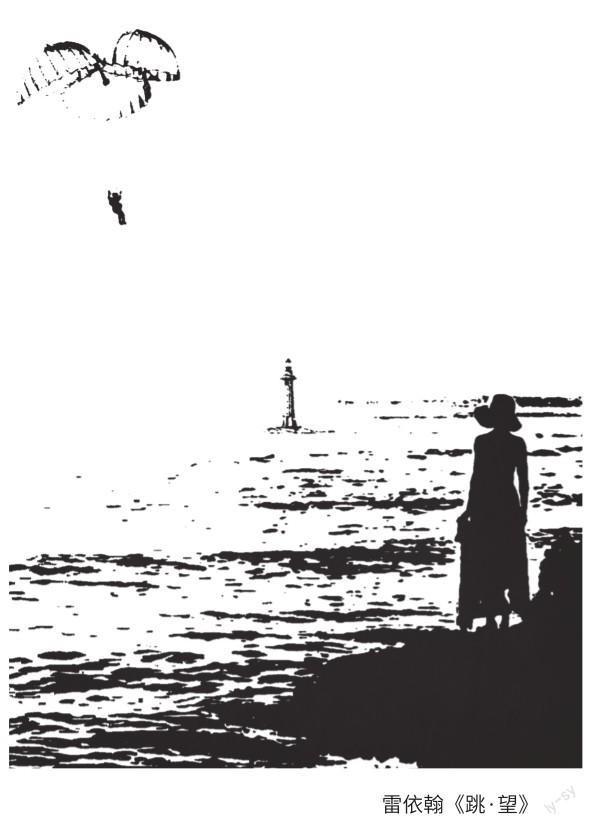
就像莱辛在《拉奥孔》中对诗画模仿符号的差异所说的“绘画里一切都是可以眼见的,而且都是以同一方式成为可以眼见的……诗人在把他的对象生动地呈现在眼前,使得我们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它的语言文字更清楚时,他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朱朱的诗歌以光线的描写为特色,使其具有绘画的特点。然而,这种特点并不等同于现实主义将诗歌视为生活的镜像,而是通过光线和场景的选择来达成美感和抒情性。从《蒙德里安的海》到与画家相关的两首诗《当光从维米尔的画中被提取走》《霍珀》,朱朱对绘画中的静物进行了诗歌的描写,将绘画中的静态光线转化为诗歌中的动态光线。在《蒙德里安的海》中,“海是一座没有顶的小教堂,/挤满了十字架和烛光——他们爬上墙又跌落”。这三首诗歌中表现了画与诗歌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画的表达是对物体的直接摹仿,朱朱的这三首诗歌则是对画家绘画的摹仿,即对物体摹仿的摹仿。绘画作为朱朱诗歌的题材,两者对同一物体的不同表现和再现,体现了作为语言媒介和视觉媒介的不同,前者通过语言的想象抵达读者的共鸣,后者通过视觉的想象抵达观者的共鸣。朱朱的再摹仿并非是简单地运用诗歌来摹仿绘画,而是结合了绘画体验和诗人当下生活经验的再次结合,表现诗人在欣赏绘画艺术的过程中对诗歌艺术表现的再思考。
作为绘画的重要元素,色彩是眼、脑和生活经验共同产生的对光的视觉效果。闻一多提出的现代诗“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主张现代诗中表现美的意境。由色彩构成的光的节制,在朱朱的诗歌中得到体现。《霍珀》中,诗人使用“黄蜂”“七彩的纹饰”“黑色的残渣”等意象来描绘色彩,运用生物、物品来表现色彩,不同的色彩表现诗歌中物体的不同属性,服务于诗人节制的抒情。
二、“空间”意象在诗歌中的表达
朱朱的诗歌体现了“江南”“异国”和“住宅”等空间元素,正如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述,“诗人和画家是天生的现象学家。当我们注意到事物在对我们‘说话,并且如果我们赋予这一语言充分的价值,我们就和事物有了某种联系”(《空间的诗学》)。巴什拉通过对家庭住宅、抽屉、柜子等形象的分析,指出了诗歌想象力的重要性。他着重分析了诗歌中的内心空间形象。文学空间的诗学建立在场所分析的基础上。如果福柯的空间研究描绘了权力模型,那么巴什拉并不把文学空间看作一个充满恶意和斗争的空间,而是将空间视为诗歌本身的形象。正如巴什拉所言“去探索幸福空间的形象”,朱朱诗歌中“住宅”与“故乡”的相关意象代表了这样的幸福空间,“异乡”“异国”相关的意象则站在了对立面成为充满争斗的空间。
(一)“童年”与“家乡”意象
朱朱诗歌中的地域性存在和描绘,既是经验性也是非经验性的。朱朱在访谈中表示:“童年记忆或者地域经验作为一笔财富将伴随终生,但在你还无法有效转化的阶段,它们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释放出来,就让你心烦意乱,因为太切身了。”(朱朱,胡桑:《我生來从未见过静物——朱朱访谈录》,《诗探索》2020年第1期)在他的诗歌中,“家宅”的空间和“江南”的空间正是童年和家乡经验在诗歌空间中可感知的表现。诗歌文本将“家乡”重新安置在空间中,通过复杂的语言变形和交叉实现。童年相关的意象是个体倾向的无意识表达,而“故乡”相关的意象则是个体与集体经验无意识结合的产物。
朱朱的诗歌中涵盖了许多与“家宅”有关的意象。在巴什拉看来,“家宅更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即使它的外表被改造,它仍表达着内心的空间”(《空间的诗学》)。家宅由楼梯、屋顶等部分组成,是具有丰富原初性的概念,是诗人内心空间的外化。朱朱的诗歌中有一系列标题涉及“家宅”这一意象,如《楼梯上》《厨房之歌》《后院》和《皮箱》等。在《楼梯上》中:“男人在楼梯上来来回回/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下楼,在人群中孤独地死亡。”“楼梯”是房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频繁出现且在这首诗歌中作为人物切换的场景。“楼梯”是垂直交通工具,上下的动作既构成了相对的空间对立,也构成了垂直空间的交汇,“男人”的身影在楼梯的空间中不断徘徊,表现出诗人对知音的寻觅。
在《厨房之歌》中,“强大的风,/从对面的群山/吹拂到厨房里悬挂的围裙上,屋脊像一块锈蚀的钟摆跟着晃动”;在《小镇,1984》中,“那些日子里微风掀动旧屋顶/就像要吹掉退伍老兵的黄军帽”。“屋脊”和“屋顶”正是家宅的象征,作为家宅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屋顶作为家的象征及其背后的含义是重要的。“‘理解屋顶的倾斜。梦想者自己以理性的方式做梦;对他而言,尖尖的屋顶劈开团团的乌云。所有思想在接近屋顶时都变得清晰。”(《空间的诗学》)风能够将屋脊和屋顶晃动,在朱朱的笔下,“屋脊”的摇晃代表老化的住所中不稳定的因素。在巴什拉所认为的“幸福的居所”的基础上,“晃动”正是对童年回忆进行的安居但最终无法抵达的遗憾。
此外,“箱子”在巴什拉看来是重要的空间符号,“箱子——特别是小箱子——是我们最彻底掌握的东西,是自行开启的对象。当小箱子关闭的时候,它回到对象的共同体中;它在外部空间中找到自己位置。但它会自行开启”(《空间的诗学》)。箱子作为一个复杂家具,有着对隐私的需求和藏匿物体的需求。在巴什拉看来阅读“箱子”,能看到诗人隐秘的思想。在朱朱的诗歌《皮箱——献给我的父亲》中,诗人描绘皮箱的开合是诗人对“童年”经验的诗化书。“皮箱”内部的隐含空间代表了父亲的爱,“我触碰这簧片,打开箱子就像打开一个真空”。毫无疑问,由于有了一系列与家宅有关的意象,诗人的回忆逐渐在其中安顿下来,屋架、阁楼、皮箱意象的刻画,体现了诗人对于童年的回忆。
诗歌中所描绘的空间,既是诗人对现实世界中空间在诗歌空间的投影,也是诗人通过意象的堆叠与变形形成的虚构空间。在朱朱的诗歌中,涉及了“家乡”这一江南意象,诗人通过文学想象的空间与文化底蕴,对“江南”这一空间进行了无意识的书写。在朱朱的《丝缕——致扬州》《扬州郊外的黄昏》等诗歌作品中,“江南”空间被具体化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其中包括扬州的运河、湖泊和气候等特征。这些地理特征不仅仅是诗歌描写的背景,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例如,诗歌中描绘的运河、湖泊等自然元素,代表了扬州的水文化,而唐朝的月光则代表了扬州的文化遗产。朱朱通过借助城市盆景、博物馆中保存的冷僻知识、桥孔中的倒影等细节,勾勒出一个充满感官经验的江南空间。“江南”的空间建构是由个体和社会共同创造的,是由多种元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其中包括身体、感官、文化符号等。朱朱的个体无意识与社会的无意识重合,形成了对江南空间的独特书写,使“江南”成为他观看这个世界的窗口。
(二)“异乡”与“异国”意象
诗人朱朱对地域特征的情感把握不仅体现在与“家乡”相关的意象上,也体现在与“他乡”相关的意象上。在《旧上海》一诗中,诗人通过对“上海”这一特定城市的描写,展现了现代化和多元性的符号意义。诗中提到“全城的精英们能够孵化有血有肉的蛋,补丁和假领映衬着灵魂”,暗示着这座城市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通过描述狂欢节、海关大楼、外滩等场景,诗人表达了这座城市的国际化和多元性。同时,诗中也使用了“爱奥尼亚柱”“殖民时代”等词语,暗示了这座城市的殖民历史和现代性。然而,这个城市也存在着许多隐秘的角落和“盲点”,例如老石库门里的暗湿窗户,揭示了城市中的贫困和不公平现象。朱朱认为,“家乡”之外的异乡、异国都不是他的诗意安放之处。
朱朱的诗歌经常探讨异国的意象,其中包括了对异国文化、历史、地理和人文的思考与感悟。他的诗歌不仅仅是对异国的表面景象的描述,更多的是对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背后的深层意义和价值的探索。例如,在《佛罗伦萨》这首诗中,他对佛罗伦萨这座意大利城市的描写不是停留在表面。朱朱的诗歌还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例如“每当外族人/赞美我们古代的艺术却不忘监督/今天的中国人只应写政治的诗——/在他们的想象中,除了流血/我们不配像从前的艺术家追随美”。他通过对异国文化的思考和感悟批判中国现代诗歌在西方文化中的认知不足和误解。在《月亮上的新泽西——致L.Z.》中“你”和“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空间,前者所在的空间“新泽西”作为一个异国,被描绘成冷漠、舞曲、乏味,“是舒适的牢笼”,充满机械化和消费主义的气息,相比之下后者“我”的内心空间则是充满了想象、诗意和浪漫的,成为“浪漫的乐土”。作为更加现代化的国家——新西兰所代表的文化是诗人所批判的,诗人赞许自己的祖国的史诗。在“异国”与“祖国”的对比中,朱朱的诗歌表述体现了两种文化不同的交往,表现诗人对自我身份的强大认同,在此背后呼吁当代人对异国文化的探索时,既要有交流,也需要批判。
三、“流动”的意象与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空间的迁移是流动的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现代的城市街景,在马歇尔 · 伯曼看来,“车流”“人流”意象是具有现代性象征性的形式,象征现代城市的躁动、快节奏和无序性,展现现代性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控。诗人应对的重要策略之一是“流浪”。依据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中流浪的理解,这是诗人突破现代性的束缚以及对个体自由的追求的体现。
(一)“城市空间”意象与现代性
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促进了人在城市空间的流动,城市街景的空间意义和价值不断在重构。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马歇尔·伯曼指出:“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些尝试。现代性作为一个巨变,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马歇尔·伯曼对现代性的巧妙比喻与朱朱诗歌中对于“故乡”“他乡”“异国”空间的叙述,揭开的正是现代创伤,展现的是生活中因为现代性所产生的分裂与无法调和。朱朱的诗歌也表现出了这一点,它通过对故乡、他乡、异国城市的描绘,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和对空间的感知与认知的变化。从对童年故乡的叙述到异乡的叙述,诗歌内在的地理变迁追随的正是诗人现实中不断成长的步伐。从《喇叭》《故事——先给我的祖父》描绘了童年时期故乡的生活场景,再到《旧上海》中关于上海街景的叙述,《喇叭》中描绘的成年的“流浪”与“自我放逐”,正是这样的地理变迁的概述:“我并不知道从那时候开始,自己的脚步/已经悄悄迈向了成年之后的自我放逐,/迈向那注定要一生持续的流亡——为了/避免像人质,像幽灵,被重新召唤回喇叭下。”这与现代人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动不谋而合。
街道作为城区内通行和贯穿的重要通道,是一个急速流动的物理空间,也是现代性特征在诗歌中的重要意象。朱朱的诗歌《路过》正是對现代性街景的描绘,诗人投身于现代世界日常生活中运动的日常,“罩上蒸汽的镜子前,我怔忡地/倾听城区的车流。这里”。就像马歇尔·伯曼在分析波德莱尔大街上的现代主义时说:“我们在这儿看到的现代人原型,是一个被抛入了现代城市车流中的行人,一个与一大团厚重的、快速的和致命的物质与能量抗争的孤独的人。……整个现代环境转变成了一团‘运动的混乱。……这使得林荫大道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个完美的象征:每个资本主义单位的合理性,导致了将所有这些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社会系统中的无政府主义非合理性。”([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现代的车流取代了原始的田园诗带来的光环。此外,人行道呈现各种各样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人们被迫忘记自己的身份通过比较从而认识自己。在《路过》中呈现了古典文学教授、音乐学院毕业的女孩,“几代人的激情转眼已耗尽,每个人/匆匆地走着,诅咒着,抱怨着”,不同背景、阶级的人们在城市的物理空间内交会、分离,人群的流动也正是现代性街景的重要表征,表现现代人的匆忙无力。
(二)“流浪”的意象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多次提到“流浪”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流浪是一种与固定空间脱钩的流动,是流动的极端状态。”“流浪使人们变得无根无据,但也可以通过流浪来获得自由和身份的重新塑造。”“流浪者的身份和位置是不稳定的,他们的流动可能会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也具有创造和创新的潜力。”([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流浪”作为一种行动,与现代人规律的工作生活不同,前者是不确定的自由漫游状态,后者是单调机械化的状态。“流浪”与固定的空间脱节,能够让诗人观察到固定的机械生活所不存在的诗意。朱朱诗歌中的流动性,正是他以流浪者自居,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流浪诗学应对策略。
在《月亮上的新泽西》中,“惊讶于你的流浪这么快就到达了终点——/我们年轻时梦想的乐土/已经被简化成一座舒适的囚笼”,朱朱对比了现代化后新泽西的温柔的“牢笼”,将“流浪”称为年轻时候的乐土,暗示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对个体的现实和舒服,表现了对个体自由的渴望。在《小镇,1984》中运用“溜冰,看电影,游荡在老街上,/用口哨吹奏着一支《流浪者之歌》”表现了在小镇中漫游的特征,朱朱将流浪的追求作为一种对现代性不断流动的特点的回应,将流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于朱朱来说,将游荡在老街上视为一种乐土上的自由活动,暗示朱朱通过回到小镇记忆来冲破固定的、机械化的生活所带来的对个体的限制和束缚。总的来说,朱朱诗歌中体现的光线的变化与空间的变迁,体现了他对现代人生活的反思,对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思考。通过“流浪”和回忆童年的姿态来表现诗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自我选择,回归到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之中。
责任编辑 张范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