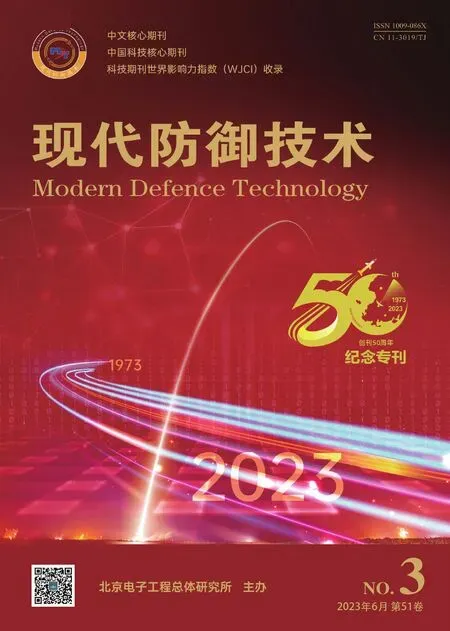面向联合作战的美国空军任务式指挥模式探析*
宗凯彬,安飞,赵文婷,颜留单,刘海军
☞指挥控制与通信☜
面向联合作战的美国空军任务式指挥模式探析*
宗凯彬,安飞,赵文婷,颜留单,刘海军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北京 100854)
2021年4月,美国空军柯蒂斯·李梅条令制定和教育中心正式发布《空军条令出版物1:空军》(AFDP-1)(2021年3月10日版),完成对空军基本条令卷1和卷2的重大更新,该条令作为美国空军的最基本条令,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导美国空军的作战行动。在此次更新的AFDP-1条令中明确提出,要将任务式指挥作为空中力量指挥控制的基本理念,通过“集中指挥、分布式控制和分散执行”的作战控制方式,取代传统上以“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为核心的空中力量运用原则,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支撑未来美军作战概念、体系架构和装备形态的持续演进,为在大国竞争和强敌对抗背景下获取优势奠定基础。针对此次美国空军基础作战条令的显著变革,将从改革背景与改革动因、任务式指挥基本原则、任务式指挥实现方式,以及任务式指挥与集中式指挥间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剖析,深入洞察美军此次变革背后的深层次内涵,并总结此次变革带来的启示和意义,为后续制定应对措施和规划发展路线提供参考借鉴。
任务式指挥;联合作战;作战条令;美国空军;作战概念
0 引言
2021年4月,美国空军柯蒂斯·李梅条令制定和教育中心发布《空军条令出版物1:空军》(AFDP-1)(2021年3月10日版)[1],以取代空军基本条令卷1和卷2(basic doctrine volume I,Volume II),其中明确将任务式指挥作为空中力量指挥控制理念,指出将通过集中指挥、分布式控制和分散执行(centralized command, distributed control,and decentralized execution)来实施任务式指挥。这是美国空军对一直以来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centralized control and decentralized execution)的空中力量运用原则的重要演进,旨在为发展新的作战概念、组织方法和装备解决方案提供统一框架,以应对未来作战环境带来的挑战,同时也体现出美国空军在聚焦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 JADC2)[2]赋能后,在联合作战概念方面的重大转变。美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称,AFDP-1可能是史上最具变革性的空军基本条令,标志着美国空军在“加速变革,否则失败”战略[3]路径上通过重要里程碑。2021年4月21日,美军刊物发表《空中力量指挥控制的演进》(evolving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airpower)一文[4],介绍了此次转变的动机,从空军士兵的角度设计任务式指挥,并阐明了在实施集中指挥、分布式控制和分散执行时的实际问题。
1 改革背景及原因
美国空军基本条令的此次变革是在大国竞争和体系化作战能力建设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在体系化作战条件下,联合部队行动的相互关联性、依赖性和挑战均日益增强,而在技术飞速进步和扩散时期,大国竞争的再度出现又削弱了美国的相对军事优势,对手已开发其自身能力和作战方式以避开并反制美军优势。对美国空军而言,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A2/AD)[5]能力导致的竞争环境削弱了在整个作战空间内的自由机动和作战能力。为确保在未来作战环境下取得胜利,必须研究部队如何通过感知、计划、决策和协调来成功完成以下任务,并对现有系统进行必要改革:
(1) 有效整合并使全球部队以及各战区部队的全域行动保持同步,以达到期望的作战效果;
(2) 确保指挥控制设施、系统和流程在遭受攻击后能迅速恢复,以保证在竞争环境中的持续战斗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军正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改进工作:
(1) 采用联合全域作战(joint all-domain operation,JADO)的新兴概念和基本作战原则,并逐步发展军种联合作战与联合兵种,整合全域部队和能力,并使其行动保持同步,从而按照指挥官选择的时间、地点和节奏达到理想的效果;
(2) 开发先进作战管理系统(advanced battle management system,ABMS)[6]并开展相关试验,以连接“传感器”与“射手”[7],从而支持联合全域作战;
(3) 采用适合竞争环境下分散作战的敏捷作战应用(agile combat employment,ACE)概念与方法[8],利用各个分散的前方作战位置(forward operating location,FOL)而非传统的主要作战基地(main operating base,MOB)实现飞机起飞、撤回及维修保养目的。
敏捷作战应用不仅使部队获得了战斗力,而且提高了部队的生存能力,更加侧重在严峻环境中进行作战。
(4) 发展“先遣联队”(lead wing)主要分队,以及针对远征、可持续的“敏捷作战应用”式作战的基地活动支援(base operations support,BOS)能力。
按照上述发展规划,美军对未来作战环境下的指挥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代指控系统需面向竞争环境下的全球一体化联合全域作战需求,同步组织开展多项任务,并确保各项任务之间相互协调。例如,在未来作战中可能需要同时完成以下几项任务:
(1) 集中制定总体作战方法,以整合全球及各战区的空中力量以及空军部队指挥官(air combat command,ACC)级别的联合资产;
(2) 为执行敏捷作战应用(agile combat employment,ACE)概念的各个分散的先遣联队分配控制活动,从而在敌人对联合部队指挥控制节点和系统发起持续的动能和非动能攻击时保持自身战斗力;
(3) 集中运用作战司令部级别的太空或赛博空间能力,以产生精准的战略效应。
然而,在美国空军当前基于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centralized control and decentralized execution)的空中力量运用原则下,其作战范式是以空战中心(air operations center,AOC)为核心,由AOC通过空中任务指令指挥空中远征联队(air expeditionary wing,AEW),而AOC几乎不向联队授予任何作战和指挥自主权,使得这种结构在与大国对手的远征作战中几乎不可行。在与近似匹敌对手交战时,敌方可以拒止美军的后勤补给,甚至可以隔绝美作战部队、切断作战部队与指挥中心间的通信联系,在得不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空中远征联队的作战行动将难以为继,使其无法有效支撑穿透式打击等作战概念落地实施[9]。此外,现有的“集中控制与分散执行”原则也无法充分解释日后作战过程中可能需要的不同空中力量的编组结构[10],亦无法辨别这些结构内部的细微差别,从而在实现“在遭受攻击后能迅速恢复,以保证在竞争环境中的持续战斗力”这一目标时面临挑战,难以支撑体系结构动态调整。
为满足未来战场环境下的联合作战需求,就需要变革现有指控系统及其组织模式(架构)。美军在《联合全域作战中的空中混合运用联队》中提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蕴藏在改革联队组织中:不再按任务类型或单一平台(战斗机、轰炸机、赛博、空运等)来划分联队,而是由具备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电子战、赛博作战等作战能力的多个中队组成混合联队,践行敏捷作战运用(agile combat employment,ACE)理念,在外部后勤和通信线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基于最后已知指令和联合部队指挥官对某个地理区域的意图,自行开发、规划和执行目标,独立完成全部任务,在被隔离或孤立情况下做出自主决策,而“空中混合运用联队”解决方案的设计思路刚好与美国空军AFDP-1文件的思路相吻合。此前,美军在《在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环境中取胜:优化印太地区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文中指出分布式指挥控制能够降低作战系统对通信架构的依赖,帮助隐身打击资产联合攻击集群渗入对手强大的综合防空系统,并成功完成作战任务,进而在大国竞争中取胜。
按照李梅条令制定和教育中心发布的最新版作战条令,美国空军现有条令体系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空军现有条令体系内容汇总
2 任务式指挥基本原则
在《AFDP-1》条令第四章“我们如何做”中,对任务式指挥内容进行了具体描述,并阐述了任务式指挥的核心原则,其主要内容如下:
空军力量指挥控制的理念是任务式指挥。任务式指挥是指挥控制的一种方法,它使下级决策具备灵活性、主动性和响应性,以实现指挥官的意图。任务式指挥为空军提供了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快速变化环境中的行动自由,以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并取得成功。考虑到空中力量的全球到达能力和战略影响,空军的任务式指挥方法能够在战术灵活性和全球风险管理之间达成平衡。
任务式指挥的核心原则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通过相互信任建立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分享经验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是可以依靠并有能力执行任务的指挥官、下属和伙伴之间形成的共同信心。
形成共同的理解。对环境(包括行动的目的、挑战和解决它们的方法)的共同理解使各级决策者能够具备做出有效决策和管理相关风险所需的洞察力和远见。
提供清晰的指挥官意图。清晰而简明地表达行动的目的、期望的结果和可接受的风险能够明确重点并帮助下属和辅助指挥官成功,即使是在事件没有按照计划发展的情况下。指挥官的意图简明地描述了成功的要素。
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任务型指令(mission-type orders,MTO)。MTO有助于完成分配给上级司令部的全部任务。MTO聚焦一次行动的目的,而不是如何完成行动的细节。MTO赋予下属在指挥官意图的指导方针范围内最大可能的行动自由。当指挥官的意图中所包含的假设在执行过程中仍然有效时,MTO是最适用和有效的。如图2所示,MTO应该基于更高级别司令部的优先事项和意图。MTO的格式分为五段,可在进行适应性修改后应用于同级或低级别梯队。计划指令(planning order,PLANORD)、作战指令(operation order,OPORD)、联合空中作战计划(joint air operations planning,JAOP)和空中作战指令(air operations directive,AOD)应作为发布MTO的基础文件。
训练纪律约束下的主动性。纪律约束下的主动性是指当现有的指令不再适用,或当不可预见的威胁或机会出现时,主动地运用创新和创造力。它建立在对任务目标、预期效果、总指挥官的意图和更宽广的战略背景的明确理解之上。
接受适当的风险。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包含不确定、复杂和模棱两可的因素。指挥官必须与下属合作分析风险,以便在保护部队和接受、管理为完成任务必须承担的风险之间达成平衡。

图2 MTO采用的五段式格式
3 任务式指挥的实现方式
无论是当前的空中力量使用原则,还是未来针对不同空军任务集的联合全域作战架构,都必须考虑集中化需求和分散需求的灵活性与多目标性。按照美军最新开发的“集中指挥、分布式控制和分散执行”的任务式指挥方式,其各环节实现的主要目标如下:
(1) 集中指挥为发展全域、全球一体化机动作战计划提供了框架。通过集中指挥,集中确定军事行动的目标、计划、任务优先级、指挥和批准的职责与权限,并为下级部队在竞争环境中作战提供规范和有条件的权限。
集中指挥是有效且高效运用空中力量的编组标准,既可实行大规模原则,又可维持兵力节约原则,可有效整合联合全域作战所需的部队和能力。由于空中力量可能产生战略级和战役级作战效应,因此应由一名空军士兵(即空军部队指挥官(air combat command,ACC))负责指挥。
(2) 分布式控制描述了各分散部署的下级部队如何利用授权协调火力、情报、信息、运动与机动(motion and maneuver,M2)、防护及后勤保障功能,并对作战效果进行评估,从而根据指挥官作战意图投送作战力量并确保战场主动。
分布式控制利用空中力量的灵活性与多目标性,确保其始终保持迅速积极的反应能力、生存能力与持续的战斗力,特别是在执行部队可能会与AOC通信中断的竞争环境或有利条件减少的作战环境中,此模式使作战部队指挥官能够基于当前态势,灵活采取不同应对策略,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最大化达成作战目标。
(3) 分散执行体现了部队如何运用战术灵活性以及在约束条件下的主动性完成作战任务。上级指挥官通过授权完成作战控制,确保作战结果能够支撑任务目标,同时给予下级部队一定的自主空间,使其能够依据实时态势制定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并能够利用转瞬即逝的机会构建相对优势,进而完成特定任务。
以下将对“集中指挥、分布式控制和分散执行”任务式指挥方式中各环节进行详细说明。
3.1 集中指挥
集中指挥应由一名指挥官级别的空军人员负责,他应广泛关注且非常了解联合部队司令(joint forces commander,JFC)的目标,从而利用全球部队以及各战区部队的资产确定空中力量的优先使用顺序,并指挥、整合、计划、协调和评估空中力量的使用。集中指挥不仅使空军部队指挥官能够应对环境变化、实现优先级排序与平衡,还允许下级部队行使主动权。集中指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保持了作战层面上的灵活性与多目标性,并且支持联合统一指挥原则。然而,在指挥关系复杂的联盟作战或者需要机构间广泛协调的稳定局势战中,统一指挥可能会被统一行动所取代。
集中指挥聚焦于以下内容:
(1) 形成并传达指挥官的明确、决定性的意图和愿景;
(2) 整合联合全域作战所需的全球部队/战区部队的动能与非动能行动及能力,从而按照规定的时间、节奏和重点实现精确的效果同步;
(3) 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各战区与指挥部的空中力量;
(4) 战略与作战计划和兵力分配;
(5) 支持分布式控制的能力和资产分配;
(6) 规定权限并进行(有条件的)授权;
(7) 向下级指挥官授权。
3.2 分布式控制
指挥官通过分布式控制可向各个分散驻地或下级部队授予活动计划权和协调权,以确保在一定控制范围内掌握主动权,特别是在实体/电子对抗环境中。下级指挥官通过分布式控制可应对作战环境的变化并利用转瞬即逝的机遇,当有明确传达的指挥官意图为下属行动提供指导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分布式控制(以及分散执行)的优势。
分布式控制与分散执行均支持部队在与上级指控中心通信中断的作战环境中连续作战。在竞争环境中作战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分布式控制,但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并且无法准确了解整体任务背景以及不断变化的作战限制因素与行动约束。
分布式控制聚焦于以下内容:
(1) 分配和执行指挥官的意图、愿景和指令;
(2) 确保按照指挥官的意愿进行兵力分配和任务分派;
(3) 局部整合动能与非动能能力以达到同步效果;
(4) 根据态势改进战役和战术计划。
3.3 分散执行
分散执行是在执行计划和指令过程中,通过授权实现有效作战控制,同时给予下级部队一定的自主空间,使其能够依据实时态势制定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并能够利用转瞬即逝的机会构建相对优势,成功完成特定任务。
为实现分散执行,空军部队指挥官与下级部队使用任务型指令,并明确传达指挥官意图,通过授权前线决策者(例如,空战管理人员、前线空中控制员),能够在复杂且迅速展开的作战中做出有效的现场决策,可在战术层面增强战斗力并迅速恢复能力。
分散执行聚焦于以下内容:
(1) 实施明确且具有前瞻性的指挥官意图;
(2) 执行按照一致认同的部队风险及任务风险评估与管理方法所确定的指令;
(3) 在战术层面整合动能与非动能行动及能力;
(4) 向能力和资格最低的层级实施有条件的授权;
(5) 通过否定式指挥,使下级指挥官在未被上级拒绝的情况下能够执行其认为适当的行动。
3.4 任务型指令
通过使用任务型指令,将使下属能在指挥官的意图范围内享有最大的自由行动权。任务型指令重点关注目的与效果,强调必须遵从上级指挥官的优先级和作战意图,但不强调具体的实现方式。指挥官通过任务型指令表明意图与方向,以提供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目标,从而使下属能够执行任务。指挥官的意图应明确各种目的、优先级、可接受的风险以及作战范围。下属应能凭借可用或易于获取的资源,仅根据指挥官的意图在指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作战。
任务型指令应清楚表明作战目标、战斗编组、指挥官意图、需由下属单位执行的任务以及最基本的协调指令。任务型指令应基于五段式指令格式(见图2),并应规定针对执行任务的下级部队指挥官的具体要求(能力、资源或连通性等)。
任务型指令应考虑以下要素:
(1) 指挥和支援的关系,包括直接联络权限;
(2) 有条件的权限;
(3) 作战区域;
(4) 目标定位优先级;
(5) 后勤保障方法;
(6) 与上级指挥部和同级部队的主通信/备用通信/应急通信/紧急通信计划以及相关的信息交换作战节奏;
(7) 预计需要指挥官作出决策的模棱两可的问题;
(8) 可接受的战略、部队和任务风险。
如果战前预估合理,计划假设将在作战实施过程中始终有效,此时任务型指令将最为适用且有效。
4 集中式指挥与任务式指挥的关系
虽然美军已经颁布最新的空中力量运用原则,并明确将以任务式指挥取代传统集中式指挥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集中式指挥方式将彻底消失。与之相反,传统的集中式指挥方式将与新提出的任务式指挥方式并存(以任务式指挥为主),并在作战使用时依据实际情况和作战需求进行选择。
在集中式指挥和任务式指挥方式间进行权衡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取决于具体情况并且需根据上级指挥部的指示运用指挥官的判断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高价值或具有时效性的目标、具有极端政治敏感性的行动、隐蔽行动/秘密行动、进攻性赛博空间作战或使用核武器)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执行特殊行动,特别是当联合部队司令有意牺牲战术效率或有效性,以换取控制战略效应并管理风险时,将可能优先采用集中指挥方式。
因此,虽然美军提出了新的空中力量运用原则,并将以此为核心开展后续能力建设。但在实际作战过程中,仍需针对具体场景和作战任务展开分析,在充分理解美军作战方式及原则,并综合各方因素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策略,将是在未来战争中取胜的关键所在。
5 启示及意义
(1) 任务式指挥是大国竞争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大国竞争时代的回归[11],美军发现其在未来战争中将在区域拒止环境下与近似匹敌对手在太平洋地区的广袤区域内开展体系化对抗(美军定义的太平洋战场跨度为4 000 km),其典型特征将表现为交战范围广、交战规模大、涉及装备多、持续时间长,且未来作战一般需要多域装备间进行复杂协调或协同,在高强度强对抗场景下,传统集中式指挥方式将在数据通信、计算处理和分析/判断/决策等方面面临极大挑战,难以实现OODA环的快速构建和有效闭合,无法有效满足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作战需求,因此必须加速开展指挥方式变革,适应未来战场无人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2) 任务式指挥是美军分布式作战概念落地实施的必要条件
为确保在未来战争中保持优势,美国防部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APPA)最早于2014年便提出了分布式空中作战概念[12],该概念是美军着眼于大国对抗而发展的全新空战模式,旨在将大型、昂贵、多功能有人战机的各类功能分解到大量低成本无人机上,构建由少量高性能有人机和大量无人机组成的协同作战体系,以较低成本实现更高作战能力,对敌再次形成不对称优势。在分布式空战概念下,大量低成本无人平台的运用将使参战装备数量显著增多,而其组合样式(含有人-无人协同)的多样化[13]和战场环境的复杂性又使传统集中指挥方式中的作战规划变得异常困难。为在最大程度上释放分布式作战的使用灵活性,就必须采用以任务目标和规则约束为前提的任务式指挥方式,通过建立以有限数量有人平台为核心的混合编队,实现对大量无人装备的分布式控制,再由无人装备以分散方式执行任务,从而在不显著增加带宽和算力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体系内大量装备间的高效协同,而指挥中心则以任务和规则分发方式,实现对有限数量有人平台的作战管控,确保达成任务目标。
(3) 任务式指挥是无人装备和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集成运用的必要基础
随着分布式作战概念的持续深化和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无人机和游弋式弹药(巡飞弹)为典型代表的新型无人装备正在现代战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4],从此前的阿美战争(纳卡冲突)到正在持续的俄乌冲突,从侦察感知到单兵清剿,从反坦克作战再到机场突击,都伴随着无人装备的广泛运用。在无人装备研制方面,美军目前已研发出Dash-X、“郊狼”(Coyote)、“弹簧刀”(Switchblade)等小型无人机/巡飞弹,同时已基于XQ-58A等大型无人平台,完成ALTIUS-600小型无人机的空中发射/投放[15],该型无人机此前已完成与MQ-1C武装无人机和“黑鹰”直升机的发射测试,可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作战需求。
由于分布式作战后无人装备不论从数量上还是可协同样式上都将呈显著增长,加之因对抗环境导致的场景变化,由此带来的高不确定性将使传统集中式指挥方式难以为继,必须依托正高速发展的智能化技术(例如美军正在开展的自主空战行动(autonomous air combat operations,AACO)、空战演进(air combat evolution, ACE)、先进战斗管理系统(advanced battle management system,ABMS)等项目)[16],通过构建与作战任务和场景匹配的目标函数,自动优化求解最佳方案,才可能实现无人装备(集群)自主作战、有人-无人高效协同,以及在对抗环境下的体系重组。而所有上述目标的达成均须以任务式指挥为前提,通过在任务目标和交战规则约束下的权力授予,为多样化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运用提供实施空间,支撑实现总体效能大幅跃升。
6 结束语
基于美军最新提出的空中力量运用原则,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空军将在其各种相互关联的发展战略、作战概念、技术能力开发、部队呈报结构和试验活动等方面,实际运用本文中阐述的各项原则并进行适应性改进。通过制定、整理和培训实用的任务型指令指南,基于持续优化的空中作战流程,不断完善空中作战指令和空中任务指令,并协调其与任务型指令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协调与整合太空/赛博空间部队、作战指令分配以及联合部队一体化运用等。
在此基础上,将依托“敏捷作战应用(ACE)”、“先遣联队”和“先进战斗管理系统(ABMS)”等能力建设项目,实现新型指挥方式落地,同时结合“蓝旗”(Blue Flag)、“红旗”(Red Flag)、“敏捷旗”(Agile Flag)等重大演习活动,全面评估“集中指挥、分布式控制和分散执行”兵力运用原则的作战效能,确保实战化能力形成,并为空军探索建设“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能力以及实施“联合作战概念”提供基础支撑和方法工具,美军在任务式指挥方面的发展动态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研究。
[1] BROWN C Q Jr. Air Force Doctrine Publication 1: The Air Force (AFDP-1)[EB/OL]. (2021-03-10)[2023-02-02]. https://www.doctrine.af.mil/Portals/61/documents/ AFDP_1/AFDP%201%20The%20Air%20Force%20Pocket% 20Size%20Booklet.pdf.
[2] 王彤, 郝兴斌. 美国“联合全域作战-概念下指挥控制能力发展分析[J]. 战术导弹技术, 2022(1): 106-112.
WANG Tong, HAO Xingbin. Analysis of Command and Contro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US Joint All-Domain Operations Concept[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 2022(1): 106-112.
[3] BROWN C Q Jr. Accelerate, Change or Lose[EB/OL]. [2023-02-02]. https://www.af.mil/Portals/1/documents/csaf/CSAF_22/CSAF_22_Strategic_Approach_Accelerate_Change_ or_Lose_31_Aug_2020.pdf.
[4] MULGUND S. Evolving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Airpower[EB/OL]. (2021-04-21)[2023-02-02]. 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Wild-Blue-Yonder/Article-Display/Article/2575321/evolving-the-command-and-control-of-airpower/.
[5] COLOM-PIELLA G. An A2/AD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Is Algeria Developing Anti-Access/Area-Denial Capabilities?[J]. Defence Studies, 2022, 22(1): 60-78.
[6] 刘禹彤, 张洋. 美空军先进作战管理系统项目进展及启示[J]. 飞航导弹, 2021(5): 13-16.
LIU Yutong, ZHANG Yang.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S Air Force Advanced Combat Management System Project[J]. Aerodynamic Missile Journal, 2021(5): 13-16.
[7] 李森, 田海林, 王刚, 等. 美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控系统(IBCS)研究[J]. 现代防御技术, 2022, 50(4): 84-100.
LI Sen, TIAN Hailin, WANG Gang, et al. Research on IAMD Battle Command System(IBCS)of the US[J]. Modern Defence Technology, 2022, 50(4): 84-100.
[8] 刘科. 联合全域战争背景下的敏捷作战概念研究[J]. 国防科技, 2022, 43(6): 71-77.
LIU Ke. Research on Agile Oper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Joint All-Domain Warfare[J].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2022, 43(6): 71-77.
[9] 苑桂萍, 张绍芳. 美军穿透型制空概念及相关导弹武器发展[J]. 战术导弹技术, 2018(1): 37-41.
YUAN Guiping, ZHANG Shaofang. Penetrating Counter Air Concept of USAF and Its Missile Weapon Development[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 2018(1): 37-41.
[10] 赵军伟, 李建华. 基于任务时限的NCIS力量编组研究[J]. 火力与指挥控制, 2015, 40(8): 117-121.
ZHAO Junwei, LI Jianhua. Study of NCIS Force Grouping Based on Task Time Constraint[J]. Fire Control & Command Control, 2015, 40(8): 117-121.
[11] 王锴. 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混合战争实践[J]. 军事文摘, 2023(2): 32-36.
WANG Kai. The Practice of Hybrid Warfare of United States in the Context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J]. Military Digest, 2023(2): 32-36.
[12] 杨斌. 空中分布式作战概念及关键技术分析[J]. 电讯技术, 2022, 62(6): 826-835.
YANG Bin. Concepts and Key Technology Analysis for Air Distributed Operations[J]. Tele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2022, 62(6): 826-835.
[13] 李磊, 汪贤锋, 王骥. 外军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最新发展动向分析[J]. 战术导弹技术, 2022(1): 113-119.
LI Lei, WANG Xianfeng, WANG Ji. Analysis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 of Manned-Unmanned Teaming of Foreign Forces[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 2022(1): 113-119.
[14] 李朝龙, 程呈, 冷伟峰, 等. 俄乌冲突中“弹簧刀”巡飞弹制导分析与思考[J]. 激光与红外, 2023, 53(2): 163-168.
LI Chaolong, CHENG Cheng, LENG Weifeng, et al. Analysis and Reflections on Guidance Technology of “Switchblade” Patrol Missile in Russia Ukraine Conflict[J]. Laser & Infrared, 2023, 53(2): 163-168.
[15] 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 Public Affairs. AFRL Successfully Completes XQ-58A Valkyrie Flight and Payload Release Test[EB/OL]. [2023-02-02]. https://www.afrl.af.mil/News/Article-Display/Article/2561387/afrl-successfully-completes-xq-58a-valkyrie-flight- and-payload-release-test/.
[16] 李磊, 蒋琪, 王彤. 美国马赛克战分析[J]. 战术导弹技术, 2019(6): 108-114.
LI Lei, JIANG Qi, WANG Tong. Analysis of Mosaic War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 2019(6): 108-114.
Analysis of Mission-Based Command of the U.S. Air Force for Joint Operations
ZONGKaibin,ANFei,ZHAOWenting,YANLiudan,LIUHaijun
(Beijing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System Engineering, Beijing 100854, China)
In April 2021, the U.S. Air Force Doctrin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Center officially released “Air Force Doctrine Publication 1: The Air Force” (AFDP-1) (March 10, 2021 Edition), completing a major update to the Air Force Basic Doctrine Volumes 1 and 2, which serve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the U.S. Air Force and will guide the combat operation for a long time. In the updated AFDP-1 doctrine,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mission-based command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air force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decentralized execution" should be replaced by "centralized command, distributed control and decentralized execution",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concept,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equipment form,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gaining advantages in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and strong enemy confrontation. In view of such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s of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s,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mission-based comm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al command paradigm, and gain the insight into the connotation behind such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ce brought by this change, which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ning.
mission-based command;joint operation;operational doctrine;U.S. air force;operational concept
2023 -03 -19 ;
2023 -05 -24
宗凯彬(1988-),男,北京人。高工,博士,研究方向为体系与系统总体设计、智能化作战等。
10.3969/j.issn.1009-086x.2023.03.008
E835.8;TJ76
A
1009-086X(2023)-03-0066-09
宗凯彬, 安飞, 赵文婷, 等.面向联合作战的美国空军任务式指挥模式探析[J].现代防御技术,2023,51(3):66-74.
Reference format:ZONG Kaibin,AN Fei,ZHAO Wenting,et al.Analysis of Mission-Based Command of the U.S. Air Force for Joint Operations[J].Modern Defence Technology,2023,51(3):66-74.
通信地址:100854 北京142信箱30分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