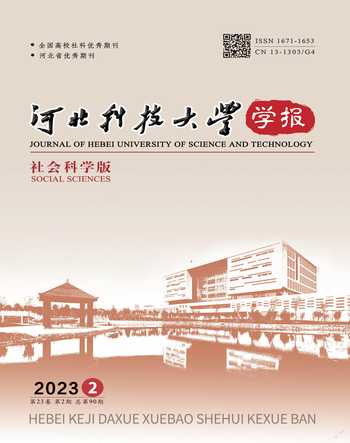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进路研究
嵇红涛 刘龙女
摘 要:当前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渐向现代过渡的后乡土社会阶段。农村纠纷逐渐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地缘关系减弱、纠纷缘由利益化等特点,单纯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农村纠纷类型。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农村法治与村民自治、公民权利救济理论的共同意涵。纠纷处理中应把握法情协调、完善行政救济与人民调解、加强各纠纷解决机制协作、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农村纠纷治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法律的本土性;人民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7535/j.issn.1671-1653.2023.02.006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n Rural Areas
JI Hongtao1, LIU Longnyu2
(1.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 China;2.Longgang Social Services Bureau, Wenzhou 325802,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rural areas are in a post-rural society that is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Rural disputes are gradually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of dispute subjects, weakene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interest oriented dispute causes. It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complex and changeable types of rural disputes simply by relying on tradi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n rural areas is an essential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as well as the common meaning of the universality and locality of the law,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and villagers' autonomy, and the theory of civil rights relief.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principles of legal situation coordination, improve administrative remedy and nongovernmental mediation,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vigorously develop the rural economy to build a multi-disciplinary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words:rural dispute governance;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the native nature of law; people's mediation
现代司法供给与农村社会纠纷解决需求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不能简单概括为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乡村百姓法律意识薄弱等,更有农村社会的权利结构、农村固有的传统礼法规则等深层次原因。除此之外,农村纠纷类型多样、矛盾复杂,这也使得采用某种单一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或现代纠纷解决机制都难以全面应对[1](P55-62),构建新形势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推进农村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一)农村纠纷性质及特点
当前,农村社会依旧并将较长时期内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学者们将其称之为“后乡土社会”[2](P55-57)。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固有的城乡界限,农村群众相继持续往返于城乡之间,原有村庄的封闭状态逐渐开放。同时,源于外界的新思想在农村社会得以蔓延,农村社会的固有结构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人们之间逐渐陌生化、利益化,导致人际信任逐渐缺失,农村纠纷数量激增。传统纠纷与现代纠纷相互交织,沿袭已久的礼法规则、宗族治理、熟人调解已经不能包治百病,现代司法纠纷解决手段也有些力不从心,单纯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或是现代的纠纷解决机制难以满足农村社会法治发展的实际需求。
1.农村纠纷的性质
第一,农村纠纷是一种冲突状态。
顾培东[3](P2-7)指出纠纷是对现有制度、规则或主流道德观念的逆叛。范愉[4](P70)认为纠纷是当事人之间因为利益分配原因而造成的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对抗行为。笔者认为纠纷是指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間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观念不同而形成的对抗状态。农村纠纷则是村集体内部人员之间或村集体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之间因为利益不均等导致的冲突状态。纠纷的发展过程历经纠纷的萌芽阶段、发生阶段和解决阶段。纠纷的萌芽阶段中当事人可能会选择容忍,将纠纷自行消解在萌芽之始。纠纷的发生阶段双方之间的纠纷多以协商或者暴力对抗等方式呈现,若纠纷仍未化解,则此时纠纷双方借由信任的第三人或司法机构介入解决。纠纷的发展不仅是时间的延续,更是各利益相关人的不断介入,从主体和空间上延展开来,具有多方关联性,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生理)对抗状态。若将纠纷简单界定为一种对抗行为,则涵盖面较窄,纠纷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泾渭分明,往往相互穿插融合。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是消解冲突状态的一种可行路径,需要注意的是,不少纠纷情形并不必然以司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才能得以妥善解决,这是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重要前提。
第二,现代纠纷与传统纠纷并存。
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纠纷的特点,农村纠纷可分为传统纠纷和现代纠纷,新形势下农村纠纷的重要特征是传统纠纷与现代纠纷并存。
费孝通提出的“乡土社会”[5](P7-9)就是典型的传统乡村样态,特点是流动性弱、交际圈相对狭小、土地是人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乡土社会中的传统纠纷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熟人之间的纠纷,比如,家庭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债务纠纷,以及围绕土地或生产而产生的宅基地纠纷、土地界址划分纠纷、庄稼毁损纠纷等。当乡村人口大规模进城往返流动,土地不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核心要素,进城务工、土地流转出让等成为获得收入的新方式,现代纠纷因而产生,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合同纠纷、产品侵权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
2.农村纠纷的特点
第一,纠纷主体多元化。农村纠纷中的参与主体涉及村集体、基层领导干部、公权力机关、村外人员等。譬如,最简单的借贷执行案件往往都需要村长、村支书等“非直接相关人员”出面参与[6](P33-35)。此外,农村纠纷发展处理过程中,极容易吸纳亲友、家族成员等近亲缘主体,纠纷主体随着纠纷发展也由两人逐渐发展为多人,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的群体纠纷。
第二,纠纷地缘关系减弱。法社会学家布莱克的“关系距离学说”指出纠纷的发生与人们空间关系的远近有关。当人们关系密切时,纠纷较少发生且往往能够自我消解[7](P1-6)。当人们关系较为疏远时,纠纷增加且不易内部化解。传统农村社会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相互信任依赖,关系紧密,纠纷解决方式简单。当“差序格局”[8](P38-40)被逐渐打破,人们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社会流动增强,对村集体的依赖减弱,纠纷的地缘关系减弱。
第三,纠纷缘由利益化。乡土社会中的熟人调解之所以屡试不爽,不仅仅是熟人这一身份具有居中调停的作用[9](P199-233),究其根本是因为纠纷的缘由多为“面子”之争,即便纠纷并非因“面子”而生,往往也可以因“面子”而解,传统纠纷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可以因顾及“面子”或者说考虑“和为贵”的思想而得到妥善解决。现代农村纠纷事由多与经济纠纷挂钩,其本身就增添了许多利益色彩,经济利益之争削弱了“人情味儿”,其纠纷处理的目的更倾向博得属于自己的或者说更大的利益,这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进路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 农村纠纷解决的实践路径
随着现代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诉讼、仲裁、行政裁决等纠纷解决机制相继在农村社会建立,当下农村主要有如下几种纠纷解决机制。
1.自决
自决是指纠纷双方通过各自力量解决解纷的方式,没有第三方的介入,主要体现为和解、斗争两种方式。自决是最为原始的纠纷解决方式,灵活便捷,没有程序限制,更符合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村民的思维方式。但自决没有外在规则的限制,完全依靠双方意志,容易演化成暴力冲突甚至导致群体纠纷,具有很大的結果不确定性。
2.说和
说和是由亲友、邻里或者村中有一定威信的人居中调停,从而化解纠纷的方式,有“民间调解”之称。民间调解纠纷的依据是民间习惯和传统礼法规则,调解纠纷的裁判者是矛盾双方信服或信任的对象,说和能够较好地缓和矛盾双方的对抗性,疏导矛盾,促成双方和解。说和是农村社会固有的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频繁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依赖关系逐渐减弱,村中有能力之人解决纠纷的积极性也逐渐降低。
3.调解
调解是基于纠纷双方自愿而进行,由中立第三方居中调停、劝解,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一致,从而解决纠纷,可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人民调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进行,依靠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人民调解员多是义务调解,缺少积极性。此外,调解员多由村干部兼任,村干部村务繁杂,往往无暇顾及。行政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并且因行政调解协议履行产生的纠纷,由于部分调解协议是“公私交易”的产物,不完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因此,行政调解协议只有部分可诉。行政调解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程序性不足,农村纠纷调解中的行政调解人员与当事人甚至具有亲缘关系。诉讼调解即法院调解,仅适用于诉讼程序当中,在执行程序、非诉程序中无法适用。法院调解以自愿为原则,但民事调解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对于法律知识缺乏的农民来说,他们本就对诉讼心存怯意,因此在很多时候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能会受到压制,导致其对法官信任度的降低。
4.诉讼
诉讼俗称“打官司”,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村社会也是如此。诉讼是现代社会法制发展的产物,对于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的“后乡土社会”农村来说,诉讼的程序性及专业性,使得诉讼成为成本最高的纠纷解决方式,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加重了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司法资源分配不均增加了经济成本,严格的程序要求增加了时间成本,诉讼的对抗性还可能会加剧双方当事人的矛盾。
5.裁决
裁决有行政裁决和仲裁裁决两种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纠纷处理方式。当前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中,行政裁决使用率较高[10](P21-35),仲裁兼具民间与司法性[11]](P94-100),由于其特征、主管范围等原因在农村使用率较低。当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的行政法,关于行政仲裁的程序等相关规定还不完善,使得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缺乏限制,容易滋生不法行为。仲裁在农村缺乏适用性条件,主要原因是仲裁的审理范围较窄,其主要适用于较大的财产性纠纷,仲裁费相对较高,并且仲裁机构多设置于省级行政区,不便于农村纠纷解决。
二、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
乡村社会共存的几种纠纷解决路径迎合了乡村群体的不同需求,但也时常陷入困境,主要表现为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效果日益下降、司法供给与农村社会需求不适配以及行政不作为等方面。
(一) 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效果日益下降
农村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以自决和说和为主,其解决纠纷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坚固的内部信任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改变了农村的物质生产方式,架起了城乡沟通的桥梁,改变了既往的农村社会结构。一方面,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依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维系的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秩序规则具有内生性,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下,人们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行为标准,礼法秩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遵循的规则。“大家都是熟人么,打个招呼就是了”“这点小事不麻烦,谁没个需要帮忙的时候”——这类话语在乡土社会中都是耳熟能详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可以胜过担保抵押等相当可靠的法律保障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强,农村人口分化为留守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口两种,外出人员思想观念开始转变,利益追求逐渐取代家族血缘和邻里关系,社会信任感减弱。多样化的纠纷类型使得传统糾纷解决机制呈现疲软之势。另一方面,传统农村社会中家族族长和德高望重的人员对农村社会管理有着有力的控制权,但“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普法活动涌向农村“稀释”了农村礼法规则的功效,公权力逐渐下沉到农村,打破了原有的治理体制,农村纠纷解决主要依靠行政权力。此外,作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是农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一些村中的精英被吸纳到村委会当中,但村委会并不具有行政权力的强制力,治理手段很难落到实处。有的村委会被村中“有本事的人”把控,而所谓“有本事的人”在村民眼里几乎等同于“能赚到钱的人”,因此形成了由经济能人把控村委会的局面。
(二) 司法供给与农村社会需求不适配
从个人的选择而言,使用何种纠纷解决方式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时间、金钱、解纷效果、公正性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譬如,诉讼的成本不包括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以及当事人投入的时间精力等,“一讼十年仇,一讼十年财”的情况屡见不鲜。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化解纠纷,是一种进行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高成本的诉讼不仅难以达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效果,还可能搅乱农村稳定局面,代价大且不利于人际关系恢复的纠纷解决方式为大多农村纠纷主体所排斥。
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欧陆法系的国家经历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法治过程,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因而选择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使用公权力进行社会建设,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行政权具有主动性,而司法权是被动的,需要当事人的积极配合才能启动,这种司法权力很难融入农村社会,“信访不信法”的普遍观念就是一种明显的行政权主动性的表征,信访自身透露着一种“民本主义”的色彩,始终游离于传统治理和现代法治之间[12](P20-24)。
从规则层面而言,现代司法裁判依据的规则是从西方引入的基于契约关系的现代法律,在农村地区存在“水土不服”现象。现实的农村社会仍具有乡土社会的某些特质,在这个熟人社会有其内生的一套规则,且早已内化于人们的习惯思维之中。繁杂的法律知识对农村人来说过于陌生,其更适用于精英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施行了“送法下乡”“基层法律服务”等一系列的普法行动,将现代法律和诉讼理念推行到农村社会。这种推行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能解决纠纷的传统方式得不到认可,国家认可的纠纷解决方式又解决不了问题。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要充分考虑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认识到农村社会的特殊性。
(三) 行政力量未发挥预期功能
“父母官”思想在老百姓心里根深蒂固,发生纠纷时,当内部无法消化,人们往往选择寻求行政力量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在地方的控制十分严格,随着税制改革,国家资源供给的后撤,行政力量在农村地区越发力不从心。行政机构在农村主要为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等,在大多数地区的基层,这些机构人力和专业资源往往不足,难以发挥设想的多元解决农村纠纷的职能,导致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不良。
农村行政调解难以奏效还表现在行政监督不足,这使得基层政权的运作偏离法治的轨道[13](P37-39)。人们认为官司的输赢就在于个人背后力量的深浅,纠纷解决过程演变成一场关系拉力赛,甚至引发了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等一系列新问题。当前,我国尚未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法,关于各部门间的权责划分不清,加之农村基层权力运作监管不严,存在各部门间权责不明
,甚至相互推诿扯皮的情况,原有的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愈演愈烈之下甚至会演变成恶劣的群体事件,对社会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影响社会稳定。
国家资源供给不足、监督不力、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等使得行政力量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应发挥的作用大打折扣,降低了行政公信力,行政力量在农村社会纠纷解决中难以发挥预期功能。
三、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是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原因所致,其根本矛盾是法律普遍性与本土性、农村法治与自治间的冲突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农村建设的落后[14](P5-11)。
(一) 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
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农村自治和现代法治以及权利救济理论的共同意涵。
1.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良好的法律”[15](P199)。这就意味着生效的法律符合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是良法之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差异使得评价法律良莠的标准不一,法律具有普适性与本土性双重含义。
关于法律的普适性,学界通常从形式主义、目的论两方面论证[16](P104-110)。形式主义认为法律是一个封闭自足的圆满体系,法只要满足了法律的构成要素就可以称之为法律,不用考虑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即“恶法亦法”。目的论则认为不同时代背景的法律不可能一致,但人类社会始终以公平正义等价值作为终极追求。法律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公平正义等人类价值的过程。耶林就曾在承认法律具有地区特色的基础上论证了法律的普适性或者人类共同价值观构建的路径[17](P120-134)。
法律的本土性是指法律与农村社会固有的秩序规则——如道德、习惯等礼法的关系处理,实现法律与本土资源的融合。苏力[18](P8)认为社会习惯、礼法规则、道德秩序等本土资源甚至比法律更具效率和效力,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性需求,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易行为提供了行为模式。经过时间过滤的礼法规则已不再是封建等级社会身份关系维护的工具,其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即保护权利,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从法律与道德关系来讲,二者并不是对立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与本土资源本是共生共存的,共同致力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农村法治建设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充分发挥法律和本土资源的各自优势和功用,实现二者的协调。
2.现代法治与农村自治
农村自治有两层含义,对个人而言意指自主决定和免受干预的自由状态;对共同体而言意味着一个组织、村落或者社区通过其代表决定公共事務、管理公共资源[19](P34-40)。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除奴隶社会外)自治和他治始终相伴共存、此消彼长。
自治与法治并不是对抗关系,二者是相谐相生的[20](P59-73),具体表现为:第一,自治促进法治的发展。法治以民主为基础,自治有助于民主建设。自治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徒法不足以为政”,法律未及之处需要自治来发挥作用。第二,法治为自治提供保障。国家通过立法赋予社会自治主体权力。法律不是唯一的社会治理手段,应当为社会自治预留空间,不应当过分干预公民生活,凡是私人可以处理的事务就应当允许社会自治。现代法治包含了良法与善治两个层面的含义[21](P114-121),善治以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宗旨。善治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治理理念,不仅要求树立法律权威,而且要求避免唯法是从,排斥其他治理方式。
现代法治和农村自治的关系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秉承善治理念,整合社会资源、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充分发挥各主体的解纷能力,协调公权力、民间机构等各方作用,实现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功效的最大化。
3.公民权利救济理论
法治社会的建设为诉讼等公力救济提供了正当性理据,同时,经济发展为公力救济打下了现实基础,诉讼等公力救济在社会救济体系中占绝对地位,掩盖了私力救济的功效并压抑了私力救济的发展。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村医疗、教育等相比于城市相差甚远,司法资源分配不均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权利的救济难度。公力救济在农村社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权利保障的作用。我国的法律法规已建立了完善的农民土地权利体系,但地方权力主体基于政绩和经济发展考虑,仍会弱化农民个体权益保护[22](P149-158)。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农村土地权益问题。
土地征迁割据了农民的土地,漏发、迟发甚至拒发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补偿款的现象时有发生[23],农民被置于利益分配链的末端,社会保障和权力监督不足,易发生权力主体以微弱的补偿来掩盖对农民弱势群体的权利侵犯的现象,由此滋生了大量的纠纷。
农民权利保护应落在实处,不应简单地将问题都归咎于农民权利意识淡薄、知识匮乏,公权力部门应敢于直面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社会的供给不足。农民权利保护应树立权利平等观、权利正当观和权利主体观[24](P44-52)。第一,树立权利平等观,平等地给与公民权利关怀。在某些方面给与农民特殊照顾,努力实现实质平等。第二,树立农民权利正当观。人权是人生而拥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而拥有的权利。人权通过法律表达而成为法律权利,所以农民具有拥有法律权利的正当性。第三,树立农民权利主体观。由于农村制度建设落后,农民往往缺乏意愿表达渠道和机会,只能被动地听从权利主体的主观安排,表达权受限,权利主体身份存在瑕疵。
(二) 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以权利保护为基础(最根本的目的——解决纠纷,为受到损害的权力提供救济),在此基础上实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结合,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1.司法实践应注重法与情的协调
司法不仅要合法还要合理,司法不仅是法律的施行过程,还包括对情理的考察。虽然农村社会关系日益疏离,农村社会依旧是一个看重人情关系的后“熟人社会”,解决纠纷不仅是维护应有利益,还注重关系恢复,为解决纠纷人们愿意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来达成和解。中庸之道依旧是普通人的首要选择。
第一,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应当实现优势互补、良好对接。目前,司法在农村社会的权威尚未确立。诉讼的程序性特质使其在农村社会生存艰难,人们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对法律采取默示规避。而人们熟知且接受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处理中可以弥补诉讼的不足,二者优势互补,构建农村的良好秩序。对于较为重大的纠纷,适合使用终局性的诉讼来解决,对于较小的传统纠纷则适合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解决。
第二,将乡村有威望的人士吸纳到诉讼程序当中,他们熟知的乡土知识可以有效弥补法官地方性知识的不足。此外,将传统农村社会权威人士吸纳到诉讼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人们对于诉讼的防备心理,增加诉讼的人情味儿,以情感作为纠纷解决的润滑剂,弱化诉讼的对抗性,有利于纠纷的解决以及增加人们对于审判结果的信服。
第三,在司法实践中
适度融入习惯法。习惯法可溯源于传统社会中礼治、德治、交往规则等对人们行为的约束。
在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法可适当吸纳习惯法,地方习惯是某一地区人们长久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社会规则,在社群团体内具有高度的认可度。
第四,提高办案效率,做好法律援助。农村纠纷大多简单、标的额小,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以及速裁程序,司法机关针对此类案件需更加重视办案的效率,以节省当事人的成本。我国法律资源分配不够均衡,律所、法律援助机构、法院等至多设置到县,农村司法资源极为匮乏,导致法律适用困难。农村法律援助工作除依靠律师事务所和司法行政机关外,应当加大农村司法投入,建立专门面向农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村居民提供法律服务,缩小司法与农村的距离。
2.完善行政救济和人民调解制度
行政救济作为农村纠纷解决方法中为人民所相对信赖且易于施行的一种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完善行政救济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各部门职责。行政部门设置往往过于繁杂,部分职能混同,分工不明。如果政府权力运行稍有偏差,容易出现相互推诿扯皮,使群众诉苦无门,耗费心力。
第二,行政救济要兼顾程序性与灵活性。政府工作要依法进行,行政救济的效率性和积极性优于司法救济,不能过分强调程序性,应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兼顾灵活性,做到高效便民。
第三,建设阳光政府,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加强行政监督,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重大事项组织听证,让当事人了解纠纷解决的过程,增强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度,避免纠纷的扩大。
第四,加强各级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司法所是一线司法行政机关,负有排解纠纷的职责,还具有连接基层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间的桥梁作用。司法所应积极发挥地方优势,做好农村纠纷的预防工作及纠纷发生之后的指导和分流工作,有序且有效地促进纠纷解决[25](P84-91)。
第五,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推进村民自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保障人民权利,广泛听取民意是政府优化服务的前提。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听取农民的利益诉求,依民意办事,谨防以个人主观意志独断专裁,要真正落实农民权利主体地位。
此外,人民调解是农村社区自主解决纠纷实现自治的重要途径,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也是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应有之义。调解过程中应宣传法律知识,提升人们的法律意识。完善人民调解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乡镇财政转移支付和村委会支持有限,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持续开展,建议设立专项人民调解资金并做好监督工作,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保障调解员的工资,提升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另外,要适当提升人民调解员的门槛,提升调解员的工作素养,不能简单地由村领导兼任,從而提高人民调解的专业性。
3.加强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为了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各种资源,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更好的发挥功用,应在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加强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构建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使纠纷解决更具体系化。
第一,协调诉讼与调解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法院的最终审查权是人民调解协议的坚实后盾,但这并不等同于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确保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若存在违法的情况,可确认调解协议无效,进而转入诉讼程序。人民调节制度的运作,应坚持政法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相互协作,综合排查社会纠纷。此外,应当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司法活动,法院也应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与支持,可以吸收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定期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和业务指导。有司法做后盾,可以有效增强百姓对于人民调解的信赖。
第二,协调诉讼与行政机制的关系,明确法院对行政行为仅进行合法性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来看,
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双方当事人可在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后共同向人民法院确认该协议的效力,被确认后的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双方当事人未共同向法院申请确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的情形尚未明确规定。有别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具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加大了行政调解协议的可信赖程度,若双方未共同向法院申请确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发生纠纷时,一方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调解协议审查,经由法院审查后确认行政协议合法合规且确系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可以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
第三,协调诉讼与仲裁的关系。仲裁作为一种非硬性且专业性较强的民间纠纷处理方式能有效应对农村纠纷,但由于仲裁委员会设置的行政级别要求、仲裁的门槛成本等多种因素使得鲜有农村居民在遇到具体纠纷时选择仲裁处理。人民法院可协商仲裁委员会在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设置附仲裁机构或建立以现有基层法院为入口对接仲裁的纠纷处理通道,便于农村群众选择相对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民商事仲裁与诉讼衔接时,应权衡把握排除司法对仲裁的不合理干预、保障仲裁效率、司法尊重支持仲裁裁决等原则。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加大对仲裁的支持,对仲裁协议审查的要求适当放宽,扩大可仲裁的事项,更好地发挥仲裁在纠纷处理中的作用。
4.发展经济以强化村民维权观念
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农村社会善治,要保障农民权利,更要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首先应完善农村制度建设,为农村发展保驾护航。土地征迁获得补偿款是农民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应当按照规定悉数发放给农民,使其享受农村建设的成果。其次,实现公平分配,对农村信贷提供政策支持。现有的金融体制以经济效益作为信贷资格评审的唯一指标,致使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困难,难以扩大生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明显偏向城市,多用于城市建设,对农村的支持较少,应当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最后,加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就业问题,改善农村土地荒芜、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构建和谐农村。
四、结语
处于“后乡土社会”的农村,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弱流动性的封闭村庄逐渐开放起来,人们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随着城乡之间沟通联系的增强,其思想观念不断转变,人际信任关系逐渐减弱……种种变化导致农村纠纷日益复杂且解决难度增加,农村纠纷解决机制面临困境,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文化因素的互斥(现代法治建设与农村传统自治的冲突、现代法律与礼法秩序的冲突)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农民权利救济缺位。构建多元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要求倡导普遍一体化法治的同时要兼顾地方性知识,法治和自治理论要求在大力推进现代化法律规则的同时要尊重地方人们之间的原有“自生秩序”。农村法治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大力推进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法治化、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程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衔接[J].法律适用,2016(2).
[2]刘奇.中国乡土社会面临十大转变[J].中国发展观察,2018(7).
[3]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4]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6]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J].当代法学,1993(3).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9]陈柏峰.暴力与屈辱:陈村的纠纷解决[J].法律和社会科学,2006(1).
[10]孔繁华.行政与司法之间:行政裁决范围的厘定与反思[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1).
[11]李向玉.农村集体土地权属之争:问题、成因与司法终局之路径选择[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12]封丽霞.中国人为什么“偏好”上访?——一个法文化视角的观察[J].理论与改革,2013(4).
[13]李倩.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2016(10).
[14] 陆学艺,杨桂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1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6]唐崛.论法律普适性价值基础的重构[J].社会科学家,2018(7).
[17]张世明.再思耶林之问:法学是一门科学吗?[J].法治研究,2019(3).
[1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9]陈佩.社会自治中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北京:中央党校,2016.
[20]杨嬛.他治与自治互动下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变迁以及启示[J].中国农村研究,2017(1).
[21]王利明.法治:良法与善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
[22]陈菲菲,肖泽晟.我国农村土地权益分配上的利益冲突与平衡[J].江苏社会科学,2020(3).
[23]沈冠楠.万安县建峰村多个村小组征地补偿款迟迟未发放[EB/OL]. https://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21/10/12/019416678.shtml,2022-09-01.
[24]刘同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法治转型——以农民权利为视角[J].法学,2013(9).
[25]彭小霞.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研究[J].行政与法,2014(4).
收稿日期:20220819
基金项目: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2021年度研究课题(2021-ZD-01)
作者简介:嵇红涛(1997-),男,江苏连云港人,廈门大学法学院2022级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刘龙女(1992-),女,山西运城人,温州市龙港市社会事业局办事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