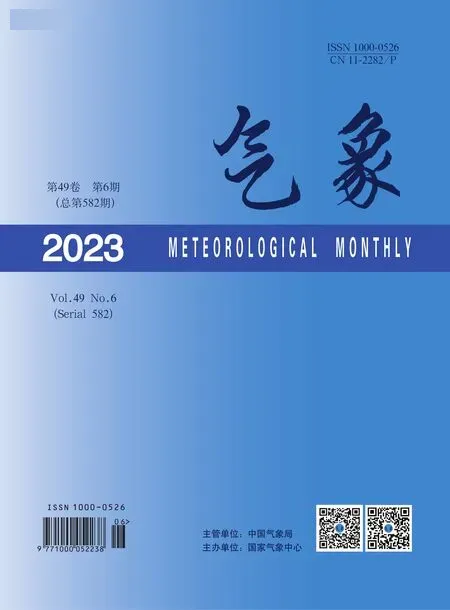闽南沿海一次海雾过程的多源资料综合分析*
张 伟 李 菲 吕巧谊 崔梦雪 张妤晴 陈德花
1 厦门市海峡气象开放重点实验室,厦门 361012
2 厦门市气象台,厦门 361012
提 要: 基于自动站资料、ERA5再分析资料、葵花8号卫星资料、翔安站多源观测资料,分析了2021年4月1日闽南沿海一次大雾过程的环流形势、演变特征和微物理结构。结果表明此次是一次典型的海雾过程。雾形成时500 hPa为偏西—西南气流,低层为一致的西南气流与反气旋下沉气流,近地面存在逆温层和湿层,为海雾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静稳的环流形势和充沛的水汽条件。此次大雾过程存在雾和低云的相互转化。白天以低云为主,傍晚随着气温的下降和整层风速的减小,低云逐渐接地转变为雾。清晨由于偏西气流的作用,沿海的雾再次转变为低云。利用气溶胶激光雷达推演雾顶高度,雾的初生和发展阶段厚度相对较低且波动性大,成熟阶段雾顶高度约为100 m。微物理参数分析表明雾过程的平均粒子数浓度为52.4 个·cm-3,液态水含量为0.084 g·m-3,平均直径为9.4 μm;1分钟平均粒子数浓度最大达到132.6 个·cm-3,液态水含量达到0.7321 g·m-3。此次过程不同阶段粒子数浓度和液态水含量的谱分布特征具有较大差异,其中数浓度的谱分布在初生、发展和消散阶段,以单峰结构为主,峰值直径为4~6 μm;成熟阶段表现为双峰结构特征,主峰位于4~5 μm,次峰位于24~26 μm;液态水含量同样为双峰分布,但主峰位于24~26 μm,次峰位于5~6 μm;表明雾的粒子数浓度受小粒子影响为主,但液态水含量以20~30 μm的粒子贡献最大。从发展到成熟阶段谱对比来看,20~30 μm粒子数量的增加使得液态水含量明显增大,这是导致能见度进一步下降的主要原因。
引 言
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的微小水滴或冰晶导致的一种灾害性天气。海雾是冬春季节闽南沿海的重大气象灾害之一,对沿岸城市的港口船舶进出和机场飞机起降等航行安全产生巨大影响(韩美等,2016)。由于海上缺乏观测资料,对海雾的实时地基监测难度较大,且数值模式对海上能见度定量预报的TS评分低(Zhou et al,2012),导致海雾预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开展相关研究极其重要。
台湾海峡是我国沿海主要的雾区之一(王彬华,1983)。学者针对台湾海峡内的海雾做了较多的统计分析(许金镜,1990;苏鸿明,1998)、环流分型(陈千盛,1986)、卫星反演(张春桂等,2009)和进展综述(韩美等,2016)等工作。研究指出台湾海峡海雾主要出现在3—5月(苏鸿明,1998),夜间出现概率高于白天,南部高于北部(马治国等,2011)。平流冷却降温是海雾形成的主要机制之一。闽南沿海存在一条带状冷水区域,上游的偏南暖湿气流遇冷水带被冷却凝结,在静稳的天气形势下就容易形成海雾(白彬人,2006)。海雾形成时,海温通常不高于25℃(王彬华,1983),海面风速通常低于5 m·s-1,气海温差介于0.5~3℃(气温大于海温),以1℃附近概率最大(林卫华等,2008)。
近年来随着观测设备的快速发展,基于边界层梯度观测(陆春松等,2010;梁绵等,2019)、毫米波云雷达(岑炬辉等,2021;胡树贞等,2022)、气溶胶粒径谱仪(郭丽君等,2015;Guo et al,2015)等多源融合资料的研究逐渐增多,进一步加深了对雾形成过程中边界层精细化结构的认知。雾滴谱仪的应用则加深了对雾的微物理过程的认知(Gerber, 1981;Gultepe et al,2006)。国外针对雾滴谱的研究起步较早。Eldridge(1961)研究了美国地区的雾滴谱特征,Kunkel(1971)基于雾滴谱参数,建立了能见度与液态水含量的参数化公式。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华南沿海(黄辉军等,2010;岳岩裕等,2013;徐峰等,2012)、东南沿海(张曦等,2016;张伟等,2021)、华东沿海(杨中秋等,1989)、黄渤海(Wang et al,2020;黄彬等,2014;2018)及其县郊(祖繁等,2020)、城市(李子华等,1993;李子华和彭中贵,1994;刘端阳等,2009;王庆等,2019;2021)、山地(吴兑等,2007)等开展了诸多观测试验,对不同类型雾的微物理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研究表明降温冷却对雾的爆发性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濮梅娟等,2008)。雾滴谱在降温过程中得到爆发性拓宽,成熟阶段的滴谱形态主要呈现单峰或双峰分布特征,主峰集中在小粒子端(王庆等,2019)。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征,雾越强双峰特征结构越明显(张浩等,2021)。对于不同的观测环境,雾滴数浓度量级可以从10 个·cm-3变化到103个·cm-3,液态水含量通常低于0.5 g·m-3。
2021年3月末至4月初,闽南沿海及台湾海峡发生了一次大范围的强浓雾过程,以4月1日夜间的雾过程最为强盛,对海上交通影响最为明显。本文基于翔安区气象局布设的自动站、微波辐射计、风廓线雷达、3D气溶胶激光雷达等多源观测资料,结合ERA5再分析资料,分析此次雾过程的环流形势、边界层特征等。利用雾滴谱仪分析了雾过程的微物理参数特征,研究其演变过程中的微物理过程,以期为此类大雾的预报以及模式模拟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采用资料
使用的资料如下:(1)闽南地区133个区域自动站能见度观测资料(站点海拔高度均在200 m以下);(2)翔安站多源垂直观测资料,包括微波辐射计、风廓线雷达和3D气溶胶激光雷达资料(观测设备分布及其参数分别见图1、表1);(3)欧洲中心(ECMWF)第五代全球再分析数据产品(ERA5);(4)葵花8号高分辨卫星红外通道观测资料(水平分辨率:2 km×2 km);(5)雾滴谱观测资料,采样仪器为美国Droplet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公司的FM-120型雾滴谱仪,采样频率为1 Hz,测量的粒子直径范围为2~50 μm(祖繁等,2020),分为30个非等间距区间,采样地点为翔安区气象局业务楼顶,海拔高度约为20 m,距离海岸线不足1 km。

图1 (a)闽南沿海能见度测站分布,(b)翔安区气象局场内观测设备布局Fig.1 Distribution of (a) visibility stations in southern coast of Fujian, and (b) observation instruments in Xiang’an District
1.2 微物理参数计算方法
本文使用的微物理参数包括粒子数浓度(N,单位:个·cm-3)、液态水含量(L,单位:g·m-3)、平均直径(rm,单位:μm)、中值体积直径(MVD,单位:μm,由仪器自动输出)等,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为直径,n(r)为分区间的粒子数浓度,Lr为单个区间的液态水含量,ρ为液态水的密度。
2 雾过程概况
2021年4月1日,受稳定的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闽南沿海出现了一次大范围雾过程。统计4月1日08:00至2日08:00(北京时,下同)闽南区域最低能见度(图2),1000 m以下能见度站点基本出现在沿海以及湾口地区,尤其是200 m以下能见度基本出现在沿海,越深入内陆能见度越高,叠加一致的偏南暖湿气流,初步表明这是一次平流海雾过程。从能见度区间分布来看,1 km以下站点数为66个,占比为49.6%;其中最低能见度介于500~1000 m的站点数为10个,占比为7.5%,比例相对较低。200~500 m能见度站点数为25个,占比为18.8%。过程最低能见度低于200 m站点数为31个,占比为23.3%。逐分钟最低能见度为66 m,出现在翔安站,时间为2日04:04。

图2 2021年4月1日08:00至2日08:00闽南地区最低能见度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minimum visibility in southern coast of Fujian from 08:00 BT 1 to 08:00 BT 2 April 2021
以过程最低能见度出现的翔安站为例,分析能见度和各气象要素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图3)。1日17:00之前,翔安站气温约为22℃,能见度较高,基本在3000 m以上。17:00起气温逐步下降,从21.7℃下降至21℃。与此同时,能见度呈现快速振荡下降的趋势,在18:07达到最低,为531 m。此后随着气温的短暂上升,能见度也随之逐渐上升,一度超过2000 m。19:20能见度快速下降,雾呈现爆发性发展的特征,15分钟内能见度从2000 m以上下降至250 m 左右,气温在此过程中逐渐下降。22:37随着气温的进一步下降,能见度也持续下降。1日23:00 至2日05:00能见度基本在200 m以下,为本次过程的最强时段。在此过程中受长波辐射冷却作用影响,气温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最低达到20.5℃。风向以西南风为主,10分钟平均风力小于2 m·s-1。2日05:20起,陆地上的风向偏西分量加大,翔安站能见度快速上升至3000 m以上。整个雾过程中温度露点差基本在0.2℃以内,相对湿度接近100%,水汽充沛。能见度与气温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气温下降伴随着能见度的下降,表明降温是能见度下降的主要诱因之一。依据能见度的演变趋势,对雾进行阶段划分。将17:01—19:22定义为初生阶段,19:23—22:36为发展阶段,22:37—05:18为雾的成熟阶段,05:19之后为消散阶段。

图3 2021年4月1日17:00至2日06:00翔安站逐分钟能见度(V)、温度(T)、露点温度(Td)和10分钟平均风(风羽)Fig.3 One-min observed visibility (V), temperature (T), dew point temperature (Td), 10 min average wind (barb) at Xiang’an Station from 17:00 BT 1 to 06:00 BT 2 April 2021
3 雾的环流形势分析
1日20时,副热带高压主体位于海上,华南地区500 hPa以偏西—西南气流控制为主(图4a)。700 hPa 至地面均为西南气流以及弱的反气旋环流控制,有利于水汽输送和层结的稳定。850 hPa闽南沿海风速为12 m·s-1,达到低空急流的标准(图4b)。925 hPa从南海中北部至闽南地区存在一支显著气流,其中心风速约为8 m·s-1(图4c)。近地面西南地区存在弱的低压倒槽(图4d),闽南处于均压场控制,气压梯度小,无锋面影响。海峡内为一致的西南气流控制,风速约为2~4 m·s-1。环流形势分析表明此次大雾过程受单一暖湿气流影响,无锋面系统参与,且夜间气温下降幅度很小。结合最低能见度的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证明此次大雾为平流海雾过程。

图4 2021年4月1日20:00(a)500 hPa,(b)850 hPa,(c)925 hPa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dagpm)和风场(风矢),(d)海平面气压场(等值线,单位:hPa)和地面风场(风矢)Fig.4 Geopotential height (contour, unit: dagpm) and wind field (wind vector) at (a) 500 hPa, (b) 850 hPa, (c) 925 hPa, (d) surface wind field (wind vector) and mean sea level pressure (contour, unit: hPa) at 20:00 BT 1 April 2021
借助厦门站(与翔安站直线距离约为26 km)2000 m以下秒级探空数据(图5)分析垂直层结特征。1日20:00(图5a)低层相对湿度较大,400 m以下相对湿度大于90%,且2000 m以下均为一致的西南气流,水汽条件较好。高湿区之上400~500 m高度层存在一定的逆温层。对流抑制能量(CIN)较大,达到198.7 J·kg-1;自由对流高度高,达到了700 hPa附近(图略),表明低层存在明显的抑制层,层结稳定,逆温层之下高湿区的水汽不易向上扩散。2日08:00(图5b)探空可见湿层变薄,仅250 m以下存在浅薄的湿层,在此以上湿度快速减小,因此天空云量少。受辐射和风向转变的影响,雾退回海上,陆上能见度快速上升。

图5 2021年4月(a)1日20:00,(b)2日08:00厦门站2000 m以下温度、湿度和风廓线Fig.5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wind profiles at Xiamen Station below 2000 m height at (a) 20:00 BT 1 and (b) 08:00 BT 2 April 2021
4 海雾多源观测资料分析
4.1 雾的卫星反演特征
由于夜间低层云雾在长波红外和短波红外通道发射率存在差别,造成其亮温存在一定的差异(张春桂等,2009)。基于葵花8号高分辨率卫星的长波与短波红外亮温差异分析海上雾的发展过程(图6)。为避免可见光对短波红外的干扰,从20:00开始分析。可以看到1日20:00(图6a),闽南沿海卫星双通道存在亮温差异,温差约为1~3 K,且此区域内长波红外亮温值较高,位于289~291 K,表明云顶高度相对较低且梯度小,纹理相对均匀并覆盖至沿海地区,证明此时闽南沿海存在一条带状分布的海雾(或低云)带,其宽度约为30 km。23:00(图6b)海雾快速发展,范围快速扩大,存在爆发性发展的特征,与此同时陆地上翔安站的能见度也持续下降,进入成熟阶段,这与翔安站能见度观测趋势一致。2日02:00—04:00(图6c,6e),海雾带维持并有所扩大,同时进一步向陆地和海峡内扩展。06:00(图6f)海雾带相比于04:00范围有所减小,但仍旧覆盖海峡南部海区以及翔安地区,同时云顶亮温略有所上升,但此时翔安站观测的能见度已经上升。猜测此时大范围的云雾仍旧存在,但由于近地层风向转为偏西风(陆风,图3)的缘故,原本覆盖近地层的雾转变为不接地的低云,此过程将在下文由激光气溶胶雷达资料进一步佐证分析。这也是使用卫星监测海雾的难点之一,即无法明确区分低云和雾。

图6 2021年4月1日20:00至2日06:00葵花8号卫星长波红外通道(10.5~12.5 μm)平均与短红外通道(3.7~4.0 μm)亮温差异分布Fig.6 TBB difference between average long wave (10.5-12.5 μm) and short wave (3.7-4.0 μm) infrared channel of Himawari-8 satellite from 20:00 BT 1 to 06:00 BT 2 April 2021
4.2 雾的边界层特征
基于风廓线雷达、微波辐射计分析海雾生消过程中的边界层特征(图7)。从图中可见,1—2日翔安沿海大气1500 m以下水平风场基本以一致的偏西南风为主,与探空风向基本一致。90%以上的高相对湿度层基本维持在1000 m高度以下,尤其是近地面的相对湿度基本维持在95%以上,湿度条件较好。分时段来看,1日12:00之前1000 m以下风速较小。受太阳辐射的影响,低层高湿度层厚度从500 m 以上逐渐下降到300 m以内,湿层变薄。14:00 低层风速逐渐增强至12 m·s-1,叠加上整层一致的偏南气流,水汽输送效应明显,使得近地面的高相对湿度层也明显增厚。17:00近地面90%以上的相对湿度层厚度增加。与此同时,低层风速也逐渐减小,从6~8 m·s-1逐渐减弱至2~4 m·s-1,弱风速层厚度快速增厚,天气形势更加静稳,翔安站能见度也同步下降。18:00以后500 m以下风速整体快速减小,2日凌晨个别时次还出现近地面整层的静小风,同期近地面95%以上的相对湿度层厚度维持在200 m以内。

注:粉红实线:90%相对湿度线。图7 2021年4月1日09:00至2日08:00翔安站风廓线雷达水平风场(风矢,黑点表示水平风速≤4 m·s-1)和微波辐射计相对湿度(填色)时序图Fig.7 Time series of horizontal wind field measured by wind profiler (wind vector, black dots correspond to wind speed ≤4 m·s-1) and relative humidity measured by microwave radiometer (colored) at Xiang’an Station from 09:00 BT 1 to 08:00 BT 2 April 2021
基于激光气溶胶雷达的后向散射系数、消光系数和退偏比参数分析雾的垂直演变特征(图8)。主要分析图8a~8c中信噪比高于100(黑线)以下区域。其中退偏比为激光雷达同时探测后向散射光中垂直分量与平行分量回波信号比值,其数值反映了大气气溶胶粒子和云粒子的非球形特征,数值越接近零表示越接近于球形(刘东,2005)。由图可见1日10:00—18:00,近地面400 m高度内的后向散射系数(图8a)与消光系数(图8c)廓线随时间变化呈明显的带状高值区且高度逐渐降低。从图8b也可看到同期相应高度的退偏比小值区呈一致的趋势变化。此时段内风廓线雷达测得垂直方向上大气主要为微弱的下沉运动,下沉速度介于-0.1~0 m·s-1(图8d)。判断此时间段内低空的云层在正午后开始逐渐向地面发展,云底逐渐降低,接地的时间与地面能见度快速下降的时间完全一致,低云发展为雾。1日18:00—22:00,近地层的后向散射与消光系数廓线高值区呈现波动特征,此阶段近地面的能见度也呈现波动特征,结合退偏比廓线,推测雾顶降低至100 m之下或有零星的低云飘过;1日22:00至2日03:00,后向散射系数与消光系数廓线在近地面约100 m范围相应一致出现高值区域和退偏比的低值区,厚度持续稳定。100 m以上退偏比有所增大,数值在0.3~0.4,推测该时间段内100 m以下为雾区(球形粒子),雾顶覆有颗粒物层(不规则形状)。这证明成熟阶段的海雾雾顶高度仅为100 m左右。2日05:00之后,后向散射系数和消光系数大值区有所抬升,高度介于200~400 m。此时段地面能见度快速逐渐抬升。可推测该时间段内近地面100 m以下的雾开始消散,在200~400 m高度出现明显的云层。表明2日05:00以后雾不再接地,而是转变为低云。

注:激光气溶胶雷达起始高度为75 m;图8a~8c中黑线为信噪比质量控制线,黑线以下区域信噪比高于100。图8 2021年4月1日09:00至2日09:00翔安站(a~c)气溶胶激光雷达(a)后向散射系数,(b)退偏比,(c)消光系数,(d)风廓线雷达垂直速度廓线Fig.8 Time series of (a) backscattering coefficient, (b) depolarization ratio, (c) extinction coefficient measured by aerosol lidar, and (d) vertical velocity of wind profiler at Xiang’an Station from 09:00 BT 1 to 09:00 BT 2 April 2021
4.3 气海温差
合适的气海温差是平流海雾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林卫华等,2008)。分析海温和气海温差在海雾生消过程中的演变特征。从海温分布来看,闽南沿海存在一条明显的冷水带(图9等值线)。台湾海峡南部近海海域的海温达到22℃以上,至北部近海海温下降至17℃附近,温差超过5℃,存在明显的温度梯度。海上的偏南气流将南方的暖湿空气向北输送至较冷的近海区域后,暖湿气流被冷却。并且,由于海上偏南风力较大,至陆地上风力逐渐减小,夜间陆上低于2 m·s-1。因此从沿海至陆地存在明显的风速辐合,有利于水汽在海岸带堆积,在静稳的环流形势下易形成平流雾。从气海温差的分布来看,台湾海峡西侧基本为正值,气温均大于海温,海洋为冷的下垫面,至海峡东侧逐渐转为负值,海洋为暖的下垫面。卫星反演海雾区域(图6)均位于气海温差大于零的区域,也进一步证明平流冷却是台湾海峡内海雾形成的重要机制。分时段来看,1日17:00闽南近海的气海温差介于1~3℃;入夜后由于长波辐射冷却作用,气温逐渐下降,气海温差逐渐减小;23:00(海雾发展阶段)闽南近近海的气海温差介于0.5~2℃;至2日清晨气海温差逐渐减小,海表面的冷却作用减弱,加上翔安站转为偏西风,使得海雾逐渐退回到海上,陆地区域转变为低云。

图9 2021年4月(a)1日17:00和(b)1日23:00,(c)2日06:00海温(等值线,单位:℃)、气海温差(填色)和风场(风矢)Fig.9 SST (contour, unit: ℃) and difference in air an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colored) and wind (wind vector) at (a) 17:00 BT 1, (b) 23:00 BT 1 and (c) 06:00 BT 2 April 2021
以上多源资料分析表明,在海雾发生发展过程中,闽南沿海地区低云和雾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过程。整层一致的偏南气流和近海冷水带提供了良好的水汽和降温条件,使得海峡西岸的低云带持续维持。白天由于近地层气温较高,以低云为主。傍晚起云顶辐射冷却作用导致云体上层较冷的空气下沉,同时近地层气温逐渐下降,低层水汽凝结使得沿海地区的低云逐渐降低并发展为雾。清晨当地面转为偏西风时,沿岸的雾再次转变为低云。
4.4 雾的微物理参数演变特征
基于FM-120型雾滴谱仪测得的雾滴谱数据,分析海雾在不同阶段的粒子数浓度、液态水含量、平均直径等微物理参数演变特征(图10,表2),由于能见度为逐分钟资料,因此各微物理参数也均处理成逐分钟平均。

表2 雾不同阶段各微物理参数特征Table 2 Distribution of micro-physical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phases of fog event

注:黑色虚线为各阶段的分界线。图10 2021年4月1日17:00至2日06:00(a)能见度,(b)数浓度(灰线)、液态水含量(黑线),(c)中值体积直径(黑线)、平均直径(灰线)随时间的变化Fig.10 Temporal varation of (a) visibility, (b) particle number concentration (grey line) and liquid water content (black line), and (c) median volume diameter (black line), mean diameter (grey line) from 17:00 BT 1 to 07:00 BT 2 April 2021
阶段1(初始阶段,1日17:01—19:22)的能见度基本呈现波动变化特征。粒子数浓度的平均值为6.0 个·cm-3,1分钟平均最大值为11.5 个·cm-3;液态水含量量级约为10-2~10-3g·m-3,其平均值为0.0092 g·m-3,最大值为0.025 g·m-3;中值体积直径介于15.1~25.9 μm;平均直径介于7.5~13.6 μm且始终小于中值体积直径。当能见度下降时,各物理量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大,其中液态水含量和粒子数浓度增大幅度较为一致,中值体积直径增幅略大于平均直径增幅。
阶段2(1日19:23—22:36)为快速发展阶段,能见度由2000 m以上快速下降至400 m附近。粒子数浓度和液态水含量随之快速增大。此阶段平均能见度为357 m,平均粒子数浓度和液态水含量相比于第一阶段均明显增大,其中粒子数浓度平均值增大至43.8 个·cm-3,最大值达到85.1 个·cm-3;平均液态水含量为0.0341 g·m-3,最大达到0.0658 g·m-3;中值体积直径相比于阶段1也有所增大,最大达到29.1 μm,增幅相比于粒子数浓度等较小;平均直径相比于阶段1反而减小,这是由于此阶段小粒子数量增大幅度更大,导致平均直径减小。
阶段3(1日22:37—05:18)为雾最强时段,平均能见度为179 m。与之相对应的平均粒子数浓度和液态水含量也进一步增大。平均粒子数浓度进一步增大至61.7 个·cm-3,最大达到132.6 个·cm-3;平均液态水含量达到0.1165 g·m-3,最大值达到0.7321 g·m-3,均出现在2日04:00前后,这与能见度的最低值对应;能见度达到最低值时,平均直径也明显增大,最大达到了18.8 μm,表明此时大粒子数量明显增多,导致平均直径明显增大。分析此阶段各微物理参数特征可知,虽然能见度变化幅度减小,但微物理参数的标准差相较于前两个阶段却明显增大。这是由于海雾以平流雾为主,空间分布的不均匀特征较之内陆辐射雾或混合雾更明显,导致粒子数浓度等参数变化幅度更大。
阶段4为雾消散阶段。随着能见度的快速上升,除平均直径以外的各微物理参数均快速下降。
从整个过程的平均来看,雾的平均粒子数浓度为52.4 个·cm-3,平均液态水含量为0.084 g·m-3。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表3),闽南沿海粒子数浓度与广东湛江(Zhao et al, 2013)基本持平,略低于黄海区域的山东青岛(Wang et al, 2020)。虽有沿海地区各有差异,但整体数浓度介于40~70 个·cm-3,量级变化不大。过程平均液态水含量均在0.1 g·m-3以下,但闽南沿海相比于上述两个地区较大,这是由于闽南沿海海雾中存在更多的大粒子,平均直径更大,因此同等浓度情况下液态水含量更高。与南京(刘端阳等,2009)、重庆(李子华和吴君,1995)等城市区域相比,闽南沿海的粒子数浓度明显偏小、液态水含量更高,这是由于沿海地区水汽更加充沛,且受气溶胶颗粒物影响小。

表3 闽南沿海雾微物理特征量及与其他地区对比Table 3 Micro-physical parameters of fog in Xiang’an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areas
从不同阶段各区间的粒子数浓度分布特征来看(图11a),阶段4(消散阶段)整体数浓度最低,往上依次为阶段1(初生阶段)、阶段2(发展阶段)以及阶段3(成熟阶段)。从雾滴谱分布特征来看,阶段4呈现单峰分布特征,阶段1和阶段2的双峰结构逐渐显现。阶段3则是呈现典型的双峰特征,主峰值为4~5 μm,次峰值位于24~26 μm。这表明不同浓度雾的滴谱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雾强度越强,双峰分布特征就越明显。但不论何种阶段,10 μm以下小粒子的数量占比均超过75%,表明雾滴的数浓度主要受小粒子影响。从不同阶段的粒子数浓度对比来看,阶段1所有区间的平均粒子数浓度量级均在100以下,峰值直径为5~6 μm,对应的数浓度为0.89 个·cm-3。阶段2各区间的粒子数浓度快速增大,峰值直径为4~5 μm,达到10.50 个·cm-3,相比于阶段1的峰值直径浓度增大约11倍。20 μm以上大粒子的数浓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大,增大幅度整体介于3~9倍。阶段3(成熟阶段)粒子数浓度在各区间均为最大,且呈现出双峰分布特征。主峰值直径位于第三档(4~5 μm),其平均数浓度达到14.06 个·cm-3,次峰值位于24~26 μm,峰值粒子数浓度约为1.1 个·cm-3。10 μm直径以内的粒子数浓度合计达到44.5 个·cm-3,占比达到81.5%。30 μm以上粒子数浓度快速减小,浓度均在0.5 个·cm-3以下。阶段4除前三个区间以外,其余所有区间粒子数浓度都在0.1 个·cm-3以下,表明消散阶段粒子数浓度的量级会迅速减小。

图11 阶段1~阶段4(a)平均雾滴数浓度和(b)液态水含量尺度分布Fig.11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a) number concentration and (b) liquid water content in Phase one to Phase four
从不同阶段各区间的液态水含量分布特征来看(图11b),阶段1为单峰分布特征,峰值位于24~26 μm,液态水含量为0.58 mg·m-3。各区间的液态水含量均在1 mg·m-3以下。阶段2各区间液态水含量均快速增大,并且呈现双峰特征。主峰位于24~26 μm,其数值为1.96 mg·m-3,相比于阶段1峰值增大约2倍;次峰值位于5~6 μm,为1.06 mg·m-3。阶段3与阶段2分布特征基本类似,同样为双峰分布,且数值进一步增大。主峰值同样为24~26 μm,其数值达到9.37 mg·m-3,是阶段2的4.8倍;次峰值(1.16 mg·m-3)也同样为5~6 μm,增大幅度明显小于主峰;此阶段20~30 μm直径的粒子对液态水含量的贡献率达到53.2%。阶段4各区间液态水含量快速减小,其量级基本在10-1mg·m-3以下。
深入对比阶段2和阶段3粒子数浓度和液态水含量的差异。两者均呈现双峰分布特征,但峰值分布相反。液态水含量的主峰位于大粒子端,而数浓度则位于小粒子端,这主要是由于液态水含量与粒子直径的3次方成正比,同时也表明雾中粒子数浓度主要受小粒子浓度影响,而液态水含量主要受20~30 μm直径粒子影响为主。阶段3的粒子数浓度在所有区间内均在阶段2之上,但小粒子端数浓度差别相对较小。主峰4~5 μm的数浓度分别为10.5 个·cm-3和14.06 个·cm-3,两者相差不到50%。但随着粒子直径的增大,数浓度差异逐渐增大,在25 μm附近差异最大,阶段3对应的数值为阶段2的4.8倍。液态水含量的分布也是如此,小粒子端增大幅度较小,20~30 μm增大幅度更大。这表明大粒子数浓度的增大对于雾强度的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加强为强浓雾具有重要作用。
5 结 论
本文利用自动站资料、ERA5再分析资料、葵花8号高分辨率卫星资料、翔安站多源观测资料等,分析了2021年4月1日闽南沿海一次大雾过程演变特征、环流形势和垂直结构特征。基于FM-120型雾滴谱仪资料,对比分析了海雾在不同阶段的微物理参数演变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此次大雾主要发生在一致的西南气流中,200 m以下低能见度主要出现在沿海地区,为典型的海雾过程。低层至近地面均为反气旋环流控制,探空温湿廓线表明存在近地面逆温层和湿层,为海雾的发生发展提供静稳的环流形势和充沛的水汽条件。
(2)多源资料分析表明,在海雾发生发展过程中低云和雾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过程。白天以低云为主,傍晚起云顶辐射冷却作用导致云体上层较冷的空气下沉,同时近地层气温逐渐下降,低层水汽凝结使得沿海地区的低云逐渐降低并发展为雾。清晨当地面转为偏西风时,雾再次转变为低云。单纯通过卫星无法有效区分雾和低云,但可以结合气溶胶激光雷达共同判定。雾期间气溶胶激光雷达测得的近地层消光系数达到3~4 km-1,消光系数大值区的厚度与雾的强度演变趋势一致,可用于推演雾顶的高度。雾的初生和发展阶段厚度相对较低且波动性大,成熟阶段雾顶高度约为100 m。
(3)海温分析表明,台湾海峡中部至闽南近海的海温存在较大的梯度。近海的冷水带导致气温逐渐高于海温,气海温差介于0.5~2℃。雾区集中在气温大于海温的区域,海上的偏南气流将南方的暖湿空气向北输送至较冷的近海区域后,原本相对饱和的暖湿气流被冷却凝结,在静稳的环流形势下易形成平流海雾。
(4)雾滴谱分析表明,本次雾过程平均粒子数浓度为52.4 个·cm-3,液态水含量为0.084 g·m-3。平均直径为9.4 μm。不同阶段粒子数浓度、液态水含量等微物理参数差异较大。初生和消散阶段各参数较小,发展阶段快速增大,成熟阶段达到最大,1分钟平均粒子数浓度最大达到132.6 个·cm-3,平均液态水含量达到0.7321 g·m-3。雾在各阶段的粒子数浓度和液态水含量谱分布具有较大差异。其中粒子数浓度在初生、发展和消散阶段以单峰结构为主,峰值直径为4~6 μm。成熟阶段表现为双峰结构特征,主峰位于4~5 μm,次峰位于24~26 μm。液态水含量除消散阶段外,整体呈现双峰分布特征,主峰位于24~26 μm,次峰位于5~6 μm,峰值分布与粒子数浓度相反。这表明雾滴数浓度受小粒子影响为主,但液态水含量以20~30 μm 的粒子贡献最大。发展和成熟阶段谱分布对比表明,10 μm以下小粒子增加幅度小,而20~30 μm区间增大幅度较大,因此大粒子数浓度的增大对于雾强度的进一步增强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