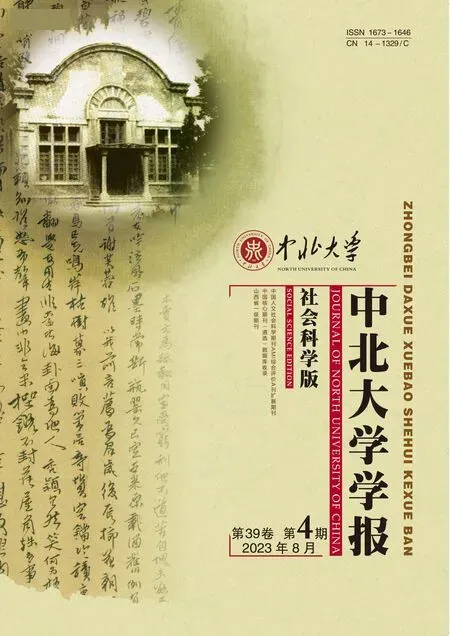论宋代以前“一产多子”现象的灾祥与成因
刘 涛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一产多子”, 顾名思义, 即妇女一次妊娠生产两个以上婴儿, 即多胞胎。 “一产多子”本应该包含双胞胎即孪生子的情况, 但是古代双胞胎的概率远远高于三胎及以上的, 而且在古代社会观念中双胞胎与三胞胎是两种性质。 因此, 本文“一产多子”的研究范畴仅针对三胞胎及以上的情况。 由于古代重男轻女思想存在, 加上某些地区还有溺死女婴的习俗, 能够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多是三胎且为男孩, 因此, 史书多称其为“一产三男”。
“一产多子”这种不受人力干预的超低概率的自然事件, 在中国古代往往会与灾祥休咎相关联, 用以预测国家兴衰等政治事件。 自《后汉书·唐檀传》第一次以官方视角记载“一产多子”起, 便带有浓厚的妖异色彩。 翻阅汉代至宋初的官修《五行志》, 我们可以发现, 官方将“一产多子”现象定义为灾异之兆远远超过祥瑞。 因此,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一产多子”是灾异之兆确为宋代以前的认知主流。 但是, “一产多子”由灾转祥的认知变化并不是单向的, 魏晋南北朝时曾被认为是祥瑞之兆并行封赏之举, 而进入大一统的唐代又以灾异视之。 汉代将“一产多子”视作灾异的依据是什么?魏晋时以“一产多子”为祥瑞而唐代却仍以灾异视之的原因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给出具体的结论。 “一产多子”自元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 但是数量并不是很多。 元末杨维桢在《三男词》中考查历史发现后世以之为祥而古代则为灾异[1]68;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2]464、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3]239-240和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4]1287-1288均有或详或略的考证。 1929年, 王成竹在《民俗周刊》第85期发表《一产三男有赏》考证赏赐“一产多子”源于勾践。[5]安徽师范大学王彦章在《清代一产三男旌表政策之流变》中讨论了清代的一产三男旌表政策的变化。[6]东北师范大学刘佳在《一产多子: 社会与医疗视野下的多胞胎诠释——以明代历史为中心》一文中重点关注宋代以后官方对于“一产多子”现象的诠释并结合中医妇科胎孕理论对此进行解释。[7]滨州学院王凤翔、 岳云艳在《休咎之征: 中国古代多胞胎生育探微》中对包括双胞胎在内的多胞胎生育现象进行探究, 指出中国古代早期推崇早育多子, 以多胞胎为“吉庆之事”, 在古代中后期, 随着多胞胎出现频率增加, 受限于难产、 怪胎、 伦理等因素, 人们以“不祥”去认知多胞胎, 并附会以灾异之兆。[8]本文以《汉书·五行志》为线索, 以历代关于“一产多子”的史书记载为基本材料, 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 从具体处考察宋代以前“一产多子”的灾祥认定原因, 以揭示政治因素对生育行为、 观念的影响。
1 “一产多子”定为灾异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代由阴阳五行衍生的灾祥休咎的观念来源于先秦, 经过战国邹衍、 西汉董仲舒等人的发展, 阴阳五行逐渐成为国家统治的政治话语。 溯其本源, 殷商、 西周时期的王和王族“藉由祖先崇拜”垄断了国家政治话语, 成为宇宙的中心, “他们的权威和统治凌驾于四方之上”。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式微, 新生的政治势力包括巫师、 方士以及上层精英等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新生的地方诸侯提供政治解读的服务, 打破了王与王族的神权垄断。 从此, 新构建的政治话语以五行系统为核心并成为当时通行的话语体系, 以此用来讨论国家事务。[9]97-99但是将五行与阴阳结合起来, 并用此解释朝代兴衰更替源于战国时的邹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 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 施及黎庶矣, 乃深观阴阳消息, 而作怪迂之变, 《终始》《大圣》之篇, 十馀万言。 其语闳大不经,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德转移, 治各有宜, 而符应若兹。[10]3038
邹衍有感于享国者无德且奢靡成性, 于是用五德相克循环的学说来解释朝代更替, 并且每一个朝代都有对应的“德”、 受命之符和颜色。
邹衍创造这套理论本身是想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以约束君主的政治权力。 “一统帝国的新君主必须要承受天命和五德始终之运才能实行统治, 而‘天命’与‘运’必须有天降祥瑞之符来证实。”[9]178汉代的陆贾、 董仲舒、 刘向父子又接续发展了这套理论。 “刘歆用五行相生循环系统地揭示了从远古至汉朝更换的原因, 可以说是对远古历史的重新构建, 这一解释成为正统之说被写进历史。”[9]182
真正总结先秦至汉代五行理论以及征验实例的是班固的《汉书·五行志》。 《汉书》虽为班固仿《史记》之作, 但其中《五行志》为《史记》所未作。 在此之后, 历代史书多沿袭《汉书》体例设置《五行志》, 命名稍有不同, 或为《灵征志》, 影响深远直至《清史稿》。 《汉书·五行志》并非班固阴阳五行思想的体现, 班固只是《五行志》的编纂者, 他在绪论中说到:
汉兴, 承秦灭学之后, 景、 武之世,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阴阳, 为儒者宗。 宣、 元之后, 刘向治《穀梁春秋》, 数其祸福, 传以《洪范》, 与仲舒错。 至向子歆治《左氏传》, 其《春秋》意亦已乖矣; 言《五行传》, 又颇不同。 是以扌监仲舒, 别向、 歆, 传载眭孟、 夏侯胜、 京房、 谷永、 李寻之徒所陈行事, 讫于王莽, 举十二世, 以传《春秋》, 著于篇。[11]1901-1902
《志》主要反映了先秦至汉代五行思想的演变与转化, 以洪范五行传解释灾异, 使洪范五行传学说在春秋公羊灾异学说、 京房易学说、 明堂月令学说等先秦、 西汉以来形成的灾异学说中成为主流。 其理论来源于《尚书·洪范》篇的九畴, 即五行、 敬用五事、 农用八政、 协用五纪、 建用皇极、 乂用三德、 明用稽疑、 念用庶徴、 乡用五福、 威用六极。 “汉代所盛行的洪范五行传学说, 不仅在五行部分改变了《洪范》篇的原始顺序; 并且在‘五事’部分更附会了原与‘庶征’无涉的‘皇极’ ‘五福’ ‘六极’等项, 进而将五行相胜的观念糅合在其中, 并增益诸多种妖、 孽、 祸、 痾、 祥等等妖异项目, 成为一个繁复的灾异禁忌体系。”[12]
虽然《汉书·五行志》并未将“一产多子”纳入这一体系进行解释, 但是, 后世史书记载“一产多子”时所持的灾异解释皆本于此。 因此, 研究“一产多子”的灾祥认定需从《汉书·五行志》中寻找理论依据。
2 中国古代早期“一产多子”的灾祥性质
中国古代对“一产多子”现象的灾祥性质认定存在很大分歧。 在官方层面, 如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 以北宋为限分为两个阶段: 北宋以前, 官方主流观点是将“一产多子”视作妖异, 偶见祥瑞之兆的记载; 北宋至清代, 朝廷多以此作为人口繁衍的吉兆, 并行封赏之举。 清代学者赵翼针对古代“一产多子”的现象详考历史上对于“一产多子”的态度, 得出“可知一产三男、 四男皆是变异, 非吉祥也”的结论。[2]464
《国语·越语上》曾记载春秋时期越国奖励生育的政策: “生三人, 公与之母; 生二人, 公与之饩。”韦昭注曰: “人生三者亦希耳。”[13]603若是按照韦昭的说法, 越国针对“一产多子”进行奖赏, 应该算是中国最早关于“一产多子”的记载。 但是, 有学者并不认为此处“生三人”指的是一胎生三子, 汪少华认为, 一方面, 如果越王只是对双胞胎、 三胞胎进行奖励, 根据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 这样的生育奖励政策很难覆盖到多数人, 对于鼓励生育无甚助益; 另一方面, 后世学者可能误解了韦昭的注, “假如‘人生三者亦希耳’是指一胎生三个婴儿却用‘亦’字, 那是废话。 因为‘一产三男, 史必书之, 纪异也’”[14]。 笔者也持此观点, 因此, 不认为《国语》是中国最早关于“一产多子”的记载。
关于“一产三子”的最早记载应该是西汉应劭的《风俗通义》, 其中说到: “今俗间多有禁忌生三子者, 五月生者, 以为妨害父母, 服中子犯礼伤孝, 莫肯收举。”[15]128唐代马总《意林》引《风俗通》作: “不养并生三子: 俗说似六畜, 妨父母。”[16]398宋代《太平御览》引此亦云:“俗说生子至于三子, 似六畜, 言其妨父母, 故不举之也。”[17]1663汉代民间风俗认为, 生三胞胎、 五月以及服丧期间生产都会妨害父母。 因此, 不肯收养。 《意林》引文认为“一产多子”像“六畜”, 即父母就像家畜一样, 对父母不利。 至于当时“不举子”的现象, 王子今教授认为, 源于“秦汉时期基于神秘主义信仰的民间礼俗”[18], 而“一产多子”的妖异认定或许也基于此。
到了东汉, “一产多子”的咎征不仅仅是民间态度, 而且上升到了官方层面, 如《后汉书·唐檀传》记载了“一产多子”现象以及征验结果:
永宁元年, 南昌有妇人生四子, 祗复问檀变异之应。 檀以为京师当有兵气, 其祸发于萧墙。 至延光四年, 中黄门孙程扬兵殿省, 诛皇后兄车骑将军阎显等, 立济阴王为天子, 果如所占。[19]182
这应该是古代正史中第一次出现“一产多子”的确切记载, 但是, 《后汉书·五行志》并没有收录此事。 或许是因为《后汉书》本为范晔所撰, 但书未竟而身先死, 列传为其本人所作, 但八志包括《五行志》采自司马彪, 所以在列传中记载的“一产多子”现象并未出现在《五行志》中。 根据《唐檀传》记载可见, 汉代时, 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将“一产多子”视为不祥的妖异现象, 且由妨害父母升格到国家内乱动荡的灾异之兆, 在汉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产多子”都未被视作祥瑞。
3 中医胎孕理论与“一产多子”的灾祥关系
班固《汉书·五行志》中没有收录“一产多子”, 所以我们在其中很难找到“一产多子”与灾异之间的直接联系。 若要理清其中的关系就需要借助后世史书中的《五行志》和中国古代中医胎孕理论。 北齐魏收的《魏书》第一次在正史的《五行志》中记载了“一产多子”现象, 卷一百一十二下《灵征志》“人痾”条记曰:
高祖延兴三年秋, 秀容郡妇人一产四男, 四产十六男。[20]3174
这是“人痾”条收录“一产多子”的首例。 关于“人痾”的定义我们还得需要在《汉书·五行志》中寻找答案, 其中, 班固在两个地方给出了定义, 其一为“五事”即貌、 言、 视、 听、 思 与“五行”相对应, 也就是“五事”与“庶征”相联系, 以定吉凶征兆, 《志》曰:
凡草物之类谓之妖……及人, 谓之痾。 痾, 病貌, 言浸深也……貌之不恭, 是谓不肃。 肃, 敬也。 内曰恭, 外曰敬。 人君行己, 体貌不恭, 怠慢骄蹇, 则不能敬万事, 失在狂易, 故其咎狂也。 上嫚下暴, 则阴气胜, 故其罚常雨也……上失威仪, 则下有强臣害君上者, 故有下体生于上之痾。[11]1944-1945
人君“体貌不恭, 怠慢骄蹇” 等失德行为带来“阴气盛”的结果, 所以导致了人类所见的妖异现象, “人痾”则是妖异之中程度最深的。 《魏书·灵征志》中关于“人痾”形成的理论更明晰:
貌之不恭, 是谓不肃。 上嫚下暴, 则阴气胜, 水伤百谷, 衣食不足, 奸宄并作, 故其极恶也。 一曰, 民多被刑, 貌丑恶也。 班固以为六畜谓之祸, 言其著也; 及人, 谓之痾, 痾, 病貌, 言寝深也。[20]3173
其二为“皇极”, 其本质是上天对统治者进行监督与控制, “汉理论家们把皇极概念明确化固定化, 把皇帝——其身体行为以及其内在道德——固定为皇极的焦点, 视其为人类和宇宙秩序或失序负责的主体”[9]192-193, 《志》曰:
皇, 君也。 极, 中; 建, 立也。 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 不得其中, 则不能立万事, 失在眊悖, 故其咎眊也。 ……君乱且弱, 人之所叛, 天之所去, 不有明王之诛, 则有篡弑之祸, 故有下人伐上之痾。[11]2065
《魏书》将“一产多子”归入第一种“人痾”, 《新唐书》则归为第二种, 史家并没有深入解释其中的逻辑, 而中医特有的阴阳五行理论为“一产多子”与“人痾”之间搭建了逻辑桥梁。
古代中医理论与灾祥征验理论都根植于阴阳五行之上。 据许筱颖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中讲, 五行学说将人体的五脏分别配属五行, 并以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 同时, 中医运用阴阳学说来阐释人体的生理功能、 疾病的发生原因和病理变化, 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灵柩·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 有名而无形。”[21]14-34可以发现的最早系统地用医理解释“一产多子”现象的是南朝齐的褚澄, 他在《褚氏遗书》中提出了“胼胎(双胞胎)”和“品胎(三胞胎)”的概念:
男女之合, 二情交畅, 阴血先至, 阳精后冲, 血开裹精, 精入为骨, 而男形成矣; 阳精先入, 阴血后参, 精开裹血, 血入居本, 而女形成矣。 ……阴阳均至, 非男非女之身; 精血散分, 胼胎、 品胎之兆。[22]1
褚澄从男女阴阳的角度论证了胎儿性别的成因, 同时, 提出男女精血散分是形成双胞胎、 三胞胎的原因。 《易》曰: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23]473这也是后世中医分辨胎儿性别的理论来源, 褚澄之后元代的朱震亨从精血主导胎儿性别延及子宫和性别的联系:
阴阳交媾, 胎孕乃凝, 所藏之处, 名曰子宫, 一系在下, 上有两歧, 一达于左, 一达于右。 精胜其血, 则阳为之主, 受气于左子宫而男形成; 精不胜血, 则阴为之主, 受气于右子宫而女形成。[24]9
无论是褚澄还是朱震亨, 古代中医都认为父母阴阳精血对于胎儿形成与性别有莫大影响, 而妇女受孕并产子一事也反映了阴阳动态变化的过程。 胚胎的形成过程中需要父母的精血, 其中, 父为阳, 母为阴; 精为阳, 血为阴。 《春秋繁露·基义》曰: “君为阳, 臣为阴; 父为阳, 子为阴; 夫为阳, 妻为阴。”[25]342阴阳失衡就是政治生态的乱象。 《新唐书·五行志》在“一产多子”现象后又说“凡物反常则为妖, 亦阴气盛则母道壮也。”[26]954史家认为“一产多子”现象的出现说明胎儿母亲代表的阴气过于强势, 压制了阳气。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说:“《汉书·五行志》以一产三男列于人痾, 其说以为母气盛也, 故谓之咎征。”[27]1472虽然今本《汉书·五行志》并未发现“一产三男”的记载, 但是可以看到, 在灾异征验逻辑中“母气盛”是导致“一产多子”的直接原因, 而中医胎孕理论是补足这一逻辑链条的重要一环。
4 “一产多子”由灾入祥的畸变
直到魏晋、 隋唐, “一产多子”仍被视作为妖异, 但稍早于《魏书》的《晋书》于《载记》中记载了后赵石勒将“一产多子”当作祥瑞并封赏的史事:
黎阳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 武携其妻子诣襄国上书自陈。 勒下书以为二仪谐畅, 和气所致, 赐其乳婢一口, 谷一百石, 杂彩四十匹。 ……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 赐其衣帛廪食, 乳婢一口, 复三岁勿事。[28]2737-2747
《晋书斠注》曰: “《御览》三百六十一引《后赵书》作‘勒赐乳母、 谷、 帛, 以为休祥’。”[29]1728此处史书明确将“一产多子”记作祥瑞, 似乎斩断了自汉代至唐宋之间“一产多子”由灾至祥的发展脉络, 变得极为突兀。
东晋太兴二年(319年), 前赵刘耀太宰、 大将军石勒自称赵王, 于是大赦天下, 改元赵王元年, 史称“后赵”。 之后, 石勒攻城略地, 据有北方大半, 对前赵政权颇有取而代之之意。 当年北方天降大雨, 中山、 常山(今属河北省)一带尤其严重, 滹沲河(今滹沱河)泛滥, 大水冲毁山林, 大量木材沿滹沲河顺流而下, 造成华北平原之上木材堆积如山。 次年, 石勒“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27]2737, 定都襄国, 下令以去年大水冲出大量木材为上天所降祥瑞, 是上天想让他修建宫殿。 于是, 石勒下诏仿洛阳太极殿营造建德殿。 恰在此时, 黎阳人陈武之妻一产三男一女, 陈武带着妻子赶到襄国觐见并将此事上陈石勒。 此时作为新都的襄国初定, 并且需要祥瑞来为大兴土木提供合理性, 石勒将此次“一产多子”事件认定为“二仪谐畅, 和气所致”, 并赏赐给陈武“乳婢一口, 谷一百石, 杂采四十匹”[28]2737。
在儒家天命观中, 灾异与祥瑞均是上天意志的体现, “上天之意志绝对不是毫无章法可循, 天地万物与上天互相感应, 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都会被上天所感应, 而上天通过灾异祥瑞来表明对人类活动的态度”[30]。 灾异现象意味着统治者违逆天意, 且会带来宇宙失序; 而祥瑞则昭示上天对皇帝政权合法性以及统治行为的认可。 《吕氏春秋·应同篇》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 天必先见祥乎下民。”[31]251汉代董仲舒说祥瑞之符乃是“受命之符”[11]4024。 这套理论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并以此获得了下层阶级对政权的认可, 实现了社会凝聚力的构建。 “符瑞不再是不同性质的皇权交替的象征, 而是唯一且永恒的皇权体现, 那就是天命之所在, 呈现天之意志的皇权。”[9]178所以, 皇帝在政权中必须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也就是上天对于自己统治的认可。 董仲舒还谈到: “天令之谓命, 命非圣人不行……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 以顺命也。”[11]4043-4044天命与皇权的互动构建了“天人感应”的主体, 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 魏晋时期, 地方割据政权纷纷称帝称王, 传统的大一统局面被打破, 新生政权的统治者亟需祥瑞之符证明合法性。
在陈武妻子一产三男一女的祥瑞出现后, 后赵境内祥瑞频现。 负责营造建德殿的校尉王和挖到了一块墓碑, 上面刻有铭文: “律权石, 重四钧, 同律度量衡, 有新氏造。”众人反应不同“议者未详, 或以为瑞”。 之后茌平令师欢捕获一只黑兔, 将其献给石勒, 程遐等人说: “龙飞革命之祥, 于晋以水承金, 兔阴精之兽, 玄为水色, 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28]2743
祥瑞未必可靠, 一方面, 有臣子虚报祥瑞以求仕进之嫌; 另一方面, 也满足了石勒以祥瑞之符自证统治权威之需。 此事之后, 石勒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太初。 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八月, 石勒改称赵天王, 行皇帝事; 九月, 称皇帝, 再次大赦天下, 改元建平, 将都城由襄国迁往临漳。 称帝后, 再次出现“一产多子”现象: 堂阳人陈猪一产三男, 石勒照例赏赐。 之后, 高句丽、 凉州牧、 晋荆州牧等接连向石勒进献名品方物、 珍宝奇兽, 而且后赵境内还出现了“济阴木连理, 甘露降苑乡”的祥瑞之兆。 于是, 石勒“以休瑞并臻, 遐方慕义”并“赦三岁刑已下, 均百姓去年逋调”以及赏赐官员。[28]2747
石勒将“一产多子”定性为祥瑞并不意味着此现象正式由妖异转变为祥瑞, 此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勒改元建国需要祥瑞的加持, 服务现实政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期, 地方政权割据混战, 百姓民不聊生, 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 地方遭遇一次战争便人口锐减。 因此, “一产多子”现象很难大量出现, 也就没有出现灾祥的最终定性。 长江以南的东晋仍然将“一产多子”视作灾异, 如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中记载: “吴赤乌七年, 有妇人, 一生三子。”[32]108根据此条前后所举事例, 干宝将“一产多子”仍视作“人痾”。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将“一产多子”现象看作祥瑞之符属于个案, 不能打破自汉以来的灾异性质, 直到唐代才有了新变化。 柳宗元《为广南郑相公奏百姓产三男状》记载了上书皇帝赏赐“一产三男”:
右, 臣所部贞节坊百姓某妻产三男者。 臣详究往例, 实谓休徵, 已量事给绢三十疋, 充其乳养者。
伏以陛下勤恤黎元, 感通天地, 灵心昭答, 景福已兴。 方使亿兆繁滋, 区夏充牣, 故表祥于字育, 是启运于升平。 事杳化源, 庆延邦本, 鳞羽之瑞, 曾何足云。 臣幸列藩维, 尝叨枢近, 私贺之至。[33]2477
从章奏来看, 唐朝出现一百姓妻一产三男, 柳宗元“详究往例”认为此事为休祥之兆, 昭示皇帝的统治上应天命, 繁殖人口, 国祚绵长, 应当赏赐。 近代学者岑仲勉在《唐集质疑·柳柳州外集》中疑此文非柳宗元所作, 证据有二: 一题目不合, 唐代应称“岭南”, 宋代始称“广南”, 郑相公若为唐代郑絪, 官职应为岭南节度观察使广州刺史; 二于情理不通, 岑仲勉认为:“此等琐节, 与谢上表异, 于其人之进退、 休戚无关, 且永不隶岭南……余则谓题目苟不误者, 断非柳文。”[34]421-422施子愉在《柳宗元年谱》中也引用了岑仲勉的结论。 笔者不从校勘、 职官等角度进行考证, 单从“一产多子”的灾祥的角度出发, 自魏晋南北朝至五代, “一产多子”仍未能摆脱妖异的色彩。(1)《新五代史·唐本纪庄宗下》记曰: (同光二年)冬十月癸未, 左熊威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子。 《唐本纪明宗》记曰:(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 陕州硖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 丁酉, 以象笏三十二赐百官之无笏者。 徐无党于“赐象笏”后注曰: 是时朝廷衰弱之甚, 故书。 《汉本纪隐帝》记曰: (乾祐元年五月)乙亥, 魏州内黄民武进妻一产三男子。 河决滑州鱼池。 旱, 蝗。
《新五代史》中记载左熊威军将赵晖之妻一产三男一事, 北宋徐无党注曰: “此亦变异, 而书者, 重人事, 故谨之。 后世以此为善祥, 故于乱世书, 以见不然。”[35]104虽然徐无党没有言此事的灾异征验, 但是, 他断然否定北宋时以此类事为休征的看法, 认为五代时“一产多子”当为变异。 由此来看, 《为广南郑相公奏百姓产三男状》一文中信誓旦旦地认定“一产多子”为祥瑞之兆, 与唐代官方对此事的态度大相径庭, 不只是与新旧两唐书的记载相左, 与唐代当时的文献也相矛盾。 唐代天文学家并在中央政府的天文机构担任太史令的瞿昙悉达在《开元占经》中征引《天镜》曰: “妇女一时生三男, 不出三年, 外国来; 生三女, 国有阴私。”[36]789作为唐代天文工作的指导用书, 《开元占经》将“一产多子”认定为灾异, 列入“人生子异形”条, 与《五行志》中“人痾”同义, 并且指出不同情况下对应的征验结果。 所以, 《为广南郑相公奏百姓产三男状》一文很难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为柳宗元所作, 且唐代以“一产多子”现象为灾异当属主流。
唐代以后, “一产多子”的灾祥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灾异的成分逐渐弱化, 或者说更多的是强调“一产多子”的异而不是灾。 《新五代史》中左熊威军将赵晖之妻的记载恰好佐证这一点, 史书记载此事除徐无党所说的原因外, 还有另一方面。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古之国史, 闻异则书, 未必皆审其休咎, 详其美恶也。”[37]66所以, 《新五代史》中出现“一产多子”的记载也许单纯因为异而非其他。 除了灾的意味下降, “一产多子”出现了祥瑞的成分。 明末朱国桢《涌幢小品》中记载有南唐时“一产多子”之事:
南唐时, 金陵人康国辅娶司马氏, 一产三男, 唐主以为人瑞, 皆封将军, 其后蕃衍, 号千秋康氏。[38]433
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的“千秋康氏”条也记载了此事[39]71,但是记载简略。 正史中并未曾出现此事记载, 但据南宋文天祥为康氏后人所作《瑞山康氏族谱序》可知此事当属真实。(2)文天祥《瑞山康氏族谱序》记曰: (康氏)数传至国辅,南唐时娶司马氏, 一产三男, 以为人瑞, 皆封将军。[40]101由此可知, 五代时“一产多子”现象同时存在祥与异的认定, 也代表了“一产多子”由“人痾”到“人瑞”的转变。
宋代结束了五代乱世, 迎来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生产力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 加上宋代陈自明《妇女良方大全》、 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等中医胎孕理论实践的进步, 妇女妊娠生子有了更好的保障。 因此, “一产多子”的出现较前代更为频繁。 《宋史·五行志》专门记载:
自天圣迄治平, 妇人生四男者二, 生三男者四十四, 生二男一女者一。 熙宁元年距元丰七年, 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 而四男者一, 三男一女者一。 元丰八年至元符二年, 生三男者十八, 而四男者二, 三男一女者一。 元符三年至靖康, 生三男者十九, 而四男者一。 前志以为人民蕃息之验。[41]924
宋代统治阶级将大量出现的“一产多子”现象普遍视作祥瑞, 此时更多强调“一产多子”带来的人口繁衍的盛世景象, 与皇帝有关的灾异征验就弱化了许多, 因为在古代农耕社会, 大量的人口就是意味着生产力。 与南宋对峙的金国政府与宋秉持相似的态度:
礼官言: “民或一产三男, 内有才行可用者可令察举, 量材叙用。 其驱婢所生, 旧制官给钱百贯, 以资乳哺, 尚书省请更给钱四十贯, 赎以为良。”制可。[42]234
《金史》记载金国礼官向皇帝建议民众一产三男中有才能出众的可举官, 仆俾生产的可以增加赏赐钱财以赎良。 以至后世, “一产多子”逐渐摆脱灾祥征验色彩, 更强调本身所带来的人口数量的增长, 政府也不断给予赏赐, 直到清康熙二年(1663年)成为定制:
康熙二年定: 凡一产三男, 或男女并产, 八旗由礼部具题, 直省由各该督抚具题, 礼部题覆。 行户部准给米五石、 布十疋。十三年定: 一产三男, 仍准题覆, 其男女并产, 及一产三女者, 不准题覆。二十三年谕: 一产三男事, 令礼部成议, 即交户部具奏, 照例赏给。[43]2645-2646
至此,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产多子”问题有了官方的最终定论, 有清一代, 无论是官方文书还是民间文人笔记, 将“一产多子”视作“人瑞”成为绝对主流。
5 结 语
受儒家天人感应、 阴阳五行、 灾异祥瑞等天命观影响, 古代社会中“一产多子”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生育行为, 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自汉代开始, 社会的主流认知将“一产多子”视作灾异, 而宋代后的社会逐渐将其纳入祥瑞范畴。 在梳理历代史书的记载后, 发现“一产多子”由灾入祥的演变并不是单向的, 而是存在畸变, 其原因与权力斗争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