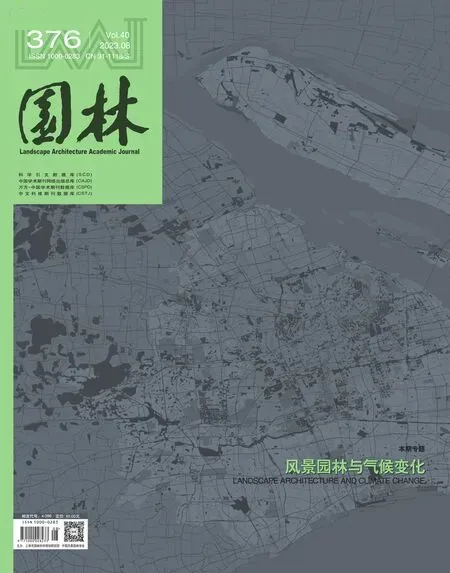基于景观指数分析的福建漳州珪后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研究
朱志琴 郭青海,2* 李达维
(1.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18;2.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院,杭州 310018;3.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乡村文化空间作为传统人居智慧与场所精神的体现,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加强乡村文化空间建设,提升乡村文化服务功能,与自然生态相结合开展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以进一步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珪后村文化空间景观为研究对象,运用GIS和Fragstats等空间分析软件,选取体现乡村文化景观发展特征的景观指数,对乡村物质文化景观空间的形态和结构进行量化分析。结合景观生态学的“斑块—廊道—基质”理论,探讨乡村振兴中生态振兴对文化振兴的触发作用,提出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以期为乡村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寻找实现路径,为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和案例支持。
乡村景观;文化景观;景观格局;可持续设计;景观生态学
乡村景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村民自发建设的状态,规划、建设和使用都由当地居民依据风俗和生活习惯等自主安排,存在着无序性、凌乱性等特征[1]。在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下,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在各地紧密实施,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模仿城市建设、总体布局单一等问题,使乡村生态景观格局遭到破坏[2]。如何平衡乡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突出乡村文化特色,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乡村中的文化空间作为传统人居智慧与场所精神的体现,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是乡村振兴工作的内核。文化景观研究方面,汤茂林[3]提出文化景观是指人类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自然材料变成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景观。乡村文化景观是人类缔造文化景观的关键类型之一,体现了乡村社会及族群日积月累的生活智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是农业文明的结晶[4]。乡村在长久发展历程中积累的独特文化和场所精神是乡村人情美的体现,而外部的环境空间以及各类建筑则作为载体,对于传达这些历史文化和场所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乡村文化景观建设中,文化景观格局的修补主要以物质空间构成要素及分布的解译为依托,借助场所理论、空间句法、图底理论等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解释文化景观的空间现状特征和问题[5-6]。这些方法着重于物质空间层面的外形解析,无法深入了解乡村文化景观空间内生发展的模式与趋势,难以从根本上推动乡村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传统的乡村景观设计方法多从感官角度出发,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难以从区域层面上掌握景观空间肌理特征,弱化了乡村文化景观在“斑块—廊道—基质”上的整体协同。在乡村建设中,以乡村生态保护为基础的生态景观设计,一方面能够维持和提升乡村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对生态景观多功能的需求[7]。乡村生态建设正从单纯的环境治理发展到生态品质的提升,乡村文化景观不仅具有生态系统功能,更是乡村精神文化的载体。乡村文化景观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触发将提升乡村景观的可持续性。由于乡村景观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需要逐步进行提升改造,减少盲目建设的风险。乡村景观规划是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其中景观生态过程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乡村文化景观的建设尤其注重景观生态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景观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以提高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8]。随着GIS空间分析、遥感技术等方法的不断发展,乡村文化景观的定量分析逐步深入和丰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乡村生态基底情况[9]。如何突破传统空间及景观设计方法的局限,探索乡村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的实现路径,优化乡村文化景观格局,是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考。
文章以福建省漳州市珪后村文化空间景观资源为研究对象,选取多个景观生态学中的景观指数进行量化研究,利用GIS和Fragstats等分析软件,分析珪后村乡村文化景观空间的形态和结构。基于指数计算的结果,探讨生态振兴对文化振兴的触发作用,提出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为乡村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寻找实现路径,为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依据和案例支持。
1 研究区域概况
珪后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岩溪镇的中心位置,村庄地形走势低缓,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农业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占全村面积的75.29%。珪后村历史文化景观主要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宗祠建筑和民居建筑(图1)。村庄聚落中追远堂、棣芬堂、叶文龙故居、普济岩、赠公祠、升厝、楼仔厝、聚星堂这8处建筑被列入福建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然而保护措施效果不明显,村落历史建筑资源搁置,未能有效形成旅游路线和引导游客行为,也影响了游客的体验感。周边建筑风貌差异明显,公共空间以硬质铺装为主,绿地较少,且空间破碎化严重(图2)。

图1 珪后村区位示意与平面图Fig.1 Location diagram and plan of Guihou Village

图2 珪后村文化景观分布图Fig.2 Cultural landscape distribution map of Guihou Village
2 研究方法
2.1 景观指数
景观格局的分析是景观生态学中阐释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生态效应的重要方法[10],景观指数是体现景观结构及过程的量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景观空间的组成及配置,是景观格局信息的浓缩[11]。景观指数主要通过斑块水平、类型水平及景观水平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其测算依托GIS和Fragstats软件,通过GIS将景观空间的信息实现由栅格到矢量的处理,提取需要的空间信息,再利用Fragstats对空间信息进行统计计算,得到对应的景观指数,用以体现景观空间的形态、结构,反映景观格局的特征[12-13]。
本文从聚落层面和景观斑块层面选取反映乡村文化景观特征的景观指数,包括斑块密度、蔓延度指数、连通度指数、最大斑块指数、斑块类型面积、斑块面积百分比和散布与并列指数等(表1)。蔓延度指数和连通度指数能体现景观的连通性,指数越大,景观的连通性越高。散布与并列指数表征景观格局的空间分布排列特征,数值越大,斑块分布越均匀,景观多样性越高。以此描述珪后村文化景观空间的形态、结构和异质性,解释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

表1 景观指数计算及说明Tab.1 Calcul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index
利用GIS软件的shp面数据勾绘工具对珪后村主聚落区景观类型,包括交通及通行、农田、水域、建筑、未知用地、绿地以及文化景观进行详细的分类提取。在核对之后,为各类景观类型的shp矢量数据添加类型属性字段,获取包括景观分类属性的矢量图层。利用GIS软件转换成栅格数据,导入Fragstats软件进行景观指数计算。
在此基础上,从斑块、廊道和基质三个层面剖析乡村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景观斑块层面,以乡村文化景观斑块的优势度及其特点为研究重点;景观廊道层面,主要分析乡村文化景观廊道连接度及通达性;景观基质层面,重点探讨乡村文化景观面域上的破碎化程度及空间分布格局。
2.2 景观优化路径
乡村文化景观蕴含着深厚且独特的风土人情,由村落山水空间格局、位置形态、承载文化价值的空间实体,如街巷、广场、建筑等的物质要素,以及乡村长期发展累积形成的独特民俗风情、节庆活动、集体记忆和价值认同等非物质要素组成。乡村文化景观的优化,首先需要对主体结构复杂的乡村文化景观进行梳理划分,然后构建适宜乡村发展的从景观格局分析到景观设计的景观指数化分析和优化路径(图3)。针对乡村文化景观的空间特性,通过对已有的一些景观或资源分类与评估体系进行分析和总结,结合实地调研,根据研究对象实际的文化景观特征进行调整,将乡村物质要素层面的文化景观分为民居建筑、宗祠建筑、历史遗迹类、农业生产类和公共空间等5类。

图3 乡村文化景观格局优化路径Fig.3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3 乡村文化景观格局分析结果
3.1 文化景观格局指数
从村庄聚落层面(表2,图4)上显示,珪后村建筑密度较高,斑块数量较多,斑块功能单一,整体布局较为零散,景观破碎度高。从斑块密度来看,普通民居斑块密度为612.72个/hm2,文化景观中农业生产类景观斑块密度为3.063个/hm2,景观破碎化程度较高。现有的斑块功能较为单一重复,削弱了景观异质性,让游客和居民产生审美疲劳。珪后村廊道景观呈现主轴廊道占优势,主要以主聚落南两侧的G355国道及村落内交通干线组成,但景观连通性低。聚落层面上,珪后村景观蔓延度指数为60.24,连通度指数为0.35,表现出珪后村整体景观连通度指数较低,景观空间连通性较差。从景观斑块层面(表3)上显示,历史遗迹类景观的连通度为0.039,宗祠建筑景观连通度为0.047,文化景观的连通度处于较低水平。农田(40%)是珪后村的优势景观类型,绿地、水域等生态用地面积占比次之。聚落层面的IJI指数为81.73,处于较高水平,景观多样性较高。在景观斑块层面,河流景观斑块的散布与并列指数较低(6.45),空间分布明显不均。文化景观中,宗祠建筑及公共空间则拥有相对较高的散布与并列指数,空间分布较为均衡。

表2 珪后村聚落层面上的景观指数Tab.2 Cult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level index of Guihou Village

表3 珪后村斑块层面上的景观指数Tab.3 Landscape index at patch and type level of Guihou Village

图4 珪后村主聚落区景观破碎度分布Fig.4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 the main settlement area of Guihou Village
3.2 文化景观格局特征
3.2.1 斑块层面的特征
在斑块层面,文化景观斑块呈现较为破碎化和离散分布的格局。珪后村文化景观斑块在功能上存在单一重复的问题,多为民居建筑及宗祠建筑,且建筑外围多为硬质铺装的空地,绿化效果不佳(图5)。以公园绿地为主的公共空间占比较小,仅为0.5313,斑块密度为2.017个/hm2,破碎度较高,连通度指数仅有0.1905,难以满足居民日常交往活动需求的同时,生态性较为匮乏。
3.2.2 廊道层面的特征
珪后村文化景观的主轴廊道位于其核心保护区的南侧,是连接内外交通的重要廊道,其吸引力与活力明显高于内部景观斑块通道,形成主轴廊道突显,内部文化廊道断裂的格局(图6)。在珪后村现有的景观规划中,未能形成较合理的景观游线,以将不同功能的景观斑块紧密串联,增强景观廊道的连通性与延伸性。珪后村文化景观廊道存在较多断点,完整性与延伸性不足,不利于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图6 珪后村主轴廊道及内部廊道示例Fig.6 Example of main shaft corridor and internal corridor in Guihou Village
3.2.3 基质层面的特征
从珪后村主聚落景观的破碎度空间分布可以看出,核心保护区内破碎度较高,整体文化景观处于较高破碎化。文化景观破碎度过高,会降低景观的吸引力,不利于人流聚集,难以激发分区活力。而在文化景观类型分布上,核心保护区内部以传统文化景观如历史建筑、宗祠建筑为主,核心保护区以外新建地块则以现代文化景观如党建公园、法治文化公园等为主,同时,在新建的景观斑块中,存在大体量的现代景观地标小品(图7),相较于传统的历史遗迹等景观,缺乏地方文化特性,削弱了珪后村文化景观的辨识度。

图7 珪后村现代景观地标小品Fig.7 Guihou Village modern landscape landmark pieces
4 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
4.1 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目标
珪后村文化景观格局特征存在斑块功能单一,生态斑块匮乏;廊道主轴突显,文化廊道断裂;基质活力不足,分区特色缺失等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制定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乡村生态振兴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基础性作用[14],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发展趋势正在变得更加系统与综合,也更加关注人文主义在其中的表现[15]。在乡村文化景观的建设过程中,以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质”范式开展针对性的文化景观更新建设,基于景观格局分析的结果,寻找提高景观指数适应性的对应策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进而为乡村文化景观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实现渐进式的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
珪后村有着丰富多样的传统风俗,位于珪后村中心的普济岩供奉着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三位民族英雄,珪塘叶氏族亲们会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七至十八日齐聚于此,举行“三公下水操”纪念活动,至今已有700多年。每年在追远堂举行的元宵点灯活动,在2018年列入漳州市级非遗项目,是珪塘叶氏宗祠文化的重要展现载体。珪塘民俗文化节上演的芗剧、舞龙等,展现了独特而源远流长的闽南民俗文化,这些文化活动至今已达百年以上,历经岁月的洗礼愈加珍贵。因此,珪后村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包括4个方面,即延续传统风俗、传承宗族文化、保护传统古建和助力经济发展(图8),以实现文化景观的文化性、经济性和生态性的协调发展。

图8 珪后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目标Fig.8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Guihou Village
4.2 斑块层面:整合斑块提升景观整体性
整合和修补珪后村内部分体量微小且功能重复的景观斑块,强化斑块功能,实现文化景观斑块的内在提质和破碎度的改善,进而提升生态功能,以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图9)。对于珪后村主聚落区西侧的活动中心、篮球场、法制公园等公共空间,重点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增加居民交流活动的景观斑块,满足居民日常所需。通过整体设计将主聚落区内零散分布的宅间绿地合并串联,提升宅间绿地的美感度和村域特色。位于主聚落区中心位置的党建公园、健身广场以及古树保护区等公共绿化空间,以强化重要节点为手段,进行节点空间绿化的重点提升。

图9 珪后村文化景观斑块整合图Fig.9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patches in Guihou Village
4.3 廊道层面:修复廊道增强景观连通性
根据场地的立地条件和历史文化沿革,将珪后村人文空间的游线规划大致分为“珪后历史文化游线”和“珪后风土人情游线”(图10)。其中“珪后历史文化游线”位于核心保护区的西南面,主要有楼仔厝、普济岩、叶文龙故居、追远堂4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节点,建成时间的跨度从唐代到民国将近1 300年,可以从不同时期的建筑里领略年代独特的文化韵味。“珪后风土人情游线”位于核心保护区的东北面,主要有升厝、大学厝、下仔厝三个具有一定人文底蕴的节点,对其进行策略性塑造,构建完善的游线系统。这三处古厝各具特色,功能齐全,从居住到教学再到祭祀,可以从这条游线了解珪后村的风土人情。同时,在廊道规划设计中增加点状的休憩交流空间,丰富景观层次,搭配乡土植物,形成观景与生活相交织的廊道功能,满足居民和游客的不同需求。以廊道的修复串联不同的景观斑块,从而增强景观的连通性,实现珪后村文化空间生态廊道功能的提升。

图10 珪后村文化景观廊道修复Fig.10 Linear repair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Guihou Village
4.4 基质层面:优化分区提高景观多功能性
针对珪后村聚落内文化景观分散且发展水平不均的现状,从优化区域特色重点着手,挖掘不同分区的特色所在,塑造多景观功能分区(图11)。利用主聚落区北侧现有的乡情馆,打造文化展示功能区,同时完善区域解说、游览等配套设施。主聚落西侧整合公共空间及周边闲置用地,增设具有村域文化内涵的景观小品,提升景观特色感知度,打造居民休闲和活动的空间。主聚落区南侧作为对外展示的名片,进行功能性创新的文化景观提升,配建文化服务中心,引入VR、AR等新技术展现村域历史盛景。主聚落区西侧部分建筑单体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进行修复和改造,同时整治周边环境,引入现代休闲业态,提升片区发展活力。

图11 珪后村文化景观分区优化Fig.11 Optimiz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zoning in Guihou Village
5 讨论
5.1 景观指数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景观指数是将景观空间的结构与其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对应起来[16],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在土地利用变化、覆被变化及水土保持[10,17-19]、生态系统服务、景观生态评价、生态安全格局等方面[16,20-21]。近年来,也有学者将景观格局的变化引入文化景观的发展保护研究中[12,22-23],景观指数的发展呈现从自然景观生态领域向文化景观领域延伸的趋势。相关研究印证了景观指数法在文化景观研究中的适用性,提供了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24-25],启发了本研究“景观格局分析—景观规划设计”的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路径。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在珪后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建设中的研究表明,从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质”三个层面选取适宜的景观指数剖析乡村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总结和揭示乡村文化景观格局现存问题,由此提出相应的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目标及策略,对乡村文化景观格局优化及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2 “景观格局—景观设计”的设计策略
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景观设计,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相应的尝试,张志豪等[26]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设计”模式,从斑块、廊道、基质三个层面开展面向未来社区建设的景观更新设计方法的研究,为城市老旧小区空间优化提供了新的规划设计视角;傅伯杰等[27]提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应从景观格局延伸至生态系统过程和服务,深入理解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在生态系统管理及景观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证明,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能够科学有效地指导景观规划设计。因此,本研究基于景观指数分析,对乡村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进行量化研究,从“斑块—基质—廊道”层面开展文化景观针对性的景观设计,形成景观格局分析到景观规划设计的设计模式,将景观文化服务和自然生态相融合,探讨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这一研究模式为乡村文化景观的布局调整及优化设计提供一种新的尝试,同时延伸了景观生态学研究范式在乡村文化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5.3 生态振兴触发文化振兴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乡村的新征程。其中,生态振兴是根基,文化振兴是灵魂,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宜居的基底环境,也离不开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然环境破坏与资源消耗趋紧使众多乡村产业面临转型的考验[28]。生态失衡会导致乡村文化景观流失、变迁甚至消亡,因此,乡村文化景观应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本研究基于景观指数分析,深入剖析乡村文化景观格局基底,通过景观格局特征分析,明晰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乡村文化景观格局优化路径及可持续设计策略,以提升乡村文化景观生态功能,促进文化景观服务和自然生态相融合,进而触发生态振兴激发文化振兴,保障乡村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随着城乡统筹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景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和改变,因此,在乡村文化景观保护的进程中,传统的设计方法已难以适用乡村发展,结合乡村实际情况,适应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路径亟待开发。将景观指数分析方法用于乡村聚落文化景观评价和设计中,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景观指数用于解释乡村文化景观格局特征,结合不同层面景观指数的量化研究,明晰了珪后村乡村文化景观格局存在的斑块功能单一、文化廊道断裂、分区特色缺失等问题。进而运用“景观格局—景观设计”的景观指数化分析优化路径,基于“基质—廊道—斑块”研究范式,提出乡村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包括:(1)整合和修补功能重复的景观斑块,更新强化斑块功能,实现文化景观斑块的内在提质和破碎度的改善;(2)修复内部文化廊道,串联特色景观斑块,丰富景观游线,提升景观异质性及文化空间生态廊道功能;(3)优化区域特色重点,挖掘分区特色,塑造多景观功能分区。最终以乡村文化景观的可持续设计的方式呈现符合乡村特色的,生态友好的乡村文化空间新格局。这一分析方法和设计策略不仅适用于乡村文化景观格局优化,也对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为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研究提供了发展方向的参考。然而,乡村文化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趋势,文化景观建设中人的活动和需求,以及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提出后的落地实践等问题,仍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